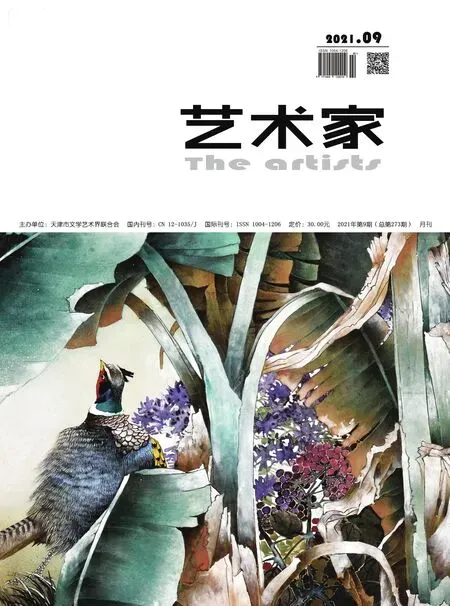與梅“形”自處詩舞
——評析古典舞《寒依疏影》
□張懷玲 福建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一、詩舞虛實的有形與無形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意思是將自己的內心情感或狀態用語言表達出來。這種語言文字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能引發人的感受或作用于人。詩中文字直觀表達是有形,文字的背后暗藏著無形。與舞蹈藝術相關的詩組詞,是詩歌。音樂、舞蹈、詩歌,從藝術的角度看,是藝術形態迥然不同的三個藝術門類。《禮記·樂記》記載:“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人體動作表現出來直觀的是有形,映射的則是無形[1]。在主觀和客觀來看,詩與舞蹈都是虛實相生相伴的化身,在虛實中不斷轉化,若把實實相結合必然是一潭死水,虛虛相結合則是無,而虛實結合則是意無窮的活水。
(一)文化詩作的境
“千百年來的詩人藝術家已經發現了不少,保藏在他們的作品里,千百年后的世界仍會有新的表現。”[1]筆者認為這就是文化,中國文化藝術必不可少的就是詩,詩對人們的生活是極為重要的。在古代,舞蹈的記錄也常常通過詩來體現,詩人當下的心境與環境等因素形成的詩,是一種記錄,一種藝術的二度創造,其經過幾番造境,能否升華,在于詩人的高超表達與處理情感的高明之處。蘇東坡詩云: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
例如,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在品詩時,我們就能感受到詩的境和意。我們從小習詩,在面對一些情與景時,腦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現許多詩句來表達此刻的心情。由此可見,文化詩作的境是“存在”的,這種“存在”不受時空的限制,是一種萬物皆在“我心”的境。
(二)古典舞蹈的境
古典舞的追求是在一個不斷創境的過程中,將行化神,這種追求如中國傳統文化一樣耐人尋味、綿綿不斷、其味無窮[2]。在古典舞的表達中,境是存在的。例如,佟睿睿的舞蹈作品《扇舞丹青》,以舞作畫,使用扇子做道具,融入中華民族書法藝術的形和神。舞者在表演時借用一把扇子,將中國古典舞的形神表達在身體創造的舞臺實境中。《扇舞丹青》舞蹈中所營造的境,是舞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描繪,仿佛一位畫家在書畫丹青,在古典舞韻律的融合下,舞蹈營造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意境。其中,舞蹈動作與道具的運用也使“文化”活了起來,使舞蹈達到景中生境、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
意境是“情”與“景”(意象)的結晶。舞者可以用肢體動作創造出不同的景來表述同一種“情”,也可以用一種“情”描述不同的景,在情景中生境。在舞蹈美學中,“情”與“境”是一對范疇,兩者是離不開的。清人布顏圖謂:“情景者,境界也。”王國維又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古典舞蹈通過肢體的表達將情感升華,令人感動,通過對情感的刻畫,在境的特殊造象中,“述說”著境中的另一番天地。
二、詩舞內外的詠詩賦形
人們常以“誦讀”的方式將詩的情感和意境展現出來,“詠詩”的方式是對詩的再次品味。每個人的誦讀方式不同,可以是心里默讀,也有直接用口表達出來。傳統模式下,我們常用詠詩,加之細細品析詩中字眼、音調、組合、整體等方式,層層加深對詩的理解和感悟。中國傳統文化中,詩中不乏描物,這些具體的形象是有形可循的,而其中表達的境是無形的,畫面感中有形中藏無形,由表及里。在藝術中,舞蹈是視聽綜合的直觀藝術,以情動人的藝術形式,通過人的肢體動作語言表達情感[2]。藝術來源于生活,形可以指具體形象,就如人們看到一首詩可以立刻在腦海中浮現出畫面,達到在詩中塑造形象,表達更深層次含義的目的。當舞蹈用肢體來表達時,舞者的身體反應是強烈的,是需要舞者用身體去塑形象,臨摹出舞蹈所需要表達的畫面的。比如,舞蹈作品《寒依疏影》中,舞者用一支梅花作為道具,并配合自身的肢體動作,對梅的形象進行刻畫。古典舞近年來大多都是舞人表情、舞物表意等,運用古史題材使“古典”氣息愈加濃烈。筆者認為這樣的古典舞蹈是值得研究的。從中國的審美標準來看,這樣的題材及古典舞的形式是對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重新賦予傳統一種形象,將“感同身受”再一次形象地表達出來,使古典舞蹈可以做到再一次藝術升華。
(一)詩中梅的描與賦
古往今來,不少人詠梅,但是高啟的《詠梅九首》有其獨到之處。詩中第一句就表示梅花來自仙界降于凡間,在平凡中自帶仙氣,縱然它們已降生到地上,卻終究是超凡出塵、氣質異于俗中眾花。第二句生動表現了梅的高潔精神,展現了梅的獨立而不驚,秀麗而不艷俗,襯托出梅花的不俗氣質和靈秀仙骨。第三句承上啟下,寫出了疏疏梅影與清寒依附著,梅花的報春是凋落之時,但上天愛惜美人,連人間默默無聞的青苔也為它垂憐,輕輕地掩蓋住它的香氣。梅花的所作所為是奉獻而不求回報的,以至于世間萬物對它溫柔。最后作者借抬高南朝詩人何遜的詠梅佳作而表現了他的自負,似乎只有他自己才是梅的知己。梅花花開花落,寂寞獨處于世間,若不是靈魂的惺惺相惜,高啟又能怎讀懂梅花,與梅花相依作伴。
(二)舞中梅的形與象
古有詠梅詩,今有詠梅舞。獨舞《寒依疏影》中,舞者用一支梅花做道具,將其“生長”在手臂之上,與身體融為一體,大膽而有趣地點明舞的是梅,表的是情,動作橫向性居多。其一,“橫向暗示”準確地體現了含蓄的情感特征,能把各種動作串聯在一起,使整個舞蹈貫穿含蓄的情感基調,繼承民族舞蹈的風格[3]。在《寒依疏影》舞蹈作品中,舞蹈的開始,舞者左右移動,在連貫舞蹈動作中加入定點造型,在定點造型中運用更多手臂動作,更好地在形態上塑造寒風中梅的形象。在開始部分,舞者將自身具象化為梅,其身體就如梅的枝干,手中梅花道具則是生長的梅花,再配合相應的舞蹈動作,將梅的形象表達得很靈動且不失穩重。其二,在高潮部分,舞者動作幅度加大,流動全場,拉大調度,動作由快變慢,由慢變快,來回切換,音樂節奏弱拍與重拍亦是如此,使梅在變化的環境中體現出處世不驚的品質。這部分表演很考驗舞者的基本功,是舞者基本舞蹈素養的體現,舞蹈中梅形象的塑造及編導想要營造的境也都在這個部分慢慢顯現,讓觀者在感受到梅的“心理活動”后,能聯想到梅的高貴品質,寓情于景 。舞蹈進入高潮即將結束時,舞者立半腳掌定點,一個回頭,展現梅的秀麗且不艷俗。舞者收放自如,在外柔內剛的古典舞韻律中將梅的美展現得淋漓盡致。其三,在高潮褪去的舞蹈動作與音樂中,舞者動作柔和,氣息變得輕緩,手輕撫道具梅花,不知是梅花對她的溫柔,還是她對梅花的溫柔,兩者融為一體,惺惺相惜,緩緩向后走收尾,此時舞臺的燈光轉至暗淡,就如詩中所說“月下美人歸”。“梅”這位美人好似在詩中悄無聲息地走了,卻深深地走進古典舞《寒依疏影》的形象與意象表達中。
(三)詩舞結合的梅之意象
詩與舞的結合是中國式審美的一種,藝術是情之深處的表達,是境的升華。自古以來不少人詠頌梅,但能達到其精神和靈魂的獨立境界的不多,詩人高啟則是其中一位。高啟的《詠梅九首》在藝術手法上是值得后人學習和思考的,給舞蹈創作提供了一個與文化結合的機會。高啟依于梅,舞依于詩,我們應拋開陳規的束縛,找尋靈魂的相伴相惜,將優秀的傳統文化繼承下來,而詩與舞把“文”與“藝”雙向結合起來,彰顯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結語
優秀傳統文化值得我們去學習與發揚,這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它與其他藝術形式在求同存異中發揮了各自的藝術特色,就像詩與舞蹈的融合,是發展中的產物,兩者有自己的獨特風格,融合在一起又能展現整個中華文化的共性。因此,我們應在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深度挖掘更多內容,為舞蹈藝術找尋更多的可能性及文化發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