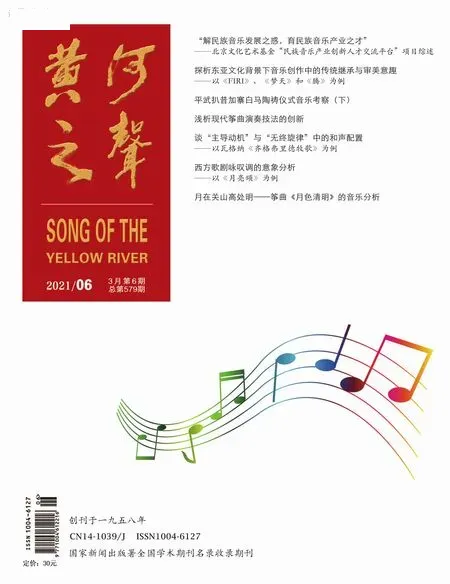中華傳統器樂美育的學術品格研究
劉 劍
中華傳統器樂美育,以其“雅正無邪”、“志存經世”、“得窺天地堂奧”之弦上“二十四”清雅況味[1],培養人的信仰、情懷、擔當和想象、創造、境界,培養人與天地往還的廣博之愛,與時代共呼吸的進步之責,將道德、智慧、知識化為涓涓清流,激勵人們傳承美育文化,創造美好未來生活。提升中華傳統器樂美育的研究水平,淬煉其學術品格,是做好美育工作的殊上方略。
一、建構“天人之學”的學科體系
傳統器樂的美學品格,是在儒道佛思想的涵泳和古代科技工藝的“匠心”中逐漸形成的,體現了不同樂器類別中的人文意象質地和美學表現技藝,它是藝術審美品質的文化自覺和美學生命。器樂美育正是基于這種幾千年形成的中華器樂美學精神,對人的生命歷程具有潤物細無聲般的化育培元功能,屬于對人的本體層面的生命意識、生命價值、生命意義的教育。
傳統器樂的時代性人文價值和科學性技藝品質,是中國傳統器樂在歷史時空中,己淬煉成就的既精微又自圓的美育文化基因“天人之學”[2]的致用,即“天人和諧”、“天人合一”、“尚正取中”、“和而不同”的美學品格,是將真善融入美的形式,美成為天人知性與道德的中介,成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中國人文學科奇葩。天人之學的“天”,概指宇宙、天地、自然萬物,泛指自然演化的客觀規律;天人之學的“人”,指涉人類社會歷史過程中的人性、人生、自我等,以人的解放超越和自由全面發展為理論旨歸。中國5000年文明史傳承的天人之學,歷代思想家們的闡釋都涉及其世界觀、方法論、人性論、社會觀、歷史觀等,而文學與藝術,更是深得天人之學的文化滋養。雖然天人之學歷史上出現過牽強附會的“天人感應”說和“天人混沌”說,這種或神學迷信,或邏輯邊界不清,阻礙了科技理性和邏輯思維的獨立發展,但古代的思想家們通過不斷摒棄校正,仍不失其人文性與科學性的思想光輝。
先說時代性人文價值。任何藝術作品都必然地要回答時代之問,這是藝術的生命。音樂藝術的“當機而發,即身而沒”的時空瞬間性、模糊性、多義性、延伸性等生發特征,使其審美的時代性意蘊,深深地打上了“妙通萬象”的“共同意象”和“仁智自見”的即時性,一方面打破了物理時空的局限,一方面又必然地“無數妙境宛然現于目前”,這正是杰出作品成為經典永流傳的內在原因。如琵琶舞曲《十面埋伏》、《霸王別姬》的英雄浩氣,成為千古流傳的陽剛審美標志;《昭君出塞》、《塞上曲》的家國情懷,成為中華民族永恒的審美意象;《潯陽琵琶》、《春江花月夜》的古代商道敘事,成為今天“一帶一路”的精神傳承,等等,這種經過洗練概括、取舍重組、以意立象、以聲寫神的特征,是傳統器樂時代性人文價值的審美生命之所在,它或格調和靜清遠,古澹恬逸;或指法潔潤圓堅,溜健柔剛;或樂曲宏細輕重,遲速陰陽。它是精神的、致遠的、意象的、描述的,是充溢著更多的個人情感的可游、可觀、可訴的意境。
再說科學性技藝品質。傳統器樂的科技品質,是貫穿于工匠精神中的縝密態度及其巧思妙想的創造,從大量的歷史典籍和考古發現中得知,中華器樂的科技品質,主要表現在對樂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風”“八音”的材質、結構、音響的考量;對“五聲”音階中宮、商、角、徵、羽和諧成律的研究;對琴、弦、弓、索、孔、口的練制技巧;對金、木、水、火、土“五常”相生相克樂理機制的辯證;對陰、陽、剛、柔四氣升降沉浮的體驗;對吹、拉、彈、打演奏技巧蘊含的力學智慧和藝術創新,等等。這種藝道的精妙把握與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造物技巧,達到了“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返璞歸真境界,使中國傳統器樂“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樂者法天地四時而成韻律節奏。人的心靈體會、想象、創造,是如此的理性和愜意,如此的天人交合而又相分多彩,這是知識和智性、規則和法度的隱形表達,是人文與理性二者價值力量之間相互作用的發生機制。傳統器樂文化品質的研究,跨越人文和科學的體系,特別是新時代大數據智能科技、腦成像電信號的采集分析,幫助我們打開大腦里的“黑箱子”靈魂奧秘,計算樂器音質音色音韻的物理量化,將為器樂的美學分析盡可能提供更為科學的、實證的數據模型。
不難看出,中國器樂美育學科不僅傳授藝術帶來的審美情感,而且蘊含深厚濃郁的家國情懷、自然情趣、社會理性、道德精神和科學奧秘、工藝技術、智性知識、法度規則等美育學科內涵和架構。近現代以來,傳統器樂文化隨著中國美育的內涵而發展變遷,自強調對國民性之改造與國家之自新圖強,到提升國民文明程度,振奮民族精神,再到新時代的無限潛力的夢想激發,等等,使藝術美育的地位愈發突出,功能更加彰顯,影響日益深廣。藝術與審美都是人類生命靈魂和精神境界自由的表現,但通識藝術美育學科不同于藝術專業教育學科,前者是指人人可共享側重于人文素養的通識教育,而后者是指以藝術為專門技能和職業的教育,然二者的人文功能是重合的,要通過多學科的交叉、整合、融合,建構門類齊全、藝哲融通的美育學科集群平臺,使美育學科名符其實地成為人類學習知識、提升境界的制度安排,具有明確的研究對象、獨特的概念體系,清晰的知識規訓,進而展開器樂美育學科的知識生產和學術創建。
二、創新“中國樂派”的話語方式
中華器樂藝術文化,是具有鮮明的儒道佛文化基因,具有傳統農業文明的自然意蘊式樂器形制和音樂節律及其經典作品、經典理論,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風”“八音”,概括了中華傳統器樂的風格和品類,且從價值體系到表現技術都有鮮明的取向和方式。這里的話語方式,是指中華器樂文化自信自強自覺發展背后的原理、學理、哲理,為世界藝術界貢獻學術新知、中國樂論、中國經典、中國智慧,在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通過批判反思的器樂文化自覺,揭示中華傳統器樂文化殊勝的理論邏輯和經典器樂作品意蘊,進而開闊世界視野,站上國際舞臺,創造具有鮮明華夏民族特色的兼收并蓄包容互鑒的中國樂派理論,這應是我們新時代文化強國的一個重大使命。
比較中西器樂文化的差異,正是為了在人類共同共通的生命情緒銓釋基礎上,根據中西歷史發展、經濟基礎、民族信仰、文化基因等殊異性,能夠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中西器樂文化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美學價值選擇上,中國器樂文化是在偏重于人文價值基礎上的道藝合一性價值取向,而西方器樂文化是偏重于科學理性基礎上的藝道二元性價值取向;二是從審美思維方法上,中國器樂文化是一種從人與世界的關系出發的自我心性、智性、靈性、悟性為生命旨歸的理解,而西方器樂文化是一種從實體世界出發的在人的科學認知范式下的以形式美、藝術美為主要目標的感悟理解。從西方音樂史的大量史料數據中可以看到,西方器樂表現形式豐富,僅體裁類別就可分為結構形式的舞曲、進行曲、前奏曲、幻想曲、即興曲、序曲、組曲、奏鳴曲、交響曲、圓舞曲等,雖其內容、風格,演奏形式不同,但都特別追求結構、曲式、技巧等形式唯美要素。比如,貝多芬的《C小調第五交響曲》[3],因其第一樂章主題那蜚聲于世的四個強音符振撼力,被貝多芬形容為“命運的敲門聲”,因此人們又將這首曲子稱之為《命運交響曲》。在這部不過30分鐘的曲子里,貝多芬通過四個樂章的音樂演繹,把對命運的反省、追問、奮搏乃至把握的哲思,凝練為“命運的敲門聲”、“扼住命運的咽喉”、“英雄交響曲”的音樂意象,百年來醫治了多少流血的心靈,皈依了多少彷徨的游魂,又使更多的人心靈得到凈化和升華,為人類世界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精神豐碑。
中國傳統器樂以禮樂文明教化為圭臬,在儒道佛文化的涵泳中,強調:“樂者,德之華也”,認為“審音而知樂,審樂而知政”。其作品也多以文學性的標題和序語,強調其教化意蘊和心性悟得,使樂曲的真善美高度融合為一。比如,由古曲《潯陽琵琶》、《夕陽簫鼓》等曲目整理創作的民樂絲竹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分別以詩的語言“江樓鐘鼓”、“月上東山”、“風回曲水”、“花影層疊”、“水云深際”、“漁歌唱晚”、“回瀾拍岸”、“橈鳴遠瀨”、“欸乃歸舟”、“尾聲”共10個小標題展開樂思,呈現江南絲竹音樂清秀細膩的特色。樂曲通過優美柔婉的旋律、豐富巧妙的配器和具有展衍性的變奏曲結構,形象地描繪月夜春江不僅景色迷人,而且可以盡情想象白居易《琵琶行》里絲綢水路上的商賈官人、匹夫販婦、走卒船工等三教九流和琵琶幽思、江州司馬的長卷史詩。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是中國傳統中的藝術功能,用當代的話說,就是要五感齊發,身心開啟,標題是什么,形式如何表現,此時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音樂所激發的人對事物的感覺、對世界的經驗、對他人的理解、對生命的態度。
三、打造數智平臺的集群資源
中華器樂藝術美育有著豐厚的文化資源,是華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寶庫,承載著祖先的精神、智慧、價值、信仰和精微而自圓的器樂知識認知范式。建構獨樹一幟的中華器樂美育愿景,就是要揭示其起源和發生的條件、基礎、機制、過程及其學科框架,形成體系嚴謹、定位精準、邊界清晰、人文精神濃郁、藝匠品質優秀的學科課程體系,把美育落實到課程建設開發上。因此,打造數智化課程資源的集群平臺,是提升器樂美育學術品格的重要手段,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一是要提升對傳統音樂文化基因的萃取能力和創新銓釋能力,從禮樂文明的歷代音樂典籍和樂器考古遺存中,確認中國樂派的美學特質,建立殊勝的銓釋邊界,顯示中華器樂的獨立性和主體性,使我們不僅能夠聽到千年的遺音,看到遠古的舞韻,感悟歷史遂道中的理性智慧,更要開創一種新時代、新場域、新受眾、新方法的全新表達和話語體系;二是要充分認識中華器樂是世界音樂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建構特色鮮明的中國音樂文化,就要立足于全球視野,增強我們的國際話語權,研究中國音樂的國際表達,借鑒吸收其它民族先進文化的精華,創造中西互鑒、平等交流的傳統音樂文化發展契機,讓我們的美育課程資源,為世界貢獻中國美育智慧、美育精神、美育力量;三是要順應國家教育部提出的“新文科建設”和“新時代藝術美育工作意見”的要求部署,在學科的論域拓展、價值重塑、科類融合、研究范式和美育教學平臺建設、課程集群優化等方面,彰顯中國器樂的人文心性和科學理性的音樂美學美育質地,使華夏器樂文化在“載道”、“體用”、“質性”上,真正筑牢其人文價值與科學理性的美育建構愿景;四是要打造優質精品課程,形成課程標準、課程教材、課程資料、課程模式、課程團隊、課程評價等方面構成的科學體系,并堅持不懈對課程進行優化和更新,使課程資源平臺成為錘煉優質精品課的學術高地,成為MOOC(慕課)、網絡直播、QQ群答疑互動等數智化教學改革的前沿陣地,為器樂美育獨特的浸潤、熏陶、感染、共情、喚醒、激發的課程思政和創新創造功能發揮重要作用。比如,我在主持獲獎的2019年山西省教學成果大賽二等獎《中國器樂的美育追求》作品建設打造中,就探索出了“以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為人文教化目標——以學生的想象創造能力培養為理性目標——以不同專業班級教學背景為美育課程切入點——以數智化為課程研究和教學手段——以師生教學資源的平等共建、互享相長為教學模式”的課程建設路徑,為傳統器樂的學術研究和教學資源開發,提供了大量真實可靠的數據。
四、豐富學術質性的研究范式
提升中華傳統器樂美育的學術質性,就必須在豐富器樂美育的學術研究范式上做足文章。學術及學術質性,前者強調其學問、成果、理論和方法,后者是其研究的內涵、屬性、精神、品格等,是形上層面。范式是學術研究的規制、方法、整合的手段。器樂美育的學術質性特征,可概括為藝術性、學科性、教育性和范式性,而范式性是它的生命之本、精神之魂、品格之境,因為,它是求真理、求創造的思維方法和理性“工具”,并飽含著感情、理性、視野、境界、修養、人格等,都“大象無形”地滲透于美育文本、美育課堂、美育實踐等范式規制之中,構成了一種情理交融、意象相合的理性世界。概括器樂美育豐富的研究范式,可歸納為:交叉融合范式、學理思辨范式、作品實證范式、數據量化范式、數智推演范式等。不同的研究范式,是基于的學科、理論、方法的不同而展開的學術研究,其學問或成果又不斷地推動著知識的更新、生產和傳播,造福人類社會。器樂美育的學術研究范式,是學者和教師治學的科學態度和基本價值觀的蘊含,而市場化的社會又復雜地異化了學術,違背了學術精神和學術規則,嚴重危及學術事業的生命,我們必須予以警惕,要心懷敬畏之心。
器樂美育的研究范式應用,要根據課題性質和問題導向,可綜合使用,可單獨進路。這里,我們通過對劉天華創作于30年代的二胡獨奏曲《光明行》[4]的作品實證分析,以期揭示這部作品的人之本、藝之體、育之用的學術質性。《光明行》吸收多民族豐富的演奏技法和表現風格,集各民族音樂藝術之大成,使樂曲旋律鏗鏘有力,氣勢雄壯豪邁,富于激情,滿載覺醒時代熱烈喧鬧的氣息,表達了知識分子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和變革現實的抱負理想,以及不怕挫折失敗,堅持探索光明和進步出路的信念和意志。全曲為多段體(引子、四個樂段和尾聲)結構,又結合循環變奏和復三部曲式的特點,采用頓弓、跳弓以模擬軍鼓敲擊,威武雄壯,分弓以顯示寬闊有力,顫弓抖弓演奏以展示意境壯闊,內外弦交替演奏以顯示深沉而不屈,三和弦分解式旋律以顯示向上熱情和進取力量等,這些三部曲式、豐富技法、循環變奏、同音重復、激情揉弦、玄妙滑音、三和弦分解旋律,融合了民族大家庭中不同的風格、演技的藝術再創造,都使樂曲生氣勃勃,樂思動人,意象光明,藝術是一種解放身心的力量,是喚醒包括人文與科技等一切創造力量的源頭,是各民族音樂文化的共性基因。不同的器樂藝術雖形式多樣,風格迥異,但其學術的質性分析一定要守正,突顯內在的、內涵的思想性和價值性,通過對作品的穿透式分析和整體性探究,對其獲得意義和建構上的解釋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對象的本質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