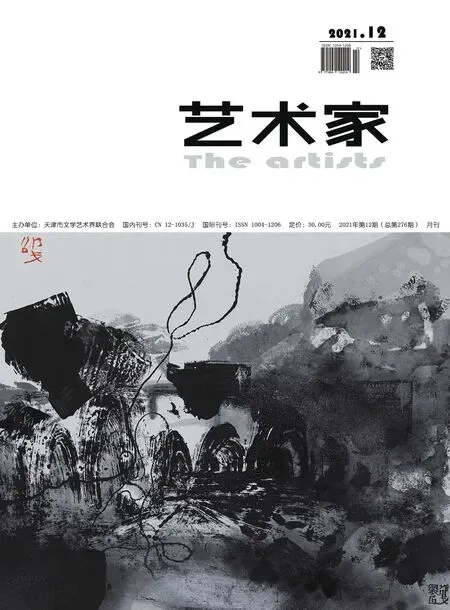舞蹈與雜技藝術特征的比較
□肖 瑤 福建師范大學
在漫長的藝術史發展長河中,舞蹈與雜技是最為親密的“姊妹”藝術。從漢代“百戲”藝術興起開始,舞蹈藝術與雜技藝術同臺演出,也是從這時開始互相融合借鑒,取長補短。從古至今,無論是在舞蹈表演中,還是雜技表演中都不難見到“舞技不分”的現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它們二者有著相同的藝術媒介——都是以人的身體作為物質載體。但在現代社會中二者又漸漸形成了分野,發展為兩個獨立的藝術種類。這便可說明二者具備足以彼此區分的個性。本文將對舞蹈和雜技在表現手段、藝術形象、表演目的以及道具使用方面所具備的差異性來論述二者獨特的藝術個性。
舞蹈與雜技這兩種藝術形式從它們發展以來就一直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二者長期以來界限模糊的歷史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上古時期的樂舞“舞武不分”,從手執干戚的“干戚舞”到發揚蹈厲的“大武”都是非常鮮明的例子。始于春秋時期,成熟于漢代的“百戲”藝術,使舞蹈與雜技的融合達到了一個高峰。我國傳統舞蹈最獨特的色彩之一就是糅合了武術和雜技兩大因素,這與西漢時期的“百戲”的表演形式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從這時開始,許多雜技中的特有動作,如折腰、倒立、騰跳、翻滾等高難度動作都被傳統舞蹈吸收,發展成舞蹈的語言。這樣的結合可以在擴大舞蹈表現力的同時使舞蹈藝人的專業技巧得到提高。在現代的藝術創作中,舞蹈與雜技仍然延續了相互交融、相互吸收這一特征,中國古典舞對高難度動作的追求,借助雜技的技術來增強舞蹈表演的觀賞性;雜技表演對審美性的追求,借助舞蹈的特長來增強雜技表演的寓意性,使其藝術感染力進一步得到深化等。如此長時間的相互交融必然難以區分。但是事實上,任何一門學科,任何藝術與藝術之間都存在共性,都會有互相重合的“模糊地帶”。舞蹈與雜技也是因為它們有著相同的物質載體和表現手段,本質上的共性自然構成了在藝術創作中的相互借鑒。但是在藝術發展的長河中,舞蹈與雜技最終形成了概念上的分野,成為兩個不同的藝術種類,這也就說明了二者間還是存在能夠予以分辨的邊界。
一、舞蹈與雜技的表現手段
舞蹈與雜技都是通過演員的肢體動作以及在舞臺上的空間變化流動進行藝術表現,它們有著相同的物質載體——人的身體。從藝術的展示和存在方式來看,舞蹈與雜技都是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通過動作的變化來進行藝術表現的。因此從時、空、力這三大要素來說,無疑,舞蹈和雜技是共通的。因此對于同屬人體動作藝術的舞蹈和雜技來說,它們的主要表現手段毋庸置疑都是人體動作——在人的身體能承受、能達到的范圍內試驗創造出來的動作。
俄羅斯著名芭蕾編導福金曾說:“舞者們追求的不是肌肉的力量而是純潔的詩意。”因此,就舞蹈動作而言,通常是要能夠表現一定的思想感情或者敘述一定程度的事件內容,同時也對舞蹈動作提出了要在一般人體動作的基礎上具有一定抽象寓意色彩的要求,它要具備抒情或敘事的能力。舞蹈動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能夠描繪人物情感、思想和性格特征的表情性動作,第二類是展示人物行動的目的和具體內容的說明性動作,第三類是沒有明顯含義主要起裝飾和襯托作用的連接性動作。這三類動作,既有與生活動作相聯系的簡單動作,如“回頭”“伸手”等,也有經過演員反復訓練才能掌握的高難度技巧動作,如“探海”“云里”等。但無論以上哪種動作,都只是作為外在形式呈現,以飽滿的情感為其內核,是一種用來表現人物思想感情、塑造人物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的一種表現手段。在動作的基礎上,舞蹈演員的面部表情也成為表現手段之一。單純靠動作在實際的表現過程中可能會表現不徹底,因此就有了對舞蹈演員表情豐富的要求,無論是在舞蹈訓練還是舞蹈表演的過程,舞蹈演員的表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劇中人物塑造的需要,隨著情節事件、人物心理甚至是音樂的發展在不斷變化著的。
就雜技表演來說對動作的選擇與應用并不同于舞蹈。“東方人體文化研究體系”創建者劉峻驤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國雜技史》中提出雜技審美的基本要素講究的是“險、難、奇、謔”“它的許多節目從道具動作開始的鋪墊,都要向險的峰境推進……險中求穩,舉重若輕成為雜技藝術重要的審美原則”“‘難’是雜技審美的核心、‘奇’是雜技審美的重要元素、‘謔’或幽默美是雜技藝術的重要審美原則”。實際上,我們在欣賞的過程中也常常會驚嘆,并對雜技演員高難度動作的呈現贊嘆不已。這些在表演過程中展現出來的一般人難以達到的技藝便是雜技最重要的表達手段。它并不旨在抒情敘事,因此在選擇動作時就更加偏向于那些難度極大的動作。它將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動作作為表演內容,因此雜技的表現手段就要求演員能夠運用自己的身體做出一種極限性的且常人難以做到的動作。再加上在雜技表演的整個過程中都是追求險中求穩、動中求靜。因此雜技演員的面部表情和細節處理不如舞蹈表演豐富,因為演員需要身心達到集中收緊的狀態,才能確保演出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二、舞蹈與雜技的藝術形象
作為表演藝術范疇的舞蹈與雜技,都需要在創作過程中選定一個特定的藝術形象,這個形象可模糊、可具體,范圍也可大可小。舞蹈與雜技都源于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的產物,二者在創作過程中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最終塑造的藝術形象還是存在較大差異的。
舞蹈創作時主要是以社會生活為原型,舞蹈作品的主要表現對象是社會生活。編導在生活中遇到的令人感動、深有感觸的人,都會成為舞蹈直接或間接表現的內容。通過塑造鮮明人物性格的藝術形象來表現社會生活,表達作者對生活的審美與理想愿望。除此以外,物也是舞蹈作品進行藝術表現的對象。我國民族藝術的“緣物寄情、托物言志”表現手法被舞蹈編導們很好地進行了沿用。借著對動植物、客觀景物的描寫與表現,來抒發藝術家個人的情感和愿望。雖然是以物為對象,但其內核仍然是情感,具有深刻的內涵。總而言之,舞蹈是借助人體動作的發展變化來表達一部舞蹈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著重描述其他藝術形式難以表現的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細膩的情感、深刻的思想、鮮明的性格以及社會生活的矛盾沖突中人的情感。通過創造出可被人具體感知的、生動的舞蹈形象,能夠表達作者——舞者的審美情感、審美理想,反映社會生活的審美屬性。
與舞蹈相比,雜技的藝術形象更加精練集中。它并不像舞蹈那么具體,不以塑造具有具體情感內涵內核的人物形象,承擔過多的情感內涵和反映復雜的社會生活為目的。盡管同為一種表演藝術,而且演員在表演過程中也會塑造角色、有一定的表情達意。但整體上,與舞蹈傳達出來的有各種情感和性格特征的生動、具體的形象不同,雜技呈現出來的人物形象是概括性的,具有堅強、勇敢的內在品質。
三、舞蹈與雜技的表演目的
聞一多先生在《說舞》中曾說:“舞是生命情調最直接,最實質,最強求,最尖銳,最單純而又最充足的表現。”這句話說明了舞蹈與人的生命、情感存在聯系,并且是其他藝術形式不能比的最為緊密的聯系。舞蹈是與人的生命、性情聯系最為緊密的藝術,也是最能夠充分表達人的情感的藝術。舞蹈通過人體動作來表達那些矛盾復雜的情感并給予其一定的表現形式。當然,在舞蹈作品中也不少見一些高難度的技巧動作和驚人的柔韌性動作,如“虎跳”“毽子拉拉提”等,優秀演員的必經之路就是對身體技能的開發。但是這些在舞蹈中始終都是為了表演,技術在舞蹈中是情感的外化、延伸;而思想感情、情緒則是技術的內在含義。在舞蹈作品中,高難度技巧動作設計與編排都是為了服務于內容,通過技巧展現人物特定的心境、精神狀態和思想感情,始終以圓滿地塑造某一人物形象和營造某種藝術氛圍為目標,為最終追求。舞蹈演員超人的肢體把握能力、肌肉控制能力也都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完成對舞蹈作品藝術形象的塑造。
呂藝生先生曾說:“雜技并不著意表現人的情感,而只是通過令人贊佩的技藝,觀照人自身的勇敢與極致的美,觀照人所具有的無限的生命力和能量。”因此對于雜技來說,表達復雜情感并不是它的藝術特長,它的表演目的就在于將自己的最高力量完整地呈現在舞臺上,在整個呈現過程中展現他最為極致的勇敢、耐力,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人體具有的生命力與無限潛力。雜技表演激發了人體內在所具有的無限潛力,通過挖掘潛力和呈現技藝使人受到鼓舞,并帶來強烈的視覺體驗。但是這種視覺體驗終究是直線型、單純型、概括性的情感,所以它往往并不會觸及觀者的內心深處,也無法引導人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或許與舞蹈相比較而言,雜技才是更為純粹的“直觀藝術”。
四、舞蹈與雜技的道具使用
舞蹈與雜技都屬于對道具有熟練使用技能的藝術。對于雜技與舞蹈來說,道具使用的差異體現在各自承擔的功能作用不一樣上。
在舞蹈中,道具一般帶有一定的指向性。恰如其分地道具使用,既能準確地體現舞蹈作品的風格,又能體現舞蹈作品特定的環境,但最重要的是,它是演員用來“說話”的工具:它解決了舞蹈肌體語言敘述時面臨的局限性問題。道具在舞蹈中的巧妙運用不僅可以提升肌體語言的表現力,還能為舞蹈營造出一個較為具體的意象與意境。例如宋代的《采蓮舞》,蓮花式樣的頭飾以及舞蹈時的蓮花底座的運用,不僅體現出宋代人極愛簪花的風俗習慣,還通過仙女下凡采摘蓮花體現出一種無拘無束的人生態度。在這個作品中鮮明地體現出道具“蓮花”所發揮的敘事性作用,是幫助舞蹈完整表達感情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道具的使用也是雜技表演過程中不能缺少的重要元素。高空雜技的空中舞獅、高空走索等,器械雜技一類的鉆壇子、鉆木桶等,在表演過程中無一不需要借助道具的輔助來完整呈現。在雜技表演中運用道具首先是保證雜技表演自身的完整性,其次是通過道具增加表演的驚險性與觀賞性。盛行于漢代民間的“胸突铦峰”就是類似于今天的“上刀山”,用刀子扎成階梯,藝人赤腳踩著刀刃上到最高處,以胸腹抵在刀尖上,四肢懸空而臥。可想而知,演員在表演時的每一步都是扣人心弦的,也足以體現其驚險性。
作為同屬于人體藝術的舞蹈與雜技來說,本質上的共性使其相互交融發展,這也是它們能夠進行融合的基礎。但在藝術特征上的差異又使它們各具特色。舞蹈藝術追求的是表現矛盾與復雜的內心獨白,社會生活中那些令人深思的現象也是它所追求和所能表現的。在完美地完成這些藝術任務的同時,舞蹈還能夠直入人的內心深處,帶給觀者強烈的情感體驗。而雜技所追求的極致的高難度動作,在特定的藝術空間完成好自己的本體任務,使其在自身的發展道路上堅定不移地前進。
舞蹈離不開技術,技術是舞蹈表現手段之一,而隨著現代雜技藝術的進一步發展,對其藝術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現代雜技藝術中融入舞蹈元素,不僅是繼承傳統的表現,同時也可以提高其藝術表現力,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