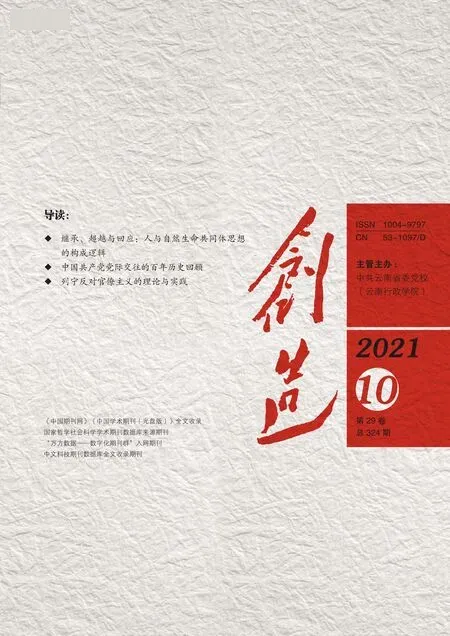云南易地扶貧集中安置點面臨的變更風險及其治理
蔣 健
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奮斗的歷史,是一部不斷帶領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歷史。建黨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對世界、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政治承諾,隨著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困擾中國人民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從此成為歷史。在這場黨帶領人民脫貧攻堅的偉大戰(zhàn)役中,全國共有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其中有960萬農村貧困人口通過易地搬遷擺脫貧困,解決了“一方水土養(yǎng)不活一方人”的困境,云南就有150萬人(包括99.6117萬建檔立卡戶),他們有的就地后移,有的離開世居的農村進入城市,成為新市民。這些環(huán)境、生活、身份等的變更,既為搬遷群眾后續(xù)過上美好生活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讓搬遷群眾后續(xù)能否穩(wěn)得住、能否適應新環(huán)境新生活面臨各種風險考驗。本文主要就云南19個萬人以上城市化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面臨的變更風險及其治理進行分析。
一、云南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的基本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云南的歷史發(fā)展中,發(fā)生過兩次重大的社會形態(tài)變遷。第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11個少數民族一步跨千年,直接從原始社會形態(tài)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次是今天在黨的領導下,近100萬農村貧困人口直接從農村進入城鎮(zhèn),由農民變成市民,實現農村貧困人口的社會發(fā)展大跨越,一步跨進小康社會。
(一)易地扶貧移民集中安置基本情況
云南是全國重點易地扶貧搬遷省份之一,搬遷農村人口多達150萬,占全國近1/6,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有99.6117萬人,約占全國搬遷總人口的10.4%,居第三位;全省共建設集中安置點2832個、安置房24.46萬套,其中800~3000人的大型安置點有139個,3000~10000人的特大型安置點有14個,10000人以上的超大型安置點有19個,居全國第一。①數據來自調研材料。這些集中安置點,除昭陽區(qū)的靖安易地扶貧安置點屬于新建城鎮(zhèn)外,其余主要位于縣城周邊,同原有城鎮(zhèn)融為一體,推進了當地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
這些安置點,從安置類型來看,有城市化集中安置、鄉(xiāng)鎮(zhèn)集鎮(zhèn)集中安置和農村集中安置三類;從搬遷安置移民來源來看,有跨縣域集中安置(如昭陽區(qū)靖安新區(qū)移民來自6個縣、魯甸卯家灣片區(qū)移民來自5個縣)、跨鄉(xiāng)鎮(zhèn)集中安置(如會澤縣城集中安置點移民涉及本縣22個鄉(xiāng)鎮(zhèn))、本鄉(xiāng)鎮(zhèn)集中安置和本行政村集中安置四類;從安置點管理機構及區(qū)劃設置來看,有新設行政區(qū)劃組建新的管理機構的(如會澤在移民安置點新設兩個街道辦事處、7個社區(qū))、有組建臨時管理機構代為管理的(如昭陽區(qū)靖安易地扶貧安置移民新區(qū))、有直接劃歸原有行政區(qū)劃機構管理的、也有未改變原有管理機構的幾類。
目前,在各級黨委、政府努力下,搬遷群眾已入住新的居住地,開啟新的生活,除位于昭陽區(qū)的靖安扶貧安置新區(qū)外,其余所有安置點都并入或者設立新的實體性區(qū)劃及機構進行管理。為讓搬遷群眾在搬得出的基礎上實現穩(wěn)得住、能致富,云南省于2020年3月印發(fā)了《云南省異地扶貧搬遷“穩(wěn)得住”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從11個方面明確了未來五年的40項“穩(wěn)得住”工作任務,并將每一項任務落實到具體責任部門。
(二)易地扶貧移民集中安置點的特殊性分析
通過對這19個萬人以上超大型易地扶貧集中安置點的調查,發(fā)現這些新建的扶貧移民安置社區(qū)具有不同于原有社區(qū)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既為做好新社區(qū)后續(xù)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也使新社區(qū)存在或面臨一些與老社區(qū)不一樣的風險。
1.社區(qū)成員同質性強。具體表現為社區(qū)成員身份同質、收入同質和需求同質三個方面。從身份同質來看,這些社區(qū)的成員都是由農民身份轉變而來的新市民,絕大多數屬于建檔立卡貧困戶,只有少部分是隨遷戶。從收入同質來看,涉及收入低與收入來源少兩個方面,屬于剛擺脫貧困的低收入群體,他們進入新社區(qū)后的收入來源主要為打工收入,包括為居住地附近的種植業(yè)打工、扶貧車間打工,還有一部分外出務工,其收入大多數僅能解決最基本的城市生活需要,由于收入來源少,不少50歲左右的移民找不到活干,處于賦閑狀態(tài)。從需求同質來看,普遍渴望就業(yè)和有活干,這些進入城市生活的新市民目前最關心或者最擔憂的就是未來的生存發(fā)展問題,普遍感覺在這里生活不像在遷出地,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要花錢,而收入來源又非常有限,擔心一旦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來源生活怎么辦。這些同質性猶如一柄雙刃劍,一方面,易于管理者找到社區(qū)群眾的共同需求,有利于促進社區(qū)的管理;另一方面,也蘊藏著社會不穩(wěn)定風險,一旦他們的需求得不到實現或者面臨需求滿足危機時,這些同質性的社區(qū)成員就會產生共同訴求,形成訴求壓力,導致風險升級,甚至演變成群體一致的社會行動,對社會及管理者造成巨大的發(fā)展與維穩(wěn)壓力。
2.產、區(qū)融合。在原有城市社區(qū)中,社區(qū)居民生產工作地同其居住地是不統一規(guī)劃考慮的,很少有兩者在一起的,尤其是這些城市社區(qū)居民基本都不從事種植養(yǎng)殖業(yè)。扶貧搬遷移民安置區(qū)為解決安置點移民的生計問題,使其盡快適應新環(huán)境、新生活,多考慮讓其就近就業(yè),當地黨委、政府均在這些超大型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及其附近規(guī)劃建立了種植養(yǎng)殖業(yè)基地和扶貧車間,通過吸引企業(yè)進駐或由企業(yè)發(fā)展種植養(yǎng)殖業(yè)來解決搬遷群眾的就近就業(yè)問題,從而形成了安置點生產工作地與移民居住區(qū)在一起的“產”在“區(qū)”邊的“產、區(qū)”融合規(guī)劃建設發(fā)展特色。
3.戶、居分離。據調查,搬遷群眾由于對扶貧搬遷安置政策不了解、不信任,擔心遷戶會導致附著在原有搬出地戶籍及農村戶籍上的待遇與利益會隨著農村戶籍轉變?yōu)榘崛氲爻擎?zhèn)居民戶籍而被取消,多采取觀望態(tài)度,不愿遷戶,致使絕大多數搬遷戶戶口與居住地分離。現行政策對搬遷戶的戶籍遷移也是采取動員、自愿而不是強制的態(tài)度,如《方案》規(guī)定的“群眾搬遷后原戶籍地址實際不存在的,原則上應將戶口遷移至新居住地”,僅是針對原戶籍地址已經不存在的要遷移至新地址,而且是原則上而不是必須遷,其余的則是由“當地政府積極組織動員群眾將戶口遷移至實際居住新址”。造成安置點絕大多數居民“戶、居”分離,不像老社區(qū)絕大多數居民“戶、居”統一。
4.生存壓力普遍大于原住民。這些新市民在遷出地普遍有林地、承包地和宅居地“三地”。在原住地,再怎么困難也不用擔心生存問題和吃飯問題。但在遷入地,所面臨的一切都是全新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居住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變化,他們不僅要適應這些變化的環(huán)境及生活,還要擔心未來的生存和發(fā)展。雖然對現在的居住環(huán)境比較滿意,但大多對未來具有擔憂與恐懼心理,擔心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收入低難以支付遷入地的生活成本,甚至連基本的生存與吃飯問題都難以解決,心理壓力普遍高于當地的原住民。
二、易地扶貧集中安置點面臨的變更風險分析
風險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一定條件下,風險會演化升級、會轉化為事故與災難,造成難以彌補的生命與財產損失,因此,必須樹立風險意識,加強對各類風險的辨識與管控。
中國現在已進入風險社會,“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在國際國內面臨的矛盾風險挑戰(zhàn)都不少,決不能掉以輕心”①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于防范風險挑戰(zhàn)、應對突發(fā)事件論述摘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8.。確保扶貧安置點搬遷群眾在搬入地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需要做好異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后續(xù)管理,尤其是這些安置點的風險管理。要通過風險辨識、風險分析,了解安置點存在哪些風險和風險源,通過對這些風險的評估建立起相應的風險管控機制,維護好安置點的社會穩(wěn)定,為群眾創(chuàng)造一個平安、和諧的生活環(huán)境。
(一)變更風險的認知
“變更”一詞最早出自《管子·法法》,“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鄉(xiāng)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其含義為改變、更動。現代意義的風險概念則來自西方,最初主要是形容商船在頻繁的貨物運輸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由觸礁或海難等因素導致損失的危險。對風險的理解可以從客觀和主觀兩個層面來認識,首先,風險是一種客觀存在,是“關于不愿發(fā)生的事件發(fā)生的不確定性的客觀體現”②王巍.國家風險——開放時代的不測風云[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14.,是“可能發(fā)生的危險”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330.。其次,風險也是一種主觀認知,是損失的不確定性,其不確定性就是人的主觀判斷,不同的人對同一風險往往會有不同的認知,“作為一種可測定的不確定性,風險與人們的主觀認識和預期聯系在一起”④袁方.社會風險與社會風險管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37.。變更必然產生變化、更新,也就意味著產生不確定性,同時也因為人們對變化、更新的未來的不可知、不可測,變更就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這種因事物的改變、更動而產生的風險,我們就稱之為變更風險。
在管理領域,變更管理是安全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管理者如果對變更管理不當就有可能因其潛在的風險因子引發(fā)重大安全風險甚至是災難性事件,因為“變更過程是高風險的過程”①鐘開斌.逆向變更風險管理——“12·31”外灘陳毅廣場擁擠踩踏事件案例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06).。比如,2014年12月31日在上海外灘陳毅廣場發(fā)生的擁擠踩踏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因變更引發(fā)的重大安全風險,再加上管理者“預防準備不足、現場管理不力、應對處置不當”②鐘開斌.公共場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外灘擁擠踩踏事件案例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3.造成重大傷亡和嚴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責任事件。這起事件中的變更主要有:組織者變更,由原來的上海市政府牽頭舉辦、上海市旅游局代表上海市政府主辦變更為黃埔區(qū)政府和上海廣播電視臺共同主辦;活動地點變更,由往年舉辦的外灘風景區(qū)變更為外灘源,不說外地人,就是不少上海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外灘源在哪里,而將兩者等同于同一個地方;公眾參與方式變更,由過去的免費參與變更為憑票參與;參與人數變更,由過去的不限制變更為3000人左右參與。導致“原計劃在外灘舉行的跨年燈光秀活動變更為在外灘源舉行不對公眾公開的燈光秀活動后,相應的外灘安保措施等應急準備工作由市級管理降為區(qū)級管理”③鐘開斌.公共場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外灘擁擠踩踏事件案例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45.。
變更都有其風險,需要管理者和組織者對變更產生的風險認真加以分析評估、研判對待。作為管理者需對變更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意外情況有清醒的認識,并運用風險管理與系統管理思想建立起應對變更可能帶來的風險的變更風險管理體系,在對變更過程進行全面、系統風險評估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應對和防控各類變更風險,避免和減少因變更產生的風險帶來的突發(fā)事件發(fā)生。
(二)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面臨的變更風險
通過對現有超大型易地扶貧安置點風險源、風險點及居民群眾的走訪、調查分析,目前在這些安置點主要存在以下一些變更風險。
1.政策變更風險。隨著脫貧攻堅的全面完成,絕對貧困問題在我國已成為歷史,脫貧攻堅時的政策將會被鄉(xiāng)村振興等其他政策所取代。雖然原有脫貧攻堅的一些政策內容在新政策中會有延續(xù),而且國家對建檔立卡貧困戶脫貧后也明確還有5年的過渡幫扶期,但不管怎么說,對這些建檔立卡貧困戶原有的幫扶政策確實發(fā)生了改變,原有的一些優(yōu)惠和幫扶將會逐步減少乃至取消。對于搬遷到安置點的群眾來說,政策的變更既涉及個人,也涉及新居住區(qū)基礎設施的后續(xù)完善問題,一方面,對他們還能不能適用鄉(xiāng)村振興的有關政策目前還沒有確切的說法,畢竟他們現在不是生活在農村而是城市,目前云南對他們的新政策是2020年3月印發(fā)的《方案》。另一方面,雖然集中安置的新居住點已經建成并完成搬遷入住,但在安置點仍有一些城市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需要完善,過去集中安置點的建設資金是精準扶貧政策整合和投入的專項資金,現在精準扶貧已畫上了句號,后續(xù)的建設投入從哪里來,目前沒有具體說法,而這些投入對承接安置任務的縣(市、區(qū))來說是其財力難以完成的(昭陽區(qū)靖安、紅路兩個安置點基礎設施配套缺口資金達57031.97萬元),設施的不完善會影響到安置點居民的后續(xù)生活,這些政策變更對未來安置點的社會穩(wěn)定存在著風險。
2.身份變更風險。雖然目前在安置點生活的絕大多數群眾還沒有完成戶籍遷移,還是農村戶籍,但是,按照我國對城市居民的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分類統計方法,這些沒有完成戶籍遷移的安置點群眾其身份應屬于城市常住人口,而不再是農村人口。其身份的變更面臨著既有城市人口對其市民身份的認同,也面臨著他們自身對自己市民身份的認同。與此同時,身份的變更既有利益的獲取,能夠得到現有城市居民的保障及待遇,也潛在著未來附著在其原有身份上的利益失去和減少的風險,讓這些新市民對其身份變更存在著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進而成為不穩(wěn)定因素。
3.環(huán)境變更風險。人對熟悉的環(huán)境有一種天然的依賴感和親近感,故土難離是這種依賴感與親近感最直接、最生動的體現,對新的、陌生的環(huán)境往往會有一種排斥感、恐懼感。一般來說,人在對陌生環(huán)境熟悉與適應的過程中,適應期越短,潛在的風險就越少、級別也就越低,反之,適應期越長,潛在的風險就會越多,風險的等級也會越高。集中安置點的群眾普遍都是離開曾經熟悉的、世代居住的環(huán)境搬遷到一個新的陌生環(huán)境中,這種陌生性既表現為對自然環(huán)境的陌生——農村到城市、山區(qū)到壩區(qū)、單門獨院到單元樓房,還表現為人文環(huán)境的陌生,從傳統的鄉(xiāng)鄰社會變更到陌生的城市社區(qū)社會,面臨著由農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變更。由于周邊大多數人都是新面孔,在熟悉和適應這種環(huán)境變更中,必然存在著不適應或者是排斥感,造成搬遷群眾的不安與擔憂。
4.生活變更風險。生活變更風險主要是指生活方式變更的風險。集中安置點的移民,一是生活來源獲取方式發(fā)生變化,在原住地,搬遷群眾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做什么、什么時候做完全由自己自主決定,不受或者少受他人影響,但在安置點則失去了自主選擇的可能,更多的是被動接受;二是隨著生活環(huán)境的變更,其生活方式也發(fā)生了變更,安置點的生活離不開各種電器,由于是單元房,出門要乘電梯、做飯要用電器、入廁就在家里,等等,都需要適應和改變;三是生活必需品來源的變更,過去喝的水、吃的糧食、肉食、蔬菜大都來自于自己——基本上是自產自銷,尤其是蔬菜,沒了就到自己地理弄,基本不花錢,現在所有的這一切都要到市場通過交易的方式貨幣式獲取;四是生活習慣的變更。這一切,都意味著不可知和不確定。
5.職業(yè)變更風險。搬遷群眾的職業(yè)身份將由農業(yè)從業(yè)者、家庭婦女變更為城市一產或者二產、三產從業(yè)者;職業(yè)生活習慣將由原來的相對自由、隨性變更為受約束、守規(guī)矩和整齊劃一;職業(yè)活動將由原來的獨立與自主活動變更為多人的分工協作與合作,由強調自我到強調配合。
以上變更同時、集中出現,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安置點風險發(fā)生的概率和等級,而且這些風險的疊加又會加大安置點及其附近地區(qū)風險管理的難度,增加群體性事件發(fā)生概率。如果沒有有效的風險研判與防控機制,當誘因出現的時候,這些風險就可能成為當地社會不穩(wěn)定或者是群體事件發(fā)生的助推器。
三、易地移民集中安置點變更風險治理的對策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要在危機中育先機,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戰(zhàn)。做好云南省超大型易地扶貧移民安置點的后續(xù)發(fā)展與管理工作,確保安置點群眾穩(wěn)得住、能致富,離不開對安置點的風險管理。防范和化解易地扶貧移民安置點的變更風險,避免風險疊加和風險演變升級,需要提前謀劃,下好先手棋,打好風險防控主動戰(zhàn)。
(一)樹立系統治理理念,構建系統治理機制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97.防范和化解變更風險離不開系統治理理念與系統治理行動。系統論強調以系統為對象,從整體出發(fā)來研究系統整體和組成系統整體的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而把握系統整體,達到最優(yōu)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系統思維在深化改革和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系統意識,增強系統思維能力,提高應用系統思維解決問題的本領。2013年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2014年初,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項工程極為宏大,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第一次將堅持系統觀念作為“十四五”規(guī)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發(fā)展原則。
風險的產生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不同的風險也會相互交織、互相影響。對風險的有效治理需要樹立系統觀念,運用系統思維從整體、系統的角度全面把握風險產生的各種誘因以及促進風險演變、疊加的各種因素,同時還需要掌握不同風險之間的相互影響。針對易地扶貧移民安置點各類變更風險的情況,防控和化解這些變更風險,要從整體的角度出發(fā),系統分析考慮這些變更風險與安置點其他風險的關系,厘清上述不同變更風險的內在機理以及彼此之間的內在關聯。一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個維度全方位系統構建針對易地扶貧移民安置點的管理、發(fā)展、認同、參與四條路徑協同推進的變更風險防范化解的防控處置機制;二要加強移民輸出地與安置點的溝通協調,構建移民輸出地與安置點之間的信息溝通與協同共治機制。
(二)不斷完善制度,建立安置點變更風險專職研判處置機構
在國家和社會治理過程中,制度是帶有根本性的。我國現在已經進入一個各類風險高發(fā)、多發(fā)的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在國際國內面臨的矛盾風險挑戰(zhàn)都不少,決不能掉以輕心……如果防范不及、應對不力,就會傳導、疊加、演變、升級,使小的矛盾風險挑戰(zhàn)發(fā)展成大的矛盾風險挑戰(zhàn),局部的矛盾風險挑戰(zhàn)發(fā)展成系統的矛盾風險挑戰(zhàn)……經濟、社會、文化、生態(tài)領域的矛盾風險挑戰(zhàn)轉化為政治矛盾風險挑戰(zhàn),最終危及黨的執(zhí)政地位、危及國家安全”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22.。隨著時間、環(huán)境的變化,各類風險也會發(fā)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各級黨委、政府要增強憂患意識,不斷完善各項制度,應對處置各種風險。針對這些集中安置點可能存在和面臨的風險,當地黨委、政府居安思危,已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比如:網格管理、加強基層黨組織領導、大力發(fā)展產業(yè)解決群眾生計等制度和舉措,取得了明顯成效。
但仍需對風險防控做到關口前移,提前準備和防范。“‘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維護公共安全必須防患于未然,要堅持標本兼治,既著力解決較為突出的公共安全專項問題,又用更多精力研究解決深層次問題。要堅持關口前移,加強日常防范,加強源頭治理、前端處理,針對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地毯式排查和立體化整治行動,什么問題突出就集中力量解決什么問題。要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形勢分析制度,經常評估、預判,及時發(fā)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清除公共安全隱患。”①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于防范風險挑戰(zhàn)、應對突發(fā)事件論述摘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187.因此,當前和今后做好風險防控既要總結完善既有制度,讓制度效用得到充分發(fā)揮,又要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制定出臺新的制度和舉措解決這些情況和問題。
針對安置點面臨的上述變更風險,需要在現有制度和機構的基礎上,組建專門的機構或者是責成專門機構、人員專項負責,對安置點的變更風險及風險源進行持續(xù)跟蹤監(jiān)測、評估,及時了解、掌握安置點變更風險及其風險源的演變情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當地黨委、政府報送風險研判報告,為及時管控和處置風險提供第一手資料。
(三)聚焦源頭治理,推進產業(yè)持續(xù)發(fā)展
發(fā)展中的問題要在發(fā)展中解決,發(fā)展中出現的風險要在發(fā)展中化解。超大型易地扶貧移民安置點面臨的變更風險是在發(fā)展中出現的,很大程度上是由當地和安置點發(fā)展的不足以及移民群眾對當前及未來自身發(fā)展信心不足帶來的,化解這些風險要聚焦源頭治理,找準風險產生的根源,緊緊抓住發(fā)展產業(yè)這個“牛鼻子”,通過產業(yè)的發(fā)展妥善化解移民進城后的后顧之憂,讓他們有通過誠實、努力勞動獲取養(yǎng)家并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的產業(yè)平臺與發(fā)展平臺,讓自己的未來能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要讓移民群眾穩(wěn)得住,在安居的基礎上樂業(yè),首要的是要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收入來源問題。為此,一要創(chuàng)造良好的營商環(huán)境,推進安置點及附近產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要發(fā)揮好當地政府經濟調節(jié)和公共服務職能,努力培育市場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暫時替代市場,設置企業(yè)(產業(yè))發(fā)展專員,一企(產)一員或者一企(產)多員專門幫助安置點及附近新建產業(yè)提供發(fā)展信息、化解發(fā)展風險、解決發(fā)展難題,幫助企業(yè)(產業(yè))增強發(fā)展動力與發(fā)展后勁,促進其較長時期穩(wěn)定發(fā)展,保障安置點群眾有穩(wěn)定的就業(yè)平臺。二要繼續(xù)完善現有政策,獎勵、鼓勵與激勵企業(yè)積極吸納安置點群眾就業(yè)。三要多途徑開展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培訓,提升當地群眾城鎮(zhèn)化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能力。做好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服務,大力鼓勵和創(chuàng)造條件幫助移民群眾積極就近創(chuàng)業(yè),化解其創(chuàng)業(yè)進程中的難題,通過群眾自身創(chuàng)業(yè)來帶動就業(yè),在增強自我發(fā)展能力與動力的同時,增強其對城市新生活的適應能力與融入能力。
(四)做好宣傳教育,促進群眾心理融入
如前所述,風險既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是一種主觀認知。安置點變更風險的產生既有物質與發(fā)展不足的客觀原因,又有來自移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主觀認知。做好變更風險防控不僅要提高安置點發(fā)展能力,還要提升安置點群眾的心理適應能力,讓他們盡快適應新居住地的環(huán)境、生活,從心理上接受和融入目前嶄新的城市生活。一要避免過度宣傳。要恰如其分地向群眾宣傳介紹安置點的情況,既講未來發(fā)展愿景,也講當前發(fā)展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及黨委、政府對待這些問題的態(tài)度與舉措,讓群眾對安置點的新生活有正確的心理認知和態(tài)度,樹立正確的心理預期,既對未來有美好的期盼,也對當前可能會面臨的困難有清醒的認識,進而增強戰(zhàn)勝困難的信心和勇氣,安心接受和融入目前的城市新生活。二要抓好安置點學校軟件建設,促進教育發(fā)展。孩子是國家、社會未來的希望,更是安置點群眾對未來的希望,他們寧愿自己苦一點也要讓孩子未來有一個比他們更好的生活,而且孩子的城市化融入也是家長融入的動力,穩(wěn)住孩子就是穩(wěn)住家長、穩(wěn)住移民。穩(wěn)住孩子的前提是提高安置點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讓這些孩子通過學習獲得改變命運的機會與能力,不僅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fā)掘出潛力、激發(fā)出能力,為未來發(fā)展奠定基礎,還能通過孩子的變化影響家長的行為,促進安置點社會穩(wěn)定。三要多渠道、多途徑、多主體關注移民心理健康,及時化解其心理問題。通過發(fā)揮安置點基層黨組織、基層自治組織、社會組織、黨員、社會賢達等的力量,采取多種形式關心、關注移民的心理健康,化解其心理困擾,將誘發(fā)變更風險的各種主觀因子及時消除在萌芽之中。
總之,安置點變更風險是多方面的,產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對其治理應多方發(fā)力,多維度、多角度、多路徑創(chuàng)新治理,不能有畢其功于一役的簡單思維,要樹立久久為功的堅定信念,通過發(fā)展來逐步化解安置點的變更風險,促進安置點社會和諧穩(wěn)定與群眾安居樂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