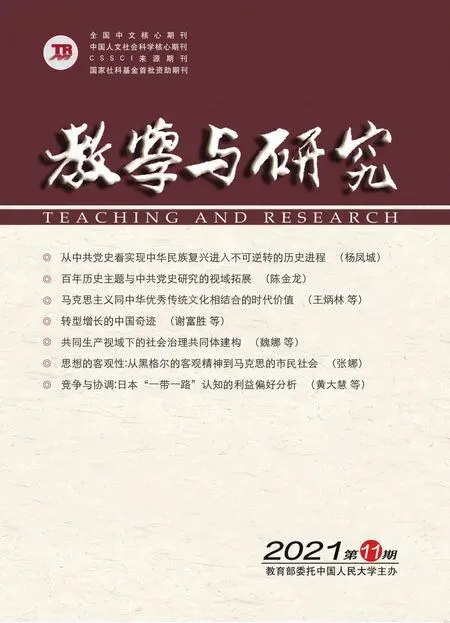競爭與協調:日本“一帶一路”認知的利益偏好分析*
黃大慧,趙天鵬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在變革國際關系與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取得了矚目的成果,既獲得了來自沿線國家的歡迎,也逐漸得到了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重視與肯定。日本作為中國的重要鄰國以及亞洲與全球有影響力的經濟大國,也在各個層面對“一帶一路”給予了高度關注,“一帶一路”一時間在日本成為高頻詞而被廣泛提及。盡管如此,日本對“一帶一路”的高度關注卻未能轉化為積極認知,從政府、學界到社會都彌漫著對“一帶一路”的警惕與擔憂。直到2017年,日本才對“一帶一路”展現出一定的接觸姿態。
關于日本的“一帶一路”認知,既有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的“縱向性”整體認知,這類研究占了絕大多數,主要梳理了安倍政府對“一帶一路”認知的階段性變化,同時聚焦于安倍政府的反應或應對;(1)“縱向性解釋”的研究參見:黃鳳志、劉瑞:《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與應對》,《現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11期;盧昊:《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變化、特征與動因分析》,《日本學刊》2018 年第 3 期;楊伯江、張曉磊:《日本參與“一帶一路”合作:轉變動因與前景分析》,《東北亞學刊》2018年第3期;等。二是集中于日本經濟界、媒體、學界等非政府力量的“橫向性”認知,此類研究有別于將日本政府作為單一理性行為體的研究,反映出日本各界對于“一帶一路”認知的多元性及其對政府認知的反作用力。(2)“橫向性解釋”的研究參見:吳寄南:《淺析智庫在日本外交決策中的作用》,《日本學刊》2008年第3期;顧鴻雁:《日本智庫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及其影響研究》,《國外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朱丹丹:《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意圖解讀及應對》,《中國周邊外交學刊》2015年第2輯;吳淑招:《從朝日新聞看日本對一帶一路態度的重大轉變》,《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8月13日,http://www.cssn.cn/gd/gd_rwhn/gd_ktsb/gjydylpxhzgyxpz/202008/t20200813_5169256.shtml;等。
本文需要解答的核心問題是,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盡管學界有不少文章論及日本政府與各行為體對“一帶一路”的認知情況,但對于這種認知的形成原因及其轉變艱難性仍缺乏更深入的研究。鑒于此,本文嘗試以“利益偏好決定國家認知”的解釋路徑闡釋日本的“一帶一路”認知問題,而非僅僅是對認知的歷史演變或是對不同行為體認知進行事實梳理。
一、解釋路徑:基于利益偏好的分析
認知(Recognition)是指雙方對彼此的意象,它由利益(Interest)決定。國家利益的構成多種多樣,不一而足,但從“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的本體論角度出發,國家利益的形成不僅是天然的物質性存在,也可以通過規范等理念性因素建構。在此基礎上,國家對利益的不同偏好(Preference)構成了國家對外認知的來源。
首先,權力競爭重視物質的相對收益。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都強調國際關系的本質是權力競爭,尤其在后者看來,以“無政府狀態”為國際政治的假定條件,國家更看重相對收益,而不會滿足于絕對收益,國際合作也因此難以實現。(3)尚會鵬:《從“國際政治”到“國際關系”——審視世界強聯結時代的國際關系本體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2期。權力競爭更容易發生在崛起國與守成國的權力轉移過程中,雙方都十分看重物質收益的孰多孰少,這種結構性矛盾會使得獲取利益的過程變得更加激烈。崛起國與守成國還會根據自身利益偏好來設計與推進地緣戰略,因此在某一重合的地理范圍內很容易造成地緣權力競爭。
不論從經濟權力還是地緣權力的視角來看,日本對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的權力地位更替十分敏感,日本并非不愿意通過與中國的合作來獲益,而是擔憂這種獲益會更有利于中國。(4)袁偉華:《權力轉移、相對收益與中日合作困境——以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反應為例》,《日本學刊》2018年第3期。尤其自2010年日本GDP排名被中國超越之后,日本與中國展開權力競爭的趨勢愈發明顯,日本全方位對華制衡顯著增強。甚至在西方學者看來,日本已經從維持穩定的國際戰略的“現狀國家”開始向“怨恨的現實主義”轉變,公開對華采取“軟硬”兩手制衡。(5)[英]克里斯托弗·休斯:《“怨恨的現實主義”與日本制衡中國崛起》,《國際政治科學》2016年第1卷第4期。在冷戰結束之后,日本不僅在爭奪東亞貿易與投資市場方面與中國競爭激烈,在圍繞“東亞”“亞太”等地區主導權方面也與中國展開了廣泛的競爭。
其次,制度合作注重物質的絕對收益。雖然新自由制度主義也認為利益是物質性的,但對于國際合作抱有期待,并不過分強調爭權奪利的競爭色彩,而是提出制度的理性安排會使得行為體傾向于合作,以獲取物質的絕對收益。合作性是制度強調的重要方面,制度的實踐與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但在現實情況中,國家實力的結構性變化、相互認知以及彼此采取的外交政策等因素,往往會導致制度既可以作為國際公共產品,也可以作為制度領導國或參與國的權力制衡工具,國際制度間的競爭并不鮮見。(6)關于“制度制衡”與“制度競爭”,賀凱和李巍分別提出了“制度現實主義”與“現實制度主義”,兩種理論雖然在分析層次、研究問題等方面各有側重,但是都強調了制度具有現實主義屬性的“競爭性”,而非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的制度與合作之間存在的高度關聯。盡管制度權力既視為國際合作的重要工具,也將其作為權力競爭的組成部分,但很明顯的是中日兩國之間后者占據了主導性。參見李巍、羅儀馥:《從規則到秩序——國際制度競爭的邏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4期。
中日在東亞制度格局中形成了長期競爭局面,兩國都希望更符合自己利益的制度方案成為地區合作的主導方案,為此雙方曾圍繞“10+3”和“10+6”機制展開過激烈的制度競爭。(7)在地區合作的制度偏好方面,中國屬于內向型,而日本屬于外向型的。例如中國更愿意通過在東盟主導的“10+3”制度框架內發揮更大的話語權,而日本更傾向于聯合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三個與日美友好的域外國家,以“10+6”制衡中國實力,推動合作進程。參見孫憶:《競爭者的合作: 中日加強經濟外交合作的原因與可能》,《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盡管如此,兩國仍然通過中日韓合作機制、亞太經合組織(APEC)、“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等機制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地區協調。在這種局面下,一方面,中日兩國的制度協調經常存在制度導向不一、外部力量強勢介入導致合作齟齬的困境,制度的競爭性淡化了兩國在東亞地區的制度合作性;另一方面,東亞的大國協調基本處于可控的范圍,中日兩國能夠在地區合作中尋求相關契合點,以獲取絕對收益,并向地區提供公共產品。由此可見,雖然制度間競爭是主流,但中日仍可以通過政策協調改變收益預期,達成競爭者之間的合作。
最后,規范塑造國家利益。國際規范作為建構主義學派的理論核心,是指國際社會成員的價值標準與行為準則,約束和塑造國家的對外行為及其互動。(8)陳拯:《建構主義國際規范演進研究述評》,《國際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國際規范理論指出,不同于物質的利益觀,國家利益既不是外部威脅的結果,也并非國內需求驅動,而是各國共享的規范和價值塑造了在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對本國利益的認定和行為選擇。(9)章遠:《話語權、國際規范和國家利益——重讀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9月8日。國際規范作為 “一個行為集體擁有的關于適當行為的共享期望”,塑造了相似行為體對于國家利益的理解。西方國家倡導的規范在自身容易擴散且接受程度較高,這不僅與西方國家相似的國內制度與文化較匹配,也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需求。基于“國以群分”的身份政治邏輯,規范競爭導致零和博弈成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普遍認同的因果推論,西方國家以容易傳播的“好規范”來定義西方規范,而將“非西方規范”定義為不享有國際合法性與傳播性的“壞規范”,這必然導致兩者之間的競爭與對立形態。(10)何銀:《規范競爭與互補——以建設和平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4期。
日本作為西方陣營的一員,對外政策具有經濟務實主義特性,但在保持與西方國家價值觀念與行為準則的集體一致時,仍然遵循利益邏輯而非義務邏輯。尤其是安倍晉三再次執政之后,面對中國倡導的規范在全球范圍內的加速擴散,日本針對中國“規范遏制”的趨勢愈發增強。在各種國際場合,安倍政府頻頻拋出“價值觀外交”“積極的和平主義”“反對以實力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海洋法治三原則”“基建建設標準”等排他性價值標準與行為準則,試圖聯合規范認知相近的國家一同構建遏制中國崛起的“規范層面”均勢。(11)日本學者湯川拓將“均勢”概括為“政策層面的均勢”“體系層面的均勢”“規范層面的均勢”,認為“規范層面的均勢”并非完全現實主義式的均勢概念,而是對于實現國際社會共同體共有利益或成員一般利益而形成的規范性和集團性體制。參見湯川拓:「國際社會における規範としての勢力均衡とその存立基盤」,『國際政治』2014年3月第176號。
基于上述分析,對“物質的相對收益”與“規范塑造的國家利益”偏好構成了日本對“一帶一路”的“競爭性”認知,對“物質的絕對收益”偏好則構成了日本對“一帶一路”的“協調性”認知,前者為主要,后者為次要。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既有競爭也有協調,這不僅符合日本長久以來對華政策的兩面性,也為判斷未來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走向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日本對“一帶一路”的“競爭性”認知
在“競爭性”認知中,“物質的相對收益”偏好,是指日本將“一帶一路”視作日本地緣經濟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的威脅;“規范塑造的國家利益”偏好,則是指日本認為“一帶一路”嚴重挑戰了西方倡導的價值觀與國際基礎設施建設標準。
(一)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利益
地緣利益既包括地緣經濟利益,也包括由地緣經濟擴展形成的地緣政治利益。地緣經濟通常被視為實現地緣政治目的的經濟手段(Economic Statecraft)。(12)Blackwill, Robert D. &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在日本看來,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秩序成為“一帶一路”擴展地緣經濟利益的重要目標,特別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成立不僅局限于交通基礎建設,中期來看,也包括構建以人民幣為基礎貨幣的地區經濟圈。”(13)淺野亮:「『一帯一路』の論理と性格―経済と安全保障の両面から―」,『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號,第32頁。日本各界對于AIIB的關注程度頗高,在機構初創時期,日本對于AIIB的關注程度甚至超過了“一帶一路”倡議本身,這側面反映出日本在處理AIIB問題上利益取舍的復雜心態。面對中國首次主導創設的國際性多邊金融機構,日本將其視為對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巨大挑戰,擔心傳統的亞洲基建市場會落入中國手中。與此同時,即使日本深知“不參加獲益便為零”,但參加則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中國經濟權力的制度化安排,并與全球金融體系的傳統主導國美國相忤。因此,日本對AIIB抱有相當程度的警惕,本質上是抗拒中國可能主導未來地區與全球基建的融資話語權,從而使日本的獲益受損。
不容否認的是,日本曾長期扮演著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建設者角色,積極開發地區經濟走廊,實施政府開發援助、調動民間資本一直是日本獲得巨大基建市場的主要手段。面對“一帶一路”的基建布局,特別是中國企業雄厚的資金實力,日本企業的危機意識不斷增強,日本政府也開始積極為本國基建市場尋求出路。在2015年5月舉辦的“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議上,日本宣布在未來5年內與ADB合作向亞洲國家提供1 1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這個數字恰好比AIIB的法定資本金多出100億美元,這無疑展現了日本對于相對收益的極度敏感,與AIIB的競爭性姿態不言而喻。(14)「第21回國際交流會議『アジアの未來』晩餐會 安倍內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外務省,2015年5月21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0521speech.html.2013年5月,日本制定了“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戰略,立下了到2020年基建訂單達到30萬億日元的雄心壯志。(15)「インフラシステム輸出支援」,外務省,2020年9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 092742.pdf.在“一帶一路”重點布局的沿線區域,日本政府除了頻頻簽下高額的基礎設施訂單之外,安倍晉三等政府官員也是不遺余力地充當起本國基礎設施的“超級推銷員”,以擠占中國的基建市場,在東南亞、南亞、中亞、非洲等地區與中國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局面。(16)例如,僅在2017年,安倍等其他日本政府官員親自作為“超級推銷員”的基建訂單成果合計194件,包括印度的孟買-艾哈邁達巴德高速鐵路項目、肯尼亞的蒙巴薩港口開發項目,俄羅斯的郵政系統項目等。
日本警惕“一帶一路”可能危及自身地緣政治利益,將中國構建“一帶一路”的動機視為“秩序修正主義”,認為中國對現今國際利益格局所處位置不滿。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認為“‘一帶一路’就是要以經濟權力為基礎,進一步擴大中國的政治權力與軍事權力。”(17)川島真:「一帯一路構想と海運事業―海運·海洋強國を目指す中國の動き」,『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號,第98頁。此外,諸如“海洋強國”“軍事港口”“新朝貢體系”等概念頻頻出現在日本對“一帶一路”的描述中,可以明顯看出日本對“一帶一路”認知的現實主義邏輯,即認為“一帶一路”體現了中國的地緣政治“野心”,中國“試圖以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18)「第3章 國益と世界全體の利益を増進する外交」,『外交青書』,2017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chapter3_01_06.html.早稻田大學教授天兒慧認為“中國創建‘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背景就在于中日兩國在解決亞洲金融危機、構建東亞共同體的過程中陷入對立局面;在東亞合作構想受挫的情況下,中國的國際協調對象開始從太平洋向西亞、南亞以及歐洲與非洲拓展,從而構建一個宏大的經濟圈,并以此為基礎構筑明顯具有強烈政治含義且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勢力圈。”(19)天兒慧:「政治から読み解く『一帯一路』-パックス アメリカーナへの挑戦と難題」,『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號,第39頁。
日本把“一帶一路”看作是“修正主義”的另一個重要背景在于中美對立博弈的國際格局。日本認為中國正在力圖打破美國為霸權的國際秩序,打造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日本學者認為,中國決心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直接動機有二:一是美國難以接受構建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二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出臺。(20)關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日本學者多提出較為消極的看法,認為美國對“新型大國關系”始終保持著極為慎重的回避姿態,“互相尊重核心利益”成為美國難以解決的首要問題。有日本學者指出,2013年之后,隨著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中美在南海與西太平洋的摩擦與網絡攻擊加劇,奧巴馬政府基本不愿再提及“新型大國關系”概念。參見神保謙:「新型の大國関係 米中外交の行方を左右」,キャノングローバル戦略研究所,2019年9月28日,https://cigs.canon/article/20150929_3309.html;高原明生:「中國の內政と日中関係」,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9月28日,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R01_China/01-takahara.pdf.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認為,美國無法接受中國與自己的對等地位,難以默許中國的核心利益,也無法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因而一個中美利益共存的國際秩序恐怕很難形成;此外,TPP則是配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在亞太地區針對中國開展的實質性圍堵。在高原明生看來,由于中國向東的利益空間擴展明顯受阻,中國開始將對外戰略由“美國第一主義”轉向“歐亞大陸第一主義”,“一帶一路”就是這一轉變的實際舉措。(21)高原明生:「アジア地域の安全保障と日本の課題」,佐倉國際交流基金,2016年8月6日,http://www.sief.jp/21/2016/bundai201612.pdf.尤其是TPP戰略可謂賭上了日本的“國運”,但缺少美國的TPP使得日本的對華“軟制衡”嚴重受挫,轉而積極謀劃構建“印太”戰略,矛頭直指“一帶一路”,與中國展開新一輪地緣競爭戰略。
(二)價值觀與國際基礎設施建設標準
日本將“一帶一路”視為與所謂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等對立的“異質化”存在。安倍政府積極推行“價值觀外交”,盡可能營造一個廣泛對抗中國的“價值觀”陣線,這是在日本相對實力衰落事實下所采用的“軟制衡”手段。(22)早在2006年第一次執政期間,安倍晉三就針對中國推行“價值觀外交”。參見黃大慧:《冷戰后日本的“價值觀外交”與中國》,《現代國際關系》2007年第5期。安倍政府刻意強調所謂共同價值觀,在外交場合言必稱“自由、民主、人權”,極力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似乎“自由、民主、人權”就是日本的標牌。(23)《揭開安倍政權“價值觀外交”虛偽面紗》,《人民日報》2013年6月14日。日本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尋求這種價值觀利益的另一層用意在于拒斥帶有中國主張的“新型國際關系”。日本對美國庇護下的國家秩序始終抱有一種依賴感,這是由于美國長期以來為日本提供了自身稀缺的安全保障與經濟賴以生存的自由貿易體制。川島真將“一帶一路”形容為“與歐美依據的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基本理解完全不同的新型國際關系試驗場”,是一種“完全不以民主主義為前提,基本上只是重視經濟關系,以利益分配構筑‘雙贏’,憑借伙伴關系相連的世界命運共同體。”(24)川島真:「一帯一路構想と海運事業―海運·海洋強國を目指す中國の動き」,『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號,第97-98頁。筑波大學教授遠藤譽也提出,“一帶一路”既是為了阻止美國回歸亞洲對華形成包圍圈,也是為了阻止向世界輸出“民主”的美國構筑的價值觀圍堵。(25)遠藤譽:「習近平主席訪英の思惑―『一帯一路』の終點」,yahoo news, 2015年10月9日,https://news.yahoo.co.jp/byline/endohomare/20151019-00050601/.
面對“一帶一路”的新理念與主張,日本開始積極以“印太”為抓手,與西方國家組建群體性力量牽制“一帶一路”。日本首先利用2016年第6屆“東京—非洲國際發展論壇”(TICAD)的機會提出了“自由且開放的印太戰略”,緊接著,同印度、美國與澳大利亞領導人緊急確認了這一戰略規劃。(26)「第1章 2017年の國際情勢と日本外交の展開」,『外交青書·白書』,2017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chapter1_00_02.html#s10201.日本的戰略方向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把與中國存在地區爭端的印度納入“價值同盟”,對“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封堵。日本不止一次地尋求與印度確認“基于價值的伙伴關系”,開創“擁有共同普適價值與戰略利益的‘日印新時代’”,稱贊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27)「日印共同聲明 自由で開かれ,繁栄し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外務省,2017年,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90053.pdf;「岸田外務大臣によるモディ·インド首相表敬」,外務省,2016年11月1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80.html;「日印ヴィジョン2025 特別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と世界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の協働」,外務省,2017年12月1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508.html.另一方面,日本突出與印太地區中小國家,特別是向與中國存在海洋領土爭端的國家施加“海洋法治”規范,借價值觀之名,行安保合作之實。日本這樣做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擴大該地區遏制中國的安全合作,并為“印太”地緣構想的順利實施增強合理性,與沿線各國共同對“一帶一路”設置障礙。
日本認為“一帶一路”倡導的基礎設施建設標準不符合西方的高標準,強調構建“高質量”建設基礎設施伙伴關系。該“伙伴關系”包括“經濟性、安全性、應對自然災害的強韌性、考慮環境與社會、以及對當地社會和經濟的貢獻”,之后固定為“開放性”“透明性”“經濟性”“財政健全性”的“四大條件”。(28)「第21回國際交流會議『アジアの未來』晩餐會」,安倍內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2017年5月21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0521speech.html.安倍晉三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在滿足‘四大條件’的前提下才可考慮與‘一帶一路’的合作”,卻又明確表示“并非認可‘四大條件’,就一定代表與‘一帶一路’合作”。事實證明,中國的基建模式在注重質量的同時,兼顧平等協商的原則,充分考慮對象國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這體現了政策溝通與民心相通的內涵。日本學者也承認,與日本追求“高質量”的精細化方式不同,“中國模式”的最大優勢在于通過精簡項目的審批手續,利用強大的組織能力與資金能力在短時間內高效率推動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落地,從而對接次區域各國制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29)Fumitaka Furuoka,“Japan Is Putting more Quality over Quantity in the Mekong”, East Asia Forum, September 27,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09/27/japan-is-putting-quality-over-quantity-in-the-mekong.除了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基建規則標準,日本政府也加緊利用2016年在伊勢志摩召開的西方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7)與2019年在大阪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等國際場合,進一步在西方國家之間擴散對國際基建規則標準的規范認同,試圖擴大自身在全球基建領域的話語權,以排除“一帶一路”在規則與標準方面的影響力。(30)「質の高いインフラ分野をめぐる國際潮流」,外務省,2020年11月1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bunya/infrastructure/index.html.
三、日本對“一帶一路”的“協調性”認知
雖然“競爭性”認知是主要方面,但在“協調性”認知下,日本也可通過制度合作得到物質的絕對收益,具體包括“維護自由貿易體制與多邊主義”“聚焦‘印太構想’的經濟合作性”以及“探索務實合作模式”三個方面。
(一)全球性體制認同:維護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
特朗普政府動搖了全球自由貿易體制與多邊主義架構,日本不得不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過度競爭,與“一帶一路”展開一定的接觸姿態。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表態轉變與特朗普政府上臺帶來的日美關系不確定性以及國際局勢的重大變化密切相關,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國優先”政策,給日本造成了強烈沖擊。在這種變局下,安倍政府可謂是“不安倍增”,自由貿易體制與地區經貿制度事關日本國家利益,一旦傾覆,后果不堪設想。在美國因素的“助推”下,日本逐漸意識到與中國繼續展開競爭無益于維護國際秩序,也無益于彼此利益,而“一帶一路”本身就是促進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的地區倡議,這順理成章地成為日本尋求中日關系由“競爭”到“協調”的突破口。2017年以來,日本的對華政策顯示出了一些靈活調整的跡象,對“一帶一路”的表態開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日本利用各種國際場合向外界傳遞對“一帶一路”的改觀,采取了較為“謹慎的積極”,一面表示“‘一帶一路’是具有潛力的經濟構想,中日合作可以滿足亞洲巨大的基建需求”,另一面又指出“在認同公平公正的亞太發展理念、透明開放的招標方式和經濟回報性高、債務可償還的前提條件下參加‘一帶一路’建設。”(31)「第23回國際交流會議『アジアの未來』晩餐會 安倍內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首相官邸,2017年6月5日,https: //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605speech.html;「第3回日中企業家及び元政府高官対話(日中CEO等サミット)歓迎レセプション」,首相官邸,2017年12月4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actions/201712/04taiwa_kangei.html.
對于AIIB,盡管日本政府至今仍未表態加入AIIB,但是與AIIB的接近值得矚目。日本綜合研究所會長寺島實郎指出“雖然日美同盟是不可撼動的根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僅僅依靠美國就可以描繪日本未來的劇情已不復存在,中日通過ADB與AIIB共同為其他國家提供基礎設施是符合現實的。”(32)寺島実郎:「大中華圏で捉える『一帯一路』」,『運輸と経済』2018年12月第78巻第12號,第28頁。2019年7月,日本派出了此前負責國家財政與基建的兩位重要官員出席在盧森堡召開的AIIB年會,被日本媒體看作是日本政府對AIIB的積極信號。(33)「中國主導のAIIBになぜ接近?日本の深謀遠慮の背景」,朝日新聞,2019年10月30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BQ462BMBQULZU00B.html.除此之外,2020年1月,AIIB也雇用了一位原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BIC)的日本籍雇員,日媒評價說“此人具有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基礎設施融資的豐富經驗。”(34)「中國のアジア投資銀、日本人登用」,西日本新聞,2020年1月14日,https://www.nishinippon.co.jp/item/o/575445/.日本綜合研究所的AIIB動態分析報告也指出AIIB關注經濟回報性,在選擇項目投融資方面較為謹慎,與ADB的合作比較廣泛,在機構運營上也具備很高的專業性,而非具有較強的中國政府色彩。報告建議“日本應當考慮加入AIIB,并為日本企業謀求更大的基建利益。”(35)佐野淳也:「AIIBの現狀とわが國の関わり方」,『アジア·マンスリー』,2018年8月號,https://www.jri.co.jp/page.jsp?id=33071.2017年以來,AIIB連續兩年獲得標普、惠譽、穆迪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最高Aaa評級,穆迪則在2019年率先給出AIIB的Aaa評級,認為其“作為國際金融機構的地位日益鞏固”。(36)《亞投行連續三年獲得穆迪Aaa評級:前景穩定》,2019年4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42732.由此可見,盡管日本想要改變對“一帶一路”的固有認知仍存在現實困難,但在AIIB保持良好績效的事實面前,日本將來是否會選擇加入也未可知。
(二)區域性制度協調:聚焦“印太構想”的經濟合作性
不同于美國以競爭為目的的“印太戰略”,日本既不愿看到“印太構想”與“一帶一路”形成過分的地緣競爭,也并不完全排除潛在的制度協調。不能否認,在構思和推行“印太構想”的過程中,日本始終秉持國際權勢斗爭的固有邏輯和對華指向性。(37)宋德星、黃釗:《日本“印太”戰略的生成機理及其戰略效能探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 11 期。毋庸置疑,“印太”的誕生就是為了與“一帶一路”爭奪地緣的相對收益,但現實主義的利益邏輯很難保證己方的利益所得一定會多于彼方,雙方往往會因為爭奪相對收益過于慘烈而陷入安全困境。尤其像日本并不能如同美國憑一己之力即可主導戰略走勢,也難以保證自身戰略意志與戰略能力是否可以與戰略目標相匹配,因此日本需要考慮除對沖、制衡的傳統戰略手段之外與新興崛起國的接觸(Engagement)策略。接觸政策要求盡可能通過與新興崛起國的互動來取得經濟利益,提高收益預期,這也是經濟全球化與經濟績效支撐政治合法性前提下的必要做法。(38)菊池努:「インド太平洋」の地域秩序とスイング·ステーツ『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ースイング·ステーツへの対応ー』,平成26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総合事業)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4年,第3頁。
日本非常清楚,如果將自身綁定在美國對抗中國的“戰車”之上,很容易陷入中美大國博弈的“斷裂帶”,最終失利的只能是日本自己。在2018年的國會施政演說上,安倍晉三提到“在‘印太戰略’的框架下,與中國也可以合作,來滿足亞洲基礎設施的龐大需求”。在2019年的國會施政演說中,安倍晉三則直接將“戰略”更名為“構想”,也并沒有像2018年一樣沿用“與自由、民主主義、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觀共有的國家聯手”這樣的表述。(39)「第百九十六回國會における安倍內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8年12月2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2019年11月,在新加坡召開的東亞峰會上,安倍晉三表明“‘印太構想’是不排除任何國家的。”(40)「第百九十八回國會における安倍內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9年12月8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siseihousin.html.從現實情況來看,印太地區的國家對中國存在很高的經濟依存度,日本也深知自身無法給予這些國家所需的所有公共產品,因此在承認“一帶一路”作為印太地區主要公共產品供給方的基礎上,避免“印太構想”與“一帶一路”的過度競爭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日本戰略學者神谷萬丈指出“日本的‘印太構想’中具有對華競爭與對華協調兩種特性,對于實現競爭戰略來說,協調戰略也同樣重要。”(41)神谷萬丈:「『競爭戦略』のための『協力戦略』―日本の「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構想)の複合的構造―」,SSDP安全保障·外交政策研究會,2019年2月,http://ssdpaki.la.coocan.jp/proposals/26.html.未來日本繼續貫徹這種作為矛盾體的“印太構想”是可以確定的,但是這種正相反的戰略目標是否能夠如日本所愿,恐怕并非日本一己之力可以左右。
(三)探索務實合作模式: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
自由制度主義認為,行為體的增加可以改變收益的未來預期。日本國內經濟界的逐利動機迫使日本認真思考一味競爭的后果可能是雙輸局面,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成為折中的機制協調。“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伊始,日本經濟界對“一帶一路”的態度曖昧,一是出于對倡議本身的不了解,二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消極應對,并沒有營造出日本企業參與的有利氛圍。但是隨著“一帶一路”規劃的逐步清晰,日本經濟界出現了要求考慮參與“一帶一路”的聲音,至少日本社會已經隱約意識到不參加“一帶一路”可能導致的失利,并會削弱日本產業競爭力。(42)苗吉:《多元中的演進:日本視野中的“一帶一路”倡議》,《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6卷第1期。日本官方對“一帶一路”的方針稍有變化,日本的經濟團體就會順勢而動。經團聯前后兩任會長榊原定征、中西宏明對“一帶一路”抱有很高的期待,他們多次率團來華訪問,尋求在“一帶一路”下加強中日兩國在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商機。(43)「中國首相『日本と自由貿易を擁護』経団連會長らと會談」,2018年10月10日,https://www.sankeibiz.jp/macro/news/181010/mca1810101921018-n1.htm.歷史屢次證明,日本國內經濟界充當壓力團體推動中日關系出現轉機,這背后是日本經濟界希望與中國展開經濟合作的利益動機。
利益認知決定行動策略,“第三方市場合作”成為日本政府落實中日企業合作的具體機制。“第三方市場合作”的特點在于弱化政府的介入角色,強化企業的主體性,突出兩國企業在第三國展開具體項目選取與合作的經濟利益。日本一方面仍不愿以政府與“一帶一路”簽署任何官方的合作協議,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一種折中方式為本國企業搭建一個與中國企業合作的機制平臺。“第三方市場合作”被看作是中日關系重回正軌背景下,兩國對“務實合作”的探索。在兩國領導人的共識下,中日兩國開始為“第三方市場”制定具體實施步驟,其中最具有標志性的是在2018年安倍晉三訪華期間,召開了首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但需要指出的是,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仍然會受到日本相對收益思維的掣肘,中日之間似乎對這種合作模式本身存在溫度差。從合作的現實情況來看,被寄予厚望的泰國東部經濟走廊高鐵合作項目,也因為日本企業退出投標,從中日泰的“三方合作”變成了中泰的“兩國合作”。(44)趙天鵬:《從“普遍競爭”到“第三方市場合作”:中日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新動向》,《國際論壇》2020年第1期。第三方市場合作不失為一種中日現階段經濟合作的有效路徑,但仍需要穩定的中日政治關系來保駕護航。
四、“后安倍時代”的日本“一帶一路”認知走向
2020年8月,安倍晉三辭任日本首相后,日本政治進入“后安倍時代”。首先是菅義偉作為過渡性人物,在擔任繼任首相期間依舊延續了安倍時期的外交路線,特別是對美與對華政策。時隔一年之后的2021年9月,曾長期擔任安倍內閣外務大臣的岸田文雄在選舉中勝出,成為第100任日本首相。雖然仍無法預判日本新政府會存續多久,但是在“后安倍時代”的背景下,日本的 “一帶一路”認知在承襲安倍政府后期“競爭為主,協調為輔”的同時,也面臨諸多變數。
首先,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或將更加置于“印太”視域之中,強調地緣利益的相對性,進而突出“印太”的戰略性而非構想性。菅義偉政府時期,日本在外交領域的重點方向可以歸納為 “印太”外交, 特別體現在 “印太”頻繁出現在日本政府的外交議程中。2021年4月16日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談中,兩國領導人將同盟關系的定位表述為“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并表示“深切關注中國在該地區違背國際規則的活動,包括使用經濟和其他形式的脅迫。”“強烈反對中國在東海與南海單方面破壞地區現狀的行動”。(45)「日米首脳會談」,外務省,2021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18.pdf.盡管為了規避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對于“印太”的戰略敏感性,安倍晉三執政后期將“戰略”替換為“構想”,但種種動向表明,日本近期似乎更加強調“印太”的戰略訴求,力圖發揮日本自身謀劃力,極力推動非正式的“四國安全對話”向正式的“四國聯盟機制”轉變,并以此作為“印太”構想的主體構架,進一步加強對華戰略博弈。
其次,日本將以拜登政府的“價值觀與規則同盟”形成共振為前提,以美日印澳四國的群體收益為戰略基礎,從而擴展“印太”對“一帶一路”的規范遏制。伴隨“四國安全對話”時隔10年之后于2017年的再次重啟,美日印澳四國之間在三年多時間里形成了定期的雙邊、三邊與四邊的互動機制,除了強調“印太”應具備“自由”“開放”之名外,還進一步冠以基于共同價值觀的“包容”,以尋求四國及“印太”地區東南亞國家的價值觀共性,但卻是以“包容”之名,行“排他”之實。除價值觀之外,四國將“以規則為基礎的地區秩序”“基礎設施建設的四大標準”等設置為主要議題,矛頭直接指向南海問題與“一帶一路”在該地區基礎設施領域的布局。(46)陳慶鴻:《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進展及前景》,《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6期。2021年3月,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首先舉行了視頻會議,在鞏固與深化“共有價值觀、基于法治的開放和自由的國際秩序、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國際海洋法、航行與空中航行自由”等規范領域達成共識。(47)「日米豪印首脳テレビ會議」,外務省,2021年3月1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1_000939.html.之后不久,在于日本舉行的美日雙邊外交與國防長“2+2”會議上,兩國罕見指責中國“行動與地區秩序不符,在東海與南海試圖用單方面改變現狀”等。(48)「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日米「2+2」)(概要)」,外務省,2021年3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st/page1_000942.html.9月24日,首次線下召開的四國領導人會議共同聲明提出要建立“美日印澳基礎設施伙伴關系”,為“印太”地區“提供高標準基礎設施”,并重視“對‘藍點網絡’計劃(49)2019年11月4日,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執行總裁大衛·博吉安在于泰國曼谷舉辦的第35屆東盟峰會系列會議“印度—太平洋商業論壇”上,提出了“藍點網絡”計劃。該計劃由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澳大利亞外交與貿易部(DFAT)及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三方共同發起,旨在“統籌政府、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將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標準提至高質量、可信賴的程度”。參見蘇浩、熊櫟天:《透視“藍點網絡”計劃》,《環球》2020年第2期。的繼續參與。”同時還特別指出,“要支持債務可持續與責任追究在內的國際標準與公正、開發、透明的貸款慣例,要求所有債權人都要遵守這一規則”。(50)「第2回日米豪印首脳會合」,外務省,2021年9月2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38176.pdf.在拜登政府上臺后重新強調美國要做“負責任”大國的背景下,日本以鞏固西方規范性利益為前提,積極向以東盟為中心的“印太”國家擴散“共有價值”“地區規則”與“基建標準”,進一步加強對中國“一帶一路”的規范遏制。
最后,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將會繼續基于制度協調以保證自身的經濟利益,但是在拜登政府政策調整的背景下,日本的戰略回旋空間將大大受限。盡管遭受了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但2020年“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進展卻逆勢而上,在非金融類投資領域實現了自倡議提出以來的最大增幅,絕大多數基建項目也復工復產,“一帶一路”繼續彰顯著自身的韌性與可持續性。(51)《“一帶一路”在疫情挑戰中前行》,《光明日報》2021年1月4日。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共有超過3 164個項目與“一帶一路”有關,項目總估值約4萬億美元。(52)Refinitiv: BRI Connect: An Initiative in Numbers, 8 December 2020, https://www.sgpjbg.com/baogao/23668. html.面臨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極大不確定性,日本政府無法實現經濟層面的“去中國化”,2020年11月,日本宣布加入RCEP就是寄希望通過超大型FTA獲取巨大經貿紅利的最好例證。未來,在 RCEP框架下的中日經貿合作與第三方市場合作,中日韓自貿區的進展,以及中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進程將是檢驗日本是否繼續選擇對華制度協調的試金石。但令日本心態愈發復雜的是,盡管拜登政府不會同特朗普政府一樣在經貿問題上施行極端政策,但在利用“印太”地緣工具制衡中國方面,與特朗普政府的戰略目標相差無幾,對中國采取安全與經濟雙重圍堵的戰略決心已成定局。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反建制主義政策已是過去式,但如若中美戰略競爭加速升級,日本對“一帶一路”或將不得改變協調性認知,很有可能延續安倍政府前期的對華制衡戰略。
結 論
綜上所述,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具有非常鮮明的“兩面性”。一方面,日本十分重視在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方面的物質相對收益,以及與西方國家在價值觀與國際標準方面的規范性國家利益,這使得其難以根本轉變對“一帶一路”固有的“競爭性”認知;另一方面,日本對于“一帶一路”的認知也并非一味競爭,日本認識到通過制度協調獲得物質的絕對收益是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日本與“一帶一路”在維護全球性貿易體制、地區制度協調以及“第三方市場合作”方面存在合作的空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與RCEP的簽訂也為日本尋求與中國在上述相關領域的協調提供了機會。
從長期來看,特別在美國拜登政府上臺以及中美競爭不斷加劇的國際格局之下,“后安倍時代”的日本對待“一帶一路”,仍會以“競爭性”認知為主導,“協調性”認知將進一步受限。歷史證明,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安全議題上升的情況下,日本突出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加強“攜美制華”的傾向會明顯上升。盡管日本對中國的經貿依存客觀存在,但現階段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對華的競爭戰略,再加上拜登當選總統意味著美國將重拾傳統的“同盟外交”,與盟友對共有“威脅”進行制衡。拜登政府設想與G7國家推出替代“一帶一路”的“綠色清潔倡議”就是典型例證。(53)Bloomberg: G7 Set to Back Green Rival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Program, June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6-01/g-7-set-to-back-green-rival-to-china-s-belt-and-road-program.不出意外,日本新政府仍將忠實地追隨安倍時期的外交路線,但是孤立中國的政策是不現實的,僅靠包圍相互敵對不能解決問題,如果中美關系出現調整,日本的戰略選擇將十分被動。(54)《“對抗和共生”都應是焦點》,日本《每日新聞》202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