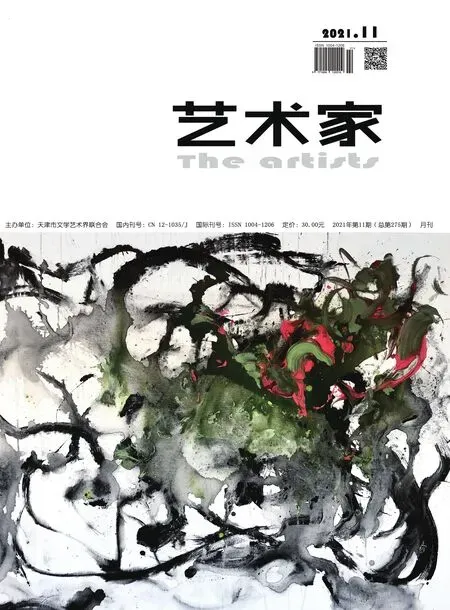亞歷山大技巧融入鋼琴演奏的中國化解讀及運用
□董晨陽 浙江音樂學院
亞歷山大技巧由澳大利亞人費德里克·麥特里亞斯·亞歷山大創造,強調意識對動作的控制和干預,讓人們可以感知肢體在運動中的狀態,并通過意識不斷引導其朝著正確、科學的方向發展,最終實現身心合一。該技巧推出后,迅速被應用于聲樂演唱、器樂演奏等領域,它在緩解心理緊張、肢體疲勞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在鋼琴領域,亞歷山大技巧可以增強演奏者肢體反應能力和感知能力,有效避免身體損傷,使演奏者通過意識和動作的配合達到人琴合一的狀態,讓眾多鋼琴學習者受益匪淺[1]。
一、亞歷山大技巧融入鋼琴演奏的中國化解讀
(一)亞歷山大技巧身心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氣韻觀
亞歷山大技巧提出了以“能量為核心”的身心統一理論,最終目標是達到體態、心態和樂態的完美融合,即演奏者在能量的驅動下身體自然放松,用內心控制自己的動作,達到理想的、符合內心標準的音色效果。對于身心統一狀態的核心——“能量”,亞歷山大技巧中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解釋,而是稱其為“暗默知識”,難以進行量化和定義,只能靠演奏者在多年的實踐中體悟,或是有經驗的教師不斷引導。其實從傳統文化語境下進行考量,能量是“氣”之所在,亞歷山大技巧的身心統一類似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作為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哲學思想,儒、道、釋等諸家各有闡述,內涵十分豐富。僅就其最淺顯的含義而言,對應到鋼琴演奏中,就是演奏者在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下,讓內心意識和肢體行為處于和諧、平衡的狀態,奏出虛實相生、空靈飛動的音色,達到物我兩忘的狀態。在鋼琴演奏中,貫穿整個過程的正是“氣”,演奏者可以通過“氣”來調整樂曲的節奏,獲得強而不響、柔而不屈的音色效果。可見,亞歷山大技巧身心統一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二)亞歷山大技巧實踐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觀
亞歷山大技巧在具體的鋼琴演奏中,對演奏者提出了諸多明確要求。首先,其提倡自我審視與革新,通過對自我的長期觀察,不斷反思和完善;其次,要求演奏者積極面對現實困難,查找原因并克服。亞歷山大技巧認為,所有演奏者都會出現緊張的問題,逃避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只有勇于面對并不斷豐富個人的實踐經歷,才能有效避免緊張。再次,亞歷山大技巧強調演奏者對個人的嚴格要求。如演奏者不能從事劇烈運動,以免造成肢體損傷,影響演奏效果。最后,亞歷山大技巧強調“適當抑制”,即演奏者在學習過程中可以刻意放慢速度或停頓,這是一種“建設性休息”,再次投入學習時則會充滿力量。以上諸多針對鋼琴演奏實踐的主張,其實都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中有所映射,其提倡的自我審視與革新,與“自省吾身,知錯改過”的省思文化是一致的,它們都主張通過自查來趨利避害,揚長避短。亞歷山大技巧鼓勵演奏者勇敢面對挑戰和困難,對應《論語》中的“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其強調的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對應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的“慎獨”,即在獨處時不僅要克服恐懼和孤獨,還要嚴于律己,這是自我完善的必要過程。其闡釋的“適當抑制”和“建設性休息”,其實就是老子的“以退為進”,看似是一種后退,其實通過積極地調整,實現退一進二。
(三)亞歷山大技巧形體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禮樂觀
形體論是亞歷山大技巧的基礎,其在形態上對鋼琴演奏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首先,演奏者應該建立儀式感和敬畏之心,演奏時要嚴格遵照不同環境的禮儀要求,從著裝到動作都要與環境相契合。其次,演奏者應盡量采用“外凸式”的演奏姿勢。這是一種盡量減少脊椎生理曲度,讓身體自然舒展的狀態,像是要擁抱別人的感覺。再次,亞歷山大技巧強調鋼琴演奏對個人修養的提升。其認為演奏者的動作其實是修養的外化,演奏者應提前對動作進行設計,給觀眾以視覺和聽覺的雙重享受。
亞歷山大技巧在形體方面的一系列主張,與中國的禮樂觀有著諸多相似之處。首先,從“禮”來看,在孔子看來,音樂學習對一個人的成長有著決定性作用。這與亞歷山大技巧強調的“演奏者要重視儀表,要對鋼琴藝術有敬畏之心”是一致的。其次,從“樂”來看,中國重要的古代音樂典籍《樂記》中曾提出了“禮樂相合”的主張。其中“禮”是要遵守的秩序,“樂”是情感表達的載體,“禮”既不能“過制”,也不能“過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身體和音樂的完美結合。這與亞歷山大技巧中提倡采用“外凸式”演奏姿態,注重個人修養的提升是相通的。
二、亞歷山大鋼琴演奏技巧中國化運用
(一)對演奏狀態的科學分析
亞歷山大技巧最突出的特點是強調并揭示了思想和身體的緊密關系,演奏者在充分認知自身形態條件的基礎上,用意識支配動作,達到心目中理想的效果。在此基礎上,還開發出了“身體感官地圖”,詳細闡明了身體部位和器官會對動作產生的影響和效果。這一點是中國鋼琴演奏者較少關注的領域。
事實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此有著明確論述。古人根據陰陽五行理論,把五音與人的五臟和五志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即五音配五臟,五臟配五行,五行配五志。可見,意識和動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很多演奏者自認為得體、舒適的演奏狀態其實是一種錯誤的狀態,即亞歷山大技巧中提出的“身心的惰性”。狀態正確、科學標準不在于演奏者的感覺,而是在于演奏能量的來源是否正確,能量傳遞是否通達。做到了這一點,演奏者自然也會感到舒適自然。在樹立這種演奏思維后,演奏者在演奏實踐中還要持續思考,讓自己的知覺越來越敏銳和準確,在這種狀態下的演奏效果才會更加細膩,更加具有個性化風格。
(二)對演奏過程的全程把握
亞歷山大技巧強調的心理、身體和音色的完美融合,其實是一種對演奏目標的追求。對此,演奏者可以結合傳統文化,對這個目標進行解讀和階段性細分。心、身、樂的積極調整和有機統一,其實就是由適而樂—適人之樂—自適之適—忘適之適的過程。由適而樂是指在鋼琴演奏前演奏者自然、放松的情緒和狀態。適人之樂即亞歷山大技巧中強調的自我探索能力。演奏者要思考和嘗試怎樣才能呈現出最理想的演奏效果。其中包含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對現場演出環境是否熟悉、有可能出現哪些突發問題等。自適之適代表著和諧、通暢的演奏狀態。對此,亞歷山大技巧提出了兩種通道。一是音符通道,即音符與音符之間的連接與發展。要求音符之間要像小溪流水一樣自然,輕重疾徐盡在演奏者的把握。二是身體通道,演奏者的身體各部位都要處于積極的響應狀態,在各司其職的同時又組成一個整體。打通了以上兩個通道,演奏便成為一個自然的情感抒發過程。忘適之適對應的是亞歷山大技巧中音樂自由精神的傳達和人的自主權的彰顯,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意境。演奏者全身心投入演奏中時,便會忘掉自己是誰。自己是作曲家還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演奏者一時也難以分辨。這種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審美體驗,正是中國傳統審美中的最高層次——意境。
(三)對演奏效果的正確認識
亞歷山大技巧中提到的“抑制論”和“建設性休息”,其實是對演奏者心態的建議。演奏者在演奏過程中,特別是在遇到困難時,要積極調整心態,以退為進。對此,演奏者要結合亞歷山大技巧的要求,從傳統文化中的“無色無相、遠離執念”方面進行思考。首先,演奏者要通過對自己的清醒認識,果斷放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無法之法”。鋼琴演奏對演奏者的文化修養、演奏技術、音樂素質等都有著明確的要求,演奏者可以通過積極的訓練實現某種目標,但是當受到客觀環境的限制時,也要主動放棄。這并非退縮,而是對自身能力合理評估后的明智選擇。其次,演奏者要主動緩解練習中的焦慮心理。很多演奏者在練習過程中一遇到困難就會出現焦躁情緒,并不斷反問自己:為什么總是彈錯?為什么練習了這么久速度還是上不去?對此,一方面,演奏者要認識到任何高質量的演奏效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必須經過一個長期、曲折和反復的過程,過分的緊張和焦慮只會欲速則不達。另一方面,演奏者要將亞歷山大技巧中的“人琴合一”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無雜念”相結合。演奏者之所以出現焦慮,是因為在演奏過程中經常出現錯誤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而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心手不一,身體各個部位沒有形成有機配合。演奏者要心無雜念,全神貫注于音樂本身,而不是僅依靠理性分析和邏輯記憶來演奏,這樣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對于整個演奏的投入,也盡可能地減輕了焦慮情緒[2]。
結語
綜上所述,演奏者運用亞歷山大技巧進行鋼琴演奏之所以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原因就在于沒有從中國傳統文化視角下進行審視和思考,使運用變成了簡單的模仿,自然難有成效。因此,演奏者要主動思考亞歷山大技巧和中國文化的相通之處,對其進行民族化的詮釋和探索,使其真正符合中國鋼琴演奏者的思維方式、身體特點和審美追求,從而使該技巧的價值和意義得到最大化地展現和發揮,這也是對該技巧的擴展與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