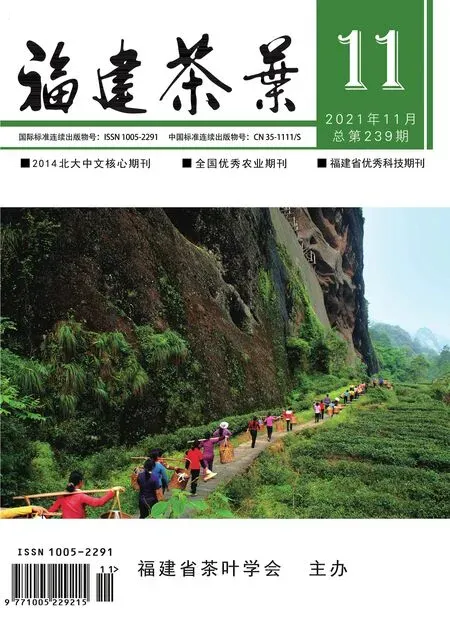試析中國傳統文人畫與“茶禪一味”的精神暗合
董朝陽
(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北京 100048)
中國的種茶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傳說時代的神農氏時期,迄今已有四千余年的發展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所衍生出的茶文化時刻流淌在華夏民族的血液里,連綿不絕,歷久彌新。茶之興“始于唐,盛于宋”,它所孕育出的情感特征以及精神價值仍然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回溯中國繪畫史,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文人畫的發展亦同步于茶文化的繁榮。佛教崇尚飲茶,有“茶禪一味”之說。《趙州錄》記載:“師(指唐朝趙州和尚)問二新到(僧):上座曾到此間否?云:不曾到。師云:吃茶去!又問那一人:曾到此間否?云:曾到。師云:吃茶去!院主問:和尚,不曾到教伊吃茶,即且置;曾到,為什么教伊吃茶去?師云:院主!院主應諾。師云:吃茶去!”這就是禪宗歷史上著名的趙州和尚“吃茶去”公案。宋代高僧圓悟克勤以禪宗的觀念和思辯來品味茶的無窮奧妙,揮毫寫下“茶禪一味”。
1 純化感覺,跡化情感
魏晉佛教、清談之風興起,品茗飲茶之風日盛,入宋之后,文人士大夫以茶會友,品悟人生之道,茶則可以幫助士子們得以精神慰藉。北宋詞人蘇東坡有茶詩:“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便是將茶與禪生動的聯系起來。文人繪畫自唐宋以來不斷演進發展,“不求形似,平淡天真”逐漸成為文人士大夫作畫的審美規范,然茶禪之境在體心在開悟,純以感覺,跡化于心靈升華,文人畫與禪茶頗多相似之處,二則詩畫結合,耐人尋味。在文人畫中不乏以描寫茶事活動為創作主題的繪畫,如宋趙佶的《文會圖》,元錢選的《盧仝煮茶圖》,明唐寅的《品茶圖》,清石濤《墨醉圖》以及近代畫家齊白石的《煮茶圖》等皆以茶為主題,輔以茶詩,可見茶已經滲透到文人墨客的哲思之中,借茶書寫胸中逸氣。其中唐寅在《品茶圖》中有一題詩:“買得青山種此茶,峰前峰后摘春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蟹眼松風娛自嘉。”不難窺探到畫家向往田園的心境,借茶明志、品茗修身,以求豁達自信的人生態度。茶禪與文人畫看似為不同文人士大夫修行體悟的審美載體,實則均有溝通物我兩境的審美機制。一方面,茶,品人生百態;畫,繪宇宙沉浮。二者都強調“開悟”,茶之為物,修身養性,“君子愛茶,茶性無邪”,畫之唯情,以求蘊藉,文人畫亦借物抒情,撩撥胸中所思所悟。另一方面,禪茶一味與文人畫皆具形而上化的哲學意味,反映出文人對于人生意義的解讀,探尋日常生活之外的精神場域。
2 “茶禪一味”與文人畫的精神暗合
2.1 脈脈禪境與悠悠哲思
在中國傳統繪畫體系中,文人畫有著別具一格的觀察方式,之所以“別具一格”,是由于它所呈現出的悠悠哲思天然上則蘊含著一種溫存的、人道的生命意識,它所凸顯的藝術氣質亦具有一種人性的光亮。正如朱良志在其文章《傳統文人畫的人文價值》這樣寫到,“文人畫的哲學思考是它的人文價值顯現的基礎。重要的不是藝術家留下的畫跡,而是伴著這些曾經出現的畫跡所包含的創作者和接受者的生命省思”。在中國,茶與禪結緣歷史悠久,佛教中僧侶們借茶苦修,禮佛參禪,便是體悟一種“空”的世界,這種“空”并不是沒有,而是通過“格物”去體味大千世界,正如佛語所講“一沙一世界,一葉一菩提”。雖然這種“空”的境遇與文人畫所強調的生命省思在呈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都是通過“格物”去把握“禪機”,文人畫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同樣有著滲透心靈的清靈意識。
茶與禪是中國茶文化所衍生出的心靈溝通的精神載體,茶禪背后所體現出的文化精髓既是物質與精神的和諧統一,又是人與物對話的媒介。由茶所體悟的脈脈禪境一方面擺脫了塵世的紛擾與冗繁,凈化身心,明心見性。另一方面在自省中體味一種超然物外的閑適、通達的人生態度。誠然,文人畫所強調的精神性意念一是通過既定的繪畫題材、故事進行寫照,二是借助筆墨意趣傳達時間性和生命意識。茶禪一味與文人畫在精神觀照、審美趣味等方面既有“格物”所通向的生命真實,又有智慧性的思考與哲問。
2.2 應以懷古與隱逸志趣
文人畫又稱“士夫畫”,是古代文人士大夫聊以自娛,抒寫胸中逸氣的重要表達方式。當然,文人畫在其中所抒發出的懷古之意以及隱逸志趣亦是文人們逃避塵世紛擾、追求內心寧靜的真實寫照。元朝畫家趙孟頫在文人畫上標榜古意,有“畫無古意,雖工無益”之談,從中便能窺探其懷古之心態。元朝是中國文人畫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嚴苛,漢化遲滯的時代,文人隱遁避世,追尋內心閑適的生活狀態。元朝畫家趙原在其作品《陸羽烹茶圖》的題記中寫道:“山中茅屋是誰家?兀坐閑吟到日斜。俗客不來山鳥散,呼童汲水煮新茶。”從一個側面反應出元朝社會的政治生態,同時也折射出當時文人士大夫的隱逸懷古的精神世界。佛家遁世修行、日常參禪,在飲茶中對治昏沉,感受清修的內涵。誠然飲茶已不僅僅是一種日常化的生活關照,也具備了一種智慧性的哲理化思考。一言以蔽之,“茶”是內心與佛法溝通的媒介。唐朝趙州和尚“吃茶去”這段公案便是“茶禪一味”最好的注腳,更是借茶言志而觀自在心,飲茶修身,以此回應人生的課題。黃蘗希運禪師云:“終日吃飯,未曾嚼得一粒米;整日行,未曾踏得一片地。”佛教在茶的澀澀清香中感受精神世界的虛空之境,這“空”之境便是禪茶之境,禪者飲茶意不在茶,其背后通達清凈之心在于隱逸懷古。
3 明心見性,澄澈空明
明心見性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人畫和茶文化所強調精神意涵的重要寫照。明心清心是文人畫在傳達個人心境,舒放人生性靈的前提之一;茶禪之境意在清心凈心,就如學者葛兆光在其文《茶禪閑語》所寫那樣:“禪家多‘吃茶’,正在于水乃天下至清之物,茶又為水中至清之味,文人追求清雅的人品與情趣,便不可不吃茶,欲入禪體道,便更不可不吃茶,吃好茶。”神會和尚所謂“不起心,常無相清凈”便是對清心凈心的令一種闡釋。
在中國,儒、道、釋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合發展也促成了茶與禪超越物質媒介而具有一種永恒的人文精神。茶禪文化在中國所凝練出的精神價值一則是茶與禪結緣以來,兩者之間的人文情趣已然脫離生活本身的意義上升為一種審美情感;二則禪茶所體現出的清修之境實能實現精神的釋然,心靈的凈化。這些皆與文人畫有著精神的暗合。明朝畫家文征明《茶具十詠圖》以詩書畫結合的方式描寫了空山寂寥之境中一隱士獨坐凝思,有一茶童烹茶的場景,反映出畫家寄情山水,遠離世俗紛擾,追求內心寧靜的閑適生活。陳洪綬的《停琴品茗圖》以雅氣十足的珊瑚石、蓮花、爐火等來渲染高古空淡的環境,兩位高士琴弦收場,相對而坐,香茶間進,品茗論古。如此空谷優雅之境,將人物內心的隱逸情調以及文人清心明澈的品茶習俗躍然紙上,同時茶的清淡、蓮的高潔也暗喻了作者凈心獨處時澄澈空明的人生態度。近代畫家豐子愷以明朝園信的《天目山居》中的“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茶。”為題描繪了一隱士僧,獨坐山間屋舍,吃一苦茶,便有“悠然見南山”,他以群山為伴,靜心、凈心、明心。不難發現,文人畫中茶與禪,茶與詩的結合亦契合了中國古人所追尋的淡泊自然,尋求平常心的清凈心境。這也是文人畫借助茶文化獲得精神寄托,體悟人生之道的另一種審美機制。
綜上所述,中國茶文化所體現出的“茶禪一味”與文人畫兩者之間的精神性表達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生活的煙火氣而具有一種形而上化的哲學意味。茶與禪、茶與畫、茶與詩在融合過程中早已超越物象本身從而具備了獨特的藝術審美形式。茶禪文化與中國傳統文人畫的精神暗合不僅豐富了文人墨客的內心世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所凸顯出的人文價值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