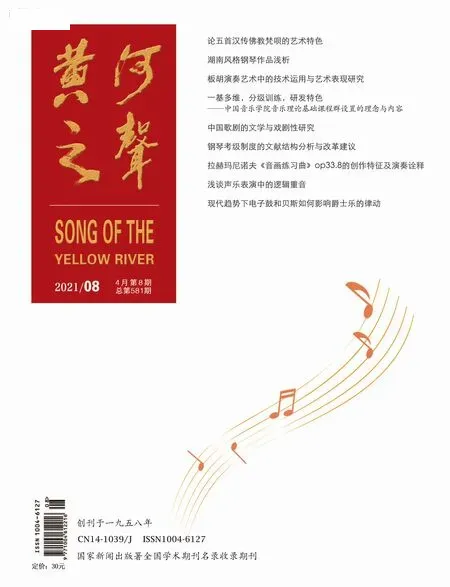文化自信背景下探索巴山“背二歌”傳承方式研究
肖 珺
文化自信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七一講話中指出的,堅持文化自信,就是堅持中國特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也多次談到中國傳統文化,表達了對傳統文化思想和價值的尊崇。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成員之一!本文通過探索巴山“背二歌”這一傳統民間文化的傳承方式,使我們優秀的民間傳統文化得以繼承發揚光大!
“傳承”是一種文化藝術形式在代與代之間不斷傳遞、承接的意思。任何一種文化形式都會涉及傳承的問題。民間音樂自然不會例外。傳承方式即傳承所采用的方法和形式。由于“背二歌”在古今不同時代演唱的生態環境已發生了很大變化,那么,它的傳承方式勢必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要掌握其傳承的真實情況。就需要先從歷史階段的不同分為傳統傳承與當代傳承兩種情況來考察。這兩個時期的傳承方式有諸多不同特點。
所謂傳統傳承,指無公路(大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時期,此時期還存在山路人力運輸的勞動形式,其傳承的方式主要是脫離勞動場合的家族式和結合勞動環境的剽學式,前者是一對一的私傳方式,后者是多對一的模仿學習方式。而當代傳承,指有公路(大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不久)時期,此時期由于公路修建起來,原有的人力運輸方式不復存在了。因而其演唱和傳承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其傳承方式主要有一對多的師徒式與社會化教唱的公傳方式。以上兩個時期傳承方式的共性聯系是都用口傳心授的民間方式,尚未運用依據樂譜教材傳承的方法。下面分別論述之。
一、傳統傳承方式:家族式和剽學式
論及民間音樂的傳承方式,2002年以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口傳心授”乃其主要傳承方式。之后,蒲亨強教授發表論文《剽學—值得注意的民間音樂的傳承方式》,自此,對于傳承方式的認識又多了一個途徑,那就是“剽學”,即偷聽模仿而學的方式。那么,對照巴山“背二歌”的傳統傳承方式,大致有“口傳心授”的家族父子式與勞動場合的剽學式兩種,下面分別分析概述。
(一)家族式傳承——以代表人袁吉芳①為分析標本
家族式傳承是常見的一種傳承方式,以“口傳心授”的形式居多。自古以來,很多的民間藝人為了自己的手藝不被外人傳去,一般他們都會以“口傳心授”的方式,把自己的技藝傳授于自己的長子或次子。據考證,巴山“背二歌”的傳承,最開始也是這樣一代一代把“背二歌”流傳下來的,以前的背二哥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背二哥”。這個現象從傳承人袁吉芳講述他的身世就可以得證。袁吉芳打小就生活在大巴山偏遠的農村。據本人講,解放前,由于家里窮他在南江縣城靠背運貨物為生,爺爺和父親都是當地有名的“背二哥”,父親是舊社會的老高中生,文人、讀了些許書,經常在家中教他唱山歌和背二歌。他父親活到97歲,現已去世。他現在掌握的大量背二歌,很多就是從他父親教授中學來的。至今,袁吉芳唱歌的熱情仍不減當年,在采訪過程中,筆者發現,袁吉芳的女兒也特別愛唱歌,尤其“背二歌”唱的好。袁老激動的說,“我女兒像我,她的歌都是從我這么學的,現在我老了,再過幾年就唱不動了,我就是想讓背二歌一代一代傳承下去,不至于消失。”可見,家族式傳承在當代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剽學式傳承
所謂“剽學”就是偷聽旁聽而學,即“基于興趣動機的,采用偷聽模仿式的,教學關系、內容、目的、場合、時間極其靈活自由的傳承方式”,無固定的師父和學樂方式。據袁老講述,雖然他在爺爺和父親的私傳中學會了不少民歌。但另有相當多的歌曲,則是他在勞動場合旁聽其他非血緣關系的背二哥長輩們唱時,自己模唱而習得的。這就是一對多的“剽學”方式。1964年他在南江縣東榆鎮響水村參加集體生產,開始隨祖輩們從事長途背運,他自己也成了背二哥。在往返于川陜兩地的運輸途中,當背累了打杵歇氣時,背二哥長輩們都會吼上一曲“背二歌”,立刻感覺渾身是勁,一口氣直沖山頂。他在聽長輩們唱時,很感興趣,就偷偷跟著學,久而久之,也唱得一手好歌了。由于袁吉芳本人自幼熱愛唱歌,也頗有音樂天賦,逐漸成長為一個著名的歌手,以唱“背二歌”而遠近聞名,成為一個重要傳人了。袁吉芳成為歌手的成長道路典型地反映了傳統傳承的基本方式和特點。從中可以得到兩點重要啟示。其一,歌手在他學習傳承的經歷中,并不單純運用一種方式,而是兼用了家族私傳和剽學兩種方式。通過多種方式學習傳承,這應該是過去民間歌手學習音樂的普遍規律吧。其二,一個民間歌種的世代傳承過程中,有突出才能的傳人往往起著關鍵的作用。這類傳人具備一些特殊的品質,比如,酷愛唱歌,音樂已成為他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愛好。在我采訪過程中,不論袁老走到哪里,只要有人喊他唱,只要有幾個聽眾,他就會非常投入地唱起背二歌來,完全旁若無人的狀態。他唱歌完全沒有功利的希求,只是為了抒發自己的感情,希望更多的人來欣賞。可見,他是多么熱愛民歌啊!又如,具備相當程度的音樂素質,也是很重要的。像袁老,從來沒受過專業教育,更沒專門學過音樂技術,但他唱歌音準節奏都很好,而且充滿表現欲和激情。這就只能歸結為他具有一定的音樂天賦了。這些品質,也正可解釋,為什么大量的人民都會唱歌,但真正唱得好的,能成為傳人的則屈指可數。從這樣的研究結論中,我們還得到另一個重要啟示,在當代繼承保護優秀音樂遺產的工作中,重視和保護好代表傳人,給他們創造更好的傳承條件,是至關重要的。
二、當代傳承方式:師徒式與社會化傳授
當代傳承方式發生了諸多重要的變化,最突出的是,出現了師徒式與社會化傳授的方式。下面分別論述。
(一)師徒式傳承
“師徒式”傳承,指傳承音樂過程中,已有明確的師徒身份關系區別。教與學雙方都有明確的對象,形成了清楚的師承關系。徒弟要拜師學藝,師傅只傳授技藝于徒弟,均可稱之為師徒式傳承。這就改變了傳統傳承中父親與兒子的關系,也改變了剽學中模仿而學,并無明確師徒身份的格局。如筆者采風過程中曾問及袁老是否有師傅教唱民歌,袁老講述,文化大革命以后,到各地參加比賽,曾拜有兩位老師,都是南江縣文化館的老館長,一位是何文浩(已故)、鄭開江(71歲,已退休)。他說,這兩位老師主要從歌唱方法上對他進行了培訓,教他如何正確發聲,如何對歌曲進行處理。如:巴山“背二歌”最后一句甩腔,不能唱的太弱,必須要符合此時歌者的心境,必須長吸一口氣,把“耶-嘿!”嘆上去!經這兩位老師處理的歌曲,他提高了演唱技能,后來去各地參加比賽就他得到更多好評,獲得了很多獎。他心里非常感激師傅的教導。在近些年來,為了推廣普及背二歌的演唱范圍,袁老自己也開始招收喜歡唱歌的青年人當徒弟,教他們唱歌,他自己也當起了師傅,成為新的師徒傳承人。
(二)社會化傳授:建立傳習所
在背二歌演唱的生態環境不復存在的社會條件下,如何將它有效地傳承下去,已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大問題。好在這個問題同時得到代表傳人和各級文化部門的重視。由此,逐漸建立起社會化傳授的思路和機制。這種機制的形成,首先得力于代表傳人將“背二歌”世代傳承下去的強烈愿望,其次,也得到政府部門和廣大群眾的大力支持。近年來,在袁老和一批傳人的呼吁和身體力行中,利用背二歌已產生的藝術影響和社會力量的扶持,在當地借用寺廟場地,掛牌建立了“巴山背二歌傳習所”,由袁老主持教學活動,免費招收周邊熱愛唱歌的婦女和青年人,每天下午到所內演唱各種民歌,并由袁老親自指導教唱,儼然像一個音樂課堂,人們都興致勃勃地參與學習和演唱,使“背二歌”音樂走向社會,形成了良好的傳承氛圍。此外,當地政府在開發旅游文化時,也有意識地將背二歌演唱納入到景區文化活動中。背二歌代表傳人也經常到景區為游客演唱,在豐富景區文化項目的同時,也將“背二歌”向更廣大的人群宣傳和傳承下去。
三、傳統傳承與當代傳承的異同
傳統與當代的傳承方式各有不同,其差異主要表現在結合或脫離原生的勞動環境,由此引發了在傳承方式上的一些差異。雖然有這些差異,但作為一種音樂藝術形式。依靠于代表傳人的有機傳承,當代背二歌仍然保留了其詞曲上的傳統特色仍然在口頭傳承。
(一)傳統傳承的實用性與情感性
傳統的巴山“背二哥”產生于“無公路時期”,時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的漫長歷史年代。這個時期山區還未建設公路,才可能產生這一人力背運過程中的特殊民歌,它是實用性與情感性交融的產物。所謂實用性即體現在背二哥們在翻山越嶺販運物資時非常勞累,休息時唱起這種歌,有解除疲勞、鼓舞干勁、提高工效的功能。因此它原來目的是很實用的。與此同時,在實用功能之外,“背二哥”們在打杵歇氣時唱起這種歌,也有消除煩悶、愉悅心情的沖動,這時情不自禁地吼唱山歌,也就具有了自由抒發情懷的情感藝術功能。這樣,就在實用性與情感藝術形態的交融中產生了“背二歌”這種特殊形式。境時,人們也把它作為一種純藝術形式在運用。在傳統時期,背二歌既是實用與藝術融合的形態,但更多還是一種藝術形式。
(二)當代傳承的藝術性與表演性
我們在當代所能聽到的“背二歌”,實際上是從新中國建立后“通公路時期”的純藝術形態的“背二歌”,由于已經脫離了長途運輸的特定環境,只能依靠一些傳人將它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而傳唱。這些歌雖然已經脫離了勞動環境,但由于傳承人的父輩或祖輩都唱過或聽過傳統的“背二歌”,他們本人也不同程度地參加過這種勞動歌唱,所以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其傳統的音樂特色,我們在當代,仍然能欣賞到這種獨特精神產品的美。應該歸功于這些熱愛民歌的傳人,他們現多年事已高,如果再不注意保存和傳承,這一寶貴財富將永遠消失。這種當代“背二歌”雖已不與勞動場合結合,但這些傳人非常喜歡唱,經常參加縣里、市里參加各種比賽,使得“背二歌”的傳統特色得到發揚。讓更多的人們了解它的美,具有特殊的審美價值。事實上,據民歌手袁吉芳講述,他幼年時聽到父親在家中休息時也不時唱起“背二歌”,說明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的傳統時期,“背二歌”在勞動中唱,在脫離勞動環境。但由于傳承人的父輩或祖輩都唱過或聽過傳統的巴山“背二歌”。他們本人也不同程度地參加過這種勞動歌唱,所以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其傳統的音樂特色,我們在當代,仍然能欣賞到這種獨特精神產品的美。應該歸功于這些熱愛民歌的傳人,他們現多年事已高,如果再不注意保存和傳承,這一寶貴財富將永遠消失。這種當代“背二歌”雖已不與勞動場合結合,但這些傳人非常喜歡唱,經常參加縣里、市里參加各種比賽,使得“背二歌”的傳統特色得到發揚。讓更多的人們了解它的美,具有特殊的審美價值。事實上,據民歌手袁吉芳講述,他幼年時聽到父親在家中休息時也不時唱起“背二歌”,說明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的傳統時期,“背二歌”在勞動中唱,在脫離勞動環境時,人們也把它作為一種純藝術形式在運用。在傳統時期,背二歌既是實用與藝術融合的形態,但更多還是一種藝術形式。當代背二歌,嚴格地說,正繼承了傳統時期純藝術的形態。含混地將當代與傳統時期的“背二歌”視為一物是不對的,這會使我們看不到歷史真相。但認為當代“背二歌”與傳統“背二歌”是兩個東西,也是不正確的,它會使我們看不到歷史與當下的有機延續性,從而不能認識傳統與當代“背二歌”的特色和當代意義。■
注釋:
① 袁吉芳,現年60歲,巴山“背二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