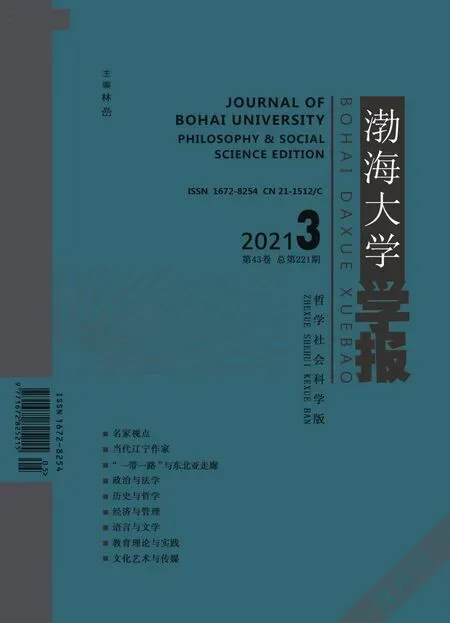叩開文明之門的動力系統
雷廣臻(渤海大學,遼寧錦州 121013)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紅山文化等以歷代累積的用火技術、和合泥土燒制陶器的成就、筑巢(筑屋文化)的進步、解決食物問題對生業方式的拓展、完備服飾增進人的“禮儀體面”、祭祀禮儀的形成(事鬼)、“旁羅日月星辰”“知幽明”“通神明”創制的歷法(事神)和使用銅器等形成基礎,成為文明進步的一個個里程碑,形成了新石器時代集大成的文化高峰,叩開中華文明之門。后代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天地人、日月星、四時序、鬼神祀、衣食住行、心物合、禮儀、敬天法祖等,均在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中體現出來。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紅山文化等社會發展的動力系統是什么?這是本文研究的主題。
動力,泛指事物運動和發展的推動力量,本文指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呈同一性,創造了輝煌的文明成就,必有動力系統存在其中。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動力系統主要有復合工具子系統、復合思維子系統和抽象思維子系統,文化的交流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一、復合工具的普遍制作和使用成為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紅山文化等發展的根本動力
工具,泛指人類從事勞動、生產的器具。在制作和使用工具方面人類與動物分野,這一觀點并沒有過時。我們知道,有的動物會把身邊的物體當作工具,如有研究者觀察黑猩猩會用薄樹葉做成釣白蟻的工具。有時黑猩猩會使用草葉、木棍等多種不同類型的工具,這并不奇怪。人類在初始階段也像黑猩猩會把身邊的物體當作工具,也會使用草葉、木棍和石塊等多種不同類型的工具,當然也會制作工具。但人類很快超越了簡單制作和使用單一工具階段,較快進入了更高級的制作和使用工具階段,即制作與使用復合工具階段。由此人類在制作和使用工具的此階段與動物最后分野。
工具做功系統一般分為三個子系統,即動力系統、動力傳遞系統和做功工具。加工對象雖然在工具做功系統之內,但本文不做研究。工業革命只是改變了動力和動力傳遞的方式及工具的復合程度,而沒有改變工具做功系統及其三個子系統的合成結構。信息時代也是如此,信息也需要動力、動力傳遞及做功“工具”。
人們最初使用單一工具。今天常見的有使用石塊和加工石塊而成的石斧。石塊和石斧就是人們的工具,但是單一的工具。單一工具的特點是單一而未與其他工具組合,從物體上不可再劃分。此階段使用工具的具體形式是人握石塊,直接做工或投擲出去,作用于勞動對象。工具是單一的,動力也是單一的,動力與工具之間是簡單、直接的傳遞。
人類逐漸把單一的生產工具發展為復合工具。人類經過長期摸索,發明了用綁扎、黏合等方法,把不同物質材料制成的幾個部件組合成一件工具,這就是復合工具。弓箭是較早的復合工具。弓箭的制作和使用改變了動力、動力傳遞與工具的關系,成為一種成熟的復合工具的運用體系。早在距今3 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中國境內的人類就開始使用弓箭了。早期的弓箭用一根竹竿或樹棍,截成箭桿,一端削尖。嚴格說來這不算是成熟的復合工具的運用體系,但以此技術為基礎,人們逐漸把骨片、貝殼或石片磨制成鋒利的形狀,安裝在矢桿一端,制成了骨鏃、貝鏃或石鏃的弓箭(當今出土的實物往往僅留下箭鏃,那是箭桿沒有保留下來的緣故),用弓發射出去。有韌性的弓弦與有彈性的弓臂構成弓,直接做功的箭頭、箭桿也要組合在一起成為箭,而且弓與箭組合在一起做功。這就告別了以往工具的單一性。也就是說,弓箭從物體上已經可以區分為弓弦、弓臂、箭頭和箭桿等部分。此時,不僅工具不是單一的性質,動力傳遞也不是人直接作用于工具,而是間接地作用于工具。當人們用力拉弦迫使弓體變形時,把自身的能量儲存進去;松手釋放,弓體在迅速恢復原狀的同時,把儲存的能量立即釋放出來,從而將搭在弦上的箭強力地彈射出去。這一過程,人力改變物體形狀彈性,從而將彈性勢能轉化為動能。動力經過轉換而傳遞,工具已經是復合系統。應當指出,復合工具產生之后,單一生產工具并沒有被淘汰,仍然保留下來,這是人類的好習慣。人類經常是在發明新工具的同時保留下舊工具,使隨著發明不斷遞進的生產工具呈現出歷史性和層次性。
上文已述,復合工具的出現當在舊石器時代,但復合工具的普遍使用則在新石器時代。北京東胡林、浙江上山和小黃山等遺址及興隆洼文化、裴李崗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盤、石磨棒,石磨盤與石磨棒組合成一種復合工具。一些考古學文化出土的石鋤、石犁等都是捆綁在木柄上使用的,成為另一種復合工具。為石斧裝上柄,為石鋤、石犁等捆上木柄,把不同的東西組合到一起形成復合工具而做功,功效大增。
從新石器時代若干遺址中發現了骨柄石刃刀。紅山文化系列發現了多種骨柄石刃刀。以骨器為柄,以石器為刃,二者組合,即為石刃刀裝上柄,形成了細石器與骨柄組合的新型復合工具。人們把細石器鑲嵌在骨槽里做成的骨柄石刃刀,是一種極具特色的復合工具。
原初的骨柄石刃刀用的石刃是燧石類,后來在骨柄上固定了三片至四片瑪瑙刀片,切皮、割肉鋒利異常、輕便快捷。渤海北岸小河沿文化的骨柄石刃刀有了新的改進,在骨柄槽內填充了黑色膠質物質(結構要素),進一步把骨柄與石刃粘接牢固。
復合工具一旦在社會占有基本動力地位,由復合工具帶來的思維方法會把復合工具應用于新石器時代的其他相關領域,復合工具思維和方法會支配社會的各個方面,到處可見“物”的組合。如諸多考古學文化居住區的道路、壕溝、中心房屋、周邊居室、灶、灰坑和門道等形成合理的空間結構,多室與單室組合,石塊、泥土、木草與木柱建筑材料密切結合,所建的半地穴式房屋,地上部分與地下部分組合。河姆渡文化形成了獨特的卯榫結合技術。諸考古學文化的陶器形成了新的組合:飲食所用的缽和碗,炊煮所用的罐和釜,汲水所用的壺和瓶等形成獨特組合,旋渦紋、幾何紋、龍紋、魚紋、花紋、谷穗紋和八角星紋等形成裝飾藝術的組合。有的陶器形成了人的形象與其他要素的某種組合。
考古人員在渤海北岸的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營子二道杖房大南溝小河沿文化遺址發現了距今4800—4300年的數件臂環飾。有三只臂環飾結構分為三層,內層襯有織物,涂黑色膠體,粘上數行小蚌珠。這是用膠體組合的復合式臂環。
復合工具實質上是一種組合工具。使用組合而成的復合工具,人們做工的力度、范圍和效率都加大了。復合工具標志著生產力發生了革命,為新石器時代發生重大變革和進步提供了主要動力,也為新石器時代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新石器時代之所以走向文明也主要依賴于復合工具的普遍創造和使用。
復合工具普遍制作和使用的意義不僅表明復合工具是一個偉大的進步,而且表明復合工具的普遍創造和使用本身是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分水嶺,復合工具標志了新石器時代的基本特征。這涉及新石器時代的根本特征等重大理論問題。今天看來,以往以磨制石器的出現等作為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特征,已經缺乏說服力。磨制石器的出現是某種力量作用的結果,是一個過程的結果,而不是力量和過程本身。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特征應該從“動力”上找,因此把復合工具的普遍創造和使用看作是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特征,更便于揭示新石器時代的本質特征。
二、復合(組合)思維是推動新石器時代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
從根本上說,復合工具改變了人們的思維,形成復合(組合)思維,為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力量。組合的精神力量發揮作用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空間上不同結構要素從而組合、創造了新事物;二是深度上思維不斷抽象化使社會和思維更加有理性。
紅山文化等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到處都呈現了復合工具及復合工具思維所帶來的變化。人們懂得了不同物體可以組合成為另一個物體,組合(復合)思維由此產生并且延伸開來,在社會生產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復合工具而產生的復合思維的主要特點是告別了單一性思維,形成了組合性(復合)思維,并且在組合思維的作用下形成了組合“實踐”。古人用石器(包括玉器)、陶器和木器等創造出了異形人、異形動物。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有許多出土遺物,把人與動物的肢體、器官移位組合,如把人的肢體加到獸、鳥和蛇等動物身上,或把獸、鳥或蛇等動物的器官移位組合到人身上。這是上古人類的一種組合性“實踐”,也是社會進步帶來的普遍的“心靈手巧”的表現(表明了技術和工藝的進步)。
出土于遼寧省朝陽市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雙鸮玉佩,兩端雕琢對稱相同的鸮首形象。鳥獸紋玉佩也是一種異形組合玉器,佩體依其造型的外部輪廓,雕琢出相互組合的一獸一鳥①。這是獸鳥合體思維的產物。
良渚文化玉器有人與獸面的多種組合關系的實物。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紋飾內容是神人獸面圖像及其簡化與抽象的圖案,形成獨特的風格。
新石器時代人們創造了異形遺物,上古文獻也記載了異形人和異形動物,應該對這種巧合進行闡釋。
東漢人王延壽在《魯靈光殿賦》中說到我們的人文先祖伏羲、女媧是蛇軀、鱗身。
《山海經》記載了更多的異形人或異形動物。一是人面鳥身,二是人面獸身,三是人面魚身,四是鳥身龍首,五是多頭、多身現象,六是獸首蛇身。
上述古文獻記載的異形人和異形動物的一個共同點也是把動物的肢體或器官移位組合,如把人的肢體加到獸、鳥或蛇等動物身上,或把獸、鳥、蛇等動物的器官移位組合到人身上。這是上古人類的一種極具深度的思維。說到底是一種基于復合工具的組合思維。組合思維激勵人類不斷求索、不斷進取。
上述《山海經》等古文獻關于異形動物或異形人的記載,雖然與今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遺物暗合,但在漫長的歲月里曾被許多研究者斥為“荒誕不經”。其實,這些“荒誕不經”的含義極深、意義重大,給今人尋找上古人類的組合思維和行為之痕跡留下了文獻依據。《山海經·海外西經》記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今天發現的許多新石器時代的玉龍,其形象就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紅山文化、安徽凌家灘文化和江蘇常州青城墩遺址等都發現了“尾交首上”的玉龍。上古人們人為地創造了玉龍等異形物,正好反映了新石器時代人類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復合(組合)思維。
新石器時代的組合思維也擴展到古代音樂和舞蹈等領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河南賈湖遺址(早中晚三期)出土了一批精致骨笛,紅山文化區也有骨笛出土。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已具備了四聲、五聲、六聲和七聲音階,形成了聲音的和諧組合。馬家窯文化彩陶盆上的神化人物舞蹈紋,證明早期舞蹈和音樂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舞蹈已有塤、笛、鼓等伴奏,早已告別了“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呂氏春秋·古樂》)的階段。新石器時代人們的舞蹈和音樂的功能也是組合地體現出來,組合了敬環境、求生育、聯眾心、交四鄰、聘四方、祈求五谷豐登和《總禽獸之極》(希望鳥獸繁殖達到最高極限)的綜合祈求。
復合思維的空間要素組合與深度抽象化是并行不悖的。復合思維的空間要素組合是一個飛躍,復合思維的深度抽象化也是一個飛躍。后一個飛躍更深刻、影響更深遠。
復合思維深度抽象化這個飛躍是循序漸進的。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可通過分析“直觀取象”認知方法的幾個階段來表述。
新石器時代先人認識事物,起初主要是觀物取象或直觀取象。據傳述,孔子研究過這種方法,他編定后的《易經》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組合思維的形成經歷了直觀取象認知方法從低級向高級發展三個階段的演進。
初級的直觀取象認知方法主要是簡單直觀取象。以特定事物為母范、摹本觀物取象,形成具體事物之物象(象形)。思維中離不開具體事物的物象,但觀物取象不是單就一個事物來“觀”,要經過不同角度的對比觀察,既要“仰觀”,又要“俯視”;天地與“鳥獸之文”都兼顧;遠近相較、大小相權。
古人直觀取象,總是要把其要求、理念和意識等加于所取之象上。隨著復合工具的進步,人們不滿足于初級的直觀取象,要求改變原有初級之象。客觀需要和升華的理念都需要對象(象形)進行改變。需要有新的思維來處理,于是便有新的思維產生。
在初級直觀取象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再提煉,就形成了變形之象,從而進入直觀取象的中級階段。變形之象的重要特點是以想象為橋梁,由一種物象跨越到另一種物象。
變形之象再進一步,進入組合象形思維階段。組合象形思維與復合工具思維并進,把具體物象上升到一般物象,把握了物類的共同性質,實現了由個別到一般、由象及理的過程,提升人的想象力和思維能力。
組合取象思維再進一步,上升為理性取象思維,也就形成了抽象象形。
組合之象變成理性取象或抽象之象,產生了兩個重要成果,一是產生了龍思維,二是叩開了象形文字的大門。
三、組合思維作為精神動力催生了龍思維和早期象形文字
組合思維在空間上組合要素、在深度上高度抽象化,標志著新石器時代人們思維水平出現巨大飛躍。這個巨大飛躍催生了兩個成果,一是龍思維(龍文化),一是早期象形文字。
(一)組合思維催生了龍思維,產生了龍形象。在許多新石器時代考古學遺址發現了石龍、玉龍、堆塑龍和蚌龍等。遼寧省凌源田家溝紅山文化遺址發現了玉蛇龍,為龍形象的又一類型。
新石器時代普遍使用復合工具及其思維和經驗,為尋找龍的起源提供了基本線索。
古人制作的異形物和古文獻記載的異形人和異形動物其實就是龍的前身。龍思維為什么會形成?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人類早期生活在自然環境中,與動物相伴,要存活下來,必須向為伴的動物學習,而且要取各種動物之長,增加自己的本領,然后去創造、去征服。取眾物之長,進而把其“長”(精華)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龍。
什么是龍?一言以蔽之,龍就是天地間一切事物的精華組合,這種精華組合的精髓是陰陽和合。
上古文獻所記載,紅山文化等文物所呈示,上古人類從直觀取象到變形之象,再到抽象出萬物集合之龍,是思維和行為的雙重進步。
紅山文化玉龍的組合思維是新石器時代人們思維水平的一個高峰,具有很高的思維價值,也為中華民族成為龍的民族提供了翔實的實證和思想材料。
(二)組合思維催生了早期象形文字。組合思維提升到抽象思維階段,催生了早期象形文字。浙江義烏的橋頭遺址最早的年代距今約9000年。目前在該遺址發現了短線組合紋和三個太陽紋飾,其中一個太陽紋飾中間劃出一道線,表示冉冉升起的太陽。距今約8000年的河南省舞陽賈湖遺址以利器把符號刻在龜甲、骨器上形成賈湖契刻,其中九個刻符在龜甲上,五個刻符在骨器上,三個刻符在陶器上。刻符與漢字的基本結構一致。渤海北岸距今約7000年的內蒙古敖漢旗寶國吐鄉小山遺址,在2 號房中發現四靈紋陶尊,有豬、鹿、鳥和另外一種未讀出的動物的圖案。
安徽蚌埠雙堆遺址的早期地層距今約7000年。雙墩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有大批刻畫符號和泥塑藝術品。其中陶器上的刻畫符號達600 余件,還有特殊形符號等,已具文字的象形、會意和指事等含義。大汶口文化在陶尊上刻畫符號,共有數種數十個符號。有學者認為已是表達語言功能的成熟文字。
紅山文化玉器極具象形意義,有的直接入象形文字,如斜口筒形器類似象形“且”字,玉龜(鱉) 類似象形“龜”字,鳳形玉器類似象形“鳳”字,雙首玉器(并封) 類似象形“虹”字,等等。遼寧省朝陽市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神廟后的山臺入象形文字“邑”字。牛河梁紅山文化神廟的形狀類似甲骨文的象形“中”字形②。
渤海北岸內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小河沿文化遺址出土了一件大口直腹罐陶器,器物外表刻有七個互相有關聯的文字符號,表意完整。有人認為這些文字符號記錄了一次大洪水暴發前后的情況。
四、文化交流也是促進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等考古學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顯示,中華大地區域之間文化與人員的交流很早就開始了,呈縱橫交錯強勢交流態勢。渤海北部的查海—興隆洼文化及后繼的趙寶溝文化等,交流、融合而為紅山文化。以鎮江營文化為代表的渤海西部文化與以查海—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為代表的渤海北部文化也曾密切交流。由鎮江營文化發展而來的后崗一期文化,其紅頂碗文化因素被紅山文化繼承;北京平谷上宅遺址與北方興隆洼文化遺址發現了制作方法相同的骨柄石刃刀,只有用文化交流來解釋這一現象;河北省蔚縣的三關遺址,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器物同時同地出現,也是文化交流的證據。
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也已經相互交流。遼東半島南部小珠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有來自山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因素。山東龍山文化制作精美的蛋殼黑陶、紅地紅彩陶器、紅地黑彩陶器等在遼東半島出現。遼東半島的玉器制品和直口筒形罐也傳入山東半島。美觀的八角星紋,在遼西丘陵山區、內蒙古草原地帶和山東大汶口文化都出現了。
在遼寧旅順郭家村(上層)遺址發現了舟形陶器,說明當時已有的較為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為文化互動提供了工具。
遼南的小珠山文化和遼寧新樂下層文化都繼承了遼西、遼中和遼南共有的石磨盤、石磨棒、細石器和之字紋陶器等文化因素。
河南裴李崗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早于紅山文化,這兩種考古學文化影響過遼西的古文化。紅山文化器物具有河南裴李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的折線篦紋。河北磁山文化和河南裴李崗文化的折線篦紋也在沈陽新樂文化出現。
距今5000年前,紅山文化強勢發展,有越過燕山的明顯跡象,不僅進入華北平原,而且一度進入山東。紅山文化的玉豬龍在河北姜家梁遺址出現,甚至在陜西省韓城梁帶村周代墓葬出現;紅山文化的多孔玉璧在山東省野店遺址出現。北京、天津地區鎮江營文化的釜、鼎、壺等在山東北辛文化發現。其他文化交流的現象不勝枚舉。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融合的部族越來越多、融合的區域越來越大、融合的程度越來越深、融合的內容越來越豐富。
新石器時代的人們更加嚴格禁止一定范圍內血緣親屬成員間通婚,必須實行族外婚,因而對外交流也是必然的行為,但從氏族來說實行的是族外婚,從部落來說則實行的是部落內婚。無論如何,只要實行族外婚,就有文化交流。
新石器時代中國境內的考古學文化已是“滿天星斗”,各考古學文化之間幾乎沒有空置地帶,有的是交叉地帶,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區(交叉區),文化的融合區正是文化的交流區,“雞犬之聲相聞”,物品的交換和文化的交流在空間上已沒有障礙。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交流有時通過別的考古學文化進行傳導。一般說來,文化交流發生于兩個不同文化體之間,但有時要通過其他文化的傳導來實現。長距離的考古學文化遺址具有相同的文化因素,有些文化因素的形成不是直接交流而形成,而是通過中間的考古學文化傳導而來,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的融合區有時范圍很大,不能因為兩種或多種考古學文化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就誤認為兩種或多種考古學文化之間有直接交流,而忽略了其他考古學文化的中介作用,以致影響了對考古學文化本來面貌的認識。
新石器時代的人們開通便捷通道,交換物產、互相觀察和學習,既共享了物質層面的因素,也學習了人與自然相處的能力。
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交流、遷移和擴散雖然對作為對象的一個文化體來說是外因,但往往這種外因啟動了內因,起到了重要作用。眾所周知,紅山文化玉龍對許多區域的考古學文化產生了作用。紅山文化的積石冢作為東北地區石墓文化的源頭,經醫巫閭山向遼東半島的遷徙進駐,在遼寧南部和北部及吉林西南部,出現了與紅山文化積石冢基本特征一致的積石墓、大石蓋墓、石棚墓和石棺墓等墓葬習俗,該石墓文化經河北、山西又傳至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
總之,文化的交流是新石器時代不可小覷的重要社會推動力量。
①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②雷廣臻主編:《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巨型禮儀建筑群綜合研究》,科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