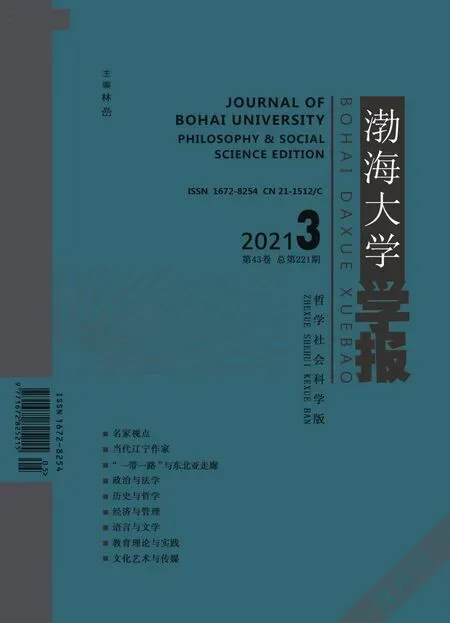民族聲樂作品中時代性的把握
——以《我的祖國》為例
趙 巍(沈陽音樂學院繼續教育學院,遼寧沈陽 110004)
民族聲樂原本是對我國包含民歌、戲曲和說唱等所有傳統聲樂藝術的總稱,如今則是指區別于傳統聲樂,但又建立在傳統聲樂基礎上,吸收美聲唱法而形成的一種聲樂藝術。本文所提到的民族聲樂即是后者。民族聲樂的演唱方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逐漸得到發展的,聲樂作品與演唱方法在不同時期都具有不同的時代性。何為音樂的時代性,李佺民在《談音樂的民族性和時代性》一文中說道:“音樂如同其他藝術、其他社會意識形態一樣,都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會現實。社會生活隨著時代在變化發展,反映社會生活的音樂,也隨著在變化發展。所謂音樂的時代性,講的就是音樂同時代的關系。”[1]
音樂與時代之關系的相關記載中,《樂記》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1](32)可見,民族聲樂作品中的時代性問題是不能被忽視的,脫離時代性去審視、分析和演繹作品,其內容會失意,情感會失真,作品會變得黯淡無光索然無味。特別是面對經典的時代作品,抓住作品中時代性的相關因素,是開啟和演繹作品的根本所在。以《我的祖國》為例,該曲創作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仍被廣泛傳唱,從創作到演唱,從主題內容到思想情感,都使得作品留有深刻的時代烙印。作品中所承載的時代性,即該作品藝術魅力的根源,也是把握作品保持原貌原味的關鍵所在。
一、社會生活因素
李佺民在《談音樂的民族性和時代性》一文中提道:“一個時代的音樂,要適應時代的需要,反映時代的社會生活,體現時代精神,具有時代的藝術特點;而這些音樂,又首先作用于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這些,就是音樂的時代性這一概念所包含的內容。”[1](32)受具體時期社會思想、政治、經濟等的影響,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時代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人們對未來生活充滿了無限的美好希望,各行各業都是動力十足、干勁十足。在摸索中前行,十年“文革”后迎來了改革開放,社會生活進入了嶄新的春天,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面貌都煥然一新。從音樂創作來看,民族聲樂作品的主題內容和傳達的思想隨著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也發生了改變。在解放戰爭時期,聲樂作品的題材大多是以奮勇殺敵、對現實的控訴、軍民魚水情和鼓勵生產等內容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萬象更新,聲樂作品多以歌頌黨和國家、展現幸福生活為主要內容。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民族聲樂作品的題材更是豐富多彩。
歌曲《我的祖國》創作于1956年,是電影《上甘嶺》中的插曲,該電影是為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兩周年而拍攝的。這里的時間信息非常明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和平幸福的生活剛剛開始又被迫拿起武器保家衛國。滿心愿景的新生活被打亂,有志之士舍家衛國奔赴前線,人民群眾積極抗戰,全國上下一心,戰爭最終取得了勝利。從唱詞方面看,該曲可分為三個段落,曲詞充分展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將當時的時代精神展現無遺。第一段唱詞,“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到處都有明媚的風光。”該段唱詞通過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表達了對祖國母親的熱愛之情。第二段唱詞,“姑娘好象花兒一樣,小伙兒心胸多寬廣。為了開辟新天地,喚醒了沉睡的高山,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這是英雄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該段唱詞以姑娘和小伙兒指代所有中華兒女,贊揚了中華兒女英勇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極具民族特性。第三段唱詞,“好山好水好地方,條條大路都寬敞。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這是強大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到處都有和平的陽光。”該段唱詞既展現了中華兒女的熱情待客之情,同時也表明了中華兒女面對外敵入侵而堅守國土家園的態度和決心[2]。
三段唱詞依次展現了當時人民對來之不易的新中國的熱愛,團結一致不畏艱辛開創新生活的十足熱情,堅決維護用血肉換來的和平生活,敵人膽敢侵犯必誅之。而當時的情況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遭受戰爭之苦的人們期盼著未來的新生活。深刻明白國定方可家安的中華兒女面對祖國又有可能遭受外敵入侵的現實,他們保家衛國的信念和決心十分堅定。歌詞中的描繪和情感的表達,真切地反映了我國當時的國情、社會生活和人們的精神面貌。作品貼近社會生活,因此能夠迅速產生強大的共鳴感。對沒有經過戰爭而獲得和平的人來說,無法親身體會,這就需要在作品中抓住時代性的信息和特點,通過多種途徑和渠道使自己努力靠近作品中的時代性,感受作品所蘊含的時代精神,從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感悟作品的內在情感,與作品產生共鳴。任何作品的創作,都無法擺脫同時期社會生活所帶來的影響,正所謂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理解作品時,我們又需要回歸作品的社會生活,貼近時代。可見,社會生活這一因素在把握作品時代性上具有主要的作用。
二、個人因素
受所處社會生活的影響,作家個人的成長會因為同處某一社會時期而具有較為相似的時代精神和時代特征。張前曾在其論著《音樂美學教程》中談道:“一個時代的政治與經濟狀況、思想與文化思潮以及時尚潮流等,無疑會對作曲家的生活狀態、情感體驗、思想意識、審美趣味等產生影響。在這種具有時代特征的諸多因素影響下,音樂家創作的音樂作品也自然會體現出其所處時代的特征。”[3]對于作品來說,詞曲不同作者就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對作品的演唱者來說又是一個獨立個體。同時代的三個人具有同樣的時代精神和特征,但因個體的成長經歷不同,對事物的認知、理解和表現也存在著不同。
歌曲《我的祖國》,喬羽作詞,劉熾作曲,郭蘭英首唱。詞作家喬羽,1927年生人,山東濟寧人,高中期間曾在小學當教員,1946—1948年就讀于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藝術學院,畢業后開始從事專業創作。作曲家劉熾,1921年生人,陜西西安人,自幼隨民間藝人學習鼓樂,后為解決溫飽進入佛堂打掃,跟隨師父學習唐代古樂,這些經歷為劉熾日后的音樂創作打下了堅實基礎。劉熾1936年參加工農紅軍,1939年考入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1940年在魯藝音樂系畢業并進入音樂室進行研究生學習。解放戰爭時期,劉熾曾到東北開展多項與音樂相關工作。歌唱家郭蘭英,1930年生人,山西人,自幼家境貧寒,因為家里人口多又無米下鍋,嬰兒時期遭到父母遺棄,還好有姑姑養至3 歲送回父母身邊,4歲便被送去學習晉劇,6 歲時又因家里揭不開鍋,險些被賣給人販子,但最終還是被家人賣給了太原的戲班當學徒。雖然郭蘭英天生一副好嗓子,有天賦又聰明,練功又勤奮,但由于她入門晚、輩分小,經常遭打罵,5年的戲班生活是她人生中最灰暗的痛苦經歷。但是她在逆境中仍刻苦學藝,而功夫不負有心人,天賦加勤奮,13歲的郭蘭英已是臺上的名角。1945年,郭蘭英進入“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工作團”工作學習。1956年,在喬羽先生的推薦下,郭蘭英演唱了《我的祖國》,此后成了家喻戶曉的歌唱家。
從以上三人的簡要生平看,三人都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同成長。三人生活的時代相同,因此時代精神和時代特征大體上是一致的。但又因為三人的成長經歷不同,在個人因素上對于時代性的理解和表現也會產生不同。從詞作家喬羽生平看,成長經歷相對劉熾和郭蘭英二人要平坦些,因此唱詞中更多了質樸與淡雅,但又不失愛國護國的情感表達。從作曲家劉熾生平看,他是普通大眾出身,參加過革命,見過沙場的殘忍。因此,他在《關于〈我的祖國〉》一文中寫道:“著力追求兩點:1.民族風格;2.時代感情。”“總體設計方向明確后,我將自己整個身心、感情投入創作中。寫這首歌的獨唱部分時,臨死前的七連指導員的形象浮現我的眼前。他的呼吸已經很急促,腦子里閃現的是他的一生。生在長江邊一個漁船上,‘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他回憶著迎風的稻浪,那是他同父母弟妹們一起薅草、施肥的地方。此刻又多想再回去看看啊!聽到護士小王唱歌,他的心仿佛緊緊貼在祖國母親的懷抱,他就這樣含著笑離開了人世。寫副歌部分時,我自己仿佛就在坑道里,同戰士們在一起歌唱著‘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到處都有明媚的春光。’這時,祖國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心底。我們感覺到祖國給了我們無窮的力量,祖國人民同我們在坑道里一齊歌唱。”[4]通過這段文字,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整個創作的過程,更為我們提供了如何把握該作品中時代性的方法。歌唱家郭蘭英無疑是一位勞苦大眾的典型代表,她身上所體現的時代精神更貼近人民群眾,而她的個人經歷則為她演唱這首歌增添了濃厚的摯切之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就沒有現在和平陽光的生活,這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才換來的。如今有人來犯,必將毫不猶豫將其趕走。郭蘭英將這種時代精神融入其整個演唱過程,而且這種時代精神和時代情懷根植在內心中,所以無論何時演唱,都能將觀眾帶回到作品時代,勾起無數人的回憶,產生共鳴。
作曲家徐沛東曾這樣說:“我相信我的作品具有創造性,但是我沒有領導新潮,我只不過把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和感情傳給聽眾。”[5]“善于捕捉時代風貌,這是每個作曲家要不斷告誡自己的,你不能落伍,生活在這個時代,必須要有這個時代的感覺。”“一個作家的作品,如果得不到當代聽眾、觀眾的認可,不能引起當代觀眾的共鳴,我想這不能說是成功的作品。”[6]因此說,對民族聲樂作品時代性的把握,個人因素是十分重要的。了解創作者自身的時代特征,及其創作方法和思路,了解首唱者的個人經歷找到其與作品的共鳴點,對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時代性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從演唱方法上把握作品中的時代性
正如前文所說,現如今的民族聲樂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形成的一門聲樂藝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始,民族聲樂的發展處于大膽嘗試和摸索階段,從歌唱家和作品數量看,民族聲樂藝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不僅增添了傳統演唱的濃厚韻味,而且更為自然順暢,發聲方法也更為科學化。20世紀60年代,由于教學方法不夠成熟統一,民族聲樂藝術的腳步被放緩。“文革”期間雖有優秀歌唱家脫穎而出,但民族聲樂處于低谷時期。直到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民族聲樂無論是演唱技巧還是氣質風貌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高質的發展。時至今日,民族聲樂演唱和教學依然在不停地向前探索中。
在2019年央視元宵晚會上,由老藝術家郭蘭英先生、著名歌唱家張也和青年歌唱家周旋,老中青三代人一同將《我的祖國》再次唱響,濃濃的歷史感、民族情和愛國主義精神將整臺晚會推向高潮。從晚會現場的反響看,郭蘭英先生一開口,便將所有觀眾的歷史回憶喚起,全場共鳴感爆表。而張也和周旋的演唱,則更體現了80年代后民族聲樂藝術所帶有的傳情美感,但與郭蘭英先生相比較卻略顯缺少了些歷史感和時代感。由此可見,民族聲樂自身的演唱方法在不同時期也具有不同時代的特征。
無論是教學還是演出,我們大部分會選用已經出版發行的作品,這就意味著該作品有首唱或者其他人演唱的不同版本。一般首唱或是原唱對我們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因為一首作品的創作者,都會根據自己創作的需要而進行首唱者的選擇,這個首唱者從各個方面看都要符合作品的需要,而首唱者自身的藝術修養則會為作品增添更為豐富的色彩和時代氣息。郭蘭英演唱的《我的祖國》即是如此,自身嗓音甜美且音域寬闊,扎實的晉劇功底使她咬字清晰,韻腔別具一格,加之晉劇粗獷和激越的演唱風格影響,使其演唱質樸,充滿韌勁,聲音凝聚而有穿透力,充分展示了中華兒女的一顆赤子之心,其獨特的演唱方法也成為作品中時代性的一個標識。因此,對首唱者演唱方法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把握作品中時代性的原汁原味。
對民族聲樂作品中時代性的把握,必須重視作品的創作受時代社會的深刻影響,不能忽視詞曲作家和演唱者的個人因素的干預,不能輕視演唱方法所給的時代性提示,方能更好地理解作品中的時代性,還原作品的時代性,再呈現出其時代性。而這一過程需要通過閱讀資料、專業技能及擴展技能的日積月累得以實現。時代在向前邁進,民族聲樂藝術穩步向前發展,具有時代性的作品與我們的跨度越來越大。我們只有從作品產生的年代、創作者和演唱者的自身因素,以及當時民族聲樂藝術發展的程度出發,才能貼近作品,走進作品,才能感受到作品的藝術魅力,抓住作品的藝術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