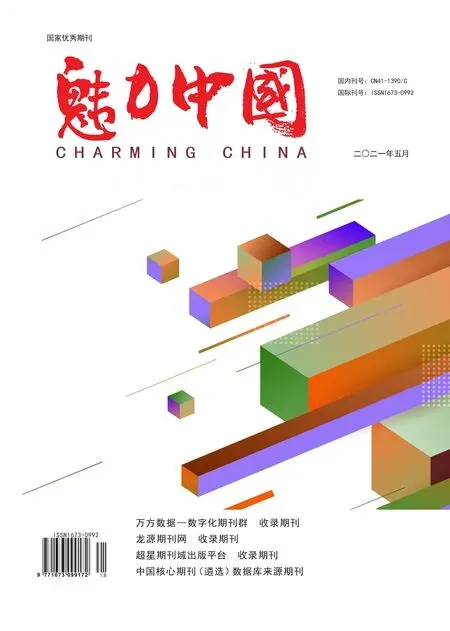論儒家傳統的三個時代
楊洋
(中共肥西縣委黨校,安徽 合肥 231200)
儒家傳統,這一伴隨中華文明兩千多年的傳統,不管你或愛或恨,或冷靜的審視或激烈的怒罵,它總是擺在我們面前,你不能把它當作“博物館里的東西”,它是我們的“當下”,它早已積淀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因此有必要對這一傳統的來龍去脈進行一次審查。
一、儒家傳統的古典時代
儒家傳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傳統,“從原始儒家,到現在依然在發展中的各種儒家思潮,其關注的重點和思想形態,一直在不斷地發展和變化,儒生的社會角色和自我定位也因儒學與中國政治秩序的關系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筆者此處的儒家傳統的古典時代即是指制度化的儒家傳統。儒家傳統,從創造者孔子開始,經過歷代儒者的發展,成為了中國諸多傳統中的主流。本文無意就這一發展過程進行詳細地梳理和分析,而是就晚清時所已鑄就形成的制度化儒家傳統進行靜態的描述。在這一制度化的儒家傳統中,儒家傳統與君主制傳統的關系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環。儒家傳統依附于君主制傳統,借君主制傳統這一“軀體”施展影響;君主制傳統亦依賴于儒家傳統為其提供其自身的“合法性”依據。但是這兩種傳統并不是“天衣無縫”的完美結合,而是“張力與合力”并存的,這種“張力與合力”并存的關系,也是維持古典中國社會活力的重要因素。
首先說一下兩種傳統的“張力”,這種“張力”表現在許多方面,本文僅就核心的“內圣”與“外王”來“以偏概全”。在儒家傳統中,“內圣”是“外王”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內圣”才能成為具有無限權力的“外王”。在君主制傳統中,卻是顛倒過來的,“外王”就是“內圣”,此種意義上,“外王”成了“內圣”的先決條件。從實際情況來看,儒家往往借“內圣外王”這一“理想形象”來制約君主,然而現實卻常常是權力戰勝了道德。
再說一下合力,儒家傳統中也有許多對君主制傳統有維持作用的元素,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儒家傳統中有一重要的原則“親親”,即是以血緣宗法為基礎的社會原則。“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指導原則和基本方針,亦即構成了這個民族的某種共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那么君主制所具有的世襲性,依據“親親”原則,自然是可以成立的。
正是在這兩種傳統彼此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之下,才共同維持了數千年中華文明這一龐大的復雜社會系統的持續性,但是這種內在的活力,在面對極具沖擊力的另一文明時,斷裂了。這次斷裂,導致儒家傳統與君主制傳統的分離,也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總結。
二、儒家傳統的變革時代
晚清以來,儒家傳統面臨著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中華文明遭到了一種強有力文明的沖擊,新文化運動所呼喊的“科學”與“民主”的兩大口號是這一挑戰的集中表現,不幸的是,許多中國人尚未理解真正的“科學”與“民主”之前,就錯誤地運用他們所理解的“科學”與“民主”來審視評價儒家傳統。
對“科學”產生了“科學萬能主義”,更具體的說就是以自然科學的手段處理一切中國人遇到的問題且堅信最終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自然科學的手段得到解決。以這種觀點來審視儒家傳統,可想而知,儒家傳統大多數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完全是“非科學”的一堆歷史的垃圾。對“民主”產生了“制度萬能主義”,以為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國便可以解決一切政治問題,而不管“民主”背后所隱含的西方所獨有的特殊的歷史、社會、宗教等條件。在這種觀點的觀照下,儒家傳統所具有的“民本”觀念不過是一種幼稚的、原始的、低級的思想。
儒家傳統此一時期的討論,總是與政治相關聯,而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近代早期的“洋務運動”,妄圖既保存儒家傳統又保存君主制傳統,在“中體西用”的原則下只引進自然科學,甲午戰爭的慘敗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失敗。辛亥革命后,君主制傳統宣告結束,儒家傳統也成為了“游魂”。民國時,無論是袁世凱、張勛這類野心勃勃的軍閥,還是王國維、嚴復這類中國杰出的知識分子,都把儒家傳統與君主制傳統看成一體的。袁世凱為實現君主制傳統的復辟而提倡儒家傳統;王國維因君主制傳統的破滅而認為儒家傳統也隨之消亡而自殺,他是為了儒家傳統而死。對于許多的知識分子來說,儒家傳統與君主制傳統就是一體的,一榮俱榮、一辱俱辱。儒家傳統成了君主制傳統消亡后的“替罪羔羊”。
三、儒家傳統的展望時代
在近代百年風雨過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儒家傳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人們不再把儒家傳統與政治緊密相連,而是把儒家傳統置于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大背景下來思考。
在對待儒家傳統時我們時常會遇到如下的觀點:“儒家文明也只具有了‘歷史的意義’,而且現代中國文明和任何其他民族文化如西方文化一樣,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通過平裝本的古籍來使世界理解‘孔子的智慧’。因此,在一個真實的世界歷史中,當所有過去的成就都成了沒有圍墻的博物館的陳列品時,每一個國家的過去也就成了其他國家的歷史,這意味著非儒家化和傳統感的喪失。”列文森是韋伯“現代性”的信奉者,帶著悲觀的情感預示著所有偉大的古典文明都將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成為“博物館的陳列品”。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這個觀點:“實質性傳統將在何處終結?答案是它將永遠不會終結。至少,只要人類還生存著它就不會終結。然而傳統從來沒有處在通衢大道上。如果它沒有遇到艱難曲折,那么它也就不會經歷如此巨大的發展了。傳統經歷了發展和變遷,它們不斷得到豐富,它們也曾受到削弱。變化著的環境、利益和利益沖突的后果以及活躍著的理智能力和想像力,都給傳統施加了所有各種各樣的壓力。就在它們給傳統施加壓力的時候,它們本身也難逃脫傳統。”在希爾斯看來,所謂的“現代性”也不過是一種傳統而已。傳統與現代并不是一組非此即彼的范疇,而是古典傳統與現代以來的啟蒙傳統在現代社會的彼此磨合消融。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一個真實的世界歷史中”,所有古典文明的偉大傳統都沒有被啟蒙傳統所取代,而是共同構成了“世界”的諸多傳統的一種而已。未來的世界,必將是諸傳統共存發展的多元世界,儒家傳統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具有勃勃生機的傳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