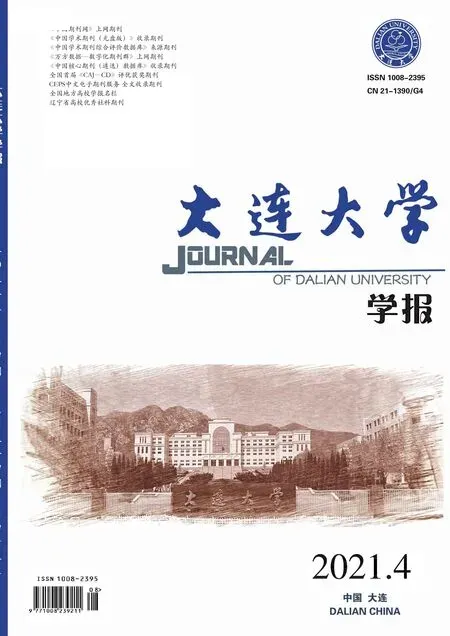認知干預下的程式序列深加工
楊勇飛
(1.湖南工商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2.湖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一、引言
程式語言/序列(formulaic language/sequence)是語言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日常用語 (尤口語) 中十分普遍,如“by and large”“spill the beans”“at times”“would you like to X?”“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t make him drink”等固定或半固定表達,它們使用時整體提取,無需再利用規則語法生成,因而可大大減少語用者在線加工的認知負荷,提高語言交際的流利性、準確性和地道性[1]。對于程式語言,傳統的語法研究只負責語法性解釋,但無法解決語言的自然性(naturalness)問題;單純的詞義分析可以提供(部分)直義理解上的線索,但在面對一些超組構、乖戾搭配及其拓展語義時則顯得蒼白無力。
究其原因,程式語言作為語言的多詞單位(multiword unit)或“長單詞”結構[2],兼有詞匯、語法和語境等特征。并且,大量來自語料庫語言學、一/二語言習得、構式語法等研究的證據表明程式序列并非語言的邊緣現象,而是語言基于使用本質的真實反映[3]。語塊(程式序列)能力作為二語綜合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4],語塊的數量與口語流利性、準確性呈正相關性[5]。根據黃燕、王海嘯[6]研究,中國學生程式序列的使用具有中介語特征,與本族語者相比明顯表現出知識缺乏、過度使用和使用不足等特點。那么,如何在當下課堂教學環境下有效促進中國學習者二語(英語)程式序列的習得,同時提高其語言運用和語言創新能力?
這不僅取決于學習者內部因素(如學習者的學習風格、動機等個體差異),還取決于諸如教學教法、輸入頻率、母語與二語的搭配異同等學習者外部因素的干預。目前國內外程式序列實證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的探討,對于前者的研究相對較少[7]。馬廣惠[8]3認為,對于語塊(程式序列)研究來說,首先需要建構充分、系統的詞塊描述理論體系,并從心理語言學、認知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等角度做多學科闡釋;然后從應用的角度,采用多方印證法,從語料庫中提取和生成通用或專用的二語詞塊表,用于二語詞塊教學研究。本文中,我們嘗試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做適切分析;在充分借鑒Boers、Lindstromberg[9]“深加工”概念的基礎上,我們將主要圍繞程式序列的形義構式單位及其分析性特征展開,著重凸顯認知干預下、以意義為中心的程式序列深加工。這既是程式序列教的問題、也是程式序列學的問題,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促進二語(英語)學習者語言綜合運用能力的快速發展。
二、對“程式序列”內涵及其形義構式特征的再思考
“程式序列”的概念最早由Wray[10]提出,用以指稱“連續的或非連續的詞語或其他成分所組成的序列結構,具有或呈現出預制塊特點;它們整體存儲在記憶中,使用時直接提取而無需語法生成與分析”①A sequence, continuous or discontinuous, of words or other elements, which is, or appears to be, prefabricated: that is, stored and retrieved whole from memory at the time of use, rather than being subject to generation or analysis by the language grammar (Wray, 2002:9).。從文獻研究來看,用以描述程式序列的相關術語很多,如語塊(目前使用最廣)、預制塊、詞匯短語、習語、慣用語、詞束、組詞搭配、公式語等50幾種[10]。程式序列作為語言編碼的一種自然形式,兼顧了“程式”的規約性和“序列”的線性組配關系。同時,它作為一個意義擴展單位又凸顯了特定語境下語義語用、主體認知、社會文化等的動態交互關系。因此,本文力主從“構式”角度來進一步剖析程式序列的句法語義等特點。
首先,從Wray對于程式序列的上述定義來看,它立足于心理語言學視角,主要涉及程式序列判定的三方面標準:預制性、固定性和易提取性[11]。不過,程式序列的“固定性”只是部分的(見下文分析),程式序列的“易提取性”具有相對性,與使用頻率之間并不一定正相關[12]143。此外,Wray對于程式序列的界定過于寬泛,未涉及意義或功能因素,這顯然不利于程式序列的識別和析取,譬如詞串“and in the”“and of the”等雖高頻出現,但缺乏內在語義關聯,沒有明確的意義或功能,不能算作程式語。鑒于此,Wray[13]28,[10]265從“詞/語素等價(morpheme-equivalent)”角度進一步把程式序列限定為“單個單詞或不完整詞串(如“plenty of”),或包含句法槽(gaps)的詞串,它們使用時被看作為一個詞素(黑體為作者所加),而不是基于各部件的形義組合體”②Wray(2008)對于“程式序列”最新的定義是,“a word or word string, whether incomplete or including gaps for inserted variable items, that is processed like a morpheme, that is, without recourse to any form-meaning matching of any subparts it may have(p.28)”.。
在語言中,詞素是最小的音義結合單位,其內部結構相對穩定;詞素進一步構成詞,包括單詞素詞和多詞素詞兩大類。Wray的這種詞素等價的觀點實則強調了程式序列既可以是單詞序列,又可以是詞素序列的雙重特征。那么,對于程式序列的詞匯化,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依據某一句法規則來作分析[14],例如習語“by and large”“ first off”等在搭配上都不符合句法規則,并且部件詞“by”“large”“ first”“off”等都降格為詞法上的分析(而不是句法分析),即針對程式序列構詞理據的分析。
其次,基于詞素的界定方法雖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程式序列形義完型體的特征(即整存整取的特點),但與之同時忽略了(部分)程式序列本身所具有的創新性(能產性)。例如,大量半固定/半封閉程式序列可以通過句法槽運用(如類比,遞推等)實現結構拓展,如程式序列“a(n)___ago”用以指稱“過去的某個時間點”,其句法槽允許填入諸如“hour”“week” “year”“very long time”等表達時間的詞語,再又如程式序列“___think nothing of____”包含兩個句法槽,表達“個體行為的不合常理”意義(如“He thinks nothing of sleeping 4 hours a day.”),其中句法槽一為有靈(animated)主語,而句法槽二為非常規性活動或事件等內容[12]132。Pawley、Syder[15]把它們稱之為產出性(productive)程式序列,認為這些結構盡管在形式和分布上會受一定限制,但都具備自身的小語法(mini-grammar),也即說話者可以利用規則實現結構的局部性能產,這符合構式的“增效”特點,同時也表明了程式序列從詞匯到語法的連續體特征。
相較于非程式序列,程式序列表現出語言組塊化(chunking)和最佳信息載體的特征,因此在心理表征上具有一定的加工優勢[16-18]。在口語表達中,聽/說話者在線語言編碼時會受到語言單位頻率、顯著度、線索競爭、意義協商等的影響,程式序列的內部構件之間盡管存在各種常規或非常規句法語義關系,但都不影響它作為一個形義單位(構式)被整體檢索和提取。這符合語言的經濟省力原則。從常規的話輪交替來看,聽/說話者更在意信息遞達的流利性和準確性,而不是規則的遞歸運用與語法生成。
這主要是因為程式序列以意義為驅動,所有程式序列的構型變化在形式上都受制于某一特定語義語用功能,如話題轉換、語篇組織、社會交互等[12]10-11,119-120,換言之,在話語交流中所有程式序列都被看作一個意義單位,它并非先驗的、多義的,而是經驗的、單義的(至少在起初階段),是交際雙方特定社會文化背景、共同興趣愛好的語義集束[2]。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程式序列的這種形義整體性并不代表它在結構上缺乏分析性①Vega Moreno[21]163-164 指出,學界關于習語(慣用語)的“可分析性”或“可分解性”問題,一般不做嚴格區分。然而,可分析性和可分解性從根本上反映了習語研究的兩種思路,前者側重于構成部分的直義(或隱喻義)直接參與到習語整體意義的建構中,后者側重于習語的整理意義可進一步分解為各個構成部分的意義。因此,習語的可分析性是局部的,它反映了習語字面義與整體義之間的某種語義關聯,而習語可分解性是整體的,它反映了習語構成部分對于習語整體義的直接貢獻關系。本文中,我們主要參照習語(慣用語)的可分析性本質展開討論。,即使是一些高度規約化的慣用語(程式序列),在理解上仍可以從字面上管窺一二,如“pass the buck(推卸責任)”“all of a sudden (突然地)”“pull the strings(拉關系)”等的黑體部分仍是直義的,再如water under the bridge(橋下的水;無法挽回的過去)兼有直義和隱喻義,且二者的語義關聯性強。此外,各種由引喻(allusion)構成的慣用語都有其歷史、文化、宗教、文學等淵源[19],如“face the music”(直面苦難;接受懲罰)源于劇場舞臺表演中,演員經常會由于緊張或怯場而造成忘詞等尷尬的局面,但只要音樂一響,演員就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顯然,程式序列的這種可分析性體現了其詞源上的考據。Wray[20]31-33指出,程式序列被看作為詞素等價物并不是因為其形式或意義上的乖戾性,而是因為其使用的型式特征(patterns of usage)(黑體為作者所加)。這些型式(程式序列)起先并無異于各種新奇表達,其結構自身特有的語法、語義和語音等特征是參照人的體驗經驗后逐漸建構起來的,如慣用語“believe you me(我確信)”除了結構上已完全固化外,語音上也發生了明顯變化(be‵lieve‵you‵me)。隨著語言的使用,部分程式序列的組構性(分析性)可能會逐漸降低或消失,如俚語“kick the bucket(突然死亡)”結構上大體相當于一個詞,且字面意義已接近漂白(bleaching),但在語用強化和語用推理下會逐漸層創出新的意義來。
三、程式序列深加工的維度分析
通常而言,深加工意味著更多認知力(包括注意力)的投入與參與,其目的之一是促進相關內容的記憶保留與長時發展。程式序列本質上體現為程序性知識;實現陳述性知識向程序性知識轉化既符合真實言語交際的需要,也體現了人類記憶組織的一般規律[3]。在二語(英語)習得中,程式序列的深加工可以考慮從其形義構式特征出發,既包括自下而上的詞義、韻律、搭配等的分析,也包括自上而下的構式義(功能)、語境(語體)等的分析。
(一)程式序列的原型性
針對長期困擾語言理論的“本族語式選擇”和“本族語式提取(fluency)”,Nation[1]483認為最合理的解釋是記憶中存儲程式序列的數量。確切地說,是記憶中原型程式序列的數量有助于語言表達的自然性與地道性,如習語、慣用語等。在日常會話中,程式序列的原型性可體現在不同情形下特定的話語方式上,如例(1-2),
(1) a.Your call is important to us (in a calling).
b.Your telephone call has great importance to us.
(2) a.I hear you (in a discussion).
b.I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saying.
上例(1-2)中a、b兩句意義相當,可相互替換,但在特定語境下a句更自然、更易被選擇接受。對此,Corrigan等[22]認為主要是因為a句體現了原型程式序列的用法,具有“限制性形式”和“限制性分布”兩方面區別性特征。其中,限制性形式指程式序列在結構上相對固定,在詞匯選擇和重組搭配上受到更多限制,如“beg the question(回避問題實質)”“commit suicide(自殺)”“blow a fuse(大怒)”等能夠允許的變換(如詞匯替換,句法調整等)十分有限。限制性分布指原型程式序列與某一特定文體和交際情境相符,具有文體學研究意義,如“This paper argues…”“This article analyzes…”等主要用于學術性報告中。
Wray[10]25認為,程式序列原型反映了操本族語者特定情境下的某種言語偏愛方式,其主要原因是它們具有減少語用者在線加工的認知負荷、凸顯語用情境框架(framing)以及創設共有知識平臺(如通用語的使用)促進雙方交際順利進行等作用[2]195。不過,原型程式序列的限制性形式和限制性分布特征并非絕對,而是會隨著在線語言加工的需要以及語言的使用(部分地)發生變異,如日常用語“Have a nice day!”可推衍為“Have a good day!”“Have a great day”等,再又如“beg the question”(見上文)除了形式上經歷再分析過程外,如名詞復數形式(beg the questions)、名詞限定成分(beg some fundamental、larger questions)等的擴展使用[23],其意義也在不斷推演變化,如發展出“提出相關問題”等意義。
那么,關鍵問題是如何正確判別原型性程式序列?一般而言,程式序列原型的使用頻率相較于非原型程式序列而言更高,且其部件詞之間語義關聯性強,有特定的語義語用功能等,因此借助大型語料庫的統計方法和技術較容易識別和提取,當然也有例外情況,如習語“rain cats and dogs”等使用頻率較低,但語用規約化程度很高。另外,一些高頻詞串(如“that in the”)本身缺乏實在意義或功能,不能算作程式序列。對此,Wood[24],Lin[25,26],馬廣惠[8]等提倡運用語料庫、文獻收集、心理實證、基于本族語者的人工識別等多方印證法來判定和析取程式序列。當然,這只能保證概率上的無限接近,更多相關判定方法還有待后續研究(如三(四)的韻律識別法)。
(二)程式序列的構型—功能連續體
在二語(英語)習得中,程式序列種類繁多、數量龐大,Wray[10,13]的“詞素等價”觀點一定程度上統一和強化了我們對程式序列的界定和看法。但是,程式序列的詞素等價特性體現的只是其心理表征上的一種完型特征,并不代表其內部結構都整齊劃一。
通常,程式序列指由兩個或多個詞語所組成的詞匯序列,如復合詞、動詞短語、搭配、習語以及句子等(參見Wood[24]),但Corrigan等[22]認為,單個詞語同樣可充當程式語使用,其根本原因是程式序列本質上體現為一種語言使用型式(見上文),具有形義構式的特征,并且(也更為關鍵),其意義(功能)表達相較于其形式而言更為重要。因此,我們可用“Hallo”代“Nice to meet you”,“thanks”代“Thank you very much”,“well”代“Let me see”等行使相關語用功能的表達。這反映了概念化背景下語言一義多形的特點,同時也反映了程式序列在構型上由單個詞到整個長句的連續體特征。
Kecskes等[2]認為,程式序列構型發展的內生動力是意義或功能的表達,因而建議從功能角度把程式序列劃分為語法單元(如“be going to”),固定語義單位(如“as a matter of fact”),動詞短語(如“put up with”),言語公式語(speech formulas)(如“not bad”),情境語(situation-bound utterances)(如“welcome abroad”)以及習語(如“spill the beans”)等7大類。它們各自表征特有的意義功能,但在語義(功能)透明度上表現出一定的連續體特征(也即“功能連續體”)。譬如,從語法單元到習語,程式序列的分解性逐漸降低,而其任意性(規約性)則逐漸增強。其中,言語公式語和情境語的用法相當,都包含了豐富的社會語用文化知識,但前者使用范圍比后者更為廣泛。
(三)程式序列的共選語義關系
共選理論是指導多詞單位研究的重要方法[27],其基本理論前提是:語言交際的基本單位是詞組,而非詞,單個詞只有進入某一詞組后意義才變得明晰,如動詞see常用于“理解”,而非“視覺上可見”的共選意義。共選既是形式上的,也是意義上的,二者密不可分。共選發展的直接結果是形成各種擴展意義單位(本文指程式序列);共選主要包括詞匯與詞匯共選,詞匯與語法共選以及型式與意義共選三大類。
第一類針對程式序列的組詞搭配關系。舉例來說,名詞ebb 主要與low搭配共選,表達“某人斗志/意氣低下”的消極意義,并且“at LOW ebb”允許形式上的部分變化,如“at its lowest ebb”“reached a low ebb”“their lowest ebb”“at a particularly low ebb”等[28]121。這表明程式序列部件詞之間的共選語義關系既可體現在具體詞形上,也可體現在抽象詞元之間(即LOW-EBB)[27]2。基于詞元搭配的序列分析可以從詞元形式、左/右搭配詞、形式距離三個維度展開進一步討論[29]。詞元以節點的形式儲存在心理詞庫中,詞元間的搭配強度、可分解程度與其句法、詞匯靈活性正相關[30,31],如“pull someone's leg(開某人的玩笑)”有時態和語態的變化(“you're pullingmy leg” “my legwas being pulled”),“spill the beans(泄密)”名詞部分可被量化和修飾(“she didn't spillany of those preciousbeans”“she did not spillabean”),對于以上程序序列的再分析過程,Vega Moreno[21]160認為,慣用語(程式序列)的這種句法靈活性關鍵在于部件詞與整體之間有某種(直義或隱喻義)關聯。
第二類針對程式序列的語義傾向和類聯結意義。如果說第一類主要關注程式序列的橫向組合關系,那么這里則主要關注其縱向的聚合關系。譬如,動詞cause后主要接消極意義的名詞(如“causepain”“causeinflation”),而動詞provide后主要接積極或中性意義的名詞(如“provideinformation”“provideservice”)。再又如,近義短語序列“a__of”和“an__of”雖都用以表達數量關系,且句法槽位置主要為名詞,但前者多用數量名詞(如“abottleof”),后者多用行為名詞(如“anengagementof”),即從動詞演變過來的名詞[32]13。
第三類針對半封閉性程式序列,其型式與意義共選一方面凸顯了程式序列從詞匯到語法的連續體特征,另一方面則強調了程式序列作為一個完型意義單位在語篇組織、話語交際、社會語用等情境下的作用(如語義韻的情感態度意義)。例如,分裂構式“That's what X VP”除了用于凸顯述題(主語或賓語)信息外,還具有明顯的指示性[33]。另外,程式語“It should be noted that…”常用于學術報告中提請注意,“I don't know if …”常用來表達作者的不確定態度,等。
(四)程式序列的韻律分布
本節內容討論與原型程式序列有關,但在以往研究中幾乎不予重視[25,26],認為口語程式序列與書面語程式序列并無二致。Wray[10],Wood[24]等甚至還認為,二語(英語)學習者要想達到操本族語者的語言水平和語言流利性只需儲備與后者近乎相當的程式序列就可以了。這實際上忽略了口語程式序列在數量上絕對占優,以及口語程式序列除了在拼寫、構型、語義等方面表現出心理完型特征外,還體現在語音層面上,也即每一程式序列都含有其特定的韻律結構,并表現出語音上的連貫性(phonological coherence)。試舉例說明。
(3)The trouble is organic produce isn't cheap.
a.(The) trouble IS, organic produce isn't cheap.
*b.The TROUble is organic produce, isn't cheap.
*c.The TROUble, is organic produce isn't cheap.
(4)She has eyes in the back of her head.
a.She has eyes in the back of her HEAD.
*b.She has EYES in the back of her head.
*c.She has eyes in the BACK of her head.
例(3)在口語中使用十分頻繁,朗朗上口,部分語音可直接脫落(如冠詞,3a),但并不影響其語義上的理解。基于韻律學角度來看,該例有2處值得思考:一是語音停頓處在謂詞之后(而不是之前,3b, c);二是句法重音落在功能詞(“IS”,3a)上,而不是實詞(“TROUble”, 3b, c)上。例(4)中短語“to have eyes in the back of one's head”的習語表達(意指“十分機警、警覺”)重音落在名詞“HEAD”上(4a),而不是其他(4b, c)。這些語音上的規約化/習慣性用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程式序列的語音串特點,也即程式序列所具有的韻律結構特征。根據Lin[25,26]的研究,相關程式序列的韻律分析是近年來口語語料庫研究的重點話題之一,并以此揭示語言基于使用的構型特征以及自然語言的處理過程,以及助推二語程式序列的教學,為程式序列的進一步識別提供方法上的支持。
從文獻研究來看,程式序列的韻律特征主要包括“調型一致、節奏快、內部缺少停頓、有特定(restricted)重音”等幾方面[25]3,它們作為某一型式結構的外在語音形式,對于意義的準確表達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如例(3-4)語義表達有其對應的重音分布,再又如“my ears are burning”的習語表達(意指“有人在背后議論你”)重音應落在動詞“BURNing”上,而不是名詞“EARS”(“my EARS are burning”,屬直陳表達)上,半封閉程式序 列“as far as ____ is concerned”“from the ____point of view”等的默認重音值在句法空擋上,以及言語公式語“do you know”在語境作用下(“Do you / know, he was still in bed!”)動詞“know”具有先抑后揚的語調特點,等。
Boers、Lindstrombeg[9]指出,基于人類記憶以及語用偏好的特點,大量程式序列在構詞理據上呈現出語音方面的特征,如重復(如“wonderofwonders,奇中之奇”,“fair'sfair,彼此都要講公道”),押韻(如“mealson wheals,上門送餐服務”“makeor break,要么成功要么失敗”),頭韻(如“cash andcarry, 現購自運”“frompillar topost,四處奔走”),元韻(如“small talk,閑談”“jump the gun,搶跑”),輔韻(如“casual acquaintance,泛泛之交”“further afield,在遠方”),等。其中,頭韻在英語程式序列使用中最為廣泛、也最為重要,具體原因除了英語在音節重音、曲折形式、詞序等方面的特征外,還包括其歷史文化遺留方面的原因(參見Boers & Lindstrombeg[9]117-119)。
四、凸顯以意義為中心的程式序列深加工
由第三章分析可知,二語程式序列本身包含了豐富的語音、句法語義、個人語用、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因此,對其的深加工就應該是在廣度、深度上的多維度不斷深挖。本文認為,多維分析固然有助于全方位把握程式序列的用法用義,但不可均衡使力,要實現程式序列由陳述性知識向程序性知識轉化,以促進個人二語語言能力(如語言的流利性、準確性和地道性)的快速發展,應凸顯以意義(功能)為中心的程式序列深加工,從轉/隱喻視角、語用推理以及圖示(化)結構等認知角度強化對程式序列在生成和理解上的分析。
(一)轉/隱喻視角
以Lakoff等[34,35]為代表的認知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是基于體驗的,具有個人心理或生理基礎,語言中大量的概念隱喻往往折射了人們對于各種概念及其之間復雜關系的積極探索,如LIFE IS JOURNEY, TIME IS SPACE等。通常,概念隱喻通過對具體認知域(源域)的深挖以逐步建立起對抽象目標域(靶域)的理解。這對于程式序列的生成和理解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以語言中“情感”類程式表達來說,人們往往從自身經驗出發來建構和理解這一抽象概念,如例(5)[36]195-196,
(5)a.Your insincere apology justadded fuel to the fire.
b.She wasdoing a slow burn.
c.You made myblood boil
d.He’s justletting off steam.
例(5)各句劃線部分均表達了“生氣、發怒”等情感意義,但在概念隱喻選擇上有所區分:5a, b為ANGER IS FIRE,5c, d為ANGER IS THE HEAT OF A FLUID (IN A CONTAINER)。從個人情感體驗來看,生氣/發怒必然會引起生理上的變化(如體溫等的上升),也即“ANGER IS HEAT”構成了理解該類情感的基礎[36],但是囿于社會文化、個人語用等原因,這一基礎隱喻會經歷各種不同概念化過程,如源域選擇,5a, b的源域為固態性的,而5c, d的源域為液態性的;另外,5a-d不同程式序列的選擇體現了語義描寫的精細化(elaboration)過程和意義上的側顯,如5a凸顯發大火的原因,5b凸顯怒火的強度較低且可控,5c凸顯怒火的強度達到極點(極度生氣),5d凸顯怒氣緩解的方式。
事實上,這種精細化語義描寫主要通過轉喻視角化實現[37],其前提是存在某一事件框架或共有文化知識。根據劉正光、周紅民[31]研究,共有文化知識是指一定社區群體之間對某一概念所擁有的規約化知識,因此又作“理想認知模型ICM”“圖式”“腳本”等理解,程式序列通過規劃約知識實現語義選擇和結構拓展,其主要認知機制是轉喻。以“火”事件框架來說,一方面燃料、熱量、火焰大小、燃燒速度、火的危險性和破壞性等都屬于該事件框架部分,是隱性的背景性知識,另一方面在語用強化(或語境支持下)只有部分事件框架能夠獲得語義聚焦或凸顯,如5a“added fuel to the fire”,5b“doing a slow burn”通過轉喻視角化“動作(過程)指代結果”和“行為狀態指代結果”以強化不同的語義概念內容(見上文分析)。再又如,日常熟語“I hear you (in a discussion)”用行為方式轉指行為結果;根據“手”的形狀、用途、功能等共有文化知識,我們可進一步生成諸如“all hands on deck(做好準備,THE HAND STANDS FOR THE PERSON)”“keep one's hands in (保持練習,THE HAND STANDS FOR THE SKILL)”“give sb a free hand(放手讓某人干, HAVING THE HAND FREE STANDS FOR FREEDOM)”等程式序列。
以上分析說明,在程式序列生成和理解中,轉、隱喻并非完全對立,轉/隱喻之間的互動或意義協商往往表現在轉喻更具基礎性,更有助于發掘細微語義上的差別。很多情況下,慣用語,慣用語(程式序列)的生成和理解需要概念隱喻、轉喻和約定知識的共同參與[31](括號部分為作者所加)。
(二)語用推理
章節四(一)的分析表明,大量(二語)程序序列的生成和理解具有概念性基礎,是隱喻、轉喻等多方認知機制共同作用后的結果。這給我們的啟示是:程式序列的意義并非任意的,而是有理據的,是可以進一步分析的。對此,學者們意見不一。
劉向東[14]認為,諸如“kick the bucket(死了;翹辮子)”“cats and dogs(傾盆大雨) ”“chew the fat(閑談)”等在結構上已詞匯化為詞,在語義上已接近于“死喻”,其所謂的句法可分析性只是一個偽命題,任何對它們可能的分析本質上無異于詞源理據上的歷時考證。馬利軍、張積家[38]基于實證類研究指出,在程式序列(尤習語)理解中句法和語義分析均發揮重要作用,程式序列并沒有詞匯化,不能使用統一的加工模型來整合程式序列的理解機制。Vega Moreno[21],劉正光[19]等則認為,程式序列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它可同時具有任意性和分解性的雙重特點,應視為由任意性到分解性構成的一個連續體。
本文認為,程式序列的構型—功能連續體特征(參見三(二)分析)客觀上決定了我們對程式序列的生成和理解不能也不可以僅僅歸結于某一方法上;基于語言使用的特點來看,程式序列的生成主要包括兩種方式或途徑:概念映射和語用推理。二者相互聯系,都凸顯意義的中心地位,但在意義構建過程上各有所側重。“概念映射”認為程式序列產生于概念系統,是概念域而不是詞本身參與了程式序列的構建;概念之間的聯系通過隱喻等認知機制建立起聯系來,程式序列的選擇反映了概念形成的具體化過程。
與之相對,“語用推理”認為程式序列的產生源于豐富的語用交際環境,是社會文化、個人認知、語用強化等交互作用后的結構選擇,如程式語“What's X doing in Y?”( 如 What's the fly doing in my soup?)兼有直義和引申義的雙重理解,其具體用法要依據語境才能判定。再又如,“jump the gun”的“搶跑”意義與源語背景—比賽時,發令槍沒響就先跑出去了—有關,“show someone the rope”的“傳授秘訣”意義與源語背景—帆船航海時,教會新船員如何掌握系船繩的正確方法—有關,等。程式序列產生之初往往在形義(包括語音)上表現出一定的乖戾性,如“by and large”,“ first off”等在搭配上有違語法基本規則,其形義完型體及其(準)詞匯化過程是過度使用后的必然結果。關鍵的是,程式序列的生成并不能證明某概念結構的存在,如例子“kick the bucket”與“死”,“cats and dogs”與“傾盆大雨”,“chew the fat”與“閑談”等之間并沒有概念上的必然聯系,它們形式與意義上的關聯是在一定語用推理后強加的。對此,我們可基于對程式序列意義(功能)的熟悉程度,從構詞成分上對其意義進行分解。譬如,程式語“break the ice(打破沉默)”中的break,“draw the line(劃清界限)”中的draw,“pull strings(拉關系)”中的pull等仍是直義的,再又如程式語“pop the question(求婚)”中question隱喻映射為“marriage-related question”“give up the ghost(斷氣)”中ghost隱喻映射為“people's soul or spirits”,等。這些分析可以有效加速對其整體意義的理解和記憶。劉正光[19,31]也指出,在程式序列的理解過程中,知識可反作用于概念結構,程式序列意義的熟悉程度具有制約作用。當人們知道了程式語意義時,傾向于去發現程式語結構,同時將尋求意義的策略轉向建立程式結構與意義之間的聯系。因此,在二語(程式序列)教學中,凸顯其意義(功能)形成過程的精細化分析顯得尤為重要。
(三)圖示化與圖示結構
程式序列的圖示結構與圖示化與語法有關,且主要反映在半固定程式序列上,是語言頻繁使用、類比和推理后的結果,如“NP think-TENSE nothing of doing sth (VP) (表個體行為的不合常理)”“If I were you (the president/the headmaster, etc.)…( 表忠告)”“Someone (NP) V1 it Adj to V2…(表主觀評價)”“If it be-TENSE good enough for NP, it be-TENSE good enough for me (表個體行為的合理性)”等在結構上都有一定數量的句法空擋,允許依據自身的“小語法(mini-grammar)”實現句法擴展。Pawley、Syder[15]211把它們稱之為“詞匯化句干”,是緣其意義功能上的文化規約性、形義結合的整體性以及詞語選擇的任意性等特征,其關鍵是對某一會話含義、言語行為功能等的表達,如例子“This iswater under the bridge”劃線部分換成“This iswater below the bridge”后,它的隱喻義消失了,再又如“If I were you…”換成“If I were the person…”后,它的表忠告功能不復存在了。這說明程式序列形式上的(部分)任意性以一定的表義功能為目的,其形式—意義(功能)的組合既是規約的,又是整體性的。
基于程式序列的圖示知識,我們可以進一步充實和拓展其結構,但這種語言創造性(圖示化能力)是有限的,如上述例子“Someone (NP) V1 it Adj to V2…”的評價義表述中可用于V1的選擇僅涉及 find, make, think, consider等幾個詞,而常用的形容詞也只有difficult, hard, easy, clear, impossible,necessary, likely等幾個,再又如程式序列“NP1 a NP2 (once a week)”表頻率義時其NP1只限填入數詞,而NP2只限填入表時間單位的名詞(如日、月、年等)。已有研究表明,基于語料庫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程式序列內在結構上的語義韻、類聯結等圖示化知識,如近義短語序列“a__of”和“an__of”雖然都用以表達數量關系,且句法槽位置主要為名詞,但前者多為數量名詞,后者多為行為名詞,即從動詞演變過來的名詞(見上文),再又如動詞短語“border/bordering on”后接的主要為消極(尤心理上)意義的名詞,如“antagonism, apathy,arrogance, carelessness, chaos, conspiracy, contempt,cruelty, cynicism”等[12]135。
五、結語
本文借鑒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觀點,從形義構式、心理完型、(準)詞匯化、可分析性等角度闡明了程式序列構型使用的特點,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二語(英語)程式序列深加工的多維性及其主要認知機制干預過程。文中選擇從程式序列(而不是其他)角度來探究語言的多詞單位或長單詞結構主要是參考了其程序性知識結構、構型選擇限制、意義(功能)驅動等特點,這既反映在語言運用上,也反映在心理記憶上,因而能更有效地揭示語言基于使用的特點,以及語言結構(化)的任意性、規約性和分析性(分解性)“三位一體”的動態發展特征。
程式序列反映了本族語式選擇和本族語式流利性(地道性),對于二語習得及促進二語綜合能力發展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從內容選擇、策略方法等方面加強對程式序列的深加工以增進其記憶、強化其知識結構與語言應用的關聯。認知語言學的語言基于使用、語義具有中心地位以及語義即概念化過程等觀點對于程式序列的習得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程式序列在心理上不管是詞(等價),還是大于詞的句法單位,自身都攜帶了豐富的社會文化、個人認知、語用語體等信息,從構型—功能連續體角度出發能較充分地揭示程式序列構建的復雜性及其形義構式動態發展的特點。
本文中,強調以意義為中心的程式序列深加工不僅在于順應語言基于使用的特點,還在于凸顯隱/轉喻、語用推理等認知—概念化過程能從更深層次角度揭示程式序列的生成和理解。程式序列本身并非不可分析,而是在程度上有區分,這恰如劉正光[19]所指出的:程式序列兼有任意性和分解性的雙重特征,應視為由任意性到分解性構成的連續體,約定性是普遍的,任意性是部分的,分解性是局部的。盡管多數學者認為像“kick the bucket”“spill the beans”等程式語在結構上已高度凝練無法分析,但實際上其部件詞kick強調“一次性快速踢打”,beans預設的“容器(container)隱喻”等一定程度上對其整體義理解仍有貢獻。這說明,凸顯程式序列意義上的深加工并不是要摒棄其在形式上的刻畫描寫,恰恰相反,程式序列任何形式上的變化都是有意義的,我們可從原型結構,共選搭配以及音韻變化等角度強化其(程式序列)對于概念的精細化描寫。限于篇幅,本文研究只是理論上的進一步深挖,更多程式序列的相關研究還有待后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