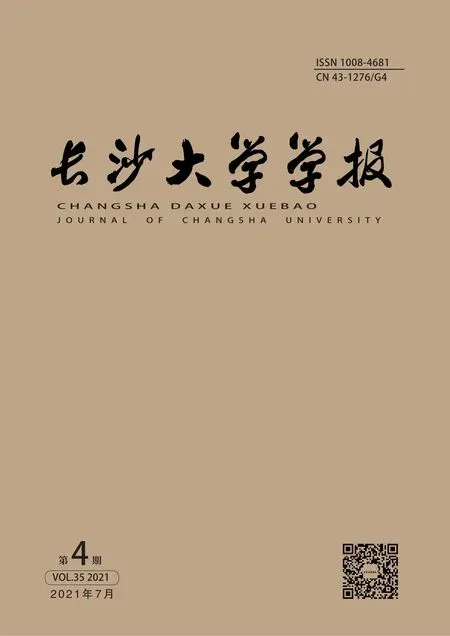論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的演進(jìn)歷程
桂運(yùn)奇
(皖西學(xué)院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安徽 六安 237000)
近年來(lái),在關(guān)于五四前后思想轉(zhuǎn)型的研究中,“自我”已經(jīng)成為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重要課題①。近代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最有意思也最令人驚奇的不是知識(shí)分子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階層中的實(shí)況,而是知識(shí)分子如何想象自己,如何定位理想中的自己”[1]277。作為五四前后思想轉(zhuǎn)型的典型知識(shí)分子,青年毛澤東對(duì)近代國(guó)人應(yīng)如何完善自己、如何成就理想的自己,以使自身轉(zhuǎn)變成一個(gè)有益于國(guó)家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步的人,進(jìn)行了艱辛思索,最終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與認(rèn)識(shí)。這便是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②的演進(jìn)與形成。“自我”是一個(gè)十分復(fù)雜、范圍非常廣的問(wèn)題。本文從心理特質(zhì)這一微觀視角,來(lái)探討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的演進(jìn)歷程。
一 由“圣賢”到“新民”: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的首次轉(zhuǎn)變
民初以來(lái),動(dòng)蕩黑暗的現(xiàn)實(shí)政治和社會(huì)環(huán)境促使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不斷反思國(guó)民性、思索國(guó)人應(yīng)具有哪些心理特質(zhì)以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青年毛澤東察覺(jué)到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內(nèi)環(huán)境“蓋舉世昏昏,皆是斫我心靈,喪我志氣”[2]84;有識(shí)之士雖心系國(guó)家前途命運(yùn),卻因不知“己之本領(lǐng)何在”,“徒以膚末之見(jiàn)”言救國(guó),招致“求途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勝言”[2]84。反觀普通民眾,“渾渾噩噩”,“只知道私爭(zhēng)”,“只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時(shí)”,而對(duì)于現(xiàn)代國(guó)民應(yīng)有的“共同生活,久遠(yuǎn)觀念”等心理特質(zhì)卻“很少懂得”,“多半未曾夢(mèng)見(jiàn)”,依舊“人人自營(yíng)散處”,
①代表性成果如:余英時(shí)指出,五四后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由于是從民主與科學(xué)的角度來(lái)理解西方文化的,因此不能深入西方關(guān)于“個(gè)人”與“自我”的研究和討論,也忽視了“個(gè)人”與“自我”的價(jià)值與意義(余英時(shí).中國(guó)近代個(gè)人觀的改變[C]//許紀(jì)霖,宋宏.現(xiàn)代中國(guó)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7-205)。許紀(jì)霖指出,五四所塑造的自我,依循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思想脈絡(luò),依然有大我和小我之分。小我與個(gè)人私欲有關(guān),大我則代表著公共價(jià)值、公共利益乃至一個(gè)超越一切的世界(許紀(jì)霖.家國(guó)天下:現(xiàn)代中國(guó)的個(gè)人、國(guó)家與世界認(rèn)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69)。王汎森指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不再受傳統(tǒng)禮法道德之限制,其內(nèi)容是開(kāi)放的,是無(wú)限可能的向上主義(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guó)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8:33)。
②學(xué)界對(duì)青年毛澤東“自我”思想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如:彭大成指出,青年毛澤東的“自我實(shí)現(xiàn)說(shuō)”深受湖湘文化圣賢君子人格理想的影響,二者是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的(彭大成.湖湘文化與毛澤東[M].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104)。莫志斌指出,青年毛澤東特別務(wù)實(shí),強(qiáng)調(diào)以具體社會(huì)活動(dòng)實(shí)踐作為實(shí)現(xiàn)理想“自我”的基礎(chǔ)(莫志斌.青年毛澤東思想研究[M].長(zhǎng)沙:湖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250)。金民卿指出,青年毛澤東是“自我清算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在清算了自我思想結(jié)構(gòu)中的各種錯(cuò)誤思想后才成為堅(jiān)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金民卿.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zhuǎn)變之路[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5:298)。本文則立足于現(xiàn)有成果的研究基礎(chǔ),以微觀視角,力求深入探究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的演進(jìn)歷程。“沒(méi)有有組織的社會(huì)”[3]。據(jù)此,青年毛澤東感慨:吾國(guó)思想與道德,偽而不真、虛而不實(shí);國(guó)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jié)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86。因此,他認(rèn)為,黑暗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導(dǎo)致國(guó)人缺乏作為現(xiàn)代國(guó)民應(yīng)有的心理特質(zhì),也難以為改善國(guó)家現(xiàn)實(shí)處境作出貢獻(xiàn)。那么,國(guó)人應(yīng)追求哪些心理特質(zhì)以完善“自我”,使自己轉(zhuǎn)變成一個(gè)有益于國(guó)家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步的現(xiàn)代國(guó)民呢?青年毛澤東對(duì)此展開(kāi)了艱辛思索。
梁?jiǎn)⒊摹缎旅裾f(shuō)》是關(guān)于近代先進(jìn)分子設(shè)想如何塑造“新民”的一部里程碑式的文獻(xiàn),書(shū)中所提到的“新民”體現(xiàn)了梁?jiǎn)⒊瑢?duì)現(xiàn)代國(guó)民的認(rèn)知,其對(duì)民初知識(shí)分子思考何為現(xiàn)代國(guó)民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梁氏熟悉宋明理學(xué),深受傳統(tǒng)儒家修身觀念的影響,通過(guò)《新民說(shuō)》即可看出此點(diǎn),因?yàn)樗麜r(shí)常援引宋明理學(xué)來(lái)談?wù)撊说摹白晕摇彼茉欤?]45。青年毛澤東深受梁?jiǎn)⒊枷牒脱哉f(shuō)的影響[5]86,且信服傳統(tǒng)儒家修身觀念。因此,在思索國(guó)人應(yīng)具備怎樣的心理特質(zhì)以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時(shí),他最初尚不能走出圣賢人格理想的心境,并認(rèn)同以圣賢的道德品格作為國(guó)人追求“良善自我”的價(jià)值尺度。他將當(dāng)時(shí)缺乏現(xiàn)代國(guó)民心理素質(zhì),只顧眼前私利的國(guó)人稱為“小人”,并稱贊覺(jué)悟的知識(shí)分子為“圣賢”;同時(shí)號(hào)召對(duì)“小人”伸出援手,“開(kāi)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于圣域。彼時(shí)天下皆為圣賢,而無(wú)凡愚”[2]89。青年毛澤東認(rèn)為,個(gè)人要修成圣賢的道德人格必須具有“內(nèi)省之明”與“外觀之識(shí)”,使自身“內(nèi)而思維,外而行事”[2]86。如此,個(gè)人才能夠弄清自身本領(lǐng)的長(zhǎng)短之處,找到正確救國(guó)救民的方法。在日常生活與學(xué)習(xí)的過(guò)程中,青年毛澤東更是努力以圣賢品格來(lái)砥礪自我修養(yǎng)。他認(rèn)為德業(yè)俱全的人可被稱為圣賢,而有大功大名卻欠于品德之人,只能被稱為豪杰[6]449。他在同學(xué)中提倡“三不談”,不談金錢(qián)、家庭瑣事與男女問(wèn)題[7]79,以求一心一意塑造“良善自我”品格。
在青年毛澤東看來(lái),普通民眾要實(shí)現(xiàn)超凡入圣,應(yīng)具有追求“大本大源”的心理特質(zhì),因?yàn)槭ト苏撸暗么蟊菊咭病保?]87。他指出,孔子之所以成為“至圣先師”,“惟在得一大本而已”;他之所以“獨(dú)服曾文正”,視其“完滿無(wú)缺”,是因?yàn)樵谒哪恐薪荣t獨(dú)有曾國(guó)藩抓住了“大本大源”[2]88。青年毛澤東視本源為“宇宙之真理”,強(qiáng)調(diào)國(guó)人皆為宇宙之一體,故大本大源“各具于人人之心中”[2]87。如果國(guó)人都能夠以追求“大本大源”來(lái)完善“自我”品性,則“天下之事可為”[2]87-88。對(duì)于時(shí)人以立志謀求自我完善的行為,青年毛澤東認(rèn)為:“志者,吾有見(jiàn)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謂也。”[2]88個(gè)人真欲立志,必須將追尋真理奉為自身言行準(zhǔn)則,視為達(dá)成目的的方向,如此“方為真志”,否則終身未得真理,即“終身無(wú)志”[2]86。他批評(píng)國(guó)人不顧宇宙本源,無(wú)視真理,只欲冥行,盲目將先輩處世行為立為己志,實(shí)為“盲從之志”,并稱“此種人,大都可憫”[2]87。可見(jiàn),在青年毛澤東心中,追尋“大本大源”、塑造圣賢品格,是國(guó)人成就個(gè)人發(fā)展、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的重要推進(jìn)力量。
與此同時(shí),傳統(tǒng)圣賢人格理想在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的修身理念中也有一個(gè)逐漸滑離的趨勢(shì)。他越來(lái)越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群體和國(guó)家的奉獻(xiàn)與責(zé)任才是國(guó)人自我完善的目標(biāo),而非圣賢人格理想。事實(shí)上,在轉(zhuǎn)型時(shí)代的中國(guó)思想界,儒家道德倫理由于受到西潮的震蕩與沖擊而面臨“解紐”,已不可能成為知識(shí)分子對(duì)現(xiàn)代國(guó)民理想人格的實(shí)質(zhì)定義①?gòu)垶壬赋觯^轉(zhuǎn)型時(shí)代,是指1895年至1920年初,前后大約二十五年的時(shí)間,這是中國(guó)思想文化由傳統(tǒng)過(guò)渡到現(xiàn)代、承先啟后的關(guān)鍵時(shí)代。他闡釋“解紐”并非解體,是指這一時(shí)期儒家的兩組理想,即人格理想(圣賢君子)和社會(huì)理想(天下國(guó)家)的形式尚存,但在其時(shí)知識(shí)分子心中已逐漸動(dòng)搖而失去吸引力(張灝.張灝自選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09,115)。。青年毛澤東作為轉(zhuǎn)型時(shí)代的典型知識(shí)分子,自然認(rèn)為現(xiàn)代國(guó)民理應(yīng)如傳統(tǒng)社會(huì)的人一樣去追求人格理想與社會(huì)理想的實(shí)現(xiàn)。但是,他對(duì)現(xiàn)代國(guó)民“良善自我”的定義更多的已不再是圣賢觀念,而是逐漸認(rèn)識(shí)到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是思想界的強(qiáng)權(quán),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致使中國(guó)人郁郁做兩千年偶像的奴隸[8]。在他看來(lái),那些諸如“君為臣綱”“君君臣臣”的事,已非“民國(guó)所宜”[9]。
青年毛澤東指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lái)都是“干著奴隸的生活”。在封建皇權(quán)的桎梏下,國(guó)人沒(méi)有能力也不被允許“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xí)”,致使國(guó)人“只知道各營(yíng)最不合算最沒(méi)出息的私利”[10]。而如今,封建皇權(quán)已被推翻,國(guó)家在思想、政治、經(jīng)濟(jì)等各方面得以解放,置身于這樣的時(shí)代機(jī)遇中,青年毛澤東指出,國(guó)人號(hào)稱共和國(guó)民,就應(yīng)該改變沒(méi)有幾個(gè)懂得什么是共和國(guó)民的麻木心態(tài)[11],且要把權(quán)利思想、義務(wù)思想納入自我塑造之中,喚醒自身的“國(guó)民”資格和身份。因此,他呼吁,人民應(yīng)改變“鉗口結(jié)舌,合手并腳,半死半生”的昏聵麻木狀態(tài),幡然醒悟自身對(duì)國(guó)家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應(yīng)說(shuō)話的當(dāng)說(shuō)話,應(yīng)反抗的當(dāng)反抗,認(rèn)識(shí)到掃清民族和社會(huì)的頹敗乃全國(guó)人民的責(zé)任,不敢辭亦不能辭[12]。
梁?jiǎn)⒊摹缎旅裾f(shuō)》作為影響幾代知識(shí)分子的經(jīng)典文獻(xiàn),它所關(guān)心的就是如何塑造“新民”,也就是脫離奴隸狀態(tài),丟掉麻木陳腐、自私自利的民族劣根性后所形成的現(xiàn)代國(guó)民。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毛澤東雖置身于這樣一個(gè)“新民”觀念崛起的時(shí)代,但他對(duì)現(xiàn)代國(guó)民“良善自我”的定義實(shí)際上不可能完全擺脫傳統(tǒng)修身觀念,只不過(guò)圣賢的修身理念淡薄了,傾向于“新民要使自我醒覺(jué)”,以及存有公德心和公共心等為國(guó)家的種種心理特質(zhì)。
二 從“新民”到“新人”: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的再度轉(zhuǎn)向
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興起后,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封建倫理和道德遭到青年的強(qiáng)烈批判和指責(zé),人的覺(jué)醒和解放成為突出的時(shí)代主題。如何打破舊有的倫理道德、宗法禮教對(duì)“人”的束縛和桎梏,如何才能成為一個(gè)具有人格獨(dú)立、個(gè)性解放特質(zhì),秉持自由和平等、民主與科學(xué)理念的“新人”,成為時(shí)人思索的熱門(mén)話題。1915年前后,中國(guó)處于名為共和實(shí)為專制的尷尬境地,這使青年毛澤東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如不打破封建思想在人們頭腦中的統(tǒng)治地位,個(gè)人就不能獲得獨(dú)立人格和自由個(gè)性,則《新民說(shuō)》所倡導(dǎo)的公德心、公共心于現(xiàn)實(shí)根本無(wú)法讓國(guó)人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更遑論讓國(guó)人成長(zhǎng)為有益于國(guó)家、社會(huì)進(jìn)步和發(fā)展的人。因此,青年毛澤東在思索國(guó)人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應(yīng)具有哪些心理特質(zhì)時(shí),也就由“新民”轉(zhuǎn)向了對(duì)“新人”的關(guān)注。當(dāng)然,這里的“新人”顯然是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主義意義上的“新人”。
毛澤東指出,國(guó)人雖號(hào)稱共和國(guó)民,但都很迷信,迷信鬼神、迷信強(qiáng)權(quán),“全然不認(rèn)有個(gè)人,不認(rèn)有自己,不認(rèn)有真理”,國(guó)民心里“沒(méi)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么”[13]。對(duì)其時(shí)思想界盛行的“國(guó)民大,各人小,國(guó)民重,各人輕之勢(shì)”等觀點(diǎn),青年毛澤東“以為不然”,而是認(rèn)為“先有各人而后有國(guó)民,非各人由國(guó)民而發(fā)生”,國(guó)民之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人之生命由國(guó)民之生命所派生”[2]242。作為五四青年中的典型代表,青年毛澤東深刻感受到國(guó)民若仍處于盲從、迷昧狀態(tài),只會(huì)造成 “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組織、風(fēng)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阻力甚大的狀況,因此必須對(duì)國(guó)民的“良善自我”做全方位的重新定義,以“造成新國(guó)民及有開(kāi)拓能力之人才”,使其轉(zhuǎn)變成“新人”[2]96。
《新民說(shuō)》鼓吹以國(guó)家為旨?xì)w的“新民”是人們的修身理想,但隨著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持續(xù)深入,時(shí)代主題亦發(fā)生變化。在無(wú)政府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影響下,“國(guó)家”逐漸成為一些激進(jìn)青年批判和鄙夷的對(duì)象①羅志田指出,清末民初的中國(guó)讀書(shū)人內(nèi)心始終存有一種“道高于國(guó)”的觀念,總向往一種在民族國(guó)家之上的“大同”境界,當(dāng)其不得不在“世界”與“民族國(guó)家”之間進(jìn)行選擇時(shí),選擇忠于“世界”的雖少之又少,但世界主義始終是他們不能忘懷的(許紀(jì)霖,宋宏.現(xiàn)代中國(guó)思想的核心觀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46)。。一戰(zhàn)之后,列強(qiáng)爭(zhēng)奪殖民地、壓迫弱小民族的事實(shí)使青年毛澤東認(rèn)識(shí)到,強(qiáng)調(diào)“國(guó)家”話語(yǔ)以謀取民族振興不過(guò)是“一種謬論”,只會(huì)導(dǎo)致大國(guó)擴(kuò)充帝國(guó)主義,使弱小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11]。反思中國(guó)歷史,他認(rèn)為“我們這四千年文明古國(guó),簡(jiǎn)直等于沒(méi)有國(guó)。國(guó)只是一個(gè)空的架子,其內(nèi)面全沒(méi)有什么東西”[14]。在青年毛澤東看來(lái),國(guó)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wèn)題[8],因?yàn)榇髧?guó)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chǔ),國(guó)民全體是以國(guó)民個(gè)人做基礎(chǔ),空談國(guó)家與國(guó)民,而不先行建設(shè)地方、健全個(gè)人,只會(huì)造成國(guó)家沒(méi)有物質(zhì)基礎(chǔ),必定立腳不住[14]。毛澤東指出:放眼世界,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國(guó)的旗子變成了紅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但中國(guó)呢?多年來(lái)假共和大亂戰(zhàn)的慘痛現(xiàn)實(shí),“迫人不得不醒覺(jué),知道全國(guó)的總建設(shè)在一個(gè)期內(nèi)完全無(wú)望”;索性分裂,打破空洞無(wú)組織的大中國(guó),實(shí)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非這樣不能救中國(guó)[14]。
隨著青年毛澤東國(guó)家觀的轉(zhuǎn)變,以往“新民”式的“良善自我”理念在其思想中逐漸消退。他重新思考個(gè)人應(yīng)追求哪些理想,具備哪些心理特質(zhì),才能夠使“自我”趨于良善,轉(zhuǎn)變成一個(gè)完善“新人”。在青年毛澤東看來(lái),人要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成為合格的“人”,他的心理特質(zhì)應(yīng)該是“有意識(shí)的”,能夠運(yùn)用理智思維和自由意志去擘畫(huà)自己的理想,時(shí)時(shí)反思自己為什么要這樣做。青年毛澤東指出,從戊戌變法至民初,國(guó)人思想雖有變化,但并非透徹的變化,仍然深受傳統(tǒng)文化或習(xí)俗的影響,不知不識(shí),渾渾噩噩,因此僅可以說(shuō)是“籠統(tǒng)的變化,盲目的變化”[8]。國(guó)人以“立志”來(lái)規(guī)劃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標(biāo),他極為贊同,但強(qiáng)調(diào)國(guó)人不要盲目地以先輩及近代先賢處世行為為己志,而是要做到依自己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不為強(qiáng)有力者所利用,不失卻個(gè)人主觀性靈[2]86。那么,個(gè)人人生理想和目標(biāo)確定后,該如何進(jìn)行、如何規(guī)劃?青年毛澤東認(rèn)為需要做長(zhǎng)期的預(yù)備和精密的計(jì)劃,同時(shí)要持續(xù)省察自己,能夠知道自己的短處[2]557。更進(jìn)一步說(shuō),應(yīng)做點(diǎn)準(zhǔn)備功夫,但不是隨便無(wú)意地、放任地去準(zhǔn)備,實(shí)在要有意地、有組織地去準(zhǔn)備,要時(shí)時(shí)反思怎樣別開(kāi)新局面、怎樣可以創(chuàng)造自己的新生命[2]475。
另外,青年毛澤東指出,人要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還應(yīng)該具有“人為的”心理特質(zhì)。受西方進(jìn)化論思想影響,青年毛澤東認(rèn)為人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規(guī)定吾人之力”,暗示人在自然面前有無(wú)力的一面,有被環(huán)境決定的可能。但他更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可以通過(guò)“人為的”努力去克服自然,因?yàn)椤拔崛艘嘤幸?guī)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雖微,而不能謂其無(wú)影響”[2]272。在青年毛澤東看來(lái),“自然,乃先天的、非人為的”,是一種保持現(xiàn)狀的生活狀態(tài)。個(gè)人處于變化萬(wàn)千的世界,生存其中至為不易,如仍依“自然”狀態(tài)生活,“則不免有危及生存發(fā)達(dá)之事”[2]272。所以,他建議國(guó)人如欲塑造“良善自我”,并成為有益于國(guó)家社會(huì)之人就必須要持有“人為的”心理特質(zhì)。所謂“人為的”心理特質(zhì)就是個(gè)人通過(guò)積極有為、奮發(fā)圖強(qiáng),對(duì)國(guó)家社會(huì)盡義務(wù)責(zé)任。義務(wù)責(zé)任“乃后天的、人為的”,雖不自然,卻能“善吾人之生存發(fā)達(dá)”[2]272。那么,個(gè)人如何能做到積極有為、奮發(fā)圖強(qiáng)?青年毛澤東提到了“意志”。他說(shuō)“意志本原于沖動(dòng)”,也就是說(shuō)個(gè)人先天就具有“意志”,如“武勇、不畏、敢為、耐久”等種種人的天性“皆意志之事”;但意志“非天命而全乎人力”,個(gè)人只要有堅(jiān)強(qiáng)意志,就可以成為“人生事業(yè)之先驅(qū)”,進(jìn)而轉(zhuǎn)弱為強(qiáng),身心完善,成就“良善自我”[2]72。
必須強(qiáng)調(diào)的是,由“新民”轉(zhuǎn)向“新人”并非意味著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后國(guó)民思想已經(jīng)在青年毛澤東的心中失去力量,而是表現(xiàn)為“新人”興起但“新民”思想余波不衰。究其原因,是因?yàn)樾挛幕\(yùn)動(dòng)前后的思想界雜糅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無(wú)政府主義、各種社會(huì)主義思想①王汎森對(duì)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前后的思想界有精彩的論述,稱其為“一個(gè)調(diào)色盤(pán)”。他指出,當(dāng)時(shí)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無(wú)政府主義、各種社會(huì)主義思想一起構(gòu)成了一個(gè)調(diào)色盤(pán),而“國(guó)民”思想已經(jīng)沉淀為一種底色。面對(duì)這些極其含混復(fù)雜的色調(diào),未在西方受過(guò)長(zhǎng)期教育的人很難區(qū)分清楚,至于一般青年,則“往往不能道其所以”(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guó)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8:40)。,普通青年知識(shí)分子身處此種含混復(fù)雜的思想環(huán)境中,很難清楚地界定某一種思想的確切含義②毛澤東在1920年給友人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坦誠(chéng)地說(shuō):“現(xiàn)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xué)說(shuō),都還沒(méi)有得到一個(gè)比較明了的概念。”他還表示自己想從國(guó)外學(xué)說(shuō)、譯本及時(shí)人所辦的報(bào)章雜志中汲取中外古今的學(xué)說(shuō)精華,并編成一本書(shū),以弄清楚各種主義、學(xué)說(shuō)的概念(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473)。。故在受時(shí)代主題影響而熱議“新人”的同時(shí),青年毛澤東思想中附會(huì)糅合了“新民”思想實(shí)屬難免。
三 依歸馬克思主義“新人”: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的最終形成
經(jīng)歷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洗禮之后,青年毛澤東對(duì)“良善自我”的定義由“新民”轉(zhuǎn)向“新人”,認(rèn)為理想的自我不僅僅是一切以“國(guó)家”為旨?xì)w的“民”,更應(yīng)是單個(gè)的,不受各種舊社會(huì)舊禮教規(guī)范約束,且有自主意識(shí)、積極有為、奮發(fā)向上的“人”。為追尋這一“自我”的理想狀態(tài),青年毛澤東嘗試走無(wú)政府主義道路,希望創(chuàng)造一個(gè)“勞動(dòng)者得完全平均分配,子弟得完全人格獨(dú)立”的“新社會(huì)”[2]454。1919年春,他設(shè)想在岳麓山建設(shè)新村,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xué)校及旁的新社會(huì)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創(chuàng)造一種新精神、新生活、新社會(huì)[16]。1920年,青年毛澤東設(shè)想和籌劃了“湖南共和國(guó)”方案,該方案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它是要“劃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民眾可以“自營(yíng)食、自營(yíng)衣、自營(yíng)住”,創(chuàng)造一種“人間天上,大風(fēng)泱泱”式的新生活、新理想、新天地[17]。可見(jiàn),在無(wú)政府主義的影響下,青年毛澤東認(rèn)為人只有擺脫舊社會(huì)舊禮教的桎梏束縛,身處“新社會(huì)”,富有“新精神”,過(guò)有“新生活”,才算是“人”[17]。
然而,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政治的黑暗與腐化、民眾思想的迂腐和麻木,使青年毛澤東很快認(rèn)識(shí)到以創(chuàng)造“新村”引導(dǎo)民眾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轉(zhuǎn)變成理想“新人”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其時(shí),青年毛澤東持續(xù)發(fā)文呼吁“自決主義”,號(hào)召民眾應(yīng)該醒覺(jué),奮起以爭(zhēng)自由,積極投身自決自治。他指出,自己所主張的“湖南共和國(guó)”非“部落主義”和“割據(jù)主義”,而是要使民眾在“一塊地域文明”中行使自決自治,以“從容發(fā)展其本性,創(chuàng)造其文明”,進(jìn)而“實(shí)施新理想,創(chuàng)造新生活”,養(yǎng)成“良善自我”,變成理想“新人”[17]。但現(xiàn)實(shí)的情形是,為政者孤陋寡聞,昏聵無(wú)識(shí),不知自身缺陷,無(wú)責(zé)任之觀念與振奮之精神,這致使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wú)希望”;廣大民眾則“多數(shù)不能自覺(jué),不能奮起主張,有話不說(shuō),有意不伸”[18]。對(duì)于自治主張,多數(shù)民眾竟然“莫名其妙,甚或大驚小怪,詫為奇離”,而自己苦心謀劃的“湖南共和國(guó)”方案,又“知者絕少”。青年毛澤東感慨國(guó)人腦筋不清晰,無(wú)理想,無(wú)遠(yuǎn)計(jì)。幾個(gè)月來(lái),他已看透了。他意識(shí)到“自治問(wèn)題發(fā)生,空氣至為黯淡”,“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2]548。
彷徨之際,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為青年毛澤東探索“良善自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事實(shí)上,1919年上半年,青年毛澤東還盛贊克魯泡特金主義相較于馬克思主義而言,其思想“更廣,更深遠(yuǎn)”[19]。而至1920年11月下旬,隨著湖南自治運(yùn)動(dòng)的失敗和“湖南共和國(guó)”方案的破滅,他反思“自治”只是“應(yīng)付目前環(huán)境的一種權(quán)宜之計(jì),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2]571。他開(kāi)始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并認(rèn)識(shí)到十月革命之所以能成就“空前大業(yè)”,是因?yàn)椤坝兄髁x”,“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15]。這一新的啟示讓青年毛澤東意識(shí)到,研究用什么方法、從哪一方面入手去改造社會(huì),并能夠形成一股“善良的有勢(shì)力的士氣”,還需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使大家“變成主義的結(jié)合”,而不是“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jié)合”[2]554。青年毛澤東強(qiáng)調(diào):“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2]554那么,“人”究竟應(yīng)該信仰什么“主義”呢?改良理想破滅的慘痛經(jīng)歷, 使得青年毛澤東醒悟到無(wú)政府主義、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主義“都只是理論上說(shuō)得好聽(tīng),事實(shí)上做不到”,而對(duì)于蔡和森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方法來(lái)改造中國(guó)的主張,他“表示深切的贊同”[20]8。可見(jiàn),至1920年11月下旬,由信仰馬克思主義來(lái)達(dá)到個(gè)人完善“自我”的目的,這一思路在青年毛澤東的心目中是非常清晰的。
十月革命成功背后“黨眾”所發(fā)揮的作用給青年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1920年11月在給羅璈階的信中,他指出要為中國(guó)“造成一種有勢(shì)力的新空氣”,就必須要有“一班刻苦勵(lì)志且信守主義的人”[2]554。因?yàn)閭€(gè)人的想法只會(huì)是“一個(gè)人的冥想”且影響力只“限于一個(gè)人知道”,這是“人自為戰(zhàn)”,是“浪戰(zhàn)”,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經(jīng)濟(jì)的”[2]465。相反,結(jié)合個(gè)人成為“一個(gè)高尚純粹勇猛精進(jìn)的同志團(tuán)體”,形成“共同討論,共同進(jìn)行”,是“聯(lián)軍”,是“同盟軍”,是“可以操戰(zhàn)勝攻取的勝券的”[2]465。同年12月,在給好友蔡和森的信中,他開(kāi)篇即強(qiáng)調(diào)新民學(xué)會(huì)作為一個(gè)團(tuán)體所發(fā)揮的積極作用:“學(xué)會(huì)建立以后,頓成功了一種共同的意識(shí),于個(gè)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響。”[20]2信件末尾,他不忘提醒蔡和森“同志聯(lián)絡(luò)問(wèn)題”極為緊要,“改造中國(guó)與世界的大業(yè),斷不是少數(shù)人可以包辦的”,大家應(yīng)該結(jié)為同心,形成團(tuán)體,“攜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20]10。
總之,在1920年下半年,毛澤東已完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21]136,他開(kāi)始贊同和肯定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和專政的方法與理論,他先前對(duì)“新人”的定義也開(kāi)始發(fā)生轉(zhuǎn)變,注重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新人”,也就是能夠堅(jiān)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依靠團(tuán)體與組織力量和運(yùn)用暴力革命手段,以建立社會(huì)主義新社會(huì)為目標(biāo)的一代“新人”,而這一理想的“新人”所具有的重要心理特質(zhì)就是能信仰馬克思主義、能攜手同心過(guò)好團(tuán)體生活。
四 結(jié)語(yǔ)
作為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典型知識(shí)分子,青年毛澤東對(duì)國(guó)人應(yīng)追尋哪些心理特質(zhì)以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進(jìn)而成為一個(gè)有益于國(guó)家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步的人,展開(kāi)了艱辛探索。身處民初新舊思想轉(zhuǎn)型的時(shí)代,青年毛澤東不可能完全擺脫傳統(tǒng)修身觀念的影響,因此,追尋“大本大源”,塑造圣賢品格一度被他認(rèn)為是國(guó)人實(shí)現(xiàn)“良善自我”應(yīng)具備的心理特質(zhì)。不過(guò),儒家道德倫理終究已沒(méi)落,不可能成為民初先進(jìn)分子定義國(guó)人“良善自我”的實(shí)質(zhì)標(biāo)準(zhǔn)。相反,梁?jiǎn)⒊摹靶旅瘛崩砟睿褳榘ㄇ嗄昝珴蓶|在內(nèi)的先進(jìn)分子所共持。因此,他對(duì)國(guó)人“良善自我”的考慮更看重“新民”所具有的公德心、公共心等心理特質(zhì)。
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興起后,思想界掀起了對(duì)“何為人”的討論風(fēng)潮。此時(shí),單個(gè)的,不受各種舊社會(huì)舊禮教規(guī)范約束,且具有自主意識(shí)、積極有為、奮發(fā)向上的“新人”,成為青年毛澤東心目中“自我”的理想狀態(tài)。以往《新民說(shuō)》所鼓吹的種種為國(guó)家的心理特質(zhì)雖并未被青年毛澤東完全否定,但“有意識(shí)的”“人為的”等“新人”所具有的心理特質(zhì)已經(jīng)悄悄主導(dǎo)了其對(duì)國(guó)人“良善自我”的構(gòu)想與認(rèn)識(shí)。
不過(guò),至1920年11月下旬,隨著湖南自治運(yùn)動(dòng)的失敗與“湖南共和國(guó)”方案的破滅,青年毛澤東深刻認(rèn)識(shí)到,以社會(huì)改良為旨趣的“新人”想要?jiǎng)?chuàng)造“新社會(huì)”,于現(xiàn)實(shí)根本走不通。相反,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實(shí)啟示青年毛澤東:依靠主義和團(tuán)體來(lái)達(dá)到建立“新社會(huì)”的理想是一條可行道路。他對(duì)“新人”的定義亦由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主義轉(zhuǎn)向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新人”,并將信仰馬克思主義和過(guò)團(tuán)體生活視為國(guó)人“良善自我”的標(biāo)準(zhǔn)。至此,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得以形成。可以說(shuō),青年毛澤東“良善自我”觀的最終形成是其對(duì)馬克思主義“人”的發(fā)展學(xué)說(shuō)的繼承和升華,為之后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在革命、建設(shè)與改革的各個(gè)時(shí)期加強(qiáng)自我修養(yǎng)、完善自我品格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