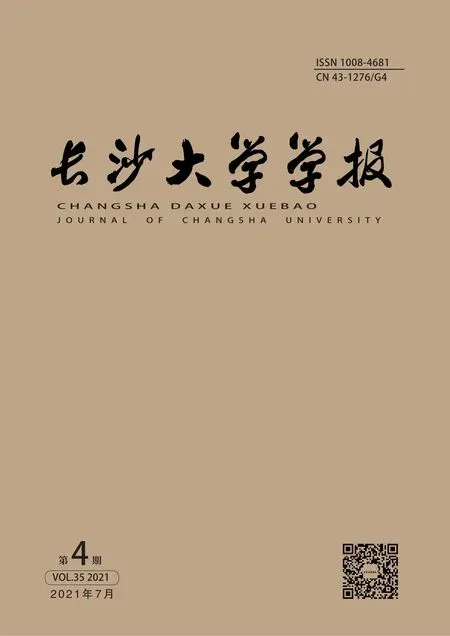韓愈散文駢散融合探析
成松柳,吳思聰
(長沙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410076)
中國古代學者對文學本質問題多有探討,對于內容與形式孰輕孰重亦爭論不休。從“文質彬彬”到“文筆之爭”,從古文衰微到駢文興盛,古文的變革如“古文運動”等多與駢文對立。但文學的本質是相通的,任何文體都有其內在發展規律,且一種文體的發展離不開其他文體的影響,“古文運動”中不只有文體的對立,也有許多吸收和融合,韓愈散文亦受到駢文與古文的共同影響。
韓愈散文在唐代獨樹一幟,對后世亦影響深遠。唐以后提及古文,皆離不開韓愈,他既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也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但韓愈的散文并不完全如他所說,只從三代兩漢之書中的古文發展而來,更是從偏向審美特性的南北朝駢文而來。一方面,韓愈以復興儒學為己任,他的文道觀念使其往往以駢文為對立面,大力發展古文的創作;另一方面,駢文文體源遠流長,且便于逞才使氣,在唐代使用廣泛且無可替代,韓愈散文創作受之影響,多注重文辭。在唐代駢散互相影響之背景和韓愈文道觀念的影響下,韓愈散文呈現駢散融合的特色,本文將從韓愈散文的語言特色、句型結構和文章布局進行探析。
一 韓愈散文駢散融合的背景
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在唐代都經歷了重大的變革,兩者也不可避免地有了互融。駢文中的浮靡之風與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的改觀,古文也不斷發展起來,韓愈散文就產生于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在韓愈之前的諸多駢文與古文的斗爭,為韓柳領導的“古文運動”奠定了基礎,也為韓愈散文的駢散融合提供了經驗。
(一)唐代駢文的變革
魏晉南北朝之時,人們對于文學作品形式美的研究不斷深入,駢文順應文學自覺發展規律且走向繁榮。至韓愈所處的唐代,駢文發展有了新的轉向,駢文作品也有了新的風格,相比古文仍占主流。唐初的駢文,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代文風的影響,綺麗婉約,適合宮廷應和,其創作多藻飾而少內容,后在初唐四杰和陳子昂的筆下文風才有了轉變。自此,唐代駢文的氣勢與意境開始博大,思想和內容也不斷充實。盛唐時,整個社會氛圍都較昂揚激越,駢文內容豐富、感情基調上揚、氣勢雄渾,已有駢散融合的端倪。“燕許大手筆”雖多廟堂臺閣之作,但作品大都典雅莊重、博大恢宏,書序和碑文等作也多有拓展。當時有名的駢文作家也大多是大詩人,頗具盛唐氣象。中唐時期,駢文幾經改革后不再居于統治地位,廟堂之類的應用文與抒情敘事文的駢體也都有了不同的變化。而晚唐駢文在國勢衰微、社會混亂之下逐漸走向華麗浮泛。
駢文在唐代長期占據文壇的主要原因,一是駢文具有符合文人審美要求的特性,在表現漢字之美方面比古文有優勢,也可展現文人的才氣,受到諸多讀書人的偏好。駢文便于逞才使氣,在形式上多有雕琢,將用典、對偶、聲律等的形式之美發揮到極致,使作者顯得博學淵雅。雖在內容的表達上有缺陷,但在審美性上仍有價值。二是科舉制和官場公文的需要。進士科中所考的律賦使得想要入仕的讀書人都須做好駢文,而上傳下達的公文也須采用駢體,駢文運用廣泛且無法被替代。三是優秀的駢文作家對其改革創新,使它得到長足的發展。唐代在韓愈之前,已有初唐四杰致力于駢文文風的轉變,后陳子昂力倡革新,宋之問、李嶠倡導疏宕有致;“燕許”、王維、李白、杜甫、李華、元結的駢文氣象高昂,陸贄的駢文流暢。這些對韓柳在散文上的創作以及“古文運動”都有著重要影響。
(二)唐代駢文與古文的融合
每種文體的發展都有衰微與興盛之時,駢文在唐代雖占主流,但許多有識之士早已認識到其弊端。駢文在六朝發展至頂峰后,對于形式美的追求走向極端,只注重四六的格式和聲律,將華麗的辭藻和生僻的典故用至其中,最終落入俗套,失去內容和真情的表達,這正是唐代“古文運動”要反對駢文的原因。古文的精練生動、簡明實用更符合韓愈等人的需要,在他們的努力下,古文開始不斷崛起。后有學韓愈者一味追求古奧怪澀,完全反對駢文和文辭藻繪,復古模擬之風過甚,又使得古文走向另一種桎梏,晚唐駢文因此又興起。
唐代駢文較散文更為繁盛,但駢文也從唐代開始受古文影響產生了新的蛻變。駢體文與散體文長期共存,古文運動的成功與駢散之間的相互批駁和借鑒是密不可分的。駢散在功用上各有長短,但二者也是相輔相成的,駢體與散體只是體制,稍加變化就可以改駢成散,韓愈許多文章中的句子就是如此。其實從張說、蘇颋、常袞等人創作駢文開始,駢文就有了駢散融合的趨勢,有了逐漸散體化、素淡化的趨勢。文章好壞與駢散無必然關系,內容與形式的和諧才至關重要,而韓愈散文正是形神兼備才成就深遠。
二 韓愈散文駢散融合的特點
韓愈散文受駢文和古文的共同影響,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所體現。清代劉熙載評價其散文道:“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1]20-21韓愈散文內容之豐厚,來源于對現實生活的體察和對前人思想的繼承;形式之多彩,來源于對前代諸多文體的融會貫通,包括古文與駢文的諸多技法。觀其文章布局,文典結合、鋪陳渲染、化駢為散;觀其語詞特色,新詞生動、口語自然、虛詞調和;觀其句法結構,用韻靈活、奇偶并行、長短句相間。總之,從謀篇到用詞造句,皆可看出韓愈散文出神入化之特點。
(一)謀篇
駢文在謀篇上自有長處。劉師培曾言:“有韻及四六之文,中間有勁氣,文章前后即活。反之,一篇自首至尾奄奄無生氣,文雖四平八穩,而辭采晦,音節沉,毫無活躍之氣,即所謂死也。”[2]170韓愈散文的謀篇布局與駢文風格緊密相關,雖然韓愈行文無定法,以內容的表達為宗旨,自成高格,但其謀篇取了駢文之長:以典入文,自然曉暢;時有鋪陳,含蓄深遠;化駢為散,推陳出新。
駢文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用典,可以展現作者的積累,這使得駢文自六朝以來就受到諸多文人的推崇,這在韓愈散文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其全文可由典故布局,整篇皆圍繞一個典故來闡述觀點,如在《雜說》中,韓愈用伯樂與千里馬之事表達對人才難被發現的嘆息;《送董邵南序》開頭提及荊軻高漸離之事,暗示今非昔比;《答陳商書》以齊王好竽之事來鼓勵陳商不隨波逐流。此外,在《原道》《原性》《原毀》等論說文中,韓愈所用典故出自不同的經書、子書、史書甚至佛家典籍,可以看出韓愈學識之淵博,用典廣泛且密而不繁,這也是韓愈文章布局謀篇中的重要一筆。用典恰當可以增強文章的說服力,可以增加淵雅之氣與含蓄之妙,韓愈所用皆契合文章主旨大意,與純粹堆砌典故的駢文相比,顯得更明白流暢。
駢文以四六句式為主,在對句中呈現出典麗精工的特色。韓愈散文繼承了駢文句式的一些特點,又大膽出新。袁枚曾說過:“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 腎,為奧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為句,或數十字為句,拗之,練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8]1549四六句式往往一個偶對結束就已句意完整,但韓愈經常采用散而長或錯綜排比的句子。韓愈的散文中時有對句,亦多大氣磅礴、沉郁頓挫的長句,以及簡練精悍、意味深長的短句,這些更能增強表達的力量。《柳子厚墓志銘》中,韓愈在下論“士窮乃見節義”[3]572后,即用長句層層深入地論述了人情冷暖、世風日下之現象,與柳宗元的高潔義氣做對比,更顯悲憤。《藍田縣丞廳壁記》中也用一個長句描述縣丞行事,使其神態畢現,完整的句子由“文書行”“卷其前”“目吏”“則退”[4]100等短句組成,尖銳地諷刺了官場弊病,更顯對郁郁不得志的人才的惋惜。韓愈在論述和描繪上使用長句使得語氣文情更為飽滿。不過方東樹也曾評價韓愈“筆力強,造語奇,取境闊,蓄勢遠,用法變化而深嚴,橫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間有長語漫勢,傷多成習氣”[5]219,可見長句的使用也需妥當處理,以避免造成閱讀障礙。
六朝駢文十分重視辭藻,尤其是形式上的美感。韓愈則提出“惟古于詞必己出”[3]604“惟陳言之務去”[4]190,重視詞語的創新。韓愈散文中有“耳濡目染”“跋前躓后”“下塞上聾”“粉白黛綠”“形單影只”“任重道遠”“神施鬼設”等詞,這些詞一三、二四字相對,是韓愈從諸多經典中提煉而成,言簡意賅、對稱工整。此外還有許多疊詞,如“油油翼翼”“矯矯亢亢”“倫倫睨睨”“戚戚嗟嗟”等,形式精致,彰顯個人風格。韓愈的許多散文讀起來艱澀難懂、佶屈聱牙,與他所選用的詞語是分不開的,如《曹成王碑》中“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 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 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4]478,所用動詞都極生僻。韓愈為了反駢而復古,但有時過于追求奇特,反而不利于內容的表達。不過他那些融合了駢文技巧的文章,倒顯得文從字順。
2008年北京奧運會取得的優異成績足以向世界證明我國已經實現體育大國的目標,后奧運周期,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成為我國體育發展新的認知,群眾體育由此重新登上體育發展的大舞臺。自2008年以來,我國群眾體育發展態勢迅猛,群眾體育領域研究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長足發展。然而通過知識圖譜的分析也發現我國群眾體育研究存在跨單位之間的合作力度不夠、缺乏中心作者群等問題。因此,后續相關研究應當注重不同機構與作者之間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從而為我國群眾體育發展夯實理論基礎。
韓愈在駢文的基礎上對傳統文體進行了諸多改革。六朝時駢文盛行,在韓愈和古文運動之前,祭文多是駢體,以四言為主,講究韻律,句式整齊,風格莊重典雅,便于當眾朗誦,韓愈本人亦有諸多四字祭文流傳于世,如《祭柳子厚文》《祭河南張員外文》《祭穆員外文》等。但在《歐陽生哀辭》中,韓愈先用散體描寫了歐陽詹的生平,蘊含深切的惋惜與悲痛,最后用“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4]339這類四字與五字語句,進行了總結,加深了感慨。最能打動人的《祭十二郎文》是散體,全文傾訴真情,不同凡俗,影響深遠。六朝后碑志基本使用駢文,雖能做到情文并茂,但限制了寫人敘事功能,而韓愈使碑志從記載資料的應用文變為充滿文學性的文體,既可抒情言志,又充滿傳記色彩。在《柳州羅池廟碑》中,韓愈采用玄幻手法表達對柳宗元的贊嘆;而在《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中,又用詼諧的語言描述了一位不與世俗同流的奇男子王適。韓愈對駢文的改革體現在許多應用文中,這些文體長期流于僵化的程式,而韓愈使其煥然一新。
(二)遣詞
韓愈散文在用詞上具有突出成就。首先,他能從駢文固定套語中吸取經驗,從前人之作中提煉詞語,創作出所作文章需要的新詞,推陳出新;其次,韓愈對俚言俗語的運用得心應手,對駢文的淵博雅致之氣與古文的艱澀之風都處理得當,使得文章平易暢達,突顯駢文與古文融合的特色;最后,韓愈在虛詞的運用上也有所發展,使得駢文與古文的融合與轉換更為靈活。
唐代聲律發展已較為完善,尤其體現在詩歌上,文章自然也不例外。韓愈散文在聲律上用韻自然,散語之中夾有聲調和節奏。與許多古文完全無韻相異,與諸多辭賦駢文要求嚴格也有些許不同,韓愈采用散句來押韻。《后漢三賢贊》中“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4]66,語句雖散,用韻卻齊。《子產不毀鄉校頌》開頭說“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游于鄉之校,眾口囂囂”[4]75,四字與五字相間,卻依然押韻。韓愈用韻有時較為松散自然,如《柳州羅池廟碑》中的最后一段字數與騷體不合,用韻也多有改換;《送李愿歸盤谷序》中最后一句,本可以每個短句都押韻,一韻到底,卻出現了“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4]274這句短語將其打斷。用虛詞和語氣詞押韻來源已久,屈原的《離騷》中就有大量的“兮”,韓愈對此也頗為精通。《送孟東野序》中許多句末為“之”“者”“也”“耶”等字,《送董邵南序》中多“哉”“矣”等字,《送李愿歸盤谷序》和《歐陽生哀辭》中有大量的“兮”字,《祭十二郎文》中則有“嗚呼”“乎”等字,這些字多無具體意義,在句尾重復出現,疊加起來卻合乎韻律。
韓愈常年做官,文集中有數篇上書和表狀,這些都需要文辭委婉,雖不及漢賦的“勸百諷一”,但仍需極盡鋪陳方能達到目的。如在《諫佛骨表》中先直接下結論——“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3]684,后用上古的軒轅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禹等為例來說明無佛之前的統治者如何長壽,又舉殷湯、湯第四代孫太戊、湯第十代孫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穆王等例來佐證帝王的長壽與佛無關。韓愈知道自己此舉定然激怒皇帝,所以進行了大量鋪陳。《燕喜亭記》中,韓愈為亭屋周邊的每一處盛景都取了含義豐富的名字,包括山丘、石谷、土谷、山洞、池塘、山泉以及廳屋,看起來有些眼花繚亂,但這些取名皆與對友人的關懷相關,讀者從中既能感受到山間美景,又能收獲勸誡,意義深遠。
駢文在唐代雖占主流但有弊端,如過于注重雕琢詞句、鋪陳泛濫,影響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中唐時期要求革新的古文家勢力較弱,韓愈既以執道者自居,就得大力提倡古文,反對駢文和浮靡文風。他在《答呂毉山人書》中講道:“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于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4]243駢文在科舉和公文中占據重要地位,導致入仕之人更注重形式的雕琢,真正的思想則難以表達,韓愈對于這種現象很是不滿。因此,他在文體復古中常取古書“單行直下”的散文句法,并習得了堯典、舜典之“渾渾無涯的氣格”[4]245。
例如,在給學生講解《媽媽的愛》這篇詩歌的時候,教師可以讓學生有感情地朗讀,讀出媽媽對孩子無私的關愛以及孩子對媽媽的感恩之情。然后,教師可以對學生進行啟發,引導學生理解詩歌的具體內容,感受修辭手法的運用,激發學生對母親的感恩之情。最后,教師可讓學生進行寫作練習,自己創作簡單樸實的詩歌來表達對母親的愛,以此來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達到促進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雙向提高的目的。
韓愈散文在句法上對駢文既有繼承又有突破。在聲律上,韓愈發揚了駢賦押韻的特性,用韻靈活,散句亦可押韻;在句型上,不拘定格,多有奇偶并行、駢散夾雜之語。韓愈散文中長句雄健有力,短句精簡靈便,二者在韓愈筆下超脫了駢四儷六的格式,在敘事和抒情上加強了表達效果,使文章讀起來抑揚頓挫、感人至深。
雖然翻轉課堂起始于課前視頻知識傳授,但本文作者認為,課前知識傳投并非只能通過視頻實現。鑒于微課的制作人力、技術、時間成本太大,任課教師可以上傳課件或者提供與教材配套的網絡學習平臺資源實現課前知識傳授。目前,由于多媒體技術的推廣,任課教師都對英語精讀的教材進行了PPT課件制作,出版社也提供了參考課件和網絡平臺學習資源。如果摒棄現有的這些資源,教師都把時間花在重新制作微課上,勢必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甚至會出現事倍功半的情況。因此,實施翻轉課堂模式的教師;可以靈活應用現有課件和網絡平臺資源,根據學生水平選取相關內容,進行資源的整合和優化,然后將課前學習內容給學生上傳到指定網絡平臺上。
(三)造句
韓愈對虛詞的運用也有創新。先秦兩漢之文發展至唐代的一個重要變化便是:虛詞在文章的節奏、音律和格式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利用虛詞,既可增強文章的抑揚頓挫,也可豐富對句的形式,韓愈散文中可見大量的虛詞銜接其中。一方面,文章中的虛詞有助于抒發感情,增強或舒緩語氣;另一方面,韓愈運用虛詞使得文章更顯自然靈活。方東樹道:“而于不經意語助虛字,尤宜措意:必使堅重穩老,不同便文隨意帶使。此惟杜、韓二家最不茍。”[5]222《祭十二郎文》作為韓愈感情流露至深之文,其中的虛詞對于感情的表達作用是巨大的。如“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4]380,于句首連用三個轉折連詞“而”,感情強烈,層層深入。陳子昂在《堂弟孜墓志銘》中連用四個“歟”:“嗚呼,其無命歟!遭命歟!天不忱歟!道固謬歟!”[6]28李華在其成就最高的駢文《吊古戰場文》中也說道:“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6]65韓愈在《祭十二郎文》中也有著相似的句子:“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4]380此處連用三個“邪”字,加重了語氣和情感的表達,加深了節奏和韻律,讀之感人肺腑。至于使文章更自然靈活,則可見《答李翊書》中有關氣與言關系的論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4]191用“也”“而”“之”“則”等虛詞使氣與言的定義和關系清楚地展現出來。
閱讀推廣既是一種活動的服務形式,則可能會在多個地點、多個不同空間、以多種不同形式呈現,其多樣性特征相對于圖書館傳統的固定地點、單一形式的服務而言,其辨識度更低。因而,它更需要代表其特質的標識來標明服務的前后一致性及增加讀者的辨識度,而品牌化則可以將具有多樣性特點的閱讀推廣統一在一個框架或主旨下來實現。
韓愈雖提倡古文,但他也在散文中大量運用了駢偶的修辭手法和對句,并對對仗的句子加詞改造,這比駢文又多了幾分松散自然。但語句仍具有形式上的對仗,既能彰顯文采,又有利于朗誦和流傳,在精美整齊的句式中意義得以凸顯。許多對偶句在現代仍有警示意味,如《師說》中的“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4]49,《進學解》中的“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4]50等,形式對仗,內容精辟,自然且不露痕跡。錢基博曾評論《進學解》說:“雖抒憤慨,亦道功力;圓亮出以儷體,骨力仍是散文;濃郁而不傷縟雕,沈浸而能為流轉;參漢賦之句法,而運以當日之唐格。”[7]155意思是它既吸收了駢偶句法,又自有骨氣。
通過綜合營養狀態指數對水庫水質進行富營養化評價,汾河二庫綜合營養狀態指數處于30~50,屬于中營養水體。
三 韓愈散文駢散融合的成因
在駢文為主流、古文衰微的大背景下,韓愈的文道觀念和他古文的創作實踐也有一些矛盾之處。一方面,韓愈的思想與儒家密切相關,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他自是排斥佛老,而且他也認為自己繼承了儒家的真正道統,因此渴望復興儒學、重振古文,這使得他的文章重視現實性和功利性,為此他系統性地提出“文以明道”理論。另一方面,韓愈此舉又使得文與道有了分離,也使得散文的文學性和審美性在文章中得到了更好的發展。雖然韓愈大力倡導古文,想要完全革除浮靡文風,但他對于駢文辭藻與形式之美有著深刻的認識,重視文辭的表達,也注重吸取和借鑒駢文的技法,因此其散文創作呈現出駢散融合之特色。
(一)“文以明道”與對古文的推崇
韓愈散文中有大量通俗化與大眾化的口語詞匯,這些口語化詞匯能使文章更自然簡明,在駢文與古文融合的散文中也更能見其價值。而在一些需要直接抒發感情的作品中,口語化的詞更能體現感情的自然真摯,如《祭柳子厚文》的最后一段無一生僻詞,即使字數固定,也很好地表達了韓愈的哀痛與對友人的贊美。而在刻畫人物和敘事時,口語化的語言更為鮮明生動。《張中丞傳后敘》是韓愈對李翰所著《張巡傳》的補充,韓愈在文中對多個人物的事跡都有刻畫,尤其是對南霽云的描寫無任何套話虛語,也無僻字怪句,口語化的語言皆體現了他對人物透徹的觀察。
在車牌定位模型中改進了Yolov2模型,重組了特征圖,融合多級細粒度特征,以適應車牌在輸入圖片中的結構化特征。為驗證其有效性,以上述自制數據集作為實驗數據,比較Yolov2模型、Yolov2模型與不同特征圖重組、及FAST RCNN所訓練的檢測器效果如圖5所示,訓練時為避免過擬合及提升速度,選用動量常數為0.9,學習率為動態衰減,初始值為0.001,衰減步長為10000,衰減率為0.1,批大小為10,共迭代10次,批迭代次數為5000,框架為Darknet。
在《與馮宿論文書》中韓愈道:“仆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4]220韓愈認為那些隨大眾的時文即駢文是令他下筆都感到慚愧的,其中難有真正的思想和感情,這對于他的傳道也是有礙的。在《答崔立之書》中韓愈又提到“乃類于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4]186,愈發突出自己的審美意味。在《題哀辭后》中韓愈說自己“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4]340,可見他改革文風就是為了習得古道,并發揚自己堅持的道。韓愈在當時能不與時俗合流,踐行自己的為文之法,在古文創作上多有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心中的堅持。在“文以明道”思想的指導下,韓愈推崇古文,并在駢文的主流中開拓出新的道路,使得駢文與古文不斷融合與蛻變。
(二)“文道并重”及對駢文的借鑒
韓愈雖重道,但也并未就此輕文。他提出“文以明道”,但這樣反而使“道”與“文”得以分開,使“文”在文學性上可以單獨地、更好地發展。因此,韓愈的感情可以在文章中不受束縛地表達,他隨意“舒憂娛悲”,甚至“以文為戲”,這也使得他在文學創作方面獲得極大的自由,并取得豐碩的創作成果。韓愈志向高遠,注重文學對現實的社會作用,但并非閉門著書,他的古文也并不是單純的弘道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常被同時代的人不理解,也受到后世儒家學者的批判。但韓愈對駢文有著包容的心態,且有不拘駢散的創作實績,開拓了文章的創作之路。即使面對諸多不理解,韓愈依然堅持自己獨特的風格,值得后世學習借鑒。
韓愈創作的《送窮文》《毛穎傳》等文就曾引發諸多爭議。他在《答張籍書》中自我辯解道:“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4]148可見他承認文學在娛樂上的重要作用。后世亦有許多人批評韓愈“以文為戲”,對韓愈所論之道有諸多不滿,這也從側面證明韓愈并沒有完全把文學當成一個純粹的傳道工具。而且,韓愈并不只是研習儒家經典,對諸子百家也都有涉獵。在《進學解》中韓愈就說自己“上規姚、姒”“下逮《莊》《騷》”[4]51,對于不同風格的作品也能從中學到知識,從而充實自己的文章。韓愈的觀念并不狹隘,因此其散文既能傳承厚重的思想,又能吸收駢文的形式。
法拉利812 Superfast上下車的便利程度不亞于一輛普通的大眾高爾夫,并且駕駛席側車窗可在120公里/小時的車速下保持開啟而不會產生刺耳的噪音。不僅如此,當前車速和擋位等信息還可以實時呈現在副駕駛的眼前,這無疑為駕駛員和副駕駛之間的交流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韓愈散文成就非凡,最重要源于他對文學本質的認識。韓愈認識到文學的獨特價值,認為許多流傳千古的文章與道德和政事并無關系,成就高低主要取決于文學自身的藝術特點。韓愈在《新修滕王閣記》中說“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4]102,這說明他對于駢文的美和功用是有體會的。在《答陳生書》中韓愈也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4]197,他雖然重視傳道,但也注重文辭,而這正是他超越前人之處。“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4]163,韓愈對于“文”的作用有著明確的認識。
將文學視為傳道的工具,這對古文來說也是一種束縛。雖然古文在論述時的生動大都超過駢文,但駢文的文采亦不能完全拋棄。無論駢文還是古文,它們終究具有相同的本質屬性和歷史淵源,且它們的終極指向即明道也有相通之處,但它們的創作終究受到創作者自身才華和經歷的限制。而韓愈能在駢文和散文中找到平衡,文道并重,創作出駢散融合、內容與文采兼具的優秀作品,領導古文運動,并影響后世,可見其才華和能力。袁枚曾道:“韓、柳琢句,時有六朝余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為也。惟其不屑為,亦復不能為,而古文之道終焉。”[8]1549后世學韓愈者多矣,但都難以沖破文體之限反而受其束縛。韓愈將駢文與散文之優勢融會貫通,不持偏見,文章自有高格、終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