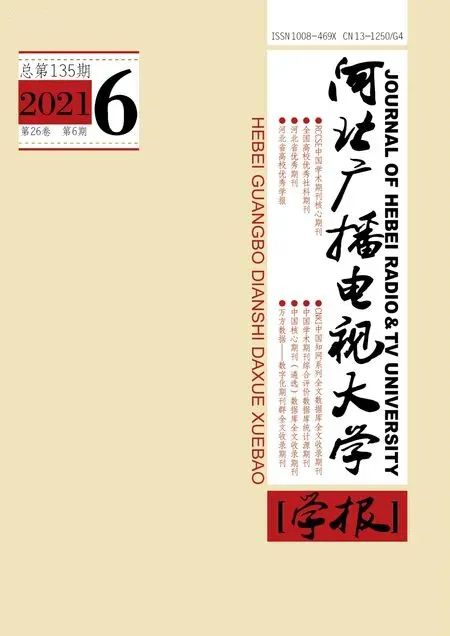1928年國民政府設(shè)立北平特別市的歷史考察
潘 鳴
(河北科技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 河北 石家莊 050018)
1928年4月,蔣介石聯(lián)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對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集團發(fā)動二次北伐。同年6月,北伐軍攻占北京,①本文為表述方便起見,將北京與北平兩個名稱并用,泛指時稱北京,專指1928年6月20日后的國民政府統(tǒng)治時期稱北平。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于6月20日決定將北京改為北平,并設(shè)立北平特別市。北平特別市的設(shè)立,是北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之一。北京自此從傳統(tǒng)的地域型政區(qū)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城市型政區(qū)。②“地域型政區(qū)”指傳統(tǒng)的以“城鄉(xiāng)合治”為主要特征的政區(qū),城市在行政區(qū)中的中心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城市型政區(qū)”是近代以來出現(xiàn)的,以“城鄉(xiāng)分治”為本質(zhì)特征的一種政區(qū)類型。在城市型政區(qū)中,城市不僅是區(qū)域的政治中心,而且已成為區(qū)域的經(jīng)濟中心。參見劉君德、靳潤成、周克瑜編著:《中國政區(qū)地理》,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頁。設(shè)市后,北京擺脫了以往條塊分割的管理模式,建立了統(tǒng)轄全市各項行政事務(wù)的政權(quán)機構(gòu)北平市政府,為當(dāng)代北京城市管理系統(tǒng)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
目前學(xué)術(shù)界的相關(guān)研究對國民政府設(shè)立北平特別市的活動多有涉及,且一些論著對北京設(shè)市在市制③市制指城市的管理體制,包括城市的行政組織結(jié)構(gòu)、職能結(jié)構(gòu)、管理方式和運行機制。參見劉君德、范今朝:《中國市制的歷史演變與當(dāng)代改革》,南京:東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變革層面上的重要意義給予了充分肯定。④如有研究者指出,北平特別市的設(shè)立使北京完成了城市功能轉(zhuǎn)型,北京由國家的附庸轉(zhuǎn)變?yōu)榫哂凶灾我饬x、獨立法人意義的城市(孫冬虎、王均:《民國北京(北平)城市形態(tài)與功能演變》,廣州:華南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頁);另有研究者指出,北平市政府的組建改變了以前市政機構(gòu)政出多門、事權(quán)分散的局面,北京自此成為一個獨立的城市實體,開始進行系統(tǒng)的近代意義上的都市建設(shè)(袁熹:《近代北京的城市管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然而既往學(xué)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多聚焦于設(shè)市前后各方圍繞國都南遷引發(fā)的爭論以及遷都對北平經(jīng)濟社會造成的影響等方面①參見李淑蘭:《北京史稿》,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頁;曹子西主編,習(xí)五一、鄧亦兵著:《北京通史》(第9卷),北京:中國書店,1994年版,第40頁;王崗主編:《北京政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9頁;許慧琦:《故都新貌:遷都后到抗戰(zhàn)前的北平城市消費》,臺北:臺灣學(xué)生書局,2008年版,第33-39頁;陳鵬:《試論1928年遷都對北京的影響》,《北京社會科學(xué)》,2010年第4期等。,而對設(shè)市過程中的政治運作及其產(chǎn)生的影響關(guān)注較少。②王煦注意到了派系政治活動對北平市政府的組建及運作產(chǎn)生的影響,但分析較為簡略,無從展現(xiàn)各方勢力角逐互動的過程。參見王煦:《舊都新造:民國時期北平市政建設(shè)研究(1928—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3頁。如果仔細檢視近年來新開放的一些檔案資料,我們會發(fā)現(xiàn)設(shè)市過程復(fù)雜曲折,不但市制模式的選擇深受派系角力的影響,新市制的實際運行情況也與設(shè)計初衷存在較大偏差。本文以設(shè)市過程中的派系政治活動為切入點,通過梳理解讀有關(guān)各方的檔案資料,并與當(dāng)時的報刊輿論比堪印證,嘗試重建國民政府設(shè)立北平特別市的相關(guān)史實,進而揭示這一過程在北京城市發(fā)展歷程中的深遠影響。
一、北平特別市設(shè)立的歷史背景
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中,城鎮(zhèn)只是地域型政區(qū)中的行政中心或經(jīng)濟中心,而非單獨的一級行政區(qū),古代的北京也不例外。在漫長的帝都歲月里,北京城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一直實行由國家與地方行政機構(gòu)共同進行管理的雙重管理體制。清代由步軍統(tǒng)領(lǐng)衙門、五城兵馬司及順天府下轄的大興、宛平兩縣共治京師的模式正是這種雙重管理體制的典型代表。晚清庚子事變中,北京原有的城市管理體系遭到嚴(yán)重破壞。此后經(jīng)過清末的官制改革,大、宛兩縣逐步退出對北京城區(qū)的管理,北京由此形成了中央各部的派出機構(gòu)直接管理市政與警察機構(gòu)兼辦市政的體制。民國肇建后,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北京市政的體制進一步發(fā)展。1912年,清末北京的教育管理機構(gòu)京師督學(xué)局改組為京師學(xué)務(wù)局,隸屬于北京政府教育部;次年,清末承擔(dān)京師主要市政管理職能的內(nèi)外城巡警總廳改組為京師警察廳,隸屬于北京政府內(nèi)務(wù)部。③袁熹:《近代北京的城市管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第19頁。1914年4月內(nèi)務(wù)總長朱啟鈐奉令“督辦京都市政”,并于同年6月建立同樣隸屬于內(nèi)務(wù)部的京都市政公所。④京都市政公所編纂:《京都市政匯覽》,北京:京華印書局,1919年版,第1頁。同年10月4日,北京政府頒布《京兆尹官制》,將順天府改稱“京兆”,設(shè)立京兆特別行政區(qū),直隸于中央政府。⑤《京兆尹官制》,《政府公報》,1914年第869號,第5-6頁。
民初由中央各部派出機構(gòu)直接治理京師的模式,體現(xiàn)了北京政府在市政管理專業(yè)化方面的長足進步。但就行政區(qū)劃而言,北京城區(qū)仍是傳統(tǒng)的地域型政區(qū)京兆區(qū)的一部分,并沒有建立獨立的城市政權(quán),既往政出多門的管理格局也無從改變。京師學(xué)務(wù)局的一位科長曾撰文指出,當(dāng)時北京的地方行政機關(guān),均直隸于中央政府,無最高行政長官為之統(tǒng)轄,“致地方一切事業(yè),無通盤計劃,遂未能平均發(fā)展”。京師“雖名為首善之區(qū),實無異無主之地,以視各省區(qū)由最高行政長官負責(zé)者,不諦霄壤”。⑥姚金紳:《京師學(xué)務(wù)局之組織及行政》,《京師教育周報》,1927年第1卷第6-7期合刊,第10-11頁。“九龍治水式”的市政管理體制嚴(yán)重制約了北京的城市發(fā)展,建立獨立的城市型政區(qū)是未來的必由之路。
北京政府曾于1921年7月頒布《市自治制》,將北京定名為“京都市”,表示要組織民選的自治機構(gòu)來管理市政。不過《市自治制》深受當(dāng)時日本地方行政制度的影響,仍將“市”定位為地域型政區(qū)中的自治體,而非有獨立地域的行政實體。后來因時局動蕩,《市自治制》所規(guī)定的自治機構(gòu)也未能在北京建立起來。⑦王均:《京都市的概念與地域》,《中國方域——行政區(qū)劃與地名》,1996年第2期。
這一時期真正在市制變革上取得重要突破的是南方的國民黨政權(quán)。1921年,孫中山的獨子孫科受廣東省長陳炯明委派,草擬了《廣州市暫行條例》8章57條,不久正式施行。《廣州市暫行條例》明確規(guī)定“廣州市為地方行政區(qū)域,直接隸屬于省政府,不入縣行政范圍”;并仿照當(dāng)時美國市政機構(gòu)的組織模式設(shè)立市行政委員會(相當(dāng)于市政府),“市行政事務(wù)由市行政委員會議決執(zhí)行之”,市行政委員會由市長與各局局長組成,市長綜理全市行政事務(wù),為行政委員會主席。⑧《廣州市暫行條例》:廣州市市政廳總務(wù)科編輯股編:《廣州市市政例規(guī)章程匯編》,1924年,“市制”,第7-18頁。《廣州市暫行條例》確立了市作為國家行政建制的地位,明確了市行政機構(gòu)屬于一級國家政權(quán),由此開創(chuàng)了日后國民政府時期的設(shè)市模式。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立即著手組織上海和南京這兩個東南大都市的市政府。同年5月7日和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先后通過了內(nèi)容基本相同的《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與《南京特別市暫行條例》,規(guī)定上海和南京兩市直轄于中央政府,不入省縣行政范圍;兩市市長由中央政府任命,綜理全市行政事務(wù)。①《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國民政府公報》,1927年寧字第2號,第12-21頁;《南京特別市暫行條例》:《國民政府公報》,1927年寧字第5號,第9-17頁。滬、寧兩市組織條例的頒布,標(biāo)志著國民政府的城市管理體制進一步成型,為將來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施新市制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
二、二次北伐與北平特別市的設(shè)立
1928年4月,國民政府舉行二次北伐,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分別率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集團軍向張作霖統(tǒng)率的安國軍發(fā)起攻擊。5月,李宗仁、白崇禧所率的第四集團軍也加入北伐軍的序列之中。雖然蔣介石在出征誓師時表示此役的目標(biāo)是“直搗幽燕,長驅(qū)關(guān)外”②《渡江北伐告誡前方將士書》(1928年4月1日),秦孝儀主編:《“總統(tǒng)”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95頁。,但國民政府在二次北伐開始時并未對北京未來的行政建制作出具體安排。不過北伐軍出師后,蔣介石親率的第一集團軍勢如破竹,同年5月1日即已攻下山東省會濟南。此時國民政府認(rèn)為,占領(lǐng)北京、天津等華北大都市似已不成問題,但還未制訂“全國共同適用之(市)組織法,以致設(shè)市以前既無標(biāo)準(zhǔn)可資依據(jù),設(shè)市以后與關(guān)系省市縣又每因權(quán)限問題及確定區(qū)域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③內(nèi)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纂:《內(nèi)政年鑒》,“民政篇”第一章,“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B)107頁。。因此,5月2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百三十九次會議議決將“市政府組織法交法制局起草”④《第一百三十九次中央政治會議》,《中央日報》(上海)1928年5月3日。。然而就在次日,日本突然出兵濟南,打亂了國民政府的北伐部署。蔣介石很快決定第一集團軍繞道北伐,但不久又得到情報,稱“日使煽動各國公使,謂借口于辛丑之不平等條約,出兵北京云”,這增加了蔣對北伐軍接收北京時日本可能出兵干涉的顧慮。⑤周美華編注:《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3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版,第325頁、第330頁、第331頁。此時蔣介石意識到由第一集團軍直接接收京津已不現(xiàn)實,遂制定了“奉軍退出關(guān)外,京津由第三集團軍和平接收”的計劃,并在取得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闿等人的同意后,于5月22日電告閻錫山。同日,蔣介石還把這一計劃電告給馮玉祥,稱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奉軍在“我軍互爭京津之時”,乘機“蹈隙反攻”⑥周美華編注:《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3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版,第396-397頁。。在當(dāng)時北伐軍的四個集團軍首領(lǐng)中,閻錫山與奉系和日本的關(guān)系都較好,由閻錫山來和平接收京津,可望得到奉系和日本的諒解與合作。⑦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20頁。
此后各路北伐軍進展順利,很快迫近京津,攻占北京后京兆區(qū)的存廢問題也被提上議事日程。5月29日,蔣介石前往河南新鄉(xiāng)附近的柳衛(wèi)車站會見馮玉祥,“計議一切”。經(jīng)過會談,蔣認(rèn)為“對占領(lǐng)京津之處置及有關(guān)外僑之安慰問題皆已商獲(馮玉祥)同意”⑧周美華編注:《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3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版,第443頁。。次日,蔣介石又趕到已被第三集團軍攻占的石家莊會晤閻錫山,“商收復(fù)北京、天津事宜”⑨閻伯川先生紀(jì)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8年版,第980-981頁。。與閻錫山的會見更讓蔣介石感到滿意,甚至給蔣留下了“與百川兄商談軍事外交政治各事,皆知己之談,其老成謀國,甚足欽佩”的印象。⑩《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8年6月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xué)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然而蔣馮閻三人在未來北京的前途問題上并未達成一致。6月1日,當(dāng)蔣介石尚在石家莊之時,馮玉祥電請第一集團軍第二師師長徐庭瑤轉(zhuǎn)呈蔣介石,就先前蔣對“直省政治設(shè)施及委員人選”的垂詢作出答復(fù)。馮玉祥建議:“直省政務(wù)機關(guān)設(shè)置,似仍應(yīng)按原有規(guī)模,置直隸省政府及京兆特別區(qū)政府”,并請蔣同意其部下鹿鐘麟、何其鞏等人“分別委充直隸省政府及京兆特別區(qū)政府委員”,明確要求保留京兆區(qū)。①《馮玉祥電徐庭瑤轉(zhuǎn)蔣中正》(1928年6月1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典藏號:002-090101-00004-040。次日,離開石家莊的蔣介石南下柳衛(wèi)車站,將與閻錫山會談的結(jié)果通告馮玉祥。此時馮玉祥得知蔣介石已決心要將京津地盤交給閻錫山,只得表示退讓,作出“頗能以公忘私”的姿態(tài)。②周美華編注:《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3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版,第471頁。蔣介石走后,馮玉祥又立即致電閻錫山,表示“所有直隸省政府及京兆特別區(qū)政府主席人選,至希迅速推薦,以便早日決定,早日進行”③《馮玉祥六月二日冬電》(1928年6月2日),《民國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8年版,第985頁。。5日,閻錫山回電馮玉祥,表示“所有直隸京兆暨各特別區(qū)用人、行政事宜,敢不竭其愚誠,勉力籌計”④《復(fù)馮玉祥歌辰電》(1928年6月5日),《民國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8年版,第984頁。。實際上也表明了希望保留京兆區(qū)的態(tài)度。至于為何馮閻兩人都主張保留京兆區(qū),這明顯與當(dāng)時的“遷都之爭”有直接關(guān)系。北伐軍進入北京前夕,國民政府未來的建都地點已成為當(dāng)時輿論關(guān)注的焦點問題。馮、閻兩人作為北方軍事集團的首領(lǐng),自然都希望國都留在北京,以便對中央政府直接施加影響。⑤關(guān)于兩次北伐期間的遷都之爭及其背景,參見許小青:《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兩次遷都之爭》,《暨南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2年第6期。保留京兆區(qū),明顯是其阻止國都南遷的重要手段。
與此同時,由著名法學(xué)家王世杰任局長的國民政府法制局通過“一面研究,一面分函各特別市政府及普通市政府,征詢施政實況及改訂組織法之意見”,很快“分別草就《特別市組織法草案》及《市組織法草案》”,提交中央政治會議。⑥內(nèi)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纂:《內(nèi)政年鑒》,“民政篇”第一章,“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B)107頁。經(jīng)5月30日召開的該會第一百四十二次會議決議,“指定薛篤弼、蔡元培、李烈鈞、孔祥熙、陳果夫五委員審查,由薛委員召集開會,南京、上海兩特別市得派代表陳述意見”⑦《第一四二次中央政治會議》,《中央日報》(上海)1928年6月1日。。法制局在《特別市組織法草案》的起草說明中表示,該草案以南京、上海兩特別市的組織法為范本,“對于現(xiàn)行制度大體予以保存,以免新舊法規(guī)交替多事紛更”。據(jù)此,該草案“總則”部分第一條即規(guī)定:“特別市直隸國民政府,不入省縣行政范圍。”⑧內(nèi)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纂:《內(nèi)政年鑒》,“民政篇”第一章,“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B)107-108頁。草案公布后,圍繞著“特別市之地位、隸屬及職權(quán)”等問題,國民政府內(nèi)部出現(xiàn)了“絕對相反之兩種意見”。滬、寧兩特別市政府代表支持草案原則,認(rèn)為“特別市政府為辦理全市行政之事務(wù)機關(guān),市區(qū)以內(nèi)國家行政事務(wù),不應(yīng)委諸省政府辦理”。而主管全國地方行政事務(wù)的內(nèi)政部則主張“市為自治單位,不能變?yōu)樘貏e行政區(qū);特別市應(yīng)隸屬于省政府;特別市政府不應(yīng)兼理國家行政”⑨內(nèi)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纂:《內(nèi)政年鑒》,“民政篇”第一章,“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B)112頁。。值得玩味的是,此時的內(nèi)政部長正是馮玉祥的部下薛篤弼,而副部長則是閻錫山的部下趙丕廉。內(nèi)政部作此表示,恐怕不無弱化北京設(shè)市后的地位,以策應(yīng)馮、閻保留京兆區(qū)主張的意圖。
此時蔣介石早已下定決心定都南京,自然不會贊同繼續(xù)保留京兆區(qū)。⑩蔣介石在同年6月18日的南京軍校紀(jì)念周講話中明確表示:“國都問題不應(yīng)再來討論,總理早已確定”,并強調(diào)國都“(設(shè))在北京毫無理由”。周美華編注:《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3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版,第529-530頁。6月4日,經(jīng)蔣介石授意,國民政府發(fā)表閻錫山為京津衛(wèi)戍總司令,由閻錫山部接收京津已成定局。6日,蔣介石致電馮玉祥,告知“中央諸人多主張京兆區(qū)以大興、宛平二縣劃為北京特別市范圍之內(nèi),以其余縣劃歸直隸省內(nèi),以京兆名稱至今復(fù)不能存在也”,并征詢馮玉祥對此的意見。?《蔣中正電馮玉祥》(1928年6月6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典藏號:002-090101-00004-304。馮玉祥意識到自己已被排斥出局,只好復(fù)電表示“京兆特別區(qū)名稱取消,正符鄙意”?《馮玉祥電蔣中正》(1928年6月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典藏號:002-090101-00009-128。。而作為既得利益者的閻錫山,自然更不會再堅持前議了。8日,第三集團軍孫楚部首先進入北京。?《國民革命軍孫楚部今日入城接防》,《世界日報》1928年6月8日。當(dāng)日下午,第三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商震在京師總商會代表閻錫山發(fā)表八項意見,其中提到:“國民政府確已取消京兆名稱,并將所屬各縣歸于直隸范圍,將來如何,應(yīng)俟閻總司令到京后方能決定。”①《商震談話》,《世界日報》1928年6月9日。然而未來北京的行政建置并非閻錫山所能決定。6月12日,即閻錫山進京的次日,受蔣介石直接領(lǐng)導(dǎo)的戰(zhàn)地政務(wù)委員會主席委員蔣作賓率領(lǐng)該會人員抵達北京,準(zhǔn)備接收京兆及直隸的各項政務(wù)。蔣作賓在抵京次日向新聞界表示:“按照中央意見,將于北京趕速成立特別市,天津亦然,使有多人專力于都會市政之整頓。京兆特別區(qū),應(yīng)予廢除。”②《蔣作賓之重要談話》,《世界日報》1928年6月14日。此時廢區(qū)設(shè)市已是水到渠成。14日,譚延闿主持召開國民政府委員會第七十二次會議,內(nèi)政部長薛篤弼在會上正式提出“關(guān)于直隸省京兆區(qū)名稱之改定及區(qū)域之劃分”方案三種:
(一)直隸、京兆兩省區(qū)舊管區(qū)域合并為一,改名朔方省或冀北省。(二)直隸京兆兩省區(qū)管轄區(qū)域仍舊,惟將直隸省改為河朔省,京兆改北平區(qū)。(三)將直隸原有之口北道屬十縣及舊名永遵屬十縣,一律劃歸舊京兆區(qū),改名北平省,除口北道屬及永遵屬各十縣外之舊直隸管轄區(qū)域,改名河朔省。
同時,薛篤弼還正式提議“北京及天津均宜定為特別市,設(shè)置特別市政府”③洪喜美編:《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jì)錄匯編》(第2冊),臺北:“國史館”,2000年版,第308頁。。會議決議將此案送交中央政治會議審議。此時直隸已落入閻錫山的夾袋之中,他自然不愿將直隸省和京兆區(qū)劃為兩省或繼續(xù)保留京兆區(qū)。因此,閻錫山很快與蔣作賓會商,通過他向國民政府陳述京兆直隸“宜合并不宜劃分之意”,并于18日致電在南京的趙丕廉,令其秘密征求直隸籍國民黨元老張繼的意見,如果張繼也同意此議,“即請其代表出席國務(wù)會議說明之”④《致趙丕廉巧電》(1928年6月18日),《民國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8年版,第1005頁。。6月20日,譚延闿主持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四五次會議,與會者“議事至一時乃散,章程多費時間也”⑤譚延闿:《譚延闿日記》(第19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53頁。。會議根據(jù)國民政府秘書處送交的薛篤弼所提“對于京兆直隸區(qū)域名稱問題”的三種辦法作出如下決議:
(一)直隸省改名河北省。(二)舊京兆區(qū)各縣并入河北省。(三)北京改名北平。(四)北平、天津為特別市。⑥《中央政治會議對于京兆直隸區(qū)名稱問題之決議》,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1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yīng)社”,1959年版,第4060頁。根據(jù)《革命文獻》編撰者所加的按語,“河北”“北平”兩個名稱都是譚延闿當(dāng)天在會場上提出的,并非出自薛篤弼提交的方案。
同次會議還議決通過了《特別市組織法》,該法“總則”第一條明確規(guī)定:“特別市直轄于國民政府,不入省縣行政范圍。”⑦《特別市組織法》(1928年6月2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政治”(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頁。至此,作為首都的“北京”降格為當(dāng)時國民政府設(shè)置的四個特別市之一的“北平”,但也由此成為脫離地域型政區(qū)的城市行政實體。
三、北平特別市設(shè)立的得失探討
北京政府的“自治”市制模式在京師籌備數(shù)年終無結(jié)果,但國民政府的“訓(xùn)政”市制模式卻因無需進行調(diào)查戶口、組織選舉等工作,在接管北京僅一個月后就將設(shè)市計劃變?yōu)楝F(xiàn)實。1928年7月13日,首任市長何其鞏宣誓就職,北平市政府正式成立。依照《特別市組織法》,市政府設(shè)立財政、土地、社會、公安、衛(wèi)生、教育、工務(wù)、公用八局,舊有的京師警察廳及京師學(xué)務(wù)局,均予撤銷,“市行政始告完整”⑧北平市工務(wù)局編印:《北平市都市計劃設(shè)計資料》(第一集),1947年,第9頁。。北平特別市和北平市政府的設(shè)立,標(biāo)志著北京的城市建設(shè)已走上規(guī)范化與法制化的道路,市政管理的專業(yè)化水平也顯著提高,是近代北京城市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然而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設(shè)市過程中,南京政府與馮、閻兩大集團之間曾圍繞市制模式發(fā)生過激烈的爭執(zhí),而其后南京政府制定的新市制卻迅速落實,這表明設(shè)立北平特別市其實也是中央政府與北方實力派之間達成政治妥協(xié)的產(chǎn)物。馮玉祥與北京政府有很深的歷史淵源,曾希望借保留直隸省與京兆區(qū)舊制來阻遏中央勢力北進,閻錫山亦有此意。但在“濟南慘案”之后,蔣介石迫于內(nèi)外壓力決定將京津交由閻錫山接收,馮玉祥爭奪北京不成,遂不再堅持保留京兆區(qū),而閻錫山為鞏固既得利益,更是積極與中央政府合作。北平特別市在政治妥協(xié)中誕生,也因此成為國民政府政治版圖中的邊緣地區(qū)。此后北方各實力集團仍不斷在北平上演合縱連橫的政治大戲,北平市政府雖已在形式上實現(xiàn)了市政統(tǒng)一,但用人行政受到當(dāng)時華北政治生態(tài)的諸多影響,依然缺乏穩(wěn)定性。設(shè)市帶來的制度紅利因此不能充分釋放,北平市也難以在短期內(nèi)展現(xiàn)出新氣象。①關(guān)于北平市政府成立后的人事結(jié)構(gòu)與權(quán)力分配,將另文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