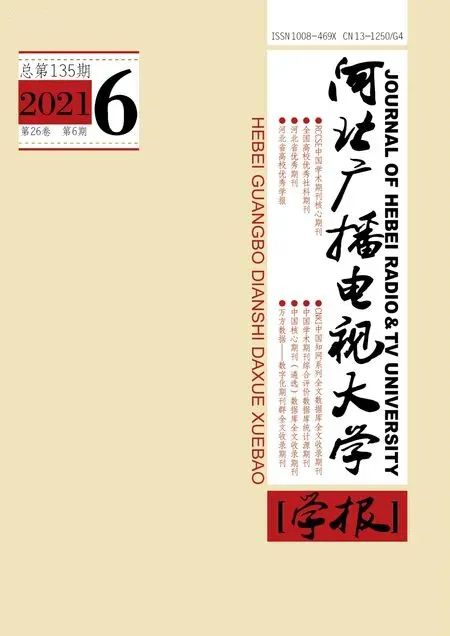論《紅樓夢》中的佛教思想
崔雪茹,徐景文
(西南財經大學, 四川 成都 611130)
《紅樓夢》作為明清章回體小說中最負盛名的作品,作者曹雪芹在創作時融入佛教的思想結晶。曹雪芹“生于繁華,終于淪落”,他受到了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又因為個人的遭遇,而極為明顯地傾向于佛教思想。因緣果報思想、無常觀、人生八苦和色空觀等思想始終貫穿在《紅樓夢》的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中,使整本書蘊含著豐富的佛教文化元素。
一、《紅樓夢》的佛教文化背景
《紅樓夢》誕生于18世紀中國封建社會末期,這段時期看似海晏河清,但其實各種社會矛盾正在不斷激化。作者曹雪芹生長在南京,少年時代過著富貴繁華的生活,但后來家境衰敗,不可避免地由盛轉衰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哀。而《紅樓夢》一書正是曹雪芹于生活貧困之中創作的。藝術來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都離不開它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和作者的個人經歷。
曹雪芹創作的時候正是清朝佛教教育大興之時,尤其是雍正皇帝極為重視佛教,親制了《揀魔辨異錄》和《御選語錄》作為佛教教育的教科書。雍正十一年,他頒布“上諭”,開篇寫道:“朕惟三教之覺民于海內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1]雍正皇帝認為儒、釋、道三教是平等的,應該互相協調融合。他認為佛教五戒十善的目的在于教導人們止惡揚善。“清代統治階級廢除了度牒制度,并且大量印刷佛典刊發全國,僧尼人數激增,使得佛教更為盛行。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都大力推崇佛教。清世祖順治皇帝有‘逃禪’之名,清圣祖康熙更是五次巡幸五臺山,駐蹕菩薩頂。雍正皇帝以‘宗師’自居,并用帝王的威嚴干預禪宗內部派系之爭,還時常與侍從或僧人討論佛教相關問題。”[2]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完成了由雍正開始的漢文大藏經的雕刻,即“龍藏”。“1773年,乾隆皇帝又派學者把漢文《大藏經》譯成滿文,歷時18年之久最終完成,與由藏文譯成的蒙文《大藏經》同時雕印。他明確指出翻譯滿文藏經的目的是使百姓‘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這個態度表明了清代諸位皇帝的共同想法。”[3]
禪宗是中國漢傳佛教中影響最大的一個宗派,融合儒家和道教的文化,是典型的中國化的佛教,其對中華民族思想層面和道德觀念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而儒、佛的漸漸融合同時拉近了封建士大夫和佛教的聯系,每當他們生活困頓不如意時,就會轉去參禪說經,甚至投向青燈古佛,以找尋自我達到超脫的境界。曹雪芹自然也頗受其影響,他能詩善賦,知識淵博,既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又有著錚錚傲骨,不甘世俗,禪宗中對傳統的叛逆性自然是對曹雪芹具有極大吸引力的。禪宗不但影響了這本小說的主題思想、人物形象,也讓這本小說放射出佛光神影,散發著文化獨有的、永恒的魅力。
二、《紅樓夢》體現了佛教的因緣果報觀
佛教教義中講“因緣果報”,在《紅樓夢》中因緣果報思想的影響隨處可見。小說第一回就借用甄士隱的夢境告訴了讀者寶黛前世的緣由,便有了“石頭下凡歷劫,絳珠還淚”的因緣果報。所以,賈寶玉與林黛玉初次見面時就有早已認識的感覺,之后林黛玉的流淚也印證了“絳珠還淚”的因緣果報。
1.因緣果報觀的內涵
佛教常以事物相互間的關系來說明它們產生和變化的現象。其中引起事物產生或毀滅的主要條件叫作因,而外部的輔助條件叫作緣,合稱為因緣。《阿毗達磨俱舍論》卷6說:因緣合,諸法聚生。[4]有生命和情感的萬物所經歷的種種善惡遭遇和生老病死都源于“業”的作用。
晉代釋慧遠的《三報論》分析了因緣果報觀,其中所說的“三業”分別指人的行為、語言和思想活動。“業”又有善惡之分,根據它們不同的性質,就會相應得到不同的報應。“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后報。現報者,善惡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現報是現在造業現在就受報,生報是現在造業要等到來生才受報,后報是現在造業要等到二生或多生以后才受報。這便形成了“輪回”,因此三業、三報、三世便構成了“因緣果報”。[5]因緣即我們常說的因果,實指原因和結果,它連接了過去、現在和未來。因緣果報也就是因果報應、善惡業報,這是一種民間和佛教界普遍流傳的觀念,指有善惡的行為就必會有樂苦的結果。
2.因緣果報觀在《紅樓夢》中的運用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里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幸;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紅樓夢十二曲收尾《飛鳥各投林》中短短幾句,其實就已經將紅樓夢的哲理與核心思想揭示得十分透徹了。文中主人公賈寶玉和林黛玉相識、相知、相愛、相離這一過程,都歸結于前世種下的因——木石前緣。
林黛玉本是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絳珠仙草,賈寶玉則是警幻仙子處的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西方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那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絳珠仙草,十分嬌娜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6](P4)因此,絳珠仙草為了報恩,償還神瑛侍者所給予的甘露,想要把自己一生的眼淚還給神瑛侍者。“還”字正點明了二者的淵源,林黛玉總是因為賈寶玉的各種事情而落淚,這正是絳珠仙草在償還雨露之恩。而在林黛玉初次進賈府的時候,賈寶玉說了一句“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6](P33),彼時的林黛玉也是“一見便大吃一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見過的,何等眼熟!’”[6](P32)這便是前世的因與果,若無前世神瑛侍者與絳珠仙草之因緣,便也無今生的寶黛相知。
既然寶黛愛情起源于前世的“緣”,那么寶黛愛情最終的悲劇結尾一樣逃不過“緣”字。依據佛教所說,這個“緣”便是世界上所有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條件,連接著某個時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構成一個永恒的循環。寶黛愛情從起源到悲劇結尾,便是這個“緣”字串聯其中,構成了一個從前世到今生的必然過程,這也讓《紅樓夢》更加連續流暢,更加體現了佛教思想。所謂“緣起則聚,緣盡則散”,便是寶黛愛情的最好印證。
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務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畫的竟無一個;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6](P16)
寧國府和榮國府過著極其奢華的生活,導致他們日后的家破人亡,說明賈府歷經若干年發展后也該償還他們所積累的善惡了,這是賈府由盛轉衰的因緣果報。
因緣果報亦貫穿在蔣玉菡和花襲人之間。花襲人是寶玉的貼身侍女,而她也一直希望能夠成為寶玉身邊最親近的女人,她通過打擊身邊其他的丫頭來千方百計地博得王夫人的信賴與肯定,但最終還是抵不過命運的安排,她與寶玉是沒有緣分的。在小說第二十八回中,賈寶玉在一次飲酒宴會上認識了蔣玉菡,席中蔣玉菡的一句“花氣襲人知晝暖”牽起了他與花襲人之間的宿怨。后來賈寶玉在得到蔣玉菡的大紅汗巾后,為了回贈,就將花襲人的松花汗巾給了他。在這一來二去不經意的細節當中,蔣、花二人的因緣逐漸展開。賈府沒落后,寶玉看破紅塵,遁入空門,花襲人不得不接受改嫁的命運。她后來又遇到了蔣玉菡,當蔣玉菡看到紅汗巾時,便明白花襲人原來是寶玉的丫頭。因為蔣玉菡心中念念不忘與寶玉的舊情,在萬般糾結后,他特意將寶玉曾經贈與他的那條松花汗巾拿了出來,花襲人看后也就很快明白了那人就是蔣玉菡。在高鶚的續寫部分,蔣玉菡和花襲人最終成婚,也許這樣的結局正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由相互贈送汗巾的“因”,引出蔣、花二人成婚的“果”。
因此,無論是賈府的命運,寶、黛的木石緣,還是蔣、花的汗巾緣,仿佛都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好的。因緣果報在小說中的運用,也為故事情節增添了一種悲劇的色彩。
三、《紅樓夢》體現了佛教的無常觀
佛教中有三大法印之說,即“諸法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7]所謂無常,是指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流動的,而不是永恒不變的;無我則是指事物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只是因緣而生,最后隨緣而滅,因此人對自己的生命沒有主宰的權力。只有經過這樣“無常”“無我”兩個過程,才能最終看到那唯一永恒不滅的涅槃寂靜,也就是佛教所講的“空”。
縱觀整本《紅樓夢》,便會發現這種“無常”“無我”的思想貫穿于這本書的始終。譬如,在第一回“甄士隱夢幻通靈”中,曹雪芹就借甄士隱之口解注《好了歌》,訴說他心中的“無常”。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說甚么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讀完整首解注詞,給人的感覺就是無奈——今天我們還是“金滿箱,銀滿箱”,明天可能就是在路邊乞討的可憐乞丐;年輕的時候還是“脂正濃,粉正香”,年老后就必然是兩鬢斑白、人老珠黃;人生在世時功名顯赫、大富大貴,到最后可能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首解注詞,道出了世事無常變化,貧富貴賤、容貌美丑可能都只是一瞬間的事,指不定下一瞬間人生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人們對此卻無可奈何。這便是佛教的“無常”,對世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無常”,就算所有人都唾棄,它也會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默默地注視著天下蒼生。
在人們看來,這“無常”已是悲慘至極,但在佛教看來,人生的痛苦還不僅僅局限于此,他們認為人的一生不僅僅是“無常”的,更是“無我”的。《紅樓夢》中有哪個角色的人生是可以完完全全由自己去主宰的?薛家婢女香蓮原本是甄家小姐英蓮,卻因一次火災走失,成為了下賤的婢女,最后甚至被薛蟠正妻夏金桂凌辱,而對這一切她完全改變不了,只能自己一個人默默地承受;寶黛愛情早在神瑛侍者和絳珠仙草那一世就注定了不會有什么結果,只能以悲劇收場,他們兩個又能做什么?不過是在黛玉去世后,寶玉傷心欲絕、昏睡幾天幾夜罷了。而到了最后,一切都成了空:甄士隱看破紅塵,隨著跛足道人出家了;顯赫一時的四大家族紛紛家道中落,變得破敗不堪;甚至連寶玉都選擇了出家為僧。這便是佛教所謂最后的“涅槃寂靜”,一切皆空。
這樣的結果看似冷酷無情,甚至讓人心冷于人世間的一切美好事物,實則不然。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就是借這種“無常”“無我”的佛教思想警示人們:人生如夢,當時的美好只是一時的存在,如果陷落其中便會耽誤一生的美好時光,但只要你看破了這些夢幻美景,便能避免苦海沉淪,得到最終的“涅槃寂靜”。
曹雪芹以他特有的筆觸和恢弘的氣勢,描繪出了當時那個社會的紛紛擾擾,筆下充滿了貧富、盛衰、榮辱、生死等的相互轉化。《紅樓夢》中充滿了對人生就如夢幻般的體悟,而這種人生夢幻感也就是對佛教中“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認知,且其中最大的癡迷者是賈寶玉,最大的幻滅者也是賈寶玉,而最大的醒悟者還是賈寶玉。黛玉葬花可謂《紅樓夢》中的經典橋段,它的經典就在于那一首令人如泣如訴的《葬花吟》,纏綿悱惻地道盡了黛玉那積聚一生的憂愁和凄苦。林黛玉孤寂地走在花徑上,掃花、拾花、埋花,看似葬花,實則哀己。《紅樓夢》中彌漫著濃郁的無常情結,這正是來源于佛教中的無常觀。“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消耗……”[6](P54)書中的《恨無常》一曲與開卷第一回中的《好了歌》暗相呼應,表達了作者的無常觀。《好了歌》中“好”便是“了”,在正好的時候,也是悲劇開始的時候。這是作者在看透人世的滄桑無常后對世人的警醒,告誡我們不要迷戀塵世的榮華,而忘記去追求涅槃寂靜的境界。
四、《紅樓夢》體現了佛教的人生觀和色空觀
1.《紅樓夢》中體現的佛教人生觀
紅樓中人人都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求不得、怨憎會、五蘊盛”在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曹雪芹用生動的藝術手法及表現力,闡述了人一生中不免會遇到的各種苦,同時告訴讀者,正是因為這些苦,才磨煉了人們的心志,啟發了人們超越苦難、尋求解脫之道的覺悟。[8]
“老苦”的典型代表是賈母,賈母一生榮華富貴,是賈家最德高望重的人,小說中屢次提到賈母的衰老,比如在第三十九回中,賈母自我嘆息:“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6](P409)賈母不僅是在自嘲,更多的是感嘆年老后雖掌控賈府,兒孫滿堂,受人人敬重但卻事事無能為力。不孝子賈赦欲納自己的得力丫頭鴛鴦為妾,賈母知道后渾身打戰,兒子不孝也是她的遺憾。賈母也曾掌管過府上財政,早已看出王熙鳳的權變機關,眼看守護一輩子的家由盛轉衰卻無能為力,甚至后面還要拿出自己的積蓄來補貼。
“病苦”的典型代表自然就是林黛玉,第三回有這樣一段話:“眾人見黛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弱不勝衣,卻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癥。”[6](P25)身體嬌弱雖造就了她獨特的病態卻有才氣的美感,但我們從開篇就可以預見黛玉凄涼的結局。黛玉寄人籬下,愛而不得,心思縝密,處處小心,最終淚盡而亡,不可謂不苦。
“死苦”的代表是多種多樣的,有很多的小角色之死都讓人印象深刻。比如秦鐘之死,“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鐘魂魄哪里肯就去,又記念著家中無人管理家務;又惦記著智能兒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6](P158)秦鐘臨終之時是有悔恨之意的,他出身寒門,被家族長輩寄予厚望,卻誤入歧途,放縱情欲,失了功名,又失了親人,他的死暗含著秦家的終結。
愛別離之苦,指眾生不由自主與相愛之人或事離別的痛苦。最令人嘆息的是大觀園的十二金釵,美貌絕倫,才情出眾,可惜紅顏薄命,大都香消玉殞。林黛玉愛情親情均是求而不得;薛寶釵雖并無大苦,但夫君婚后出家,不可謂不苦;元春自小遠離家人,宮中暴卒;探春精明能干卻不得不遠嫁;迎春嫁給“中山狼”,被折磨至死;惜春看破紅塵,出家為尼,獨守青燈古佛。如此,愛而不得幾乎是大觀園中女性共同的結局。
2.《紅樓夢》中體現的佛教色空觀
(1)佛教色空觀的基本含義。《心經》“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9]這句話是對佛教色空觀的集中闡釋。色,不僅指女色,還指物欲縱橫、五彩斑斕的世界。空,是色的根本。“色”與“空”的關系為“由空見色,由色入空”,欲望、離別、煩惱是修行色空觀的三大障礙。
(2)《紅樓夢》中的色空觀。《紅樓夢》第一回中寫道:“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6](P3)由此可見,《紅樓夢》從一開始就與佛教的色空觀結下了情緣。
色空觀在人物上的體現。無才補天的頑石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帶入紅塵,由空見色。這一過程是在說賈寶玉的經歷,他投胎到富貴的賈府,身邊又有眾多才貌雙全的女子做伴,并與這些人情感交織,寶玉便由色生情,傳情入色。在整部小說中,寶玉悟情的過程是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的。首先,他周旋于園中各姐妹之間,因產生的“濫情”而感到煩惱。他想同時討好園中所有他喜歡的姐妹,并努力讓大家不發生爭執,可他在其中的調和不但失敗了,自己還遭到貶謗。寶玉時喜時悲的生活狀態,讓他發出“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的感嘆,這是寶玉悟情的開始。其次,他又說,如果他趁著各姐妹們還在世,自己先死去,讓姐妹們的眼淚流成大河,將他的尸首漂到偏僻安靜之處,他便也死得得時了。然而當他在梨香院遭冷落后,便又從此深悟:人生情緣分定不同,等將來自己離世了,也不知道誰會真正為自己而哭泣。從這里他開始轉變為專情。最后,在黛玉問了寶玉很多問題后,寶玉在經過一番思考后有了“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的覺悟。這時他破除了色空觀的障礙,達到了“空”。所以也就有了最終寶玉的結局,他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而去,自此了無蹤影。
色空觀在詩詞上的體現。跛足道人唱的《好了歌》中,“好”與“了”的關系就如同“色”與“空”的關系,并且“好”就是“色”,“了”就是“空”。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10]
在看透人世的滄桑無常后,作者警醒世人不要因迷戀塵世的繁華而忘記了追求“空”的境界。書中“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真”“有”為色,“假”“無”為空,都體現了佛教的色空觀。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談到,《紅樓夢》中的解脫是真解脫,他說:“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歷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歷數千里冒不測之險投縲紲之中所索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11]可見,佛教的“空”貫穿了《紅樓夢》整本書。
佛教有八苦,《紅樓夢》中人人都因為這些苦而煩惱,強權橫行,官員貪腐,人性敗落,有才尚需有運,有家世方可談用武之地,不平等是主旋律,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空”才是最后且唯一的超脫。對賈府中的人來說,悟透名利才是空,比如在第三十一回中,襲人被寶玉踢了一腳而吐血,想到“少年吐血,年月不保”[6](P381)等話,可見生命脆弱,走到盡頭之時,往往更能放下功利之心。賈府眾人悟透的不僅僅是名利富貴,還有對情的執念。人身在局中,自然是當局者迷,只有悟透才可以跳到局外。癩頭和尚寫給寶玉的兩首詩:“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只因鍛煉通靈后,便向人間惹是非!”“粉漬脂痕污寶光,房櫳日夜困鴛鴦。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債償清好散場!”[6](P256)這兩首詩是曹雪芹對賈寶玉一生經歷和最后結局的概括。“賈寶玉這樣的闊少爺,本來可以無拘無束、無憂無慮地安享富貴榮華,再隨便讀幾句子曰詩云,寫點八股時文,功名利祿也不在話下。但賈寶玉沒有走這條道路。由于當時的時代和社會的影響,使他逐漸產生了叛逆思想,與自己的階級和家庭發生了越來越尖銳的矛盾,招惹了不少‘是非’,遭到種種打擊和摧殘。這使他透過包圍自己的胭脂紅粉,進一步看清了丑惡的環境,更增強了他的反抗,最后夢醒散場,出家了事。詩中的‘散場’,也是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及整個封建社會必然崩潰、沒落的命運的暗示:所謂雍乾盛世和那表面的暫時繁榮不會太長久了,徹底衰微破敗和樹倒猢猻散的日子在等待著他們。”[12]
曹雪芹想表達的空,除了揭示只有空才能解脫之外,他也是在嘆息,世間之人沉溺于世俗之中無法擺脫,不斷輪回于世間,經受折磨。人生的悲劇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這是最讓人痛心的。
在書的開頭,有一個叫英蓮的女子被人販子抱走,其父甄士隱丟了孩子又丟了房子,后聽了一僧一道的《好了歌》幡然醒悟,遂離開了。英蓮就是后面的香菱,英蓮音通“應憐”,不僅是暗指她身世凄慘,更重要的是指她忘了自己的來處。書中第七回,周瑞家的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里?”“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里的人?”[6](P74)香菱都答說不知道。不知道也就是忘記了過去的痛楚,依然沉溺于人間樂事,到最后落得不如意的結局。如果從空的角度看,悲而不自知,身在苦痛之中也不自知,自然是難以擺脫苦痛的,更難以遁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境界。
《紅樓夢》作為晚清時期最著名的章回體小說,在描繪當時社會風貌的同時,作者曹雪芹也將自己的情感色彩和感悟體驗融入其中,借著書中各色各樣的人物之口訴說著自己對佛教的感悟與理解——寶黛愛情的緣、小說中人物命運的“無常”和“無我”、四大家族的因果報應,使得《紅樓夢》富有了對佛教思想的深遠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