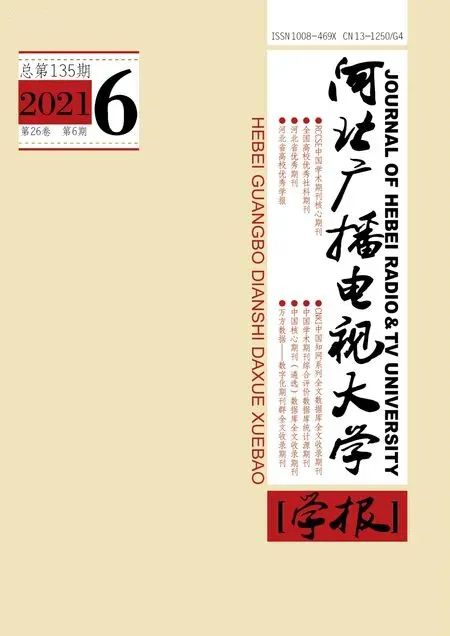李提摩太與晚清洋務派官僚之間的文化博弈
楊秀敏,牛云平
(1. 河北經貿大學 外國語學院, 河北 石家莊 050061; 2. 中國人民大學 外國語學院, 北京 100872)
1870年李提摩太受英國新教浸禮派的派遣來中國傳教,他以一個拯救者的心態,迫切希望以“肉體拯救”和“心智拯救”為手段,來最終實現對中國人的“靈魂拯救”,完成“中華歸主”的傳教使命。但在與晚清洋務派官僚之間的文化博弈中,李提摩太的傳教努力往往事倍功半,因為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對于他的“打包兜售”的做法始終存有戒心。他們對于作為傳教手段的“肉體拯救”和“心智拯救”基本上是接受的,甚至是歡迎和感恩的,但對于李提摩太的“靈魂拯救”的傳教目的,始終保持警惕和抵制心態。在這種情況下,李提摩太的任何傳教努力都會“大打折扣”。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是晚清外交史上的關鍵人物,他們與李提摩太之間的文化博弈,成為我們從微觀上了解晚清中西方文化交流與沖突的一個關鍵切入點。
一、李提摩太的妥協與堅持
李提摩太在1870年來到山東,最初兩年在煙臺傳教,但收效甚微。他很快就意識到外國傳教士通常采用的直接灌輸的說教方式在中國根本行不通,雖然他每天都滿懷希望地去布道,工作態度也勤勤懇懇,但這種傳教方式毫無成效,這使他非常沮喪。“我了解到,當地很多做生意的人一起立了一個誓約,表示絕不進禮拜堂去支持外國人的布道。因而,那些參與聆聽布道的,大部分是來自農村的、偶然路過的流浪者,他們出于好奇,來看看外國人及其野蠻的服飾。在煙臺的前兩年,我盡力嘗試以街頭布道的形式傳播福音,但取得的成效卻不值得一提。從那以后,我開始實施‘尋找上等人’的計劃。”[1](P32)直接傳教的失敗迫使李提摩太意識到必須尋求新的傳教策略。很快,他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向:要想靠近“上等人”的靈魂,傳教士就必須首先要幫助官僚階層解決迫在眉睫的現實困難,即一方面要幫助官僚階層對普通民眾實施“肉體拯救”,解決百姓的病痛溫飽;另一方面還要以“西學”架起與官僚階層溝通的橋梁,滿足他們在心智上對西學的好奇與渴求,通過對他們進行“心智拯救”來謀求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從而為傳教事業減少阻力鋪平道路。如果缺少了“肉體拯救”和“心智拯救”這兩種手段作為中間鋪墊,傳教士就根本無法靠近中國人,尤其是對社會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上等人”,更談不上去實現所謂“拯救中國人靈魂”的目標。
在中國45年的傳教活動中,李提摩太利用“肉體拯救”和“心智拯救”方式成功地融入晚清的社會生活中。他通過賑災、治病、設立孤兒院和學校、創辦報刊,舉辦科學演講和有獎征文等活動成功吸引了官僚階層的關注,并與當時眾多上層官僚保持著密切聯系,對晚清社會生活發揮了深刻影響。對于作為傳教士的李提摩太來說,在“肉體”“心智”“靈魂”三種救贖中,顯然“靈魂拯救”才是最終目的,而“肉體”和“心智”只不過是輔助手段,但在現實面前,他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協,在“肉體拯救”和“心智拯救”方面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但是他仍然希望將“靈魂”的拯救“夾帶”其中。但事實上,晚清官僚一直對李提摩太的企圖心知肚明。針對“肉體拯救”和“心智拯救”等活動,他們對李提摩太保持著友善態度和感激之情,甚至多次延請李提摩太參與到俗世政務的改革與管理中,但一旦涉及宗教問題,他們就會立馬翻臉,“忘恩負義”地斬斷李提摩太“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企圖。在這種拉鋸戰中,李提摩太也始終不忘他的傳教使命,在面臨重要抉擇時,頭腦清醒地堅守著自己的立場。以下兩個典型事例,清楚地表明了李提摩太“妥協”背后的“堅持”。
李提摩太晚年在回憶錄中,提到了他與洋務派重要代表性人物張之洞之間的接觸。 張之洞在1882年出任山西巡撫期間,一上任就開始積極籌劃一系列改革措施,謀求政務和經濟上的變革。他在太原府的衙門舊檔里,發現了李提摩太給前任巡撫曾國荃提過的一些關于修筑鐵路、開挖礦藏、開辦工業和制造廠等方面的建議后,便派一個代表團找到李提摩太,問他是否能夠放棄傳教工作,參與山西的政務改革,將自己的觀點付諸實施。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給代表團)的回答是,盡管我理解改革的價值,但我不是個專家。中國的改革要想順利進行,引進大量各個領域的外國專家,是十分有必要的。……不論物質上的進步多么急迫,傳教士所從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我不能完全離開崇高的傳教職位去從事低級世俗工作。因此,我謝絕了巡撫的好意和報酬。……不久,他被改任湖廣總督,駐武昌。他還沒有忘記在山西時我給他提的建議。他建立了一座鋼鐵廠,開始修筑鐵路,開辦各種工業和現代學校。這些都是我在山西時向他提議的。他又一次邀請我參與他的幕府,而我又一次拒絕了。我也有一種感覺,在這邀請下面,仍然遺留著強烈的排外情緒,我擔心那會在工作中導致過多的摩擦。”[1](P150-151)從李提摩太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張之洞的確有魄力和有眼光,頭腦清醒、辦事認真,為了推動洋務,他敢于大膽起用外國傳教士參與到政務的管理和改革之中,但前提是要求李提摩太放棄傳教。而李提摩太雖然對中國當時的“民生”問題比較關切,也對如何改革地方政務,如何推動中國的洋務運動有一些切實的見解和主張。但歸根結底,作為傳教士的李提摩太沒有在張之洞的盛情延請下妥協,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堅守著自己來華傳教的最初設想和底線,不為所動。
另一個事例是發生在義和團運動之后,在山西大學的建立和管理問題上。根據李提摩太的記載,1900年,義和團殺死了很多傳教士和教徒,僅在山西教案中,就有數千名傳教士和當地基督徒被殺。1901年,李提摩太參與了山西教案的善后處理工作。他提議從賠款中拿出五十萬兩,在山西建立一所西式大學,因為他認為教案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教育的落后,建立西式學校可以改變人們的無知和迷信,從而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最后,商定的結果是建立山西大學。山西大學在章程中規定,大學分中、西兩個學部:中學部由中國人負責管理,教授中國傳統學問;西學部由李提摩太負責管理,期限為十年,主要教授西學。在籌建大學的談判過程中,山西巡撫岑春煊派一位道臺找到李提摩太,希望得到李提摩太的承諾,在大學的章程中加上永遠不在學校中教授基督教的條款,對此,李提摩太反應強烈。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是決不會同意這種建議的,因為我覺得,如果接受了這樣的條款,就意味著承認傳教士們所傳授、所信仰的東西對這所大學毫無價值,也就等于承認對傳教士和本地基督徒的屠殺是正義的。”[1](P283-285)雙方就此進行了長達8個小時的談判,雖然清政府的這位道臺非常聰明、很有耐力,也不乏談判技巧,但李提摩太自始至終堅持著自己的主張,就是不肯讓步。
綜上所述,雖然李提摩太積極建議地方官員采取各種改革舉措,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地幫危扶困、救濟災民、創建學校,但這些都不過是為了他所謂的“開化民智”,以接近官僚階層,取得官僚的信任,為傳教創造條件。作為一個傳教士,李提摩太決不甘心僅僅從事對中國人的“肉體拯救”和“心智拯救”。在與洋務派官僚階層的博弈中,他非常清楚自己來中國的目的,也決不會單單去為了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而放棄自己的傳教使命。
二、官僚階層的妥協與堅持
在清王朝上層官僚階層中,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曾國荃、丁寶楨、翁同龢、恭親王、慶親王、袁世凱等都曾與李提摩太有過接觸,其中尤以李鴻章、張之洞與李提摩太的聯系最為密切。梳理史料我們發現,在這些人與李提摩太的交往中,幾乎所有人都表現出明顯的“兩面性”。凡是屬于“肉體拯救”和“心智拯救”層面的問題,一般來說,他們都會采取朋友般的支持態度,有時會主動提供方便,甚至提供一定的資助,與李提摩太成為很好的“工作伙伴”;但是一旦涉及“靈魂拯救”這個根本問題時,他們立馬就會一臉冷漠,毫不妥協。
在上文事例中提到的張之洞對李提摩太的態度,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一方面迫切想從西方人那里尋求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出路,另一方面又對基督教心存芥蒂,極力排斥。
李鴻章與李提摩太的交往就更為頻繁。通過對史料的詳細梳理,我們從中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僚階層在與外國傳教士交往當中所采取的基本態度。
李提摩太與李鴻章的最初接觸就是從“肉體拯救”開始的。1875年,李鴻章帶領一幫人在煙臺準備簽訂《煙臺條約》,當時,李提摩太正負責照料浸禮會在煙臺的醫院。由于李鴻章的很多隨員和士兵都患上了熱病和痢疾,他們便來李提摩太所在的醫院治病。李提摩太不僅很快治好了這些人的病,而且還順帶贈送了一些藥品給李鴻章,讓他分發給他的隨員和護兵,這讓李鴻章對他產生了最初的好感,為此李鴻章還寫了一封信差人送給李提摩太以表謝意。1877年,李提摩太準備去山西賑災。為了防止在途中遇到攔截或阻撓,他出發之前,向李鴻章尋求幫助,李鴻章欣然答應,給他提供了一張通行證。1878年,李提摩太從英國籌集到的救災款經電匯到達上海。但由于當時的中國尚無電報,只能通過船只運送銀子。李鴻章就幫忙派人將這些銀子押送到太原交給李提摩太。1878年,李鴻章上書朝廷稱應對參與賑災的傳教士予以嘉獎,“以慰遠人慕化之誠”。在這里我們暫且不論李鴻章的表述是否妥帖,但他在一定程度上為傳教士爭取到了一分尊重,這對于在賑災中付出了很多努力,甚至是以生命為代價的傳教士來說,也是一種安慰。據李提摩太回憶錄記載:“上報朝廷的奏章中,為參加賑災工作的官員請求匾額和頂戴等賞賜,但那些贊助了大量救濟金,或者冒著生命危險在極容易感染傷寒病的救災現場工作了兩年的外國人,卻不在名單之內。然而,李鴻章卻給我們請賜了爵位……只是在階別上要低得多。”[1](P122)1890年在李鴻章的幫助下,李提摩太獲得了擔任天津《時報》主筆的機會;1894年,李提摩太準備把他發表在《時報》上的文章結集出版,李鴻章以《西學的重要性》為題為李提摩太的文集作序等。由此可見,李鴻章對傳教士在中國積極傳播西學、救災濟困、開醫院、辦報刊之類的活動,多有支持和贊譽,甚至有時候還大膽表現出一種難得的公允態度。
但是在宗教問題上,李鴻章始終是謹慎而警惕的。如同李提摩太在同洋務派官僚階層的拉鋸戰中始終頭腦清醒地堅持他的傳教使命一樣,李鴻章在與傳教士的交往中,在有些時候無論表現得多么友善熱情,他的反基督教立場是自始至終、毫不含混、一以貫之的。他對傳教士的友善態度,是服從于推動洋務運動這個大目標的,而并不表明他在對待基督教問題上會有任何“讓步”。他相信西方文化不過靠的就是軍事、經濟等硬實力,這正是西方稱霸的根基,也正是眼下中國所需,但是他根本無法理解西方的宗教到底能夠給一個國家帶來什么實際上的好處,所以對基督教一直保持高度戒備和排斥。1884年,李提摩太去北京會見公使巴夏禮,提出基督教教會正在遭受來自中國的眾多官員、士紳和一般民眾的干涉、騷擾和迫害。他列舉了14項事例來證明上述觀點,其中第2條就是:“直隸的李鴻章總督在為一本書作序時,事實上是在排斥基督教”。1877年,李鴻章致信給美國康涅迪格州哈特福德的中國留學事務局,讓他們選派資質聰穎的幼童學習法律和礦業,同時指出不要學習傳教和醫學這些行業。因為中國不需要這方面的人才。1887年,李鴻章在一次會談中直接向李提摩太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基督教到底能給一個國家帶來什么好處?”[1](P188)1890年,長江流域發生了許多反對基督徒的事件,李提摩太認為導致這些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清政府的很多書中都有對基督教的誹謗內容。為此,他請求李鴻章“結束針對基督教的各種惡毒的宣傳報道。但他(李鴻章)沒有采取行動的心思”。[1](P195)關于1895年他與李鴻章的交往活動,李提摩太在其回憶錄中失望地寫道:“……在他總督任內,二十年時間里,我一直致力于賑災、出版和中國的改革,但他從來不承認基督教會為中國做了一點好事。針對他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為,畢德格先生(Pethick,美國人,曾任美國駐天津副領事,后入李鴻章幕府做其私人秘書)概括道:‘誰能從荊棘叢中收獲葡萄?’”[1](P241-242)1896年訪美期間,李鴻章在紐約各教會領袖歡迎會上說:“若以大道言之,本大臣恒謂基督之福音,實近于吾儒之圣道。……又考貴國人論道之真源,每曰人一而可分為三:人身,一也;人性,二也;人靈,三也。身以醫院救,性以學校救,靈以教會救。本大臣素佩督理此事之人竭力盡心,其吃緊為人處,實已一無缺憾。所惜救靈一說,儒教奉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訓詞以為圭臬,故至今存而不論;本大臣亦不甚了了,不必多言。”[2](P206)以上種種事例清晰勾勒出了李鴻章面對西方傳教士的另一種態度。雖然他與西方傳教士頻繁交往,甚至被視為晚清官僚階層中最熱衷于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但是在宗教問題上,他一直堅守儒家文化傳統,典型地代表了晚清官僚階層對基督教的拒斥心態。
三、結語:擺脫困境的不同“藥方”
19世紀中后期,晚清官僚階層與外國傳教士之間的文化博弈的實質是對于科學與宗教關系的不同理解。西方傳教士認為科學與宗教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他們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是一種二合一的“配方”:中國既要接受西方的科學又要接受西方的基督教。“科學沒有宗教會導致人的自私和道德敗壞;而宗教沒有科學也常常會導致人的心胸狹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們像一對孿生子——從天堂來的兩個天使,充滿光明,生命和歡樂來祝福人類。我們就是宗教和科學這兩者的代表,用我們的出版物來向中國人宣揚,兩者互不排斥,而且是相輔相成的。”[3](P28)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則更進一步提出,在這兩種“配方”中,基督教比科學更具根本性,中國人只有接受了基督教,才有可能把握西方科學的根本。在《自西徂東》一書中,花之安指出洋務派所做的努力,其實都只不過是徒襲西學皮毛而已。“中國人亦有明白而警悟、謹慎而有為,勤勉而學西國之學者,但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而不得西學精深之理,雖學亦無甚益耳。”[4](P3)他認為洋務派所提倡的西學之于中國,就如同一些攀爬植物寄生在一棵老樹上,雖顯一抹蔥蘢之意,但畢竟攀爬植物沒有根而難以為繼,而老樹也會因為其他植物的寄生日漸枯萎。他說西學根植于基督教,中國人只有接受基督教,才能使西學根深葉茂、果實甜美。“然則中國欲求西國之美好者,須知其從根本而出,其理于何而得乎,非從耶穌道理,何以致此乎?”[4](P3)可以說,花之安的確是敏銳而成功地預言了洋務運動的失敗,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人并非如他所希望的那樣,在接受西方科學后更深一層地走向對基督教的接受。
對于外國傳教士這類兜售基督教的論調,晚清官僚知識階層自然是不屑一顧的。雖然晚清社會已經陷入列強環伺的巨大危機之中,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對于中國官僚知識階層來說,自身文化傳統的內核依然堅不可摧。李鴻章雖然積極倡導洋務,并與外國傳教士頻頻接觸,但他始終恪守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古訓,對于基督教沒有絲毫讓步,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對于中國官僚知識階層來說,即使洋務運動失敗了、戊戌變法流產了,但是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解藥也絕不是轉向基督教,而是要以自身文化傳統為根基,一直沿著科學民主、求富求強的現實目的繼續深入。在這兩種觀點的對立中,已隱約可見在洋務派和改革派退出歷史舞臺以后,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未來之路所可能做出的路徑選擇,同時也可以預見基督教在此后的中國仍然會長期處于被抵制狀態。正如保羅·科恩所指出的那樣:“十九世紀末,傳教士最無成效的說教是向中國人兜售說:西方的知識和制度以及相伴隨的富強,都是根源于基督教。”[5](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