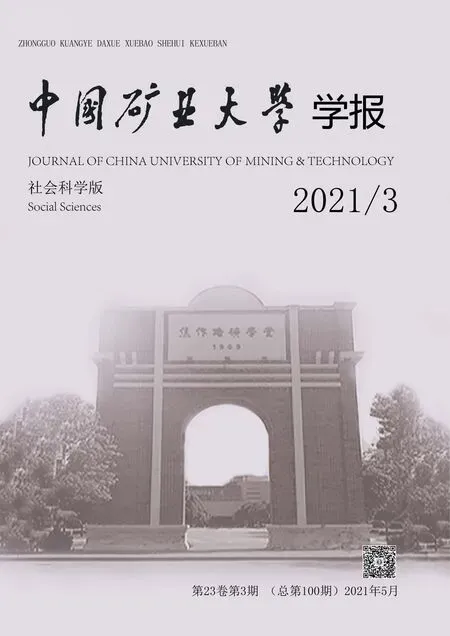家族博弈、精英行為與鄉(xiāng)村治理
疏仁華
2015年9月,在國家實施脫貧攻堅戰(zhàn)略的背景下,筆者有幸赴Y縣F村聯(lián)系結對幫扶對象,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第一次到村里的時候,縣里派到村里的扶貧工作隊隊長談及了F村的一些基本情況,并告之筆者:“這是本縣脫貧工作掛牌督戰(zhàn)的一個貧困村,集體經(jīng)濟薄弱,村委班子建設基礎不夠牢固。”當筆者問及原因時,工作隊隊長說:“家族之間的長期不團結是村莊班子建設和經(jīng)濟發(fā)展滯后的重要原因。”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家族的復興與重建,家族研究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研究者從不同角度闡釋家族與村莊治理的關系,有正效應、負效應和調(diào)和論三種觀點。有學者認為,家族作為非正式制度,在國家資源無法滲透到社會基層的每一個角落時,它完全可以作為國家資源的一種補充,參與村莊治理并發(fā)揮正式制度無法替代的作用。也有學者認為,家族是封建殘余的沉渣泛起,抑制著現(xiàn)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利于鄉(xiāng)村現(xiàn)代制度的運行。持調(diào)和論的學者認為,家族經(jīng)過幾十年的洗禮和自身的嬗變,已逐漸擺脫其落后性的一面,并表現(xiàn)出與當代社會趨同的特征。只要有效地對家族行為進行規(guī)范和引導,家族可以實現(xiàn)華麗轉身,進而成為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那么,F(xiàn)村作為一個有著一定家族背景的村落,其家族行為、家族精英是如何影響村莊政治的呢?它們之間又有什么樣的規(guī)律性聯(lián)系呢?在隨后結對扶貧工作的幾年時間里,筆者多次深入村莊農(nóng)戶,訪談村民,與村干部促膝談心,查閱資料,逐漸了解到F村的家族關系、家族行為與鄉(xiāng)村治理之間的復雜關系,也由此洞察了中國鄉(xiāng)村振興和村莊現(xiàn)代化所面臨的特殊處境和復雜問題。
一、 F村的基本概況與歷史沿革
F村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靠近長江,離Y縣城約60公里的T鎮(zhèn)境內(nèi),村域面積約6.66平方公里。耕地面積2200畝,其中水田約1300畝,旱地約900畝,林地5000余畝,水域面積1400余畝。全村轄19個村民組,有Z莊、C莊、S莊和Y莊4個自然村。全村715戶,總人口2618人,以Z姓和C姓為主,其中Z姓人口占50%,主要居住在Z莊,C姓人口占45%,居住在C莊,另有佘、楊等小姓人口。全村貧困戶101戶,貧困人口277人。
F村1961年前與鄰近的L村是合并村,叫L耕作區(qū),1961年撤區(qū)后成立F大隊,黨組織名稱為F大隊支部委員會,下設3個黨小組,分別是Z莊黨小組、S莊黨小組和C莊黨小組,1984年改F大隊為F村,黨組織名稱更名為F村黨支部委員會,同樣下設原有的3個黨小組。此時F村只有村支部委員會,村支部里有5個支委,其中Z姓有4人,C姓1人。黨支書記由Z姓擔任。村民委員會雖有機構,但由于沒有村民委員會主任,機構實際處在癱瘓狀態(tài),村民委員會的事務實際上由村總支委代理。2011年,村民委員會班子得以健全。2016年上級撤銷F村黨支部委員會,設立F村總支部委員會,下設Z莊、C莊和S莊3個黨支部,共有黨員61人。
F村的村莊矛盾在歷史上主要表現(xiàn)為Z莊Z氏家族和C莊C氏家族之間的矛盾。據(jù)現(xiàn)已年逾八旬的老支書介紹,Z家和C家是明代從江西移民到此定居的,那個時代兩家的先輩還是表兄弟關系,家族之間和睦相處。兩個家族的結怨源于太平天國時期一次保護家園的戰(zhàn)斗。為了共同抵御外侵,兩家商議由C家誘敵深入,Z家斷其后路,結果由于Z家未能及時參加戰(zhàn)斗,貽誤時機,導致C家男丁寡不敵眾,死傷慘重。最后C氏先人發(fā)誓與Z家永不來往,不允許結親,如有違犯,為全族所不允,從此兩家成為世仇。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兩家經(jīng)常會發(fā)生一些民事糾紛。
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家族不同,F(xiàn)村現(xiàn)階段的家族不再有完整意義上的族譜、宗祠、族田、族規(guī)和族長,其重建并非原來家族組織的復原。家族的物質(zhì)象征已基本上不存在,其顯性的標志就是新修的族譜和村莊的一些儀式性活動,比如祭祖、子女結婚和上學等一些集會。家族組織也沒有統(tǒng)一的結構模式和常設機構,只根據(jù)具體的工作或村莊事務的需要進行臨時性的組合,家族中也沒有經(jīng)過村民推選的族長,村里的一些“賢人”“能人”或“熱心人”被村民自發(fā)地認定為“召集人”或“領頭人”,輩分和年齡決定家族事務的傳統(tǒng)日漸式微。
二、 村莊行為:兩個家族之間的博弈
F村的家族行為主要體現(xiàn)在村莊公共資源的分配和村莊事件的處理上。他們相互博弈的不僅僅是家族利益,還有家族的名聲,也就是影響力。在20世紀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前,國家權力直接掌管著村莊,公共資源的分配由人民公社和大隊直接控制,家族之間的爭權奪利未能釀成大的事件,但相互爭奪公共資源也時而有之,如干旱季節(jié)對水資源的爭奪。隨著20世紀80年代國家權力從村莊的撤去和村民自治的推行,這兩個家族便粉墨登場,上演著鄉(xiāng)村政治場域中的一幕幕舞劇。
村莊選舉之爭。根據(jù)村民自治法,村級的村民委員會是由有選舉權的村民直接選舉產(chǎn)生,得票最多的大多是村主任的候選人。2000年前后,F(xiàn)村共進行了3次選舉,基本沒有一次是成功的。村委會的行政職能由鄉(xiāng)鎮(zhèn)任命的村支委代為行使。我們對已逾八旬的村原黨支部Z書記進行了深度訪談。他是一個參軍退伍回鄉(xiāng)的軍人,20世紀80年代末在村里擔任黨支部書記,2007年底卸任,掌管村級事務將近20年。回憶起當年的村莊選舉,他深有感觸地說道:“F村由于歷史上的兩家結怨,開展工作是不易的,每次選舉,鄉(xiāng)上都派許多干部深入農(nóng)村開展工作,希望平衡Z莊和C莊的矛盾。選舉當天,都派派出所民警和聯(lián)防隊員到村里維持秩序,這也體現(xiàn)上級對F村的重視,但每次選舉都有矛盾,C家都認為我是Z姓的書記,肯定偏袒本族。從心里講,我確實希望我們Z家能有人擔任村主任。但上面的意思是希望能選出C姓家族中一個有本事的人來當村主任,以便平衡兩個家族的矛盾,可這種意圖始終未能如愿。尤其是2007年的那次選舉,Z姓和C姓比拼得厲害,雙方通過吃飯、送禮、委托他人打招呼等方式將本村莊在家的村民和打工在外的有選舉權的村民動員回村。另外,雙方還積極拉攏本村的佘、楊等小姓村民參加。鄉(xiāng)干部了解情況后,派駐工作組指導選舉工作,并要求村民公平公正地選出有能力帶領大家致富的村莊領頭人。在選舉當天,C姓的部分村民檢舉Z姓之間存在相互吃請、賄選等情況,要求工作組處理,工作組因為無法取證,宣布選舉正常進行。C家于是認為上級領導偏袒Z姓,便召集了其家族的七八個人,在一個選舉點摔碎了票箱,撕毀了選票。盡管派出所最后處理了部分C姓帶頭鬧事的人,但此次選舉以失敗而告終。”
對這次選舉事件的失敗,我們也找到了當時破壞選舉的幾個C姓人,他們對當年的行為也直言不諱。當問起當年為何“攪局”選舉,他們說,“鄉(xiāng)鎮(zhèn)政府不太公平。一是村支書長期由Z家人擔任,在支委中Z家人也多,這明顯說明上面的干部不把我們C家當回事;二是我們已經(jīng)反映他們請客拉票,但上面不調(diào)查處理,我們認為存在偏袒,所以才干了那件事(指破壞選舉一事)。”但問及“如果現(xiàn)在再進行村莊選舉時,你們采取什么態(tài)度?”時,他們笑著說:“只要公平,不管選出哪家人,我們都會同意的。”
對待當年的選舉風波,鄉(xiāng)鎮(zhèn)政府似乎習以為常。我們也找到了當時聯(lián)系F村并指導村莊選舉的一位鄉(xiāng)鎮(zhèn)干部。他介紹說,“F村兩族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Z姓與C姓之間互不服氣,盡管兩邊都有能力不錯的候選人,但都擔心選上的一方在以后的工作中可能壓制另一方,尤其是C家不服氣,鬧得厲害,他們說,村支書已經(jīng)是Z家人,村主任就應該選C家人。上面(指鄉(xiāng)政府)也想選一個C家人當村主任,以平衡家族之間的矛盾,但真選起舉來(口頭語,就是選舉),上面就無法控制了。至于C家反映Z家拉關系,請客吃飯,似乎兩家都有。在農(nóng)村,相互幫忙吃飯的現(xiàn)象很普遍,說這就是拉票行為,也無法查證。經(jīng)過這么多年的發(fā)展,兩姓之間關系出現(xiàn)了很大和解,但還沒有徹底消融,相互間時常還有些隔閡。作為鄉(xiāng)鎮(zhèn)政府,只能做一些說服、引導等正面工作,不能強行地要老百姓選誰,上面規(guī)定村委會必須由村民自己選舉產(chǎn)生,強行搞出一個村委會,老百姓會上訪告狀的,反而給基層鄉(xiāng)鎮(zhèn)造成不好的影響。”
鄉(xiāng)鎮(zhèn)干部沒有有效地壓制家族力量對選舉的“干擾”,對選舉所采取的這種看似“聽之任之”的態(tài)度,并非他們不作為。他們知道《村民自治法》,更知道村治中各種力量相互牽制的復雜性。在家族之間矛盾還沒有徹底消解的前提下,如果地方政府大包大攬,強行搞出一個鄉(xiāng)鎮(zhèn)領導“滿意”的選舉結果,很有可能導致村莊“雞犬不寧”,出現(xiàn)治理失靈。
對于廣大村民來說,選出一個能力強,能帶村民共同致富的村莊帶頭人是自己的愿望,但這種愿望往往與家族利益關聯(lián)在一起。很多村民往往是站在本族的立場上,考慮較多的是本族的利益。在村民的民主法制意識還未發(fā)展成熟之際,強烈的家族意識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村莊的權力運作。
村民選舉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封閉的民間敘事文本,而是一個融合了國家制度、村莊基礎、鄉(xiāng)村干部和村民等各種力量交鋒的場域,也是家族勢力等民間諸種力量爭奪話語權、支配權和“爭面子”的一個舞臺。作為國家,希望村民自治制度在農(nóng)村得以運行落實;作為鄉(xiāng)村的基層管理干部,考慮的是鄉(xiāng)鎮(zhèn)工作如何平衡地開展和村莊的穩(wěn)定;作為村民,希望自己的利益得以維護。各家族的現(xiàn)實性立場是擔心異姓上臺后,將村民委員會這個平臺變成維護本家族利益的一個工具,從而使得村莊公共資源分配不均。Z姓與C姓都希望通過拉票來推舉本族人擔任村莊領頭人,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都存在著同樣的目的,即希冀村莊領頭人為本族人爭取更多的村莊資源和“面子”。而選舉是其取得家族政治和公共資源分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所以,村莊選舉也就成為家族在政治領域里相互爭奪權力最集中的事件。
山林承包之爭。F村擁有5000多畝山林。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村委和村民對山林無人問津。隨著農(nóng)村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有幾個外地商人來村里商談承包山林一事,這引起了村民的關注。一些有經(jīng)濟頭腦的村民意識到承包山林是未來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增長點,可以帶來豐厚的利潤。由于村支書是Z姓的緣故,一些頭腦靈活的Z姓村民便開始頻繁出入村委會,找Z支書商討承包山林發(fā)展養(yǎng)殖業(yè)。C姓村民得知后,認為山林是公共資源,不能只經(jīng)村支書同意就可以承包給本家族成員經(jīng)營。C姓家族也有懂得經(jīng)營之道的能人,他們也提出要承包山林,由此拉開了Z姓與C姓之間承包山林的一場爭奪戰(zhàn)。C姓深知通過村民投票來決定山林承包的歸屬權自己占不了上風,因為他們知道Z姓占村莊總人口的50%,有投票權的人要超過本族人口,他們提出了公開競標的投標方式。招投標是工程領域較為公平的解決不同主體之間競爭的一種處理方式。在設定標的后,誰出價愈高誰就中標。由于投標不能只在Z姓與C姓兩家之間進行,最后村支委研究讓所有愿意競標的人都參加投標。自然,由于外地商人的財力雄厚,最終以最高價結束了Z姓與C姓之間的山林承包之爭。
人民公社解體后,作為對基層政權的制約和監(jiān)督,家族組織的功能是不容忽視的,它適時填補了基層權力運行的“真空”,有效地制衡了基層權力掌握者在農(nóng)村公共資源分配和公共產(chǎn)品供給上的隨意性和傾向性,保證了村莊公共權力的公平運行。山林承包事件所表現(xiàn)出來的家族之爭成為支持村莊權力公平運行的一個作用力,家族對村莊事務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制約和監(jiān)督村委公平公正使用公共權力的重要力量。
在現(xiàn)實的村莊管理上,家族勢力之間的相互博弈并非一般意義上理解的相互斗爭、爾虞我詐,它也是一種有積極意義的治理方式,能有效地平衡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對各種權力的運作形成一定的制衡和監(jiān)督,保證基層管理的平穩(wěn)和有序運行。至于出現(xiàn)的一些事件,如選舉中的一些不和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弱勢群體期待公平的一種訴求和表達,它需要制度設計者及操作者有更多的政治耐心,去從事政治教育和政治引導。
家族的村莊行為再現(xiàn)了鄉(xiāng)村生活的生動圖景,從微觀上反映了家族成員在村莊社會各個方面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網(wǎng)絡特征,宏觀上則體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農(nóng)村社會結構的變遷。了解家族活動,可以從群體行動的視角觀察中國農(nóng)民群體的內(nèi)部凝聚力,以及他們與國家體制力量之間的博弈關系,這也為我們深刻認識傳統(tǒng)社會組織在現(xiàn)代社會中成長的制度性空間找到理論觀測點。
三、 新家族精英:家族利益的平衡者
新家族精英,是指“那些在鄉(xiāng)村社會中占有較多傳統(tǒng)資源并在宗族活動中發(fā)揮主導作用的鄉(xiāng)村能人”(1)朱炳祥:《村民自治與宗族關系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3頁。。一般地,他們都是家族中具有崇高威望的人,并通過自己的行為凝聚整個家族成員并有效地管理著家族事務。在20世紀80年代家族復興之初,一些年長者憑借其在家族中有著良好的威望成為家族權力的掌握者。他們介入村莊政治后,便理所當然地成為村莊家族事務的代理人。家族精英本來是傳統(tǒng)權力角色,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口流動的不斷加速和城鄉(xiāng)文化的不斷交融,在農(nóng)村中迅速興起了一批有著一定知識、財力和視野的村莊階層,他們大多具有初、高中文化,甚至部分村民具有大學文化,他們通過外出務工或自主創(chuàng)業(yè)擁有了一定的財富積累,成為經(jīng)濟能人或稱“經(jīng)濟精英”,同時也了解國家在農(nóng)村的政策。他們大多與新生代農(nóng)民工一起產(chǎn)生并成長的,與傳統(tǒng)家族中的“長輩權威”相比,他們更具有現(xiàn)代社會的“智力權威”“財力權威”和“政治權威”,我們稱之為新家族精英(2)疏仁華:《流動視域下當代家族的民間實態(tài)和發(fā)展走向》,《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新家族精英已經(jīng)從歷史上家族矛盾的陰霾中走出,他們不再遵守先人定下的族規(guī),他們中的年輕人已經(jīng)突破了兩姓之間不通婚的藩籬,Z姓與C姓開始聯(lián)姻,盡管聯(lián)姻戶在F村只有十幾戶人家,在整個村莊的715戶中占少數(shù),但一定意義上打破了祖上的鐵律。
新家族精英并非表現(xiàn)出對村莊政治的不感興趣。他們經(jīng)歷過在城市的一段打拼之后,就有著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或從事村莊管理的愿望。F村目前的60多個黨員,40歲以下占一半以上,這足以說明青年人對政治的熱情。村總支部的5個支委,均有初中以上的文化和外出務工的經(jīng)歷,家庭經(jīng)濟狀況也很好,算得上是村莊的能人。現(xiàn)任的村書記就是新家族精英的一個代表。他1992年高中畢業(yè),跟隨家族成員外出打工,迅速積累了一些財富,回鄉(xiāng)后在鎮(zhèn)上開了一個超市,超市日常管理由其妻子和女兒打理,兒子大學畢業(yè)后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他回村關心集體事務,愿意為村民提供服務,被老百姓視為“當家人”。2007年,由老支書的舉薦而被鄉(xiāng)鎮(zhèn)黨委任命為村書記。由于村委會沒有村主任,他實際上也是村委會的實際“掌門人”。
那么在維護本家族利益和村莊公共利益時,這位新家族精英又是如何行使村莊公共權力的呢?讓我們從修路事件說起。
要想富,先修路。2015年,村黨總支研究要修一條通往鎮(zhèn)政府的水泥路。實際上,上一屆村支委就提議修路,但由于道路規(guī)劃要占用3個村莊部分村民的土地,在征求村民意見時,雖然都表達了修路的愿望,但由于村級集體經(jīng)濟薄弱,村里無法擔負占用村民土地的費用,再加上一部分村民的反對,這一提議被擱置了。
新任書記上任后,修建道路一事再次擺上議事日程。經(jīng)過艱苦的工作,他提出修路占用的土地按照人口比例,由4個自然村各拿出一塊土地由村委統(tǒng)籌,小姓村民優(yōu)先選地,不要補償土地的可以享受一定的經(jīng)濟補貼。修路的義務工也按人口攤派。方案提出后,Z莊Z姓部分村民反對,認為這有損Z姓村民的集體利益。但Z書記認為,只有犧牲本族的一些利益,才能得到其他村民的擁護。通過Z書記耐心的說服工作,Z莊村民最終同意了這一方案。2017年10月,這條擱置了十余年的道路終于全線貫通。
村民從開始不同意方案到最終同意方案這一立場的轉變,還是取決于對家族成員之間的關系認同。在村民們來看來,Z書記首先是家族的負責人,然后才是政府的干部。如果不同意本族負責人提出的主張,可能會影響家族精英的權威和影響,這對維護Z氏家族的長遠利益是不利的。對Z書記來說,“打親情牌”往往要比“打政治牌”更為奏效。如果不顧本家族的人際關系,冒著撕破人情面子的風險,行使所謂的行政權力,換來的極有可能是本族村民的閑言碎語、評頭論足和最終的不配合,甚至是一片反對的聲音。所以在鄉(xiāng)村社會,有時縱向的“政治型”關系遠遠沒有橫向的網(wǎng)絡如家族、合作社等具有共同利益或者偏好的組織關系強,“橫向組織成員間的信任感也比縱向組織要強得多”(3)魏媛:《宗族“資源”與鄉(xiāng)村治理--以公社解體后的淮安市X村為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7。。在同一個家族內(nèi),血緣親情的凝聚性是強有力的,尤其是大姓之間的凝聚力,只有解決了大姓的問題,才能化解村莊管理上的問題。“雖然出于吝嗇、嫉妒、陰謀或其他原因他們發(fā)生了爭吵,但事情一旦決定下來,宗族成員仍共同行動,而且統(tǒng)一該宗族的力量再次占優(yōu)勢。”(4)許烺光:《宗族、種姓、俱樂部》,薛剛譯,尚會鵬校,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75頁。
近幾年,隨著國家扶貧力度的不斷加大,村莊貧困人口的扶貧資金也在不斷提高。如何確定貧困戶,享受國家扶貧政策也是考驗村莊負責人能否公平行政的又一考驗。作為Z姓家族的代理人,從情感出發(fā)多分配一些指標給本族村民,也屬合情之舉,但他們又意識到必須平衡好與其他異姓村民的關系。一旦異姓村民舉報上訪,對于村干部來說,都是一件能影響其政治前途的大事。從村莊調(diào)查來看,掌握實權的村莊精英從貧困戶確定的條件、遴選、調(diào)查家庭實際情況、公開信息到公示結果,他們都能認真對待,未發(fā)現(xiàn)舉報、上訪和為分配不平衡而鬧事的事件。家族精英較好地顧及了不同家族的利益。
F村的村莊事件,最起碼從個案事件上證明了新家族精英在處理家族利益的問題上,其眼光不僅僅只盯在本族利益上,往往尋找與其他家族利益的平衡點。選擇一種既不損失本族較多的利益,同時又為他族所接受的一種方式。“當選為村干部的宗族精英生活在宗族姓下,其行政作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熟人們的監(jiān)督,不能不考慮大眾輿論,使其行為不得越出這種信任和規(guī)矩,否則會受到宗族強有力的懲罰。”(5)賀雪峰:《鄉(xiāng)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xiāng)村社會性質(zh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43頁。從我們所觀察到的村莊事件中,上臺后新的家族精英并非將維護本族利益作為其施政的唯一目標,其身上所表現(xiàn)的二重性往往使他們能統(tǒng)籌兼顧好其他家族的利益訴求和村莊整體的利益格局。
在新家族精英表現(xiàn)出對現(xiàn)代村莊民主政治的極大關注的前提下,村莊精英、家族事務與現(xiàn)代政治生活交織在一起,多重互滲,也并非完全是件壞事。在一些典型的家族村莊,家族精英與村治的正式主體(即村干部)往往是重合的,村莊的家族精英都能部分或全部地進入村治的正式組織中。他們一方面是鄉(xiāng)村自治組織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是本族利益的維護者。他們在雙重角色的扮演中實現(xiàn)一定的村莊治理目標。在村治過程中,作為村莊當家人的村委和家族精英之間的行動也往往是“合流”的,尤其是涉及村莊的一些重大事件,也能達成一致的共識。F村村級公路的貫通就是二者合流共建的產(chǎn)物。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這些村莊家族精英不能進入村委班子,就有可能產(chǎn)生內(nèi)耗以及村委與村民的脫離,就會成為鄉(xiāng)村治理過程中的一股破壞性力量。所以,鄉(xiāng)村政治與家族行為之間的互動以及家族精英二重性的行為邏輯,可以通過制度規(guī)范,形塑為鄉(xiāng)村治理的地方樣本。
鄉(xiāng)村的主體是農(nóng)民,農(nóng)民的狀況如何,直接影響著鄉(xiāng)村治理的成效。在改革開放和城市化進程中產(chǎn)生的新家族精英成為有知識、懂技術、會管理、明法律的農(nóng)業(yè)勞動者,雖然他們身上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家族主義的血緣印記,但在很多事件中,他們僅僅把家族關系作為一種資源動員,“他們懂得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內(nèi)持續(xù)調(diào)動民眾的情緒,借助更多的社會資源、維權手段與基層政府人員、村干部進行博弈”(6)佘杰新:《鄉(xiāng)村治理中宗族文化的兩面性及其應對——基于“烏坎事件”和鄉(xiāng)村反腐視角》,《湖南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一旦成為村莊的領頭人,他們往往會平衡家族內(nèi)外的矛盾,公平地分配村莊公共資源,有效地從事村莊管理。
在中國鄉(xiāng)村逐漸“分子化”“原子化”的時期,很多村莊精英和權威隨著社會流動進入城市,致使鄉(xiāng)村社會中的“能人”基礎越來越不穩(wěn)固,在一些鄉(xiāng)村已經(jīng)出現(xiàn)無人可治、無人能治的治理窘境。F村村書記在談到未來的村莊治理時,也表現(xiàn)出對未來村治的擔憂。“如果政府不出臺相關的政策,培養(yǎng)一些能接班而且愿意接班的村莊帶頭人,后果不堪設想。”尤其是“在鄉(xiāng)村政權向服務型政權轉型過程中,農(nóng)村治理將更多地依賴于民間權威”(7)賀振華:《轉型時期的農(nóng)村治理及宗族:一個合作博弈的框架》,《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06年第1期。。所以,培育新的家族精英、加強對家族內(nèi)核心權威人物的培養(yǎng)和引導是重建鄉(xiāng)村治理社會力量的重要內(nèi)容。
四、 重構空間:現(xiàn)代村莊治理的秩序選擇
不同的政治模式?jīng)Q定著社會關系中不同歸屬關系,公共機構與個體,社會群體間信任的社會關系等在資源控制與分配關系網(wǎng)絡中的功能、角色和運行。作為現(xiàn)代中國最基層的村莊政治,它必須維系著國家權威、民間關系、公共意識與村民等不同群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使國家、社會、村民相互間的利益得以調(diào)解并協(xié)調(diào)行動的一致性。在這一過程中,政府通過與民間組織、村民個人合作處理和應對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事務,保證著村莊的穩(wěn)定、平衡和環(huán)境的和諧,使得行動主體有著高度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生態(tài)獲得感。
政府與民間組織、村民個人之間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國鄉(xiāng)村,村治的多元化主體一直參與著鄉(xiāng)村治理。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國家政權對鄉(xiāng)村進行強力控制,在鄉(xiāng)村底層,體制外的一些傳統(tǒng)的組織資源也通過不同的方式介入鄉(xiāng)村政治,盡管由于正式政治組織的集權化、行政化的強勢,民間力量的介入是薄弱的,影響力不明顯。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國家資源從鄉(xiāng)村的撤出,代表國家政權的鄉(xiāng)村基層組織“大(國家)共同體”本位出現(xiàn)了動搖,“小(村莊社會組織)共同體”的權力出現(xiàn)了迅速爬升。家族組織、村落共同體、鄉(xiāng)賢理事會,還有一些業(yè)緣性組織迅速形成了一股體制外的力量,在農(nóng)村活躍起來,并按照自治性的原則處理著農(nóng)村基層社會的一些公共事務,從而引申出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的兩條運行軌跡。一條是作為正式的政治資源的村黨支部、村委會按照國家意志行使著鄉(xiāng)村治理的職責;另一條是家族組織等非正式的傳統(tǒng)組織資源按照其自治性的原則治理著底層鄉(xiāng)村,正式政治資源與傳統(tǒng)組織交織在一起形塑著鄉(xiāng)村政治的基本格局。在治理主體上,村干部往往是家族精英;在治理方式上,村治往往信賴于家族組織的調(diào)解與支持;而在治理效果上,確實也存在著村委會不能解決的一些村莊事件,而到了家族組織那里便迎刃而解了。這種現(xiàn)象,在中國的基層農(nóng)村并不是個別現(xiàn)象。肖唐鏢在對江西、安徽、山西等一些村莊進行田野調(diào)查時,也明確認識到村莊治理中并存的兩種格局。“在行政村層面,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按照行政性邏輯治理著公共事務。但在村莊層面,發(fā)揮作用的基本上是民間的自發(fā)性力量,并已經(jīng)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自治化的治理結構。”(8)肖唐鏢:《村莊治理中的傳統(tǒng)組織與民主建設——以宗族與村莊組織為例》,《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3期。
當然,這種非正式的傳統(tǒng)組織資源——家族力量介入村莊政治并非偶然。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國家公共權力從鄉(xiāng)村社會的撤出,鄉(xiāng)村治理出現(xiàn)“真空”,這種真空既表現(xiàn)為國家不能有效、及時地整合和動員鄉(xiāng)村社會資源進行“補位”,公共權威未能控制鄉(xiāng)村社會的無序,同時也表現(xiàn)為長期處在人民公社“整體性社會”下村民對正式組織認同感的打破。而家族作為正式制度外的村莊傳統(tǒng)資源,它維系著鄉(xiāng)村基層社會的日常秩序,調(diào)節(jié)鄉(xiāng)土社會各方面的沖突,維護著社會的支持功能,較為充分地滿足農(nóng)民對公共產(chǎn)品、公共服務和文化歸屬的需求,為國家節(jié)約了大量的管理成本,發(fā)揮著國家和其他權力機構和社會組織都無法比擬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國鄉(xiāng)村社會面臨的當前特殊處境下,家族仍然是我國鄉(xiāng)村治理中的一個十分有效的組織。
家族作為一種“隱性共同體”仍然有其生存的空間。一方面,家族能夠適應社會環(huán)境,調(diào)整著自身的組織原則、組織結構和活動方式方法,這種“靈活性”和“開放性”,使其“具有堅韌的生命力”(9)馮爾康:《中國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2頁。;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它被植入了時代賦予的鮮活實踐內(nèi)涵,豐富了歷史發(fā)展所蘊含的合理文化內(nèi)核,能在國家法律規(guī)定的前提下演繹著現(xiàn)代鄉(xiāng)土社會生動的邏輯秩序。中國鄉(xiāng)村治理是由國家對鄉(xiāng)村秩序的維系和塑造形成的外生秩序的實踐,以及鄉(xiāng)村社會內(nèi)生秩序的實踐兩部分組成。即使最強有力外來力量對農(nóng)村社會的改變,也借助于農(nóng)村自身的結構來起作用(10)賀雪峰:《村治的邏輯:農(nóng)民行動單元的視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期。。所以,在中國當前的村莊治理的特殊境遇中,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規(guī)律性認識:“大共同體”本位是中國農(nóng)村政治組織結構的本質(zhì)所在,它保障了中國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內(nèi)涵。但我們必須也要看到,“大共同體”本位所建構的“大傳統(tǒng)”無法窮盡當今鄉(xiāng)村社會的諸多面向,也無法涵蓋當今鄉(xiāng)村社會組織的所有形式,自然也就無法詮釋當下中國鄉(xiāng)村生活的生動實踐。“大共同體”下的正式組織資源(體制內(nèi))與“小共同體”非正式組織資源(體制外)在大多場合下是一種互構的博弈狀態(tài)而非對立狀態(tài)。因此,對待體制內(nèi)正式的與體制外非正式的組織資源和組織力量,不管是內(nèi)生還是外生的,都不能簡單地視為“要誰不要誰”的替代性制度選擇,而要強調(diào)它們之間組織形態(tài)和治理方式的互補。
塞繆爾·亨廷頓指出:“組織是通往政治權力之路,也是政治穩(wěn)定的基礎,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身處正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之中的當今世界,誰能組織政治,誰就能掌握未來。”(11)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第427頁。在中國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迫切需要創(chuàng)設制度性空間來促進現(xiàn)代組織的成長,為現(xiàn)代鄉(xiāng)村政治提供新的理論視點和實踐注釋。但現(xiàn)代組織并非“空穴來風”,其形成和發(fā)展都需要吸納傳統(tǒng)的組織資源。家族作為當下鄉(xiāng)村政治體制外的傳統(tǒng)資源,正在村莊政治的互構和博弈中演繹著當代鄉(xiāng)土社會的生動邏輯,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推動著村莊治理的有序化行進。
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中國的村莊治理的主體是由體制精英、非體制精英和農(nóng)民三者組成。體制精英的授權來源和權威主要來自“大共同體”(國家),在傳統(tǒng)社會中,它可以通過“一竿子到底”的方式完成村莊治理。但進入現(xiàn)代社會后,一個有生命力的鄉(xiāng)村社會建設僅僅依靠國家權力和社會公共機構所支持的單一主體是很難達到“善治”效果的。“一個社區(qū)的善治,需要利用好國家與社會的資源,形成一個與政府合作的民主基層,從而才能將民眾有效組織起來,實現(xiàn)善治目標。”(12)王陽、劉炳輝:《宗族的現(xiàn)代國家改造與村莊治理——以南部G市郊區(qū)“橫村”社區(qū)治理經(jīng)驗為例》,《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因此,我國的鄉(xiāng)村善治,它應該是在以政府行為為主導的推動下,整合與重構鄉(xiāng)村社會內(nèi)生型傳統(tǒng)組織資源多元共治的結果。這是解決中國鄉(xiāng)村當下的特殊處境與復雜問題必須選擇的本土化方案。
從以上的觀測中,我們可以引申出這樣的一個理論解釋:要構建一個有序的治理空間,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治理結構。這種治理結構必須最大程度地利用各種傳統(tǒng)資源中的合理因素,并與其治理內(nèi)容進行有效的整合,形成“共謀”的關聯(lián)博弈;不存在一個獨立于傳統(tǒng)之外的有效治理機制,制度的多樣性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tǒng)和文化傳統(tǒng)密切相關。現(xiàn)代社會生命力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傳統(tǒng)資源中的合理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內(nèi)生性力量的支持。中國的村莊治理應該是本土化的,它必須依托傳統(tǒng)組織資源所建構的文化網(wǎng)絡和村莊價值體系,形成鄉(xiāng)村權力運作的文化基礎和村莊共同體意識。“有效的鄉(xiāng)村自治,就必然要求尊重各地的客觀情況,尊重各地的村民群眾意愿,以自上而下制度建構的法治為保障,探索以德治為引領、以自治為核心的差異化治理。”(13)陳文勝:《以“三治”完善鄉(xiāng)村治理》,《人民日報》2018年3月2日,第5版。建構“大共同體本位”或“小共同體本位”的任何一種模式來進行鄉(xiāng)村治理都會使當代中國農(nóng)村社會組織陷入困境。相反,從“大共同體”本位的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的演進要借助與“小共同體”的合作,也就是說,鄉(xiāng)村治理的現(xiàn)代化可能需要選擇一條以“小共同體”為“中介”的路徑。因此,預留給傳統(tǒng)資源力量的彈性空間,使“小共同體”有效地參與村莊建設是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現(xiàn)代化的秩序選擇和實踐要求。
習近平指出:“設計和發(fā)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xiàn)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nèi)容有機統(tǒng)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fā)、從實際出發(fā),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fā)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jīng)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xiàn)實要求、著眼解決現(xiàn)實問題,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yǎng)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4)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5-286頁。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珍視我國長期歷史積淀而傳承下來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這些歷史傳統(tǒng)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歷久而彌堅,成為中華文化的基因復制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時間的推移不一定導致地方傳統(tǒng)的‘衰落’,而只能引起不同社會力量交錯和互動模式的變化。”(15)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臺三村五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第149頁。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組織資源是鄉(xiāng)村治理的根本,脫離了這個根本,就丟棄了鄉(xiāng)土文化的“鄉(xiāng)情”“鄉(xiāng)愁”“鄉(xiāng)音”。所以,只有用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不斷挖掘家族與鄉(xiāng)村治理進而與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相契合的有效資源,引導其成為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的重要力量,才能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鄉(xiāng)村振興。這也就涉及,如何將中國優(yōu)秀鄉(xiāng)土文化中深藏于國民心理結構中的對政治生活的認知、理解和期待,通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運用于具體的治理實踐和制度構建中。因此,對待村落家族文化的態(tài)度,我們一定要意識到它不僅僅是一種文化,也是鄉(xiāng)村生活的一種體制。它“不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處置的東西。它是社會形式中的主要部分,它的未來走向與中國社會經(jīng)濟水平的發(fā)展密切相關,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相輔相成”(16)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的一項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