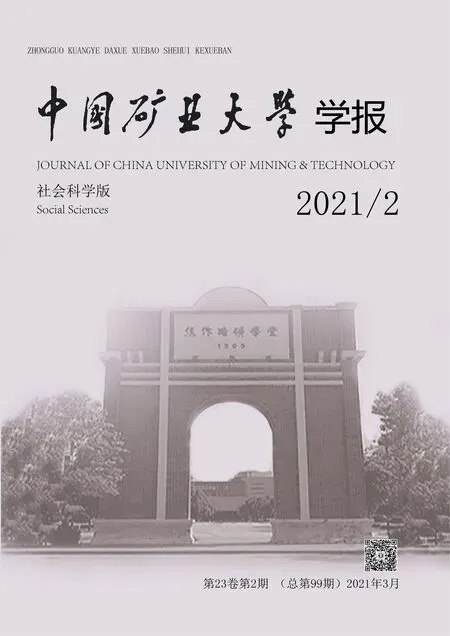稅收立法中的立法依據條款研究
郭昌盛
引 言
一般情況下,立法依據條款屬于法理學、憲法等傳統部門法研究的范疇,國內學界關于立法目的條款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憲法與民法關系上,且已經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然而,由于財稅法學研究長期以來與傳統部門法之間缺乏充分的溝通,學界關于立法依據條款的研究和討論并未對財稅法學界產生顯著影響。稅收立法中是否有必要設置立法依據條款以及立法依據條款該如何表述尚缺乏充分的討論,筆者擬在吸收和借鑒傳統部門法關于立法依據條款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稅收立法中立法依據條款的現狀進行梳理和分析,探討稅收法律中立法依據條款設置的必要性和具體表述方式,以期助益于稅收立法的科學性,為進一步完善稅收立法、提升稅收立法的規范性表達提供參考。
一、 稅收立法中立法依據條款設置的必要性
對稅法中立法依據條款設置的必要性展開分析,必須具備關于立法依據條款的充足的理論儲備,尤其是對立法依據條款的內涵、意義和價值了然于胸。關于立法依據的分類,有多種不同的說法。立法依據包括法律依據、政策依據、事實依據和理論依據(1)饒龍飛:《立法根據論——兼評梁慧星先生的“立法權源”觀》,《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彼)》2008年第1期。,主要是指立法者立某個法的法律根據和事實根據(2)胡建淼:《中外行政法規:分解與比較》上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0頁。。本文所討論的立法依據僅指立法的法律依據。
(一) 關于“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論戰
學界關于立法依據條款設置必要性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法律中是否需要明確“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種立法權源條款上,為此,來自不同部門法的研究者曾發生過激烈的論戰。在起草《物權法》的過程中,梁慧星教授認為在法律中寫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做法直接違背了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應當刪去“根據憲法”四個字(3)梁慧星:《不宜規定“依據憲法,制定本法”》,《社會科學報》2006年11月16日,第001版。。這一論斷招致學界多人的反對。童之偉教授將梁慧星教授的觀點概括為“全國人大立法不宜根據憲法說”,認為該說“對建設法治國家的事業在理論上是非常有害的”“會毀滅憲法、毀滅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而“(在法律中規定‘根據憲法’)是全國人大為維護憲法至上性應該采取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措施”(4)童之偉:《立法“根據憲法”無可非議——評“全國人大立法不宜根據憲法說”》,《中國法學》2007年第1期。。這兩種論斷過于上綱上線,過于強調“根據憲法”的意識形態性或者政治性,沒有從純粹的學術研究視角展開討論,無益于學術智識的增進。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將“根據憲法”寫入法律,都需要進行充分的論證,而且在與觀點相反方商榷時應該準確理解對方的觀點以及理由,避免出現偷換概念、樹立假想敵的討論。
“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表述實際上涉及憲法與部門法的關系問題,雖然民法和憲法學者曾就憲法和民法的關系展開過多次論戰,最近一次論戰是在民法典編纂時討論是否需要將“根據憲法”寫入民法總則第一條,但總體上這些論戰并不影響當前學界對憲法和民法關系的主流觀點,最終《民法總則》明確了其立法依據是“根據憲法”。理論上,憲法與部門法之間存在三重關系,即“法律對憲法的具體化”“法律的合憲性解釋”和“法律的合憲性審查”(5)張翔:《憲法與部門法的三重關系》,《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1期。,而“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主要體現在第一重關系上,即憲法是普通法律立法的基礎與依據,普通法律是憲法的實施法(6)胡峻:《“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作為立法技術的運用》,《法治研究》2009年第7期。。從法秩序的統一與協調的視角來看,憲法與部門法關系命題的解決方案在于憲法實現和憲法解釋(7)錢寧峰:《憲法與部門法關系命題的困境與求解》,《江蘇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而憲法的實現就在于部門法立法對憲法內容的進一步明確和細化。在法律中寫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不僅是立法者依憲立法的自我確證和事實陳述,也是立法權法定(包括權源法定和法源法定)原則的規范要求(8)葉海波:《“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內涵》,《法學家》2013年第5期。。其中,權源法定主要是解決立法主體以憲法身份(全國人大是全國人民的代表機關、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國家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法源法定主要是解決法律的內容源于憲法的哪些規定。在現代社會,制定法律除極少數例外情形,都必須要有依據,法律的制定要以憲法為根據(9)周旺生:《立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486頁。。法律文本中設置“立法根據”條款的目的在于保障立法的合法性、明確法的效力等級以及實現法的可操作性(10)汪全勝、張鵬:《法律文本中“立法根據”條款的設置論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從我國立法實踐來看,“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及類似字眼在我國立法中的落實情況并不理想。截至2019年9月,我國現行有效法律共有276件,其中規定了“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以及類似字眼的法律不到30%,公法中規定“根據憲法”的比例明顯高于私法,且不同法律中的表述也不盡相同,因此,我國的法律中到底寫不寫“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更多的是一種雜亂無章、隨意無序的局面(11)王鍇:《憲法與民法的關系論綱》,《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1期。,且《憲法》作為立法的依據基本上是“政治表態”意義上的(12)莫紀宏:《從〈憲法〉在我國立法中的適用看我國現行〈憲法〉實施的狀況》,《法學雜志》2012年第12期。,但是這種現實不能成為立法不寫“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理由(13)參見王鍇:《〈監察法〉要不要寫“根據憲法、制定本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44d570102x3dq.html,2019年9月7日。。
(二) 稅收立法權與立法依據條款
《憲法》第六十二條第三款以及《立法法》第七條第二款規定,全國人大行使“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職權,《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職權。可見,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立法職權上的區別是,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則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14)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1頁。。問題在于,憲法并沒有對“基本法律”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也沒有對其他方面基本法律的內涵予以界定。因此,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權限并沒有完整的、清晰的界定和表述。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定的立法權限,是基于加強立法機關的權威而作出的制度選擇(15)韓大元:《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憲法地位》,《法學評論》2013年第6期。,并不是要削弱全國人大地位。因此,全國人大作為最高立法機關,其立法權并不僅限于制定基本法律,也有權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根據官方統計,目前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有40余件,這些法律除了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基本法律以外還有不少的“其他的基本法律”,包括《兵役法》《義務教育法》《工會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已經廢止)、兩稅合一之后的《企業所得稅法》等(16)許安標:《憲法及相關法解讀》,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238頁。,最近由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是《外商投資法》。
憲法和部門法關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憲法約束立法機關,立法機關通過制定法律來具體化憲法以形成部門法秩序,即法律是對憲法內容的具體化(17)張翔:《憲法與部門法的三重關系》,《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1期。。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立法機關依據憲法制定的。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任何法律從根本上均依據憲法制定,但并非所有部門法或者法律都需要在具體條文中列明立法依據。雖然各部門法都是憲法的子法,但它們與憲法的距離和聯結點是有所區別的(18)馬嶺:《憲法與部門法關系探討》,《法學》2005年第12期。,這也是憲法有別于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原因所在。
財稅作為現代社會國家治理的關鍵,關乎政府與人民、立法與行政、中央與地方的關系(19)劉劍文、苗連營、熊文釗、熊偉:《財稅法學與憲法學的對話:國家憲法任務、公民基本權利與財稅法治建設》,《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1期。,涉及公民權利保障、國家財政運行乃至政府的更迭(20)查爾斯·亞當斯:《善與惡:稅收在文明進程中的影響》,翟繼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頁。等重大問題,因此,稅法與憲法的距離相對于《保險法》《電子商務法》等技術性強的法律來說要近得多(21)在我國立法實踐中,金融立法,環境保護立法,食品安全立法,消防、建筑、規劃等技術性強的法律都沒有規定“根據憲法”等類似的立法依據條款。。稅法的立法依據直接涉及立法的基礎和制度的合法性,與立法主體、立法權、授權立法、稅收法定原則等相關,需要在具體立法之前加以明確(22)張守文:《關于房產稅立法的三大基本問題》,《稅務研究》2012年第11期。。由于稅收立法直接關系到國家與國民之間財富分配的界限,不同納稅人群體之間稅負分配的公平,不同地區之間財政收入的多寡等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近年來社會各界圍繞房地產稅法的規則如何設計、個人所得稅法修訂、增值稅改革等稅制設計和稅法制定的討論一度引發熱議,實際上就是社會公眾對稅收立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問題的關注。
2015年《立法法》修改,修改后的第八條將“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規定為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項,且立法權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該規定同樣沒有對“基本制度”進行明確,因此,在全國人大一年僅召開一次的憲制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實際行使稅收法律的立法權。憲法第五十六條和《立法法》第八條第6項的規定被認為是稅收法定原則在憲法及其相關法律中的確立,官方也明確表示:“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收立法和稅收法律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我國憲法所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23)《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就〈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意見〉答問》,2015年3月26日,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503/t20150326_1207519.html.可見,稅收法律的立法依據實際上是非常明確的——憲法是所有稅收法律的立法依據,既然稅收法律的立法依據已經明確,那么在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稅收立法時,就應當在稅收法律中明確該部法律的立法依據。
二、 稅收立法中立法依據條款設置的歷史與現狀
我國稅收立法中立法依據條款的設置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稅收立法史上是有跡可循的,然而,近年來稅收立法中立法依據條款普遍缺失。
(一) 稅收立法史中的立法依據條款
我國現行18個稅種只有6個稅種的法律法規規定了立法目的條款,但同時規定了立法依據條款的僅有關稅1個稅種,且關稅的立法依據并非憲法,而是《海關法》,這主要是因為現行關稅的法律依據主要是國務院頒布的《進出口關稅條例》,而該條例則是“根據《海關法》的有關規定”(主要是《海關法》第五章)制定的。因此,我國現行18個稅種的法律都沒有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以及類似表述的立法依據條款。
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國稅收立法中沒有規定立法依據條款是因為早期的稅收法律法規制定時間過早,當時的法治意識不強所致。這種觀點并不符合我國稅收立法的歷史,實際上,現行稅收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立法依據條款并非我國稅收立法的歷史慣性或立法傳統,也并非因為我國立法的法治意識不強、法治不彰、法治建設進程緩慢,更有可能是由于不同時期立法機關的具體組成人員或者立法者的立法思路不同所致。早在1950年,原政務院就在其頒布的《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24)該條例已于1987年11月24日被國務院廢止。第一條規定了立法依據條款,即“本條例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十條的規定,并參照新解放區農村實際情況制定之”(2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已失效)第四十條規定“關于財政:建立國家預算決算制度,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范圍,厲行精簡節約,逐步平衡財政收支,積累國家生產資金。國家的稅收政策,應以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及國家建設的需要為原則,簡化稅制,實行合理負擔。”。全國人大常委會1958年頒布的《農業稅條例》第一條同樣也規定了立法依據(26)該條例已經于2005年隨著農業稅的廢除而廢止。,表述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零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的規定,制定本條例。”這兩部在建國初期頒布實施的農業稅條例不僅規定了立法依據條款,而且還對立法所依據的具體條文和內容進行了明確。可見,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稅收立法中是相當重視立法依據條款的設置的。
在1958年到1990年三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國進行過多次稅制改革,出臺了大量稅收法律法規。然而,中央層面出臺的稅收法律法規都沒有規定立法依據條款。與此相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稅收法律法規中仍然規定了立法依據條款。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于1990年開征牧業稅時在法律文件第一條規定:“根據憲法第五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有關規定,結合我區牧業經濟情況,特制定本辦法。”(27)《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牧業稅征收辦法》(新政發〔1990〕31號,簡稱《牧業稅辦法》,已失效)。然而,《牧業稅辦法》在2002年修訂時,立法依據條款被修改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有關規定,結合自治區實際,制定本辦法。”2003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再次修改了該條款,改為“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發〔2000〕7號文件)和《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新黨發〔2003〕10號文件)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2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牧業稅征收暫行辦法》(新政辦發〔2003〕128號,簡稱《牧業稅暫行辦法》)。雖然《牧業稅暫行辦法》仍然沒有被明文廢止,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已經通過規范性文件在全區范圍內免征牧業稅的方式實質上廢除了牧業稅(29)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在全區范圍免征農業稅牧業稅的通知》(新政發〔2005〕43號)。。同樣開征了牧業稅的內蒙古自治區也在相關法律文件第一條規定:“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發〔2000〕7號),以及《內蒙古自治區農村牧區稅費改革試點方案》(內黨發〔2002〕12號),制定本辦法。”(30)《內蒙古自治區牧業稅征收辦法(試行)》(內政辦發〔2002〕28號)。甘肅省和青海省則在法律文件中將立法依據條款表述為“根據國家牧業稅收有關規定,結合我省實際,制定本辦法。”(31)《甘肅省牧業稅征收辦法》(省政辦〔2000〕第17號,已失效)、《青海省牧業稅征收管理暫行辦法》(青政〔2000〕19號,已失效)。
部分地方政府在征收牧業稅時規定了立法依據條款,從開征牧業稅的地區來看,這四個省(區)都分布在我國西北部和北部,且兩個明確了具體立法依據的省(區)還都是少數民族自治區,這兩個少數民族自治區開征牧業稅實際上是行使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的地方立法權(32)《憲法》第4條第3款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民族區域自治法》第34條規定:“第三十四條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國家稅法的時候,除應由國家統一審批的減免稅收項目以外,對屬于地方財政收入的某些需要從稅收上加以照顧和鼓勵的,可以實行減稅或者免稅。”,而且在中央提出要對農村稅費改革后(3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發〔2000〕7號文)。,這兩個地方政府為了落實中央農村稅費改革精神,對牧業稅法規進行修改,并對牧業稅的立法依據條款進行了相應調整。甘肅省和青海省開征牧業稅時規定的立法依據條款完全一致,這種現象更有可能是地方政府之間在立法過程中相互借鑒的結果。
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稅收立法實踐曾多次在稅收法律文件第一條規定了立法依據條款,這些立法依據條款有的直接明確了立法依據的具體條文;有的在明確立法法律依據的同時,還對立法的事實依據進行了規定;新疆、青海、內蒙古、甘肅等省級政府發布的牧業稅法律文件雖然在立法依據條款的具體表述上有所區別,甚至多次更改,但始終對稅收立法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問題予以重視。此外,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以及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之后,我國的法治意識不能說不強。然而,在全國人大法工委數次就稅法草案征求意見時,筆者都曾建議在稅收法律第一條對立法依據進行規定,增加“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表述。遺憾的是,這一建議并沒有被采納,自2013年以來出臺的所有稅收法律都沒有對立法依據進行規定。因此,稅收法律法規沒有設立立法依據條款并不是由于早期立法時法治意識不強導致的。我國稅收立法中立法依據條款設置隨意,以及近年來普遍缺失的情況著實令人費解。
(二) 現行稅種立法依據分析
我國現行18個稅種,除了企業所得稅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確定的之外,其他稅種都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國務院立法確定的。目前,以法律形式確定的稅種有個人所得稅(1980)、企業所得稅(2008)、車船稅(2011)、環境保護稅(2016)、煙葉稅(2017)、耕地占用稅(2018)、車輛購置稅(2018)、資源稅(2019)8個稅種,其余稅種仍然是以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的。個人所得稅自1980年開征以來一直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實施的,法律文本中一直都沒有規定立法依據條款,且數次修改均未說明修法的法律依據,因此,個人所得稅的立法依據始終未曾明確,但不可否認的是,個人所得稅的立法屬于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權限范圍,因此,憲法是個人所得稅實質上的立法依據。
198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實施國營企業利改稅和改革工商稅制的過程中,擬定有關稅收條例,以草案形式發布試行(3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國務院改革工商稅制發布有關稅收條例草案試行的決定》(1984年9月18日通過,簡稱“1984授權”,已廢止)。。財政部擬定了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等稅收條例(草案),且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等稅收條例草案由國務院發布,并自1984年10月1日起實施。在“1984授權”決定作出不到一年,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對于有關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的問題制定暫行的規定或條例(35)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的決定》,1985年4月10日通過,簡稱“1985授權”)。,由于“1984授權”規定國務院擬定的稅收條例要“以草案形式發布”,且該授權已經在2009年被廢止,而“1985授權”規定國務院制定“暫行的規定或條例”,這與我國稅收法規主要是暫行條例的現實正好對應,因此,“1985授權”被認為是我國現行稅收暫行條例的立法依據。實際上,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首先,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3個稅種的草案自1984年試行,一直到1993年才發布了暫行條例,因此,這三個稅種至少在198—1993年期間的立法依據不是“1985授權”;其次,“1984授權”中已經明確了房產稅為地方稅種,雖然國務院1986年才發布《房產稅暫行條例》,但該條例實際上在1984年就已經形成草案,只是在1985授權發布后,將原來的房產稅條例草案的名稱改成了《房產稅暫行條例》。最后,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立法依據也不是“1985授權”,因為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比“1985授權”要早兩個月。
現行企業所得稅是在三次稅制合并基礎上形成的:第一次稅制合并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1991年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于1980年和1981年發布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合并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即對三資企業適用的所得稅法進行了稅制合并、統一、簡化;第二次稅制合并是國務院于1993年將其1984年發布的《國營企業所得稅條例(草案)》《國營企業調節稅征收辦法》、1985年發布的《集體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1988年發布的《私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4部行政法規合并為《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合并統一了內資企業適用的所得稅制;第三次稅制合并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2008年將其1991年發布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和國務院于1994年發布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合并為《企業所得稅法》,對內外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制進行了統一。從我國企業所得稅制歷史沿革來看,兩稅合一前三資企業適用的所得稅法律依據是以法律形式確立的,其立法依據雖未明確,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是憲法賦予的權力;《國營企業所得稅條例(草案)》和《國營企業調節稅征收辦法》和“1984授權”文件同時發布,可以認為這兩部行政法規是依據“1984授權”制定的;《集體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與“1985授權”同時發布,《私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發布在“1985授權”之后,因而這兩部行政法規是根據“1985授權”發布的;國務院1993年進行的稅制合并實際上也是依據“1985授權”而制定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至于2008年的兩稅合一,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最高立法機關積極行使憲法賦予的立法權的結果。因此,我國企業所得稅實質上的立法依據是較為復雜的,“1984授權”和“1985授權”都曾充當過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法的立法依據,但最終仍然是以憲法作為現行《企業所得稅法》的立法依據的。
車船稅的立法依據同樣較為復雜。國務院2007年將原政務院1951年發布的《車船使用牌照稅暫行條例》和1986年發布的《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合并為《車船稅暫行條例》,該條例于2011年上升為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了《車船稅法》,該法出臺的背景和必要性就是“按照全國人大授權決定和立法法有關規定,國務院制定的稅收單行條例在條件成熟時應當上升為法律”。其意義主要有:一是體現稅收法定原則;二是促進稅收法律體系建設;三是通過立法完善了稅制,體現稅負公平;四是作為第一部由條例升格的法律和第一部地方稅法律,具有標志性作用(36)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有關問題的解讀(2011)。。原政務院發布《車船使用牌照稅暫行條例》時我國尚未制定憲法,因而其立法依據實際上是《共同綱領》,而1986年的《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和2007年的《車船稅暫行條例》的立法依據實際上都是“1985授權”。可見,現行《車船稅法》的立法依據實際上是“1985授權”和《立法法》,但“1985授權”和《立法法》的立法依據是憲法,因此,《車船稅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賦予的權力制定的法律。
需要注意的是,環境保護稅作為排污費實施費改稅后實施的新稅種,其實質上的立法依據究竟為何可能存在分歧。我國《環境保護法》2014年修訂后在第四十三條增加了“依照法律規定征收環境保護稅的,不再征收排污費”的規定,當時我國并沒有制定《環境保護稅法》,甚至連《環境保護稅法(征求意見稿)》都沒有發布。問題就在于《環境保護稅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是否屬于環境保護稅的立法依據?《環境保護法》是否屬于《環境保護稅法》的上位法呢?《環境保護法》確實屬于環境保護稅的立法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其《2014年立法工作計劃》中已經明確要“制定單行稅法”(37)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立法工作計劃》(2013年12月16日原則通過,2014年4月14日修改)。,雖然沒有具體明確“單行稅法”的內容,但國務院《2014年立法工作計劃》(38)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國務院2014年立法工作計劃〉的通知》(國辦發〔2014〕7號,2014月2月13日)。中明確提到由財政部、稅務總局、環境保護部起草《環境保護稅法》。可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修改《環境保護法》之前就已經有了出臺環境保護稅的立法計劃,因而在《環境保護法》中進行“超前立法”,規定了環境保護稅。但環境保護稅在《環境保護法》中的立法依據并不局限于第四十三條的規定,《環境保護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采取財政、稅收、價格、政府采購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鼓勵和支持環境保護產業的發展,第二十二條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法定要求基礎上,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的,人民政府應當依法采取財政、稅收、價格、政府采購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勵和支持”。因此,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同樣是環境保護稅的立法依據。另外,從環境保護稅的制度來源看,環境保護稅由排污費實施費改稅而來,原排污費的法律依據《征收排污費暫行辦法》在第一條就明確其立法依據,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第18條關于‘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數量和濃度,根據規定收取排污費’的規定,制訂本辦法”。因此,《環境保護法》中關于排污費或環境保護稅的規定屬于《環境保護稅法》的立法依據。至于《環境保護法》是否為《環境保護稅法》的上位法,筆者認為不宜草率認定。雖然《環境保護法》相關條款在理論上可以解釋為《環境保護稅法》的立法依據,但立法依據并不是上位法和下位法關系成立的充要條件。“上位法”和“下位法”是根據位階的不同對法律規范所作的區分(39)汪全勝:《“上位法優于下位法”適用規則芻議》,《行政法學研究》2005年第4期。,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上位法優先于下位法,在我國立法實踐中,下位法一般是對上位法的內容進行大量的重復立法,而且形式上立法結構基本一致(40)屈茂輝:《我國上位法與下位法內容相關性實證分析》,《中國法學》2014年第2期。。而《環境保護稅法》在立法結構、立法內容等方面與《環境保護法》存在明顯區別,兩部法律均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因此,不應認定兩者之間是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18個稅種實質上的立法依據是十分復雜的,既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據憲法賦予的權力制定法律來確定,也有國務院依據“1984授權”和“1985授權”確定的,還有依據《海關法》確定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以及黨中央審議通過的《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意見》的最終目標就是將稅收法律的立法依據統一為憲法,并適時廢止“1985授權”。雖然近幾年稅收立法中均未規定立法依據條款,但其“根據憲法”制定稅收法律的內在是十分明顯的。即便如此,未來在完善稅收法律時仍然應當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將立法依據條款明確宣示。
三、 稅收立法中立法依據條款的具體表述
立法依據條款的表述是立法目的條款本身價值的具體體現,在我國立法實踐中,立法依據條款的表述仍然雜亂無章,立法語言表述的確定性與模糊性并存(41)劉愛龍:《立法語言的表述倫理》,《現代法學》2006年第2期。,亟需對立法依據條款的具體表述方式進一步完善。
(一) 我國立法實踐中的立法依據條款的表述
按照我國的立法慣例,一部法律的第一條一般是對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據的說明(42)周云帆:《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立法評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先表述立法目的,再表述立法依據(4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立法技術規范(試行)(一)》(法工委發〔2009〕62號文)。,且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據一并表述在同一款中。從我國的立法實踐來看,立法依據條款的表述大致上有以下幾種類型:
1. 立法目的+籠統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種表述方式最為常見,例如:《立法法》《法官法》《教育法》《刑事訴訟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行政許可法》《農村土地承包法》《預算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公務員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監察法》《國歌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處罰法》《體育法》《繼承法》等。需要注意的是,《繼承法》在規定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據時,將兩項內容雜糅在了一起,其第一條規定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為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制定本法。”這種表述方式雖然簡單、直接,但其存在的問題是立法依據憲法上哪些規定或者哪個條文并不明確,容易落入立法的形式主義窠臼。
2. 立法目的+立法依據,立法依據包含法律依據和事實依據。例如,《刑法》第一條規定“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一條規定“根據憲法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制定本法。”其中,“根據憲法”是法律依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和“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則是事實依據。這種表述方式的特色在于立法依據中包括了事實依據,有利于增強立法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另外,將“我國的實際情況”或者“具體經驗”作為立法依據,實際上也為我國國家政策的法律化提供了入口,對于提高社會治理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3. 立法目的+立法依據,明確立法依據的具體條文。例如,國務院發布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第一條規定:“根據憲法第十九條‘鼓勵自學成才’的規定,制定本條例。”這種表述方式不僅具體指明了立法所依據的具體條文,還對條文中的具體內容進行了精確的明示。但這種表述方式的困境在于,當憲法中有多個條文(可能集中規定在某一章或某一節)或者專門設章、節規定某一事項時,全面列舉條文內容就會顯得十分冗贅,此時就需要通過“列舉+概述”的方式來明確。以《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為例,《憲法》第十九條是對我國教育事業教育等級的集中規定,而第二十四條是對教育事業中精神文明建設不同內容的規定,第四十五至四十七條還規定了受教育權利和義務等事項,這些規定共同構成了教育事業的憲法依據,而條例僅僅以憲法第十九條“鼓勵自學成才”的字眼作為立法依據,過于狹隘。
4. 無立法目的,立法依據條款單獨成為一條,且對立法依據的內容進行概述。例如,《國務院組織法》第一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國務院的規定,制定本組織法。”這種表述方式的特殊性有兩個方面:一是沒有規定立法目的,這主要是因為《國務院組織法》屬于政治性法律,是通過立法形式將憲法確立的國務院的最高行政機關的地位確定下來,不規定立法目的也無可厚非。雖然《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目的,但這兩部法律與《國務院組織法》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適用于各級法院和檢察院的組織、設置等事項,而《國務院組織法》僅適用于或者僅規定了國務院組織事項。二是立法依據條款采取了“概述式”的表述,主要是因為憲法在第三章“國家機構”中專門設第三節對國務院進行了規定,而且憲法其他條文中也對國務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規定(44)例如,《憲法》第一百一十條并非規定在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三節“國務院”部分,但該條明確“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實際上也是“憲法有關國務院的規定”。,因此,這一概述式的表述方式更為合適。
5. 無立法目的,立法依據條款單獨成為一條,不指明立法依據具體條文。例如,《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雖然沒有規定立法目的條款,但在序言中對立法宗旨或目的進行了充分說明。《戒嚴法》第一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本法。”《締結條約程序法》第一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本法。”這種表述方式與前述第一種表述方式的區別在于沒有立法目的條款,除此之外,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表述方式沒有本質區別。
6. 無立法目的,立法依據條款同時明確其所依據的具體條文內容和憲法原則。例如,《兵役法》第一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五條‘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圣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和其他有關條款的規定,制定本法。”該規定的特色不僅在于直接明確了立法所依據的具體憲法條文及內容,而且“其他有關條款”的表述實際上是對不便于逐一列舉的體現各項憲法原則的條文進行了概括,兼具針對性和靈活性。
7. 無立法目的,立法依據條款單獨成為一條,且包括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這種表述方式與前述第二種表述方式的唯一區別在于沒有規定立法目的,其余情況完全一致。
8. 立法目的+立法依據,立法依據除了憲法,還有其他法律。這種表述方式也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兩類:一類是具體指出其他法律的名稱,如《義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民辦教育促進法》都在第一條規定:“根據憲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第一條規定:“根據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制定本法。”另一類是不具體指出其他法律的名稱,如《科學技術普及法》第一條規定:“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制定本法。”這種表述方式中的立法依據雖然包括了憲法和其他法律,但需要注意的是,憲法和該部法律本身是母法與子法或者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但立法依據中的“其他法律”與該部法律本身之間并非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而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因為這些“其他法律”是就某一領域事務“在時間、空間、對象以及立法事項上作出的一般性規定”,而該部法律本身則是“適用于特定時間、特定空間、特定主體、特定事項的法律規范”(45)汪全勝:《“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關系及適用問題探討》,《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9. 立法目的+立法依據,但立法依據不是憲法。如《國防教育法》第一條規定:“根據國防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職業教育法》第一條規定:“根據教育法和勞動法,制定本法。”這種立法依據表述方式中的法律與該部法律之間仍然屬于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雖然屬于立法依據,但教育、國防等事項在《憲法》中并非沒有相關規定,因此沒有將憲法列入立法依據條款中,屬于立法依據條款在表述上的重大缺陷,應在未來修法時進一步完善。
由此可見,我國立法實踐中立法依據條款的表述方式五花八門,并沒有固定的方式,即使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立法依據條款如何表述作出規定后,我國立法實踐仍然未能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對立法依據條款進行確定或修改,至今仍然有將近150部法律的立法依據條款的表述方式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要求。
(二) 立法依據條款表述方式的選擇
全國人大常委會曾于2009年規定:“法律一般不明示某部具體的法律為立法依據。但是,憲法或者其他法律對制定該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應當明示憲法或者該法律為立法依據。”(4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立法技術規范(試行)(一)》(法工委發〔2009〕62號文)。有人曾在《環境保護稅法》制定過程中提出《環境保護稅法》的立法依據表述為“依據憲法原則制定本法”(47)黃新華:《環境保護稅的立法目的》,《稅務研究》2014年第7期。。該建議意識到稅收法律中應當設置立法依據條款,但在具體表述上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要求有所沖突。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對立法依據的具體表述進行了規定,即立法依據的表述應該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或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的規定,制定本法”(48)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立法技術規范(試行)(一)》(法工委發〔2009〕62號文)。的方式來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立法依據條款表述方式的規定不僅與我國的立法實踐差距過大,而且與學界理論研究也存在一些沖突。葉海波教授認為,法律的立法依據應當更加明確地表述為“根據憲法第×條,制定本法”(49)葉海波:《“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內涵》,《法學家》2013年第5期。。周旺生教授認為,立法依據不宜寫得過于籠統,不要籠統地說“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而應該是“根據憲法關于×××的規定,制定本法”;同時,也不宜過于具體,即不宜規定“根據憲法第××條的規定,制定本法”,以避免憲法條文變動時該法律的立法依據的合法性存在問題(50)周旺生:《立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486頁。。僅抽象地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好處在于,可以表明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對憲法的尊重,且當憲法文本(條文序號或者條文內容)被修改后,只要法律的內容不與現行憲法相抵觸,依據憲法所產生的法律、法規仍然具有繼續生效的法律效力。但是,“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表述可能會存在法律的合憲性問題,即立法者可能并沒有依據憲法來制定法律,或者立法者根本不知道是依據憲法的何種規定來制定法律。由于“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本身的內涵就存在不確定性,就可能為立法者架空憲法或者不按照憲法辦事提供借口(51)莫紀宏:《從憲法第100條看憲法適用理論的缺失》,《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9期。。
稅收法律的立法依據條款在表述方式上應該指明其所依據的具體條文,以明示稅收立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我國整部《憲法》僅在第五十六條規定公民的納稅義務時涉及稅收問題,且官方已經明確表明稅收法定原則是憲法確立的原則,因此,可以表述為:“根據憲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制定本法”。有學者擔心未來《憲法》修改時(包括條文序號或者條文內容修改)會帶來稅收法律的合法性問題,這種擔心有些多余。倘若未來《憲法》修改后,第五十六條規定的內容與稅收無關,或者《憲法》中直接設立財政章節,完全可以在修改《憲法》的同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集中對稅收法律的立法依據條款進行修改。在國、地稅機構合并后,我國稅收法律中“地方稅務機關”或者“國家稅務機關”的表述全部改成了“稅務機關”,這種做法不僅可行,而且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四、 結 語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以來,我國稅收立法明顯提速,已有多部稅收暫行條例升格為法律。然而,在稅收立法的過程中,立法依據條款始終未得到立法者和研究者的重視。本文主要是借鑒法理學、憲法學等傳統部門法對立法依據條款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國立法實踐中立法依據條款的設置和表述方式現狀,對進一步完善我國稅收立法的立法依據條款及其表述方式進行了討論,不僅有助于繼續完善稅收立法,而且對加強財稅法學與傳統部門法學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