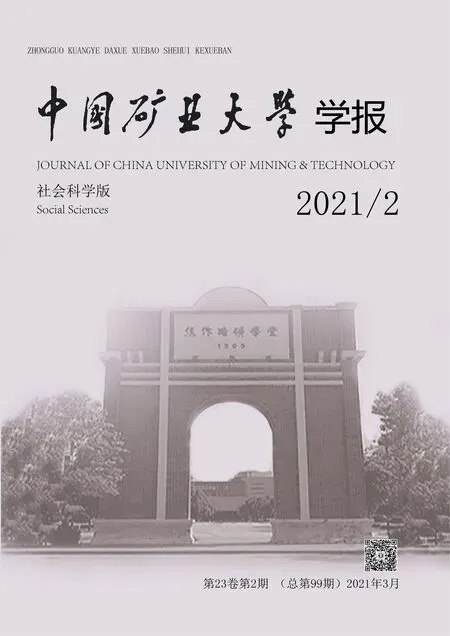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近現代史的敘事方式轉變
胡 靜, 歐陽恩良
歷史是科學和藝術的混合體。歷史的敘事方式,按照歷史實在的編排,注入歷史想象的成分。歷史實在表達歷史的科學性,是由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等串聯起來的歷史序列。歷史想象體現了歷史的藝術感,在語言學、修辭學、美學等學科的渲染中激活了歷史。歷史實在提供了敘事文本,敘事過程通過歷史想象的途徑和手段進行表達,兩者結合的過程構成了熱奈特所闡述的敘事理論:敘事存在“故事、敘事和敘述”三個層面的含義,分別指敘事的所指、能指和敘述行為(1)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王文融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6-7頁。。在中國近現代史中,社會變革的復雜性和多樣化致使歷史敘事方式形成了多次流變與轉換。近現代史敘事方式的邏輯進路歷經了革命性敘事、現代性敘事、后現代性敘事的演進。敘事方式的嬗遞,透射出意識形態的姿態,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平衡、道德力量與民族原則的把控推進著歷史敘事的連續性。
一、 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的嫁接:革命性敘事方式
在革命性敘事方式中,歷史現象和事實的闡釋更趨向于表達歷史真實性。從事實的層次躍升到表象背后的另一個層次,需要主觀的價值表達,即學理上的歷史與意識上的政治融合,從而完成歷史現象的邏輯連貫性與時代順從性。革命性敘事方式在意識形態的強勢話語中是一種嚴整性的存在。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是規整的學術化的代表著作。革命性敘事方式或以借助修辭學的審美,弱化政治情勢,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則是革命語義下詩意化的體現。
(一) 革命性敘事方式——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胡繩早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中對歷史分期問題進行了獨到的闡述,為中國近代歷史的復雜性尋覓到突破口和線索,循此線索整合了零散的歷史現象。通過對碎片化的歷史背景、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整理,實現了歷史實在的整體化和系統化。歷時近半個世紀,《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終得問世。胡繩在此作中以毛澤東關于新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論斷為依據,超越了按照革命性質劃分的標準,以社會性質的變遷來論證新中國成立的必然性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開拓了中共黨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敘述的新路徑,形成了與黨史編纂體系一致的革命史觀,體現了胡繩駕馭史料的能力以及對尊重史實的嚴肅態度。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是在革命敘事的范疇中,運用了伯克的歷史敘事理論,即情景、行為主體、行為、行為方式、目的等要素整合形成歷史實在的邏輯,綜合而成的反思史范本。反思史要求對史料進行還原、整合,通過對史料的解釋把歷史想象嫁接在歷史實在中。撰述這種歷史不僅需要對時光流逝有一定理解,還要對史學家及其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有充分的認識,并且要有意識地縮短該距離(2)海登?懷特:《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陳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125頁。。胡繩先生首先設定了歷史敘事的情景,以階級斗爭作為標準,運用階級分析法對史料進行歸整。在立論時,把農民和資產階級的力量作為近代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力量,有意突出義和團、潛在弱化戊戌變法的作用,宣揚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思想,強調用階級分析法闡釋中國近代史,對人物和事件作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在著作中,胡繩充分挖掘和利用史料,以革命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依據革命主題的變化,界定了“三次革命高潮”的分期,論述了行為主體的變動、壯大的進階,揭示了行為主體在現實動力中形成的實踐目的。
革命性敘事方式以史料為支撐詮釋歷史實在。胡繩歷史實在的研究理路,與19世紀西方史學家所理解的“歷史學方法”具有耦合性,與托克維爾的形式解釋理念不謀而合,拋卻歷史的幻象,深度挖掘檔案史料,以文獻的援引和情節化的論證作為解釋策略。《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的敘事方式,闡述了被文獻所印證的并且延伸出的事件和故事,對事件的發生起因、發展趨勢、人物作用、后續影響等進行情節化的概述。在故事中觀照現實、探尋規律,提取出所援用的各種原則,闡明歷史發展的規律性,體現了歷史敘事方式的獨特性以及胡繩“有史有論,史論結合”論述模式的最高境界。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胡繩嚴格遵從革命敘事方式,純熟運用邏輯演繹的方法:以革命背景為前提,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規律為革命敘事的導引,梳理革命事件的因果邏輯;以三段論模式闡釋革命歷程,體現了歷史實在的必然性和革命發展的規律性,顯示了“論從史出”的歷史詮釋特質,奠定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概念化體系,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方法產生了導向作用。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詮釋了歷史理解模式的要義和內涵。歷史想象嫁接在結構嚴謹、復雜交錯的歷史實在基礎上,描繪了風云變幻、天地翻覆的革命景象。全書夾敘夾議,行文流暢貫通、渾然一體,風格質樸、語言生動活潑,以深入淺出的歷史解釋模式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勾勒出遼闊的歷史想象空間。比如描寫太平天國起義前期,太平軍所到之處,廣大下層人民“像潮水一樣涌進了太平軍的隊伍。因此,太平軍就能夠像滾雪球一樣地擴大起來”(3)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1頁。;“當太平軍向南京進軍過程中,好像用篩子把舊社會篩了一道一樣,篩出來的跟著它一起走了,剩下的照舊留在本地”(4)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第118頁。。再如評價《天朝田畝制度》時,“是一幅交織著現實和幻夢,交織著徹底的斗爭性和不切實際的空想的圖畫。這里面既有由革命的烈火燃起來的大膽的想象,又充分暴露了小生產者的狹隘的實際主義,既閃耀著歷史的遠見;又覆壓著舊時代的沉重的陰影”(5)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第113頁。。以散文詩般的表達,描述了中國近代史上各種政治力量的交替和社會現象的演變,賦予了歷史想象以立體圖景,體現了革命敘事中的民族原則。
歷史實在展現審美,歷史想象抒發感受。只要在審美和感受相結合的基礎之上,人們就能將世界的歷史從一種由毫無意義的沖突與爭斗構成的荒誕主義史詩,轉變成一部有著明確道德意義的悲劇(6)海登?懷特:《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第139頁。。整個近現代史的論述沉浸在革命的氛圍和語境中,胡繩先生以科學把握歷史史實為基礎,對歷史現象的元素進行預設,通過對“實在”概念的梳理和分析,再現了歷史場景,使得歷史解釋更加具體化;同時遵從時代和政治背景,把歷史記述設定在倫理的框架中,符合主流價值體系的要求。通過想象,充實并連接了直接觀察到的脫節的歷史實在碎片,字里行間流露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胡繩先生建構了一種回應現實的史學范式和敘事方式:貫通了民族精神和物質力量,在特定習俗和道德觀念上產生文化共振。
(二) 革命性敘事方式——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中國近代歷史在動態中承受著接踵而至的外生力量的沖擊,獨特的社會機制壓迫著內生力量。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的近30年中,歷史學界缺乏縱深連貫、實事求是梳理近代歷史全貌的著作。陳旭麓先生歷經了“文革”時代,在《近代史思辨錄》中回顧了建構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背景和動力:“近代社會的巨變,時而駭浪滔天,時而峰回路轉。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疾苦,是那樣激勵著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萬象雜陳、新陳代謝飛速的近代社會作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機。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學家那樣由概念推論出存在,而是認真地思考歷史的勢態,占有資料,從存在去思辨事變的由來及其演進,尋找它的規律。”(7)陳旭麓:《陳旭麓文集》第四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65-166頁。包羅萬象的思想大解放運動,營造了日益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陳旭麓先生打破了近代史研究的框架,顛覆了近代史研究的模型,以獨特的敘事方式開創了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填補了近代史敘事方式的空白,其敘事風格雖然受政治操控的時代背景影響,但不乏新的突破。
陳旭麓先生熟讀經史,國學功底深厚、辭章優美,把語言學、修辭學的底蘊發揮在歷史研究中,詩性與歷史的客觀性渾然天成,以活潑生動的語言風格營造了絢麗壯觀的歷史想象,突破了“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異,很少有不同風格和個性的顯現”(8)陳旭麓:《陳旭麓文集》第四卷,第165-166頁。的傳統歷史分析法。陳旭麓先生在《近代史思辨錄》“自序”中“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的詩句,流露了時代像浪潮奔騰,歷史像沙痕累積的情感,把歷史看作生命體,類比于生態系統的新陳代謝,形象地描繪了歷史實在的嬗變與遞進、特質與要素,糅合了修辭的魅力與實質,鍛造了歷史的真實,同時又煥發了歷史想象色彩。
陳旭麓先生開創了歷史敘事的新格局:政治是歷史學的骨架、經濟是歷史學的血脈、文學是歷史學的靈魂,只有多重要素的交匯與貫通,歷史學方能洋溢出歷史實在的科學性和歷史想象的文藝性。既不是從具象的紀實中演繹出概念推論,也不是從虛構的純思中幻化古今。一個人的學術巔峰狀態總是透過他深廣的論域具體地體現出來的,而論域的深廣又最足以考驗他的視野和學力(9)周武:《蒼涼的黃昏——晚年陳旭麓與新時期中國史學》,《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6期。。歷時十余年,完成了“中國本土史學的標志性文本”——《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這部煌煌巨作,詮釋了一種全新的、獨特的敘事方式。通過對革命語境中情節和事件的描述,賦予歷史實在自在的形式和內容,又自為地為歷史想象提供了修辭學話語,在詩性中凸顯歷史的主旨和要義。在洞察中國近代社會的興衰更替中積累了關于時代巨變的思考,形成了近代中國新陳代謝的敘事理路。
首先,為歷史實在奠定了革命的場所。陳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中,分析了中國近代以來各階層的思想轉變,突破了政治界限,強調了人民的歷史地位,把人民的歷史活動和貢獻置于歷史新陳代謝的動態中考量。打破了以階級斗爭、侵略與反侵略為主線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研究格局,沖擊了“兩個過程”的框架束縛,依循近代社會的演進邏輯,探索歷史進程的演變規律;沖破了凝固性的傳統社會,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構建革命敘事的系統化和體系化的近代史。《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其布局結構:分析了近代歷史進程的塔形層次,闡述了歷史實在的演變路徑;論述了“改良派”在不同歷史時段內的演化過程;陳述了秘密會黨、農民戰爭、人口問題、軍閥變遷等復雜的事實。以宏大的歷史視野把近代歷史作為完整的社會形態進行研究,他看到的歷史就不只是表象的歷史,而是前后、上下、左右彼此具有內在關聯的歷史,是整體通貫的歷史(10)周武:《世變、思辨與淹貫之境——陳旭麓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6期。。陳旭麓先生通過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重維度的嚴謹考據,實現了歷史本身賦予的真實性。馮契先生稱贊陳旭麓先生:“劉知幾謂史家須具‘才、學、識’三長,而世罕兼之。旭麓卻是當之無愧的‘三長’兼具的史家。”(11)馮契:《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序》,《陳旭麓文集》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30頁。
其次,嫁接在錯綜復雜的歷史場景中,遵從藝術風格的特征,實現歷史想象的架構。陳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中,剖析了“革命”和“改良”的共性與差異;研究了愛國與賣國、侵略與進步等的辯證關系;觸及了進步與保守、激進與平緩的交錯;洞察了民族沖突與階級斗爭的轉化;反思了新舊矛盾的相互紐結和互相滲透;重構了正義與非正義、變革與反變革的內涵;澄清了“西學東漸”與“中體西用”的流變;界定了“海派”的價值所屬;透析了由“夷”到“洋”的民族心路歷程;整合了反傳統與現代回歸的要素等。以浪漫主義的筆調,對整個歷史領域進行意義重構,深化了歷史敘事方式的意蘊。以豐腴的歷史想象陳述了歷史遞嬗的曲折,在歷史的緯度中,流露了陳旭麓先生扎實的學術底蘊;在歷史的經度中,富含了陳旭麓先生宏闊的思辨魅力。陳旭麓先生以妥帖的辭章,彰顯了歷史實在的厚度和歷史想象的力度,反映了陳旭麓先生厚實史識與精巧想象的融合,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嫁接的渾然天成。李書磊在答記者采訪中盛贊:“陳先生的書明達而深刻,有一種老吏斷獄般的入骨。中國近代史能得國人如此談論,也算是二百年來中國人所受苦難的一種補償與救贖,有了這樣的書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苦沒有白受,也不能說我們沒有希望擺脫命運的輪回了。我相信反思與覺悟的力量。”(12)李書磊:《文化危機中的知識分子職業——答采訪者》,《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2期。
歷史想象與時代旨趣相契合。對各階段和各歷史時期的史料掌握程度以及對事實的理解程度,影響著史學家對人文底蘊和歷史精神的透析程度,因而歷史實在的解釋方式和模式也略有差異。在革命的宏大歷史視野中,滲透了史學家個人的創作意識和理念,造就了近代史學家的情結,以飽滿的歷史想象填充在歷史實在中,最終以美學的風格進行表述。
二、 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的糅合:現代性敘事方式
現代性敘事對現代化的認識和認同傾向于通過歷史想象來實現。學術邏輯與時代背景的融合作用,推動了歷史解釋向現代化方向轉變。歷史是不確定性的另一個名稱,永遠向發展新理論體系的可能性敞開著。因為歷史是一個變化、修正和發展的領域,它的目的是開放(13)麥克?瑞安:《馬克思主義與解構》,李昀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頁。。近現代史在自由開放的向度中,彰顯了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的深度糅合。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歷程》的現代性敘事方式在內容和架構上突破了傳統的敘事框架,體現了敘事方式的與時俱進和創新性。
虞和平先生被尊崇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泰斗,以宏大的國際視野觀察近代中國,以大歷史的格局建構了經典的現代化敘事模式,《中國現代化歷程》是體現其風格的典型范本。李大釗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歷史橫向是歷史,縱向是社會,橫縱交錯呈現了空間視域的社會結構。《中國現代化歷程》依照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規律展開,既揭示了橫向的歷史,又剖開了歷史的縱向。現代化語義下的歷史以社會結構為主線和依托,遵循時代主題和意識形態的言辭模式,賦予了近現代史現實性和時效性。現代化趨勢中,歷史實在以社會合理性為基準,為歷史想象提供科學論據和信念支撐;附著在歷史想象的審美功能上,伸張了現代化敘事方式自由的向度。虞和平先生的現代化敘事范式囊括了革命范式的規則,又附加了現代性敘事技巧。
(一) 《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現代性敘事方式的架構
《中國現代化歷程》以世界的現代化潮流為背景,根植于中國國情,建構了符合現代化特點的解釋體系。現代化敘事方式以探討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演變過程為目標,堅持社會資源分配的原則,以多學科綜合交叉為敘事手段,以馬克思的現代化理論為路徑,為現代性敘事中歷史實在的出場設定了特殊的時空條件。
虞和平先生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分析了世界現代化的引導作用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填充了歷史想象的表達。世界現代化的三個進階:英國的“早發內生型”(14)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歷程?緒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頁。、美國的“原態移植外生型”(15)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歷程?緒論》,第51頁。、日本的“嫁接移植外生型”(16)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歷程?緒論》,第59頁。,為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創設了大歷史背景。在這部通史中,虞先生對160年的中國現代化歷程進行了科學系統的劃分:以現代化為主軸和線索,審視了中國現代化從資本主義現代化向蘇聯式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過渡,進而轉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深化并創新了中國現代化的解釋體系。
虞和平先生以馬克思的現代化理論為方法論抓手,契合了馬克思主義政黨意識形態一元化的原則。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先進成分在中國滲透和擴散,不僅包括科技和社會發展等基礎層面,還涉及民主和法權等上層建筑維度。虞和平先生在分析處理內因與外因、傳統與現代、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等關系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敘事方式的基本遵循。譬如考察傳統制度與意識形態對現代化的制約作用、論述重農抑商的傳統意識對中國現代化的壓抑效果、分析商人與商人行會組織的繁榮因素,以及頻繁的世界貿易打破了傳統經濟思維和經濟質素等,力求點與面的合理結合,發揮了歷史想象從點輻射到面的敘事技巧,為中國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的對流開拓了嶄新的解釋空間。
(二) 《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現代性敘事方式的創新
虞和平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者對歷史的尊重和敬畏是研究范式的基礎,也是歷史實在表達的原則。用歷史學方法研究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就應該力求再現中國現代化進展過程的全貌,考察其內在的運動機制和規律,分析其成敗得失的經驗和教訓(17)李儉:《新范式和新史學——虞和平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339頁。。在框架的安排、內容的表述上,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之間巧妙互補。如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正面論述了辛亥革命,對有爭議的太平天國運動、二次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等領域較少涉及,從而真正做到“從固有的‘線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脫出來”(18)李儉:《新范式和新史學——虞和平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75頁。。在論述外資利用問題時,回避了頗具爭議的義和團運動,避免了論據的歧義和不必要的學術爭端。又如論證“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的關聯時,強調“革命既是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種重要動力,也為現代化建設解決制度、道路問題,并掃除障礙”(19)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歷程?緒論》,第22頁。,論證了“革命化”是現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因素,達到了遵從歷史實在又強化歷史想象的效果。
虞和平先生現代化敘事方式的內容創新,重點體現在對現代化進程階段和道路劃分的歷史實在敘述中。在“前提與準備”的章節增加了傳統社會的裂變與動力因素;“啟動與抉擇”中擴充了畸形發展與道路分野;“改道與騰飛”中,強調歷史過程的連續性和整體性,克服了以往研究側重于“指標體系”的片面性。《中國現代化歷程》涵蓋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傳承關系,發揮了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包容性,分析政治現代化與經濟現代化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權的角色互補、區域現代化模式的建設、現代化解釋體系與現代化道路選擇等。對羅榮渠先生的“傳導性”現代化進行補充和拓展,提出“傳動性”現代化,一方面強調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對中國現代化的誘導作用;另一方面強調中國人的自主追求作用(20)李儉:《新范式和新史學——虞和平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72頁。,體現了虞和平先生廣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學術洞察力,以厚實的歷史實在功底,創新了合乎時代的歷史想象。
虞和平先生的現代化敘事方式借鑒了國外現代化研究理論,融匯了中國歷史學敘事方法,貫通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和現實中,賦予了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研究模式。觀照客觀的歷史實在,靈活把控和處理歷史想象的尺度,建構了合理的現代史解釋體系,形成了完整的內容架構,創生了區別于革命史敘事的獨特風格。虞和平先生對于中國早期現代化整體狀況的深入思考和宏觀把握,彰顯了深厚的學力和較強的理論思辨力,以至在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中實現自由切換。
三、 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的交織:后現代性敘事方式
后現代性敘事方式,在學理層面賦予歷史想象更廣闊的表達空間,以實現歷史想象對歷史現象合理性的彌補。在敘述技巧上,巴爾特認為事實只是語言學上的存在,事實在修辭學中可以詩性、可以修辭化,由靜態的單維度、動態的雙重維度擴展歷史事件的外延和內涵。后現代性敘事方式以修辭學、美學作為工具,在歷史實在的基礎上對歷史想象進行演繹,在歷史詮釋中體現修辭的魅力,把歷史置于審美的層面。柯文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注:以下簡稱《歷史三調》)作為后現代性敘事方式的范本,體現了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深層次的交織,流露了情懷和溫度。
《歷史三調》作為一部史學論著,體現了柯文的現實觀,以及在“歷史實在”中折射出的文化特殊性;作為一部史學理論,闡發了柯文歷史敘事方式的異質性;作為一部歷史哲學著作,探索了“歷史想象”的認知論。柯文以義和團運動為案例和載體,用浪漫化的筆調描述了義和團在基督教神話氛圍中的傳奇史實,思考了歷史記憶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關系;記述了封建救贖的情節,以戲劇化的色彩描繪了封建制度下的農民階級意識,探討了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復雜關系。記憶的話語里歷史研究的作用被認識到了,它似乎也不過是意識形態中的一個因素,按照精英階層的興趣和需要陳述歷史,把它當作一種爭奪權力的工具,為在建構、解構和重構集體身份方面有權力為專有名詞進行語義界定者所使用(21)陳啟能、王學典、姜芃:《消解歷史的秩序》,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頁。。被政治化了的歷史,在時間和空間上呈現出不同的面相,同時也賦予了歷史想象更廣闊的發揮空間。
柯文歷史敘事方式的三個層面——事件、經歷和神話,類同于弗洛伊德對人的三個層次的界定——自我、本我和超我。柯文延承了黑格爾的浪漫主義風格,借鑒了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提喻模式對歷史進行深層分裂和消解。柯文通過對歷史實在的分析,反思了傳統和西方史學家把中國歷史局限在一個總括的框架內的解釋模式,批判了近現代主流哲學文化的理論基礎和思維方式。他認為“只有采用開放式的變化模式,輔以開放式的問題,史學家才能勾畫出一幅對歷史事實比較敏感的中國近世史的畫面”(22)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頁。,否定了西方解釋學者整體性和中心性的歷史敘事方式。柯文的史學思想具有明顯的后現代主義傾向,既不過度苛求歷史實在的中規中矩,也不標榜歷史想象的溫情脈脈。
(一) 作為事件的后現代敘事方式——建構
柯文強調歷史進程的偶然性和歧向性,否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反對“宏大敘事”的歷史撰述方式,契合了后現代主義的觀點。他認為歷史的演進沒有終點,主張碎片化的歷史是歷史實在的認知途徑,符合后現代化理論中的歷史發展規律和終極目標。在《歷史三調》中,柯文并沒有系統、整體地爬梳歷史細節的真實性,而是反對對歷史進行概括性的定論。柯文主張研究中國歷史應當定位于“中國史境”,把參與者關注的問題作為歷史事件研究的起點,運用“移情方法”突破歷史研究的直線方式和理論框架,他所謂的“移情”是指“進入中國內部,開始了解中國人自己是怎樣理解、感受他們最近的一段歷史的。”(23)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第11頁。柯文闡述了對歷史的解釋不僅要理解事件本身的緣起,而且要連通前后歷史進程的關系,“我們在理解和解釋歷史時,必須有意識地尊奉(在實踐從未完全實現過)社會公認的關于準確性和真實性的,即辨別歷史上不同的個人的經歷之間有無聯系和把空間和時間跨度很大的大量零散史料組合起來寫出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的能力。”(24)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化的義和團》,杜繼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頁。柯文建構的敘事方式以描述碎片化的歷史為主線,將其鑲嵌在歷史發展的過程和時空序列中,力求最大尺度地還原歷史真實,使得歷史實在更具張力。楊念群認為:“柯文對義和團的分析與國內學者一貫強調義和團運動的性質、社會構成與源流追蹤,并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的研究途徑大為不同,體現出了相當明顯的后現代取向,表露出了相當純粹的后現代立場。”(25)楊念群:《“后現代”思潮在中國——兼論其與20世紀90年代各種思潮的復雜關系》,《開放年代》2003年第3期。這足以顯示柯文在對歷史實在的處理上,采用了宏闊的思維模式。
(二) 作為經歷的后現代敘事方式——解構
《歷史三調》的第二部分,柯文以“經歷”解構歷史。“每個群體的經歷都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沒有任何兩個群體是以相同的方式經歷義和團運動的。”(26)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第51頁。他認為歷史學家無法完全揭橥歷史真諦,憑借個人主觀歷史想象,只能部分恢復歷史實在。由于當事人的回憶和記錄側重點不同,導致意識的盲目性和多元化。圍繞傳統和文化展開,分析“經歷”的歷史特征,每個參與者在不完整的歷史實在中博弈著,引發目的和行動的多樣性;地域特點和文化差異,導致揭示的歷史人格具有相對性和片面性;處于同一歷史漩渦的個人經歷為歷史想象填補了空間的連續性,塑造了“每個參與者個人經歷的綜合體”(27)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第53頁。的歷史。柯文在歷史敘事方式中重視跨文化比較研究,對西方文化過于理性的反感,正是對人存在樣態的理解;從歷史想象的文化空間、社會空間等角度,解釋了歷史實在中人格的相對性。在《歷史三調》中,“義和團的文書揭帖用宗教詞匯來建構義和團運動,直接表明上天的意志,旨在消除外國在中國的影響力。把義和團運動當作上帝和魔鬼之間的一場大決戰。”(28)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第51頁。以人本的視角分析義和團宗教謠言與社會環境的聯系,建立個人記憶與社會心理的關系。后現代主義者主張從人本心理和情感維度研究歷史,柯文更傾向于滲透情感世界,考察義和團成員的思想感情,恐懼以及夢想。柯文的歷史敘事,運用心理學、宗教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交織方法解析了義和團運動,凸現了中國民眾的思維模式,印證了“歷史學家是現實與歷史之間的調解人”(29)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第235頁。,符合后現代理論的旨趣。
(三) 作為神話的后現代敘事方式——重構
后現代的觀點強調史學應當以一種敘述文本的方式呈現,重新拼接歷史的演進序列是消解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之間沖突的途徑。歷史現象的重構擊破了歷史隔離感和“本質性”規定。柯文在第三部分中重構了一個過去與現在的平衡點,塑造了以實證為主、主觀動因為輔的后現代敘事模式。
神化歷史的過程是權力對歷史的“篡改”過程。不同時代和處境的革命家和政治家遵從意識形態和現實觀照,抽取歷史片段、進行夸張和變形的雕塑,以賦予特殊的價值判斷,進而重構“歷史神話”,創造“歷史事實”。“事實是一種混合物,它是意念與所與底混合物,我們既可以說是套上意念的所與,也可以說是填入所與的意念。”(30)金岳霖:《知識論》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741頁。神話制造者出于政治企圖和情感修飾等目的對史料進行篩選,塑造歷史的絕對化和統一化。對“義和團”的多面解讀足以證實神話制造者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圖:在追求“科學”與“理性”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義和團被貶低為“迷信”,被抨擊為舊文化中最邪惡的東西,象征著落后愚昧;在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浪潮中,義和團被解讀為愛國主義革命運動;“文化大革命”時期,義和團被標榜為反抗的革命榜樣,被神話為“民族精神”的寫照。歷史與政治的結合為建立社會共識造勢,激發民眾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導致歷史敘事的極端性和片面性。
柯文置身于人本主義的高度,平衡了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的偏激,申張了后現代主義“破權威”“去中心”的觀點,同時否定了“歷史虛無主義”,倡導歷史實在的遵從和敬畏。柯文客觀的省察“‘義和團’不僅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而且是一種群體記憶進行文化建構的結果,還有可能是權力運作過程中不同的派別對之進行話語構造的結果。”(31)柯文:《以人類學觀點看義和團》,《二十一世紀》1998年第2期。他認為文化差異致使自我認知的歪曲,指明歷史參與者在文化、社會向度上的局限性,倡導客觀解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歷史,即對歷史想象的客觀定位和依附。偉大的歷史,恰恰是在歷史學家對過去時代的想象為他對當前各種問題的見識所闡明時才寫出來的(32)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歷史是什么?》,吳柱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年,第23頁。。柯文的后現代思維范式,凸顯了歷史實在的共時性和歷時性,與歷史想象糅合,為現代化敘事模式提供了鏡鑒。
四、 結 論
近現代史的敘事方式是歷史話語的編纂形式。現象、內容、語言、想象、心理等歷史的質素,在時代前進中呈現了迥然不同的歷史思維模式。歷史實在本該存在于意識形態之外,然而貫之于歷史想象的修飾和編織,增添了歷史現象的人文氣息和生動性,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摧毀了歷史本真。人是歷史的建構者與記述者,歷史研究與時代文化背景和社會意識形態不會斷然的隔離,因此呈現出來的不是孤立的、冰冷的歷史,而是傾注了主體目的性和主觀意念的歷史,實現闡發歷史規律、影射現實的雙重目的。人們對歷史的理解總是從“片面的理解”出發,經過“自我批判”達到“客觀的理解”(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4頁。。近現代史的敘事方式也經歷著由片面到整體的演變過程,其需要歷史實在和歷史想象的平衡。
革命性敘事方式與革命時期嚴酷的政治斗爭形勢密切相聯,歷史實在與歷史想象的不對等的敘事方式,壓制了歷史想象的空間邏輯,壓縮了對歷史想象的包容性,但為歷史想象提供了語言維度和修辭維度的生存空間。現代性敘事方式中,歷史研究者在把握歷史實在時更加關注與主體之間的體感距離,給予了歷史想象更多的容忍度,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歷史內在與意識形態互動與糾葛的窠臼。后現代性敘事方式中,在“去中心化”和反對理性氛圍中預示了歷史實在的出場范式。后現代主義強調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反思和批判,其敘事行為呈現出叛逆性、狂歡化傾向,缺乏明確的邊界意識,對傳統敘事方式全方位解構,缺乏哲學思辨的理論自覺,植入過多的主觀訴求,歷史想象的比重過大,因而敘事立場更加自由,建構了更加豐滿的歷史想象,展示了更加自主的敘事方式。
歷史與政治的交互作用,體現在“學術與政治乃是命運共同體,因而具有指向民族獨立、民族復興的學術研究范式,同時也是奠定于中國共產黨政治實踐的基礎上,體現民族性內涵及其與時代性的銜接”(34)吳漢全:《試論中共根據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學術建設》,《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5期。。跌宕起伏的歷史,在宏大敘事與精簡敘事的交融中發揮了對現實與時代的鏡鑒作用。與時代相稱的敘事方式是表達歷史最貼切的模式,在敘事方式的嬗遞中,無一例外地閃現著對歷史實在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