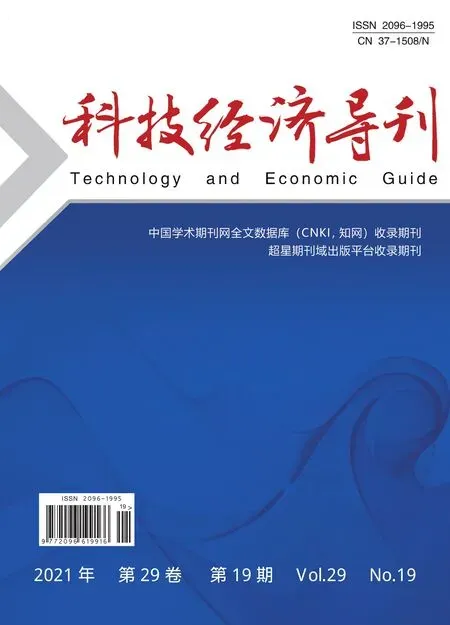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分析
王婧瑜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管學院,陜西 楊凌712100)
盡管我國長期以來致力于拉動內需,也出臺了若干刺激內需的政策,仍然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在數字普惠金融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其移動支付的優勢提升居民消費力度顯得尤為必要,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也顯得迫在眉睫。居民消費的增長是經濟增長與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數字普惠金融推動的移動手機支付,革新了傳統的支付方式,為人民帶來了更便捷的生活體驗,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深遠的,結合現狀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這一課題,有助于挖掘提升居民消費的方法途徑,促進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1.課題研究背景及意義
我國正處于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階段,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對于投資與出口的依賴程度較大,為了促進我國的經濟轉型升級,拉動我國居民消費、擴大內需,將成為未來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但傳統金融體系一直以來都過于注重深度而輕視廣度,社會各階層享受到的金融服務有顯著差異,數字技術的發展讓金融服務變得更加便捷,也降低了金融服務的成本與應用門檻,根據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數據,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總指數由2011年的49.4上升到2018年的229.9,短短幾年內實現了迅猛增長,作為一種全新的金融業態,研究其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及實踐意義,也對今后我國擴大內需、打好經濟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1]
2.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歷程及現狀分析
2.1 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歷程
數字普惠金融最早提出是在2005年,自概念提出以來,各個國家都開始重視其發展,并制定相應的政策,以擴大普惠金融業務渠道,傳統金融機構模式較為單一,且業務擴展渠道較窄,商業可持續性低,行業與社會力求創造全新的金融模式,我國也出臺相關扶持政策,讓數字普惠金融不斷發展與突破。但在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下,信息技術在普惠金融領域鋪展運用,產生了數字普惠金融,為傳統普惠金融業務大大擴大了廣度,降低了普惠金融業務的門檻,也突破了其發展的瓶頸,數字普惠金融相較于普惠金融而言,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風控能力也更好,在金融領域得到了極為廣泛的應用,不僅拓展了傳統金融領域的邊界,也為進一步提升居民消費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2 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現狀
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迅捷,且不斷完善,呈現出極為蓬勃的發展態勢,第43次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顯示,我國2018年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9.6%,入網門檻低,居民使用網絡的成本低,普及率高,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也越來越快,當前,數字普惠金融用戶群體正覆蓋全年齡層,越來越多人的生活離不開數字普惠金融業務,正成為居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助手,不僅包含轉賬支付、信貸、理財、保險等業務,還不斷擴張服務領域,正在持續拓展自身的深度與廣度。[2]未來也將持續推進數字服務基礎建設,助力全范圍居民消費水平的增長。
3.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分析
3.1 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
數據表明,我國的最終消費支出一路走低,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更是逐漸降低,從2000年居民消費支出在GDP占比的46.9%到2018年的38.9%,可以顯著看出我國居民消費低迷的趨勢。[3]當前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仍然是生存型消費為主,享受型消費為輔,尤其是2020年疫情以來,居民消費降級的話題引發熱議,中國結構性轉型升級顯得更加艱難。為了進一步優化居民消費結構,讓居民消費與經濟發展步伐一致,金融行業需要做出自己的努力,釋放潛在的消費需求,數字普惠金融兼具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的特點,能夠大幅度提升消費者的支付便利性,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刺激了消費的需求,如以支付寶、微信錢包等的第三方支付平臺讓支付變得具有簡便性、安全性與快速性,依托于智能手機的普及,第三方支付平臺能夠使得消費場景能夠隨時隨地的產生,讓消費變得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進而刺激了居民消費欲望。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也大大降低了消費者的流動性約束,使得居民消費水平得到提高,傳統普惠金融常因為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使得金融服務存在較高的風險性,也使得金融業務門檻較高,雙方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較大,但在大數據時代,數字普惠金融大幅提升了雙方信息的透明性,且降低金融服務門檻,傳統金融業常常忽略的消費“長尾”群體也能享受金融服務帶來的消費優勢,解決了消費者資產流動性不足的問題,挖掘了大批受到消費流動性制約的群體的消費潛能,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
3.2 有利于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
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就是消費,居民消費是經濟高速增長、并高質量發展的不二法門,對于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4]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降低消費者預防性儲蓄的比重,也就能自然增加消費者的財富效應,讓消費者更樂于進行享受性消費。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消費結構的優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數字普惠金融帶來了互聯網理財業務的興起,貨幣基金業務體量逐步增加,購買余額寶、財付通等基礎理財產品的網民規模越來越大,到2020年,我國購買了此類及相關理財產品的網民規模達到6.1億,理財規模的體量也從2013年的0.22萬億增長到了2020年的15.5萬億,相較于傳統儲蓄,互聯網理財讓消費者的財富增速更快,相較于傳統金融,互聯網理財門檻更低,還可以隨時查看自己的收益,得到網民的一致追捧,網民財富增長加快,消費能力增強,消費結構也隨之變化。同時,第三方支付平臺與互聯網貨幣基金業務無縫對接,讓消費者能夠根據自己不同期限的儲備需求進行緩沖,同時還有基于大數據產生的數字保險業務,讓居民消費更加安全,對于風險規避型的消費者而言,也降低了他們預防性儲蓄的動機,更愿意將儲蓄用于當下的消費中,消費者不僅提升了消費水平,也無形中轉變了傳統消費觀念,促成了消費結構的轉變。除此之外,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讓商業氛圍更趨向良性發展,商家能夠不受時間與地域限制,在線上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既可以滿足居民最低層次的消費需求,也可以緩解高層次消費的預算約束。隨著線上購物平臺的發展,居民還可以購買發展型與享受型消費商品,如旅游產品、教育產品等,都能夠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優化,消費結構的優化又能進一步助長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3.3 建立了有效的消費水平提升作用機制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漸擴大,抑制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結合絕對收入假說可知,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消費傾向呈現出正相關,收入差距的擴大會抑制居民的消費傾向,進而降低居民消費水平,同時,結合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理論,高收入群體對于高端消費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而低收入群體對于高端消費呈現出不足,儲蓄高而消費低,受限于預算的結束,因此較大的收入差距會導致居民消費結構優化速度慢。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金融服務向中下層收入群體延展,中下層收入群體也可以獲得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增加了他們的經營性收入,進一步提高其未來收入,也降低了他們預防性儲蓄的比重,且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使經濟進一步增長,對于縮短城鄉收入差距是有益的,也就能夠建立更有效的消費水平提升作用機制,2000年到2016年中國進口消費品占總消費比重平均為42.47%,居民消費需求外溢嚴重,這是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新機遇與新挑戰。[5]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使產業升級,填補國內高端產品的供給缺口,進一步優化消費結構,其引發的商業模式創新與技術創新也能夠促進產業升級,信息技術與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的融合,拓展了商品、服務的營銷空間,建立更有效的消費水平提升作用機制,挖掘更多消費群體的消費潛能,讓居民整體消費水平穩步提升。
4.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趨勢思考
為了進一步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首先,我國應當持續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及消費結構的優化,才能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再助推數字普惠金融進一步升級。為此,國家應當進一步提升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并幫助更多居民掌握互聯網使用技能,讓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到更多地區,并持續推廣數字普惠金融的移動支付服務,讓更多居民建立電子支付賬戶,并在欠發達地區加強數字普惠金融業務普及與宣傳,逐步提升地區的數字化進程。此外,數字普惠金融業務發展還應當堅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為導向,不僅落實“數字”,更要落實“普惠”,讓低收入地區的居民能夠借助數字普惠金融業務提升自己的收入,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緩解其消費約束,才能進一步為經濟發展提供長久動力。
5.結語
本文結合數字普惠金融相關概念及發展歷程、發展現狀,從多個角度論證了數字普惠金融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整體而言,數字普惠金融讓金融服務覆蓋面更廣,為低收入地區居民消費也提供了條件,同時其可得性與便利性也助推了居民消費,其提供的理財業務、保險業務等也幫助居民建立消費信心,調整居民消費結構,促進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對于居民消費具有正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