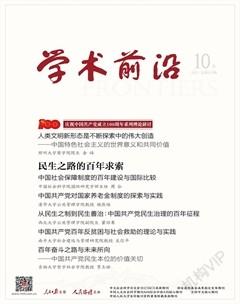從民生之制到民生善治:中國共產黨民生治理的百年征程
【關鍵詞】民生治理? 民生政策? 民生善治
【中圖分類號】 D632.1?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9.003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我們要時刻不忘這個初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1]。自1921年始,正是堅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中國共產黨將一百年的風雨兼程化作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歷史成就。[2]可以說,發展民生、改善民生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首要目標,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的奮斗史因而也是中國人民福祉增進的民生史。[3]黨的民生治理是以平等滿足人民群眾不同時期的生存、生命、生計、生活訴求為目標,通過保障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使人民群眾的民生福祉得以持續實現的政策設計、制度安排及實踐路徑。在此基礎上,中國人民實現了從饑餓到溫飽再到全面小康的歷史跨越,夯實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民生保障與物質條件。學術界關于中國共產黨民生治理發展的相關命題討論,已經形成較為系統的理論成果。現有研究通過時間脈絡提挈,從歷史演進、實踐舉措、經驗方法等方面整理并凝練中國共產黨以發展民生、改善民生為目標的民生治理實踐,并對黨的民生觀、治理觀進行理論邏輯、實踐啟示、經驗總結等維度的全面解讀[4],這對于廓清黨在民生治理方面的思想架構、理論精髓以及實踐機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本文通過回顧中國共產黨“均地權、建政權、強治權”的民生治理實踐演變,從歷史變遷、政策邏輯和實現路徑三大維度進一步分析黨的民生治理經驗,以求為實現民生善治提供借鑒。
土地分配、制度保障與民生善治:百年民生治理的歷史變遷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土地分配謀求政權建立。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始終為解決中國人民的民生問題不懈奮斗。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求索民生問題的真理歷程中,將工人階級的民生難題作為自己奮斗的重中之重。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要制定關于工人和農民以及婦女的法律,其中改良工人待遇,包括廢除包工制;八小時工作制;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工廠保險;保護女工和童工;保護失業工人等。[5]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黨的革命事業和前途命運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八七會議”正確分析了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與主要矛盾,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的總方針,明確了以農民群眾為主體的革命運動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選擇。由此,中國共產黨民生政策的重點從對工人階級的關注轉變為對工農階級的關注。更進一步地,在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中明確提出“沒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這些土地給佃農及無地的農民”行動策略[6],夯實了通過土地保障農民民生、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民生方針。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蘇維埃政府陸續出臺了《土地暫行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等土地法規,以明確土地分配原則、實行孤寡救助等方式有效地保障了農民階級的地權,初步踐行保障農民民生、動員農民參與中國革命的方針。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沿襲了保障工人階級民生權益的革命傳統,通過出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等法律法規的形式,從勞動保險、失業救濟等方面切實保障了工人階級的民生水平。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政府以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為目標,堅持維護民族團結、緩和階級間矛盾,保障人民安心工作、生產與作戰。根據不同人群的民生所需,邊區政府民生保障的工作也多有側重:針對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中國共產黨領導實施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的政策,一方面通過“保證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借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之后,又須實行交租交息……須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借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7]。針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則通過“勞資兩利”的勞動政策保障工人階級的民生權益,即“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增加邊區的生產,同樣地為了增強抗戰力量……嚴禁高利貸的剝削,嚴禁操作市場壟斷投機。實行一種中介制度,在政府中介之下,勞資雙方訂立勞動契約,酌量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改良生活待遇”[8]。上述民生治理措施既保證了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基本生計,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地主、資本家的利益,進而促成階級矛盾的緩和與階級團結。與此同時,為了通過民生政策平衡不同人群的利益,促進團結,謀取戰爭勝利,邊區政府在黨的領導下開展了針對抗日軍人及其家屬、災民難民、少數民族等群體的民生保障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基于對民族矛盾向階級矛盾轉移的基本判斷,作出了轉變民生政策的決定。為了奪取革命的最終勝利,中國共產黨人需要更加廣泛地團結工農階級,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到解放戰爭中來。由此,中國共產黨將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贏得了農民階級的廣泛擁護。踴躍參與到解放戰爭中的農民階級成為人民解放軍有力的“后勤保障”,也匯聚成中國革命最堅實的力量源泉。隨著革命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也在大中型城市中開始勞動保險制度的初步探索與嘗試,這既保障了工人階級的民生,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勞動保險制度的確立積累了寶貴的初步經驗。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經濟社會條件約束下的二元民生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基于計劃經濟體制的規劃要求和國家經濟實力尚不發達的現實,采取了城鄉二元的民生保障方式。
對于城市居民而言,勞動保險、公費醫療構成了民生保障的核心。1951年2月,以《東北公營企業戰時暫行勞動保險條例》為藍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正式出臺,條例對全國范圍內職工百人以上的國營、公私合營、私營和合作社營企業及鐵路、航運、郵電等企業單位職工及其直系親屬的醫療、生育、年老、疾病、傷殘、死亡等待遇及職工福利問題作了明文規定。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社會保險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標志著社會保險體系的初步構建。1952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于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公費醫療制度開始建立。[9]此后幾年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了勞動保險與公費醫療制度,增加了覆蓋人數。同一時期,中央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還就職工福利、社會福利事業、福利工廠、生活困難補助等發布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內容涵蓋發放職工生活困難補助、冬季取暖補貼、探親補貼、交通補貼、休假療養等福利性補貼,設立托兒所、幼兒園、食堂、洗澡堂、醫務室、閱覽室、體育場等福利性設施,以及在大型國有企業設置職工子弟學校,等等。至此,以勞動保險與公費醫療制度為核心、職工福利為補充的城市居民民生保障體系趨于完善。
考慮到國家財力與農民通過地權分配所獲得的民生保障,對于農村居民的民生保障以社區互濟共助式的“五保”制度和合作醫療制度為主。1956年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農業合作社對于社內缺乏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應當統一籌劃……在生活上給予適當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生養死葬都有指靠”[10],“五保”制度正是以此為起點逐步開始探索與發展。然而,“五保”制度僅僅是針對農村最困難群體的兜底性救濟,農村居民所面臨的民生困境依舊巨大,尤其是在醫療衛生領域。為解決諸如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惡劣等相關問題,中國共產黨采取了社區互濟式的合作醫療制度,通過培養“半農半醫”的衛生員,充分利用“兩根手指、一根針、一把草”滿足農村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農村合作醫療的相關經驗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充分肯定,稱贊“合作醫療好”。伴隨著合作醫療經驗在全國的迅速推廣,該制度也被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還在農村建立了免費的基礎教育制度與救災制度,與“五保”制度和合作醫療制度相輔相成,構建起中國農村居民的民生保障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以民生治理促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民生政策成為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輔助手段,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制度的建立,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緩解了經濟轉型和體制變革的陣痛,體現了民生政策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1978年,中國共產黨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主張,改革開放偉大戰略的核心之一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過去幾十年的民生保障政策,絕大部分是依托公有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基礎構建起來的,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中國民生保障政策的改革。
作為市場經濟改革和國企改革的配套措施,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是改革開放時期民生保障政策的核心。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依次建立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與失業保險,形成城鎮職工“五險并行”的格局。此后,歷經十數年的探索,中國政府以全民醫保和人人享有養老金為目標,于2009年頒布并實施“三年醫改”方案,同時啟動農村居民養老保險試點[11],在隨后的幾年里逐步構建起適用于全體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制度。至此,社會保險成為“制度性全覆蓋”的中國共產黨民生保障政策的核心。
社會救助方面,面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貧困問題,中國以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范本構建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9月,國務院頒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標志著城市居民低保制度正式確立;2007年,頒布《國務院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由此建立起農村低保制度;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發揮社會救助的積極作用,在城市和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之外又確立了特困人員供養、受災人員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業救助和臨時救助等制度,最終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主體的綜合性社會救助體系。
社會福利方面,隨著改革開放與國企改革的深入,原本由單位提供的社會福利無力延續,轉而以社會化的方式實現。1984年3月,民政部在福建漳州舉辦的經驗交流會上提出“社會福利社會辦”的觀點,鼓勵社會各界力量創辦社會福利事業。從此,社會福利的供給模式開始從國家包辦向國家、集體、個人合辦轉變,中國社會福利也開始引入社會資源,朝著多元化供給的方向發展。[12]
義務教育方面,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文盲、半文盲人數高達2.3億。為了提升國民素質,增強國際競爭力,教育部于1986年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明文規定了“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方案,提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合理設置小學、初級中等學校,使兒童、少年就近入學”,從此確立了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的法律地位。[1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從民生之制走向民生善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日漸增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生治理水平亦隨之不斷提高,并逐漸擺脫了服務于市場經濟改革的從屬地位,轉而成為人民不斷提升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制度保障,民生善治的目標正在漸次實現。
第一,民生制度的公平性、互濟性不斷提升,碎片化的制度逐步整合。從2014年起,經濟支撐能力的增強和社會管理水平的提高,促使從城鄉分別推進生活救助制度、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的思路,轉變為統籌整合的城鄉居民社會救助制度、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實現了企業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并軌,強化了民生保障不同制度項目的整合程度及協同程度。除此之外,基本養老保險中央調劑金制度、基本醫療保險跨省異地就醫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以及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政策的完善,進一步提升了民生保障項目省際的系統性協同化程度,使民生保障制度逐步從碎片走向整合。
第二,民生領域的政府支出水平不斷提升。當前,民生領域的支出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逐年提升,甚至一躍成為全國一般公共支出中規模最大、比例最高的項目。據財政部《2020年財政收支情況》顯示,以2020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例,2020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45588億元,其中教育支出36337億元,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32581億元,衛生健康支出19201億元[14],分別位列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項目的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僅這三項民生支出就占到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35.9%,足見民生支出規模之宏大、地位之重要。
第三,民生領域的保障項目逐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民生保障項目的數量逐步攀升,服務質量同步提高。2017年1月23日,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中提出的民生保障項目涵蓋公共教育、勞動就業創業、社會保險、衛生醫療、社會服務、住房保障、公共文化體育、殘疾人服務等8個領域81項公共服務;今年3月30日最新頒布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2021年版)》重新梳理了基本公共服務項目,包含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優軍服務保障、文體服務保障等9個方面、22大類、80個服務項目[15],服務內容更加清晰,服務頻次和服務規范更加明確,更有利于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均地權、建政權與強治權:百年民生治理的政策邏輯
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治理經歷了從均地權到建政權再到強治權的邏輯演變,其背后所反映的是民生治理環境和主要矛盾的變遷。地權確立了民生治理的起點,政權落實了民生治理的內容,治權強化了民生治理的維度和層次。
以均地權確立民生治理起點。人類歷史中任何國家的初始化,均是將土地作為政治活動的對象并賦予其主權意義。[16]近代中國,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以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為綱領,故而在成立之初就盡可能地團結一切無產階級者。其中,農民階級作為受剝削和壓迫最深最重的階層,成為了革命戰爭時期最廣泛的支援力量。針對革命任務在不同時期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基于時代環境的動態研判靈活地調整土地政策,有步驟地終結了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業生產資料的壟斷,盡最大可能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翻了身,從而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一方面為革命戰爭支援必要的物資,另一方面動員人民群眾參與到革命戰爭隊伍之中。以土地政策為代表的民生治理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的支持,依靠人民群眾成就了中華民族獨立解放這一歷史偉業。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農民對黨和新政權形成了政治認同,構成了中國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邏輯起點。[17]
以建政權落實民生治理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政權的全面建立,中國共產黨依靠人民確立了政權的政治合法性。為進一步鞏固政權,中國共產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將取之于民的權力用之于民,推動中國民生事業朝著長期性、動態性、綜合性的方向發展,這既是黨的執政之基,也是黨的力量源泉。[18]通過建立經濟體制、制定階段性發展計劃、明確社會基本矛盾,綜合研判各時期民生治理的重點難點,并通過體制性建設為人民提供符合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民生服務,將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貫穿于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黨和政府通過“為人民服務”將權力滲透于基層和各級治理機構,構建起規范運作的民生治理運行體系,保障了各類民生治理內容在全國范圍內的有效落實。
以強治權豐富民生治理層次。治權是政府治理國家的權力,作為主權的派生性權力[19],其在數量上的增減變化并不會增強或弱化主權。[20]在民生治理的探索和建設過程中,國家治權的下沉和讓渡一方面促成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的自治模式,另一方面也壯大和鼓勵了參與民生改善的社會力量,實現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有效銜接,彼此互相成就。民生治權的強化是實現民生善治的重要條件,特別是多元民生治權主體在民生治理領域中扮演了動員、協調、組織和保障的重要角色,發揮了補齊單一權力結構下民生治理短板的作用,構建了現代社會多元化、多層次的民生治理格局,民生治理的維度也因此更加豐富、立體。
從民生之制到民生善治:百年民生治理的實現路徑
民生治理是政府、社會和公眾在民生需求和民生政策之間達成均衡的善治行為,其實現路徑在于依據時代特性回應民生需求,遵循規律性形成民生政策,重視適配性實現民生善治。
依據時代性回應民生需求。民生政策的發展具有鮮明的歷史性,是不同時期民生治理的外在表現。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繼承弘揚馬克思主義所蘊含的人文和民生思想之余,還批判地吸收了西方人文主義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著保障民生、為民謀利在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基礎性、保障性地位,并將其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又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進入21世紀,科學發展觀又提出“和諧民生”的理念。總之,從固國安邦、穩定發展到和諧社會、公平共享,中國共產黨民生政策的治理導向直觀地反映出不同時期民生需求鮮明的時代特征。
進入新發展階段,民生治理應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現實參照,瞄準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具體內涵,積極回應民生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代全民民生需求內容呈現出多層次、全方面和高質量特征。從過去的“物質文化需要”到如今的“美好生活需要”,民生治理既要持續發展物質文化的“硬需要”,也要著力建設更加民主法治、更加公平正義、更加安全體面、更加全面持續的社會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在主觀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層面的“軟需要”[21]。一方面,要加強兜底性、基礎性、普惠性民生建設,健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保障制度體系。另一方面,要實現從學有所教到學有良教,實現更好的教育;從業有所屬到業有所專,實現更好的就業,從勞有所得到勞有多得,實現更滿意的收入;從風險化解到國民保障,實現更可靠的社會保障;從病有所醫到健康中國,實現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從住有所居到住有所適,實現更舒適的居住條件;從環境保護到生態文明,實現更優美的生活環境;從文以化之到精神樂之,實現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時,新時代民生治理要著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矛盾。應以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為依托,凝聚社會共識,為民生治理積蓄社會力量;以國家機構改革為契機,深化社會保障與民生領域的改革;以主體聯動為重點,形成對保障水平、覆蓋統籌、管理協調等民生難點治理的社會合力。要對民生保障中的“硬骨頭”下大力氣進行治理,加強制度整合,提高管理效能,縮小人群間、地區間、制度間的差距,以共享發展成果為目標,形成民生治理的合作收益路徑。[22]
遵循規律性形成民生政策。民生政策的選擇具有特定的發展規律,不同時期的民生需求對于民生治理具有關鍵的導向性作用。與此同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治理能力也對民生治理產生了重要的調節作用。因此,不同時期民生政策的選擇是在民生需求、時代環境與治理能力共同約束下的適應性選擇。
新時代民生治理需要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推動頂層設計的制度創新、民生保障的管理創新、民生治理的機制創新和均等受益的服務創新。首先,面對日益開放的市場經濟活動與勞動力就業流動形態,推動頂層設計的制度創新。要基于便攜性和可及性原則,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以及區域間的互通發展;基于系統韌性原則,將管理重心前置于風險發生前的科學預警,合理儲備保障資源,科學謀劃應對方案,保持民生保障系統的適應性,提升民生保障系統的穩定性和抗逆性。其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動民生保障的管理創新。對現行民生保障的管理制度、經辦模式和監督體系進行創新,根據不同類型的公共事業,分類形成規范、統一、高效的包含服務宗旨、服務清單、業務流程、專業術語、人員要求等內容的標準化監督管理體系;建立健全市場及社會化公共服務機構的評定評估和準入退出機制,提高行業服務水平,提升民生保障管理、運行和監督效率;通過對制度結構、項目類別、費基費率與待遇進行統籌調整,進一步提升社會保險制度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再次,在新時代的中國語境下,推動民生治理的機制創新。民生治理需要市場和社會在政府主導下的有效推動和有序參與,以及在三者相互信任、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深化彼此間的溝通與協商,從而凝結共識加強互聯、互嵌,創建良好的合作環境;明晰利益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確立公平統一的協同參與規則與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構建激勵相容的合作治理框架。最后,在技術革命的浪潮下,推動均等受益的服務創新。借助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逐步實現深度融合的公共服務系統、高效運作的經辦管理系統以及公開透明的信息互聯系統;根據人口與需求分布特征,整合服務資源與信息,推出契合需求、覆蓋全面、內容豐富的項目包,差異化匹配智能設施,合理設置服務半徑,實現資源配置與民生需求相吻合;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有效發揮大數據、區塊鏈等在信息整合、精準預測、信息公開以及服務供給方面的技術和平臺優勢,及時進行政策評估,準確反饋群眾訴求,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的省域貫通和全國漫游,增強民眾對民生服務的滿意度和獲得感。
重視適配性實現民生善治。民生需求的滿足是實現民生善治的重要體現,在特定的經濟社會條件下進行民生治理,需要不斷提升民生政策的適配性。唯有實現民生治理的內容涵蓋上多維立體、需求對接上現實可行、服務供給上精準有效,才能夠實現民生善治。
基于新時代民生需要的現實考量,為實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為重點的“民生七有”,解決人民群眾“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住房難、養老難”的“民生五難”問題,需要立足“民生三度”(危險度、風險度、適存度)目標,提升“民生三感”水平[23],通過民生保障的制度設計,實現民生善治的最終目標。首先,通過危險度抑制,提升人民群眾安全感。危險度抑制是民生保障的基本目標,主要包括個體經濟危機度和健康危機度。為提升居民生活安全感,應發揮好社會救濟等政策在居民基本生活保障中的作用,抑制個體危機和社會危機的發生,避免危機致貧和危機返貧。其次,通過風險度化解,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風險度化解是民生保障的重點目標,主要包括養老風險、疾病風險、失業風險和失能風險等。應通過社會保險等政策進一步提升社會成員個體及其家庭的風險抵御能力,完善城鄉社會保險體系,提升各項社會保險的協同與融合程度,不斷增強社會風險的化解能力。最后,通過適存度提升,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感。適存度提升是民生保障的關鍵目標,主要包括生態環境適存度、社會生活適存度和精神文化適存度等,其構成了居民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內涵。要堅持“房住不炒”的目標,依托“兜底保用、經濟適用、市場享用”等分層分類政策工具,確保住有所居和住有宜居;堅持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通過“開發紅線、生活橙線、生態綠線”等自然環境預警機制,確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文以化之和精神樂之”的理念,加強公民教育,倡導全民參與,全面提升國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本文系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全生命周期視域下健康老齡化體系路徑研究”和陜西高校青年創新團隊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1BSH021、21JP117)
注釋
[1]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求是》,2018年第1期。
[2]季正聚、王瑤:《熱話題與冷思考——新中國70年:輝煌成就、基本經驗與內在邏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3期。
[3]戴衛東:《中國共產黨民生思想的實踐邏輯與治理特征——以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為視角的考察》,《社會保障研究》,2021年第3期。
[4]張遠新、吳素霞:《中國共產黨百年來領導民生建設的歷史考察及基本經驗》,《江漢論壇》,2021年第5期;蒲新微、衡元元:《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求索與未來展望》,《蘭州學刊》,2021年第5期;郭定平、梁君思:《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體系的四重邏輯》,《探索》,2020年第6期。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33頁。
[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二七)》,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94~297頁。
[7]韓延龍、常兆儒主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四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83~184頁。
[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匯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第17頁。
[9]席恒、余澍、李東方:《光榮與夢想:中國共產黨社會保障100年回顧》,《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10]《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頁。
[11]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70年發展(1949—2019):回顧與展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
[12]林閩鋼、梁譽:《我國社會福利70年發展歷程與總體趨勢》,《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7期。
[13]劉磊明、王玉國:《從基本普及到全面普及再到均衡優質 新中國義務教育制度“三步走”》,《中國教育報》,2020年2月27日,第6版。
[14]《2020年財政收支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站,2021年1月28日,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101/t20210128_3650522.htm。
[15]王皓田:《高質量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經濟參考報》,2021年5月7日,第1版。
[16]趙煒:《原始地權分裂中的國家政權集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17]趙曉峰:《服務權能與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政權建設的基本邏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18]任曉莉:《改善民生:黨的執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中國教育報》,2011年7月11日,第4版。
[19]范佳睿:《主權與治權的統一與分離對海上戰略通道安全的影響論析》,《當代亞太》,2020年第5期。
[20]盛文軍、王慶國、田銀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主權》,《社會主義研究》,1999年第3期。
[21]鄭功成:《習近平關于民生系列重要論述的思想內涵與外延》,《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22]席恒:《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重在創新》,《陜西日報》,2015年3月21日,第5版。
[23]翟紹果:《從民生之制到民生之治》,《中國社會保障》,2020年第4期。
責 編/張 貝
From the System for Livelihood Protection to the Good Governance of Livelihood: The CPC's Centennial Governan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Zhai Shaoguo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journey of the CPC's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ance has undergon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land distribution to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to good governan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volved with the policy logic of land equalization, establishment of regime, and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Ente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we should follow the policy logic of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ance; focus on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need, the logical regularity of people's livelihood policy and the practical adaptability of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ance; create a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ance that has multi-dimensional coverage, connects people's needs in a realistic and feasible manner, and provid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servic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ystem for guaranteeing people's livelihood towards the good governan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s: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ance, people's livelihood policy, good governance of people's livelih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