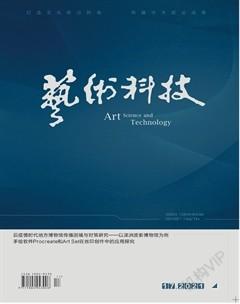涉農電視劇中農村形象建構及對鄉村文化振興的意義
摘要:電視劇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進行傳播,能夠對受眾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涉農電視劇中的農村形象分為物質形象和精神形象,是一種能引起人們思想和情感波動的具體形態。《山海情》作為一部爆火的涉農扶貧劇,在建構農村形象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在分析劇中農村形象的基礎上,指出該劇中農村形象的建構過程。鄉村文化振興決定鄉村振興的效果,塑造涉農電視劇中具有時代氣質的農村形象,可以激發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體動力即農民的精神,弘揚新鄉風文化,讓農民樹立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我覺醒、自我建設,振興鄉村文化。
關鍵詞:涉農電視劇;農村形象;建構;鄉村文化振興
中圖分類號:J9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7-0-03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文化作品出現在熒幕當中。除了娛樂化的電視作品外,也出現了越來越多貼合國家發展趨勢,唱響社會發展主旋律的影視作品。電視劇《山海情》是脫貧系列中的爆品,在眾多農村電視劇當中表現亮眼。鄉村振興,文化先行,這些電視劇的播出為鄉村振興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也助推了鄉村文化的繁榮。從鄉村文化振興的視角出發塑造農村形象,建構迎合時代主題、具有正向能量的鄉村形象,有利于激發農民的精神,發揮鄉村文化振興的多重功能,喚起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共鳴,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1 涉農電視劇《山海情》走紅原因解析
山海情講述的是20世紀90年代,在扶貧政策及福建對口扶貧的幫助下,西海固的村民從西海固地區搬遷至玉泉營地,經歷物質轉變和精神轉變,最終扎根在玉泉營地,走向康莊大道的故事。《山海情》作為2021年的開篇佳作,貼合時代發展,集結了眾多戲骨,為近年來農村題材電視劇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山海情》之所以能在瓶頸期的農村劇中突出重圍,與其自身的特色密不可分[1]。
1.1 以情動人:“離鄉”與“守土”之間的糾纏
《山海情》與歷史題材有關,講述的是吊莊移民政策的實施過程,政策的落實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此類劇情往往容易陷入模式化的敘事過程當中,講述的故事呈現出千篇一律、宣傳味道濃重的表象。但《山海情》側重于鄉村發展中的心靈變遷史,以“情”動人。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指出:“從基層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生于斯長于斯,對于生長在土地上的人民來說,土地就是他們的生命,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追求的是落葉歸根。跟隨國家政策從養育他們的土地搬遷至玉泉營地,這對西海固的村民尤其是老一輩的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村干部馬德福為了讓村民們脫貧致富,提倡全村搬遷,年長的村民寧愿貧窮也不愿離鄉。隨著矛盾的激化、調和、上升,故事情節不斷發展,中國農民在“離鄉”與“守土”間達成了平衡[2]。
1.2 全景展示:微觀和宏觀攜手并進敘事
涉農劇要在微觀與宏觀層面并行。微觀層面即講述家長里短、禮治秩序、鄉風農耕等以人為本的故事,宏觀層面則從全劇立意、戰略角度進行規劃。《山海情》刻畫了農民與家鄉的難舍難分、基層干部與農民的沖突、家庭間的矛盾,展現了大批青年才俊為鄉村振興作出的奉獻、村民為了脫貧付出的奮斗、脫貧政策實施的不易[3]。該劇既從宏觀立意把控全局,又從微觀層面吸引受眾。從兩個層面把握整部劇情,能與受眾建立親密關系,拉近與受眾的距離,也能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受眾的大局意識。
1.3 感官盛宴:視聽語言營造劇情氛圍
在視聽語言方面,《山海情》營造的場景、人物真實,貼近現實情境,與色彩鮮艷、飽和度高、干凈整潔的鄉村環境相較,劇中的土黃色更能讓受眾融入情境中。《山海情》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西北寧夏地區,在場景展示中,破舊不堪的土房子、漫天荒野大地與真實情況相符合,人物粗糙的肌膚、黝黑的膚色、殘破的服裝能立刻將觀眾帶入故事中。在電視劇語言表達方面,尤其是在鄉村題材電視劇的創作中,不同地區的方言具有普通話所不具備的感染力。釋義學家伽達默爾認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世界觀,人因為有了語言,所以才有了一個‘世界,才對世界有了一種特殊的態度”。該劇所用的寧夏方言能讓受眾身臨其境,讓人物更加細致立體,增強了人物的真實性和感染力。
正所謂“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農村題材電視劇的創作也應具有長遠的眼光[4]。
2 時代鏡像:《山海情》中農村形象的現代性建構
農村題材類的電視劇一方面代表著客觀世界中的農村形象是如何被展現到電視劇當中的,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受眾對農村形象的解讀和認知過程。形象指的是能夠引起人們思想、感情波動的具體形態或者姿態。本文探討的農村形象指由大眾傳播媒介建構、塑造的反映在大眾媒介載體上的農村形象,它分為物質形象和精神形象。這種農村形象與客觀形象之間存在差距,能夠說明建構者對“被塑造形象者”的理解、觀點、看法和態度等。農村形象的建構受農村在客觀現實中存在的實體形象、媒介以及受眾的認知三種因素的影響,三者彼此往來、互動,共同塑造了農村形象[5]。
2.1 物質形象
《山海情》從脫貧攻堅的角度出發,尋找符合自身實際和特色的脫貧方法,分析涉農題材電視劇中的農村形象,有助于我們理解涉農題材電視劇中的農村形象是什么,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這種農村形象的塑造與當下鄉村文化振興之間有什么關系。劇中的物質形象包括鄉村圖景、農業、農民、其他相關人物。鄉村圖景體現為電視劇中人物所處的物質環境、自然環境,劇中的鄉村圖景展現為符合現實形象的西北農村景象,荒漠戈壁,土房磚瓦,頻繁發生的沙塵暴,生存環境及自然環境極其惡劣。物質環境如房屋的表象特征為破敗不堪,難耐風雨;生活工具,如家具、勞作工具、出行工具等,呈現出質樸、簡陋、不便的特點。鄉村圖像整體難以生存、條件艱苦、簡陋破敗。隨著劇情的深入,劇中人物的居住環境和自然環境與原先的形象也呈現出鮮明的差異性,村民們把樣板村從荒漠建設為綠地,破土房建設成磚瓦房,發展庭院經濟,逐漸脫貧走上致富之路。在農業形象中,涌泉村由種植業、扶貧養殖畜牧業轉變為種植蘑菇的庭院經濟、勞務輸出等。農業形象也可以理解為農村的經濟支撐,脫貧劇重點講述的是農村的經濟發展,劇中金灘村從單一薄弱的經濟來源轉變為多元化的發展渠道[6]。
鄉村人物形象是劇中的重點呈現元素。人物是劇情創作過程中的靈魂主線,人物的行為產生劇情,推動情節的發展。劇中,人物形象可以分為傳統封建人物和具有新氣象的年輕一代。既有為了一頭驢賣掉女兒的水花父親,扎根涌泉村不愿搬遷的李大友,也有在封建禮教的枷鎖中爭取脫貧、改變命運,最終過上幸福生活的李水花、馬德福、麥苗、馬得寶等眾多青年,以及為了金灘村的明天辛勤耕耘的白崇禮教師這類中年人物形象。這些人物的外表形象呈現出濃烈的西北調性,或是黝黑的皮膚,或是與大地融為一體的土黃色肌膚,質樸而熱烈,勤勞而勇敢。不同的人物形象在劇中產生對比、沖突,從而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7]。鄉村物質形象的刻畫會在第一時間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形成受眾眼中的“主我”印象,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受眾認知。
2.2 精神形象
農村精神形象指的是受眾在電視劇中感受到的關于鄉土文化、價值表達的心理圖像,包括鄉土文化、主流話語、主旨表達。劇中主要展現了金灘村尋根與斷根、傳統與現代的爭鋒[8]。從頭至尾貫穿的老一輩堅守的“守根”價值觀,與主線情節吊莊移民之間存在尖銳的分歧,通過基層干部馬德福的勸說“根有兩端,一端在先人那里,一端在年輕人那里”和新一代年輕人以身示范的作用,涌泉村整村搬遷,展現了鄉土文化中的落葉歸根、堅守土地,以及與政策共行、與時俱進的新農民、新思想。傳統與現代的矛盾體現在劇中女性代表人物李水花的解放之路上。她不甘被賣,在搬遷至金灘村后通過自身努力擺脫貧困,追求獨立解放,是新時期獨立女性的代表。
鄉村振興需要思想“振興”,在脫貧道路上,村民需要和頑固思想作斗爭,擺脫封建惡俗傳統,走向新時代,這也是本劇展現的鄉村精神之一。主流話語影響農村題材電視劇的創作,為新時期的農村形象賦予了新的意義。本劇的主流話語即展現脫貧攻堅過程的艱苦,呼吁村民與基層干部跟黨走,展現辛勤奮斗、不言放棄、奉獻自我的精神。這些鄉村精神形象通過畫面語言與故事情節的發展從側面展現,能讓觀眾體會該劇主旨,進而產生共情,能引導觀眾的認知與行為,營造鄉村文化振興的氛圍,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3 鄉村形象建構對鄉村文化振興的影響
3.1 重振主人公精神
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發展基礎,要實現物質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文明建設的協調統一發展。其中,推動農民受眾思想意識覺醒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途徑之一,要重振鄉村振興的主人公——農民的精神[9]。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建構鄉村形象,傳遞相關信息與意義,給觀眾帶來感性的認知和情感波動,受眾對接收到的信息進行解碼,進而進一步調整自身的行為。格伯納的涵化理論認為,“電視所創造的‘象征性現實與客觀現實存在一定差距,電視通過輸入主流價值觀,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引導輿論,從而使公眾意見趨于一致”。電視劇作為大眾傳播媒介或新媒體平臺播出的演劇形式,對農村形象進行塑造,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受眾認知,引導受眾行為,弘揚新時代新鄉風文化,呼吁摒棄傳統惡俗、封建觀念,振興鄉村文化。
3.2 樹立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我覺醒
塑造積極向上、貼近群眾、符合時代特征的農村物質形象及精神形象,傳遞去糟粕、留精華的鄉村文化,以及健康的鄉村倫理觀,能夠引導農民樹立文化自信與自覺,加強農民思想道德建設,形成文化自我覺醒、自我建設,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占領農村陣地,凝聚鄉村振興的精神力量,振興鄉村文化[10]。鄉村文化振興的效果決定著鄉村振興的效果,決定著全面小康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質量。要發揮大眾媒介的傳播功能,利用電視劇對鄉村形象的塑造傳遞正向價值觀,為鄉村振興培養主體動力。
3.3 發揮文化振興的經濟功能
從文化治理的視角看,鄉村文化振興具有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的多種功能和價值。通過農村形象的熒屏呈現,農村形象被轉換成商品進行售賣,延長了商品自身的價值鏈。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理論認為亞文化收編的方式分為兩種:一是意識形態收編,二是以商品的形式收編。在商品收編里,農村形象被符號化,進而轉化成商品進行售賣。打造劇中農村形象供受眾觀看本身就是一種商品化行為,電視劇播出后所帶來的閩寧鎮地區的旅游熱、周邊產品的流行,也延長了該劇的價值效益鏈。利用劇中農村形象傳播當地鄉村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產業,推動相關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是文化振興的經濟功能之一。
4 結語
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精神力量、文化源泉,要激發農民的精神,助力鄉村文化振興。可將宏觀立意與微觀敘事相結合,利用鄉村文化資源,在農村題材電視劇中塑造符合時代發展特征的、具有正向能量、貼近受眾的鄉村形象,激發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體動力,推動鄉村文化振興。
參考文獻:
[1] 石姝敏.電影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研究——以電影宣傳片《啥是佩奇》為例[J].戲劇之家,2019(16):104-105.
[2] 甘露穎.自媒體時代“網絡縮寫”的話語特征解析[J].新媒體研究,2021(7):102-104,115.
[3] 丁月明.中國傳統文化視域下電影女性形象塑造分析——以電影《霸王別姬》為例[J].戲劇之家,2019(15):83-84.
[4] 王燦.以《風味人間》為例探究飲食文化類紀錄片傳播新走向[J].戲劇之家,2019(15):79-80.
[5] 位云玲.原創文化類綜藝節目持續走紅的原因探究——以《上新了!故宮》為例[J].藝術評鑒,2019(7):169-170,76.
[6] 馮廣圣.互嵌與協同:社會結構變遷語境下鄉村傳播結構演變及其影響[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2):91-101.
[7] 位云玲.新聞反轉的內在機理、影響及治理探究[J].新聞知識,2019(4):86-89.
[8] 陳奕樊.“快手”清流類鄉村短視頻中的農村形象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19.
[9] 李惠敏.助力鄉村文化自信:涉農紀錄片的當代價值研究——以《記住鄉愁》為例[J].東南傳播,2020(6):35-37.
[10] 楊藝,謝慧.融合傳播語境下鄉村文化振興的路徑研究——以江蘇鹽城市A鎮為例[J].東南傳播,2020(7):51-52.
作者簡介:霍煜芝(1997—),女,新疆阿圖什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文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