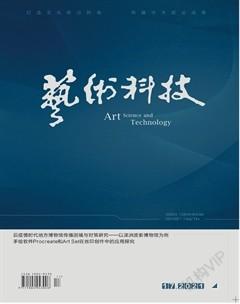敦煌壁畫對重彩山水畫創作的啟示
摘要:敦煌壁畫在世人眼中帶有古老神秘的色彩,第61窟的《五臺山圖》有很多可以被沿用到個人創作中的創作技法,對個人創作而言,學習其相關創作方法具有實踐意義。本文根據《五臺山圖》的色彩、空間構成、樹石法,對應時代文化,具體分析其對重彩山水畫創作的啟示。
關鍵詞:敦煌壁畫;重彩山水畫;《五臺山圖》
中圖分類號:J218.6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7-0-03
敦煌壁畫具有與世俗繪畫不同的審美特征,對青山綠水的描繪,或是獨立畫幅,或是存在于經變畫、故事畫當中,人們能從中感受到人對自然空間形成的美感認知。敦煌石窟自北朝伊始歷經十六國,與青綠山水的發展和興盛步調一致。在漫長的時光里,青綠山水在其裝飾填彩的色彩裝飾功能上逐漸擁有了獨特的藝術性,自然三維空間也變成了斑駁神秘的平面壁畫。
《五臺山圖》是敦煌壁畫中比較完整的、在五代洞窟的畫幅中尺寸較大的洞窟壁畫。第61窟是五代曹氏歸義軍的功德窟,人稱“文殊堂”,主要是為供奉文殊菩薩而修的。第61窟的《五臺山圖》可以被稱作山水畫,但又不只是對樹石云水的描繪,它是一幅難得的佛教史跡畫,巧妙地用山水作為紐帶將五臺山的不同地標聯系在一起,中間穿插了許多古代社會生活場面,如文殊菩薩道場、山川道路上的往來旅客、在寺廟里的送供拜佛者、佛塔寺院的高僧等等。并且每一處建筑都配有解釋的文字,可以說是藝術性極高的鳥瞰“地圖”。此外,《五臺山圖》擴充了佛教的歷史材料,完善了文字資料的記載內容,這些對于一件繪畫作品來說是彌足珍貴的。
本文從敦煌壁畫第61窟的重彩山水畫《五臺山圖》出發,探討其對重彩山水畫創作的借鑒意義及其對當代繪畫的啟示。
1 《五臺山圖》的色彩構成和獨特性
《五臺山圖》片段可獨立可連貫,每段小篇幅的色彩結構都有或大或小的差異,綠色、黃色、青色、赤色、白色、黑色是主要顏色。山川、山巒以綠色來概括,是畫幅的主要顏色基調;另一個面積較大的顏色是黃色,穿插在山石的結構中來表現土壤與山石層次;建筑多有白墻青瓦的特點,城墻圍欄多有赤色;黑白兩色出現在人物的衣物、道路、神獸等中,此處不一一贅述。
第一,綠色。《五臺山圖》中綠色的成分是天然的礦物質顏料,其中石綠的穩定性強,千年過去,壁畫上的綠色依然干凈清晰,可以看出石綠顏料質地細膩。大部分綠色是淡色的汁綠,筆者認為存在調色多遍再上色的情況,由于是分段式的模塊繪畫,所以綠色有強有弱,有比較明顯的變化,部分頭綠、二綠和三綠的區別也是比較明顯的。
第二,青色。在《五臺山圖》中,青色是比較統一和穩定的,大部分都用于石塊的頂部、房屋的瓦片、屋頂、基座處,壁畫上的顏色更偏向于花青。青金石這樣的藍色銅礦制作出的顏料穩定性強、融合度高,能較好地與其他繪畫顏料融合,所以壁畫的色彩保持得較好,水準較高。
第三,赤色。赤色即紅色,其顏色多來自紅土、朱砂、丹石等礦物,《五臺山圖》中的紅色多偏向于朱砂,即使過去了千年,顏色依然飽滿鮮艷,只有少量赤色和其他顏色混合略微發黑。赤色在壁畫中被用于勾勒建筑圍欄,填充墻壁和地標背景色。此外,一些有赭石成分的偏紅棕色的赤色在畫面中占比也較大,人物、牛、馬、駱駝等的皮膚和衣著配飾較多地使用這種赤色。
第四,黃色。《五臺山圖》中的黃色顏料成分主要包括石黃、黃土。黃色更多地被運用在山石道路上,和赤色配合使用。
第五,黑色。黑色的主要成分是墨,在《五臺山圖》中以勾勒主線條和書寫地標出現。不過,有些地方出現的黑色明顯不是原本黑色的元素,如經幡旗幟等,這些地方的黑色應是其他顏色氧化脫落逐漸發黑形成的。此外,黑色的成分不夠純,部分黑色摻雜了青色的成分。
第六,白色。白色的原料來自方解石等。白色往往會作為底層的顏色與石窟土面接觸,起著底色的作用,很多壁畫都是以白色為底,《五臺山圖》也不例外。
也有學者認為,敦煌石窟的壁畫與中國傳統的“五色”配色體系不謀而合,并以此為理論依據,最終建立了一套色彩與空間相互連接對應的“五色”配色體系。筆者認為這樣的配色體系是由不同的物質研磨調和出的,的確是有“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氣質。
關山月先生對莫高窟進行了全面考察后認為:“至唐代,作品已奠定東方藝術固有之典型,線條嚴謹,用色金碧輝煌,畫面繁雜偉大,宋而后因佛教漸形衰落,佛教藝術亦無特殊表現,且用色簡單而近沉冷。”[1]在《五臺山圖》中,綠色被大面積使用,成為全畫幅的主要基調,也與五代時期的畫面色彩特點相近。
《五臺山圖》畫面色調既清新又濃郁。以五代
-61窟西壁-五臺山圖127弘化寺(位于124“天壽寺”右邊,126“法華寺”上方)為例,這是《五臺山圖》的一部分。圖中一名男性官員在寺廟的院落中參拜作揖,寺廟墻體背面靠山,周邊山巒環繞呈“C”形環繞。
汁綠、石綠、花青、赭石、黃土這幾種顏色較為相近,較多冷暖色的搭配使用讓畫面比較柔和清新,由于色彩的飽和度比較高,畫面又呈現出既清新又濃郁的調子。尤其是山丘土堆的部分,用赭石的顏色作底,順著石頭的結構依次染上花青、赭石、石綠,顏色層次既融合又分明,師法自然又頗富美感。同樣的上色結構在寺廟院落中也有所體現,使用花青讓屋頂屋檐看起來較為清雅,房屋和墻邊的底座都用石綠,看起來較為厚重穩定。可以看出,這些冷色和暖色是當時的工匠刻意布置規劃的,從一些敦煌壁畫上遺留的“青”“祿”字樣和藏經洞出土的大量線描畫稿上的“夕”“工”“甘”字樣可以推斷出畫工們都有一套色標體系,這些冷暖色的使用代表了當時的畫工對色標體系有比較完整的認知,體現出畫工的智慧。
在《五臺山圖》中,明度的強弱對比較為明顯,石頭的陽面所用赭石顏色較淡,而兩側的陰面略重。裝飾土地部分的赭石色,顏色比較飽滿,明度較暗,充當了地面的固有色。在青、綠兩色的運用中,也可以明確地看到明度對比,提升了藝術效果。
《五臺山圖》的畫面以綠色為主、黃色為輔,畫面的整體風貌既清新又濃郁,不斷迭代演變的敦煌壁畫展現了那一代人色彩創作的獨特性,與同時期五代的青綠山水的色彩風格趨近,有同有異。
2 敦煌壁畫《五臺山圖》的畫面構圖和空間構成
《五臺山圖》屬于文殊菩薩的道場全景,前文已提到它是一幅難得的佛教史跡畫。畫作根據山西五臺山的地貌、真實地理位置和現實生活繪制,再現了一千多年前五臺山佛國圣境的宗教氛圍和世俗風情。畫面中的物象元素主要有山巒、樹石、云紋、植被、道路、建筑、人物、飛禽、牛馬、車馬器、生活工具、神話異獸等。其中物象元素豐富,兼具生活化圖景和佛教史跡傳說的神秘色彩。
在《五臺山圖》的部分畫面中,寺庵蘭若、城池房宇是畫面表達的主體,通過山川道路將這兩個主體銜接在一起,有整體的視覺效果,生動地描繪了弘化寺和佛光寺,這也是比較經典的畫面,下文具體分析這一畫面的構圖和空間構成。
縱覽以佛光寺為主的建筑周邊,大小山巒排序有致,也有主次之分。以唐代的構圖形式來看,主要是平遠構圖方法。這一段中有兩塊主要的山峰,前面一塊山坡別出心裁,山坡的道路上有往來行人、車馬、駱駝,看起來較為平緩;后一段山峰的山勢較為聳立,夾雜著豐富的植被草木和小建筑。而兩塊山峰之間,寺庵蘭若、城池房宇分布均勻,并未刻意地區分焦點透視,沒有遵循近大遠小的關系。但這一畫面遵循著“賓主朝揖”的主次關系,可以看到,“大佛光之寺”在畫面較為中心的位置,既不太偏,也沒有過于醒目呆板,十分得宜。這種平遠的構成關系能涵蓋很多想要表達的內容,再以山水為紐帶,將巨幅尺寸的《五臺山圖》組織起來,使畫面既有震撼力、沖擊感,又有細節和內容,實為這類題材繪畫的完美構圖選擇。雖然在當時沒有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去概括這種構成關系,直到郭熙的《林泉高致》才涉及“平遠”的定義,但也能看到,在五代時期,石窟壁畫構圖程式已經有了初步的表現。
在局部的構成關系上,也可以看到盛唐時期的構成方法對五代時期的影響。在“大佛光之寺”的周圍就可以看見局部的左右對比,有高山左右環繞,左邊山勢拉高,在“大佛光之寺”的右前方有一些小型的土坡。這樣的山勢高度處理,讓“大佛光之寺”背面靠山,前方有路通行,產生了左松右緊、左實右虛的畫面對比效果,一張一弛為建筑主體服務。在“弘化之寺”背后三山成“C”字形排列有序,中間山峰山勢較高,兩側山勢較低環繞寺廟,這樣的三山構成源于古代的傳統樣式,一般用于表現遠山,在“弘化之寺”周圍有局部的應用。在《五臺山圖》中也有很多局部的金字塔構成和闕形構成運用[2]。其有兩個共性:一方面,在這樣的巨幅尺寸山水壁畫的處理上,五代的畫工有意識地在大的構圖中不斷調整每一塊局部建筑周圍的構圖,以此讓畫面不單調;另一方面,在大多數局部處理的過程中,都是優先使寺廟建筑等背靠山,這一點大多是受古代傳統風水觀念的影響。
《五臺山圖》在地理交通的描繪上比較嚴謹,由此引發了一個關于“大佛光之寺”的趣事。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們前往山西五臺山尋找他們在敦煌壁畫中看到的唐代寺廟“大佛光之寺”。據說,當時遵循《五臺山圖》找到了唐代木結構的建筑——大佛光之寺,推翻了日本建筑學者“中國大地已沒有唐代以前的木構建筑”的斷言。不過,由于唐武宗時期的“大舉滅法”,《五臺山圖》中表現的大部分建筑已在當時消失了。
《五臺山圖》的構成方法對當前的重彩畫山水創作有重要意義,其嚴謹地概括山川地貌的手法也是值得學習的。《五臺山圖》將獨立分散的寺庵蘭若、城池房宇等融合成巨幅山水畫,把三維的空間轉化成了二維的平面壁畫,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3 敦煌壁畫《五臺山圖》樹石法的風格特點
從《五臺山圖》的局部細節來看,山川上的植被比較豐富,在繪畫技法上沒有同一時期的山水名家純熟雅致,風格上是不同的。在這一時期就可以看見點葉,具體表現為狀似芭蕉的樹木葉片舒展,排列有節奏感,在疏密關系上樹頭密集、樹尾疏朗,自上而下都是向上生長,葉片帶有彈性的弧度;而一些圓點小樹渾圓有力,圓點中間的小樹樹枝筆直上升,在唐以后多見這樣的畫法,與如今的重彩山水畫有異曲同工之處。也有比較獨特的雙鉤填色雜樹:樹頭造型中空,周圍的葉片排列一圈,中間留白,中間有紅色小點似小花小果的果樹。這一類型的樹木風格獨特,頗有西域風情,與當時多元的文化特征吻合。樹木的穿插排列也非常講究攢三聚五的特點,掩映在房屋建筑左右。可以看出,樹木的繪畫被唐以后的繪畫技法影響,在風格特征上仍保留當時的地域文化特點。正如許俊先生在《絲路遺珍——敦煌壁畫精品集》的序言里所云:“山水畫更強調人與自然的融合,是借助自然山水意象地表達人文精神。”在重彩山水畫創作上可以由此打開思路,在學習前人繪畫技法的基礎上,可不拘泥于形式而表現當代的萬千氣象,表現出當下的文化特征和氛圍。
在《五臺山圖》中,山峰石塊多與小丘陵和遠方的山巒組合。通過色彩的區分,山峰的層次結構清楚,在寺廟建筑周圍的石頭按近景處理,少皴法少苔點,更多的是展現石頭的結構造型,而遠處的山巒山峰有零星的小樹苔點。這樣通過大面積色彩的布置,有效地和房屋建筑呼應。少皴法、重色彩、重結構對于重彩畫的創作來說也具有實踐意義,在師法自然的前提下表現山川的意象,能夠呈現大面積的裝飾效果。
4 結語
本文根據敦煌壁畫《五臺山圖》的色彩、空間構成、樹石法,對應時代文化進行具體分析,以供當代重彩山水畫創作參考,可以總結為三點:第一,在傳統的敦煌五色配色法基礎上具體調配畫面色塊比例,可以通過色彩的明度、冷暖色等中西融合的理論技巧展現畫面;第二,《五臺山圖》為我們很好地示范了如何在二維畫面中展現比較宏觀的三維場景,整體畫面構圖方法從“三遠”入手,再具體通過不同畫面構成調整局部;第三,《五臺山圖》的樹石技法雖然不純熟多樣,但不多見的風格特點能夠啟示創作者如何表現當下的文化特征與時代主旋律。
參考文獻:
[1] 關山月.我所走過的藝術道路——在一個座談會上談話[M]//關山月論畫.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91:13.
[2] 趙聲良.從敦煌壁畫看唐代青綠山水[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8(5):6-14.
作者簡介:孫卿舒(1996—),女,江蘇常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畫重彩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