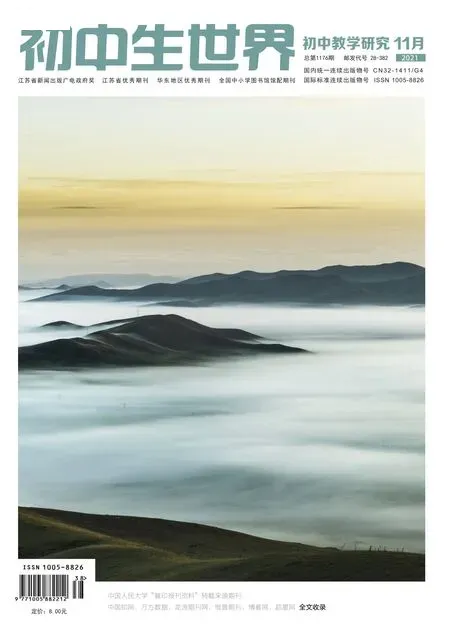過程化寫作要實現三個轉化
——以黃厚江老師作文講評課為例
■虞衛華
關于過程化寫作,國內學者已從不同的層面開展了研究。在研究與實踐的過程中,“過程”的含義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榮維東教授認為:過程化寫作是“由‘關注結果’轉向關注‘寫作過程’,由關注‘寫作產品’到關注‘寫作主體’,由關注‘外在結果’到關注作者的‘思維過程’”[1]。我嘗試結合黃厚江老師《享受語文課堂——黃厚江本色語文教學典型案例》一書中的具體案例和語境進行梳理和辨析,探討過程化寫作的具體操作方法。
一、邏輯起點——聚焦“過程”:從教學到寫作
傳統的寫作教學,包括情境化的師生活動,學生在具備寫作動機、了解寫作要求之后動筆、完成,教師進行批改,師生再完成后續的交流、修改。在這一過程中,寫作是獨立進行的,也就是說,學生是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完成寫作的。而過程化寫作旨在打破“教—寫—評”的線性流程,將“教”和“評”置于“寫”的過程中,三者相互滲透、相互促進,構建共存的生態環境。
后續的教學過程直接轉化為寫作過程,原本由“寫”和“教”兩個獨立部分組成的教學過程整合為“寫”的過程,在寫作的過程中滲入教師的“教”和“評”。“教”和“評”有了明確的目標指向和現實的操作步驟,從而可以有效發揮引導的作用。寫作構成了寫作教學的主體活動,從而使寫作教學在寫作的“過程”中實現。
二、呈現方式——改變“過程”:從封閉到開放
寫作過程由封閉到開放,實質上是教師介入學生的寫作過程。教師能夠及時發現和解決學生寫作中的問題,避免學生出現諸如“審題錯誤”“詳略不當”等問題;教師也能及時為學生提供寫作支點,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學生寫作中“閉門造車”。
“寫出人物的個性”一課中,黃厚江老師采用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互評的方式打開教學空間。一篇作文是由教師、兩名學生以及作者共同完成批改的。在這一過程中,全體學生都可以隨時參與討論,共同完成作文批改的任務。每個片段被兩名學生批改之后,教師就選擇三篇(或三類)共同講評,這三篇通常是評分差距較大或評分都在90 分以上的文章。如果說這樣的開放程度還不夠,那么在接下來的一個環節中,教學空間的開放程度更加明顯。黃老師問:“今天有寫黃老師的嗎?”實際上,很多學生都是寫黃老師的,因此,課堂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學生們的興致更高,交流范圍更廣。黃老師以寫作對象和批改教師的雙重身份參與其中,教學效果十分明顯。這樣的評講不僅拓展了評講主體的范圍,而且強化了學生的寫作體驗。更為重要的是,評講不只是停留在課堂教學中,而且指向學生今后的寫作經驗。
寫作理論的指導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實踐的依托和檢驗,很容易變為空洞的說教。教師只有將之與學生的寫作實踐相結合,并在實踐中反復操練,不斷檢驗,才能將寫作的理論知識落到實處,發揮理論之于實踐的指導作用。
三、操作流程——實施“過程”:從寫作到教學
寫作過程就是教學過程,與其說是教師參與學生的寫作過程,不如說是教師將學生的現時寫作狀態作為寫作教學的第一手資料。學生的寫作狀態是寫作教學最直接的學情,教師應該有針對性地開展教學活動。這其中不僅包括對教學起點的把握,而且應當能夠凸顯教學的難點,并最終在這一動態過程中將學生的寫作引向教學終點。
黃厚江老師在對題目為《感動》的作文的批改中,發現學生“一個普遍的問題是沒有‘感動’”。他分析問題的癥結,學生“心中沒有感動,筆下哪來的感動呢?沒有值得感動的事,又哪會有感動的文章呢?”。于是,黃老師將自身生活中遭遇的故事,以及自己“準備以此為題材寫一篇小散文”的想法引入了課堂教學,請學生們出謀劃策。經過一番討論,學生們理解了“感動”的內涵:不一定要有催人淚下的場景和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個鼓勵的眼神,一聲親切的問候,一次平常的微笑”都可以讓人感動。學生建議以“感激”為題目進行寫作。這節課看似是學生幫助黃老師寫作,實際上是師生共同參與了寫作過程。
結合以上案例,我認為,在過程化寫作的具體操作中,教師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首先,聚焦學情,教學要有針對性。作文講評課的目標不是為了講解而評價,教師應該以解決問題為目標,充分了解學情,針對學生的具體寫作狀態,有針對性地進行講評。
其次,教寫結合,不著痕跡。“教”是為了“寫”,“寫”的過程中滲透著“教”。教師結合實踐將寫作理論傳授給學生,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的寫作習慣和寫作實踐。
最后,強化體驗,內化評講內容。評講作文的根本目的是幫助學生突破寫作瓶頸,因此在過程化寫作中,教師要引導學生思考什么是好文章,反思自身寫作的問題。學生在寫作過程中學習寫作知識,思考寫作問題,增強寫作體驗,才能養成良好的寫作習慣,提升寫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