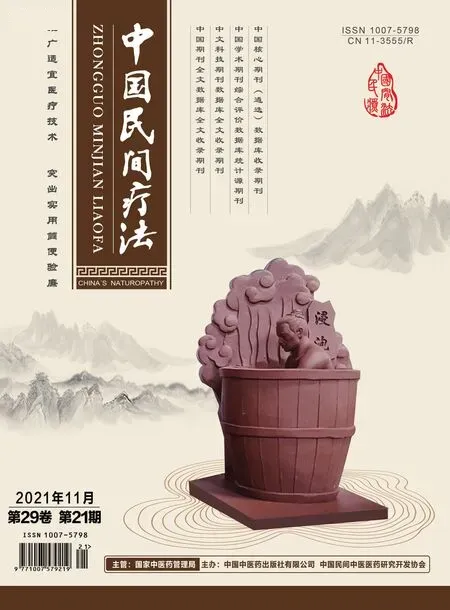腸通膏外敷治療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的臨床觀察※
任繼剛,張 哲,付 雯,陳 艷,劉 慧,雷 梟
(1.川北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四川 南充 637000;2.川北醫(yī)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0)
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PGID)為腹部手術后常見的臨床并發(fā)癥之一,指患者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內(nèi)集聚大量分泌物和氣體,臨床表現(xiàn)為肛門排便、排氣功能減弱,伴腹脹、腹痛等胃腸道癥狀,甚至導致全身炎性反應[1-3]。PGID的發(fā)生直接影響患者術后康復,盡快恢復患者胃腸功能和正常飲食是外科圍手術期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而現(xiàn)代醫(yī)學尚缺乏有效方法或藥物。現(xiàn)代研究證實,中醫(yī)藥治療PGID具有良好的療效,且方法較多。本課題組在前期已研制出治療術后腹脹的外用中藥制劑腸通膏,療效顯著[4-5],基于PGID的中醫(yī)病機,本研究進一步分析腸通膏外敷治療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的療效,現(xiàn)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3月至2020年7月川北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治療的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患者100例,按手術先后順序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每組50例。對照組男30例,女20例;平均年齡(43.65±10.45)歲;病程1~31個月,平均10(6,13)個月;其中胃十二指腸手術10例,結直腸手術13例,闌尾手術8例,肝臟手術10例,膽囊及膽道手術9例。治療組男31例,女19例;平均年齡(44.80±11.90)歲;病程1~25個月,平均10(6,15)個月;其中胃十二指腸手術9例,結直腸手術15例,闌尾手術7例,肝臟手術9例,膽囊及膽道手術10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過醫(yī)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審批號:2018KF009)。
1.2 診斷標準 ①西醫(yī)診斷參照《功能性胃腸病羅馬Ⅲ診斷標準》制定:表現(xiàn)為腹痛、腹脹、惡心、早飽、嘔吐、腹瀉及排便困難等;通過腹平片、腹部CT、消化道造影等檢查協(xié)助診斷[6]。②中醫(yī)診斷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中脾虛濕滯證[7]和《中醫(y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脾虛濕滯證[8]。主癥:食少納呆,體倦乏力;大便頻數(shù)或稀溏;食后或午后腹脹。次癥:神疲懶言,面色微黃;口淡不渴;舌質淡胖;脈沉細或弦數(shù)。具備主癥2項、次癥1項或主癥1項、次癥2項即可診斷。
1.3 納入標準 符合上述診斷標準;年齡18~65歲;簽署知情同意書。
1.4 排除標準 合并心、腦、腎等嚴重疾病者;有機械性腸梗阻者;神志昏迷、癡呆或皮膚感覺功能減退者;發(fā)熱患者;臍周局部皮膚有破損及瘙癢者;對敷貼藥物過敏者。
1.5 剔除標準 未完成治療者;治療記錄不完整者;治療過程中同時采用了其他的治療方法,無法判斷療效者。
2 治療方法
2.1 基礎治療 兩組患者均予以補液、營養(yǎng)支持、保持電解質穩(wěn)定等基礎治療,術后按照要求常規(guī)禁食,給予抗生素預防術后感染的發(fā)生。術后6 h開始治療,共治療72 h。
2.2 對照組 采用多源治療儀治療。患者仰臥位,暴露腹部,將多源治療儀(成都鑫博浩科技有限公司,型號:MF-C02B)垂直照射于患者腹部上方15~20 cm處,選擇中溫模式,以患者感到溫熱為宜。每次治療30 min,每日3次。治療過程中注意防止燙傷。
2.3 治療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配合腸通膏外敷治療。多源治療儀照射前,將腸通膏(主要成分:木香60份、枳殼70份、厚樸60份、青皮70份、檳榔40份、黃芪62份、肉桂73份、大黃82份等)均勻涂抹于患者腹部,注意避開傷口,藥膏大小根據(jù)患者體型大小、手術切口部位確定,厚度1~2 mm,在藥膏上覆蓋單層0.9%氯化鈉注射液無菌紗布,照射完畢后去除藥膏。每日3次。
3 療效觀察
3.1 觀察指標 ①記錄兩組患者首次肛門排氣時間、腸鳴音恢復時間。②術后指標恢復情況:分別于術后6、24、48、72 h記錄兩組患者腸鳴音次數(shù)、腹脹程度、伴隨癥狀,并進行評分,評分標準[9-10]見表1。③腹痛程度:采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AS)評定。劃1條10 cm長的直線,0代表無痛,10代表無法忍受的劇痛,讓患者在線上劃出代表其當下的疼痛分數(shù)。

表1 術后指標恢復情況評分標準
3.2 療效評定標準 依據(jù)治療前后術后臨床指標評分(腸鳴音、腹脹、伴隨癥狀、排氣時間)和腹痛程度評分改善情況評定。臨床痊愈:腹脹及其他癥狀消失,療效指數(shù)≥85%;顯效:腹脹明顯減輕,其余癥狀消失或減輕,療效指數(shù)為60%~<85%;有效:腹脹減輕,其余癥狀好轉,療效指數(shù)為30%~<60%;無效:腹脹及其他癥狀無改善,療效指數(shù)<30%。療效指數(shù)采用尼莫地平法計算:療效指數(shù)=(治療前評分—治療后評分)/治療前評分×100%。
3.3 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1.0統(tǒng)計軟件處理數(shù)據(jù)。計數(shù)資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符合正態(tài)分布時以均數(shù)±標準差(±s)表示,采用t檢驗,不符合正態(tài)分布時采用中位數(shù)(四分位間距)[M(Q1—Q4)]表示,采用非參數(shù)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
3.4 結果
(1)首次肛門排氣時間、腸鳴音恢復時間比較 治療組首次肛門排氣時間、腸鳴音恢復時間均短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患者首次肛門排氣時間、腸鳴音恢復時間比較(h,±s)

表2 兩組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患者首次肛門排氣時間、腸鳴音恢復時間比較(h,±s)
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
組別 例數(shù) 首次肛門排氣時間 腸鳴音恢復時間治療組 50 53.23±4.36▲ 24.60±1.89▲對照組 50 63.63±3.98 27.95±2.00
(2)術后指標評分、腹痛程度評分比較 治療前(術后6 h),兩組患者腸鳴音、伴隨癥狀、腹脹、腹痛程度評分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患者腸鳴音、伴隨癥狀、腹脹和腹痛程度評分均低于治療前(P<0.05),且治療組均低于同期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患者治療前后術后指標評分、腹痛程度評分比較(分,±s)

表3 兩組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患者治療前后術后指標評分、腹痛程度評分比較(分,±s)
注:與術后6 h比較,△P<0.05;與對照組同期比較,▲P<0.05。
組別 例數(shù) 時間 腸鳴音評分 伴隨癥狀評分治療組 50 術后6 h 2.40±0.55 2.43±0.60術后24 h 2.06±0.47△▲ 2.00±0.54△▲術后48 h 1.54±0.58△▲ 1.42±0.54△▲術后72 h 0.86±0.41△▲ 0.95±0.42△▲對照組 50 術后6 h 2.42±0.61 2.39±0.62術后24 h 2.32±0.51△ 2.32±0.59△術后48 h 1.84±0.42△ 1.76±0.63△術后72 h 1.16±0.55△ 1.48±0.62△組別 例數(shù) 時間 腹脹程度評分 腹痛程度評分治療組 50 術后6 h 2.38±0.72 6.57±0.89術后24 h 1.96±0.67△▲ 6.78±1.15△▲術后48 h 1.54±0.50△▲ 4.82±1.21△▲術后72 h 1.21±0.36△▲ 3.58±1.07△▲對照組 50 術后6 h 2.36±0.78 6.67±1.02術后24 h 2.32±0.68△ 7.42±1.21△術后48 h 1.82±0.48△ 6.14±1.20△術后72 h 1.40±0.61△ 5.06±1.19△
(3)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8.0%,明顯高于對照組的82.0%,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4。
4 討論
PGID是外科臨床常見問題,由于術前禁食禁水、麻醉及術中器械牽拉和損傷、術后疼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患者術后胃腸道功能減退,出現(xiàn)惡心、嘔吐、腹脹、腹痛、便秘等癥狀,嚴重時甚至發(fā)生腸梗阻[11]。如果不能盡快恢復患者胃腸道功能,不僅影響其手術恢復,而且會增加術后各種并發(fā)癥的發(fā)生風險,影響患者整體康復。現(xiàn)代醫(yī)學治療PGID主要采用禁食、抗感染、補液、胃腸減壓及給予胃腸動力藥等[12-13],不良反應較多,療效不佳。臨床上外科針對術后患者常采用多源治療儀治療,以減輕術后腹脹、疼痛、腹部切口脂肪液化等問題[14-15]。多源治療儀是通過以遠紅外線為主的電磁波產(chǎn)生的熱效應和非熱效應共同作用于人體,引起照射組織一系列生物效應,從而產(chǎn)生治療作用。研究發(fā)現(xiàn),多源治療儀作用于術后腹部可明顯改善腸管及周圍血液循環(huán),促進腹腔內(nèi)滲出物的吸收,減輕組織腫脹,降低組織張力,促進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恢復[16],故本研究選取多源治療儀治療作為對照組。大量臨床報道和實驗研究結果表明,中醫(yī)藥治療PGID有顯著療效[17-18],可通過多方法、多途徑發(fā)揮治療作用。
根據(jù)PGID臨床表現(xiàn)可將其歸屬于中醫(yī)“痞病”“腹痛”范疇。該類患者由于腹部手術對其脾胃功能損傷較大,加之術后禁飲禁食,術后常出現(xiàn)納差、惡心、嘔吐等脾胃虧虛癥狀。脾主運化水濕,脾胃虧虛,水濕失運,則濕濁內(nèi)生,加之手術損傷,瘀血為患,瘀血、濕濁滯留于腸間,導致臟腑功能失調、氣機不暢,進而導致患者出現(xiàn)腹脹、腹痛、排氣排便延遲等癥狀,病機總屬正虛邪實,即正氣虧虛,臟腑失和,氣滯血瘀、痰濁蘊結于腹內(nèi)[19]。因此,本研究運用行氣活血化瘀、通絡止痛、益氣健脾治法,攻補兼施。該病患者常規(guī)禁食,口服藥物改善胃腸道功能受到較大限制,故本研究采用外治法治療。將藥物貼敷于一定部位,通過穴位皮膚的滲透、吸收作用,使藥效直達病所,不僅能提高血藥濃度,還能減輕藥物的不良反應。李念芳[20]予以腹部手術后患者中藥包腹部熱敷,結果表明中藥包熱敷能降低患者腹脹、惡心等癥狀發(fā)生風險,促進術后胃腸道功能恢復,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并改善其預后。吳麗平等[21]采用傳統(tǒng)中藥熱敷治療婦產(chǎn)科腹部術后腹脹,結果證實中藥小茴香熱敷能改善術后腹脹程度。此外,大承氣沖劑對紊亂的胃電節(jié)律具有良性的調節(jié)作用[22]。可見,中醫(yī)治療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的方法較多,可明顯改善術后患者胃腸道功能紊亂癥狀[18,23]。
基于腹部手術后患者正虛邪實、腑氣不通的病機特點,本課題組在前期研究中已經(jīng)研制出腸通膏,臨床觀察發(fā)現(xiàn)其可改善術后腹脹,促進直腸癌患者根治術后腸道功能恢復[4-5],為腸通膏治療PGID臨床研究的深入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腸通膏中,檳榔、木香行氣導滯,枳殼、青皮、厚樸消痞除滿,黃芪益氣健脾和中,肉桂散寒止痛、溫經(jīng)活血,大黃通腑泄熱、行氣逐瘀,全方具有行氣活血化瘀、散寒通絡止痛、益氣健脾的功效。現(xiàn)代藥理學研究顯示,大黃含有番瀉苷,可增加結腸張力,加快腸蠕動,促進排氣,且不影響小腸對營養(yǎng)的吸收,還有明顯的糾正腸道菌群紊亂的作用[24]。木香含木香內(nèi)酯、木香堿等,能緩解胃腸氣滯所致的腹脹[25]。黃芪具有調整腸道微生態(tài)失調的作用,可改善患者胃腸道功能[26]。本研究結果也顯示,腸通膏外敷結合多源治療儀治療PGID總有效率為98.0%,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且具有溫度可控、安全簡便易行的優(yōu)勢,具有良好的經(jīng)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綜上所述,腸通膏外敷治療腹部手術后胃腸道功能紊亂,可明顯改善患者腸鳴音恢復、伴隨癥狀、腹脹和腹痛等,有利于患者術后胃腸道功能的恢復,但是對其作用機制的研究尚不足,這也是今后研究的重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