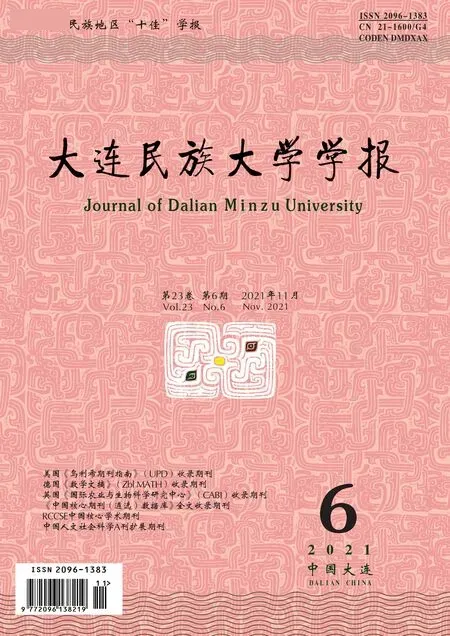游歷者的心聲
——梅卓散文創作論
高娟娟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梅卓,藏族,1966年出生在青海北部灣的門源縣浩門鎮,祖籍位于青藏高原的伊扎部落。梅卓筆耕不輟,自1987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以來,至今已出版長篇小說《太陽部落》《月亮營地》《神授·魔嶺記》,詩集《梅卓散文詩選》,小說集《人在高處》《麝香之愛》,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樹》《走馬安多》等。游走對梅卓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她的“文學創作源于游走并感動于游走的地方。”[1]317從梅卓的散文作品中,可以直觀地看到作者游歷過程中關注的問題;同時體會到其對藏地鄉親故土的印象和情感。
一、凸顯地域文化
“文化是我們適應所處的環境的重要手段。”[2]受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等的影響,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中華大地擁有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國西部地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黃土高原文化、草原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滇文化等地域文化。“各色的地域文化作為亞文化是中華文化有機整體下的子系統,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的豐富與廣博,在地域文化的絢麗多彩中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多元化的基因。”[3]梅卓沿著自己游走的路線,在散文中不斷地書寫青藏高原文化,挖掘其中蘊藏的價值與意義。
梅卓的散文創作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藏地自然風景、社會歷史、人文風貌等。梅卓在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樹》《走馬安多》等作品中,通過對藏地人物、傳統習俗、寺院建筑等的描寫,展現了獨特的地域文化。作者在多篇散文中描寫文化前輩、教育人才、文物專家等歷史文化名人。梅卓不但講述歷史人物故事,而且還側重深入探索人物生命長河中的奧秘,表現其精神品格。在歷史人物的身上,作者感受到了他們對藏地文化的熱忱,對故土的深情。梅卓歷數了藏地一大批“熱愛民族文化、并且在當地長年默默地為之付出勞動的文化人,如代尕先生、巴扎先生……丹周多杰先生等等”[4]70。在《文化前輩》一文中,許多前輩不為名利羈絆,而是將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到自己真正所熱愛的文化事業中去。其中,布特尕一生熱衷于整理研究格薩爾,即使在特殊年代遭受命運的不公正待遇,他也始終心系自己的工作,沒有因此而放棄。巴扎始終不在乎物質利益的得失,主動收集保護民俗文化,并且致力于教育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音樂代言人》一文中,代尕、扎西達杰、更嘎才旦等人為藏地的音樂事業發展作出了貢獻。《文物專家和教育專家》一文中,“尕瑪圖嘎”和“文索巴德”分別放棄了安逸的生活,執著地為藏地的文物保護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奉獻了一生。《追尋色彩的人》一文中,畫家吾要的創作源泉主要來自故鄉玉樹高原。“可以說,玉樹生活的積淀,民族文化的素養,成就了吾要。”[4]95為了報答故鄉,吾要不斷用畫筆表現高原的一花一草,讓故鄉被更多的人熟悉。多拉繼承了父親的職業,成為了一名唐卡畫師。多拉在親身實踐的同時,也努力培養更多的學生,以自己的所能,弘揚唐卡藝術。多杰卓瑪不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一生鐘情于藝術事業。正是眾文化人用自己的滿腔熱情去守護本土的文化,傳承優秀的文化因子,使得人們認識到當下與歷史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依據歷史與文化,人們能夠不斷地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充實當下的生活。
傳統習俗將歷史中人類社會生活實踐的智慧部分保留了下來。梅卓懷揣責任感與使命感,用散文創作傳承文化血脈。梅卓深入體驗多樣的傳統習俗,深究其來源與演變,品味其特有的寓意。她通過散文展現藏地的婚禮、新年、禁忌等習俗。“高原人個個能歌善舞”“每逢喜慶節日,人們歡聚一起,高歌狂舞,盡興而散,表現了高原人豪邁、樂觀的天性”[4]177。歌舞涉及歷史、宗教、戰爭、勞動、生活、愛情、民俗等多方面,反映了各個時期人民生活的圖景,折射出藏地人民的精神文化。《民間文化鋪就了玉樹的堅實大地》一文中,梅卓詳細介紹了玉樹地區多樣的民間文化。“玉樹舞蹈主要由‘伊’、‘卓’、‘熱巴’、‘熱伊’、‘鍋哇’以及寺院的宗教舞等構成,種類多達400余種,其風格的粗獷豪放,造形的形象傳神,旋律的優美生動,內涵的含蓄雋永,是世界歌舞百花園中一朵絢麗多彩的奇葩。”[4]179賽馬節、女神節、法會等是藏地人民特有的節日。梅卓在散文中生動地再現了藏地的多個節日的盛大場面。民間節日活動的傳承,體現了藏地人民生生不息的活力。
眾多的寺院建筑形成了藏地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梅卓在散文中借助數據、資料等的幫助,細致介紹了多個寺院,如拉卜楞寺、郎木寺、扎如寺、川主寺、甘孜寺、德格印經院、噶陀寺、理塘寺、松贊林寺、大昭寺、布達拉宮、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薩迦寺、昌珠寺、桑耶寺、古如甲寺、改家寺等。作者沒有停留在對寺院的簡單介紹上,而是深入探究建筑特點、追溯歷史流變。受寺院文化的感染,藏地人民擁有博大的胸懷,慈悲的心靈。圣潔的哈達、虔誠的煨桑、真摯的祝福是藏地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此外,作者還梳理了藏地帳篷、古塔等建筑物的發展演變過程。《古格:昔日王城》一文,作者親眼目睹了遺留千年的古格王宮遺址。古格王宮中的繪畫是古人在吸收了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繪畫藝術風格的基礎上,創造出的獨具古格風格的藝術精品。
對梅卓來說,對于民族歷史文化的探索和了解,不僅僅能夠體現出文化傳承變異的動態,也能增加自我生命的厚重。梅卓深入歷史的河流,了解祖輩們的足跡,摸索歷史沉積的過程,刻畫民族性格,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構成。“神話始終是文學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5]梅卓細數神話、傳說、口傳故事等,并且結合現實人生,回望歷史。《〈格薩爾王傳〉的民間資源》一文中,藏地人民非常推崇《格薩爾》。《格薩爾王傳》熔鑄了神話、傳說、歌謠等民間藝術資源,記錄了中世紀藏族社會的歷史縮影,以及藏族人民為爭取美好生活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突顯了藏族人民獨特的心理素質和審美觀念。《格薩爾王傳》在藏地占據著獨特的地位,它帶給后人勇氣、堅強和正義。依循歷史的足跡,梅卓展現出了藏地的文化生活景觀與內在的生命意識。在縱深的歷史感書寫中,讀者能夠更深刻地認識藏地的獨特面貌。
梅卓的散文凸顯了豐富的青藏高原文化。作者寄情于地域風情,在其作品中描繪了多樣的景致。可以說,梅卓的散文沉淀在地域文化之中。藏地所呈現出的地理景觀和人文景觀,帶給了作家不同的生命體驗。梅卓在散文作品中呈現出走過的地方的風景圖畫、人文風俗和歷史變遷等,突出了鮮明的地方色彩,表達對藏文化的熱愛,映射出中華文化的多姿多彩。
二、繪制生態和諧的愿景
“女性歷來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靈更適合于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6]梅卓在散文的書寫中,善于從女性自身的角度來觀察大自然;并且充分利用女性自身的感受力,感知大自然的生命力,從而體現出個性鮮明的自然觀。作者對大自然的書寫不是簡單地描摹自然風景,而是更多地注入對大自然的美學觀照。
草原、雄鷹、雪山、河流等相互依存,構成了和諧美麗的生態圖畫。梅卓反復吟詠藏地的神山和圣湖,在她的筆下,山有山的故事,水有水的故事。作者描繪了朵覺吾神山、江朵識神山、格吉神山、總炸內加瑪、色季山、本藏、瓊藏、沙藏等著名的神山;同時,形象地寫出了隱藏在神山背后的傳奇故事。《巴顏喀拉:巴玉和查拉》一文講述了巴顏喀拉山下發生的愛情悲劇故事。藏地人民與“眾多神山間的人格化的交流,是生命信息互動的交流”[4]263。他們之間是彼此生命的守護者與見證者。“生命在本質上是共生的”[7],只有加強個體生命之間的聯系,才能創建良好的生態系統,和諧發展,彼此受益。梅卓在散文中強調尊重個體生命的差異性,強化相互之間的聯系。《尕朵覺吾神山》一文,作者生動地講述了在尕朵覺吾神山的哺育下,一年四季各個個體生命茁壯成長的畫面。“尕朵覺吾的山溝和山腰生長著茂密蔥郁的灌木林,棲息著白唇鹿、馬鹿、藏羚羊、巖羊、雪豹、猞猁、黑頸鶴、雪雞和麝香鹿等珍稀動物。山上還生長著雪蓮、雪茶、雪滴石、紅景天、貝母、冬蟲夏草等罕見的高原珍貴植物。另外還有白花檉柳、黃檉柳、柏樹、蘇木、高山柳等樹種,每當暖季來臨,這些植物就為神圣的尕朵覺吾換上了春意盎然的綠裝。”[4]30山水相依,每個生命個體互相成就,彼此共同發展。
藏地人民與動物之間建立了深情厚誼。“草原上的每只牧狗都有名字,形象兇猛的會稱為雄獅,毛色潔白的會稱為海螺,人們賦予牧狗以吉祥的名號,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1]14《在青海,在茫拉河上游》一文中,梅卓敘述了牧人與牧狗互相陪伴的溫馨場景。牧狗不僅能夠幫助牧民看家護院,還能在放牧時看守牛羊。牧民家庭早已將牧狗視為家庭的一員,會為它按時準備每頓飯菜。藏族人民對馬的喜愛滲透在生活中的許多方面。馬不僅是他們的伙伴,也是他們學習的對象。對于藏族人民而言,“馬是一種象征,象征著速度、勇氣、力量,駿馬暢美的線條,流風的速度,可貴的尊嚴,忠誠的品德,威風凜凜的勇氣,威懾邪惡的力量”[4]168;而這些都是藏族人道德觀、價值觀中引以為豪的品質。“敬畏生命的倫理否認高級和低級的、富有價值和缺少價值的生命之間的區分。”[8]唯有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才能在天地之間奏響和諧的生命交響曲。
梅卓通過表現自然生態環境中的各個個體生命之間的有機聯系,更深層次映射出了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希冀。大自然為藏地人民帶來了豐富的生存資源,其中包括太陽能資源、礦產資源、水利資源以及各種珍貴的藥材等。然而,反觀人類自身的行為,梅卓對生態系統的長期穩定發展表示了一定的擔憂。《可可西里——野生動物的天堂》一文中,作者敘述了藏羚羊被非法獵捕,許多動物的生存面臨嚴峻的挑戰。梅卓揭開人類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罪惡行為,反省主體生命所應該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她在散文創作中批判反思人類的行為,從而折射出作家內心深處對人類的持續發展,以及對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的深切關心。
馬克思曾說:“人從屬于自然界當中,并且依賴于自己所身處的自然環境以及與這個環境所共同演進發展。”[9]自然界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根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只有樹立正確的生態文明觀,堅持正確的發展理念,才能促進生態安全與人類健康的有機統一。梅卓在散文中書寫生態和諧的一面,同時也呈現人對自然施暴的一面。作者為雪山消失和珍稀動物滅絕而痛心,她始終希望人類能夠努力繪制一幅美麗的生態圖景。
三、關注女性生存狀況
梅卓敏銳地覺察到了藏地女性同胞的生存困境,走進她們的生活,著力描寫藏地女性的真實生活情狀。她對牧區婦女、尼姑等邊緣人物的生存狀態尤其投以關愛的目光。不僅關注藏地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點滴,還重視她們的內心世界。
梅卓揭開長期以來覆蓋在牧區婦女、尼姑等女性身上的神秘面紗,描述她們的現實生存環境以及精神世界。《阿壩的方向》一文中,作者敘述了牧區婦女生命的軌跡。“實際上,草原上的牧女們非常辛苦,家庭的日常生活完全落在婦女的肩上,女孩從六七歲開始,就隨著母親開始勞作了,一生都在單調而繁重的勞動中度過了,可謂是家庭的脊梁。”[1]89作者在散文中一方面表達了對藏地牧區婦女的同情與理解;另一方面也對她們身上勤勞的品質表示由衷的敬佩。面對生存的考驗,牧區婦女用自己的行動去戰勝磨難,承擔自己的責任,證明自己的價值與意義。雖然由于自身經濟地位等因素的制約,藏地女性的生存面臨著各種困難,但她們在瑣碎的生活細節中維護生命的尊嚴。即使無人觀賞,婦女也會梳洗、整理自己的外表儀容,用首飾裝點自己飽經滄桑的身軀。梅卓在《美麗丹巴》一文中介紹了丹巴婦女的頭帕、常服、禮服。在丹巴地區,頭帕和服飾有各種各樣的講究,不同的場合需要呈現不同的面貌。每逢節日,丹巴婦女遵循傳統禮儀,盛裝出席。在歌聲和舞蹈中,能夠看到丹巴婦女對生活的重視和熱愛。對于生活在高原的婦女來說,即使生活艱苦平凡,但也不放棄生命的尊嚴。樂觀向上的她們感恩生命的存在,竭盡全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與意義。
梅卓沒有肆意吹噓藏地尼姑的傳奇人生,而是用平實的語言敘述她們對生命的態度。《求法的寺院和朝佛的尼姑》一文中,作者記敘了自己在路途中遇見的尼姑的情狀。來自色達的四十多歲的尼姑“三木讓”與十七八歲的外甥女要去西藏。“三木讓”的姐姐婚姻不幸,常年忍受丈夫的折磨,如今病入膏肓,扔下了女兒。“三木讓”與外甥女一起跋山涉水,走在朝圣的路上,替姐姐實現還沒有完成的愿望。梅卓為她們的故事而動容難過,久久不能釋懷。一方面,作者并沒有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過多地發表自己對這些女性的看法。另一方面,梅卓與她們站在一起,理解她們的遭遇與不堪的生活,為她們的難過而難過;同時也尊重她們頑強的掙扎。《蛇月法會與改加寺的尼姑們》一文中,作者敘述了尼姑們自身的悲慘遭遇以及艱苦的生活情景。雖然很多尼姑的現實命運充滿了荊棘,但是她們的精神面貌卻是另一番模樣。她們“在其極惡劣的生存條件下,仍然能夠擁有進取心和慈悲心”[10]。尼姑們積極克服困難,努力地活著。同時,她們也對天地間的生命充滿了關心,真誠祝福每個生命個體。
惡劣的生存環境并沒有磨滅藏地女性的意志,使得她們失去對生活的希望。她們擁抱生活,重視生命的尊嚴。梅卓真實地表現了藏地女性主體生命在苦難面前,積極煥發出潛藏在生命中的力量,不斷與苦難作斗爭,贏得生命的尊嚴。
四、結 語
總之,在梅卓對藏地的自然山水、風土人情、人文景觀等進行的知識化梳理與闡釋中,蘊含著自我主體性的感受。讀者一方面能夠從梅卓的散文中了解藏地的文化風貌;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作者心中對傳承與弘揚藏地優秀文化的那份渴望。梅卓的散文創作透露出作者在游走過程中汲取的鄉親故土帶來的經驗、智慧與尊嚴。游歷區別于旅游,更加注重途中的心靈體悟,更加側重過程而非享受。閱讀梅卓的散文能夠發現,作者傾心諦聽自己在游走過程中遇見的事物;同時她也在深入思考附著在那些人與物身上的厚重的生命故事。作為藏地兒女的一份子,梅卓堅持用創作回饋鄉親故土。“游走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感動。”[1]317梅卓懷著一顆熾熱的心游走在路上,收獲了滿滿的感動。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樹》《走馬安多》是作者在游走過程中對地域文化、生態環境以及女性現實生存思考的產物。她平靜地敘述自己的見聞,流露出內心深處的真情。她擁抱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關心生態環境和女性生存。閱讀梅卓的散文,讀者能夠跟隨作者的路線,體驗其筆下不同的文化風采,感受其帶來的生命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