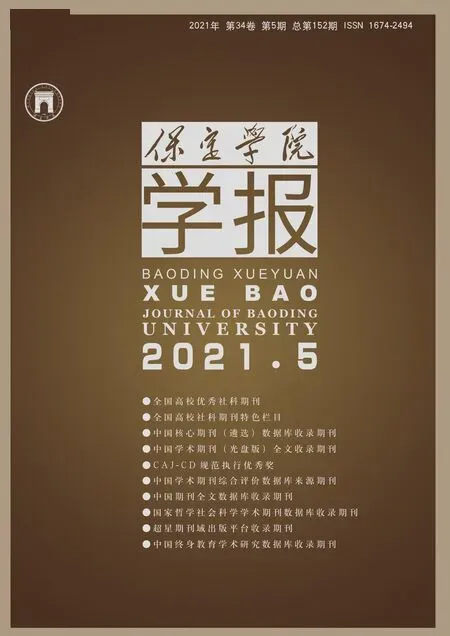道德主體的建構:孔子自識思想的闡釋
王開元
(河北大學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自識是西方哲學所著重關注的一個課題,在中國哲學中,關于自身的認識同樣被賦予了重要的意義,而考察孔子自識思想的價值即在于理解傳統哲學是如何實現對人自身的認知與建構的。勞思光認為:“‘自我問題’本為哲學之基本問題,亦是一理論性極高之問題。孔子時,中國哲學理論尚未充足發展,故孔子對此問題之見解,實遠不如稍后出現之各家學說能確立其論證。但孔子對此問題之態度,仍在《論語》中作相當程度之流露。”[1]110勞思光對孔子思想的看法是準確的,孔子也并未明確對自識問題進行理論上的建構,有關此問題的研究也缺乏一種對于建構路徑的思考,但這并不意味著孔子思想中缺乏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今天重思孔子的自識思想,即是尋求一種現代性的視角來重新解讀孔子對自身的理解,這一方面是為了揭示出孔子思想中有關自身認識的理念,使我們有一個新的視角來重新思考孔子思想的理論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借此來展現孔子是如何對道德主體進行建構的。因此,本文將從以下幾點來展開論述:首先,對孔子自識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加以闡釋,明確孔子對于自身的認知傾向;其次,借由對人自身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闡明孔子是如何對自身進行理解與建構的;最后,對孔子有關自身理解的問題進行總結,并試圖挖掘這一理解的意義所在。
一、“己”的概念與主體的彰顯
孔子曾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而子貢則認為孔子的謙辭乃是“夫子自道也”。無論是否謙辭,孔子都表現出對自己的一種認知,而這種對自身的認知具有原初的道德推動力。自我認知往往是作為哲學的本源問題出現的,決定著對他人與外物的認知,進而影響著人自身如何與他人及世界相處的模式。故而,可以說對自身的認知具有本體論上的優先性①福柯認為:“自我關注具有倫理上的優先性,因為與自身的關系具有本體論上的優先性。”(參見福柯《自我技術:福柯文選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頁)。對自身的認知不同于對外物的認知,自識所涉及的更多的是一種自我關系,即自身與自身的關系,是自我如何反思到自身并與自身相處的問題。孔子對自身的認知,即有著這一面向的理論內涵。在孔子思想中,自身被視為是一個可成就的人,而非被客觀認識的對象,“我”正是在他人與世界中才得以成就自我,這也是我們所說的“成己”的意義②關于孔子思想中的自身的定位問題,筆者在《知己與成己——試論孔子思想中的自我認知問題》中論述到,“孔子對自身的設定雖是將自身置于日用常行,但這日用常行并不是與天一分為二的,相反,天即于日用常行中顯示自身,日用常行也即天道,也即理學家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參見王開元《知己與成己——試論孔子思想中的自我認知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自我作為被成就的對象而存在,那么自我認識的任務即在于使自己是其自己或使自己成為自己。換一種說法,知己即成己,認識自己即有著對自身的建構意義。而“己”,作為因反思自我而生成的詞語,正是孔子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作為語言代詞的“己”是一個抽象的反身性的概念,意味著個體被作為他者來看待與反思。這個作為他者的“己”,具有人的一切特征,是一個完整的個體、普遍意義上的存在者。“己”概念的出現意味著人作為一個對象開始被反思,這個被反思的“己”所具有的反身性正喻示了這一反思特性。在孔子那里,作為被反思到的“己”具有大而全的人的一切屬性,這也使得每個人都可以因“己”的存在而能成就自我。
首先,“己”是區別于“我”的存在者。“我”一般是作為自謂詞使用的,故而“我”所指向的常常是具有獨特個性的這一個。《說文解字》曰:“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從戈從。,或說古垂字。一曰古殺字。”段玉裁注曰:“不但云自謂而云施身自謂者,取施與我古為疊韻。施讀施舍之施。謂用己廁于眾中,而自稱則為我也。施者,旗貌也。引申為施舍者,取義于旗流下也。”可見,“我”是處于人群之中的,是廁于眾中者,是在人群中施身自謂之稱。謂“我”,正是要顯示出“我”是獨特的,是一個與別人不同的存在者。《論語》中的“我”大都為孔子自道,可以說是第一人稱代詞。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
子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
上述所謂“我”其實就是孔子本人,是一個有限的存在者,“我”常常意味著具有更多的個性化色彩,表達著主體的個人情感態度或人生感悟。這種個性化有時候會成為一種極端的自我,成為私自的固守。“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其中的“我”就不再是人稱代詞,而是對自以為是的固執之情的描述,“勿我”即是對這種具主觀個人色彩的局限性的反抗。
然而,“己”不同于“我”,“己”是“我”所有并從“我”中剖離出來的。“我”是偏于主觀的存在者;“己”則是一個相對客觀意義的存在者。“我”是唯一的,特指的;“己”則是一個抽象的存在者。當談到“我”時,“我”是一個具有主觀情志的個體自身,“我”具有鮮明的個體性與情感特征;當談到“己”時,“己”是被審視的,此刻是一個被作為他者的存在者。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
“為己”之“己”,并沒有一個特定的對象,它可以指涉任何一個人,但作為反身詞終究是指涉學者(行為者)自己。故而,當孔子言“己”之時,其實是包含了對行為者的認識的。其實,“己”的象征意義大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實際意義,因為“己”的出現意味著自我成為一個反思的對象被意識到,意味著人對自身有了自覺的意識與認識的祈向。
其次,“己”常被作為他人的對立者出現,故有人己之分。《論語》中多有人己對舉的條目,以突出“己”的地位與價值意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憲問》)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
“己”作為一個與“人”(他人)相對的概念出現,并不是說己與人是完全對立的個體,恰恰相反,這顯示出己與人是不能割裂開來的,正是在他人中才顯示出“己”的重要性。因此,人己之分的價值不在于將自己與他人相隔開,而在于使得自己于他人中顯示出自身的價值。“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自己的價值在行仁之時最能夠顯露,為仁由己,正說明“己”的重要性,孔子這里對“己”的價值的肯定透露出的也正是對人的自覺與人的價值的肯定。但是行仁之“己”又不能隔絕他人,因為仁者必須有一個關心他人的指向,也正如孔子所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憲問》)。故而,一方面“己”區別于“人”,在與他人的相判別中獲得自身的自覺;另一方面,“己”又不離于“人”,在成就自身價值時總是經由對他人的關心而歸于仁。
“己”在與“我”的相區別中獲得了普遍意義,又在與“人”的對立中獲得了獨立意義,因此可以說“己”本身是一種人對自身的自覺與認識,它是從具體中抽象出來的個體,是一個具有人的普遍屬性的個體。因為具有這種反思性的“己”,自我也就有了成為自己或成就自己的根據,因為“己”使得個體具有了普遍的認識能力,具有普遍的知、情、意等人類能力,成為一個能知與能動的主體,從而能夠依靠自身的能力實現對自身的理解與建構。
自身居于世間生活中的定位構筑起某種認知情境,成為我們實現對自身認知的外在基礎;普遍意義的“己”使得個體具有普遍的內在人性能力,使認知者有足夠的認知力去實現對自身的理解與建構。而在這一活動之中,個體的直覺力與判斷力便是兩個關鍵的認識能力,這使得自我意識向自我認識的轉變得以可能,也使得孔子對自身的認知建構得以有效完成。
二、自我意識與德性的獲得
自我意識是將一些相關的行為看作是“我”的,即可以說是對自身活動(意識活動或行為活動)的“意識到”,其所依賴的是人自身所具有的直覺力。直覺是和自我意識相伴而生,自我意識的發生有賴于我們自身的直覺力,而面向自身的直覺也可以說是自我們對自身的“意識到”。在胡塞爾那里,自身意識“已經偏離開它的日常語義,不再具有‘自我感覺’或‘自信’的含義,而是被用來標識意識行為的一個本質特征:對自身的‘意識到’”[2]432。自我意識,可以說是超出意識之上對自己意識或心靈活動的直覺與把握,但這種把握在胡塞爾看來又不同于“反思”。胡塞爾將自身意識與反思區別開來,認為“‘反思’是在直向的意識行為進行之后而進行的第二個意識轉向自身的行為;而‘自身意識’不是一個行為,而是伴隨著每一個意向行為的內部因素,意識通過這個因素而非對象地(非把握性地)意識到自身”[2]432。關于這種不同,康德也曾從經驗和純粹兩方面對自我意識加以區分,當他“談及經驗地、后天的、但貫穿地伴隨著所有表象的自我意識時,他所指的是經驗的自我意識;而當他強調自我意識可以不為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隨時,他已經涉及到純粹的自我意識了”[2]167。實際上,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或者說在儒家思想中,對意識活動的純粹的自我意識并沒有獲得足夠的發展,當我們以自我意識去探求儒家思想時,這種意識更多的是一種經驗性的,是對自身內部意識的一種內感知。這種經驗性的自我意識所面向的是對象性的,是意識的內容,而非意識的純粹形式。這種自我意識在認識過程中,表現出對感性經驗的超越,是自身復歸到自我本身,也是實現自我理性認識的必然途徑。
孔子在對自身的認識上,并不是從純粹理智層面來理解分析自身的,我們從孔子對自身的定位中可以合理地推出,孔子對自身的認知絕不是靜態的反思與觀照,而是在感性生活基礎上的體認與覺知。孔子曾自述道: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
“志”與從心所欲等即一種對自我內在意識的把握,這種關于心的把握首先便是有著現實的情境作為基礎的,其次則是面向心之現象的自我意識,是對內心意識活動的感知。另外,《論語》中記載孔子做夢的事情: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孔子對自身的這種認知是基于感性生活的,又有著理性的判斷,是以自己的夢境體驗來對自身所作的認知。夢可以說是一種意識體驗,而對夢的回憶則是對這一意識活動的當下化反思,這也是上文所述經驗性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有著經驗的基礎,它是直覺力作用的結果,而不是認知心所推理得來的。牟宗三曾對其逆覺體證觀念做過分梳,認為逆覺體證分為兩種:“‘內在的體證’者,言即就現實生活中良心發見處直下體證而肯認之為體之謂也。不必隔絕現實生活,單在靜中閉關以求之。此所謂‘當下即是’是也。李延平之靜坐以觀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氣象為如何,此亦是逆覺也。但此逆覺,吾名曰‘超越的體證’。‘超越’者閉關(‘先王以至日閉關’之閉關)靜坐之謂也。此則須與現實生活暫隔一下。”[3]494牟宗三所謂逆覺體證或為一種工夫,然而若就對自身的認知而言,我們并不認為與現實生活隔絕的“超越的體證”是一種達成自身認知的有效方法。靜坐反思,或可以是一種省察,當靜坐是為了省察時,我們可以與自我的生活經驗相接,并借由身體的靜定實現對自身的覺識體知;然而如果這種反思的對象是與世間生活相隔絕的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則對于我們的自我認識未必有太多助益。靜坐,也不應是一味回轉的,雖是與現實生活暫隔,但不應在心意上與世間相隔離,而是借由靜坐本身實現對宇宙天道的體覺。然而至少在孔子,對自身的認識并非是由靜坐反思而得來的,而是在現實生活實踐中的身覺體知,是就現實生活中良心發見處的直下體證。這一方面需要主體主動地參與到生活實踐中去加以體驗,另一方面也需要主體發揮心之理性的直覺力去把握內在德性的活動與呈現。故而可以說,這種自識更近于牟宗三所謂內在的體證之路。因此,我們認為,直覺力或自我意識的發生必有賴于個體自身對生活實踐的參與,不存在脫離感性經驗的自我意識。
因此,孔子的自我認識中,直覺的作用即在于對自身所呈現的內在意識或德性的把握。具體而言,當我們自身與外部世界相處時,自我內部的意識便會呈現出來,而自我意識則可以對此加以把握,因而,一方面孔子對自身的設定使得這種直覺不能脫離生活情境本身,另一方面則對自身所呈現的內在意識(德性)加以自覺地把握。德性作為自身合乎天道的品性,正是自己在世間的現實實踐中身覺體知而證得的。但這種證知與確立,除了需要我們上面所說的自身體驗與理智的直覺外,還需要自我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認知判斷力對所感知到的意識或德性加以確證,這是從自身意識到自我認識的轉變依據,也是對德性自我進行有效確立的必要途徑,是從具體上升到普遍的必經之途。孔子把自身視為一個道德的存在,有著認知上的根據,而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指向自身理性的思維能力,只有對自我的理性認知能力有所把握,才能夠深入討論我們對自身的認識是如何確立起來的。
三、自我認識與主體的建立
我們對于自身的德性可以加以確證,這有賴于自身理性直覺的作用;然而,這種直覺仍然屬于自我意識的范疇,它只能告訴我們某種意識或德性是屬于我們自身的,而不能由此推斷出自我即是德性的存在或者說德性是自我之所以是自身的固有本性。道德意識本身常常是不完滿的,這種不完滿性在于這種道德意識與感性經驗還保有“一種肯定的關系”(黑格爾語),這種關系使得道德往往不受理性的制衡而易流于混沌,晚明心學的流弊即是其例。而在孔子思想中,對“天命”的預設使得道德并非僅僅是作為直覺對象的存在,而是有著自身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也使得具有德性的個體實現由自在向自為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正是由理性的判斷力完成的。
判斷力是我們自身一種理性能力,是我們實現由自我意識向自我認識轉變的根據。感性實踐中的道德意識常常是自在的,只有當此道德意識被理性判斷力所關注并成為自身的確定性時,它才成為自為的存在。在“見孺子將入于井”的事例中,惻隱之心的流露表現出一種道德意識的自覺,而只有當我們把這種惻隱之心視為一種自身所固有的本性并加以反思確證之時,自我在道德層面才是一個自為的存在,才能夠將道德加以完滿的證成。孔子謂:
天生德予余,桓魁其如予何!(《論語》)
孔子不僅對于道德有自覺的體認,而且將這種道德視為一種自身的承擔,自身不單純是有著某些德性意識,而是對自己本身的確定性有所體認,這便是基于理性判斷上的自為,是對由自我意識上升的自身認識層面的德性的確定。因此,當我們對自身的良心、意識加以命名時,其實已經有了理性的認知在內,而把這種德性加以超越意義的提升并確立為自身的本性,這是理性在綜合意義上的作用,是理性判斷力對自我意識的超越。關于這種判斷力,謝遐齡依康德思想稱之為“直感判斷力”,這對于我們理解這種自身的確證能力無疑具有啟發意義。所謂“直感判斷力”就是對“心之所同然”之共同感的作用,也即是對我們所說的自身普遍之德性的判斷。可以說,這種“直感判斷力”仍然是以自我意識為基礎的,自我意識使得這種判斷成為可能,但也正如謝遐齡所言,“康德對心之此能力僅關乎美,看得太過狹隘了”[4]30,并引伽達默爾言論,認為“伽達默爾討論鑒賞問題時首先就令人警醒地點出了一個西方思想史上的事實:‘鑒賞概念最早是道德概念,而不是審美概念。鑒賞概念描述一種真正的人性理想。’”通過將直感判斷力引入道德領域,謝遐齡便認為此種能力可以解釋中國儒學的道德理論,并由此否定了牟宗三以康德之“智的直覺”解釋儒學思想的正確性。無疑,謝遐齡對康德“直感判斷力”的解析為我們理解自身對德性的確證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啟發。由此,我們也進一步證實了判斷力在自我認識中的作用,它不僅是對外在知識的學習把握,更主要的是對自身之普遍德性的判斷,并使之成為我們自身價值的源泉,由此實現自我意識向自我認識的轉變。
康德區分了自我意識與自我認識,這一明確性的區分使我們關注到對自身的認識有別于單純的直覺或意識到,倪梁康認為自我意識與自我認識在康德那里已經涇渭分明,認為“前者是自我的顯現的存在,后者是自我的客體的存在。我們還可以說,自我意識只是將一些相關的行為看作是‘我的’,而自身認識則涉及‘什么是我’的問題”[2]170。也就可以說,在孔子對自身理解的思想中,自我意識是對我們自身內部所呈現的德性意識的把握,是將其視為“我的”;而自我認識則是由判斷力對此德性意識加以確證,從而將道德視為自身的確定性或本性,從而通過判斷解決了“什么是我”這一問題。顯然,在孔子思想中,德性的重要性即在于這種從“什么是我的”到“什么是我”的轉變之中,因為在這種轉變之中,德性或仁性由一種自由的狀態上升為主體的立身依據,從而使主體能夠自覺地依靠理性實現對道德實踐的復歸。“天生德于予”的自信即來自于孔子對自身德性的理性判斷,孔子對于道德的擔當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是意識到德性在“我”之后的自覺實踐。因此,在孔子思想中,德性已經超越了意識的范疇,經由判斷力而確證為一種理性意義上的自我本性,是自我之所以存在的理性根據與價值根源。
故而我們說,孔子對于自我意識向自我認識的轉變這一問題有著積極的看法,是以理性的判斷力對經驗性自我意識的超越。孔子曾自言自己“無知”: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
孔子對于自己“無知”的認識,一方面是以內在德性對外在知識的合理對抗,另一方面則有著在理性層面對內在德性的肯定,“無知”意味著自身理性的作用存在著由知識向德性的轉變,由外在知識性的學習向內在仁性的超越性肯認。這一點從孟子那里也可以更好地得見,孟子在對人性的認識問題上,以為惻隱之心等是人所固有的本性,孟子的論證并非是邏輯的推證,而是以自身的理性對直覺到的意識內容直下肯定,“見孺子將入于井”時的惻隱之心表現為自我的意識內容,而對此意識,孟子直接視為人性善的普遍根據,表現出理性的直接判斷力,而不是邏輯推理的作用,這也可以說是康德之“直感判斷力”。孔子雖未直接說明人性的善惡問題,但他把德性視為自身固有的本性。孔子對于自身的判斷以德性為標尺,以為自身即是德性的存在,這便是理性對直覺的超越與肯定。這在孔子對自身生命的反思中表現得較為明顯,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此所謂知天命必不單純是對外在規范的認知,代表著在自我的認知中實現對超越之天命的確信,亦即對于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把握。徐復觀認為,“孔子的所謂天命或天道或天,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出來,實際是指道德的超經驗的性格而言;因為是超經驗的,所以才有其普遍性、永恒性。因為是超經驗的,所以當時只能用傳統的天、天命、天道來加以表征。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正是孔子所說的天、天命、天道的真實內容”[5]79。徐復觀所謂道德的“超經驗的性格”其實就是理性意義上對自我意識或德性的確證,不論這種確證是否具有道德形上學的意義,都不可否認孔子對于自身德性是肯定的,是把具有普遍意義的仁性或德性視為自我擔當的內在根據的。正是在對自我德性不斷地理性確證與判斷中,主體獲得了由自我意識到自我認識的跨越。
當然,之所以說不斷的確證,主要是因為這種理性判斷總是對自我意識的確證,而自我之意識總是基于實踐的,實踐的不斷變化使得我們的理性確證也必須是一種不斷的過程,盡管在純粹意義上它總是指向作為意識的內在德性。如果我們進一步考察我們自身的德性或仁性來源,就會對理性的這種不斷確證有所理解。對于仁性或德性的來源,我們不能脫離生活實踐去考量,基于生活實踐的體驗,社會習俗與人己關系的因素都借由智性思維與感性體驗等知能內化為自身德性的一部分,而理性意義上的確證也只有不斷適應實踐,才能夠對自我意識意義上的德性加以肯定,這一點也同之前我們對實踐維度之意義的論述相一致。因此,理性的確證是一個過程,是基于感性經驗基礎上的對自我之德性的不斷肯定與超越性確證,是自我意識向自我認識轉變的依據,理性的這種判斷力一方面不離于實踐生活的墊基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不斷的確證過程中積極地復歸于實踐,成為個體價值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指導原則。
四、結語
通過對孔子自識思想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在對自身的理解中有著對自身的建構,自我意識向自我認識的轉變體現出自我被建構的涵義,“天生德于予”的自識又顯示出這一自身建構是道德意義上的。首先,在對自身的認識中,對道德意識的直覺是一種經驗性的把握,當這種自我意識上升到自我認識層面之時,自我即被提升為普遍的道德存在。其次,由于我們對自身的認知總是于生活實踐中進行,故而理解自身除了需要認知心的作用外,也還有情感、意志等多方面的因素,這也使得對自我的認知有著修身的工夫論向度。因此,可以說在孔子思想中,對自身的認識內在地蘊含著對道德自我的建構。對道德自我的建構也同時有著兩個方面的內涵:一個是本體論上的建構,使自我在道德上獲得一種普遍意義的存在,自我與普遍之道得以契合相接;另一個是實踐或工夫論層面的建構,自身在實踐中被理解認知,也在自身的修養中獲得認知的最終完成與道德主體的建構。
孔子的自識思想啟示我們要更為積極地去面對道德問題。對自身的認知建構,與對外部世界的建構不同,前者所涉及的是一種自身關系,即自身與自身的關系。這種關系需要自身對自身主體有所自覺,也需要對自身的主觀能力有足夠的關注,正如馮契所言,“認識自己不僅指能知作為主體的自覺,也指人以自己(主體本身)為對象來探究其本質力量——包括人的意識與無意識能力、理性與非理性,也包括人類進行勞動、形成社會關系等等。而且人不僅探究自身的本質力量,同時能動地以天性為基礎來塑造自己的德性,自我由自在而自為的過程,既是作為精神主體(心靈)的自覺,同時又是人的本質力量(天性化為德性)的自證和自由發展”[6]207。人自身正是在這種面向自身的理解中才建構起自身的價值,重思自我也就是重思自我作為人的本質與主觀能力,使自我有一個主體的自覺。只有這種對自身的真切關注,才能尊重自身與他人,也才能使我們在面對自我困境時有所自覺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