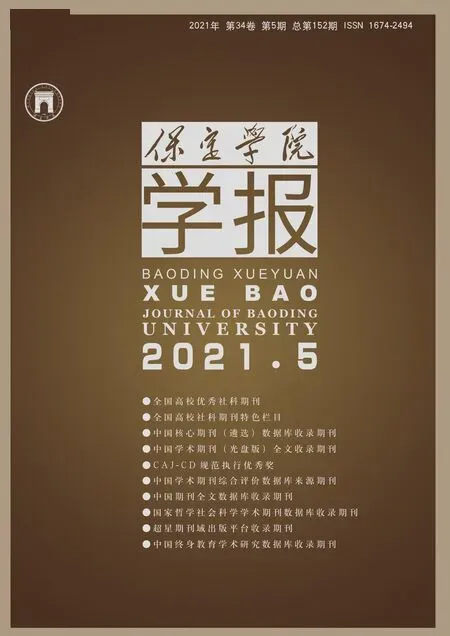“大言炎炎”:《莊子》言說(shuō)態(tài)度試論
于 暢
(山東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山東 濟(jì)南 250100)
“大言炎炎”僅是《莊子》中并不突出的一句話,對(duì)其的解讀也止于字句含義的解釋。“大言炎炎”參考注家解釋,應(yīng)為“大言淡淡”。“大言淡淡”實(shí)際上是《莊子》關(guān)于言說(shuō)的一個(gè)重要層面,即言說(shuō)態(tài)度層面。言說(shuō)態(tài)度不像對(duì)“言”直接論說(shuō)的思想觀念與顯示于文辭的表現(xiàn)形態(tài)那樣顯明易見(jiàn),但可以說(shuō)它是《莊子》之言的一個(gè)具有重要地位的層面,對(duì)于理解《莊子》之言說(shuō)有其獨(dú)特的意義。
一、“大言炎炎”釋義及界定
“大言炎炎”出自《莊子·齊物論》,其文曰:“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陸德明引李軌所注音稱:“李作淡,徒濫反。”[1]57王叔岷《莊子校詮》:“淡、炎正、假字,《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wú)味。’(卷子本《玉篇水部》引口作言)孟郊《荅友人詩(shī)》:‘道語(yǔ)必疏淡。’所謂‘大言淡淡’矣。”[2]49錢(qián)穆《莊子纂箋》引章炳麟:“‘炎’,同‘淡’。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wú)味’也。”[3]11參考以上注解,可證“大言炎炎”之“炎”是“淡”字。
《說(shuō)文》:“淡,薄味也。從水,炎聲。”“淡”由薄味引申出諸多含義,《莊子·應(yīng)帝王》:“汝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wú)容私焉,而天下治矣。”[1]300-301“淡”與“漠”并列,可見(jiàn)“淡”有淡漠的含義,且“游心于淡”可見(jiàn)“淡”與“游”有所關(guān)聯(lián)。《莊子·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1]682此就親友交往關(guān)系而言,是子桑雽答孔子“吾犯此數(shù)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之問(wèn)。由此可知“淡”與“疏”相對(duì)應(yīng),“淡”有疏淡之義。此外,“淡”還有隱約義,例如《列子·湯問(wèn)》:“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shí)其狀。”[4]187-188此處“淡淡”有隱約不清的含義。
《莊子》既有“大言炎炎”,又有“大辯不言”“大道不稱”等主張不言的說(shuō)法。《老子》中有“大音希聲,大象無(wú)形,道隱無(wú)名”的觀點(diǎn),認(rèn)為至大之道超越于有形、有限的聲音、形體以及名稱言語(yǔ),有限的名言無(wú)法完全顯現(xiàn)大道,認(rèn)為“道常無(wú)名”。《老子》主張“不言之教”,認(rèn)為“大辯若訥”,名或言是人為強(qiáng)加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人為的言有違于自然之道。《莊子》的“大辯不言”“大道不稱”與《老子》的這一觀點(diǎn)之間顯示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而《莊子》在主張言之有限的基礎(chǔ)上,對(duì)言作出了更為有針對(duì)性的思考和剖析。與《老子》有所不同的是,《莊子》著重標(biāo)示出言的變動(dòng)不定,言的不可靠導(dǎo)致其對(duì)道的不可呈現(xiàn);而另一方面,言的變幻不居又導(dǎo)向了《莊子》自身言說(shuō)的好為大言、汪洋恣肆。
《莊子》的表述中既推許大言又提倡不言,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嫌,需要對(duì)這似乎矛盾的情況加以辨析。《莊子》關(guān)于言有較多的審視和思量,對(duì)言的直接論述可分為三個(gè)方面。
其一,道與言的關(guān)系。莊子認(rèn)為:“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1]89-90莊子強(qiáng)調(diào)言的未定性,“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人各有其言,變化無(wú)定,所以言不能夠完全地呈現(xiàn)道。
其二,謂言。莊子既否定言與道的統(tǒng)一性,同時(shí)也區(qū)別言與所言對(duì)象的差異,即“謂”的命名客觀上建立了所言對(duì)象之外的一個(gè)言的存在,而非對(duì)應(yīng)所言對(duì)象本身。“天地與我并生,而萬(wàn)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wú)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一本身與“謂之一”的言是不同的,言一出口則有謂,有謂就已經(jīng)偏離了原本所言之物。而謂言在物之外形成了概念的物之“然”,物本身之外有所“謂”之物。“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馬其昶曰:“各有所行以成其道,各謂其物為然,而異己者為不然,皆私也;非真是所在。”[3]15人各有“謂”,于是有彼此不同之謂,有是非之辯言。
其三,辯言。辯言在《莊子》中事實(shí)上為是非的表現(xiàn)形式。莊子認(rèn)為爭(zhēng)辯之言出于分別,求于是非。“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言原本的溝通作用在辯言的“不能相知”中被翻覆向反面,而“辯也者有不見(jiàn)也”在為求顯明是非而“辯之以相示”的時(shí)候,反而執(zhí)其一端,遮蔽了其他可能性。在辯言中,每個(gè)人都自執(zhí)一端,無(wú)處求正。
以上可見(jiàn),莊子對(duì)言主要是持懷疑的態(tài)度,并加以審視和剖析,而稱許“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這些論述都可以劃歸于“不言”之言。可以看出,“不言”之言基本上對(duì)言這一概念與現(xiàn)象加以直接的審視。“不言”之言可以稱為論說(shuō)對(duì)象,此時(shí)的言不是話語(yǔ)口出之言,而是作為一個(gè)與道相關(guān)的言的概念和現(xiàn)象,是探討的對(duì)象。而通過(guò)對(duì)言這一對(duì)象的探討所形成的“不道之道”“不言之辯”的主張,則可認(rèn)為是對(duì)于言的思想觀念。
“大言炎炎”之言在《莊子》中少有直接的述說(shuō),而主要是反映在具體的言說(shuō)之中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一句是對(duì)不同的言的形容,其后是對(duì)人多種不同意態(tài)的形容,既是形容,與“不言”的段落相比可見(jiàn),應(yīng)不屬于對(duì)言的具有哲思的觀點(diǎn),而是對(duì)言的運(yùn)用中的狀態(tài)的表述。簡(jiǎn)言之,這是運(yùn)用中的言。《莊子》所用的言,就如惠子詰難莊子所說(shuō):“今子之言,大而無(wú)用,眾所同去也。”此處指的是莊子自身所用的言說(shuō),它的表現(xiàn)是“大而無(wú)用”,既內(nèi)容豐富,蘊(yùn)含廣博的智慧和無(wú)限的理解空間,且表達(dá)恣肆,具有磅礴的氣勢(shì)與光怪奇異的想象;又疏淡無(wú)為,不措意追求言說(shuō)的用途或接受。莊子在對(duì)“言”持懷疑態(tài)度下的“妄言之”,既包含“不言”的觀點(diǎn),也帶有對(duì)言說(shuō)的自如和自恣的態(tài)度。淡淡大言可以說(shuō)就是這種運(yùn)用在文章之中的言說(shuō)的態(tài)度。“大辯不言”“大道不稱”與“大言炎炎”屬于言的不同層面,“不言”之言屬于所論之對(duì)象,“大言炎炎”之言則歸于所用之言說(shuō),“大辯不言”“大道不稱”等是對(duì)言這一現(xiàn)象的觀點(diǎn),“大言炎炎”是對(duì)言在運(yùn)用中的態(tài)度。而對(duì)言的觀點(diǎn)也影響著言說(shuō)的態(tài)度,莊子對(duì)言的懷疑與反覆傾向使得他對(duì)言不會(huì)特意謀求推行和接受,不專門(mén)追求言說(shuō)的辯論、勸諫、教化作用,不會(huì)非常看重其言說(shuō)的實(shí)用價(jià)值,一定程度上促使生成淡淡大言的言說(shuō)態(tài)度。而與“大言炎炎”相對(duì)的“小言詹詹”則是與有彼此是非的“謂言”“辯言”相聯(lián)系的言說(shuō)態(tài)度,是“大言炎炎”要超越和消解的對(duì)象。
二、《莊子》淡淡大言的言說(shuō)態(tài)度
《莊子》的語(yǔ)言在總體上是可以用“大言淡淡”來(lái)形容的。《莊子》想象光怪,文氣恣肆,從表現(xiàn)形態(tài)看一般不認(rèn)為其淡薄無(wú)味。此處“大言淡淡”所說(shuō)的是一種言說(shuō)態(tài)度,而非表現(xiàn)形態(tài)。“淡淡”主要呈現(xiàn)為三個(gè)方面:“游”的立論態(tài)度、隱約的命題態(tài)度、疏淡的審視態(tài)度。
(一)“游”的立論態(tài)度
《人間世》中有接輿歌的故事,接輿意態(tài)與同樣記有此事的《論語(yǔ)》不同,《論語(yǔ)·微子》中說(shuō)“楚狂接輿歌而過(guò)孔子”,而《莊子·人間世》則是“楚狂接輿游其門(mén)”[1]189。相比較可見(jiàn),《莊子》中的接輿具有“游”的態(tài)度,而《莊子》中的接輿作為莊子的代言,其“游”的言說(shuō)態(tài)度也就是莊子的言說(shuō)態(tài)度。“游”的態(tài)度可歸納為游刃有余之言、游戲筆墨之言、游于無(wú)窮之言三種表現(xiàn)。
言的游刃有余,主要是指《莊子》的語(yǔ)言運(yùn)用流利自如,舉重若輕。一方面,莊子喜歡提出概念,如“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等等。命名諸多概念也體現(xiàn)了莊子對(duì)論述語(yǔ)言清晰而自如的把握。另一方面,在遣詞用句上,《莊子》言辭流麗,毫不拖沓,語(yǔ)言往往輕描淡寫(xiě),在行若無(wú)事中述說(shuō)深?yuàn)W哲理。李世熙在為《南華雪心編》作的序中稱:“夫莊子非有意于為文,而其文之天然入妙者,一若造化自有此靈境。”[5]4如前文所舉例的《人間世》中的“接輿歌”。相對(duì)比可見(jiàn),《莊子》的“接與歌”比《論語(yǔ)》增加了更多的字句,在語(yǔ)言的運(yùn)用上較《論語(yǔ)》更為流衍和優(yōu)美,也蘊(yùn)含了更多的感喟情緒。劉鳳苞評(píng)曰:“以下變調(diào),乃莊子接續(xù)楚狂之歌而長(zhǎng)言永嘆之,化板為活,有崩云裂石之音。”[5]112此是莊子言辭運(yùn)用相對(duì)純熟的表現(xiàn)。再如喻世道之危曰:“游于羿之彀中。”林希逸評(píng):“游彀中數(shù)語(yǔ)極奇絕。”[6]88其比喻往往精切而奇異,又信手拈來(lái)地說(shuō)出,沒(méi)有費(fèi)力措意雕琢的意狀。如講“三籟”時(shí)形容風(fēng)吹山木:“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fēng)。是唯無(wú)作,作則萬(wàn)竅怒呺。而獨(dú)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陸西星稱:“數(shù)句描寫(xiě)竅穴,意態(tài)如畫(huà)。”[7]15其語(yǔ)言傳神盡態(tài)而不流于瑣屑,浩蕩而往,氣勢(shì)磅礴,流麗而不見(jiàn)刻意用力處。
《莊子》在述說(shuō)思想時(shí),常反復(fù)消解,層層遞升,甚至自行否定或懷疑自己之前的言論。這種消解、否定和懷疑又往往是以輕松甚至帶有玩笑意味的態(tài)度說(shuō)出的,顯現(xiàn)出游戲筆墨的效果。郭象稱其“不經(jīng)”“狂言”[1]3,一方面是奇絕光怪的想象與宏大曠遠(yuǎn)的氣勢(shì),另一方面亦與其游戲的態(tài)度不無(wú)關(guān)聯(lián)。游戲筆墨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在立論中體現(xiàn)為不斷質(zhì)疑和消解的言說(shuō)方式。如《齊物論》在對(duì)是非、名言等進(jìn)行一系列析說(shuō)及破除之后,破是非、名言的立論本來(lái)已經(jīng)充分,而莊子卻又反觀自身,對(duì)自己的言作出質(zhì)疑:“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wú)以異矣。”[1]84-85其思維是清醒而冷靜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則是輕松的、游戲般的。在反復(fù)消解、不斷懷疑的思想下,莊子將自己之言定義為妄言,與思想相應(yīng)形成的言說(shuō)態(tài)度是戲言的,輕描淡寫(xiě)而非嚴(yán)肅訓(xùn)教;莊子看待立論的眼光則是清醒冷靜的,甚至可以無(wú)情地對(duì)自己也加以否定,而這否定又是輕輕提出,并不表現(xiàn)出他的冷靜尖銳。林希逸在《莊子鬳齋口義·發(fā)題》所云“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6]1是《莊子》難讀處之一,就與游戲筆墨的鼓舞流衍、變幻不居有關(guān)。莊子以自己的理論為妄言姑言,游戲筆墨的淡然態(tài)度消解了言的權(quán)威性和論斷性,暗示諸子論辯之言,即使是他自己的言,也并非斷言,從而在言說(shuō)態(tài)度上以戲言破除了斷言。
《天下》篇形容莊周之言云:“以謬悠之說(shuō),荒唐之言,無(wú)端崖之辭,時(shí)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jiàn)之也。”林希逸解釋為:“謬悠,虛遠(yuǎn)也;荒唐,曠大而無(wú)極也;無(wú)端崖,無(wú)首無(wú)尾也。”[6]505《莊子》游戲筆墨的態(tài)度體現(xiàn)為荒唐、謬悠,而其文勢(shì)大而遠(yuǎn),則呈現(xiàn)出游于無(wú)窮的意態(tài)。《莊子》常寫(xiě)極大的事物,可謂“好為大言”。例如對(duì)鯤鵬作極盡其大的描寫(xiě):“北冥有魚(yú),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niǎo),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又常常將極大與極小相互轉(zhuǎn)化,如“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這些“大言”,想象毫無(wú)限制,其思入于無(wú)窮。郭象評(píng)價(jià)說(shuō):“其言宏綽,其旨玄妙。”[1]3言的宏大甚至夸張并非出于現(xiàn)實(shí)認(rèn)知,而是一方面出于表達(dá)玄妙之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游于無(wú)窮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形成的立論風(fēng)格。言說(shuō)態(tài)度有時(shí)會(huì)逸出題旨,產(chǎn)生意圖之外的意味。莊子作“大言”并非完全針對(duì)于立論的目的,其目的性和指向性不強(qiáng),就如《逍遙游》中對(duì)藐姑射山神人的形容之辭“大而無(wú)當(dāng),往而不返”,令人感到“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wú)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游于無(wú)窮的大言使得立論的言說(shuō)溢出莊子要表達(dá)的論點(diǎn),甚至模糊立論說(shuō)理的意圖本身,而蘊(yùn)含更多的解讀方向,使其意旨更顯得玄妙難解,包蘊(yùn)無(wú)窮。《莊子》中的許多寓言都有巨大的解讀空間和多樣的闡釋角度,并且本身具有審美意義,而這些對(duì)說(shuō)理并無(wú)直接的用處。申說(shuō)理念固然是其意圖,但莊子并不把自己的言說(shuō)完全指向這意圖,而在其中帶有頗多興趣的意味。游于無(wú)窮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在文學(xué)方面對(duì)后世有廣遠(yuǎn)的影響。例如文言小說(shuō)尤其是志怪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美學(xué)與觀念上追求“審美驚奇”和“非常書(shū)寫(xiě)”,價(jià)值上尋求“游心寓目”的快感,就深受莊子這些謬悠荒唐之言的影響[8]。其背后自然也受到“游”的言說(shuō)態(tài)度的影響。《莊子》“大言淡淡”的態(tài)度,映射在立論的言說(shuō)上,對(duì)“謂言”“辯言”執(zhí)著于彼此、是非的指向性、措意性加以消解。同時(shí)“游”既是立論態(tài)度,也是莊子所標(biāo)舉的體道的境界,“游”的言說(shuō)態(tài)度也是在展示思想層面對(duì)道的體悟。
(二)隱約的命題態(tài)度
《莊子》有“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之語(yǔ),在言說(shuō)命意時(shí)其態(tài)度是隱約而非直言的。正如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序錄》所說(shuō):“然莊生弘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1]5《莊子》中存在著眾多的模糊與爭(zhēng)議之處,較為突出地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命意的隱約,以問(wèn)句代判斷;論題的隱約,以形象代陳述;寓意的隱約,以寓言代說(shuō)理。
命意的隱約,《莊子》常以問(wèn)句代判斷,如《齊物論》南郭子綦回答天籟之問(wèn)說(shuō)“夫吹萬(wàn)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shuí)邪”,不僅沒(méi)有描述所謂天籟的具體狀態(tài),且以問(wèn)句言說(shuō)。“怒者其誰(shuí)邪”既有可能是有“怒者”而未知的疑問(wèn),也有可能是并無(wú)“怒者”的反問(wèn),或自知“怒者”是誰(shuí)而隱含不明言的設(shè)問(wèn)。問(wèn)句本身的非確定性,相比判斷句的結(jié)論固化,與莊子無(wú)待的思想觀念更有一致性。在這多意的問(wèn)句中,天籟的含義變得隱約不清,從而給莊子所懷疑的有限的言帶來(lái)命意的開(kāi)放與自由。“莊子哲學(xué)是開(kāi)放性的批判哲學(xué)。其突出的開(kāi)放性首先表現(xiàn)為視野博大和胸懷寬廣”[9]319。判斷的言說(shuō)是明晰、固化的,有特定的命意之所謂,所以執(zhí)一端而有是非對(duì)待。而莊子的問(wèn)句,命意是不確定的,所“謂”有多種可能,從而消解“謂言”之執(zhí)與“辯言”之爭(zhēng)。言說(shuō)的“謂”被敞開(kāi)了,使得有限的言說(shuō)獲得意義的自由。問(wèn)句客觀上將結(jié)論的權(quán)力讓給讀者,帶有模糊性、可變性,且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促使其意旨變得隱約、多義,成為對(duì)言加以淡化的言說(shuō)態(tài)度的一個(gè)方面。常用問(wèn)句的言說(shuō)很多時(shí)候也與前文論及的“游”的立論態(tài)度有關(guān),帶有興趣和情緒意味的態(tài)度,會(huì)傾向于用更有情感傾向也更輕松的問(wèn)句,而非嚴(yán)肅的判斷,來(lái)對(duì)一些觀點(diǎn)加以言說(shuō)。這一傾向同樣對(duì)言說(shuō)起了隱約化的作用。
論題的隱約,以形象代陳述。例如《齊物論》中有:“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wàn)物一馬也。”[1]71-72并不直接陳說(shuō),而用“指”“馬”這種形象的事物來(lái)言說(shuō)。由此產(chǎn)生了闡釋的多種方向。如有認(rèn)為“指”“馬”是名家的“指物論”“白馬非馬”等名學(xué)的名詞,以消解名言與其所指稱對(duì)象的對(duì)應(yīng)性表達(dá)了對(duì)名言的否定。如楊國(guó)榮認(rèn)為“指”即概念,“非指”則是概念所指稱的對(duì)象。“通過(guò)運(yùn)用概念來(lái)表示概念所指稱的事物與概念本身并不一致,不如直接消除概念本身或不使用概念來(lái)表明以上關(guān)系”[10]。有把“指”釋為手指,“馬”為算籌。《禮記·投壺》載:“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qǐng)為勝者立馬。”孔穎達(dá)疏:“為勝者立馬者,謂取算以為馬,表其勝之?dāng)?shù)也。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xí)武,故云馬也。”[11]317而將“非指”之非理解為非我之指,以彼此是非解釋。如郭象說(shuō):“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于我指獨(dú)為非指矣。”[1]74正因?yàn)榍f子沒(méi)有直接陳述在這一段要說(shuō)的論題,而是選擇了“指”“馬”這樣的形象來(lái)言說(shuō),形象具有的豐富性導(dǎo)向了闡釋的多義性,呈現(xiàn)出不確指、不固定的表達(dá)效果。陳述言說(shuō)是分析的,莊子認(rèn)為“道昭而不道”,分析的明晰會(huì)偏于某一端,不見(jiàn)其余,損害道的完整,也不能夠真正把握和傳達(dá)道。而形象某種程度上消解言說(shuō)的分析傾向,以隱約的表達(dá)包容無(wú)限的意蘊(yùn),其言說(shuō)效果是體會(huì)式的。形象比陳述具有更大的包蘊(yùn)性,能容納更多的含義,如果說(shuō)前文所說(shuō)的開(kāi)放性是言說(shuō)之“放”,形象所帶來(lái)的包蘊(yùn)性則產(chǎn)生言說(shuō)之“收”的效果。
寓意的隱約,以寓言代說(shuō)理。如《養(yǎng)生主》的“薪盡火傳”故事,有生死說(shuō)(郭象、成玄英、林希逸等)、形神說(shuō)(陸西星等)、道說(shuō)(錢(qián)穆等)、個(gè)體生命與宇宙大化說(shuō)(李存山等)[12]111等。再如《齊物論》“堯欲伐三國(guó)”故事中所用的“十日”比喻:“昔者十日并出,萬(wàn)物皆照,而況德之進(jìn)乎日者乎!”有認(rèn)為是肯定十日,十日喻德之無(wú)為而無(wú)不在,照之以天,則德被天下,如司馬彪、林希逸、陸西星等。有認(rèn)為否定十日,十日指有為之害,有意有為地去向他人推行自己的德反而是有害的,如郭象、成玄英、郭嵩燾等。在諸子文學(xué)中,寓言并非《莊子》所獨(dú)有,但莊子對(duì)寓言的態(tài)度卻與其他諸子不同。其他諸子也有常用寓言故事的,但多是將寓言作為說(shuō)理的輔助。寓言并不是他們的主體或核心內(nèi)容,而是表達(dá)道理、提升文風(fēng)、益于理解的道具。在寓言的前后一般還是要說(shuō)理的。簡(jiǎn)言之,是以寓言助說(shuō)理。《莊子》則不然。在《莊子》中,寓言占據(jù)了絕大多數(shù)的篇幅,且很多時(shí)候寓言是不依附說(shuō)理而獨(dú)立存在的,很多篇章甚至是一個(gè)個(gè)寓言的連綴。在寓言的前后,多不再另外說(shuō)理。可以說(shuō),某種程度上《莊子》說(shuō)的不是用寓言作工具輔助的理,說(shuō)的就是寓言,可稱為以寓言代說(shuō)理。而寓言這種言說(shuō)形式,正是由隱約的言說(shuō)態(tài)度所選擇的。有所言就會(huì)有落實(shí)的意旨,一旦言說(shuō)落實(shí)就不再具有無(wú)限的命意方向和內(nèi)涵,也就無(wú)法接近于道。寓言的虛構(gòu)性以虛言消解有言之實(shí),以寓言代說(shuō)理使得言說(shuō)態(tài)度傾向虛靈,既近于道的存在與體會(huì)狀態(tài),也是出于莊子尚虛的審美傾向。莊子對(duì)語(yǔ)言的運(yùn)用既游刃有余,隱約就不是客觀的力有不及,而應(yīng)該是主觀態(tài)度的點(diǎn)到為止,體現(xiàn)了言說(shuō)態(tài)度隱約的偏好。莊子出于“言未始有常”的言說(shuō)觀念,以及消解、否定的思維方式等原因,傾向于制造言說(shuō)的模糊,將言說(shuō)導(dǎo)向“無(wú)常”,包含無(wú)限的變化與可能,偏尚虛靈縹緲的言說(shuō)狀態(tài)與言說(shuō)意趣。莊子令他的言說(shuō)“曼衍”而“廣”,實(shí)現(xiàn)“對(duì)‘言’不盡‘意’的一種反向利用”[9]313。莊子認(rèn)為“圣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相示的言說(shuō)因彰顯而偏頗。莊子以“懷”的隱約態(tài)度進(jìn)行言說(shuō),擺脫“謂言”“辯言”對(duì)言說(shuō)的制約固化,以期用隱約之大言更好地傳達(dá)出大道。
(三)疏淡的審視態(tài)度
莊子常常將所觀對(duì)象向外推卻疏離,以站在事物之外的視角看待世間的各種問(wèn)題,以“冷眼”觀世,其審視世事的態(tài)度是疏淡的。疏淡的審視態(tài)度可分為三個(gè)層面:外物、外我、外言。
一是外物。《大宗師》有女偊對(duì)南伯子葵講“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的過(guò)程,先是達(dá)到“外天下”而后“外物”而后“外生”等等。物在《莊子》中是一個(gè)包含比較寬泛的概念,動(dòng)植物、人都屬于物。《人間世》中櫟社樹(shù)對(duì)匠石說(shuō):“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將人與樹(shù)都視為物,本身就是脫離人自身的疏淡的審視角度。外物的態(tài)度采取超脫事物之外的視角對(duì)事物進(jìn)行審視,站到旁觀、遠(yuǎn)觀立場(chǎng)上加以言說(shuō)。莊子往往取是非兩端之外的角度,例如論是非時(shí)莊子舉出民與濕寢、民與猿猴木處對(duì)正處的不同觀點(diǎn),民、麋鹿、蝍蛆、鴟鴉對(duì)正味的不同觀點(diǎn),人與魚(yú)鳥(niǎo)對(duì)正色的不同觀點(diǎn),得出結(jié)論“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這一論證過(guò)程是站在人類與動(dòng)物物種之外的視角,論說(shuō)不同個(gè)體各有其是非。外物的態(tài)度下,莊子往往不為世間成見(jiàn)所囿,而疏離于表相,以懷疑的眼光從旁觀的角度加以審視。例如櫟社樹(shù)所說(shuō):“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邪?”表達(dá)了對(duì)“文木”所代指的追求有用的成見(jiàn)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的反駁。在外物的視角下,是非差異只是同樣的執(zhí)于一端,評(píng)價(jià)對(duì)錯(cuò)好壞的標(biāo)準(zhǔn)也并非固定不變,“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莊子對(duì)事物采取疏離的視角,在差異與變化的基礎(chǔ)上歸于同一,對(duì)世物則傾向于脫離人世的束縛和傷害,自由無(wú)待。《莊子》有多處“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塵垢之外”的言說(shuō),所處之世的人命危淺和道術(shù)相裂,促使其對(duì)人世持疏淡外離的態(tài)度:對(duì)危難的生存境遇,希望到這境遇之外的“無(wú)何有之鄉(xiāng)”“廣莫之野”,從而脫離危害和困苦;對(duì)爭(zhēng)執(zhí)的道術(shù)境遇,認(rèn)為可以“天鈞”“兩行”“道通為一”。泉涸時(shí)魚(yú)之間的相濡以沫,一方面是艱難生存的危世使然,一方面是社會(huì)性價(jià)值所褒揚(yáng)的道德,而向外一步再看,則“不如相忘于江湖”,危世生存不如保有安寧自在的生命,稱揚(yáng)所是不如忘是非、無(wú)是非。無(wú)論所看待的事物、習(xí)見(jiàn)常理等社會(huì)性價(jià)值還是所處時(shí)代的境遇,都被莊子視為欲“外”之“物”而以疏淡的態(tài)度加以審視。
二是外我。“無(wú)己”是《莊子》的重要觀點(diǎn),在言說(shuō)態(tài)度上體現(xiàn)為外我。自身的主張和立場(chǎng)一般是言說(shuō)固有的,莊子卻往往舍棄甚至否定自身,用外我以至無(wú)我的態(tài)度進(jìn)行言說(shuō)。莊子對(duì)“我”有冷靜的審視,認(rèn)為“非彼無(wú)我,非我無(wú)所取”“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與“彼”相對(duì)而生,由彼我之分產(chǎn)生不同是非的觀念。姚鼐解釋“吾喪我”說(shuō):“一除我見(jiàn),則物無(wú)不齊。”[3]9“我見(jiàn)”是言說(shuō)產(chǎn)生偏見(jiàn)的重要原因。莊子在言說(shuō)態(tài)度上也持“吾喪我”的態(tài)度,往往跳出自身的觀點(diǎn),從外我的角度審視問(wèn)題。如談夢(mèng)時(shí),從“夢(mèng)飲酒者,旦而哭泣;夢(mèng)哭泣者,旦而田獵”開(kāi)始,顯示夢(mèng)覺(jué)之間的直觀差異,“方其夢(mèng)也,不知其夢(mèng)也”是從夢(mèng)中而言,夢(mèng)中的狀態(tài)是自我觀點(diǎn)固守而不自覺(jué)的;再到“且有大覺(jué)而后知此大夢(mèng)也”提出大覺(jué),則由固我中脫離一步,有所審視,“而愚者自以為覺(jué),竊竊然知之”是說(shuō)有假覺(jué),則對(duì)這審視又生質(zhì)疑與審視。論說(shuō)層層向外衍伸,由夢(mèng)至覺(jué),已是站在夢(mèng)外來(lái)審視夢(mèng),而又對(duì)所謂覺(jué)產(chǎn)生懷疑,又有假覺(jué),是再到覺(jué)外審視覺(jué),又將“我”更加疏離。在論夢(mèng)與覺(jué)之后,指出“丘也與女,皆夢(mèng)也”。這是站在丘、女兩個(gè)人之外的立場(chǎng)上講的,丘與女都是身處大夢(mèng)之中而未覺(jué)。更向外一步,又說(shuō)“予謂女夢(mèng),亦夢(mèng)也”,“我”說(shuō)你是在夢(mèng)中,從知而言,“我”也是自以為知,實(shí)則也是愚者;從言而論,“我”既有“謂”,言的判斷一出口就是進(jìn)入是非之中執(zhí)其一端,便是也在夢(mèng)中。此時(shí)的角度是站在自身與他人之外,甚至對(duì)自己之前的判斷也加以否定和超脫,是以更疏離的立場(chǎng)加以審視。夢(mèng)、覺(jué)、大覺(jué)、假覺(jué)、丘與女、予謂女夢(mèng)是對(duì)“我”的認(rèn)知外之又外、疏之又疏的言說(shuō)過(guò)程。在言說(shuō)觀點(diǎn)時(shí),漸次地從“我”的視角疏遠(yuǎn)出來(lái),不斷以“外我”來(lái)謹(jǐn)慎地審視事物,從更廣大的視域看待世事。而對(duì)“我”本身的形體存在,莊子也持“外我”的態(tài)度,對(duì)形體的殘缺認(rèn)為“物視其所一而不見(jiàn)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對(duì)自身的利害生死也不以為意,“死生無(wú)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外我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對(duì)觀點(diǎn)的自我立場(chǎng)和形體的自我存在,都持疏遠(yuǎn)外置的態(tài)度。
三是外言。言是“未始有常”的,莊子既對(duì)有局限的言有所懷疑和審慎,在言的運(yùn)用上則很大程度地發(fā)揮了言的變化不居,甚至常有自己否定前文所言的表達(dá)方式。如《齊物論》有:“嚙缺問(wèn)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wú)知邪?’曰:‘吾惡乎知之!’”[1]96-97對(duì)提問(wèn)皆以不知回答,從言說(shuō)層面看是對(duì)言的疏離,棄置言背后的知的重要性,淡化言的判斷作用。“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可將“物之所同是”作為一部分,解作是否知道物都同樣是自是非彼的,也可作“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是否知道物的同一,可以說(shuō)都是對(duì)是否知道物之道通為一的問(wèn)題。前文已論述物各自有其是非故通為一,卻又以不知答之,而下一問(wèn)答更是對(duì)“不知”的不知,再是對(duì)物是否無(wú)知的不知。以“外言”的態(tài)度進(jìn)行言說(shuō),對(duì)言懷疑的審視使言不具備舉足輕重的地位,消解其固定性。言本身成為可以反復(fù)否定和超越的存在,在層層否定中梯級(jí)遞升。莊子不把言視作具有德、功價(jià)值的“立言”、有判斷意義的“謂言”“辯言”,認(rèn)為言有局限,不能完全表達(dá)出道的含義,對(duì)言的觀念是“不言”,而在言的運(yùn)用中態(tài)度是“外言”。理念上認(rèn)為“不言”,但在言的運(yùn)用時(shí)并不能真的沒(méi)有言說(shuō),且莊子可能不是認(rèn)為一定不能有言,而是不執(zhí)著于言,持疏淡的態(tài)度,在言之外進(jìn)行言說(shuō),有言而忘言。
三、言說(shuō)態(tài)度與表現(xiàn)形態(tài)
《莊子》對(duì)言的思想觀念與言說(shuō)態(tài)度分屬于其“言”的不同層面,淡淡大言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在《莊子》的言說(shuō)中具有重要地位,包含“游”的立論態(tài)度、隱約的命題態(tài)度、疏淡的審視態(tài)度三方面。與言說(shuō)態(tài)度不同,《莊子》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是汪洋恣肆的,淡淡大言的言說(shuō)態(tài)度與汪洋恣肆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是什么關(guān)系,對(duì)言的思想理念與二者又是什么關(guān)系,這些問(wèn)題都需要加以探究。
前輩學(xué)者諸多研究成果中有許多是以《莊子》的某某態(tài)度為題的,如政治態(tài)度、人生態(tài)度、審美態(tài)度等,這些態(tài)度與本文所希望探究的“言說(shuō)態(tài)度”不屬于同一個(gè)層面,應(yīng)歸于思想觀念范疇①對(duì)與本文所要探究的《莊子》言說(shuō)態(tài)度類似的概念和角度進(jìn)行研究的成果很少。張梅《〈莊子〉的語(yǔ)言藝術(shù)——卮言——從莊子的立言態(tài)度與立言方式談起》(《先秦兩漢文學(xué)論集》2004年6月)一文認(rèn)為,《莊子》具有不強(qiáng)立是非、姑且言之的立言態(tài)度與不從正面立論、以文為戲的立言方式,立言方式即卮言,并提到此立言方式體現(xiàn)了這一立言態(tài)度。但這篇論文的主體是卮言,而不是立言態(tài)度及其與立言方式的關(guān)系,也就自然沒(méi)有對(duì)此的更多論析,且所說(shuō)的立言態(tài)度與本文要探討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定義、范疇、思路等都不同。李明珠《莊子簡(jiǎn)省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美韻及啟示》(《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學(xué)報(bào)》2010年第4期)是以“簡(jiǎn)省”為主題的,所以也基本沒(méi)有關(guān)于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界定或與其他概念界分的論述,且其中創(chuàng)作態(tài)度與創(chuàng)作藝術(shù)并沒(méi)有區(qū)分論述。。從思想觀念層面看待言,是對(duì)言的態(tài)度,而非言說(shuō)過(guò)程中自身采用的言說(shuō)態(tài)度。涂光社《〈莊子〉心解》有一節(jié)論述《莊子》論“言”和用“言”,論“言”主要是“言”“意”之辨的討論,用“言”則是寓言、重言、卮言的運(yùn)用[9]315。對(duì)言的“論”與“用”分別開(kāi)來(lái)進(jìn)行論述的思路,對(duì)于本文劃分言的思想觀念和言說(shuō)態(tài)度有借鑒意義。對(duì)言的思想觀念是關(guān)于言的理論觀點(diǎn),言說(shuō)態(tài)度則存在于言的運(yùn)用過(guò)程。《莊子》對(duì)言的思想觀念催生并影響其言說(shuō)態(tài)度,這一方面在前文已有論述,另一方面言說(shuō)態(tài)度又并非完全是思想觀念的復(fù)制,對(duì)言的觀念實(shí)施在言說(shuō)上會(huì)出現(xiàn)變化、偏移與混雜。在思想觀念層面,《莊子》中認(rèn)為“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這與《老子》所說(shuō)“大音希聲,大象無(wú)形,道隱無(wú)名”的觀點(diǎn)是有一致性的。在言的實(shí)際運(yùn)用上,《老子》認(rèn)為“道之出口,淡乎其無(wú)味”,其對(duì)言的思想觀念與言說(shuō)運(yùn)用中的態(tài)度顯現(xiàn)為基本統(tǒng)一的面貌。《莊子》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在推許無(wú)意、自然的方面與之相類,這也是“不言”的思想觀念在言說(shuō)態(tài)度中的體現(xiàn)。而由于對(duì)言的觀念差異、個(gè)性所喜等,在其言說(shuō)態(tài)度中有諸多趣味、審美、情感的傾向。這與《老子》的“無(wú)味”不同,也較《莊子》思想觀念層面“不言”的主張有所變化。簡(jiǎn)言之,如果籠統(tǒng)地將對(duì)言的思想觀念劃歸為理性的層面,言說(shuō)態(tài)度則在理性上加入了感性成分,成為理性與感性的混合,呈現(xiàn)出對(duì)思想觀念既承續(xù)又偏移的狀態(tài)。
莊子在其思想觀念與自身意趣的多重因素下形成獨(dú)特的言說(shuō)態(tài)度,而其表現(xiàn)形態(tài)是汪洋恣肆的。汪洋恣肆可以說(shuō)是一種非常自由的言說(shuō)形式,縱恣曼衍,是動(dòng)態(tài)的展開(kāi)。淡淡大言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則具有超越性質(zhì),更多地是靜的意味。二者看似不是一致的,但事實(shí)上《莊子》之言正是從淡淡大言的言說(shuō)態(tài)度轉(zhuǎn)化到了汪洋恣肆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在淡淡大言的言說(shuō)態(tài)度中,可以歸納出三個(gè)方面的因素使得從淡淡大言到汪洋恣肆具有可能性,分別是自如、自?shī)省⒆酝咭卜謩e對(duì)應(yīng)著言說(shuō)的三個(gè)限制層面。其一,自如。前文已經(jīng)說(shuō)過(guò),莊子對(duì)言的運(yùn)用是游刃有余的,對(duì)言說(shuō)可自如運(yùn)使,達(dá)到任其自然的境界。言說(shuō)突破詞不達(dá)意的困難,而創(chuàng)造言不盡意的效果。言說(shuō)態(tài)度的自如使言沒(méi)有技巧上的限制,達(dá)到能言。其二,自?shī)省?duì)言說(shuō)藝術(shù)的興趣和審美意韻包含在言說(shuō)態(tài)度之中,成為言說(shuō)展開(kāi)的重要?jiǎng)恿ΑQ缘牡诙€(gè)限制是發(fā)出言說(shuō)的動(dòng)力,希望言說(shuō)、愿意言說(shuō)甚至以言說(shuō)為樂(lè),才能真正使言展開(kāi)。言說(shuō)態(tài)度的自?shī)蕛A向提供了言說(shuō)的動(dòng)力和樂(lè)趣,達(dá)到想言。其三,自忘。言深層的一個(gè)限制是言說(shuō)者自己,言說(shuō)的自我立場(chǎng)使說(shuō)出的言只圍繞“我”之所見(jiàn),符合“我”之利益,追隨“我”之情緒。自我是言說(shuō)的發(fā)出者,言要跟隨自我,而自我在世間又是有無(wú)數(shù)牽扯,有諸多所待,從而令言也成為有待的。莊子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則不固執(zhí)于自我立場(chǎng)。在莊子的言說(shuō)態(tài)度中,立場(chǎng)是可變化的,“我”之言是可否定的,自我是可消解的,其自忘的態(tài)度使言說(shuō)達(dá)于忘言。通過(guò)言說(shuō)態(tài)度的自如、自?shī)省⒆酝酝黄萍记伞?dòng)力、自我的多重限制,能言、想言而忘言,實(shí)現(xiàn)言說(shuō)的巨大自由。表現(xiàn)形態(tài)的產(chǎn)生是復(fù)雜而有許多偶然性的,并不能斷言淡淡大言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必然產(chǎn)生這樣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但它具有的這些因素能夠使言實(shí)現(xiàn)汪洋恣肆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成為可能。
對(duì)言的思想觀念經(jīng)過(guò)理性與感性的糅合形成言說(shuō)態(tài)度,言說(shuō)態(tài)度呈現(xiàn)出表現(xiàn)形態(tài)。如果從思想觀念直接到表現(xiàn)形態(tài),這之中是存在矛盾的。主張“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的觀念如何呈現(xiàn)為汪洋恣肆的形態(tài),這之間很可能有一個(gè)過(guò)渡。且思想觀念在付諸表現(xiàn)的時(shí)候,出于人之心、發(fā)諸人之口或筆,幾乎不可避免地受到種種主觀與感性因素的影響,甚至言說(shuō)本身就會(huì)使思想產(chǎn)生某種程度上的變動(dòng)。思想觀念經(jīng)過(guò)復(fù)雜因素作用的過(guò)程形成言說(shuō)態(tài)度,言說(shuō)態(tài)度促使表現(xiàn)形態(tài)呈現(xiàn)出來(lái),言說(shuō)態(tài)度可以說(shuō)是從思想觀念到表現(xiàn)形態(tài)的擺渡之舟。
“大言炎炎”實(shí)則為“大言淡淡”,其作為《莊子》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具有“游”的立論態(tài)度、隱約的命題態(tài)度、疏淡的審視態(tài)度三個(gè)方面。《莊子》之言,存在“大道不稱”“大辯不言”的思想觀念、“大言炎炎”的言說(shuō)態(tài)度、汪洋恣肆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三個(gè)層面。“大言炎炎”的言說(shuō)態(tài)度在思想觀念與表現(xiàn)形態(tài)之間發(fā)揮了過(guò)渡作用。從言的思想觀念到言說(shuō)態(tài)度,理念在實(shí)際書(shū)寫(xiě)過(guò)程中經(jīng)過(guò)了感性與審美的參與,表現(xiàn)出既承續(xù)又偏移的樣貌。言說(shuō)態(tài)度以其自如、自?shī)省⒆酝奶攸c(diǎn)使得形成汪洋恣肆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成為可能。《莊子》之言的三個(gè)層面之間,既具有一定的差異,又形成相連續(xù)的言的論說(shuō)過(gu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