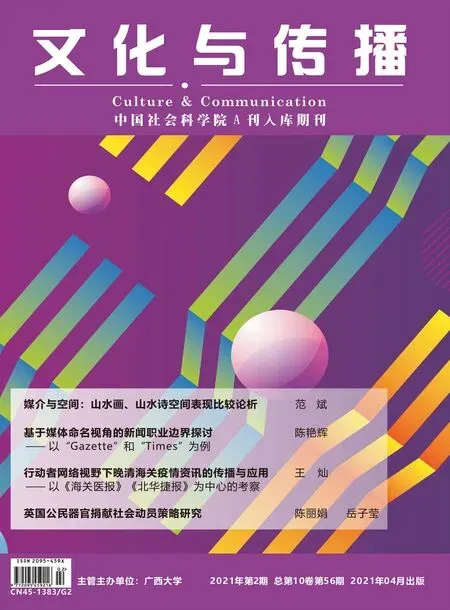“飯圈文化”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挑戰及其規制
粟 鋒
隨著全媒體時代的到來,“飯圈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滲透到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且路徑和邊界迅速拓展,不同偏好的“飯圈”之間爭奪話語權,任性互撕、野蠻生長,對網絡空間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帶來一定的沖擊。“飯圈文化”是大學生等青年群體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中基于價值判斷和主觀想象把自我情感投射到“他者”,對明星偶像產生崇拜甚至是迷戀心理,并通過應援、打榜、控評等非物質勞動對“他者”進行符合自我期待的意義編碼而形成的對象性交往和圈層互動模式。厘清“飯圈文化”的演進邏輯,重視其對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深刻影響,有序引導“飯圈文化”和諧健康發展,是新時代構建“網絡強國”、堅定網絡空間文化自信的迫切需要。
一、“飯圈文化”的演進邏輯與問題表征
“飯圈文化”作為樹立在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上的文化形態,其發展趨勢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在改革開放以前,偶像崇拜主要展現為英模榜樣文化,革命烈士董存瑞、邱少云等人,以及建設時期的雷鋒、王進喜等人都是政府官方宣傳、認可的承載民族精神和道德記憶的全民偶像,此時文藝工作者塑造的經典熒屏形象也大多與這些英模榜樣具有同質性。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下,偶像塑造從政府主導步入市場推動的新階段,具備了飯圈文化的社會經濟土壤。20世紀80年代是“飯圈文化”的萌發期,香港流行文化風靡內地,出現了熱捧“港劇”“港星”的追星族,我國臺灣地區和韓國偶像文化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娛產業化進程。21世紀初“超女”“快男”等草根選秀引發投票狂歡,飯圈文化初步成型。飯圈文化工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以“練習生”“養成系”“二次元”等手法打造具有獨特人設的流量明星,吸納了大學生在內的眾多擁躉[1]。
(一)技術沉迷與“飯圈文化”的時空壓縮
從有線到無線再到大數據技術,信息技術升級增強了人們創建飯圈的實踐能力。在唱片時代人們僅能通過購買碟帶或寄送信件等禮物來表達對偶像的喜愛,文藝工作者在Web1.0時代開始把作品搬運到網絡,便于粉絲自主下載、分享和傳播。而在Web2.0時代作品本身只是符號,粉絲基于社交網絡媒體可以創造“素人崛起”的流量奇跡。技術升級構成了飯圈文化的物質基礎,反過來又誘使粉絲與現實生活日益脫節,為在虛擬世界的虛假需求得到滿足而陶醉,沉溺在受技術控制的舒適生活。戴維·哈維把這種技術沉迷的后現代危機歸結為“時空壓縮”[2]。飯圈文化一方面使“時間空間化”,個人自由勞動時間未能轉化為學習成長的資源,“我”為了躲避現實生活的焦慮和挑戰而求助于想象的共同體,此時“我”自身的時間是面向以偶像為中心的虛擬空間自由敞開的,但事實上“我”是被壓抑和割裂著的。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個人自由勞動時間被飯圈持續的共同行動所耗費,現實生活空間降維為單調的、抽象的平面,飯圈整合粉絲的資源塑造一個完美但隔絕于自我的“他者”——流量明星,粉絲群體形成相互依賴與高度趨同的傾向。技術沉迷引發飯圈文化的時空壓縮,容易模糊粉絲群體對自我與他者、現實與虛擬的認知邊界,造成個體價值觀的矮化、空洞。
(二)資本宰制與“飯圈文化”的話語支配
資本的本質是一種在物的遮蔽下人和人的社會生產關系,具有逃離其實體性形態的演化動力。在工業時代,人們從事苦力勞動而被資本操縱和控制是直觀易感的。進入信息時代,資本以更隱蔽的宰制,以更不易讓消費者察覺的支配方式掩蓋工業化痕跡,如作為價值交換中介的貨幣從金銀、紙鈔變為數字符號(鮮花、游艇等)。在宏觀上,飯圈文化是資本工業化升級的歷史產物。內容生產商為了最大程度地榨取利潤,挖掘粉絲群體的消費潛力,統合了電視、電影、直播、短視頻等影像化渠道,培育“流量明星+IP”的泛娛樂生態,這種跨媒體的文化營銷意味著網絡信息過載和強制選擇,剝奪了非飯圈愛好者的消費話語權。在微觀上,飯圈文化具有組織嚴密、等級森嚴的網絡話語系統。飯圈是一個金字塔型的微型社會,頂端是偶像以及代表其發聲的經紀公司或官方后援會,中間層是能與偶像互動并通過接機、代拍取得其硬照、視頻資源的粉頭,大多數粉絲身處飯圈底層通過購買偶像代言產品和周邊寫真來確證粉籍。飯圈通過語言意義的編碼、共享擴大影響力,如“占C位”“走花路”“打Call”等。資本方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飯圈使用的特定話語完成用戶畫像,精準分發、推送與偶像相關的商品信息。部分大學生把感官享樂型消費當成了人的自我實現需要,在這種話語定制的“信息繭房”中甘愿被“殺熟”。
(三)身份異化與“飯圈文化”的審美虛無
互聯網時代的身份異化具有數字身份異化與職業身份異化的交疊特征[3]。文藝工作者是專門從事表演藝術的工作人員,本職是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服務,創作反映中國精神和時代面貌的優秀作品。大學生等青年一代則是整個社會結構中最具活力和創造性的群體,有望成為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棟梁之材。由于飯圈文化的滲透和資本市場的鼓動,文藝工作者在網絡社交媒體占據公共輿論優勢,成為一呼百應的明星偶像;大學生等青年群體被區隔為崇拜不同偶像的飯圈粉絲。職業身份的異化使個體的數字身份得以脫離現實生活的道德倫理約束,個人數字身份體驗也會影響現實人格塑造和審美觀念。網絡社會日益分化為明星偶像和飯圈粉絲兩大數字階層。明星偶像為了迎合目標市場、取悅特定飯圈,不再重視作品質量,借助美圖技術竭力呈現出精心設計包裝好的高顏值人設,流量明星數字身份的批量化生產催生了千篇一律的網紅臉、小鮮肉。明星偶像外在的行為表演、內在的價值表達引發粉絲群體的模仿,飯圈內部體驗的互動加深了粉絲以偶像為美的標尺的信念,比如韓式小鮮肉風靡時,中國青年“娘化”現象曾受到廣泛關注。飯圈文化中偶像符號被捧上高壇并無限放大,蠶食文藝創作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理念,不利于大學生等青年群體培養青春、陽光、活力、多元的審美趣味。
二、“飯圈文化”對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雙重影響
社會意識形態屬于觀念上層建筑,但互聯網絕非懸浮在現實世界之上的自在王國。網絡意識形態是社會意識形態與網絡空間互相嵌入的結果,不僅彌散在網絡虛擬空間,還對現實社會生活具有普遍的影響力。思想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載體,思想文化沖突的實質就是意識形態的交鋒。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確立的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4]。網絡意識形態安全要確保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的一元性、穩定性、權威性,即不容許任何一種思想文化借助網絡空間夾帶或衍生新的意識形態來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爭奪主導地位,特別是以資本主義為內核的非主流意識形態;網絡空間的任何一種思想文化都必須接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引領與規訓,使之滿足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特性的要求。飯圈文化在網絡空間的話語權意識和價值號召力日漸增強,大學生等青年群體卷入了飯圈的意識形態漩渦。
(一)消極影響:“飯圈文化”的排他性、擴張性和強制性
排他性意味著非此即彼,飯圈文化的排他性會誘發網絡空間以偶像為代表的私人資本利益與以公權力為代表的國家利益之間的緊張。明星偶像依靠IP產品的文化敘事吸納大量粉絲后,為了謀求自身在大眾主流文化的影響力,會對粉絲群體進行“提純”,把來自小眾市場以及消費忠誠度低的粉絲與飯圈“解綁”。在飯圈內部清洗的過程中,部分粉絲在資本運作下試圖染指公權力來為偶像發聲,打壓處于對立面的其他群體。一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本身也是粉絲,出于對偶像的忠誠和資本的驅動,其中極少數人濫用公權力,用政府官方賬號發布追星言論,與營銷號聯動為明星偶像造勢。飯圈文化的排他性對公號私用等行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種擠占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傳播途徑的行為性質惡劣,對黨的執政公信力帶來消極影響。
飯圈文化的擴張性是指明星偶像和粉絲群體不斷擴大勢力范圍。擴張的飯圈話語充斥著情感宣泄,其中又夾雜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痕跡。在國內網絡空間,明星偶像日常動態長年霸占熱搜、頭條,個別來自臺灣地區和韓國的藝人,發布帶有政治企圖的言論和政治問題的圖片。粉絲通過病毒式傳播把明星帶有情緒色彩的碎片化生活場景上升為網絡空間的娛樂狂歡。同時,飯圈文化具有跨國性影響,我國部分粉絲把偶像在國內形成的輿情炒作到外網并占領多國話題排行榜,在韓國明星參軍期間向韓國軍隊開展網絡應援、捐贈等等。這些現象抹黑了中國形象,損害了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長此以往,粉絲群體的政治認同、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將淪為娛樂的附庸。
強制性是權力的根本屬性,不受法律和道德規制的權力會導致失去秩序的暴力。飯圈文化的強制性源于高度組織化的結構,具有美宣、反黑、數據、公益等職能小組,集中體現在強行安利偶像、洗白偶像,為偶像爭奪影視番位、數據流量而不擇手段,引發網絡空間激烈沖突。強行安利偶像是指粉絲向普通網民(或稱路人)列舉特定明星履歷以吸引其加入飯圈,一旦遭到拒絕就對路人進行辱罵,甚至“人肉”并在線下對其進行騷擾的行為;洗白偶像是當流量明星處于某種弱勢時,粉絲通過“賣慘”以及購買職業“水軍”來造謠攻擊彼此競爭的其他明星。飯圈文化加劇網絡暴力,這種烏合之眾的“群體極化”憑借數字身份的隱匿性放縱非理性行為,違背了社會主流價值規范,滋長了非理性的網絡話語生態,沖擊了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穩定環境。
(二)積極影響:“飯圈文化”的從屬性和價值引導性
中國的飯圈文化必然從屬于群眾性精神文明和公共文化體系。因此飯圈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規訓下也可以發揮價值引導功能,促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粉絲群體中深入人心。一方面,明星偶像積極立場的鮮明宣示會得到粉絲群體的“跟風式”響應。如藝人群體在社交媒體轉發愛國“云護旗”圖片,激發了青年群體的政治參與熱情,從飯圈的情感互動演變為維護祖國統一的網絡集體行動。另一方面,飯圈話語被官方媒體改造并賦予主流意識形態內涵后,拉近了民眾與國家的心理距離,增強了粉絲群體等普通網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親切感和向心力。如“飯圈女孩”把中國國家形象擬人化為偶像“阿中哥”,在得到《人民日報》和共青團認可后,不少粉絲以創作二次元動漫等形式來支持、力挺中國。
不過,如果對飯圈文化價值引導功能認識不夠精準,也容易弄巧成拙。共青團嘗試推出團屬二次元偶像“紅旗漫”和“江山嬌”,受到網民抵制并評論說“我是你的公民,不是粉絲”。關鍵問題是主流意識形態如何規訓飯圈文化。在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作堅決斗爭時,為了在網絡空間廣泛凝聚人心,可以利用飯圈文化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輻射范圍,使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具象化、更接地氣。但在日常生活中,要維護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神圣性和權威性,不能以飯圈文化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進行肢解和再造,否則這種戲謔無異于主動釋放飯圈文化的消極影響,帶來諸如政治娛樂化等突出問題。
三、制度化治理“飯圈文化”,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
飯圈文化作為新興的思想文化風潮對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弊大于利。要構建“網絡強國”的文化自信,切實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不能任由飯圈文化占領網絡意識形態陣地。可以從平臺端、供給側和需求側三個方面入手制度化治理飯圈文化:改善技術底層架構,把技術的客觀性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性相結合,防止技術理性泛濫造成社會價值觀的分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作理念,抵制流量明星對文藝作品質量和網絡創作生態的侵蝕,同時展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博大自信和文化生命力,使飯圈文化“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強化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在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的育人格局中,突出網絡育人的重要性,提升青年群體的網絡素養,引導學生對飯圈文化形成理性認知,充當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的積極行動者。
(一)平臺規制: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網絡技術平臺的全鏈條管理
網絡社交媒體平臺是飯圈文化的技術基座,粉絲群體在不同的社交平臺開展交流活動受到特定的信息技術規制。微博、豆瓣等平臺的技術初衷是促進陌生人基于話題和興趣建立網絡互動,便于粉絲安利偶像,微信的設計更符合熟人社會的個性體驗分享。可見,任何一種思想文化在網絡空間進行傳播都要適應技術底層邏輯。但是為了確保網絡意識形態安全,不能以技術中心主義作為網絡平臺拒斥社會價值約束的幌子。既要倡導技術人員在開發、運營網絡社交平臺時注重價值關懷,也不能只依靠研發者和運營商的道德自覺來規避技術作惡。2011年國務院修訂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未對社會主流價值規范與網絡信息技術的融通提出明確倡議和管理規定。當前,我國政府對社交網絡媒體的治理主要依靠網絡打黑除惡等專項性行動,缺乏在網絡社交平臺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法制化保障。從網絡技術健康有序發展和主流意識形態安全來考慮,應當盡快出臺專門的網絡社交媒體管理法律法規,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編碼為相應的技術語言標準,力求在網絡社交軟件設計、運營和版本更新的全技術鏈中體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訴求。
(二)生產規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動網絡文藝生產的供給側改革
習近平指出“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了文藝形態”,“對新的文藝形態,我們還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5]。飯圈文化或許具備孕育新的文藝形態的潛力,但與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念還有所偏差,對網絡文藝創作帶來顯著的干擾,集中表現為:流量明星的作品存在粗制濫造現象,飯圈資本推手首要關注經濟效益而非社會效益。2015年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全國性文藝評獎制度改革的意見》,2018年國家廣電總局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文藝節目管理的通知》,對治理網絡文藝生產亂象,引導飯圈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相適應具有指導作用。第一,探索建立劣跡藝人黑名單。嚴厲整治過度包裝、模仿抄襲和獵艷媚俗的行為,以文藝評獎為指揮棒促使流量明星重建文藝工作者的身份意識,從娛樂資本和粉絲群體聯手打造的數據烏托邦中解脫出來。第二,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理念。加大審查力度,打擊惡搞經典、解構崇高,丑化英雄人物、渲染社會陰暗的歷史虛無主義文藝敘事。督促娛樂資本和流量明星靜下心來,推出有筋骨、有誠意、有溫度的作品,為粉絲群體提供優質精神食糧。第三,使市場的身軀流淌道德的血液。力戒飯圈文化的浮躁、奢華,解決過度追星炒星、高價片酬、數據造假等網絡市場頑疾。飯圈文化只有既出文藝人才,又出優質作品,才能引領網絡社會的良好風尚,凝聚網絡空間的正能量,拱衛網絡主流意識形態。
(三)需求規制:加強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生活空間
網絡空間內在的“互動性、開放性、自由性”以及移動網絡終端等數字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善使得虛擬世界無遮蔽地在現實生活中展開[6]。2019年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深化新時代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的若干意見》指出,要統籌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網絡育人應該成為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的重要銜接途徑,引導青年一代提高網絡信息素養,建立對網絡空間非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正確認知。飯圈中的粉絲群體越來越低齡化,與新生代初次進入網絡空間的年齡越來越小是一致的。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把網絡育人的關口前移。在小學階段,限制學生網絡使用時長,提醒注意保護隱私,避免網絡沉迷,學習健康使用網絡的基本技能;初高中階段,引導學生識別明顯有害的網絡信息,如色情淫穢、反動言論等,建立對偶像崇拜的初步認識,注重從優質明星偶像身上學習自身不具備的技能或品質;大學階段,啟發學生對飯圈文化開展實驗性觀察,進一步對個體成長和人生追求等深層次問題進行思考。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是推進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的重要方面,不同學段循序漸進、螺旋上升地開展網絡育人,對青年人自覺抵御、過濾非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意義重大,有利于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