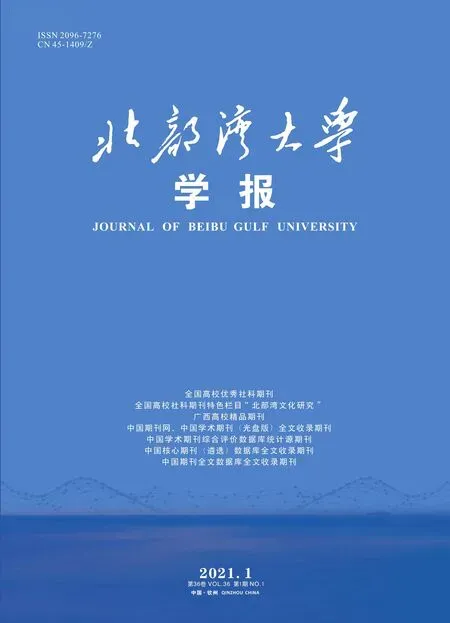“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
劉國斌
(吉林大學生物與農業工程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順應歷史潮流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尤其是在當前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以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質量變革、效率變換、動力變革為支點,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矛盾為目標的高質量發展時代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勢在必行,這對于提高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質量、提升“一帶一路”建設水平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十分必要。本文將從內涵及空間尺度、發展潛力、實現的可能、作用機制、不確定性以及推進方式等方面對“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展開具體分析。
一、“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及空間尺度界定
(一)“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學界關注的焦點,也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所在。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研究,學者們有各自的闡釋。金碚認為,高質量發展是經濟發展方式、結構以及動力更優化的經濟發展階段[1];王永昌和尹江燕認為,高質量發展是強調資源配置效率高、環境成本低、經濟質量和效益高的可持續發展[2];孫祁祥與周新發認為,高質量發展是能滿足人民群眾有效需求的可持續發展[3];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指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涵是供給體系質量高、效率高、穩定性高[4]。
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的新表述,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由速度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轉變,以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由“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通過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三大變革,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矛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對過去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是經濟數據精確、營商環境優化、產品質量保證、資源精準對接與優化配置的增長方式,是創新驅動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創新高效節能環保高附加值的增長方式,是智慧經濟為主導、高附加值為核心、質量主導數量、GDP無水分、使經濟總量成為有效經濟總量、推動產業不斷升級,推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方式。綜上可見,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由數量向質量轉變,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由“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以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為主線,以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矛盾的新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
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做進一步解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實質上就是在民族地區的語境范圍下,實現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則指的是“一帶一路”經過的民族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所以,“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可以表述為:“一帶一路”上的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由數量向質量轉變、由中高速增長向高質量階段轉變,以“一帶一路”上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通過其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轉變,加快民族地區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滿足“一帶一路”上民族地區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破解其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矛盾,進而實現其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研究的空間尺度界定
對“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不僅要分析其內涵所在,更重要的是要對其空間尺度進行界定,明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范圍。
首先,要明確民族地區的空間尺度。民族地區是我國重要的地理單元組成部分,一般而言,我國民族地區包括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和120個自治縣。也有學者從內蒙古、廣西、貴州、云南、西藏、青海、寧夏、新疆8個民族省區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等發展情況進行論述[5]。
其次,要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涵蓋范圍精準把握。“一帶一路”倡議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根據“一帶一路”規劃,“絲綢之路經濟帶”涵蓋范圍主要有新疆、重慶、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云南、西藏13省(直轄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圈定上海、福建、廣東、浙江、海南5省(直轄市)。
基于此,綜合考慮“一帶一路”倡議與民族地區的空間尺度范圍以及本文研究需要,筆者認為,“一帶一路”上的民族地區范圍主要包括: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省、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7個省(自治區)。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潛力優勢分析
(一)礦產資源優勢突出
礦產資源優勢突出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潛力優勢,從“一帶一路”上各民族地區礦產資源稟賦看[注]參考各民族地區政府網站資料整理。,民族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儲量,這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先天優勢。
截至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保有資源儲量居全國之首的有20種、居全國前三位的有45種、居全國前十位的有95種,稀土查明資源儲量居世界首位。廣西壯族自治區以鋁、錫等有色金屬為最,是全國10個重點有色金屬產區之一;在已查明資源儲量的礦產中,75種資源儲量居全國前十位,8種資源儲量居全國第一位;在35種戰略性礦產中,廣西探明資源儲量的有30種。青海省現有各類礦產135種,查明礦產88種,單礦種產地數1 121個;在已探明的礦種保有資源儲量中,有56個礦種居全國前十位。寧夏回族自治區已探明礦產資源50多種,人均自然資源潛值為全國平均值的163.59%,居全國第5位。西藏自治區已探明的礦產達70多種,在已探明儲量的26種礦產中,有11種的儲量分別名列中國的前5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礦產資源種類多、蘊藏量大,在全國已發現的162個礦種中,新疆有122種。云南有61個礦種的保有儲量居全國前10位,其中,鉛、鋅、錫、磷、銅、銀等25種礦產含量分別居全國前3位。從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帶一路”上的民族地區礦產資源十分豐富,這為其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農業資源稟賦優勢潛力巨大
“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勢在必行,從“一帶一路”上各民族地區農業資源稟賦看[注]參考2018年各民族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資料整理。,其農業本身具有資源稟賦優勢,發展潛力巨大。
內蒙古自治區牛肉產量、羊肉產量、禽蛋產量、牛奶產量分別為61.4萬噸、106.3萬噸、55.2萬噸、565.6萬噸,與2017年相比分別增長3.3%、2.1%、3.7%、2.3%,畜牧產品資源優勢突出。2018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油料產量、甘蔗產量、蔬菜產量(含食用菌)、園林水果產量、豬牛羊禽肉產量、蠶繭產量、木材產量、天然松脂產量、油茶籽產量分別為66.66萬噸、7 292.76萬噸、3 432.16萬噸、1 790.55萬噸、418.4萬噸、36.89萬噸、3 100萬立方米、70.4萬噸、23.32萬噸,同比分別增長2.7%、2.2%、4.6%、13.3%、1.6%、3.8%、1.6%、1.2%、3.3%。2018年云南省油料產量、蔬菜產量、園林水果產量、茶葉產量分別為60.98萬噸、2 205.71萬噸、757.14萬噸、42.33萬噸,同比分別增長8.4%、6.2%、4.4%、7.6%。2018年西藏自治區青稞種植面積139.58千公頃,同比增長4.1%;油菜籽種植面積22.43千公頃,同比增長0.2%;蔬菜種植面積24千公頃,同比增長3.14%;牛606.73萬頭,同比增長2.38%。2018年青海省農作物總播種面積557.25千公頃,同比增長0.35%;藥材面積44.06千公頃,同比增長16.2%;在藥材中,枸杞35.53千公頃,增加2.00千公頃;蔬菜及食用菌播種面積43.96千公頃,同比增長1.97%,特色農產品資源豐富。201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玉米產量、馬鈴薯產量(折糧)、蔬菜產量、紅棗產量、枸杞產量、葡萄產量、油料產量、牛肉產量、禽肉產量分別為234.62萬噸、36.38萬噸、550.81萬噸、5.74萬噸、9.77萬噸、19.91萬噸、7.29萬噸、11.52萬噸、3.57萬噸,與2017年相比分別增長9.2%、3.4%、2.0%、2.0%、6.3%、44.9%、5.0%、5.5%、4.3%。2018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玉米產量827.57萬噸,同比增產7.1%;棉花產量511.09萬噸,同比增產11.9%,產量占全國的83.8%;園林水果產量1 059.00萬噸,同比增產1.8%;堅果產量106.84萬噸,同比增產3.2%;羊肉產量59.38萬噸,同比增長2.0%。從這些數據不難發現,“一帶一路”民族地區農業發展具有資源稟賦優勢,這也為加快“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支撐。
(三)能源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潛力
從資源稟賦看,2018年“一帶一路”民族地區焦炭生產量達到7 557.39萬噸,同比增長4.8%,與2015年相比增加5%;2018年“一帶一路”民族地區天然氣生產量402.16億立方米,同比增長8.3%,較之2015年增長10.5%;2018年“一帶一路”民族地區發電量達到15 766.86億千瓦小時,同比增長13.7%,與2015年相比增加了31.1%;2018年“一帶一路”民族地區火力發電量為4 276.93億千瓦小時,同比增長13%,較之2015年增加19.1%[注]參考2019年各民族地區統計年鑒數據整理。。可見,“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資源豐富,具有一定優勢潛力。
從能源產業發展看,“一帶一路”民族地區能源產業發展具有比較優勢,具體看:2019年內蒙古自治區現代煤化工產業增加值增長8.2%,新能源發電增加值占電力生產行業比重為24.5%;2019年廣西壯族自治區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增長2.0%,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增長15.2%;2019年云南省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增長12.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增長8.3%;2019年寧夏回族自治區煤化工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30.1%,水電、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量322.1億千瓦時,增長6%;2019年青海省新能源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8.9%,煤化工產業增加值增長11.4%;201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5.0%;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增長10.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增長0.4%;水、風、光等清潔能源發電量同比增長14.8%,清潔能源發電量占發電量的比重為22.9%,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2019年西藏自治區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增長26.6%[注]參考2019年各民族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資料整理。。
綜上,“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經濟發展具有資源稟賦優勢和能源產業優勢,其能源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潛力,能夠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產業支持。
(四)旅游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潛力
從“一帶一路”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發展情況看[注]參考2015—2019年各民族地區統計年鑒整理。,2018年“一帶一路”民族地區旅游外匯收入達到9 753.29百萬美元,同比增長17.9%,與2014年相比增加71.7%。從各民族地區看,2014—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省、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旅游外匯收入分別增長26.8%、76.7%、82.5%、70.8%、46%、202.3%、90.4%。可見,“一帶一路”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經濟發展趨勢較好。
從“一帶一路”民族地區旅游經濟客源市場規模情況看[注]參考2015—2019年各民族地區統計年鑒整理。,2018年“一帶一路”上的民族地區旅游接待國際游客數量達到16.19百萬人次,同比增長8.7%,與2014年相比增長93.7%。其中,2014—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省、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旅游接待國際游客數量分別增長12.6%、89.9%、146%、100%、40%、200%、83.3%。可見,“一帶一路”民族地區旅游客源市場規模在不斷擴大。
基于此,我們可以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潛力較為明顯,能夠成為“一帶一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為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經濟動力支持。
三、“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的可能
(一)促進礦產業高質量發展
促進礦產業高質量發展是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礦產資源稟賦優勢、培育和壯大民族地區主導產業、推進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一是合理對“一帶一路”民族地區礦產資源進行高質量開發,要堅持習近平總書記“兩山”理論,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開發與保護共同推進,提高民族地區礦產業發展質量水平。二是依托民族地區各地區優勢礦產資源,將礦產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培育新的主導產業和支柱型產業,進而為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產業支撐,同時在傳統礦產業發展的基礎上,改變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進一步催生新的業態和模式,提高“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礦產業發展質量。三是要利用“一帶一路”契機,加快民族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合作互補,為“一帶一路”民族地區提供優質的技術和資金要素支持,提高民族地區采礦冶金等礦產業和配套產業發展,進一步延長“一帶一路”民族地區礦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滿足自身發展需要,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進而為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開辟新的市場和新的渠道,這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將礦產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優勢的可能所在。
(二)加快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
正如前文分析,“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資源較為突出,需要將民族地區農業潛力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提高農業經濟發展質量。
一是要堅持特色發展、差異化發展。盡管“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發展資源優勢突出,但各個地區的農業資源稟賦條件仍有差異,應該充分依托各地區特有的農業資源優勢,培育和壯大民族地區特色農業產業,形成新的農業產業競爭優勢,激活民族地區農業經濟發展動能,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現代化進程。
二是要加快綠色農業發展。要堅持習近平總書記“兩山”理論,強調綠色興農、質量興農,加強民族地區綠色農產品開發,在發展農業產業過程中要用綠色賦能農業,提高農業綠色GDP,積極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以綠色、低碳技術等為手段加快農業綠色轉型升級,從而提升“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經濟發展質量效益,進一步釋放農業潛力優勢。
三是要加快數字農業發展。要充分利用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產業數字化發展,進而推進種植業、養殖業、畜牧業、林業等產業部門的數字化發展,培育和打造農業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同時加快“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產品電商產業發展,通過產業融合進一步將“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資源稟賦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優勢,進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
(三)促進能源經濟高質量發展
前文分析發現,“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潛力,能夠為其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可能。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資源,轉變傳統能源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加快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能源工業轉型升級,提高能源產業發展質量和效率。一是要加快能源產業技術體系變革,以人工智能、5G、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加快“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傳統能源產業技術升級、裝備設施升級。二是要嚴格把控能源生產全過程的標準,提高能源產品質量,進而提升“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產業競爭力。
另一方面,要積極推進新能源產業發展,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豐富的水能、電能、太陽能等能源資源,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加強新能源產業布局和建設,優化“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結構,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經濟提供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動力。
此外,要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能源合作,借助“一帶一路”平臺,“一帶一路”上的民族地區應與沿線能源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地區展開深入合作,利用其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優勢,加快“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經濟轉型升級,擴大其能源產業對外開放水平,進而實現“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產業“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能源經濟高質量發展。
(四)推進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
旅游經濟發展潛力較大,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可能的依據。如何將“一帶一路”實現民族地區旅游經濟潛力轉化為經濟優勢,提高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質量,這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
一方面,要充分挖掘“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資源稟賦,開發民族地區特色旅游產業和特色旅游產品,將旅游經濟潛力優勢轉化為經濟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在同沿線國家地區旅游經濟競爭中保持特色優勢和競爭力,提高“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質量。
另一方面,要對“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賦能,提高民族地區旅游功能,通過產業融合探索“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高質量的增長動力,同時也進一步拓寬“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生態功能、教育功能、康養功能等,提高“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質量,為其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可能條件。
四、“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
(一)市場作用機制
市場作用機制是加快“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作用機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要素資源支持,而這與市場作用的發揮密不可分。在市場作用機制下,民族地區能夠與沿線國家地區實現要素資源的跨境跨地區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滿足各自礦產業、能源產業、農業產業以及旅游產業發展需求,進一步深化產業合作,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民族地區能夠利用市場作用機制,積極發展自身能源經濟、農業經濟和旅游經濟,更好地融入國內大循環,滿足自身發展需要。另一方面,能夠吸引更多沿線國家地區的技術、資金等要素資源,實現與沿線國家地區在新能源、現代農業和新興旅游業領域的競合,借助“國內國際雙循環”,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機制,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動力支持。
(二)人才支撐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人才支撐機制。正如前文所述,“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潛力在于礦產業、能源產業、農業產業以及旅游產業領域,如何高質量推進這些潛力產業,將潛力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的經濟競爭優勢,這就需要高素質人才支持,通過構建人才支撐機制,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智力支持,進而推進新能源、現代農業以及旅游業的合作交流,從而轉變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方式,培育和打造礦產業、能源產業、農業產業和旅游產業的新業態與新模式,為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所以,人才支撐機制是將“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潛力轉化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動力的重要機制。
(三)企業帶動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企業的帶動。一方面,要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加快礦產業、能源產業、現代農業、旅游產業的發展,轉變其經濟發展模式,通過龍頭企業的資金投入,加快技術創新和應用,加快裝備改造和升級,進而提高產品生產質量和效益,提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質量效益。另一方面,要加強“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企業與沿線國家地區的企業聯動,加快礦產企業、能源工業企業、農業企業、旅游企業的跨境跨地區合作交流,形成產業的良性互補,進而解決民族地區產業經濟發展短板,滿足其礦產業、能源產業、農業產業、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需求,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提供助力。
(四)產業合作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就是要培育民族地區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進而實現產業經濟提質增效,為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更應該與沿線國家地區展開積極深入合作,探討產業合作新機制,將礦產業、能源經濟、農業經濟、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潛力優勢轉為經濟增長動力優勢,從而加快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要積極推進民族地區與沿線國家地區礦產企業合作,加強技術互補和資源互補,探索礦產業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積極推進新能源產業合作,探索能源經濟合作新增長點;加快現代農業合作,提升農業合作質量和效益,轉變民族地區農業發展模式,提高農業經濟發展水平;推進冰雪旅游等旅游產業新業態、新產業的發展和合作,加快民族地區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基礎上,各民族地區要充分依托各自的能源經濟發展優勢,與“一帶一路”倡議下各經濟走廊國家和地區展開深入合作交流,加強相關企業的合作和交流,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產業合作動力。
(五)設施聯通合作機制
要積極推進完善“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與沿線國家地區設施聯通合作機制。一方面,要深化合作領域,拓寬合作內容。從交通、通信、能源、管道、口岸等基礎設施建設上的“硬件聯通”,向通關、檢驗、認證、融資等運營管理、金融支持服務等制度建設上的“軟件聯通”逐步發展,合作領域從易到難不斷拓展,合作內容則開始向政策溝通、制度對接、執法互助、標準互認與信息服務平臺建設等逐步深化。另一方面,要深化合作形式和層次。推進重點項目、簽署部門合作備忘錄、在專項領域簽署具有一定約束力的次區域或雙邊協議等。基于此,深化“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與沿線國家地區的設施互聯互通,是加快“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
(六)政府保障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引導和支持,所以,要發揮政府保障機制作用,引導和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各民族地區政府部門應該結合各自的經濟發展優勢制定和實施有利于礦產業、新能源產業、現代農業、新興旅游業發展的政策文件或法律法規,重點布局,合理規劃,進一步培育和打造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的增長極,從而提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另一方面,要積極主動融入“一帶一路”,與沿線國家地區簽署合作備忘錄,在重點產業領域展開深入合作和交流,進而為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同時,要積極對接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與沿線國家展開深度合作,進而加快“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所以,政府保障機制是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潛力轉為高質量發展動力的有效機制。
五、“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
(一)“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桎梏
“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依然面臨著其自身內部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經濟高質量發展[6]。
從民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看,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達到33 457.06元,同比增長7.8%,與2014年相比增加39.3%;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為11 790.08元,同比增長9.5%,較之2014年增加42.6%;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的絕對數為21 666.98元,同比增長6.9%,較之2014年增加37.6%。從中也能看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的差值絕對數呈增長態勢,說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這在一定層面上不利于其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從民族地區城鄉居民公共服務差距看,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城市每萬人醫療機構床位數均值為93.6張,農村每萬人醫療機構床位數均值為47.44張,城市每萬人機構床位數是農村的1.97倍。盡管這一比值在縮小,但是城鄉居民醫療差距依然較大,而且,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差距也有類似情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內部自身城鄉居民公共服務差距依然存在,不利于其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基于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依舊明顯,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二)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較弱
從“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所處地理位置看,這些地區基本上處在沿邊內陸地區,科技創新的先天條件不足,比之東部沿海等地區差距較大,經濟創新能力相對較弱。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年主營業務收入2 000萬及以上規模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達到22 869件,同比增長12.3%,較之2014年增加60.3%,2014—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年主營業務收入2 000萬及以上規模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呈增長趨勢,這在一定層面體現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的工業企業創新能力有所提升。但與東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的平均水平相比,2018年東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的平均數量為63 112.64件,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的2.76倍,且2014—2018年東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申請平均數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的2.5倍之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較弱,甚至可以說明其經濟發展的創新能力較弱。創新能力較弱,那么新技術、新業態、新產品形成和發展的可能相比較創新能力強的地區要弱,不利于“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的技術升級、產品創新、產業升級,影響其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不利于其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三)存在地緣政治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覆蓋面廣,存在地緣政治風險,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民族地區同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高質量合作,阻礙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一帶一路”部分國家政局穩定性風險較大,如緬甸等國的中央與地方政策一致性較差,政策的制定往往在政治博弈中反復搖擺;巴基斯坦執政黨與反對黨派政見分歧嚴重,國內抗議示威活動頻發。另一方面,“一帶一路”部分沿線國家和地區政府貪污腐敗現象嚴重,權力尋租情況時有發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經濟的合作和發展。此外,地區沖突、恐怖主義、宗教主義等社會風險也加劇了沿線部分國家內部的政局動蕩。因此,地緣政府風險的存在使得民族地區與沿線國家地區的潛力合作、經濟合作等存在不確定性,在一定層面阻礙了“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四)經濟貿易風險加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經濟基礎落后,投資融資環境差,經濟波動大,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逐漸顯現,導致投資面臨的經濟風險大大增加。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經常存在巨額項目赤字,內部經濟問題嚴重,投資前景不被看好,而且貿易多以邊境小額貿易為主,貿易結構單一,貿易質量相對不高,對外投資有可能變為呆賬、壞賬,債務違約風險較大。另一方面,民族地區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的直接投資項目一般都具有資金投入多、回收周期長、未來收益不確定的特點。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地方政府和企業投資熱情高漲,投資了許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項目泡沫化的風險也不斷加大。東道國的經濟運行一旦出現狀況,民族地區政府投資就極有可能遭受難以挽回的巨額損失。此外,中美貿易戰以及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都有可能對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合作產生影響,而且RCEP協定的簽署也在一定層面給“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貿合作帶來更大的挑戰。所以,經濟貿易風險加劇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之一。
六、“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進方式
(一)提升優勢特色產業發展質量
一是要加快礦產業綠色、安全、高質量發展,提升礦產資源開采技術,提高礦產資源利用效率,更新礦產企業機械設備,進一步推進民族地區礦產業高質量發展。二是要加快推進新能源產業發展,充分利用民族地區風能、水電、太陽能等新能源資源稟賦優勢,加快新能源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新能源產業投入,進一步加快民族地區能源經濟新業態、新產業發展,提高能源經濟發展質量。三是積極推進現代農業產業發展,加快民族地區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為民族地區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四是要充分利用好民族地區獨特的人文旅游資源,加快推進民族地區特色旅游業、手工藝品加工業等產業發展,形成民族地區特有的人文旅游產業鏈。積極探索旅游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拓寬民族地區旅游產業功能,提升旅游產業發展質量和效益。通過提升“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優勢特色產業,加快其經濟高質量發展,從而進一步解決其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
(二)推進民族地區產業技術創新
推進民族地區產業技術創新是提升民族地區技術水平、提高創新能力、加快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式。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產業高質量發展,產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新技術的應用和推廣,“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產業支撐,而這就需要推進民族地區的產業技術體系變革,提高技術創新能力。
要加快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5G等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和推廣,通過“大數據+產業”,對產業生產、加工、流通等產前、產中、產后環節的發展方式進一步升級,智慧智能生產、加工、經營管理等新的模式替代傳統產業發展模式,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區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業創新升級、產品創新,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實為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高質量產業支撐。
(三)加強政策和民心溝通,創新區域合作方式
一方面,加強政策對接和民心溝通。重點加強民族地區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政策對接,尤其是在礦產業、新能源產業、現代農業、新興旅游業等領域加強協同作戰,構建新的合作體制機制,進一步為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安全的外部政策環境。同時要加強民心溝通,民族地區要積極與沿線國家地區在民心溝通領域加強合作,在文化、飲食、語言等方面積極交流和溝通,加強文化交流和合作,加深民心溝通,進而為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要創新區域合作方式。要加快跨境自貿區建設,積極與沿線國家地區展開合作交流,提高經貿合作質量。通過跨境自貿區建設,打通民族地區與沿線國家地區的國際合作大通道,進而能夠為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的沿線國家優勢資源要素支持,借助其優勢資源要素來發展民族地區自身經濟,將潛力優勢轉化為經濟競爭優勢,進而提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在同沿線國家地區及經貿合作中占據主導權。
此外,要推進第三方市場合作,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可以融入“一帶一路”倡議,通過第三方市場合作搭建新的合作平臺,在產品服務、產業合作、投資合作等方面形成更高水平的合作,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持,這也是創新區域合作方式、提高“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方式。
(四)加強雙向投資,提高投資質量
通過前文分析發現,“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面臨經濟風險加劇的不確定因素,其中債務危機或者投資風險等是其重要方面。因此,“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應該加強雙向投資、提高投資質量,為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持。一方面,為規避由沿線國家經濟風險帶來的消極影響,民族地區在對外合作和交流過程中應該謹慎投資,重點在新能源、現代農業、新興旅游業等潛力經濟部門投資,在國內經濟發展形勢較好的沿線國家或地區加大投資,同時,也應考慮自身經濟發展的優勢和劣勢,提高投資質量,充分利用投資擴大民族地區國際市場,吸引沿線國家地區的技術、人才等要素流向民族地區特色優勢產業,從而加快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沿線國家和地區也要結合自身和中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優勢,合理投資中國“一帶一路”上民族地區產業等,并提高投資質量。所以,從這些方面看,加強雙向投資、提高投資質量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