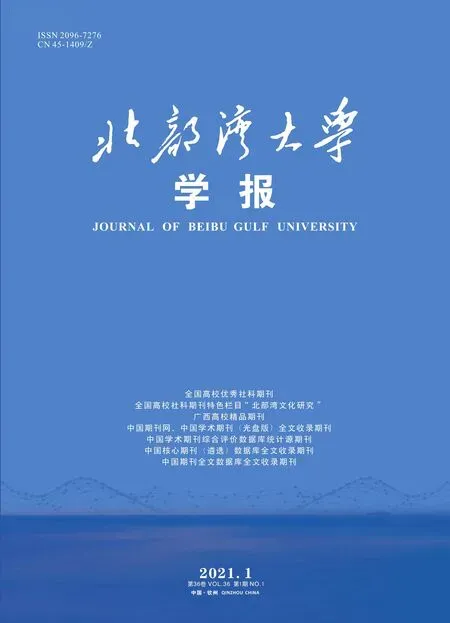中國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重新認識和評價
馮彥明
(中央民族大學經(jīng)濟學院,北京100081)
引言 對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誤解
中國農(nóng)村的傳統(tǒng)經(jīng)濟形式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樣被誤解了上百年。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舉辦過一期《筆談:關(guān)于“中國式小農(nóng)經(jīng)濟”》,其“主持人按”開宗明義:農(nóng)村研究有兩個目標,一是認識中國農(nóng)村,進而認識整個中國;二是建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社會理論,二者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照搬既有的成熟理論(主要是西方理論)解釋具有相當獨特性和變動性的中國經(jīng)驗,就談不上對農(nóng)村、對中國的正確認識[1]。筆者深以為然。實際上,我們研究和認識中國農(nóng)村和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也不僅僅是解釋中國的過去,中國特色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不僅持續(xù)存在了數(shù)千年,而且至今仍然生生不息;與此相對比,雖然西方大工業(yè)模式在短期內(nèi)創(chuàng)造了無限的物質(zhì)財富,但其給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造成的問題也同樣是無限的,特別是在當前面臨由西方模式造成的人類不可持續(xù)、而西方理論又完全“黔驢技窮”的形勢下,“反省”我們過去一段時間的看法和想法,對中國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重新進行研究,也許更具有特殊的指導意義。
確實,近百年來,“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詞匯,既令無數(shù)現(xiàn)代人、特別是學術(shù)界著迷:這樣一種經(jīng)濟形式能夠持續(xù)存在數(shù)千年,而且迄今沒有被“消滅”;又讓無數(shù)國人悔恨:在很多人看來,正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固執(zhí)(不自我變革)、孤立(封閉)和孤芳自賞(歷史的榮耀)最終使中國陷入絕境,蒙受百年恥辱。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如此的認識不能說沒有一點兒道理,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這種生產(chǎn)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jīng)在消滅”[2]873,而“受辱”也是現(xiàn)實的,偌大的一個古老文明國家被打敗而被迫割地賠款,這不能不使億萬國人感到迷惑和憤怒;時至今日,商品經(jīng)濟大潮風起云涌,特別是經(jīng)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站起來”“富起來”,而且更要“強起來”了,“小農(nóng)經(jīng)濟”不僅逐步被遺忘和遺棄,而且還成為發(fā)家致富的累贅,似乎更證明其早已被揭示的眾多弱點。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在此“現(xiàn)代化”過程中,特別是在崇洋媚外和西方話語權(quán)壟斷的背景下,不應被人們一起“遺忘”的是:中國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既不是外生的,也不是“君王意志”的體現(xiàn),而是與中華文明一起出生、存在、成長的,換句話說,“她”就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蘊含著古代賢圣的智慧,不僅為歷史上的中國,而且也為當代中國、并還有可能為世界及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作出獨特的貢獻;雖然我們蒙受過恥辱,但把此歸因于小農(nóng)經(jīng)濟恐怕也不完全客觀:“好人”被“壞人”欺負了,還把原因歸結(jié)為“好人”有缺點,而不去追究“壞人”之壞,沒有看到“壞人”可能、也只能逞兇于一時,這是不是有點兒奇談和短視?[注]雖然這樣一種認識同樣包含著中華文明的智慧之光:我們沒有抱怨、更沒有復仇西方的唯利是圖及其好戰(zhàn)、侵略,而是凡事“三省”自身,認為是由于中國分散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經(jīng)濟基礎(chǔ)和高度集權(quán)但腐敗的上層建筑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人們無視的恰恰是由“壞人”引起的、已經(jīng)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當今社會沒有、也無法解決的各種痼疾,特別是人類面臨的不可持續(xù)問題,而以某個“獨生子女”的慣用口吻“這都什么時代了”來否定過去,把一小盆洗澡水與聰明伶俐的嬰兒一起潑掉,這不僅是不了解中國,也是盲目自卑的表現(xiàn);不僅是崇洋媚外,更是被西方思想和話語“俘虜”甚至“禁錮”的表現(xiàn)。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jīng)濟系教授趙岡認為:小農(nóng)經(jīng)濟對于中國整個經(jīng)濟有重要貢獻,“但經(jīng)濟史的研究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大都持有很深的誤解與不正確的評價。曾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期,學者們認為中國歷史上主要是封建地主制度,小農(nóng)為數(shù)甚少,無足輕重。后來,慢慢有人承認小農(nóng)經(jīng)濟確實占有很大比重,但卻只產(chǎn)生了負面作用。他們認為小農(nóng)經(jīng)濟缺乏穩(wěn)定性,在態(tài)度上保守落后,所以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中國經(jīng)濟停滯落后的主要因素。這些看法與評價既不全面也不客觀”[3]。他覺得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者應該特別重視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經(jīng)驗,仔細閱讀有關(guān)文件,對于家庭農(nóng)場(“小農(nóng)經(jīng)濟”)在中國歷史上的功過應該重新加以檢討、重新評價,給它一個公正而客觀的定位。
一、關(guān)于“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提法: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還是家庭經(jīng)濟
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概念來自馬克思。馬克思把小農(nóng)經(jīng)濟視為歷史上小生產(chǎn)的一種方式,即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中的小生產(chǎn)。在馬克思看來,小農(nóng)經(jīng)濟和小生產(chǎn)是內(nèi)涵基本一致的同一系列的概念,只是涵蓋范圍大小有所差別而已[4]。馬克思明確指出:“這種小生產(chǎn)者包括手工業(yè)者,但主要是農(nóng)民,因為總的說來,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tài)中,只要這種狀態(tài)允許獨立的單個小生產(chǎn)者存在,農(nóng)民階級必然是這種小生產(chǎn)者的大多數(shù)。”[5]672
應該說,馬克思所講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根據(jù)歐洲特別是法德兩國的情況提出來的。發(fā)表于1894年11月的《法德農(nóng)民問題》,既是恩格斯悉心研究農(nóng)民問題的科學結(jié)晶,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小農(nóng)經(jīng)濟理論的集中呈現(xiàn)。馬克思通過對法國的農(nóng)民進行考察,驚嘆于法國小農(nóng)為數(shù)眾多;恩格斯后來對整個歐洲的同一事實也做過類似的描述,他說:“從愛爾蘭到西西里,從安達盧西亞到俄羅斯和保加利亞,農(nóng)民到處都是人口、生產(chǎn)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6]484他們大多是小塊土地的所有者、租佃者,他們耕種的這塊土地既不大于他們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養(yǎng)活他們的家口的限度。不僅如此,“他的祖先就曾經(jīng)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沒有人身自由的農(nóng)民”。此外,在《共產(chǎn)黨宣言》《資本論》《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等一系列重要文獻中,均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深刻論述[7]。由于歐洲與東亞特別是中國的文化幾乎完全不同,由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融合而成的生產(chǎn)方式也有巨大的差異,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是否適合中國國情,這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但遺憾的是,這一概念被學術(shù)界的一部分人想當然地搬用,成為描述中國歷史上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一個基本概念。趙岡教授認為“小農(nóng)經(jīng)濟”這種叫法不科學,是導致小農(nóng)經(jīng)濟就是小規(guī)模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誤解的原因之一。他認為西方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學家使用的“家庭農(nóng)場”一詞比較合適,因為“家庭農(nóng)場”體現(xiàn)了以個體家庭為經(jīng)營單位、獨立決策、自負盈虧的經(jīng)營模式,而且家庭農(nóng)場的規(guī)模可大可小,不一定就是小農(nóng)場或小農(nóng)經(jīng)濟,其規(guī)模取決于諸多因素,如技術(shù)條件等。另外,一個國家總?cè)丝谂c總耕地面積之比也決定著家庭農(nóng)場的平均大小。因此,“總的來說,在中國歷史上人地比例越來越惡化,家庭農(nóng)場規(guī)模越來越小,但是一旦人地比例與技術(shù)條件改變,中國的家庭農(nóng)場也可以變大”[3]。而《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在“筆談”中使用了“中國式小農(nóng)經(jīng)濟”,也是為了與傳統(tǒng)“小農(nóng)經(jīng)濟”區(qū)別開來[1]。不過,筆者認為,中國歷史上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既不是趙岡教授筆下的“家庭農(nóng)場”,也不能簡單地用“中國式小農(nóng)經(jīng)濟”來命名。
其實,從大家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和“家庭農(nóng)場”等概念的理解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類似的經(jīng)濟形式可能具有不同的內(nèi)容,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也造成了彼此之間的理解困難,更不用說準確描述一件事物了。具體來說就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不僅體現(xiàn)不了各國、特別是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本質(zhì),還帶有貶義;“家庭農(nóng)場”雖較客觀,但也沒有體現(xiàn)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本質(zhì);而“中國式小農(nóng)經(jīng)濟”既沒有擺脫貶義的色彩,也難以讓人把握其本質(zhì)。各國歷史上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不僅僅是形式上的類似或不同,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具有不同的內(nèi)容和本質(zhì)。中國歷史上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雖然在形式上可能與其他某些國家差不多,比如說都是以家庭為單位、規(guī)模都比較小,但僅僅從這兩點出發(fā)并以此為基礎(chǔ)展開分析,顯然不是差之毫厘,而是謬以千里了。因為中國的“家”不同于西方的“家庭”,而是“家天下”之“家”,是“國家”之“家”。由此所決定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也不僅僅是規(guī)模大小的問題,而是中國“家”文化的反映,是“國家”的一種體現(xiàn)。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不一定是規(guī)模很小的“小農(nóng)”,而是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規(guī)模;而從文化背景來看,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所表現(xiàn)出的家庭模式既不同于色諾芬等人描述的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完全歸家庭私有、通過實行家庭管理而獲取財富的完全獨立和孤立的家庭農(nóng)場[注]西方“經(jīng)濟”一詞即起源于此。,也不同于馬克思等人所講的在法德農(nóng)村存在的完全孤立、封閉、分散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而更多的是一種雖分田到戶但彼此又相互協(xié)作的利益共同體。換句話說,別人眼中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其實是中國農(nóng)村“大家庭”的一種生活和經(jīng)營方式,彼此之間既不對立也不用等價交換。因此我們認為,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既不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也不是家庭農(nóng)場,而是應該被稱之為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或簡稱為“家庭經(jīng)濟”。因為城市的商品化程度較高,可以被稱之為“家庭經(jīng)濟”的經(jīng)濟形式很少,所以一般也不會引起誤解),既區(qū)別于帶有貶義色彩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又區(qū)別于西方具有現(xiàn)代意義、特別是由于“圈地運動”等形成的經(jīng)營大片農(nóng)田的“家庭農(nóng)場”。與此對比,趙岡教授的“家庭農(nóng)場”中“農(nóng)場”一詞局限太多,既有時間和規(guī)模限制,又有產(chǎn)業(yè)限制。從時間上講,家庭農(nóng)場是一個現(xiàn)代概念,是對現(xiàn)代西方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描述;從規(guī)模上來說,中國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規(guī)模都很小,有“農(nóng)”而無“場”;從產(chǎn)業(yè)上來說,中國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不僅僅包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而是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主的多種經(jīng)營,此時單純一個“農(nóng)”字也代表不了全部。而如果用“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一詞,既可以體現(xiàn)“家庭”經(jīng)營的相對“小”的特點,又在不限制經(jīng)營種類的基礎(chǔ)上體現(xiàn)農(nóng)村和農(nóng)業(yè),同時,也說明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經(jīng)濟形式,既沒有褒貶之分,避免了“小農(nóng)”的貶義,又體現(xiàn)了“經(jīng)濟”豐富的內(nèi)容,成全了多種經(jīng)營如家紡、織布、鐵匠等。不過,為了交流方便,本文在探討時更多地采用“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提法。
二、關(guān)于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內(nèi)涵及其特征:特殊的組織性和社會性
學術(shù)界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內(nèi)涵的諸多分歧決定了其外延的區(qū)別。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chǎn)出現(xiàn)以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對他的生產(chǎn)資料的私有為基礎(chǔ)的小生產(chǎn):小農(nóng)、自由農(nóng)或依附農(nóng)的農(nóng)業(yè)和城市的手工業(yè)。勞動資料——土地、農(nóng)具、作坊、手工業(yè)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他們也照例是屬于生產(chǎn)者自己的。”[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08-309頁。恩格斯也說過:“中世紀社會,個體小生產(chǎn)、生產(chǎn)資料是供個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低的。”同書第441頁。“在小工業(yè)和到目前為止的各處農(nóng)業(yè)中,私有制是現(xiàn)存生產(chǎn)工具的必然結(jié)果。”[6]據(jù)此,有人將小農(nóng)經(jīng)濟界定為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內(nèi)與簡陋的手工工具相聯(lián)系的、以直接生產(chǎn)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chǔ)的、以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的、以勞動的孤立性為特征的小生產(chǎn)。或者說,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農(nóng)業(yè)中以個體家庭為基礎(chǔ)的小生產(chǎn)和小私有的統(tǒng)一。這也就造成了對小農(nóng)是否包含自耕農(nóng)、佃農(nóng)、地主或是家庭農(nóng)場持有異議[4],因為馬克思等界定的“小農(nóng)”是私有制,佃農(nóng)顯然不算是私有制;馬克思界定的“小農(nóng)”屬于自耕農(nóng)式的,有些地主自己不耕種,而將土地出租給農(nóng)民,顯然也就不算是小的、簡陋的、甚至有限的。由此看來,如果我們采用“家庭經(jīng)濟”這一概念,其內(nèi)涵就會寬泛得多,不會出現(xiàn)上述的誤解和分歧。因為家庭經(jīng)濟是一種經(jīng)營方式,并不完全反映和限制其所有制形式;同時,家庭經(jīng)濟雖然規(guī)模不大,但并不一定使用簡陋的手工工具;此外,家庭的規(guī)模有大有小,有的幾世同堂,有的則獨立門戶,也不一定是“個體家庭”和孤立生產(chǎn)。
由此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論述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一些特征也就不一定反映中國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的情況。馬克思恩格斯比較一致地認為,分散、孤立、不科學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痼疾。“在這種生產(chǎn)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個自由的土地所有者,還是一個隸屬農(nóng)民,總是獨立地作為孤立的勞動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產(chǎn)自己的生活資料。”[5]909“這種生產(chǎn)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chǎn)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2]830,“在勞動孤立進行和勞動的社會性不發(fā)展的情況下,直接表現(xiàn)為直接生產(chǎn)者對一定土地的產(chǎn)品的占有和生產(chǎn)”[5]715,“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不是社會勞動,而是孤立勞動”[5]916。這種生產(chǎn)形式“排斥協(xié)作,排斥同一生產(chǎn)過程內(nèi)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tǒng)治和支配,亦即排斥‘勞動的社會形式’”[5]910,“一小塊土地、一個農(nóng)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nóng)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內(nèi)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shù)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同時,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里,小農(nóng)經(jīng)濟以其非科學化、非積累化和脆弱性等表征了其落后性[7],認為“它既排斥生產(chǎn)資料的積聚,也排斥社會生產(chǎn)力的自由發(fā)展,使擴大再生產(chǎn)幾乎不可能”[2]830。實際上,一方面,中國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是“分”而不“散”,獨立但不孤立。中國的農(nóng)民盡管在形式上采取了與法德同樣的生產(chǎn)方式,也是分散經(jīng)營小塊土地,但是彼此之間是有著血緣和親族關(guān)系的、具有密切關(guān)系的一個團體,彼此之間不僅不排斥協(xié)作,而且還形成了一種比較緊密而且不計報酬的協(xié)作關(guān)系——中國農(nóng)村普遍存在著相互“幫忙”:不管是農(nóng)忙季節(jié),還是家里有婚喪嫁娶,不管是生病,還是蓋新房,都不乏熱鬧的場面——事實上這是不約而同的,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有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考古發(fā)現(xiàn)的情況更證明了這種組織內(nèi)部的協(xié)作能力,“在晉南、豫西地區(qū)的一系列超大規(guī)模的史前城址如山西陶寺、河南新密古城寨及新砦等遺址的發(fā)現(xiàn),更是表現(xiàn)了這些與土地打交道的中原先民驚人的協(xié)作與社會動員力量”[8]。另一方面,如果說到“科學”“積累”等問題,兩者的區(qū)別更為明顯:中國農(nóng)民的“科學”體現(xiàn)在利于持續(xù)發(fā)展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中國農(nóng)民的“積累”體現(xiàn)在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和知足常樂上,既不同于歐洲的對內(nèi)“羊吃人”和對外“地理大發(fā)現(xiàn)(擴張)”,也沒有發(fā)明歐洲列強的“堅船利炮”和不知疲倦的唯利是圖的習氣。此外,后面的分析將說明,正是這種家庭經(jīng)濟模式實現(xiàn)了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交易費用”——這可能不是“科學”而應屬于“智慧”。
小農(nóng)經(jīng)濟確實存在著脆弱性,馬克思恩格斯曾寫道:“小生產(chǎn)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chǎn)條件,則取決于無數(shù)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或喪失,都意味著貧困化,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對小農(nóng)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guī)模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chǎn)。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5]678。但中國的家庭經(jīng)濟則不同,正是由于中國農(nóng)民之間以“家”為基礎(chǔ)和紐帶形成了一種非常緊密的相互協(xié)作關(guān)系,使彼此之間既相互依賴又相互“溫暖”,互相扯皮、互挖墻腳的情況不是沒有,但相對較少。這就是過去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在小塊的土地上創(chuàng)造的溫馨與浪漫的奇跡。有了這樣的“家庭”觀念,有了具體的團結(jié)協(xié)作,特別是有了無私的幫助,也就與馬克思所說的情形有所不同:“數(shù)百萬家庭的經(jīng)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nóng)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lián)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guān)系,形成全國性的聯(lián)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9]217。也正因為如此,中國迄今沒有出現(xiàn)如此的情況:“資本主義的大生產(chǎn)將把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chǎn)壓碎,正如火車把獨輪車壓碎一樣是毫無問題的”[10]501,雖然家庭經(jīng)濟的形式確實在改變。
近年來,人們在馬克思、恩格斯論述的基礎(chǔ)上,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特征從其他角度進行了描述。馮小紅認為:“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一種分散、狹小的個體生產(chǎn),每家農(nóng)戶是一個獨立的生產(chǎn)單位,彼此之間在經(jīng)濟上沒有任何有機的聯(lián)系。”[11]仲亞東認為:“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條件下,家庭為經(jīng)濟活動的基本單位,家庭執(zhí)行生產(chǎn)決策、配置資源和分配收益等多項職能,性別分工是其主要體現(xiàn)。”[12]楊華在與英國大工業(yè)、美國大農(nóng)場比較之后,認為中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基本特征是小規(guī)模的經(jīng)營組織方式、精耕細作式的農(nóng)業(yè)耕作、農(nóng)副業(yè)結(jié)合的家庭經(jīng)濟、家庭內(nèi)部的男女勞動性別分工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chǎn)傳統(tǒng)等[13]。顯然,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的描述是針對和反映歐洲的實際的話,那么后人的這些描述雖然針對的是中國,但反映的只是中國的表面現(xiàn)象,并沒有指出中國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根本特征。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說,中國的小農(nóng)看起來分散,但實際上有其組織性。就土地來源看,它是以土地公有制(國有制或者公社所有制)為基礎(chǔ),農(nóng)民通過租佃、承包等形式分散經(jīng)營的一種經(jīng)濟形式。其中,不乏農(nóng)民自己開墾自己耕種的私田,更有租用地主的土地,但更多的是分配的公田,尤其是在封建社會初期及之前時期較常見;就家庭和勞動力的存在和運作形式看,中國的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不像歐洲的完全私有基礎(chǔ)上的分散和無組織無紀律,也不同于發(fā)端于歐洲的契約組織,而是在“家天下”背景下國家對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的一種組織形式;從經(jīng)營形式看,這種經(jīng)濟形式也是在當時條件下的一種最優(yōu)選擇——當時的土地等資源有限,人口也有限(這里不是人口少了,而是相對太多),但不能餓死(以人為本),當時的市場(沒有市場,而且市場也解決不了問題)有限,這意味著勞動力就業(yè)無從選擇,生產(chǎn)資料(土地)無從選擇,人民的物質(zhì)生活來源無從選擇。這些“無從選擇”的問題在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看來都是落后的,但市場經(jīng)濟的這種所謂先進的經(jīng)濟形式和經(jīng)濟制度所造成的一系列新問題則是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與此相對比,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這種特殊的組織形式卻很好地解決了現(xiàn)代市場所造成的問題:以“家”的方式解決了充分就業(yè)問題,保證了中國社會相對穩(wěn)定的過渡,避免了西方式的“羊吃人”的自我殘殺和對外侵略。另一方面,馬克思所說的“孤立勞動”是相對于商品生產(chǎn)和交換來說的,他用商品經(jīng)濟的眼光定義“社會勞動”,涵蓋不了中國這種家庭經(jīng)濟的起源,未能解釋在這種經(jīng)濟條件下人們之間的關(guān)系并非商品交換的等價關(guān)系,而是家庭內(nèi)部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互協(xié)作關(guān)系。社會勞動的形式有多種,商品生產(chǎn)和交換是一種,互幫互助也是一種。顯然,中國式的小農(nóng)家庭勞動,表面上看是孤立的,實際上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非商品交換的關(guān)系,所謂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指的是沒有商品交換,沒有勾心斗角、爾虞我詐,而不是沒有交往。
此外,現(xiàn)階段家庭經(jīng)濟的內(nèi)涵和特征也與時俱進。隨著土地流轉(zhuǎn)和農(nóng)民進城務工,農(nóng)村實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規(guī)模化經(jīng)營,自給自足、缺乏商品交換等特征也隨著時代變化而逐漸隱去,在以城鄉(xiāng)互動為特征的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進程中,農(nóng)民已經(jīng)或主動或被動地融入市場經(jīng)濟。這既構(gòu)成與以往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區(qū)別[14][15][16],也體現(xiàn)出中國家庭經(jīng)濟的獨特之處:它正像中國文化,既不拒絕、不排斥任何進步的、外來的變革,也不失自己本來的精神。
三、關(guān)于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起源:“家天下”的必然
正如大家所一致認為的,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chǎn)和消費,因此,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起源最早應該追溯到個體家庭的形成[4]。從世界范圍看,個體家庭的分散勞動和獨立經(jīng)營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即已出現(xiàn),恩格斯也談到交換如何使公社分化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團,即“家長仍舊是勞動農(nóng)民:他們靠自己家庭的幫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產(chǎn)他們所需要的幾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產(chǎn)品同外界交換來的”[5]1015。不過,恩格斯所說的這些情況并不適用于中國。因為中國并不是一開始就從氏族和部落分成一個個獨立的小家庭,而是一直以氏族和部落的形式存在,中國沒有從“公天下”分解為“私天下”,而是轉(zhuǎn)變成“家天下”。這恐怕是中國與歐洲相比最獨特的一點,也是決定日后中西道路、制度、文化不同的最根本之處。但從普遍意義上講,把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追溯到個體家庭的出現(xiàn)應該是有道理的。
學術(shù)界關(guān)于中國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起源時間的研究較少,目前也無明確統(tǒng)一的答案,但均認為很早就產(chǎn)生并長期存在。李根蟠結(jié)合小農(nóng)經(jīng)濟家庭經(jīng)營和生產(chǎn)資料私有的特征,在梳理相關(guān)歷史文獻的基礎(chǔ)上,指出中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歷史應該從黃帝堯舜時代算起,因為當時的農(nóng)業(yè)已經(jīng)是以個體家庭為基礎(chǔ)的小生產(chǎn)和小私有的統(tǒng)一[4]。饒夏圻則將小農(nóng)經(jīng)濟推遲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認為作為一種重要的經(jīng)濟形式,小農(nóng)經(jīng)濟大體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但并未給出其考據(jù)理由[17]。趙岡也認為,從文獻上判斷,春秋時期已經(jīng)實行了家庭農(nóng)場制,即分田到戶,到了戰(zhàn)國時期,分田到戶的土地已逐漸私有化。
比起源的時間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是如何起源的,換句話說,為什么這種經(jīng)濟形式會在中國出現(xiàn)。解決這一問題,可能不得不“借助”中國的制度基礎(chǔ)和思想文化根源。
中國的文明是從氏族和部落延續(xù)下來的一種文明,始終有著氏族和部落的觀念和概念,其文化及其后來的經(jīng)濟社會形態(tài)正是這種氏族和部落觀念的反映和延續(xù)。這樣一種氏族和部落,既是一種組織,又是一種血緣或以血緣為基礎(chǔ)的群體,更是一種理念或以理念為基礎(chǔ)的文化的反映,具體就體現(xiàn)為“家”及其觀念。這樣一種“家”的集合體決定了道德觀念的興起和延續(xù)——即德高望重、德位相適、“為政以德”,決定了“弟子之規(guī)(也即尊卑長幼之序及其規(guī)矩)”,從而也決定了“家天下”而非“私天下”的形式和內(nèi)容。因為“家”是血緣的延續(xù),是氏族和部落的延續(xù),是理念和文化的延續(xù)。
有了“家”(家的觀念和形式)就有了“家天下”(家天下的形式和內(nèi)容),有了“家天下”就有了“家庭成員”(和非家庭成員:俘虜、奴隸等),也就有了上下分層、同層分封的需要和制度體系。這樣一種制度體系在上層通過分封制形成了各個諸侯國,而到了最下層,必然是分田到戶,形成以小家庭為單位的家庭經(jīng)濟。顯然這種制度及其結(jié)果既是“家”的關(guān)懷,又是“家”的體現(xiàn),還是“家”的溫暖,也是無商品交換的必然。因為一是采用“均分”的辦法,既體現(xiàn)得到者是“家”的一員,又體現(xiàn)內(nèi)部公平;二是雖然表面公平,在同一個家庭內(nèi)部沒有你我,不分彼此,但實際上“父母”對“子女”是“公而不平”。所謂“公”是為了家庭,為了全家;所謂“不平”是有感情的親疏遠近和能力強弱之分,即使都是親生的子女。因為有了這樣一種觀念上的區(qū)別,而這種區(qū)別又是在“家里”,不是“外人”,這就出現(xiàn)了所謂的“平調(diào)”:在父母看來,這是左手與右手的關(guān)系,而不是你我關(guān)系,更不是內(nèi)外關(guān)系。富的照顧貧的,強的照顧弱的,疏遠的照顧親近的,這是天經(jīng)地義,不能考慮所謂的“等價交換”。由此決定了中國的“家”成為最高理念,“國家”是一國之“家”、各家之“國”,皇帝既是國家之主也是各家之主。各家之間沒有、不能、也不需要商品交換的形式。
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口的增多,中國的家庭規(guī)模也經(jīng)歷了從大到小的分化過程,就像我們過去的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到現(xiàn)在三口之家的演變。曹兵武對中國北方和南方的房屋面積、灶臺數(shù)量的考察也說明了這種演變。他說,從舊石器時代開始,黃河中下游的早期農(nóng)村就表現(xiàn)出以核心家庭為基本生活單位、注重家族團結(jié)和村落向心而出現(xiàn)人口和聚落規(guī)模較大的趨向。到了新石器時代,仍然存有濃厚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群居和共同生產(chǎn)與生活的積習。至于南方地區(qū),可能也存在著與中國北方相似的文化發(fā)展過程,例外的情況是黃河中下游地區(qū)與這個階段相當?shù)呐崂顛徫幕瘯r期(屬于新石器早期),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已經(jīng)成為遺址中最主要的房屋遺存,暗示著可能這里比較早就開始了生活生產(chǎn)單位向核心性小家庭的過渡進程。他認為,從裴李崗時期歷經(jīng)仰韶時期與龍山時期,中原地區(qū)社會生活中必要的公共領(lǐng)域不僅存在,而且在不斷地完善和推陳出新。仰韶文化中突出于多座小房子之上的大房子是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不但有全村一級的大房子,同時一個遺址中往往包含多個中間層次社會組織共享的具有高臺、回廊一類的較大房子。他強調(diào)了在晉南、豫西地區(qū)的一系列超大規(guī)模的史前城址如山西陶寺、河南新密古城寨及新砦等遺址的發(fā)現(xiàn)表現(xiàn)出的這些與土地打交道的中原先民驚人的協(xié)作與社會動員力量[8]。這說明了一個村莊與家庭的關(guān)系:一個村莊一般以一個家庭(一姓)為主,這個家庭按照輩分逐步分級,形成了多個分支,這就是所說的“中間層次社會組織”。每一個層級(輩)都會逐步下分,有道德、有能力者把大家籠絡在一起,形成一個相對較大的“小家庭”,而沒有道德、沒有能力的,干脆就在兒女成家后就分家(俗稱“另家”,即另立門戶),因此而形成了一個一個更小的家庭。這些更小的家庭平時分戶單干,在重大節(jié)日、婚喪嫁娶時就要集中在被稱為“祠堂”或者最高輩分、最有權(quán)威、最德高望重的人家里,通常這個地方也比較大,能容納較多的人“開會”或商議決策。仰韶文化早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不同層次的大房子統(tǒng)領(lǐng)若干座小房子聚族而居的現(xiàn)象,顯然是最基層的核心小家庭及介于村落(部落)之間的家族組織的體現(xiàn)。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龍山時代,中國各地的文化面貌發(fā)生了若干根本性的變化,出現(xiàn)了四級左右的聚落分層結(jié)構(gòu),較大的聚落遺址往往是帶圍墻的城址等,人們對同一聚落占據(jù)的時間比以前有所延長;大規(guī)模的合葬墓讓位于單人葬,個體之間的差別也在同一墓地之中清晰地表現(xiàn)出來,社會已經(jīng)具有了金字塔式的結(jié)構(gòu)。從經(jīng)濟形式看,在這個大變動和重新組合的時代,中原地區(qū)是在一種相對發(fā)達和徹底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完善的家族與聚落組織和龐大的人口規(guī)模等基礎(chǔ)上進行的。社會的金字塔結(jié)構(gòu)的底部不僅變化較少,而且承擔了一個支撐新興的貴族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穩(wěn)固的基礎(chǔ)。一直到商代,面積在幾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依然在宮殿式的房子周圍并存,并且是構(gòu)成考古發(fā)現(xiàn)中普遍使用的房屋的主體,正是暗示了這樣一種現(xiàn)象[8]。
而根據(jù)李根蟠的考察,夏商尤其是商代存在“族”的組織是十分清楚的事實。夏商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被稱為“眾”或“小人”的小農(nóng)是與貴族奴隸主同一部族或同盟部族之人。族之下有“宗氏”(宗族),宗氏之下有“分族”(大家族),分族中有“類丑”(同族人及奴隸)。同一族的人在原始社會里本是平等的,但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就發(fā)生了分化,形成了“君子”和“小人”這兩個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階級。這種狀況有著悠久的歷史。不過,“小人”雖然是處于社會下層的勞動者,備受壓迫和剝削,有時甚至到了嫁妻鬻子的地步,但他們畢竟不是奴隸,他們保持了比奴隸更高的經(jīng)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因受洪水威脅,盤庚遷都于殷,遷都前盤庚召集民眾訓話,申述了“視民利用(以)遷”的衷曲,一方面對不服從命令的民眾進行恫嚇威脅,另一方面又套近乎,聲稱“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善也)民”,并許諾“往哉生生!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尚書·盤庚中》)。這些“民”顯然與商朝統(tǒng)治者屬同一族體,有一定政治地位,并有自己的獨立家庭與生計。夏商小農(nóng)既從屬于族的組織,又生活在農(nóng)村公社之中,這是夏商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又一顯著特點。李根蟠認為,我國上古時代的井田制就是農(nóng)村公社及其變體。當時為了大規(guī)模開發(fā)黃河流域的低平地區(qū),依靠集體的力量修建了農(nóng)田溝洫系統(tǒng),并形成了土地公有私耕的農(nóng)村公社,這就是原始的井田制。史稱黃帝“明民共財”(《國語·晉語四》),以致“農(nóng)者不侵畔”,應該理解為建立了農(nóng)村公社的份地制[4]。
中國在春秋時期存在的土地所有制關(guān)系也體現(xiàn)了“家天下”的具體管理方式。巫寶山認為中國在春秋末期存在著國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三種土地所有制關(guān)系形式[18],其中的“國有制”實際上是土地的國君所有制,公有制可以理解為氏族貴族所有制,也就是氏族宗社公有制。他認為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甚至到漢代,依然存在著公有制,土地所有制主要是氏族共有,井田制是其表現(xiàn)形式。他所說的私有制是指商鞅變法后所形成的耕者有其田的個體農(nóng)戶所有制。由于商鞅變法廢除了封建,國君的土地又伴隨著對外擴張越來越大,必須確保擁有盡可能多的勞動人口以保證土地不被撂荒,于是將國君的土地劃分給個體農(nóng)民耕種,這就是對于后世小農(nóng)經(jīng)濟影響最大者——“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此外,由于秦國相較于中原地區(qū)諸國社會發(fā)展落后較多,保留著較多的氏族社會的大家庭制度,因此,商鞅變法的內(nèi)容之一就是強行拆分氏族時代的聚族而居的家庭形式——實行小家庭。這種小家庭的劃分最重要的結(jié)果是帶來財產(chǎn)的平均分配,代際之間、財產(chǎn)特別是土地的所有權(quán)會隨著人口的繁衍日益縮小。
由上可以看出,中國至少從黃帝開始就算是“統(tǒng)一”[注]這里的“統(tǒng)一”當然不是現(xiàn)在的概念,也就是地域沒有現(xiàn)在這么大,但相對歐洲那種城邦國家,這已算是很大的國家了。的大國。在這樣一個文明國家,土地是唯一的生產(chǎn)資料,歸以君王為代表的全體成員(不包含俘虜和奴隸)所有。但這種“公有”或“共有”制無法實現(xiàn)有效的生產(chǎn)(耕作),所以只能層層分配;而為了配合耕種,就以溝洫為基礎(chǔ)實行了井田形式。中華民族自古強調(diào)“以民為本”,當時主要的力量不是以武器為代表的工具而是人,所謂人多力量大,所以君王沒有舍棄這些本來是同族的農(nóng)民。而有了人就要為其提供生活和生產(chǎn)的條件,這樣,通過井田制把農(nóng)民固定在土地上則是一舉多得:農(nóng)民不僅可以自食其力,而且可以提供有效勞動,降低監(jiān)督成本,同時又可以減少因人口流動而帶來的社會不安定問題;此外,國家既有了勞動力又有了財政(租金)收入,而且國家對農(nóng)民的管理也方便了。由于有了這種有效管理和耕種方式,促進了生產(chǎn)的發(fā)展、人口的增加,但土地面積是有限的,只能按人口分配,所以隨著人口的增多,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規(guī)模就越來越小。
四、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長期持續(xù)的原因:“家”文化的載體
中國的這種家庭經(jīng)濟形式不僅產(chǎn)生很早,而且持續(xù)至今,其中原因顯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簡單地靠所謂的封建統(tǒng)治就能實現(xiàn)的。從歷史的情況看,正是由自身的特點和當時的自然、社會條件所決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采取了家庭經(jīng)濟的經(jīng)營模式;而從現(xiàn)實來看,特別是從人類可持續(xù)發(fā)展這樣一個大的角度來看,其優(yōu)勢也不是現(xiàn)代商品經(jīng)濟所能比擬的。總的來說,中國的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實際上是中國“家天下”智慧的反映和中華文明的象征。
第一,最高的效率與最優(yōu)的制度安排。首先,從現(xiàn)代西方經(jīng)濟學的角度看,家庭經(jīng)濟模式使“交易費用”和工作效率都達到了最理想狀態(tài)。按制度學派的說法,企業(yè)生產(chǎn)的現(xiàn)場監(jiān)督和質(zhì)量管理都是交易費用的一部分[注]現(xiàn)代西方經(jīng)濟學從唯利是圖的生產(chǎn)目的出發(fā),依據(jù)邊際理論,提出并論證了一個組織應達到最佳規(guī)模和最高效率,由此認為企業(yè)規(guī)模一般是越大越好,“大而不倒”。趙岡教授認為,一個企業(yè)實際上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隨部門特征和技術(shù)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他說就農(nóng)場規(guī)模而言,目前的技術(shù)條件可能達到或接近最佳規(guī)模,但過去的條件決定了“最佳規(guī)模”肯定是要小得多。趙岡教授認為,歐美的農(nóng)業(yè)政策一向是鼓勵支持家庭農(nóng)場,即因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要求的最佳規(guī)模都不大;一般的種植業(yè)生產(chǎn)工作都是在耕地上平面展開,而不能像工業(yè)生產(chǎn)那樣在一個較小的空間集中作業(y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過程和產(chǎn)品也不能像工業(yè)生產(chǎn)及其產(chǎn)品那樣標準化。因此家庭農(nóng)場的特點適應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參見趙岡:《重新評價中國歷史上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載《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1994年第1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特點決定了其如果沒有好的制度設計,將會造成交易費用極高且生產(chǎn)效率還極低。而家庭經(jīng)濟模式就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不論是與工業(yè)還是與現(xiàn)代農(nóng)場相比,古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在沒有機動和監(jiān)控設備的情況下主要靠人的勤快與“天”的恩賜吃飯,產(chǎn)品質(zhì)量也要“聽天由命”,因此生產(chǎn)過程和農(nóng)產(chǎn)品的質(zhì)量都不好把控。如果實行大農(nóng)場和集體耕種,勢必需要大量的監(jiān)工,而即便如此,生產(chǎn)效率也無法保證。據(jù)趙岡教授的考察,歐洲歷史上的大農(nóng)場,包括羅馬的那些latifundia,其效率之低下,已不乏記載,每年不知浪費多少人力于農(nóng)地現(xiàn)場監(jiān)督,直到近代在機動車輛及電訊設備出現(xiàn)以前,也只有那些在平原上大面積生產(chǎn)單一作物的種植園(plantation)才勉強解決監(jiān)工難題,把監(jiān)督費用壓縮到合理范圍之內(nèi)。其實,中國歷史上就遇到過大農(nóng)場勞動“出工不出力”的情況,如《呂氏春秋·審分》記載:“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公羊傳》(何休注)道:“民不肯盡力于公田”,都明白指出家庭農(nóng)場以外的監(jiān)督問題與耕作者之態(tài)度。趙岡教授的研究認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監(jiān)督費用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尤其突出。中國不像歐洲,有廣大的平原發(fā)展成農(nóng)業(yè)區(qū)。中國早期在華北地區(qū)及西北高原的農(nóng)耕區(qū),因為地形結(jié)構(gòu)造成排水狀況不良,又因為雨量大多集中于夏季作物生長期,暴雨無法快速宣泄,不解決排水問題便難以發(fā)展農(nóng)業(yè)。于是政府以集體的力量,在農(nóng)耕區(qū)修筑了密集排列的溝渠,以便改善地面的排水狀況。其結(jié)果是農(nóng)田被縱橫分布的溝渠切割成零星小塊,田間之交通遠比在大塊平原上更費時,監(jiān)督工作自然也更困難。在那種狀況下,若真如某些學者所想象,驅(qū)使上萬名奴隸去耕作,不知該動員多少兵力去監(jiān)督。所以,當時的天然環(huán)境促使中國選擇可行的耕作制度與組織。趙岡教授特別指出:“我們也見識了以政治教育來代替激勵機制的做法,其交易費用更可觀(大大小小的會)而效果不佳。”[3]既然如此,最好的辦法就是盡量利用工作人員自發(fā)的工作意愿來代替自上而下的監(jiān)督工作,這時家庭經(jīng)濟形式就發(fā)揮了特長:家庭經(jīng)濟靠家庭成員來勞動,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只需(甚至不需)最低限度的監(jiān)督工作,所以交易費用最少。不僅如此,家庭經(jīng)濟形式還可以有效調(diào)動家庭成員的生產(chǎn)積極性,提高生產(chǎn)效率。在家庭經(jīng)濟中,家庭成員自動自發(fā),不分晝夜,辛勤操作——芝加哥大學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T.W.Schultz)認為家庭農(nóng)場可以點土成金,即基于此種考慮。分田到戶以后,家庭成員有自發(fā)的工作意愿,《管子·乘馬》形容是“是故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這恐怕就是歷史上的家庭經(jīng)濟政策起源與形成的直接原因。曹兵武也看到了“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這一優(yōu)勢,指出“小的核心家庭作為基本的生產(chǎn)生活單位,確實有利于調(diào)動一般人生產(chǎn)生活的積極性,有利于人口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而且為社會組織的理性發(fā)展和培養(yǎng)提供了較大的余地”[8]。趙岡教授認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當政者已經(jīng)對家庭農(nóng)場的優(yōu)點有深入的認識。李悝曾指出五口之家,治田百畝,總產(chǎn)量一百五十石,全家食用九十石,其余的六十石用以納稅及市場銷售,其自我消費率是60%,余糧率高達40%,這表明生產(chǎn)效率可觀。到了歷史后期,中國的小農(nóng)戶越來越窮,這是人口過量增加、人地比例嚴重失調(diào)的后果,不能歸罪于生產(chǎn)組織。李悝所說的“農(nóng)夫之困”與后來小農(nóng)戶之“窮”,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情況,不可相提并論。他說,與歐洲比較,直到明清為止,中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是最先進的,產(chǎn)量遙遙領(lǐng)先歐洲,這主要是拜家庭農(nóng)場所賜,比起歐洲的莊園制度,效率高出許多。歐洲各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是在現(xiàn)代化投入出現(xiàn)以后才慢慢趕上中國,終于走到前頭。中國沒有自己發(fā)明農(nóng)業(yè)機械、化學肥料、農(nóng)藥、雜交育種等農(nóng)業(yè)科技[注]其中的一些農(nóng)業(yè)科技,從眼前看確實有益,但從長遠看,特別是從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來看是否有益,還需要進一步的論證。,罪不在家庭農(nóng)場之組織,即令在歐美,這些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科技也都不是農(nóng)戶自己發(fā)明的。農(nóng)業(yè)機械是內(nèi)燃機發(fā)明后的產(chǎn)物,農(nóng)藥、化肥是實驗室中產(chǎn)生的,雜交育種是達爾文及孟德爾等人的生物理論所引導出來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學術(shù)導向與思維方式,是不會發(fā)明這些事物的。我們不應歸罪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組織,認為它是農(nóng)業(yè)科學與生產(chǎn)技術(shù)落后停滯的罪魁禍首[3]。
此外,正如前述,家庭經(jīng)濟形式也是“不得不”的選擇。如果說降低監(jiān)督費用、提高生產(chǎn)效率是從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角度進行的分析,也是對“國”對“家”都有利的事情,那么實際上,家庭經(jīng)濟形式也是由當時的資源(土地)和人口條件所決定的:在適宜耕種的土地資源有限、而人口又比較多的情況下,人們?yōu)榱松顩]有別的選擇,只能耕種土地,而耕種土地又不能采取“大呼隆”的方式,最好是分田到戶,自食其力。這表明家庭經(jīng)濟模式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第二,是中華民族智慧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上述表明早在數(shù)千年前的中國就已經(jīng)解決了西方經(jīng)濟學直到19世紀中后期才根據(jù)邊際效用提出的最佳規(guī)模、最高效率等問題。不過,如果僅僅沿著“別人的”思路探討,認為中國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長期持續(xù)的原因在于這一優(yōu)勢,就還是屬于“局外人”的表象觀察,不能真正揭示其中包含的智慧(而非聰明):自然性和要素性。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花”是世界之花,“葉”是菩提之葉;“世界”是花的世界,“菩提”也是葉的菩提。所謂家庭經(jīng)濟的自然性,是就其生存和發(fā)展的整個環(huán)境即“世界”和“菩提”來講的;而所謂家庭經(jīng)濟的要素性,是就其成為當時社會經(jīng)濟和生活的一種存在形式即“花”“葉”來講的。家庭經(jīng)濟不是一種獨立的存在物,不是外生而強加給中國社會的,也不是哪一個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是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條件使然,也是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條件共同作用的一個縮影、一種反映。中國是一個“國家”,是一個以“國”的形式存在的“家”,也是以“家”的形式管理的“國”[注]與此相對應,西方的“國家”可以說是以利益契約為紐帶而形成的“成功家庭”聯(lián)合體。,“國”可以分為多個層次的“家”,“國”是最大的“家”,“小家”與“大家”相互融合而構(gòu)成了“國家”,“國家”按輩分和親疏遠近細分而形成了“小家”。所謂的“家國情懷”即來源于此,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即鐘情于此,現(xiàn)在所談的家庭經(jīng)濟也生存于此。因此,弄不清楚中國的“家文化”,就不明白中國的“家天下”,而不明白“家天下”,也就很難論述清楚包括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在內(nèi)的中國各要素的特性和存在的必然性。中華民族的智慧就包含在“家”中。
如果上面說的家庭經(jīng)濟形式是一種“不得不”的制度安排的話,那么實際上,中國的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飽含著人類的最高智慧和最大愛心:中國在從“公天下”分化的過程中既沒有采取西方式的“圈地運動”而驅(qū)趕、殺戮農(nóng)民,也沒有不管不顧農(nóng)民而任其自生自滅,而是在實行“家天下”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時深明“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民為貴,君為輕”“民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之理,踐行“以民為本”,認為“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19],“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因此,對皇親國戚分封為諸侯,對平民百姓分田到戶,使其盡人力與地力,自食其力而又量力而行。而對于廣大的農(nóng)民來說,他們都是“國”這個“大家”的成員,應該得到“大家”的關(guān)心:由于實行分田到戶,自己有了土地,就實現(xiàn)了農(nóng)民與生產(chǎn)資料(土地)的直接結(jié)合,不僅勞有所得,而且可以多勞多得,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只要賦稅不是太重,只要剝削不是太苛刻,他們就會知足常樂、安居樂業(yè),而不會暴動起義。所以從總體來看,中國社會持續(xù)穩(wěn)定,歷朝歷代都曾出現(xiàn)繁榮和盛世,這與統(tǒng)治者的開明分不開,更與廣大農(nóng)民的安定分不開,當然也與中華文明與中國智慧分不開[注]現(xiàn)在的西方人也很聰明,他們在通過“圈地”和侵略而實現(xiàn)了資本原始積累之后,開始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把失敗的責任都推給了百姓,從而使百姓在既不安居又不樂業(yè)的情況下“默默承受”社會的選擇。。
一些人試圖揭示中國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持續(xù)存在的緣由,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探索十分有限[16][20],原因可能就在于一些研究總是觸其“膚”而不得其“心”。如李桂海、徐新吾試圖從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特征(其實是結(jié)果)中尋找理由,認為自給自足的性質(zhì)意味著小農(nóng)戶可以根據(jù)外部條件和經(jīng)營狀況調(diào)整家庭的收支限度;以手工業(yè)和畜禽養(yǎng)殖相結(jié)合的復合經(jīng)濟表明小農(nóng)戶可以優(yōu)化資源配置,減少外部沖擊帶來的破壞;封閉排他性決定了小農(nóng)戶的風險規(guī)避性,他們很少愿意將剩余農(nóng)產(chǎn)品拿到市場上交易,而是先儲藏起來以應對生產(chǎn)生活的風險。因此,小農(nóng)經(jīng)濟盡管非常脆弱,但是也表現(xiàn)出極強的再生產(chǎn)能力。中國小農(nóng)家庭更高的獨立性和較少的人身依附性,導致自身更大的凝固性,構(gòu)成了中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長期存在的經(jīng)濟理由[21][22]。馬開棵、陳曦主要從政治角度加以剖析,認為中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長期存在主要是因為歷史上的地主階級及統(tǒng)治者長期推行的重農(nóng)抑商政策,長期存在的封建制度加固了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生存基礎(chǔ)[23][24]。饒夏圻認為中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長期存在得益于三方面的原因:封建土地所有制構(gòu)成了小農(nóng)經(jīng)濟長期存在的物質(zhì)基礎(chǔ),簡單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條件以及高度的自然適應性特征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長期存在的內(nèi)在原因;而重農(nóng)抑商、懷柔和培植自耕農(nóng)等政策則構(gòu)成其外在原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則是終極原因[17]。楊德才等從交易效率的視角探討,認為主要歸因于中國歷史上分工與市場交易的缺乏,而其深層次原因則在于小農(nóng)經(jīng)濟自給自足的特性以及社會分工程度的低下[20]。可以看出,這些分析猶如霧里看花,并沒有給予充分的解釋。至于葛頌等人認為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結(jié)束戰(zhàn)亂營造了思想和輿論基礎(chǔ)[25],則顯然不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長期存在的原因,而是這種經(jīng)濟模式存在的一種效果。從歷史經(jīng)驗看,安定天下的最好方式就是民有所作、民有所得、民食其力,而在農(nóng)業(yè)文明時期,特別是在農(nóng)田有限的情況下,實行家庭經(jīng)濟形式是最好的選擇。在農(nóng)耕時代,土地是唯一的生產(chǎn)資料,讓農(nóng)民擁有土地,不管是所有還是占有,既是發(fā)揮農(nóng)民個人積極性的基礎(chǔ),也是把農(nóng)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實現(xiàn)社會穩(wěn)定的條件,同時還是國家增加收入的來源。對于廣大小農(nóng)來說,“天高皇帝遠”,其所關(guān)心的只是他所在“公社(村莊)”的安定,因為公社(村莊)安定,農(nóng)民的地就安定,地安定了,生活也就安定了。這才是智慧的運用,是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統(tǒng)一而非割裂。
第三,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人類產(chǎn)生以來,曾出現(xiàn)了多個“文明”,其中又以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為代表。在這些古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得以保存至今,并展現(xiàn)出勃勃生機。無數(shù)學者、專家探討其他文明消失的原因時,試圖揭開中華文明延續(xù)和發(fā)展的秘密,但至今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jié)論。其實,文明既不是發(fā)明創(chuàng)造,也不是誰的恩賜,更不是統(tǒng)治者的規(guī)定,而是人類日常生活的總結(jié)和結(jié)晶。也就是說,文明源于生活,長于生活,而生活又在于人。凡是與人類生活緊密結(jié)合、反映人類生產(chǎn)生活規(guī)律、適應人類生活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才得以保留并延續(xù);而那些不適應人類生活、甚至脫離人類生活的東西,即便在當時被封為“圣典”,也將是曇花一現(xiàn)。依此我們來分析和判斷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三大文明消失的原因。古埃及文明以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為其象征,雖然獅身人面像代表了勇敢和智慧,但金字塔所代表的“階層”和“統(tǒng)治(地位)”才是其根本;古巴比倫文明以《漢謨拉比法典》和“空中花園”為其象征,雖然其中的“空中花園”不乏建筑、生物、水利等文明成就,但《漢謨拉比法典》的嚴苛更代表了古巴比倫王國“統(tǒng)治”的殘酷;古印度文明以婆羅門教和瓦爾納種姓制度為其象征,雖然后期產(chǎn)生了佛教,但“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墻內(nèi)”統(tǒng)治依然堅固——婆羅門教本身就是瓦爾納制度的依據(jù)。由此可以看出,這三大古國如果算得上是“文明古國”的話,其文明也只能算是“統(tǒng)治文明”:或者是統(tǒng)治者的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倫;或者是為統(tǒng)治者“制定”的文明,如古印度。既然是統(tǒng)治文明,而統(tǒng)治(者)是常變不定的,因此,其“文明”也必然隨著統(tǒng)治(者)的變更而變更,隨著統(tǒng)治(者)的崩潰而消亡。
與此相對照,中華文明則以儒家文化為其代表和象征,而儒家文化正是建立在“家”的基礎(chǔ)之上,是“家”存在的需要,也是維護“家”的秩序的體現(xiàn)。儒家講究平等,即“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和“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鼓勵創(chuàng)新,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日日新”“作新民”和“止于至善”;提倡以德治國(家),輔之以法治(家規(guī)),即“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此可以看出,中華文明既非統(tǒng)治者的文明,也非為統(tǒng)治者制定的文明,而是關(guān)于人的學說,是人的文明;是每一個個人的需要和人性的反映,也是每一個“家”(庭)的需要和家規(guī)的基礎(chǔ),更是整個“國家”的需要和持續(xù)發(fā)展的保證。雖然儒家文化被后來的統(tǒng)治者利用,這也只能說明其普遍的適用性,并不能說它是“統(tǒng)治文明”;雖然儒家文化曾被后來的統(tǒng)治者數(shù)次“打倒”,但這種“打倒”猶如摧林之風,只能使“木”更“秀于林”,并不能損害其分毫;雖然儒家文化被后來的眾多學者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進行解讀或者誤讀,從而成為“儒學”,但這些解讀和誤讀不僅代替不了原著,而且也會被大浪所淘。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此,中華文明的生命力也在于此,它是關(guān)于人的文明,只要有人存在,就需要這種文明;只要人類延續(xù),就會運用和發(fā)展這種文明;而一旦人類脫離或者哪怕是偏離這種文明所揭示的“軌道”,就會受到懲罰;一旦人們醒悟后去尋找它,試圖從它那里找到方案和答案,它就把方案和答案和盤托出。
千百年來,中國正是通過這種廣泛存在的家庭經(jīng)濟模式不僅保持了“家”的形式,更延續(xù)了“家”的本質(zhì);不僅成為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明的踐行者,更成為儒家文化的承載者和延續(xù)的傳承者;不僅使中國成為一個“國”,更使中國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家”。所有的家庭都是金字塔結(jié)構(gòu),中國這個國家也是如此。不過,中國及其各級家庭的金字塔結(jié)構(gòu)在本質(zhì)上還是“家”,是“家”的一種存在和管理形式,而且還是一種“扁平”的金字塔形式,處在下層的“塔基”不僅非常大,而且非常“穩(wěn)”(安居樂業(yè)、知足常樂),非常有“禮”(衣食足而知榮辱),非常“靜”(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也非常具有創(chuàng)新性(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注]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和封建統(tǒng)治阻礙了創(chuàng)新,其實不然,只是中國的創(chuàng)新不同于西方:中國是為了生產(chǎn)生活,西方是為了侵略擴張。從這一層面講,西方的創(chuàng)新“動力”更足。,從而保證了這種金字塔結(jié)構(gòu)管理形式的穩(wěn)定性,也就決定了其長期的可持續(xù)性。與此相對比,西方從“公天下”轉(zhuǎn)為“私天下”,既破壞了“公”,又失去了“家”,從而使其成為由一個個利益?zhèn)€體(經(jīng)濟人)通過契約組合而成的松散的、隨時都可能對立、從而隨時都可能解體的“國”。幾百年來,西方列強輪番浮沉,甚至解體分化,正反映了其從短識到短視到最后“短命”的下場,反映出其對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認識的局限性。中國雖然經(jīng)歷了近百年的恥辱,但中華文明經(jīng)久不衰,正體現(xiàn)出其不僅具有其他古代文明所不具備的特點和優(yōu)點,更反映出一個巨大的家庭經(jīng)濟群體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貢獻。
第四,啟示了未來的制度設計和發(fā)展道路。如果說前面三個方面的作用在于“過去”,在當前的條件下,中國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形式更重要的貢獻可能就是在保證中華文明延續(xù)并繁榮的基礎(chǔ)上為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明了道路。一方面,西方“私天下”的問題日益暴露,“制度性疲勞”日益嚴重,人類越來越感受到不可持續(xù)的危機;另一方面,中國的“家”以及與之相應的經(jīng)濟形式過去是、將來仍然是中華文明的承載者和踐行者,同時,家庭經(jīng)濟這種讓所有勞動者與生產(chǎn)資料直接結(jié)合、實現(xiàn)自食其力而又相互協(xié)助的制度設計和經(jīng)濟運行方式,正為我們既解決西方商品經(jīng)濟的缺陷又適應新時代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需要提供了可行的選擇。
五、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小農(nóng)經(jīng)濟”理論的發(fā)展:因地制宜
前面曾說明,“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名稱,包括其特點、作用及趨勢等理論,闡釋最權(quán)威的當然無過于馬克思、恩格斯等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不過,不管是現(xiàn)實的革命和實踐,還是為現(xiàn)實革命與實踐提供理論指導的學術(shù)研究,都不是捧“權(quán)威”,更不是迷信權(quán)威,而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樹立了典范,列寧領(lǐng)導的蘇俄農(nóng)村土地制度改革也為我們提供了直接的借鑒。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理論的現(xiàn)實依據(jù)與俄國實際國情存在極大差異,因而在對農(nóng)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列寧依據(jù)俄國農(nóng)業(yè)的實際,對馬克思恩格斯小農(nóng)經(jīng)濟理論表現(xiàn)出了持續(xù)的實踐反思,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更具適應性、發(fā)展性和現(xiàn)代性的新政策,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7]。
首先是對土地國有化的反思。早在1905—1907 年“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列寧曾認為“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nóng)民土地革命才能獲得勝利,而土地革命不實行土地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歷史使命的”[26],但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二天列寧就放棄了土地國有化的政治主張,認為“應當把土地交給農(nóng)民”。同一時間通過的由列寧起草的《土地法令》規(guī)定: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會的土地,連同所有耕畜、農(nóng)具、農(nóng)用建筑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由鄉(xiāng)土地委員會和縣農(nóng)民代表蘇維埃支配,平均分配給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以土地農(nóng)有代替土地國有,與之相隨的必然結(jié)果無疑是對農(nóng)業(yè)社會化大生產(chǎn)的放棄與對農(nóng)民家庭經(jīng)營和個體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形式的確認。
其次是對共耕制的反思。列寧曾于1918年11月提出將個體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向共耕制過渡,并認為“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條真正可靠、真正能使農(nóng)民群眾更快地過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們同其他公民處于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蘇維埃政權(quán)現(xiàn)在正竭力通過漸進的辦法一步一步地來實現(xiàn)這個共耕制”[27]。但共耕制并未實施多久,1921年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暴動和士兵嘩變,促使列寧反思其農(nóng)村經(jīng)濟政策,認識到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不能處理好國家同小農(nóng)的關(guān)系,“我國有2 000萬農(nóng)戶,農(nóng)民的9/10,更可能99%是單獨的個體勞動。”“我們必須懂得,在大生產(chǎn)徹底勝利和恢復以前,我們面對的是一些為商品流轉(zhuǎn)而生產(chǎn)的小農(nóng)、小業(yè)主、小生產(chǎn)者。而大生產(chǎn)是不可能在舊的基礎(chǔ)上恢復起來的,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幾十年。在我們這種遭受破壞的情況下,可能還要更長一些的時間。在這以前,我們還要同這樣的小生產(chǎn)者打好多年的交道。”[28]21-22為此,需要找到一種符合小農(nóng)特點與要求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形式以便與小農(nóng)政治共處,這就是繼續(xù)發(fā)展農(nóng)民的個體經(jīng)濟,恢復個體農(nóng)民之間的貿(mào)易自由。
正如劉新春等人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歷經(jīng)十月革命、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和新經(jīng)濟政策等多個時期,列寧不斷總結(jié)關(guān)于農(nóng)村工作的經(jīng)驗和教訓,其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政策的反復與調(diào)整,體現(xiàn)和反映了列寧在蘇俄農(nóng)村工作實踐中對馬克思恩格斯小農(nóng)經(jīng)濟理論的深刻反思:馬克思恩格斯關(guān)于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理論是基于英法等國小農(nóng)狀況為背景而構(gòu)建的,即使是關(guān)于東方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也是以歐洲無產(chǎn)階級支持與幫助落后國家的革命運動為前提的,因此,“決不能剝奪農(nóng)民”。列寧明確指出:“根據(jù)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lǐng)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我深信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今后只能根據(jù)經(jīng)驗來談論社會主義。”[29]不僅如此,列寧還提出:“一下子就把數(shù)量很多的小農(nóng)戶變成大農(nóng)莊是辦不到的。要在短期內(nèi)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經(jīng)營的農(nóng)業(yè)變成公共經(jīng)濟,使之具有全國性大生產(chǎn)的形式,由全體勞動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勞動義務,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勞動產(chǎn)品——要一下子做到這一點,當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某個共產(chǎn)黨人,竟然想在三年內(nèi)可以把小農(nóng)業(yè)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和經(jīng)濟根系改造過來,那他當然是一個幻想家。”[28]53
從列寧處理蘇俄的農(nóng)民問題可以看出,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有著明確的要求,這就是消滅小農(nóng)經(jīng)濟:“我們永遠也不能向小農(nóng)許諾,給他們保全個體經(jīng)濟和個人財產(chǎn)去反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的優(yōu)勢力量。我們只能向他們許諾,我們不會違反他們的意志而強行干預他們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如果我們許下的諾言使人產(chǎn)生哪怕一點點印象,以為我們是要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于黨而且對于小農(nóng)本身也是最糟糕不過的幫倒忙。”[6]500-501列寧也曾堅信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闡述,“就現(xiàn)代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來看,總的來說歷史證明了馬克思的規(guī)律是適用于農(nóng)業(yè)的,并沒有被推翻”,但在蘇俄的農(nóng)村革命實踐中也確實發(fā)現(xiàn)了“不適應”之處,并果斷地采取了創(chuàng)新性的舉措,在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正如劉新春等人所指出的:“實踐是一道邁不過的溝坎,它并不給予嚴謹?shù)睦碚撨壿嬕越z毫的寬容與遷就。急驟變化的形勢和從未有過的嚴峻挑戰(zhàn)”[7],不僅會給予我們指導,更會提供“教條主義”的教訓。
不僅如此,劉新春等人認為,當代國際學術(shù)界關(guān)于農(nóng)戶經(jīng)濟的五大基本理論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舒爾茨和波普金的“理性小農(nóng)”理論、吉爾茲和黃宗智的“農(nóng)業(yè)內(nèi)卷化”理論、斯科特和利普頓的“風險厭惡”理論、巴納姆和斯奎爾的“小農(nóng)場(戶)經(jīng)營模型”理論為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小農(nóng)經(jīng)濟理論的實踐反思提供了旁證。他們通過對“落后地區(qū)”和“傳統(tǒng)經(jīng)濟”中的“農(nóng)民經(jīng)濟行為”的實證研究,較為一致地強調(diào)“農(nóng)戶經(jīng)濟行為遵循的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個人主義行為邏輯,主張小農(nóng)經(jīng)濟行為不能以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關(guān)于資本主義農(nóng)業(yè)演進的學說來解釋”[30]。
六、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的現(xiàn)代中國實踐:新時代老作用
如果說前面的介紹都是屬于對文獻和歷史的考察,那么現(xiàn)在我們回到現(xiàn)實,看看所謂的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在當前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許更有啟發(fā)意義。
還是從趙岡教授的分析說起。他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一句為大家所服膺的格言,這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惜在這一點上歷史研究者處于不利的地位,因為歷史極少重復,也無法去實驗求證,因此做歷史研究的人在接受了一個不正確的學說后,就沒有檢驗真理、檢驗其學說正確與否的機會,這會導致其一錯到底,并且永不修正。“但是在中國卻有歷史重復出現(xiàn)之事實,而且就在眼前,有關(guān)文件及事前事后的統(tǒng)計資料十分豐富,為檢驗真理提供了具體而明確的絕佳機會。”他說,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農(nóng)村改革實行包產(chǎn)到戶,就是另一次的“分田”,也就是《呂氏春秋》中說的將“眾地”化為“分地”,古人所說的“公田不治”及“民不肯盡力于公田”,用現(xiàn)代農(nóng)民的話來說就是“干活大糊弄”。改革的效果,也如古人所說“公作則退,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趙岡教授最后說,閱讀農(nóng)村改革的文件遠比閱讀古代文獻來得親切具體,但是問題的性質(zhì)是相同的。分田到戶的貢獻是主要的,這一點是無人否認的[3]。
其實,對于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賀雪峰、溫鐵軍等人的分析非常透徹。賀雪峰先生認為,目前“中國式小農(nóng)經(jīng)濟”表現(xiàn)在中國農(nóng)民家庭上的基本特征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chǔ)的半工半耕”的勞動力再生產(chǎn)模式[31]。年輕子女外出務工以獲得務工收入,年齡比較大的父母留守在家務農(nóng)以獲取務農(nóng)收入,如果父母年齡太大不堪農(nóng)業(yè)勞動,會將承包地就近流轉(zhuǎn)給兄弟姐妹、鄰里朋友耕種。這樣形成了一種特殊而又相當穩(wěn)定且具有再生產(chǎn)能力的結(jié)構(gòu),即最早外出務工經(jīng)商的年輕人在外20年后,其父母年齡已大,務農(nóng)已力不從心,其子女又已成長起來可以開始外出務工。這樣,早期外出務工的人因不再年輕就回到家鄉(xiāng),接替父母務農(nóng),年幼子女跟著爺爺奶奶在農(nóng)村生活,還可以與自然親密接觸,開支低,消費少,而且農(nóng)村家中不僅有自家住房院落,可以自種瓜果蔬菜養(yǎng)雞養(yǎng)豬,還生活在熟人社會中,心理上有安全感,生活和生產(chǎn)中容易得到鄰里親友的互助,從這個意義上講,老年人在家務農(nóng)是比較人性化的生活。因為有老家父母的務農(nóng)收入,外出務工的年輕人的收入無論多少基本上都能接受,甚至當“月光族”也沒有問題。在賀雪峰看來,年輕人進城務工經(jīng)商,靠自己勞動賺錢,城市的燈紅酒綠是要體驗一把的,節(jié)假日老鄉(xiāng)聚會大吃大喝補償一下也是可以的,至少在他們結(jié)婚之前,收入多少都不是大的問題。另外,賀雪峰指出,中國奇跡首先是中國制造的奇跡,而中國奇跡目前仍需要依靠廉價勞動力。廉價勞動力的核心就是上述這種勞動力再生產(chǎn)模式。
上述更重要的是,賀雪峰還認為,“以代際分工為基礎(chǔ)的半工半耕”結(jié)構(gòu)及其再生產(chǎn)性,對于理解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性有重要意義[31]。發(fā)達國家工業(yè)化、城市化程度高,經(jīng)常發(fā)生各種經(jīng)濟、金融、社會、政治危機,任何人都逃脫不了這些危機的影響,所以任何危機都會引起全社會的動蕩,不僅造成社會生產(chǎn)力的巨大損失,更反映出其發(fā)展的不可持續(xù)問題。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模仿發(fā)達國家的思維和路徑,在發(fā)展過程中也難免會發(fā)生類似的危機。而在發(fā)生危機時是否有能力應對,則是決定其當前和未來前途的關(guān)鍵。賀雪峰指出:“中國城市發(fā)生危機,如果農(nóng)村這個重心仍然穩(wěn)定,則中國式危機就表現(xiàn)為城市及其部門晃幾晃,然后在穩(wěn)定重心的作用下,很快就穩(wěn)定下來。中國農(nóng)村相當穩(wěn)定的且為城市農(nóng)民工提供支持的規(guī)模巨大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重心所在,幾乎是中國面對任何復雜情況都不崩潰的關(guān)鍵之一。”他認為,中國這種模式為進城農(nóng)民提供了選擇的機會和權(quán)利,“使進城失敗的農(nóng)民工并不強留在城市”。只要目前農(nóng)村的基本經(jīng)營制度穩(wěn)定,留守在農(nóng)村的人就具有極強的生存能力,農(nóng)村可以為進城失敗的農(nóng)民工提供返鄉(xiāng)的順利通道。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即使面臨像西方那樣的經(jīng)濟社會危機,導致進城務工的人們失業(yè),這部分人還可以返回農(nóng)村,不僅可以與家人團聚享天倫之樂,而且能夠幫助家人務農(nóng)勞動,自己也可以休養(yǎng)一段時間。由于農(nóng)村有住房、糧食、蔬菜等生活條件,不會影響其基本生活,因此“休養(yǎng)”的時間長短都不會是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農(nóng)村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勞動力“蓄水池”,不僅保障了中國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進程,而且由于有農(nóng)村的基本生產(chǎn)和生活條件,保障了至少一半以上人口的生產(chǎn)生活,中國就不會出現(xiàn)大問題。“所以,中國具有其他國家不可想象的強有力的應對失業(yè)危機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每次經(jīng)濟下滑時,有學者以就業(yè)來說事,認為中國經(jīng)濟增長速度低于8%就不穩(wěn)定,這實在是錯誤的判斷。”[31]
賀雪峰總結(jié)說:“中國之所以可以在發(fā)展中保持穩(wěn)定,中國式小農(nóng)經(jīng)濟起到了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農(nóng)民家庭的農(nóng)業(yè)收入為9億農(nóng)民(包括進城農(nóng)民工)提供的基本生存保障,這使得中國社會重心穩(wěn)定;二是進城務工農(nóng)民在面臨失業(yè)時,可以選擇返回農(nóng)村,從而為國家度過經(jīng)濟危機提供緩沖;三是進城失敗的農(nóng)民可以返鄉(xiāng)。農(nóng)民可以返鄉(xiāng)是中國沒有像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普遍有大規(guī)模貧民窟的關(guān)鍵。沒有大規(guī)模貧民窟就極大地降低了由經(jīng)濟金融危機向社會失序和政治動蕩轉(zhuǎn)化的可能。”他說,中國農(nóng)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是一種不允許農(nóng)民失去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的制度安排,是對農(nóng)民利益的有力保護,也是中國式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基礎(chǔ)和特征所在。中國短期內(nèi)不可能保證所有進城務工人員的同工同酬同生活,即使實行了城鄉(xiāng)完全統(tǒng)一,從眼前看也不可能解決可能存在的危機問題,所以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營制度必然會保持穩(wěn)定,中國式小農(nóng)必然會繼續(xù)存在。
當筆者在寫作這篇文章時,全球發(fā)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階段性、決定性勝利的同時,派人奔赴意大利、伊朗等重災國家和地區(qū),援助抗疫。這次疫情又一次證明了中國農(nóng)村的積極作用。正如溫鐵軍先生所說:“在中國應對前幾輪全球經(jīng)濟危機的過程中,農(nóng)村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對于這次疫情,很多方面不可抗,但可抗的一個重要力量就在鄉(xiāng)土社會。鄉(xiāng)土將外部性巨大風險阻隔而實現(xiàn)‘脫鉤’,自主處理內(nèi)部事務,因而依然是應對全球化危機的最為低成本的載體。”[注]溫鐵軍.疫情加速全球危機,中國還能憑什么力挽狂瀾?鄉(xiāng)村建設研究根據(jù)2020年2月17日、24日溫鐵軍教授在今日頭條直播演講的整理稿。
七、研究結(jié)論與啟示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jié)論。
第一,應當將“小農(nóng)經(jīng)濟”改稱為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簡稱家庭經(jīng)濟。
第二,歷史和現(xiàn)實的實踐都已證明,做理論研究也好,在政界、實業(yè)界也罷,不能生搬硬套馬克思、恩格斯等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局限于他們的某些詞句,馬克思主義需要根據(jù)時間、地點、特別是文化的不同而創(chuàng)造性應用、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不能迷信西方,被逞一時之能的近百年的西方經(jīng)濟、科技、軍事和話語強權(quán)所迷惑。要真正堅持“四個自信”,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第三,中國的小農(nóng)(家庭)經(jīng)濟不是一種簡單的家庭私有制形式,其產(chǎn)生和持續(xù)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國“家”文化的體現(xiàn),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jié)晶和象征。這樣的經(jīng)濟形式不管規(guī)模多小,都可以達到幾個目的:一是所有勞動力(農(nóng)民)與生產(chǎn)資料(土地)的有機且有效結(jié)合,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田地有人耕;二是可以充分發(fā)揮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盡管規(guī)模不大,但可以精耕細作,在有限的范圍內(nèi)實現(xiàn)集約化經(jīng)營;三是社會穩(wěn)定,人們安居樂業(yè),知足常樂;四是國家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實現(xiàn)有效管理。人們不需要多少所謂的“科學技術(shù)”,更不需要侵略擴張,只需要安心生產(chǎn)與生活;五是更重要的,正是在這種安心的情況下,人們之間的仁、義、禮、智、信才能充分體現(xiàn)出來,人們的智慧(而非聰明)才能顯現(xiàn)出來,進而在不需要“科學技術(shù)”的同時創(chuàng)造出反映人類智慧、服務人類發(fā)展(而非用以牟利、侵略)的一系列發(fā)明創(chuàng)造[注]這就是為什么中華民族從骨子里沒有侵略的基因,中國在技術(shù)領(lǐng)域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都是為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所需,在人文社科領(lǐng)域的著述、創(chuàng)新都是為了教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經(jīng)世濟民的經(jīng)濟觀正由此而來。。
第四,中國家庭經(jīng)濟形式不僅對解決西方模式存在的頑疾有著重要的“處方”作用,更可以對未來實現(xiàn)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借鑒:可以實現(xiàn)生產(chǎn)資料與所有勞動力的直接結(jié)合,不僅能解決失業(yè)問題,也為所有人的全面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可以“模擬”出西方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家夢想的自由競爭,實現(xiàn)效率的充分提升;可以為在廢除繼承權(quán)的基礎(chǔ)上實行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為很多人試圖揭開的個人所有制提供基礎(chǔ),從而實現(xiàn)真正的公平與效益的完全統(tǒng)一,而不是顧此失彼。對此我們將另文專述。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傳統(tǒng)的家庭經(jīng)濟并不完美,比如其對科技發(fā)明的欲望不夠強烈;再比如在當前城市化、工業(yè)化的沖擊下,賀雪峰、溫鐵軍等學者所提到的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及其“貢獻”可能將不復存在,因為進城的農(nóng)民及其后代將逐漸失去耕種能力,農(nóng)村“鄉(xiāng)土社會”正在逐步消失,農(nóng)田的規(guī)模化經(jīng)營不僅必然,而且還可以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權(quán)的情況下完成。另外,農(nóng)村家庭經(jīng)濟是以土地這一特殊生產(chǎn)資料為條件存在的——土地不同于其他如機器、廠房、資本等生產(chǎn)資料,既不會移動,一般也不會“消失”。這類問題也需要我們進一步作出回答并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