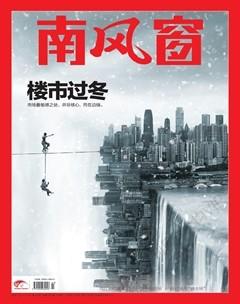科技應該是反內卷的
胡泳
在10月13日召開的2021未來組織大會上,釘釘總裁葉軍表示,普惠、開放與利他已成為釘釘最基礎的底層邏輯,即必須讓數字技術普惠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個體;同時,欲實現企業數字化,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又需要借助釘釘這樣的新生產力工具,為此,釘釘提出未來組織年度趨勢關鍵詞“數字生產力”。很大的考驗在于,數字生產力,是否能做到與數字化工作的脈搏同頻共振?當整個組織、所有員工都在線,我們的工作場所會迎來怎樣的巨變?
如果說有一個問題困擾著20世紀的管理者(從弗雷德里克·泰勒到山姆·沃爾頓),那就是:“我們如何從我們的員工身上獲得更多?”在很大程度上,這一問題顯得無比正當—誰能反對提高人的生產力這樣的目標?然而,該問題也充滿了工業時代的思維:我們(這里指“管理層”)如何從我們的員工(指必須服從管理層命令的個人)身上獲得更多(按每小時的生產量來計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問題暗含的管理模式幾乎確認了企業永遠無法從其員工身上得到最好的東西。附庸者和應征者可能會努力工作,但他們絕非是自愿工作的。
雖然數字化工具的出現使人們有能力在其所選擇的任何地點和時間展開工作,但大家仍然是上一代工人業已建立的常規的奴隸。對大多數人來說,工作的“標準”是擁有一份固定地點和固定時間的活計。作為對人們出勤、并完成自身工作的回報,企業向他們支付工資、提供福利,并提供一定程度的經濟保障。然而,這越來越被認為是一種低生產力的模式,對雇員來說不是很滿意,對雇主來說也不是很有效。
此種模式的低生產力之所以讓人越來越無法忍受,是因為網絡的普及導致了線上與線下的彌合。歲月悠悠,劉易斯·芒福德在《歷史的城市》中描繪的 17世紀“家庭與工作場所的逐漸分離”,不期然構成了當下數字化生存的反寫。今天,家庭與工作場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程序員、作家或者其他形式的“知識工人”在家中工作要便利得多,由辦公軟件連接的個體可以隨時隨地都處于工作狀態之中。而遠程工作脫離時間與空間束縛之后,再也無法以工作制而只能以成果的形式進行衡量。一個真正考驗效率的數字化時代來臨了,在效率中落后的后果則是更多工作時間侵占個人時間。
到此時刻,管理者必須跳過的最大障礙是停止衡量投入(工作時間),而開始衡量產出(實現結果)。如果承認工作的基礎是實際產生的結果,那么活動的時間和地點就幾乎變得不重要了。有許多工作對工作的時間和地點有限制,但此外的限制不應該再出自管理層了。當人們被信任、可以自己決定如何完成工作時,他們將會明了這些限制,并在相應的參數范圍內工作。
當工作只能在一個地方完成時,生活很簡單。你去工作,并貢獻你的時間。“工作”就是你在合同規定的時間內所去的一個地方,你根據你投入的時間獲得報酬,而獎勵制度反映了你的投入。現在,生活正變得更加復雜。技術已經將工作從固定地點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并給予工人更多關于何時工作的選擇。
“工作”不再是一個可以去的地方,它是一種有目的的活動。工作成為一個實現結果的過程,產出才是最重要的。獎勵對企業目標有貢獻的結果,似乎比獎勵可能對企業成功毫無貢獻的努力要合理得多。
極致效率會帶來內卷,而科技應該是反內卷的。一個真正的生產力工具,應該不止于提高辦公效率,更要投入到促進生產、將業務數字化的使用過程中。只有發展才能熨平內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