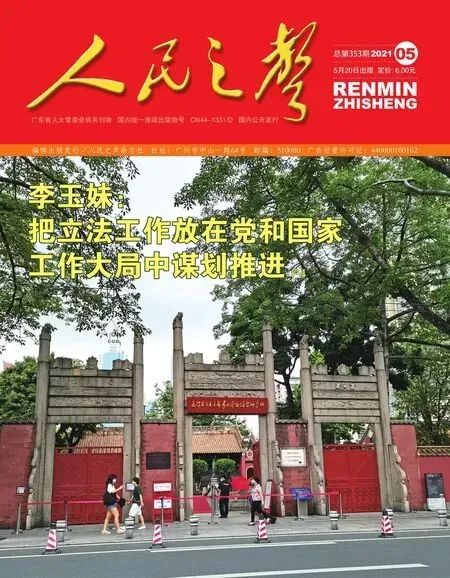打造特色步行街 傳承大灣區文化
今年這個“五一”假期,官方監測,廣州各大商圈人流和消費顯著增長。天河路商圈客流超1 000萬人次,比2019年增長超15%。北京路商圈假期累計客流量262.54萬人次,比2019年增加超過70%。然而,作為廣州老中軸線的北京路,其客流量明顯無法和新中軸線周邊的天河路與珠江新城商圈相比。這就引發了社會各界包括人大代表們對于傳統步行街復興之路的關注。
回溯今年初,廣州市人大代表劉進賢就提出了《利用廣州商業步行街文化資源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的建議。建議中提到,習近平總書記視察荔灣區西關歷史文化街區永慶坊時提出了城市規劃和建設的新理念和新途徑以及讓老城市顯現新活力的根本原則。因此,該代表就建議,廣州商業步行街的建設立足點,不能只局限于本市,應站在國內步行街建設的前沿和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服務這個高度來作充分考慮。
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廣州商業步行街有明顯的傳統商業業態,比如上下九是廣州舊城區最繁華的地段之一,西關民俗文化、嶺南騎樓建筑文化、傳統飲食文化等歷史文化資源構成西關風情畫。北京路步行街,具備了騎樓小店和大型商廈互補的結構,既能滿足小型購物和飲食,也能滿足對于品牌和高檔商品的采購。由于不斷投入翻新,北京路的硬件與面貌也在不斷提升。
不過,在筆者看來,廣州的步行街打造的經典形象依然未能承載嶺南及大灣區的現實需求。第一,在規劃、建設和管理上,步行街外街門面光鮮與內在城區環境形成強烈反差,比如老舊的上下九最為明顯,一旦透過騎樓走入內街,面對的是相當破舊陰暗的環境體驗,以至于可能讓游客望而卻步。這也是很多城市老街的通病。因為內街是當地老百姓生活的私人空間,也是形象工程的終止邊界,結果就暴露出老城區的生活真相和階層現狀。
這意味著,如果要振興步行街,始終繞不開改善當地人居環境的這一根本出發點。無論面對游客還是土著居民,政府都有責任通過深入改造,提供完善的硬件服務。這樣的步行街才是不是只有浮華門面,而是能反映城市升級進步,提供真實記憶的地方。
第二,步行街決策與管理者往往希望把老字號、民間工藝、歷史故事、現代創意、奢侈消費都堆砌一起,以為能展示多元的城市面貌。這樣的結果,造成的就是步行街面目混雜,檔次凌亂。導致高端、有檔次的品牌不愿意摻雜其中,最后能吸引人氣的幾乎都落在了小型餐飲、各種網紅店,甚至每天喊清倉的低價山寨商鋪。
步行街不是簡單的博物館或者大賣場,關鍵是要讓消費者收獲城市深層魅力并且感到興奮。要構筑步行街的內涵和將來,就要給以消費者和游客以一種明確的代表城市升級向上的精神體系,讓人產生留戀、模仿和景仰之心。否則消費者完全不用到步行街而在其他地方都能完成消費,這樣的步行街就很失敗了。
值得借鑒的比較成功的例子,就是上海新天地,專業規劃、定位和管理,帶來的是海派經典文化在現代商業需求中發揚光大,至今20年依然不老不陳舊,實現了與時代同步的地位。
第三,廣州的步行街往往在硬件上不斷追求更新換代,但是在軟實力上總是有差距。比如,純公益性、展示型的歷史非遺并不突出,沒有形成互相呼應的一脈相承體系;富有時代精神的街頭裝置藝術更是少之又少。雷同的人物銅像勉強維持著對古代生活的想象。那么遠道而來的游客,就難以理解廣州獨特的城市主張和文化,也感受不到它與其他城市的不同之處,更別說廣州在大灣區的文化歷史中的優越性。
所以代表也建議,在不賣產品或少賣產品的前提下,讓區政府部門和區內著名老字號企業以負責提供人財物支持,區政府提供場地支撐,設多個文化展示點,每個點相距一百至二百米。通過小型展、現場表演、產品體驗等方式,將老字號文化、民間工藝、文化創意和飲食文化展示出來。
實際上,類似展示應該是市場導向與專業競爭和篩選的結果。因為此前廣州也并非沒有這種嘗試,最后都是因為道路、天氣和空間的原因,沒有形成長效支持機制。倒是各種面目不清的應節擺攤成了常態,為步行街帶來人氣的同時,更是加速了步行街的面目不清。
廣州作為歷史悠久的城市,為市民和旅游者打造步行街,也是在經營一個城市的文化平臺。因此,從人大到政府的層面都應該形成合力,要更多的考慮到時代的需求,要積極學習諸如上海、杭州、成都、西安等地的經典商業街區的經驗,使之在大灣區建設中起領頭羊作用。在步行街建設過程中還要引進國內先進的商業企業集團,采取合作共建的方式,進一步增加步行街在國內的輻射力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