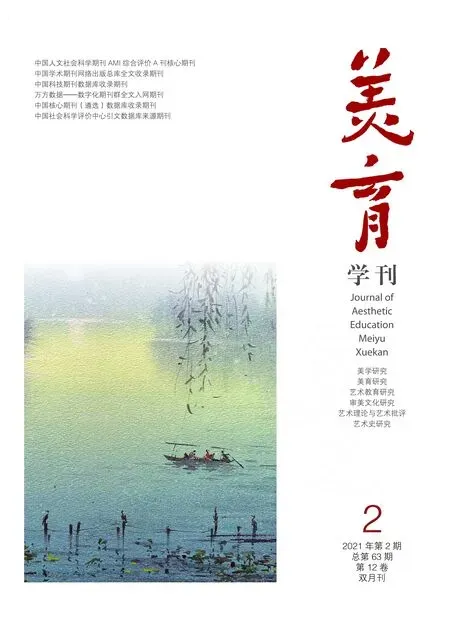日本明治時期大學的美學課程及其講座的誕生始末
鄭子路
(江西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19世紀后半期以降,隨著“西學東漸”的擴展與推進,“美學”這門“新學”逐步進入了東方人的視野。在日本,最早對“美學”進行介紹的是啟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他將“美學”譯為“善美學”(《百一新論》)、“佳趣論”(《百學連環》)、“美妙學”(《美妙學說》《奚般氏心理學》),并在《美妙學說》中對自身的美學思想進行了一次體系化的構建。(1)《百一新論》刊行于1874年,是西周于1866年至1867年在京都洋學私塾的特別講義。《百學連環》則是1870年西周在東京“育英舍”的講稿,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版本是聽講生永見裕的筆記。《美妙學說》的發表時間不明,有1872年(麻生義輝)、1877年(大久保利謙)、1879年(森縣)等幾種不同的說法。筆者認為森縣([日]森県:「西周『美妙學説』成立年時の考証」『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第14巻6號,1969年,第206頁)的說法比較準確,應是1879年1月13日西周在“宮中御談會”上的講稿。理由主要有二:(一)從該書強調美學的功利性以及措辭表現來看,受眾為天皇和各大臣的可能性很高;(二)對于“美學”的譯法與1875年至1878年刊行的《奚般氏心理學》相同。西周的這次嘗試雖然談不上嚴謹,也并不完備,但卻是日本最早的、立足于本國文化的美學體系建構,標志著日本近代美學的開始。隨后,在文部省翻譯局的囑托下,另一位啟蒙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于1883年至1884年翻譯出版了法國人維隆的著作,命名為《維氏美學》(Eugène Véron:L’esthétique,1878),第一次使用了“美學”這個漢字譯名。盡管在最初的對于“美學是什么”的認知階段,啟蒙思想家、文藝評論家們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甚至一度還造成了一種“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比學院派研究者更具影響力”[1]的現象,但真正促使美學在日本生根發芽并最終得以延續下來的,卻是各大學對于美學學科的開設,即所謂的學院派美學的成立與發展。
一、日本講座美學的誕生
日本的近代化教育,始自1872年(明治五年)的“學制頒布”。該年8月,明治政府頒布了首個關于學校制度的教育法令,效仿法國的學區制度,將日本全國分為數個學區,在學區內設置各級學校,旨在推動全民教育。在這之前的江戶時代,雖然并沒有明確的學校制度,但各藩均設有針對武士子弟的藩校、家塾或鄉學以及針對庶民子弟的寺子屋。而作為名義上的中央政府的江戶幕府,也設置了諸種高等教育機構,用以培養各類頂尖人才,如為培養儒學人才而設置的“昌平坂學問所”(后改名為學問所、昌平學校)、為培養國學人才而設置的“和學講談所”、為培養醫學人才而設置的“醫學館”、為培養西學人才而設置的“藩書和解方”(后改名為洋學所、藩書調所、開成所)等。現存于西周家的書寫于“藩書調所”時期的《西周哲學講義案》,可以看作是“日本西方哲學研究的第一聲”[2]40。
1877年4月12日,由天文方、昌平坂學問所(亦稱昌平黌)、蕃書調所、昌平學校、開成所等舊制機構合并改編而成東京大學,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的東京大學設置有法學部、理學部、醫學部、文學部四個學部,文學部中設有第一科“史學、哲學及政治學科”與第二科“和漢文學科”。1881年9月,哲學科單獨成為一科,下設心理學、世態學(社會學)、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中國哲學、審美學等課程。1886年3月,日本文部省進一步頒布《帝國大學令》,由四個學部組成的東京大學增設工科,成為五大分科大學。文學部也由此升格為由哲學、和文學、漢文學、博言學(言語學)四科組成的文科大學,“審美學”也隨之由一門課程升格為哲學科下單獨開設的一門專業。從東京大學的創建到升格為文科大學的這段時期,是日本講座美學的第一階段,也可稱之為史前期。在此階段,美學并未從哲學中獨立出來,僅作為西方哲學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由從美國學成歸國、主攻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派社會學的外山正一(1848—1900)以及特聘的數名外國教師(お雇い外國人)講授。
外山正一13歲進入蕃書調所學習英文,16歲赴英后又于18歲赴美留學,在密歇根大學獲得了哲學和理學學位。歸國后,他開創了日本首個社會學講座,并歷任東京大學教授、文科學長、大學總長、文部省大臣等職。他終身致力于進化論、斯賓塞學說的介紹,創設羅馬字學會,推動音樂、繪畫、演劇的改良,是日本近代詩的先驅。通過他晚年發表在《哲學雜志》第11卷154號上的論文《關于人生目的的我信界》(「人生の目的に関する我信界」),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他對于人生以及哲學的思考。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留學生,外山主講哲學、史學和英語,與主講邏輯學和東方哲學史的井上哲次郎(1856—1944)、主講心理學的元良勇次郎(1858—1912)、主講倫理學的中島力造(1858—1918)共同組成了東京大學哲學科最初的教授團隊。據《東京大學百年史》記載,東京大學的審美學課程就是由外山于1881年首次開講[3]588。雖然,1893年講座制正式確立后,外山轉為負責社會學講座,但負責哲學及哲學史第一講座的井上哲次郎卻認為,“在起初的數年,外山將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斯賓塞、貝恩(Bain Alexander, 1818—1903)等人的哲學史作為教材,講授哲學和邏輯學,與日本哲學研究的興盛不無關系”[4]35。作為東京大學哲學科早期畢業生的高山樗牛(1871—1902),也在后來追憶外山的文章中評價道:“作為學者,外山博士的博學是日本人中極為罕見的。”[5]562
但是不得不說,與在文藝改良運動以及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相比,外山在美學方面并沒有太多值得夸耀的成績。1890年4月27日,他在明治美術會發表了名為《日本繪畫的未來》的演講。但演講稿登報后,卻遭到了剛從德國留學歸來的年輕軍醫森鷗外(1862—1922)的猛烈批評。這次“論爭”史稱“畫題論爭”,與隨后的“審美生活論爭”一樣為歷代史家所重視。但與其他論爭不同,畫題論爭完全是有效地運用了美學原理論的森鷗外(1862—1922)的獨角戲。無論森鷗外如何地挑釁或變換方法攻擊,作為學界領袖的外山始終保持沉默。這或許是外山的策略,但外界觀感普遍認為是森鷗外取得了該次論爭的完勝。由外山兼任東京大學最初的美學講師,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他個人對于文藝的強烈熱愛以及自身所具備的較高的美學素養,另一方面也凸顯了當時日本美學界人才的匱乏。
針對這樣的情況,東京大學積極地在海外物色人才,并于1882年起將審美學課程改為由外籍教師擔任,主要有美國人斐諾洛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英國人庫珀(Charles James Cooper,生卒年未詳)、美國人科諾克(George William Knox,1853—1912)、德國人巴斯(Ludwig Busse,1862—1907)、俄國人凱倍爾(Raphael Koeber,1848—1923)等。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878年作為東京大學文學部首位外籍教師赴日任教的斐諾洛薩,以及自1893年起在東京大學任教長達21年之久的凱倍爾。其他幾位外籍教師由于任期較短,所以與他二人相較,并沒有留下太多的記錄和資料。據現有的資料可知(2)[日]伊藤吉之助·池上鎌三:「第八章 哲學科」『學術大観 総説·文學部』東京帝國大學,1942年,第324頁;『早稲田文學』1891年11月號,第68-72頁;『早稲田文學』1892年10月號,第18頁;井上哲次郎:「ラファエル·フォン·ケーベル氏を追懐す」『哲學雑誌』第438號,1923年,第60頁。:庫珀、科諾克和巴斯在東京大學任教的時間分別為1880年4月至1881年7月、1886年9月至同年12月、1887年1月至1892年12月。庫珀使用《純粹理性批判》的英文版,將康德哲學作為教學中心,開創了日本康德研究的先河[2]63-64;科諾克從漢密爾頓學院畢業后進入神學院學習,并于1877年作為基督教的牧師被派至日本,先后在筑地大學校和東京一致英和學校擔任英文、神學和心理學的講師。1886年,他接任斐諾洛薩,在東京大學短暫地教授哲學和審美學。在東京大學講授審美學期間,他使用的參考書是威廉·呂布克(Wilhelm Lübke,1828—1893)的《美術史大要》(HistoryofArt,1881),主張將事實、法則與原理的調和作為“圓滿的美”;巴斯先后求學于萊比錫大學、因斯布魯克大學、柏林大學。1887年起,執教于東京大學,教授哲學和審美學,著重于新康德學派的先驅洛采(Rudolf Lotze,1817—1881)的美學理論,提倡新形而上學,主張將自然科學的立場與觀念論的世界觀進行調和。歸國后,他先后轉輾于柯尼斯堡大學、明斯特大學,著有《洛采氏倫理學一斑》(「ロッツェ氏倫理學一斑」)(《哲學會雜志》1888年第12號)等。
二、斐諾洛薩的美學講義
斐諾洛薩出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出生那年正好是“佩里黑船”叩開日本國門的1853年。1874年,年輕的斐諾洛薩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哈佛大學哲學系畢業,并短暫地在波士頓美術館工作。1878年,經動物學家默爾斯(Edward Morse,1838—1925)介紹,赴東京大學任教。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斐諾洛薩極為推崇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一手創建了“斯賓塞俱樂部”,并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來日后,他最初擔任的課程是經濟學與哲學,后又成為邏輯學和審美學的教授。在課堂外,斐諾洛薩不但熱衷于收集和研究日本美術作品,還擔任了文部省美術事務官、東京美術學校理事等職,與助手兼翻譯的岡倉天心(1863—1913)一起赴歐考察美術行政以及相關的教育制度,積極地為日本傳統美術的保存和振興奔走,直接促成了東京美術學校的創立和《古社寺保存法》等美術相關法令的制定,被看成是日本美術的恩人。
對于日本的傳統美術,斐諾洛薩起初并不看好,但因為一次偶然的際會——1880年在奈良、京都等地的旅行中意外地發現了日本佛教美術中暗藏的古希臘的藝術傳統——而轉變立場,開始狂熱地擁護日本畫。1882年,他在龍池會的演講被大森惟中(1844—1908)整理成《美術真說》一書,在日本得到廣泛傳播,啟發了當時的人們對于“美術(3)當時“美術”與“藝術”尚未分化,Liberal arts的譯名也尚未確定,菲諾洛薩使用的“美術”可以看成我們今天所說的“藝術”。是什么”以及“美的自律性”的思考。在這次演講當中,斐諾洛薩否定了“將技術的優劣作為判斷美術是否善美的主要因素”的“技巧精良說”、“將是否能引發人們內心的愉悅作為判斷美術是否善美的主要因素”的“快樂說”、“將對自然和實物的模仿作為美學的關鍵”的“自然模仿說”,認為美術的本質并不在于作品與外界的外在關系,而應當在“事物的本體”中謀求。美術的本質在于“妙想(idea)”,即“在各個分子內面保有始終相依的關系,并時常產生一種完全唯一的感覺”。在妙想之外,作為美術的要素存在的是“旨趣”和“形狀”。這三者相互組合,構成了詩歌、音樂和繪畫。在他看來,“詩歌以旨趣的妙想為主,形狀的妙想為次。音樂則相反,以形狀的妙想為主,以旨趣的妙想為次。繪畫則不可偏廢,旨趣和形狀共同組成了車的兩輪”。并且,他還以該定義為基準,提出了“繪畫構造”的“十格”理論,即“圖線的和諧”“濃淡的和諧”“色彩的和諧”“圖線之美”“濃淡之美”“色彩之美”“旨趣的和諧”“旨趣之美”“創意”“技巧”[6]37-42。
1889年,東京美術學校正式開校。“美學及美術史”課程由已成為日本美術指導者的斐諾洛薩親自擔任。對于斐諾洛薩在東京大學的哲學講義,現在只能通過三宅雪嶺(1860—1945)、坪內逍遙(1859—1935)、井上哲次郎等人的回憶,間接地了解到他的講義在內容上統合了穆勒、斯賓塞的英國經驗論與康德至黑格爾的德國觀念論,雖然講的是進化論,但卻并不是像普通的進化論者那樣只講進化論。他將黑格爾哲學中的進化論思想與自然科學的進化論融會貫通,并在此基礎上努力尋求突破,并非刻意去迎合當時流行的物質主義,而是追求一種理想主義。[7],[4]70而他在東京美術學校的講義,則由岡倉天心翻譯、大村西崖(1868—1927)編成,現收錄于《岡倉天心全集》第八卷,所以相較于東京大學的講義,可以更加忠實地了解到他的所思所想。他認為,世界并不存在“確定的美學”,現在的當務之急也并非去辨別東西方美術方法或者相關主義的不同,而是應該促成對于美術普遍適用的“真正的美學”的誕生。以此為目標,他通過與東方的“六藝”以及“琴棋書畫”等概念對比,進而闡述了西方文脈中美術概念的形成史:
古希臘時代的畫師們并不知道有“美術”這個詞,也沒有意識到有對這個詞進行說明的必要。只有一個意思相近的詞匯——Music。然而,這個詞的意思也很難分辨清楚,只是表達為了成為高等社會的人類所需要的技藝,包含了詩歌和音樂。到了羅馬時代,開始有了Arts一詞。希臘也產生了Techne一詞。這便是英語art and technic的起源。它所包含的是以人工進行制造的創作之意,不僅包括我們今天使用的美術,還包括諸種手藝。大約在兩千年前,出現了Artes liberales一詞,用來表示Liberal arts。它作為高等技藝,與作為謀生手段的技藝區別開來。……并且在自由七藝之上又出現了Arts poetica(poetry)一詞。……到了十三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美術的復興運動以意大利為中心。……當時的畫師、雕刻師、建筑師們并不知道自己的技藝有多高超,也在不知道什么是美術的情況下創造出了一批絕世之作。……到了十八世紀初,因為詩歌、繪畫、建筑、雕刻需要能將其總括在一起的名稱,所以在法國開始出現了Beaux arts一詞,該詞到了十八世紀末被譯為英語Fine arts,也就是美術一詞的起源。[8]450-452
在斐諾洛薩看來,正是因為美術一詞的出現,所以隨之也就產生了分析其性質、為其下定義的美學這門學問。美學與美術一樣,都是“需要高尚智識的技術”。“美術哲學的本務”便是對美的本質和本體進行探尋,當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等人主張,美術的普遍定義不在于模仿自然,而是在于區別于實物的“非代表性”;第二,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主張,不管描繪什么題材,只要線條和色彩和諧看起來美即可;第三,傳統的保守主義觀點認為,繪畫必須要模仿自然;第四,伊斯特(Sir Alfred Edward East, 1844—1913)將美術分為以實用為目的而進行創作的“有限美術(Finite art/Decorative art)”,以及從材料到形式毫無限制的自由的、獨立的“無限美術(Infinite art/pure fine art)”;第五,鄧因(其人未詳)從社會學、歷史學的角度主張,“美術的盛衰與時代緊密相關”;第六,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主張,美術因“power(作家的技巧)”“imitation(以筆墨刀鋸模仿自然)”“truth(富含宗教及道德的精神)”“beauty(無關本體和性質而給人以愉悅)”“relation(事實上可畫的內涵)”等五個原因而給人以“快美”。另一方面,對于美術的定義,斐諾洛薩認為“在三十五、六年前發生了一場大革命”。這場“大革命”,即是在美術的定義中謀求音樂以及“裝飾藝術(Decorative art)”的地位。經過這場大革命,現在的美術主要由包含了“不依靠實物而是具有其他產生美的要素”的“六美術”——詩歌、音樂、繪畫、雕刻、建筑、裝飾——組成。美術衰敗的原因就在于“流于技巧(skill)”“固守宗派和主義(school ideal tradition)”以及“一味追求對自然的模仿(nature-likeness)”,而拯救其衰敗的辦法則是“獨創性(originality)”“真誠的情感(true love of subject)”以及“藝術形式上的真理(truth of art form)”。[8]453-470
斐諾洛薩的“美學及美術史”講義與西周的相比,可以看出明顯的進步。在內容上,西周介紹的美學只不過是對他人學說的忠實性轉述與啟蒙性介紹,而斐諾洛薩的講義卻包含了深刻的個人見解與批判性介紹。與稍顯滯后于時代的西周的論述相異,斐諾洛薩的講義不僅包括歷史事實的整理,而且也充分地理解和把握住了當代發展的動向;在方法上,西周是按照鮑姆嘉通的定義與方法,將人類的精神分為“知”“情”“意”三個部分進行介紹。而斐諾洛薩則明顯受到了黑格爾和斯賓賽的影響,將美學看作是美術哲學或美術的輔助學,在東西方的對比當中介紹西方的諸種學說。從這點來看,完全可以將斐諾洛薩看作日本比較美學的先驅。這也是著有《東西藝術精神的傳統與交流》的山本正男(1912—2007)為什么會在其著作中將斐諾洛薩作為最早實踐“東西藝術精神交流”的典型,并在第一章“明治時代的美學思想”中介紹了斐諾洛薩后,又專設一章用以討論斐諾洛薩[9]。但是,在高度評價斐諾洛薩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斐諾洛薩在“全面歐化”以及“廢佛毀釋”的大潮中,具有刻意抬高日本美術品價值的主觀意圖。這些相關發言受到特殊的時代及社會背景影響,未必就是客觀的。另外,也正是因為他一貫站在排斥著重對實物進行模仿的寫生主義的立場上,大力贊揚具有濃烈的裝飾性與悠久的歷史傳統的狩野派美術。所以,“著有《破除漢字》、創建羅馬字會,宣稱‘只要是廢除漢字的政策什么都贊成’”[5]563的外山正一,會在《日本繪畫的未來》中諷刺道:“當下談論我國繪畫的人大致分屬兩個流派。其中一個流派即是,聽信外國人的贊揚,認為當今世上的活美術只存在于日本的妄信一族。”[6]149
1890年,斐諾洛薩回到美國,擔任了波士頓美術館東方部的部長,開始以東方美術專家的面貌,積極地向西方世界介紹東方美術的歷史與發展。斐諾洛薩的代表作是他去世之后在有賀長雄(1860—1921)和大村西崖努力下,在日本出版的《東亞美術史綱》(EpochsofChineseandJapaneseArt,1921)。這本“集三十年的苦心探求,不吝財力與勞力,犧牲了所有的快樂”[10]40而成的遺著,主要具有以下幾點特征:第一,與著重于工藝上的技巧、以材料對美術進行分類而不問美學上的動因的西方主流著作相比,該書立足于“滲透在各個時代全體美術工藝中的國民性創意”[10]4;第二,該書并非只研究美術文獻的美術文獻史,而是以美術作品分析為主的實證性研究;第三,該書雖然通過東西間的對比展開討論,但由于“美術是可以依據世界標準而進行評判的事物”,所以該書“將重點放在東西方美術的共通性上,在世界主義的視域下,撰寫東方美術的歷史”[10]8;第四,該書將中日美術關系比作“希臘美術與羅馬美術”進行統一性論述的同時,也強調日本文明的特異性。
那么,對于在《東亞美術史綱》中自稱“曾經在波斯頓作為哲學家嘗試從實證的角度研究美術,到了日本又以考古學家的身份成為美術界的權威”[10]14的斐諾洛薩,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客觀地評價?在該書附有的序言中,曾任東京帝國大學總長、文部大臣的濱尾新(1849—1925)激賞地評價道:“在我的記憶里,斐諾洛薩君不但是美學的泰斗,而且還是美術批評的大家與美術運動的推動者。在我國從美學以及哲學的角度論述美術,就是始于斐諾洛薩。……他基于美學上的觀察,以哲理為依據,考究實物,特別是對東西方的美術作品進行比較研究,極大地顯示了他見識的廣博與作品批評的正確性。這是普通批評家遙不可及的。”[10]2-3但是另一方面,與斐諾洛薩長期共事的岡倉天心卻在講義錄《泰東巧藝史》中,較為冷靜地說:“最近,斐諾洛薩以及畢格羅(William Sturgis Bigelow,1850—1926)等對我國美術具有慧眼的外國學者陸續來到日本,推動了日本美術的發展。斐諾洛薩既是黑格爾主義者,也是斯賓賽主義者。他認真地研究東方美術,只是由于當時資料較為匱乏,所以他的結論往往有很多無法論證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他傳授體系化研究方法的功績仍不容抹滅。”[11]正如井上哲次郎所說,“斐諾洛薩雖然作為進化論者推崇斯賓賽,但與此同時他也信仰黑格爾的哲學,嘗試對兩者進行有機統合。但是在來到日本幾年之后,他開始對日本美術產生興趣,進而埋頭于此,以至于拋棄哲學,成為了日本美術的研究者”[4]60。比起在美學上對西方理論的研究與傳播的貢獻,斐諾洛薩在日本美術史學上的地位則顯得更為突出。他將美學作為藝術哲學具體地運用到美術批評與美術史研究當中,讓當時的人們廣泛地認識到了這門學問的價值。后來的坪內逍遙就曾在書中說,“近來某位美國的博識在東京屢次談到美術的真理,駁斥了世間的謬說”[12],坦言自己是效仿斐諾洛薩寫就了日本首部文藝批評理論著作《小說神髓》。而且在因有效地運用了美學的武器而在文藝批評界嶄露頭角的森鷗外那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斐諾洛薩的影子。當然,斐諾洛薩在日本備受推崇,也與其發言在當時迎合了日本人的情感需求不無關系。他重視日本傳統美術作品的立場,是在激烈的歐化主義的浪潮中感受到不安的人們所贊成的,而他將日本乃至是東方美術置于世界文明的體系之中的做法,又與高舉“脫亞入歐”旗幟希望盡早進入西方文明國行列的洋才派的努力相一致。總而言之,斐諾洛薩是外籍特聘教師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正是他一手開創了日本美術史學與藝術社會學的源流。
三、凱倍爾與美學講座
以1886年《帝國大學令》的頒布為分水嶺,日本的講座美學可以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如上文所述,在第一階段內,審美學尚未從哲學中分離出來。而以文科大學的成立為契機,東京大學的審美學講義開始步入正軌,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1890年,擴充為“審美學·美術史”講義;1891年,改稱為“美學·美術史”講義;1893年,升格為文學院20個講座中的獨立一科,成為世界上最早設置美學講座的大學;1914年,進一步增設“美學·美術史”第二講座。(4)[日]東京帝國大學編:『學術大観 総説·文學部』東京帝國大學學術大観編集委員會,1942年,第440-446頁;東京大學編:『東京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一』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1986年,第588頁。另外,關于各大學美學講座的相關情況,東京大學美學藝術學研究室曾對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北大學、九州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早稻田大學、同志社大學、關西學院大學做過調查,調查結果以極為簡潔的形式發表于日本美學會編《美學》(藤田一美:「諸大學における美學講座等開設に関する資料」『美學』第22巻3號,1971年,第68-70頁)。但在1900年大塚保治(1868—1931)從歐洲留學歸來擔任講座教授以前,“美學·美術史”的講座教授一直處于空缺狀態。大塚就任以前的這一階段,可以稱之為講座美學的第二階段或準備期。在此階段,審美學在制度上得到了確定,并且也隨著講座制的正式導入,教學研究開始有效地運轉了起來。所以,培養一批以美學為專業的日本年輕學者,也就成為這個時期學院派美學發展的當務之急。肩負起這個重擔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的,則是作為外籍特聘教師在日任教時間最長的凱倍爾。
凱倍爾與斐諾洛薩都是對日本講座美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外籍教師。他出生于俄羅斯,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俄羅斯人。6歲便進入莫斯科音樂院學習鋼琴,后在德國耶拿大學跟隨著名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學習哲學。在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后,凱倍爾先是任教于卡爾斯魯厄的音樂學院,擔任倫理學、音樂史以及音樂理論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后成為自由撰稿人,閑居慕尼黑專注于哲學著述。因為他在當時通行的哲學教科書中撰寫了愛德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的章節并且著有專論哈特曼哲學的書籍,所以為哈特曼所熟知。當時,恰好井上哲次郎委托哈特曼尋找一名接替巴斯到東京大學任教的哲學研究者,所以也就因此際遇,得到了哈特曼的推薦,來到東京大學任教。1893年就任后,他終身居住于日本,不僅在課堂內為師生們講授哲學、美學等科目長達21年,而且還在課外為少數有志者開設了希臘語、拉丁語和德語的學習班。如果說,凱倍爾來日前的主要成就在于學術方面,是作為學者對于哈特曼和叔本華哲學體系的研究——《哈特曼的哲學體系》(Dasphilos.SystemE.v.Hartmanns, 1884)、《叔本華的哲學理論》(DiePhi’osophieA.Schopenhauers,1887),那么1893年來日后,他的主要成就則體現在教學上,是作為一名教師,以自身高尚的人格和廣博的素養為日本學界培養和輸送了一大批優秀的學子——夏目漱石、阿部次郎、大西克禮、深田康算、九鬼周造、和辻哲郎、天野禎佑、安倍能成、巖波茂雄、波多野精一等。正如凱倍爾身邊的人回憶得那樣,“先生因為忙于講義等緣故,并沒能出版學術上的著作。僅僅是來日后不久,在哲學會做過一次關于叔本華與哈特曼的邏輯性關系的講座”,“據我所知,先生在公開的場合做過的演講只有兩次。一次是在為了紀念齋藤信策而召開的青年會上,另一次則是在哲學會上”(5)[日]桑木嚴翼:「ケーベル先生に就て」『哲學雑誌』第438號,1923年,第66頁;姉崎正治「ケーベル先生の追懐」『哲學雑誌』第438號,1923年,第72頁。另外,雜志《思想》也推出過“凱倍爾紀念號”(『思想·ケーベル先生追憶號』第23號,1923年)。,可見他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對學生的教育與指導上。
從大學退任后,凱倍爾本想回到歐洲移居到地中海岸旁的小鎮,但由于戰爭的爆發,他不得不在橫濱的俄國領事館內度過了人生最后的十年。在此期間,他為雜志《思潮》《思想》撰寫了一批散文,并先后在巖波書店結集出版。論文集的內容既包括發表在雜志上的散文,也包括他為了紀念席勒和哈特曼而發表在雜志Wahrbeit的論文以及在哲學會等地的演講稿。另外,作為凱倍爾散文的主要翻譯者的久保勉(1883—1972)還在《凱倍爾博士小品集》(KleineSchriften, 1918;KleineSchriften,NeueFolge, 1921;KleineSchriftenⅢ,1925)的基礎上編有《凱倍爾博士隨筆集》(巖波文庫,1928)以及回憶錄《與凱倍爾先生同行》(『ケーベル先生とともに』巖波書店,1951)。由于凱倍爾并沒有留下像斐諾洛薩那樣詳盡的講義記錄,所以我們只能通過相關的學史資料,了解到以下內容:
他用英語講課,不使用翻譯。在內容上,他的“美學美術史”講義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作為西方美學史的概要,從柏拉圖講起,追溯了亞里士多德和普洛丁的思想,在指出西方中世思想的重要性后,由萊布尼茨、鮑姆嘉通而過渡到德國觀念論。其次,依據德國觀念論的考察方法,辯證地分析了美和藝術的本質;最后,著重講以“審美認識”與“直觀”構筑的體系化美學,并對藝術進行了特別的研究。因為該門課程學名是“美學美術史”,所以在美學的講述之外,也有很多涉及到西方美術史的內容。有的年份,作為美術史的替代,也講述音樂美學。據《東京帝國大學學術大觀》(昭和十七年)所記,凱倍爾的講義“對比真正意義上的美學講義,在今天看來,也絲毫不會顯得粗略。雖然當時在大學課程上并沒有美學講讀,但他在家中購買了柏拉圖、謝林、尼采等人的原著召開講讀會,成為了實際意義上的美學講讀。除此之外,他還召開了以一般詩學以及浮士德論為題的特殊講義,并作為講師在東京音樂學校教授音樂學”。[3]590
果然比起講義的具體內容,更能讓學生乃至日本學界感佩的,恐怕還是凱倍爾的人格,即井上哲次郎所說的“凱倍爾對于錢財看得很淡,不旅行,也沒有妻子家眷。正因為如此,他得以用隱士的態度埋頭于自我喜愛的精神上的學問。……這種具有超越意義的隱士作風自不用說是高尚的,對于金錢的淡泊也著實讓人敬佩”[13]。并且作為一名教師,他與年輕的學生們平等、友善地相處,以自身高尚的人格魅力與廣博的學識素養,培養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學者。這一點正如桑木嚴翼所說,“當下在學界活躍的人們,大部分是出自先生門下”[14]。這些凱倍爾的學生們,在日后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成為哲學界、美學界的主導者。其中,夏目漱石(1867—1916)就曾專門撰文稱贊他的老師凱倍爾為東京大學文科教授中人格最優秀的人物:“如果到文科大學去問,這里人格最高尚的教授是誰?一百個的學生中有九十個,都會在說出屈指可數的日本教授之前,先回答是凱倍爾”[15];1899—1902年就讀于哲學科、長期與凱倍爾居住在一起的京都大學美學講座的開創者深田康算(1878—1928)說,“按照年月來數的話,我從認識先生到現在已經度過了23年,在我到目前為止的生涯中幾乎有一半的歲月都是與先生共同渡過的”[16],他專門謳歌道:“在我所見到的范圍內,凱倍爾是唯一一個在現實生活中活出了‘高尚靈魂’(Sch?ne Seele)的人”[17]。除此之外,也如三木清(1897—1945)所說,“教養的觀念主要就是漱石門下的弟子們在凱倍爾博士的影響下形成的”(6)[日]三木清:「読書遍歴」『読書と人生』新潮文庫版,1974年,第26頁。,以阿部次郎(1883—1935)的《三太郎的日記》以及《人格主義》為代表的、流行于大正至昭和時期的“教養主義”以及“教養派”的成立就與凱倍爾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以凱倍爾為代表的外籍教師的教導和培養下,東京大學美學專業的畢業生們開始逐漸地成熟起來。他們紛紛走出國門,到美學的發源地西歐學習和生活。學成之后,又陸續回到祖國,走上講壇,成為了獨當一面的美學研究者。作為其中的代表,大塚保治于1900年結束留歐后,出任升格為獨立部門的東京大學美學講座的初任教授;深田康算、阿部次郎、矢崎美盛(1869—1931)也分別于1910、1923、1925年歸國后,出任京都大學、東北大學和法政大學的美學教授……與此同時,慶應義塾(今慶應義塾大學)、東京專門學校(今早稻田大學)等各大私立名校也相繼開設了美學課程,一時群星璀璨,涌現出了坪內逍遙、森鷗外、岡倉天心、大西祝(1864—1900)、立花銑三郎(1867—1901)、大村西崖、金子筑水(1870—1937)、高山樗牛、島村抱月(1871—1918)、植田壽藏(1886—1973)等一大批杰出的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在他們的牽引下,日本學院派美學開始邁向了新的發展方向。
(在撰寫過程中,湖北大學梁艷萍教授和山西大學臧新明教授在資料提供、術語校正等方面,給筆者提供了較大的幫助,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