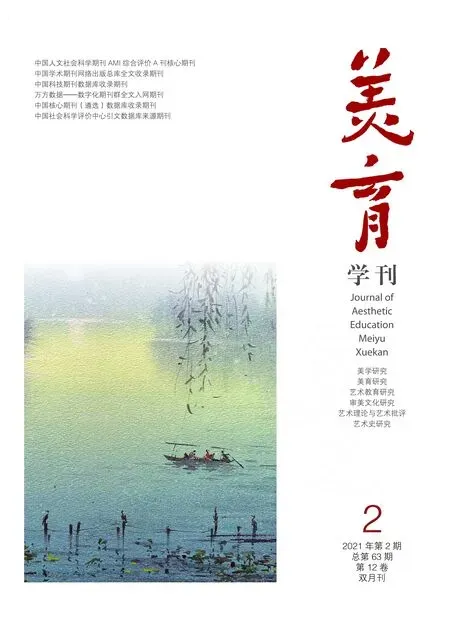現代主義藝術真實觀辨析及其審美價值重構
湯克兵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1331)
自馬奈以來,現代繪畫不同程度地反對再現古典藝術中的題材乃至肢解圖像本身,諸如線條、色彩、形狀等媒介材料顯露出它本來的面目,繪畫基底的物理屬性逐漸成為繪畫的表達媒介和主題。由于現代主義繪畫排除了隱喻與影射,脫離外在可指稱的世界,只能通過媒介來自我指涉。為此,現代主義批評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認為視覺藝術的本質及其美學意蘊在于媒介的“純粹性”。然而,格林伯格對媒介的理解僅限于純粹知覺層面的媒介“特異性”(自我指涉),也就忽略了媒介的“語境性”(他者指涉)。其實,現代藝術媒介論無需在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之間進行區分。如果要走出藝術媒介自律論的循環論證陷阱,就必須回到藝術的真實性問題域:繪畫媒介自身如何成為繪畫的主題?繪畫媒介的“可見性”是否等同于繪畫藝術的真實性?本文從媒介現象學視角來理解現代主義藝術的美學觀念:藝術的真實應該是媒介的真實,即媒介的可見性與真誠性的統一。繪畫的平面性或雕塑的三維性既是某種可見的感知物,同時也是一種令人揣測的亞媒介空間。藝術家通過對藝術媒介的巧妙操縱,讓藏匿在媒介中的訊息發出聲音(媒介真誠地“說話”),并由此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來重構主體與真實的關系,這正是現代主義藝術將對媒介表現力的探索視為一種新的實踐范式與審美意涵的原因所在。
一、繪畫媒介的可見性與真實性
傳統繪畫為了再現外在世界,往往要隱藏繪畫的媒介性要素。藝術家通常把世界看作是一幅透過窗口看到的“圖像”,世界仿佛如實投影在窗玻璃上的樣子,這種“科學化”的觀看方式,即“所知”對“所見”的理性宰制實際上遮蔽了世界的本來面貌。諸如線條、色彩、形狀等圖畫標記就只是可供心理投射或篩選的一堆材料而已。而現代主義藝術通過對客體圖像的肢解或重組,繪畫中不可還原的平面性、顏料與筆觸意識,以及長方形狀等這些被遮蔽的媒介重獲“可感”,變得“可見”。當充滿意義的“圖像—符號”被剔除,點、線、色塊這些非模仿性的要素及其載體特征就獲得了自由,其外形和感知進入整體的可見顯示階段,并最終成為藝術“表達”的媒介。
按照象征派詩人古斯塔夫·卡恩的解釋,藝術的基本目標是將主觀的事物客觀化(意念的具體化),而非將客觀的事物主觀化(經由某種性格所看到的自然),也就是把自我提升到自然之上。例如,同樣是稱贊德拉克瓦的繪畫,波德萊爾認為是顏色和形式把主題的氣氛表達得恰到好處;而卡恩看到的卻是顏色形式的主觀性和表現力,相當于或甚至超越所描寫的主題[1]61。同樣是強調媒介的表現力,波德萊爾“先入為主”強調主題至上,而顏色和形式只不過是其附屬因而變得不可見;卡恩則主張媒介的可見性,即目光能夠捕捉到藝術媒介的自主性。在這里涉及一個基本問題:我們觀畫的時候,是欣賞繪畫的肌理、線條、色彩等要素,還是逼真的外在形象?即藝術媒介的自主性到底指什么。
所謂藝術媒介的自主性,即現象學所說的回到事物本身的意向性。從形式上來看,現代主義藝術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去圖像化”的強烈意識,正如海德格爾所言,“為著把這幅畫當作純粹的物體要素來加以觀察,首先就需要我們的自然觀察方式的某種變易,需要一種去圖像化(Entbildlichung)的觀察方式。運用這種觀察方式,感知的自然的傾向才可進入圖像的把捉的方向”[2]。繪畫物性的凸顯,旨在強調繪畫的自主性,但是,繪畫又不能等同于物。因此,媒介的物性力量,對于審美想象尤其重要。
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解釋似乎遠離了波德萊爾式的象征性主題,因而更接近卡恩的媒介自主性解釋。于是,他認為現代主義藝術的核心任務是強調藝術媒介的“純粹性”, 這樣才能使得媒介的物質特性具備獨立的審美價值。他認為藝術的獨特魅力源自媒介的異質性。由于媒介的重要性與異質性,每一種藝術都將成為“純粹的”,并在其“純粹性”中找到其品質標準及其獨立性的保證。體現在繪畫領域,則是突出繪畫的“平面性”原則。“平面性”是繪畫藝術獨一無二和專屬的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將“平面性”的實現脈絡從馬奈、塞尚追溯到馬蒂斯和立體主義,而且認為以波洛克為代表的抽象表現主義以及隨后的色域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仍然是對“平面性”的延展與深化。[3]“平面性”作為繪畫的界限,不僅強調了繪畫的視覺經驗,而且是使得繪畫自我敞開的 “場所”。
事實上,格林伯格關于現代主義繪畫的媒介論解釋并非獨創,而是受惠于藝術家漢斯·霍夫曼。漢斯·霍夫曼將藝術的真實與媒介的物性表達聯系起來,他認為“任何深刻的藝術表現都是對真實一種有意識的感覺的產物。這牽涉到自然的真實和表達媒介內在生命的真實”[4]174,而表達媒介乃是給予情感與概念其可見形式的物質方式。探索媒介的性質是了解藝術本質的一部分,也是創造過程的一部分。[4]172-173據此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漢斯·霍夫曼以及后來的格林伯格等人的現代主義“媒介論”,試圖建構一條由媒介物性表達不斷向真實性推進的演化路徑,即如何使繪畫最終成為一種純粹的視覺藝術。按照格林伯格對現代主義繪畫的本質定義,“一張釘起來的畫布”也可以是一幅繪畫,盡管不必然是一幅成功的畫。在一幅畫變成一個任意物品之前,即使圖畫的平面感與畫布的物理平面合二為一,幾乎接近一張空畫布,也會伴隨著繪畫媒介的物質性與圖畫的視覺特征相互抵牾、最終融合的過程。因此,媒介與主題的融合意味著繪畫媒介的物質特性可以直接成為繪畫主題:繪畫作為實物與繪畫作為圖像之間的等同性。
二、媒介真誠性作為審美判斷的前提
格林伯格的媒介純粹性論斷,依據的是康德的自我批判邏輯。因此對媒介的理解僅限于純粹知覺層面的媒介“特異性”(自我指涉),也就忽略了媒介的“語境性”(他者指涉)。這種藝術媒介自律論更容易掉進循環論證的陷阱。當繪畫不需要通過再現或表現某種外在或內在的對象來獲得其本質,而是通過自身媒介的真實呈現的時候,那么何以保證媒介的呈現與觀看品質之間的有效統一呢?格林伯格并沒有給出解釋。不過,T. J. 克拉克某種程度上將媒介的意義生成語境化,或許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啟示。
克拉克認為,現代主義藝術媒介就最為典型地成為否定(negation)和疏離(estrangement)的場所。如此,媒介不僅是某種藝術身份的物質載體,而且也是意義生成和拆毀的隱喻性場所(site),同樣也是身份被疏離的社會場所。[5]換言之,現代藝術家在對題材、色彩、顏料、光線、線條、空間、畫的表面和布局進行不同程度的肢解和破壞的同時,實際上也迫使藝術家思考繪畫媒介自身的真誠性與純粹性,即在外在現實的不確定性這個前提下,媒介如何被闡釋為是對符號的巧妙操縱,并由此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來重構主體與真實(現實)的關系。
當藝術彰顯其獨特的媒介特征,媒介自身既是表現方式的物質載體,同時也獲得了其獨特的符號意義。我們知道,現代主義與裝飾藝術都強調幾何造型,然而現代主義在根本上不同于甚至對立于裝飾性藝術。裝飾性藝術只能以它“目的”上的優點而存在;它只能借著自身和指定物體間的關系來獲得生命。它基本上是附屬的,必然不完整的,所以必定要先滿足心靈,才不至于讓注意力分散到為其辯護和使其完整的形象。[6]與裝飾藝術必須要融入周圍環境不同,現代主義繪畫藝術基本上是獨立的,它和一切環境都不協調。現代繪畫藝術存在的理由就是它本身,因此繪畫必須創造性地利用它自身的媒介來思考繪畫的問題。由此,藝術媒介——語言,或作為語言的形式結構,是受媒介決定——的獨立性開始變成美學理論的一環:材質決定了“真實”,而待修飾的那塊平面的性質更決定了“實在”。[7]275
如果媒介或形式結構發生變化,內容和意義也就跟著變化。現代藝術對“新”的追逐就在于藝術家運用不同的造型語言(藝術媒介),或將內在情感主題化(表現性),或思考繪畫本質問題(構成性)。從藝術家的創造性以及藝術形態的豐富性來說,現代藝術風格或形式的變化建基于藝術家對材料或形式的探索與對捉摸不定的情感的表現。所以,藝術真實或者藝術家尋求的真實仍然是“每種藝術表達方式的真實”,無論是繪畫還是雕塑“都受到了其本身界限的限制,并且必須通過適用于這種藝術表達方式的方法來進行理解”[8]。
從繪畫的純粹視覺性來說,可見的只有扁平的表面、顏料與筆觸以及由此構成的形狀,而附著其上的情感或思想是不可見的,或者說是模糊和不確定的。因此,在既不參照外在事物的外觀,又避免淪為裝飾的前提下,現代主義藝術理論為保證其審美品質就要賦予媒介的真誠性和有效性。正如藝術史家琳達·諾克林所說,從繪畫的事后發展來看,大概屬現實主義求實或求真概念的轉化,這一概念從原來的“忠于個人對外在物理界或社會界的感知”之意,轉變成意指忠于材質——即忠于物體表面平面性——及(或)忠于個人內在強大的“主觀”情感或想象力而非忠于外在現實。[7]290在琳達·諾克林看來,裝飾藝術的平面性的特征影響了現代主義繪畫,最為鮮明的例子是,后印象派(尤其是高更)與法國象征主義藝術深受裝飾藝術的影響,而且都強調“以平面來表現真實”,并自覺地以“忠于物性來謀求裝飾中的真實”作為藝術準則。所以,現代主義繪畫中的“平面性”暗示的是繪畫媒介之真,而非畫家所描繪的外在世界之真,更不是這一媒介所“反映”出的這一世界之真。[7]293
更為基本的是,藝術家意識到繪畫媒介并非被動地作為彰顯主題的附屬,相反,繪畫媒介的物質特性可以構成繪畫主題或優先于主題并且具有積極因素。比實際題材或主題更為重要的形式和構圖是構成繪畫表現力的最大潛在要素。藝術家的直覺感受組織線條、色彩、形式和結構,從而使作品具有一種畫家個人的意圖的效果。[9]關于這一點,法國納比派的主要理論家莫里斯·德尼早在1890年的評論中就有類似的精妙見解,他提醒我們最好記住,“一幅圖畫——在其變成一匹戰馬,一個裸女,或某件軼事之前——基本上是一塊平面,上面涂有以某種秩序搭配起來的顏色”[1]118。
如此看來,當繪畫意識到其構成性問題,繪畫就回到了媒介本體論的問題域。繪畫的真正“主題”乃是對其自身的揭示或自我指涉:“基本上是一塊平面,上面涂有以某種秩序搭配起來的顏色”,觀察者(藝術家和觀眾)理所當然地就把“平面”當作一個猜想的亞媒介空間(總覺得媒介背后隱藏著什么),而這正是現代主義藝術將對媒介表現力的探索視為一種新的實踐范式與價值取向的原因所在。媒介的可見性背后,即是一個亞媒介空間,更是一個與創作情景與意圖關聯的語境化空間,它指向不可見的意義本身。因此,“媒介的純粹性問題出現在一個媒介變得自我指涉的時候,這時它放棄了其作為交流或表現媒介的功能。此時,這個媒介的某些特定代表性形象就被經典化(抽象畫、純音樂)而變成體現了這種媒介的內在本質了”[10]。
三、繪畫主題即媒介的符號化過程
檢索現代主義藝術的風格演化邏輯發現,各類藝術的主題即是媒介的符號化過程。在塞尚的繪畫中,可以確定的是“看見”不僅包括看到色彩的筆觸,而且還包括這些筆觸構成的對象(類似于理查德·沃爾海姆關于“看進”的“雙重性”理解);而且藝術擁有充實而連貫的世界,而世界則是在觀看中,確切來說是在感知中出現的;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越來越無法確定,觀看過程中如何產生了對事物的區分與聯系。因此表象的任務是雙重的:既要彰顯外在世界的固定性和實體性,又要承認觀者并不知道自己的視覺是如何使對象認知成為可能。在藝術史學家克拉克看來,“塞尚的繪畫將視覺意識形態——作為獨立活動的視看觀念,具有它自己的真實性,以及進入事物本身的獨特方法——推向了其邊界和臨界點”[11]。克拉克所說的“邊界和臨界點”即是繪畫中基于光學幾何學知識的直線透視問題。在傳統透視繪畫中,觀者與風景之間總要暗示一種空間上的連續性,這樣才能順利地將觀察者與理想化的客觀事物秩序聯系起來。然而這種“一目了然”的視看關系并沒有實際地呈現出視覺活動的復雜性。通過細節簡化與視點調整,塞尚實際上是既保持了描繪事物的堅實感,同時又突出了圖畫平面的二維特征。如此一來,正如梅洛-龐蒂所強調的,繪畫的媒介特征與可見主題的感知經驗之間不再涇渭分明。因為“光線、照明、陰影、反射,所有這些被研究的對象并非完全都是現實的存在,因為它們都如幽靈一般,具有的只是視覺上的存在”[12]。
傳統繪畫的媒介被掩藏于主題之下乃至要“不可見”,可見的是圖像的對等物和可操縱的符號。只有當連貫而逼真的圖像被打亂變得陌異時,目光才能投向媒介并讓其可見,這樣才有可能獲得對媒介載體性質的認識;或者說,符號遮蔽了人們射向承載著符號自身載體的目光,只有當符號被移除時,符號的媒介真相才會立刻表現出來。因此,在馬蒂斯看來,感受只有在媒介的表現過程中才能被感知,對生命的感受與表現方式之間是不能分開的,“表現方式并不包括面部反映出來或猛烈手勢泄露出來的激情”,“而是整張畫的安排都具表現力的”。[1]180
盡管畫家承認作為表現方式的媒介與繪畫主題不可分割,但媒介自身仍然是情感表現的支撐,并沒有達到要與繪畫主題融合的意識。以畢加索和布拉克為代表的立體主義進一步拉近兩者之間的距離,繪畫的媒介與主題開始融合。這意味著繪畫試圖擺脫既有觀念或意識形態的束縛,專注于探索藝術媒介自身的特性,并制造繪畫“平面”的組合效果。立體主義者承認繪畫空間是一種特殊的“平面空間”,他們對繪畫空間的拓展,顯然是對文藝復興時期阿爾貝蒂以來的繪畫觀念(如何在二維平面上創造出三維的效果)的反轉,即繪畫對象必須接受平面“擠壓”,然后再將它們“合乎邏輯”地畫在二維平面上。基于幾何學的透視法對固定視點的限制,相當于胡塞爾現象學意義的“側顯”,因為觀者總是從某個固定的視角來看事物的。也就是說,多維性的隱失其實是必然情形,不可能所有的面都必須同時呈現出來。然而,“畢加索意圖用多維性、不同的相互補充的景象的同時呈現,來消除我們的視角的局限性。因此,我們也能理解那種把空間性歸結為平面性的趨勢,立體的各個不同面似乎必須被折疊起來,必須僅僅保持在一個一目了然的平面上”[13]。畢加索力求把不同的視點統一起來,立體對象仿佛被拆開后在平面上延展開來的樣子,這樣一來,我們并不是什么也看不到(看似只有變形和扭曲的東西),然而事實上是我們看到的更多,我們可以同時(一目了然地)看到事物的多個“側顯”,這個看似無序與雜聚的視覺混合物,實際上是未經“視覺意識形態”調節前的景象(笛卡爾所謂上帝的直覺)。繪畫主題必須與媒介自身的本質協調,即主題從或隱或顯的繪畫平面構造組合中以形象的方式被“看”出來,而不是外在觀念的強行附加。在立體主義的拼貼實驗階段,繪畫平面上的報紙、字母、木頭紋理圖畫等拼貼要素本身就是實用物品的碎片。然而,由于平面既作為實際基底存在,又是一個符號性的表面,所以繪畫表面存在一種現實物與藝術表達之間的張力。如此看來,這些“碎片”能夠用雙重眼光來加以觀照,“一種將它們視為與線條和色彩并駕齊驅的形式元素,另一種將它們視為它們從中分離出來的那些實際內容的表達”[14]。隨著材料碎片的任意聚集,媒介的可塑性變成了未加修飾的、異質的“現實”(其本性乃是分散的、混雜的、偶然的)的一種譬喻。真實材料配合著顏料所建立的抽象結構,起著接近“真正現實”的主題作用,媒介與主題的積極融合和交互影響構成布拉克所說的“新的統一體”。同樣,馬列維奇的至上主義“方塊”是純粹抽象的表達,是描繪直接感覺(而非感覺的外在反映)的“新符號”。方塊是空間與節奏本身:“方塊=感覺,白底=這感覺之外的空無”。媒介的真實性同樣是被完美地策劃出來:《黑色方塊》不僅作為一幅畫中之畫,而且也作為一種對隱匿的繪畫載體的突然昭示,這種載體從通常的、表面的繪畫世界之中,且因為藝術家極為彰顯地使用強力而脫穎出來。[15]只有當“平面”否定一切感知內容與敘事邏輯,媒介的這種極端物質性才能顯現,同時這種極端物質性也才能和它所對應的絕對精神性相統一。
我們把焦點轉向抽象表現主義,美國“行動畫派”的繪畫主題與“行為”之間的關系也得到重構,繪畫的媒介即是自己的行動軌跡。以杰克遜·波洛克為代表的“行動派畫家”試圖掙脫“架上畫”的“畫框”限制,將畫布掛在粗糙的墻上或放在地板上,最大限度地將身體運動與情感的自發性有機地整合在畫布上。在《藍桿》系列畫中,波洛克發明的滴色畫法任由各種縱橫交錯的顏料與腳印、煙頭和碎木屑等雜物混融,遠離了形象與空間的構造。此時作為真實對象的畫布就成了繪畫的載體,畫面成了畫家身體痕跡的記錄。正如批評家哈羅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所說,“在某一個時刻,帆布開始在一個又一個美國畫家眼中成了表演的舞臺,而不是復制、重新設計、分析或者‘表達’一個真實或假想事物的空間。帆布上產生的不是一幅圖像,而是一個事件”[16]。由于藝術家的繪畫行為成了生活中偶發的“事件”,繪畫作品具有“與藝術家的存在相同的形而上的本質”,因此也就打破了藝術與生活之間的界限。如此一來,繪畫作品很有可能被看作是一件現實生活中的普通物品。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戰后50年代的歐洲繪畫藝術也從再現轉向了對象本身的物理真實,開始脫離現代主義繪畫的平面性規則。繪畫的事實不僅停留在色彩與線條的表現力層面,而是材料與現實的直接相遇,藝術媒介的物性漸漸成為現實。意大利藝術家阿爾伯托·布里(Alberto Burri)與盧西奧·豐塔納(Lucio Fontana)強調畫布作為材料物品的整體實在性,可以直接體驗,而不需要形式上的先入為主。藝術家并不把原材料的物質性所揭示的“本體”現實看做理想的或超自然的世界,而是看作單一的、真正的現實,所有東西都是由這種現實構成的。材料的實在性既作為表達內在“真實”的基礎,同時又是抽象的空間概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