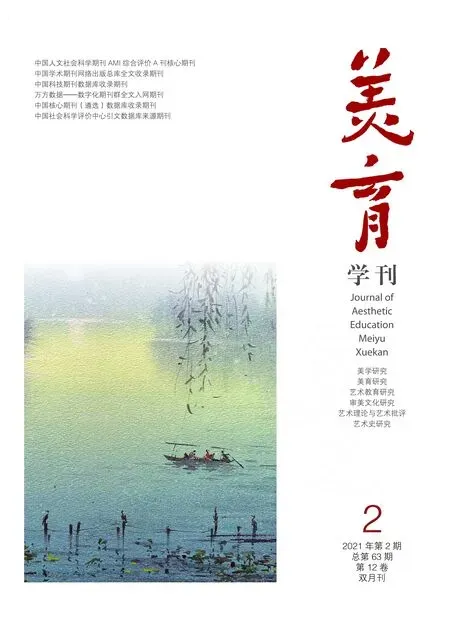作為社會溝通系統的藝術與美學
——尼克拉斯·盧曼的藝術美學溝通觀
鄭 端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是現代德國著名的社會系統理論家。身為社會系統思想總工程師的盧曼,以1984年問世的《社會系統》一書為界,其學術生涯前期主要設計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的一般原理,后期則規劃高度抽象的系統理論如何落實到現代社會復雜領域的具體操作層面,探究了幾個關鍵的社會功能系統,最終建立社會理論(Gesellschaftstheorie)的宏偉理論脈絡。1997年付梓的《社會中的藝術》(DieKunstderGesellschaft)(1)N. Luhmann, 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97.此書有英譯本;中譯本見《社會中的藝術》,張錦惠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一書描述了現代社會里藝術系統這一功能系統,書中提出的藝術系統論是其前期系統理論與后期社會理論相聯接的一座橋梁。身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社會思想家,盧曼的理論成果跨越貫通社會學、歷史學、教育學、文藝美學等諸多學術領域;近年來,國內學界對盧曼學說的研討,尚未充分重視其藝術系統論所開創的文藝研究新范式。
一、藝術作為社會溝通系統
盧曼藝術美學溝通觀的理論背景預設是,社會演化的結果導致現代社會運作的結構層面上出現了一種新的分化形式——功能分化(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現代社會作為一個全社會總系統逐漸分出形成了獨立自律、迥然有別卻又并行不悖的諸多功能系統,作為社會子系統的藝術系統(Kunstsystem)是諸功能系統之一。藝術與政治、教育等其他相鄰的社會功能系統在結構上是高度相似的,但是在系統的運作(Operation)層面上卻彼此迥然不同。在藝術系統內部執行的基本也是唯一的運作元素是藝術溝通(Kunstkommunikation),藝術溝通就是藝術運作,藝術本身是一種社會溝通(系統)。藝術系統與其他功能系統之間,存在著“結構耦合”(2)“結構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指系統與其環境之間互為存在前提、彼此依賴的關系。的相互依賴與彼此觀察,但不同的功能系統彼此終究不能直接溝通,因為藝術系統的藝術溝通與政治系統的政治溝通、教育系統的教育溝通三者之間是截然異質的溝通方式。
面對現代社會語境下的藝術運作及美學話語,盧曼的藝術系統論啟發我們將觀察思考的焦點從“美學”“藝術家”“藝術品”等概念范疇的“一階觀察”(Beobachtung erster Ordnung)的視野切換到“二階觀察”(Beobachtung zweiter Ordnung)的視角,也即將藝術視為一種溝通交流,換言之,將藝術觀察為一個社會溝通系統。
二、二階觀察慧眼觀照下的美學溝通
(一)美學溝通:一種藝術溝通
盧曼是文藝現象的二階觀察者,“二階觀察”著重觀察“一階觀察”的盲點(3)盲點的產生是由于觀察者在觀察藝術或美學時,無法同時觀察到觀察者自身(及其所使用的區分)。盧曼的觀察的概念是借助一個區分進行標示,觀察者不僅指主體之人,還主要是指系統。,是對觀察(者)本身的觀察,據此,美學或審美,由二階觀察建構成一種社會溝通,即美學溝通或審美溝通。對于美學或審美的一階觀察模式固有其專業學術方面的價值意義,但其學術洞見的取得往往是以觀察盲點為前提和代價的。盲點就是,美學研究,包括審美教育,它們只能看到其憑借專業術語區分所能看得到的東西,而看不到它們所看不到的事物;進一步而言,它們自身恰恰看不見這一點,那就是它們看不到它們所看不到的現象[1]。二階觀察者基于對一階觀察的觀察盲點的觀察,指出美學是一種溝通,一種審美溝通;美學就其學科性而言,是從現代社會學術子系統分出的一個分支系統。那么,美學是否屬于藝術系統?美學溝通與藝術溝通有何種關系?
質疑美學的藝術系統歸屬性的二階觀察者大有人在,德國盧曼研究者Gerhard Plumpe指出,美學與藝術彼此互為系統和環境,美學從來不是藝術系統自我反思的理論,而是從哲學視角對藝術施加外來觀察。Plumpe堅持美學的學科性或科學性,認為美學是哲學對18世紀藝術系統之分出形成這一新情況的回應。[2]盧曼也看到了美學的尷尬的系統歸屬性,但他力排眾議,堅持美學屬于藝術系統,審美溝通是一種藝術溝通。他認為,美學起源于哲學,是哲學的分支;而哲學一直以來擁有一種模棱兩可的地位,所以美學是“雙籍兩屬”的[3],既屬于哲學,又屬于藝術這一溝通系統。
就美學歸屬于藝術系統而言,盧曼將美學指認為藝術系統的自我反思,即藝術系統的一種自我觀察,藝術整體同一性由此成為藝術溝通主題。既然美學屬于藝術系統“反思理論”(Reflexionstheorie)[4],而反思理論屬于功能系統自我描述的一種形式,于是美學即是藝術系統的自我描述。“自我描述”(Selbstbeschreibung)是指產生系統自身同一性(Identit?t)的一種系統運作方式。藝術系統自我描述的任務是,就什么是藝術,即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加以規定。由于藝術系統是封閉運作的自我指涉的系統,唯有藝術系統自己才能界定藝術是什么[5]208-209。此種下定義的運作既不能通過經濟系統的價格規定,也不能借助學術系統的真理驗證予以確認,而是藝術自我描述的任務:將何者算作藝術的規定權交給藝術系統本身,只有藝術系統的自我觀察才能劃定系統的邊界,即何謂藝術——現代社會功能分化的運作邏輯是,只有藝術本身方能規定藝術之為藝術。
盧曼觀察著一個描述著自身的藝術系統是如何標示藝術本身的,并基于藝術系統自我描述做出了“重新描述”(Wiederbeschreibung)或“再描述”(redescription)[6]。此種“再描述”,是對于藝術系統自我觀察的外來觀察,一種來自社會的學術系統之子系統“文藝社會學”之分支系統“藝術系統論”的二階觀察。二階觀察著眼于觀察一階觀察的盲點,即包括美學在內的藝術自我描述的“偶然性”(Kontingenz,事情本來也可以是另外一種樣子,總有別的可能性)與“選擇性”(Selektivit?t,本來亦可以有其他的選擇)。以美學為代表的藝術自我描述,其一階觀察的偶然性和選擇性就在于,美學史上用于自我描述的“區分”(英語為distinction,德語為Unterscheidung)(4)“做出一個區分”(Draw a distinction)是盧曼藝術系統論也是藝術系統建構的運作緣起。受英國數學家喬治·斯賓塞布朗(George Spencer-Brown)的形式邏輯運算啟發,盧曼認為藝術系統的建構起點是在世界之中做出一個區分,這個區分瞬間將世界這一無邊無盡的運作觀察視域劃分成有差異的兩部分。,本可以被其他的區分選擇所替代——以美學為代表的藝術自我描述是基于特定首要區分語義而表征系統的難以統一的整體同一性,這些區分語義(例如“感性/理性”“美/丑”的區分)作為難以動搖的本質內核具有絕對的真實確定性,恰是這些看似真實確定的區分語義的偶然性或選擇性,是包括美學在內的藝術自我描述的觀察盲點,是系統自我描述進行反思的不思或無思前提。
根據藝術系統自我描述史的基本區分語義,盧曼對歐洲藝術自我描述的外來描述(Fremdbeschreibung)分為五個演化階段:(1)發軔期文藝復興;(2)18世紀啟蒙運動對藝術整體統一的反思,其結果即是美學(sthetik);(3)浪漫派對藝術自律化問題的應對之道——藝術批評;(4)20世紀,藝術品本身即是藝術自我描述,藝術品與藝術理論之間,藝術運作與藝術自描述之間的系統內部界限趨于崩潰;(5)當代藝術自我描述,基于系統的自我否定,達成藝術自律的極致化。[5]209-219
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藝術自我描述面臨的問題是:是什么將詩藝與戲劇和繪畫聯系起來,統一為一個整體?藝術系統就其自身的整體統一性開始反思,美學作為一種就感性感知施以評判的理論應運而生。盧曼將美學標識為“藝術的哲學式反思理論”,把美學歸列入藝術這一功能系統的自我描述之中。但盧曼也看出,“美學”作為一種“學”,一種理論,自誕生以來便不能完全擺脫其“學問”或“學科”(Wissenschaft)的基因;然而,美學的科學化原理或學科學術性只有面對“藝術批評”時才得以彰顯——作為藝術的抽象理論的美學無從判斷具體藝術品的質量,美學把藝術品評判的任務托付給藝術批評。美學自從鮑姆嘉登時代以來便主要承擔了藝術系統自我描述的任務,由此美學著眼于藝術系統抽象的結構層面,而不是藝術品生產的運作層面,就藝術品創作或觀賞的注意事項,美學不提供具體的依據。
正是歸功于誕生在18世紀的美學,藝術系統的自律才得以發祥,藝術從此不再依賴于宗教、政治、道德、科學的直接影響。藝術自律透過美學而建立起來,其弱點也如影隨形:自律性不接地氣,難以銜接起藝術品的具體運作層面;哲學式的美學與考據實證化的、著眼于藝術品本身的藝術學研究逐漸分道揚鑣。時至今日,就連盧曼也疑慮重重:與哲學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美學,仍然有效適用于藝術系統自我描述嗎?盧曼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盡管自鮑姆嘉登至黑格爾以降,作為藝術理論的美學一直與哲學之間藕斷絲連,美學也以此不得不忍受與藝術本身無甚淵源的理論化的滲透;然而,說到底,美學是對藝術演化分化中的藝術自身意義問題的回應,美學并不專注于哲學理論的普遍有效性的證明——美學作為一種源于啟蒙運動的藝術哲學,其理論反思將不同藝術門類的整體統一予以溝通主題化,促進了藝術自律化,與藝術系統自我描述史上其他四種基本區分語義一道,共同從藝術系統內部描述了藝術自身,屬于藝術系統的自我描述形式。藝術自我描述作為一種藝術溝通形式,是藝術系統面向自身同一性的溝通性反思,美學也屬于這種對藝術溝通本身加以溝通的藝術系統自我觀察及反思,所以作為審美溝通的美學是一種藝術溝通。
(二)藝術系統論視域下的美學
盧曼以二階觀察洞悉傳統的哲學式美學的潛在觀察盲點,指出美學反思藝術自律性及同一性的主要任務早已完成,藝術系統自我描述的重任已相繼被浪漫派的藝術批評以及藝術品本身所接管。但盧曼是想強調他的藝術系統論與美學之間的差異,而并非藝術系統論凌駕于美學之上。二階觀察固然看到一階觀察的盲點,但二階觀察并不必然比一階觀察高明,因為二階觀察也要選用區分進行觀察,區分自身結構必然攜帶觀察盲點。任何觀察都無法一勞永逸地揚棄盲點,只能將盲點向未來不斷推移,事實上正是盲點使得區分及觀察成為可能。那么,藝術系統論作為一種區別于美學的系統理論,與美學之間的差異何在?
與美學有別,盧曼將自己的藝術系統論標記為“審美理論”(?sthetische Theorie)[5]221,但這種審美理論的坐標并不在藝術系統內部,而是以一種高度抽象、絕緣于具體藝術操作的方式運作于學術系統內部,坐標定位是學術系統的分支系統——藝術系統論。鑒于藝術系統論是一種學術溝通,而美學被盧曼視為一種藝術溝通,二者截然不同,因此藝術系統論是一種“非美學”,是藝術系統之外的對藝術的學術論題化。藝術系統論既不為藝術美學理論提供啟迪,也不給藝術品生產開出妙藥良方,而是把來自藝術系統的“激擾”再度描述為藝術系統論的學術溝通,轉譯為二階觀察的系統理論語言。藝術系統論是對藝術系統的外來外在觀察,并不繼承以美學為代表的藝術哲學的觀察盲點。現代社會,藝術的內部觀察,即藝術自我描述,由藝術品執行,藝術品本身同時成為藝術客體和藝術哲學(即藝術理論或反思理論),運作和自我描述的界限趨于模糊。藝術的終結其實是包括美學在內的傳統藝術哲學的終結,而不以藝術具體運作為出發點的藝術外部的理論方向,如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解釋學、接受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等,對于藝術系統而言日益邊緣化,對藝術家的形式創作決策僅有微不足道的影響。藝術系統論正是洞察到知識界學院派所做出的藝術評論與職業藝術家的“運作/觀察”之間,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的自說自話的尷尬處境,才提出審美理論的對象客體應是藝術溝通(Kunstkommunikation)這一真正的社會事件。現代藝術的條件就是現代社會的條件,理論若想理解藝術,必然要將社會現實條件——功能分化、自我指涉、運作閉合等一并納入二階觀察,因為藝術是社會的運作。
盧曼批評了文藝社會學巨匠阿多諾的美學觀點,即藝術的獨立自主與社會相對立,藝術的社會性是超然外在于社會的“否定性”;相反,盧曼認為,藝術只有身處于社會之中才能走向獨立自主,藝術獨有的解放功能唯有通過現代社會的運行才是可能的[5]142。現代藝術的自律也并不似阿多諾所言,藝術自律與藝術的社會依賴性彼此矛盾沖突;自律的真相是,藝術系統作為自律化的功能系統分擔了現代社會的結構性命運,藝術不得不接受自身強加給自身的自律宿命。藝術自律并不意味著藝術自成一方超脫于權力資本邏輯宰制的審美烏托邦,相反,審美現代性的悖論是,藝術越自律,反而越要依賴于其他功能系統的正常運行:現代藝術的自律性,前所未有地依賴于經濟系統里的金錢媒介,依賴于教育系統提供的個體社會化,依賴于大眾媒體的傳播技術……
作為一種藝術自我描述范式的美學之所以難免美人遲暮的現代性命運,是由于美學終究未能順應社會結構及其語義的分化演變形勢:普遍層面上,是現代社會分出形成了伯仲之間的自律的諸功能系統;特殊層面上,是藝術系統的分化形成。西方近現代以來美學的觀察盲點,一言以蔽之,是未能不偏不倚地通盤考慮藝術(Kunst)與社會(Gesellschaft)之間的關系,反而依據較為片面的歸因作為理論反思起點,聚焦于審美個體(藝術家或觀賞者)、藝術品,以及藝術審美的周遭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環境因素進行一階觀察。由此,美學一直未能真正理解藝術系統分化的語義結果,藝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仍然晦暗不明。
藝術系統論與美學之間的差異在于,美學沒能看到,社會普遍性與藝術特殊化彼此并不矛盾沖突,而是相互制約,互為條件:藝術既是藝術本身,藝術也是社會,藝術透過社會而成為藝術。藝術系統由自身的眼光(美學只是其中一道目光)出發洞察全社會的結構和運行,建構起社會的審美現代性,即社會日常的審美化版本,社會對自身復雜性、偶然性、不確定性的理解需要借鏡于藝術慧眼;與此同時,整個社會順著多元脈絡觀察藝術,將藝術系統的視域描述為社會的一部分,恰是這一部分以多元藝術脈絡映照社會整體。
三、盧曼的藝術溝通觀
盧曼對藝術溝通的界定,挑戰乃至顛覆了對溝通本身的老生常談式的理解。盧曼拋棄了“發送者—接收者”的傳統溝通模型,批判了通訊科學將溝通理解為信息從發送者傳遞到接收者的理論預設——溝通并不是信息在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傳遞交流。盧曼將溝通這一自成一體的涌現秩序界定為一個封閉運作的自我指涉的過程,這一過程建構了藝術系統。
盧曼將藝術溝通理解為具有三重選擇環節的“三合一”的選擇性過程,藝術溝通是信息(Information)、告知(Mitteilung)和理解(Verstehen)三者之間差異的統一。三個選擇環節缺一不可,它們一起涌現,相互觀察,耦合成為藝術溝通。溝通(系統)首先從一系列信息的可能性里選出一則信息;之后選定一種特定行為,把這則信息加以傳達;最終從區分信息與告知之間差異的多種可能性里選出一種,完成理解這一環節(理解就是“信息/告知”這一區分差異本身)。藝術溝通仿佛是由后向前得以實現,只有“信息/告知”之間差異的區分得到溝通系統的觀察,理解才得以可能,溝通才能出現,并由此產生了下一次接續上來的溝通的多種銜接的可能性——后續溝通是就上一次溝通的信息環節抑或告知環節進行運作上的銜接,關系到上一次溝通的理解環節是得到了理解還是誤解。一次完整的藝術溝通,縱然完成了“信息—告知—理解”的過程,仍無法確定,這次完整的溝通是否得到后續銜接上來的溝通的接納(Annahme)或者拒絕(Ablehnung),因為即使理解了,也不代表對于整個溝通的接納;也恰恰是這種接納或拒絕的兩歧分叉得到了后續溝通的觀察,使得溝通源源不斷地持續下去[7]。換言之,一次完整的藝術溝通事實上除了三重選擇環節之外還包括第四個選擇性銜接環節,即是否接納整個溝通。而無論接納與否,總有可能誘發溝通綿綿不絕運作下去,而不是戛然而止。藝術溝通是“信息—告知—理解—接納(拒絕)”的選擇環節的環環相扣的銜接,是一個溝通運作銜接上另一個溝通運作,溝通誘發進一步溝通,溝通指向溝通,溝通再進入到溝通中去,溝通轉瞬即逝,片刻不停,溝通運作自我再生產出一個閉合的自我指涉的社會系統,盧曼稱之為藝術。
流俗的溝通觀,對于藝術溝通中“人”(Person)的角色,有著根深蒂固的誤解。無論是藝術家還是觀賞者,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雖然參與了藝術系統的溝通,但作為心理意識系統、生理系統等多系統之雜糅混成耦合體的“人”,并不是藝術系統的組成元素,“人”不屬于藝術系統,不屬于藝術溝通,但“人”是藝術這一溝通系統正常運行的“中轉站”——“人”與藝術系統經由藝術品之中介,構成了彼此的環境。盧曼將“人”放逐到藝術系統的環境之中,并非一味地反人文主義,而是基于環境比系統更復雜,尊重了人之為人的復雜性。
既然“人”參與了藝術溝通,“人”的行為或曰行動(Handlung)在溝通中的作用值得一提,畢竟藝術創作起始于“做出一個藝術區分”的行為。盧曼早年也曾認可行為是社會系統的構成要素,晚年的盧曼堅持,社會僅由溝通組成,藝術系統唯一且基本的運作方式是藝術溝通,藝術行為是為了觀察藝術溝通之復雜性而做出的對于溝通的簡化歸因——“人”被界定為藝術溝通得以歸因的位址(Adressen)[8],質言之,“人”不是藝術溝通的發起者,藝術溝通是一個自身不斷生產自身的過程,驅使“人”做出藝術行為的肇因在于系統的溝通。第一個區分的標出,是偶然意外的第一筆線條,第一個音符,第一行詩句,如若沒有溝通系統的存在,連這偶然的運作緣起也變得困難重重。自我意識強烈的藝術家和藝術受眾不是藝術溝通的發起者,取代“人”之主體地位的是自我指涉的藝術系統。[9]
盧曼得出了一個挑釁常識的論斷:“人類無法溝通,甚至連他們的大腦也不能溝通,甚至連意識也不能溝通。只有溝通能夠溝通。”[10]人不能溝通,只有溝通能溝通,這正是盧曼藝術溝通觀的駭人聽聞之處。此論斷乍一聽荒誕不經,但可從主導藝術系統觀察的“感知/溝通”(Wahrnehmung/Kommunikation)(5)參見《社會中的藝術》第一章“感知與溝通:形式的再生產”。之區分推導出來:出于系統運作封閉性,人的心理(意識)系統只能執行意識和感知的運作,而無法執行溝通的運作;只有社會系統可以執行溝通運作,換言之,是社會在溝通;而組成社會的唯一且基本的運作元素是溝通,溝通(微觀層面)和社會(宏觀層面)是循環定義的[11],所以是溝通在溝通,溝通本身進行溝通運作。溝通交流著(Die Kommunikation kommuniziert)——此種“套套邏輯”(Tautologie)表明:藝術=藝術溝通=藝術系統,藝術溝通自我建構了一個遞回(Rekursionen)循環運作的社會溝通網絡。
基于對藝術溝通的界定,盧曼就傳統的藝術學概念,例如藝術家、藝術品等,給出了系統理論的二階描述。表面上看,藝術溝通發生在藝術家和觀賞者之間,藝術家與觀賞者可以圍繞一部藝術品進行意見交流;實際上,藝術家與觀賞者雖然參與了藝術溝通且是藝術溝通必不可少的環境媒介,但根本上說,是藝術(系統)本身在進行溝通,藝術家和觀賞者都不能透過藝術品執行藝術溝通——藝術家、觀賞者、藝術品這些概念其實是藝術這個溝通系統的語義濃縮物[12],是遞回運作的溝通網絡的沉淀物,是溝通無止境地再進入到封閉系統的溝通中去,自指地建構出的藝術運作“固有值”。于是,藝術家、藝術品等概念在藝術自創生的過程里發揮一種結構功能,它們可以凝聚社會期待,由此比起藝術溝通基本事件的短暫易逝的特點,其存在更加穩定,能夠面向事件化的藝術溝通提供保障機制,在溝通遞回的前瞻與回溯的過程里仍能保持為相對不變的事物。
在藝術系統中,執行溝通的是藝術溝通的遞回網絡(Netzwerk),這一網絡產生了藝術品而不是藝術家——人們觀賞的是圖像,而不是直接觀看畫家的情感;人們沉浸于其中的是由詞句編排而成的文學,而不是直接閱讀作家的思想。藝術品并不是現代藝術系統的基本組成元素,但作為藝術區分形式組合濃縮的藝術品是一種溝通的密集化,不同藝術品之間經由“風格”的中介進行觀察與交流,拓展了藝術溝通之網絡化:藝術品是“密集溝通”(Kompaktkommunikation),也即藝術過剩溝通可能性之題材儲存。盧曼指出,必須區分“基于藝術的溝通”(Kommunikation über die Kunst)和“透過藝術而溝通”(Kommunikation durch die Kunst)這兩種溝通模式;盧曼推崇的藝術溝通模式是指后者[13]。“基于藝術的溝通”為盧曼藝術溝通觀所揚棄,原因有二:其一,以不同方式談論藝術的溝通模式并不直接關涉藝術系統的溝通性元素,而是讓藝術成為其他社會系統的溝通題材,例如教育系統就審美教育的問題展開教育溝通;其二,“基于藝術的溝通”落入了語言溝通的窠臼,即便語言是輔助藝術溝通達成的基本媒介,但藝術溝通是可以在繞開語言使用的前提下進行,藝術溝通有別于僅使用語言的溝通方式,這也適用于語言文本的藝術——文學。盧曼所青睞的藝術溝通模式是“透過藝術而溝通”,“藝術如何溝通”這一問題的答案不言而喻:透過藝術品,藝術溝通經由濃縮于藝術品中的藝術區分形式,展開溝通——當藝術觀察者(不只是人,而是溝通或系統作為自我觀察者)解譯出藝術品中所使用的藝術區分結構,辨識出藝術對象客體(比如馬塞爾·杜尚的“泉”)并非自行產生而是成功地理解“信息/告知”(Information/Mitteilung)這組區分差異,藝術溝通才算運作成功。
四、藝術溝通之媒介及其編碼
對藝術溝通而言,重要的是溝通得以繼續,總有新的溝通銜接加入到運作鏈環中來;然而,溝通自我再生產是極度困難的,“溝而不通”的或然率總是存在。為了將藝術溝通涌現的“渺茫幾率”轉化成“較高概率”,溝通媒介發揮的作用至為關鍵。
藝術溝通是困難的,溝通若想得到“理解”是不大可能的——“語言”作為最基本的溝通媒介提高了溝通之理解的可能性;藝術溝通是困難的,溝通的“抵達”需要跨越時空阻隔——包括電子媒介等在內的傳播媒介,提升了溝通之抵達的可能性;藝術溝通是困難的,溝通即便抵達而且得到了理解,溝通的提議也很難得到“接納”——作為“成功媒介”(Erfolgsmedien)或曰“象征性普遍化溝通媒介”的藝術本身,提高了溝通之成功接受的可能性。[14]任何功能系統都要利用前兩類溝通媒介,只有第三類溝通媒介,即藝術本身作為成功媒介,方能展現藝術溝通的獨樹一幟。
“成功媒介”,即“象征性普遍化溝通媒介”,此類溝通媒介將自我對來自他者的選擇的接受動機,由較小可能性轉換成較大可能性。這種溝通媒介主要有:金錢、權力、真理、愛情,以及藝術。[15]“象征性普遍化”,“普遍化”(generalisiert)意味著,藝術作為溝通媒介,在事物維度上普遍化,面臨不同場合脈絡(政治的、教育的脈絡等)始終具有可應用性:藝術本身僅有審美效應,卻讓審美化溝通在整個社會上獲取成就;而“象征性”(symbolisch)象征著社會中他者與自我的雙重偶然選擇相互協調:藝術為原本不太可能達成的溝通之契合提供動機,讓藝術家的行動選擇有效傳遞,誘發觀賞者的體驗選擇。
藝術于極度困難的溝通條件下仍履行成功媒介的功能,讓藝術溝通的成功率保持為看似不大可能的較高可能性,歸功于藝術作為成功媒介其結構是經由“二值編碼化”(bin?re Codierung)的二元圖示。媒介編碼(Mediencode)由對立的正負兩值組成:真理編碼的“真/不真”,權力編碼的“有權/無權”。盧曼對于藝術(媒介)編碼的界定,飽受學術爭議,連其本人也曾滿腹猶疑:藝術系統的多元化脈絡如此復雜、偶然與不確定,藝術是否與金錢或權力類似,擁有一套標準化編碼?[16]盧曼肯定藝術編碼的存在合理性,因為成功媒介藝術的運行是以其結構上的二值編碼為前提的,而媒介編碼的立足點“價值制度化”也是可能的:“美”與“善”“真”“財富”等價值一道,共同構成了社會期待,維持了社會系統的結構。既然存在藝術編碼,編碼的具體形式有待確認,于是盧曼提出了兩組藝術編碼化區分:首先是“美/丑”(sch?n/h?sslich)這一傳統美學的編碼化提案,鑒于所招致的質疑,即挪用學術系統中美學的編碼語義作為藝術編碼(6)Gerhard Plumpe認為,“美/丑”是美學的主導區分,而美學的本質屬性是基于藝術的哲學式溝通,“美/丑”區分服從于學術系統的“真/假”二元編碼化支配,參見Gerhard Plumpe, sthetische Kommunikation der Moderne, Bd.1,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3. p52。,他又將“美/丑”編碼方案予以歷史化,提出了“合適/不合適”(passend/unpassend或stimmig/unstimmig)這一藝術編碼化倡議。但盧曼堅持,沒有比“美/丑”這一區分更令人信服的編碼方案,因為他所說的“美的語義”(Sch?nheitssemantik)指涉的不是美的藝術造型、美的音響等,也不是德國觀念論美學里的無利害的普遍理念顯現于特殊感性的“美”,而是基于適合與否的區分做出的綜合判斷,即藝術品通過選擇性偶然運作而與之俱來的一種形式化、秩序化的溝通成就。另一方面,就“美/丑”區分是一個具備不對稱化兩面的形式來看,“美”的盧曼式定義是一個兩歧的悖論:“美”既是“丑”的對立面,也是“美”“丑”兩面的統一,即形式區分自身,換言之,“美”是對“美”與“丑”之間關系的總體判斷。然而,盧曼也深知,現代藝術運作早已不能僅用“美”或“丑”等傳統審美語義加以編碼化,“美/丑”之主導編碼要與藝術實踐無縫對接,還得倚靠二級編碼之效力:藝術生產過程中“美/丑”這一“主導編碼”的可運作化需要“合適/不合適”這一“次級編碼”作為技術輔佐,次級編碼操縱著單次選擇運作,誘導著藝術創作的具體形式決策。
藝術編碼具有化腐朽為美感的“點石成藝”功效,藝術編碼化運作達及之處,一切藝術系統之外的脈絡皆可以轉化成富于藝術感或審美品位的運作銜接及選擇傳遞:唯有藝術編碼才能決定,何種選擇屬于藝術系統,何種運作不是藝術溝通。正如愛情編碼的正值“被愛”比起負值“不被愛”更值得追求向往,藝術編碼的正值(Positivwert)是偏好值(Pr?ferenzwert),作為偏好值的正值合法化了編碼的運行,表征著編碼的完整統一,即“美/丑”區分本身是“美”的:藝術寓于“美”之內(即“美術”:beaux-arts),藝術象征了“美”的同時憑借“美/丑”懸殊差異而魔鬼化了“丑”——直到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才為“丑”之審美價值正名。基于編碼偏向,藝術媒介可以操縱溝通抵御被拒絕的風險,正值作為偏好值,發揮“銜接值”(Anschlusswert)的強大功效,象征著媒介獨有運作的可銜接性,由“美、合適”等正值出發,系統總可以開展運作。而不為媒介所偏愛的編碼負值亦屬于媒介內在的結構特征——負值象征了可銜接性條件的偶然性,其作用是對偶然性加以反思,于是“丑”“不合適”等負值可標識為“反思值”(Reflexionswert),負值反思性否認藝術的過往傳統,旨在藝術同一性的選擇性反思,是系統自我控制的工具,為藝術吸收形式生產的不確定性:為避免傳統藝術的博物館化命運,先鋒派不只描畫怪誕畸形的事物,還把日常用品甚至是垃圾、排泄物直接展覽為藝術品,藝術與生活的偶然邊界趨向消失。
五、結 語
盧曼藝術系統論獨具“二階觀察”的慧眼,洞鑒傳統藝術美學理論執著于“美學”“藝術家”“藝術品”等“一階觀察”范疇而產生的觀察盲點,轉而將藝術及美學置于現代社會多元脈絡(7)“多元脈絡” (Polykontexturalit?t)系盧曼借用德國邏輯哲學家Gotthard Günther的術語,“做出一個區分”,每個區分撐開了一支“脈絡”(Kontextur),不同的脈絡其地位均為平等,無等級宰制。社會對于藝術的觀察是多元脈絡式的,經濟、政治、教育等與藝術并列相鄰的系統各自透過經濟、政治、教育等脈絡觀察藝術;藝術也以一種多元脈絡化的模式觀察社會:紛繁的藝術門類,理念迥異的藝術家及觀眾,復雜多變的藝術品及藝術組織構成了藝術系統內部多元化脈絡。下綜合考量。于是,藝術是一種溝通交流,是一個社會溝通系統;美學是一種審美溝通,美學溝通是一種藝術溝通。盧曼藝術溝通觀挑戰了流俗見解:“人”“藝術品”等藝術溝通之外的環境因素縱然對于藝術溝通是前提條件及支援脈絡,系統理論二階觀察卻聚焦于藝術自身固有的運作邏輯——藝術溝通被描述為封閉運作、自我指涉、自我再制、循環遞回的網絡化溝通系統,如此,藝術溝通的運作主體,宏觀來看是藝術系統,微觀地看,即是藝術溝通本身。藝術溝通的持續運作化,即藝術溝通由發生率較低轉化為涌現率較高,面臨著三大難題,作為解決方案的成功媒介藝術自身尤為提高了溝通成效:具有二值編碼化結構的藝術媒介操縱著溝通運作序列,保障了選擇的銜接與傳達,換言之,藝術編碼的“美/丑”二元圖示賦予藝術以象征性普遍化的功能,降低了藝術溝通的失敗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