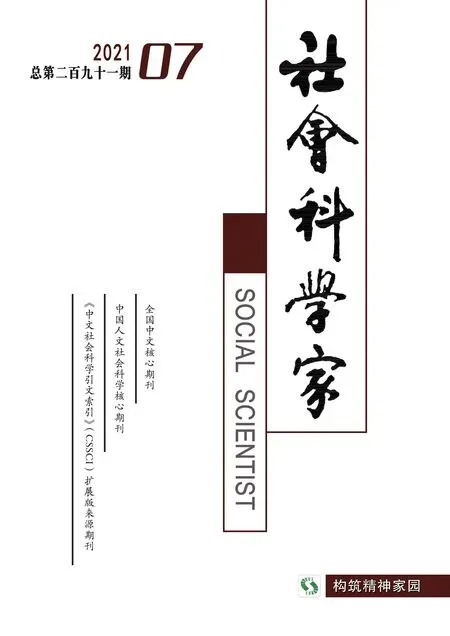刑法案例課程思政教學的規范化問題
陸 敏
(貴州財經大學 法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2016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這一重要講話精神引起全國高校教師的重視,以及對教書育人這一根本問題的深思。在這一思想引領下課程思政的教育教學改革已然引發高校及其諸多教師的嘗試和探索。為此,高校課程思政表現為“從單個開展到校際聯盟、從內容創新到形式翻新、從理論研究到課堂實踐”的發展和變化。盡管如此,課程思政的建設和推進仍可謂差強人意。當前對課程思政存在認識偏差并未消除,更需要注意的是,究竟是按照某些學者提出的“以人定課程”,還是在原有課程架構內推進課程思政①鄭強教授在202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年會上的演講。。這些內容在本質上都指向了課程思政如何規范化的問題。
課程思政比思政課更具有挑戰性,這是基于多方面因素得出的結論。最直接地表現在思政育人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上,大部分專業課教師無法企及。同時,學科的差異性也決定了課程思政存有不統一。而學生對課程思政的期待往往高于思政課,認可度和接受度更難。本文通過對刑法案例教學設計與實踐展開課程思政的探索,思考其規范化的基本問題,一方面要摒棄流于形式走過場,另一方面旨在致力于“德法兼修”新時代法治人才的培養。
一、刑法案例課程思政教學規范化的現實障礙
刑法學是法學核心課程之一,由總論和分論組成,案例教學是二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從中構筑整個刑法學的課程思政系統。從現狀來看,刑法學課程思政的推進是緩慢的,緣由在于主體的制約瓶頸、高校運行環境的限制因素以及學生維度的誤區。
(一)基于教師維度的發難
課程思政的開展一定是由教師把控和主導。有如“課程思政的關鍵在教師的思想政治素質和職業道德素養”。[1]以及“強調教師對課程思政的認識與實踐程度,方能使其取得成效”那般。[2]刑法案例課程思政教學與其他學科存有通病,它們不論是形式上的桎梏,抑或者是內容設計的缺陷,終究可以歸結為主體的問題。通過整理發現,基于主體視角的刑法課程思政沒有實質性進展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其一,當前刑法學課程思政(案例教學)并未得到足夠重視。自學科德育形成伊始,歷經了2015年到2017年專業課育人的明確提出,以及2017年至今課程思政的蓬勃發展階段。刑法學課程思政的示范教學并沒有成行和推廣,只有極少數研究指向這一問題。如提出在刑法學教學中將“四個自信”根植于學生內心的觀點,成行于2020年。[3]除此之外,未見其他刑法學課程思政的研究成果,但這不代表刑法學課程思政的教學實踐無所作為,只是說明教師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
其二,教師課程思政能力欠缺。課程思政的有效推進,取決于教師的素質和能力,而后者被認為是課程思政建設的核心變量。[4]此前提出的課程思政要“以人定課程”,意思就是先把上課教師定下來,再行課程思政教學。這種說法實際上強調的就是課程思政中教師的能力,應該看到“以人定課程”的設計是好的,在競爭中促使教師能力不斷提升。但是,這一做法并不符合中國高校的實際,如果在競爭中不能勝出的教師,意味著不能參與到教學過程,就無法完成學校的教學考核。那么,基于學校現有教學結構的考量,注重教師課程思政能力的培養,有效組織課程思政培訓,樹立典型的優秀教師、教學經驗和教學方法等做法,未必比不上“以人定課程”具有可行性。
其三,教師將學生作為課程思政的對象,勢必會減弱教學效果。學生只是教師教學與改造的對象,那么課程思政的輸入則會采取被動式,而非學生的主動性使然,根植于內心的價值引入便無從談及。加之,考試是衡量標準的課堂教學,使師生之間的互動更具有工具理性而不是價值理性,這就難以實現師生之間真實、真誠、正確有效地理解和溝通,不利于學生精神世界特別是高尚人格的形成。[5]這些將成為阻礙課程思政實效性的絆腳石。
(二)“生”于學校課程思政環境的現實拷問
課程思政改革和推進光憑教師一己之力無法完成,需要學校大環境的支持。目前高校課程思政環境還存有以下的問題:其一,運動式推進缺乏可持續性。具體表現在:一方面學校頂層設計的缺失,只是將與之有關的文件、精神傳達,并未結合本校的辦學特色制定詳細的實施方案、細則等,使得課程思政的運行呈現碎片化、教條化的不足。此外,課程思政既是全方位的有機融合,那么就不應該忽視教師思政。教師思政是課程思政開展的前提,教師自身尚未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如何做好課程思政。這部分最容易被忽視,通常只是強調教師在課堂上不能發表不當言論,不等同于教師思政。其二,不考慮學科差異性進行無差別地生搬硬套。課程思政畢竟是在專業課教學中實現有機融入,其課程的本質和性質一定還是專業課,而不是思政課,這一點一定要明確。不同的專業課在課程思政的融入和滲透上并不是一層不變的,這需要教學單位、教學團隊的精心設計及其授課教師的智慧。未能充分考慮到各專業所蘊含思政元素的差異性,急于用一套建設路徑去開展所有專業的課程思政設計,未能針對專業的個性化差異分門別類地制定建設規劃,導致建設成效不顯著。[6]其三,未形成有效的考評機制。課程思政建設最根本的問題是實效性的問題,也就是對學生起到了什么樣的價值引領,在育人方面產生了什么積極意義。目前全國范圍內只有為數不多的高校,形成了課程思政的有效性考核機制,大部分的高校還停留在文件解讀和精神傳達的層面,借鑒和觀望的態度使得課程思政的考評機制滯后。這樣使得課程思政的實效性將會大打折扣。總之,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理念沒有貫穿在高校教育教學模式中。
(三)“長”于學生對課程思政認知的期待性審視
教師是課程思政的主導人,學校大思政環境是課程思政的根基,學生卻是課程思政的最終受益人。基于前述理由暴露下的缺陷,通常學生不能對課程思政有正確的認識和理解,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分不清,以為后者是前者的重復。而最大的困境在于對專業課程的學習動機,是為了獲得學分而學習、為了考試而學習,存在懈怠心理,不會思考老師課堂上提出的問題,亦不會對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根本問題有所共鳴。并且受限于專業課程的學時問題,短暫的課堂學習無法使學生真正理解德育精華,更多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缺乏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無法開展深入學習。
二、刑法案例教學課程思政的發生機制
刑法案例教學課程思政的現實困境已然被提出,這并不會導致其課程思政的推進停滯。相反,更需要深入挖掘刑法案例教學中內含的思政育人資源。可以說,刑法案例教學在思政育人的問題上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犯罪與刑罰既是法律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其中思政育人的價值引領具有現實的帶入感和互動性。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刑法案例教學與思政育人的有機勾連。
其一,刑法案例教學的教學目標與課程思政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刑法案例教學的目標不但要確定具體審判實踐的邏輯,更為重要的是得到“一個在刑法上有關一個人的審判僅可能是一個良知的審判”[7]。長期以來,社會大眾對于犯罪人的痛恨,往往遮蔽其“雙眼”,忽視了犯罪人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也極易導致推脫犯罪本身產生的社會原因,這種情緒同樣會影響到司法工作人員。刑法學的受眾主體是法科生,他們中的大多數會成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一份子,案例教學的首要任務是要在此之前糾正這一“偏私”。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張氏叔侄案、于英生案、聶樹斌案等刑事錯案需要的是杜絕,而不是錯案追責的事后補救。此外,處罰最為嚴厲的刑罰,其強制手段可以在許多個案中以武力威脅足以引導一種合法行為,便促成良好的刑事守法狀態。這一點上與刑法的規制機能、人權保障機能不謀而合。
其二,刑法案例教學課程思政的系統性。毫不夸張地說,案例教學是刑法學教學的靈魂。從教學目標到具體的教學內容,案例教學都能形成其課程思政模塊,并且這些模塊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再現了政治認同、家國情懷、道德修養、法治意識、文化素養的價值引領,共同構建了整個刑法學課程思政的系統工程。而在刑法學教學中將“四個自信”根植于學生內心,分別體現在道路自信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刑事法治相聯系,理論自信則將刑事立法、司法和學術研究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制度自信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刑法的底氣,而文化自信則要再現中華優秀傳統法文化。[3]這樣的課程思政推進,顯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體現在刑法學教學中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的有機融合,但僅僅是冰山一隅。
其三,刑法案例教學課程思政內容的生動性和互動性。刑法案例教學著眼于基本案件事實進行刑事法律問題的分析,案件事實源于真切的生活事件,一貫保有其生動性和趣味性。而課程思政的滲透也因此得以富有生機,在互動中引發學生對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深思。同時,在教學方式方法上結合刑事訴訟程序進行案例教學的角色化,親歷其犯罪與刑罰對于個人、社會以及國家的危害性,具有積極的警示和引導意義。
綜上看出,刑法案例教學中課程思政的協同育人機制,歸納為價值主旨的同一性,教學體系的連貫性和系統性,教學內容的深刻性和靈動性,突破了傳統專業課程與思政課的分離、碎片化瓶頸。同時也表明了刑法案例教學對“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作出的回應。
三、刑法案例課程思政教學模塊的規范化設計
刑法學教學尤其是案例教學,在課程思政實施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這是其他法學課程所沒有或者不完全具備的。充分挖掘與整合案例教學中課程思政的優質資源,并進行規范化設計。可以這樣說,刑法案例教學的課程思政不僅僅是局部內容的體現,而是成體系的,其中除了廣度的延伸,也要涉及深度的解讀。
根據刑法案例課程內容的特點,大體形成如下的思政育人模塊(見表1)。

表1 刑法案例教學課程思政模塊
通過上表,我們看到與相關案例相對應的每一個模塊都有其思政育人的價值體現。愛國主義教育對侵犯國家安全犯罪案例教學的滲透和中華民族“尊老愛幼”傳統美德教育的涉親權犯罪案例教學是厚植于家國情懷的彰顯。愛家與愛國的一體性,都是致力于實現家庭幸福美滿、國家振興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精神動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協同下的危及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秩序犯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屬于社會意識范疇,要融入實際、融入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接受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教育的進展和成效。有關侵犯人身權利犯罪案例的生命主題教育融合,關涉生命價值、大學生自殺、生命發展及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引導大學生由死亡感悟生命價值、珍惜生命是生死觀教育的目標。教育不應回避死亡,對死亡的追問就是對生命意義的解讀。傷害野生動物、破壞自然資源環境犯罪案例教學的正確自然觀導入,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馬克思生態觀的核心內容,體現了“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與“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倫理觀。[8]強調正確消費觀引領下經濟犯罪案例的展開,盲目超前消費、泛化娛樂消費、崇尚符號消費和網絡消費成癮,錯誤消費取向的價值窠臼。[9]職務犯罪案例教學的廉潔教育融入,是預防社會腐敗現象滋生蔓延,促使大學生自覺將敬廉崇潔的社會規范內化為自身發展需要,外化為廉潔行為和日常生活習慣,促進自身健康發展。而誠信教育制假售假、徇私舞弊犯罪,融合了誠信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公民層面”的主要組成部分。
四、刑法案例教學課程思政的實踐運用
刑法案例課程思政教學模塊的設計為其實踐運用提供了著力點,二者的關系就是“能融入”和“如何融入”的關系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后者勝于前者。實踐運用需要接受價值引導的實效性檢驗,實效性是課程思政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具體到刑法案例課程思政的教學運用,其對“原則、要領以及標準”的體現,應該在以下的教學實踐過程得以實現。
“一個原則”是指堅持課程思政與思政課區分原則,課程思政是在專業課教學過程中的有機融入和潤物細無聲地滲透,那就一定抓主要矛盾,專業教學不能因課程思政影響其進度、影響其內容的延續性和完整性,而專業課也不能將思政育人置身事外。在刑法案例教學中滲透和整合思政育人元素,進而達到協商與人的效果,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其課程思政的實施過程,在每一個環節保證都有思政育人的考量。
“一個要領”就是切忌泛泛而談與思政育人的口號式輸入,一定不是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的簡單重復。示例1:藥家鑫故意殺人案的課程思政教學模式與運用細則(見圖1)。

圖1 案例教學課程思政運行圖
從上圖看出課程思政部分的運用包括了引導學生對生命問題的思考與深度闡釋生命倫理,課后參觀醫科大學的生命科技館以及寫一段你想對行為人吳謝宇和吳浩森說的話。這三個部分構成了此案例教學的思政育人內容,主題教育+體驗式教學相結合。課堂最多不超過五分鐘,課后至多不超過一小時。整個案例課堂教學的專業法律問題分析占到十到十五分鐘,課后作業則至少需要一個小時完成,關涉同一主題的案例教學則不再重復這一思考。
示例2選取的是趙某某遺棄、虐待母親案,這個案例的講解與互動仍然采用前述案例的模式,只是思政育人的第三部分課后作業進行調整,以“父母-子女”角色互換的心得來推進,這里主要是體驗式教學來完成家庭倫理教育。
“兩個標準”要求專業課與思政育人的融合要保有貼合度和精準度。“一個要領”解決的是“如何融入”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一定作貼合度和精準度的考量,也就是專業課與思政育人的融合是否恰當的問題。前文中列舉了學者“四個自信”課程思政的教學融合,但是在本文看來,說服力有所欠缺。通熟刑法學教學的教師都知道,刑法學教學與研究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總論部分的理論基礎教學必須追溯和借鑒德日刑法、蘇俄刑法,并對英美法系的相關理論進行介紹,最終要落實到結合我國刑事法治的實踐,將域外理論研究實現本土化的根本問題上。對學生而言文化的包容性在此處似乎比文化自信更具有現實的說服力,并以此導入寬容世界觀及道德實踐的價值引導,寬容是人類追求美好、和諧、共存的整體生存狀況,認同多元差異主體的存在事實。[10]這也正是習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因此,適正性是非常有必要的,直接關系課程思政的實效性和學生對教師所要傳遞正確價值觀的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