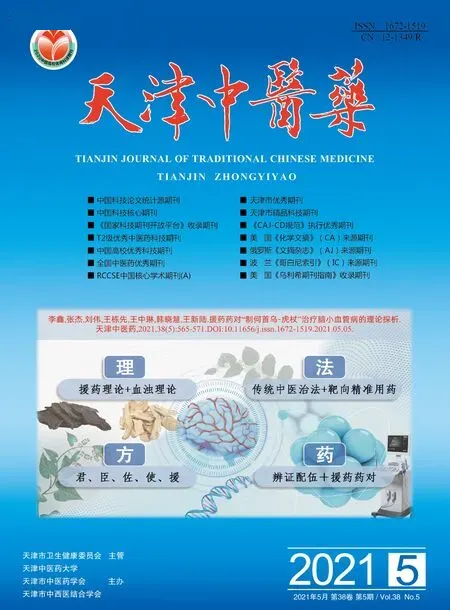國醫大師張大寧教授治療腹瀉經驗淺析*
樊威偉,張勉之,張大寧
(天津市中醫藥研究院附屬醫院,天津 300120)
腹瀉以排便次數增多,糞質稀薄為主要臨床表現,臨床分為細菌性腹瀉和非細菌性腹瀉。根據腹瀉的主要臨床表現、病機及其病理演變過程,應將其歸屬于中醫學“飧泄”“濡泄”“洞泄”“溏泄”“注泄”“五更瀉”范疇[1-4]。《古今醫通大全·瀉泄門》云:春傷于風,夏生飧泄。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又曰:“清氣在下,則生飧瀉。”又曰:“濕勝則濡泄。”又曰:“暴注下迫,皆屬于熱。”又曰:“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于寒。”根據其臨床表現,張大寧教授將腹瀉的病機概括為本虛標實,本虛以脾腎陽虛、命門火衰為主,標實以肝郁、傷食、濕熱、寒濕為主。張大寧教授是國醫大師,第四、五、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從事中醫腎病的臨床、科研與教學工作50余年,提出了“腎為人體生命之本-腎本學說”“心-腎軸心系統學說”以及“腎虛血瘀論與補腎活血法”等理論。
臨床治療中,張大寧教授針對腹瀉提出補腎健脾、溫補命門、固澀止瀉之法,以四神丸和補中益氣湯加減。筆者有幸侍診于側,現將國醫大師張大寧教授治療腹瀉的經驗介紹如下。
1 病因病機
張大寧教授認為,該病的發生一方面是由于脾腎陽虛導致命門火衰、運化功能減弱,不能腐熟水谷、運化精微,以至水谷停滯,并入大腸而泄瀉,纏綿不休。《景岳全書》:“腎為胃關,開竅于二陰,所以二便之開閉,皆腎臟之所主,今腎中陽氣不足,則命門火衰……陰氣盛極之時,即令人洞泄不止也。”指出脾腎陽虛、命門火衰是泄瀉的重要病因病機;另一方面由于情志失調、飲食所傷、感受外邪,導致脾胃氣機升降失調,使水谷精微不能輸布,運化失常,水濕內停,發生泄瀉[5-8]。現代人生活節奏快,容易導致肝氣郁結,橫逆乘脾,而致泄瀉;或由于長期飲食不節,嗜食肥甘損傷脾胃,導致土虛木乘而見泄瀉不止;又或久瀉脾氣本虧,肝氣乘脾,肝脾不調,木土不和而致泄瀉加重。所以,腹瀉產生的根本原因為因虛致實,再因實重虛。
從另一角度講,張教授認為該病的病機為“本虛標實”。“本虛標實”實際上反映了對腹瀉的“整體與局部治療相結合”的問題。中醫學認為,“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從整體來看,本虛實際上反應了腹瀉整體的、基本的病理變化;標實從臨床表現來看帶有個性的內容,而實質上反映了某一部位、某一臟腑、某一階段的病理變化。兩者的高度統一,實質上反應了“整體與局部”治療的高度結合。
2 治療大法
2.1 從脾腎論治,溫補命門 張教授治療腹瀉時,多從脾腎論治、從命門入手。他認為,中醫將大多數慢性腹瀉歸于脾腎陽虛,尤其是腎命門火衰。人身之陽根于腎而資生于脾,腎陽恢復必賴中焦水谷精微的充實,只有恢復脾陽保其化源,腎陽方能得后天之充養,而有生化之機,并使已回之陽得以鞏固,溫補脾陽對急回腎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腎陽虛怯,火不暖土,脾不運化,水失所制,則水濕之邪愈逞其勢。是故腎陽不足,則土德不及;土不制水,腎陽愈伐,水濕更甚,兩者互為因果。在治療上均當溫補元陽,培土制水,以伐腎邪。同時,根據患者臨床表現,將腹瀉又稱為腎泄、雞鳴瀉,主要是由于命門火衰、火不暖土、脾失健運所致。《素問·金匱真言論》曰:“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脾腎陽虛,陽虛則生內寒,而五更正是陰氣及盛,陽氣萌發之際,陽氣當至不至,陰氣極而下行,命門火衰者應于此時,因陰寒內盛,命門之火不能上溫脾土,脾陽不升而水谷下趨,故為泄瀉。
從脾腎論治的前提是患者必須有脾腎陽虛、命門火衰的征象。對于脾腎陽虛、命門火衰,判斷依據為:脾腎虛弱,不進食;脾腎俱虛泄瀉不食,或飯食后常泄;一切脾腎俱虛,侵晨作瀉,或飲食少思,或食而不化,或作嘔,或作瀉,或久瀉不止,脾經有濕,大便不實者;腎瀉,脾瀉;以舌淡苔白,脈沉遲無力為辨證要點。
張教授從脾腎論治、溫補命門的方劑常用四神丸。四神丸出自明代王肯堂《證治準繩》[6],由二神丸和五味子散組成。兩方合之,溫補固澀之功皆著,《絳雪園古方選注》謂“四種之藥,治腎泄有神功也”,故冠之“四神”。四神丸由煨肉豆蔻、補骨脂、五味子、吳茱萸組成。汪昂《醫方集解》認為“久泄皆由腎命門火衰,不能專責脾胃”,方中補骨脂辛苦大溫,能補相火以通君火,火旺乃能生土,故以為君;煨肉豆蔻辛溫,能行氣消食、暖胃固腸;五味子咸能補腎,酸能澀精;吳茱萸辛熱,除濕燥脾,能入少陰、厥陰氣分而補火;生姜暖胃,大棗補土,所以防水。蓋久瀉皆由腎命火衰,不能專責脾胃,故大補下焦元陽,使火旺土強,則能制水而不復妄行矣。本方為治命門火衰,火不暖土所致五更泄瀉或久瀉之代表方,以五更泄瀉,不思飲食,舌淡苔白,脈沉遲無力為辨證要點。
2.2 重視益氣升陽,調理脾胃 腹瀉的發生與中焦脾胃氣虛,氣機的升降出入運動失調有關。脾胃氣虛,升降失調,不能“升清降濁”,致使“清降”“濁升”,從而出現腹瀉。《陰陽應象大論》曰:“清氣在下,則生饗泄,濁氣在上,則生瞋脹。”清陽主升,濁陰主降,若清陽該升不升而在下,即可出現泄瀉等疾病。《景岳全書·泄瀉》云:“泄瀉之本,無由于脾胃。”脾胃失調,反水為濕、反谷為滯,從而出現腸鳴腹痛,不欲納食,四肢困軟,泄瀉無度的癥狀。脾陽不升,運化失司,濕從內生,外濕浸淫,濕邪蘊結,導致脾陽更傷。李東垣認為“清氣在陰者,乃人之脾氣衰,不能升發陽氣,故用升麻,柴胡助辛甘之味,以引元氣上升,不令饗泄也”。取升麻、柴胡的升發之性,從而使清陽得升,濁氣得降,升降協調,恢復脾胃升降樞紐之功,如此泄瀉得止。這就是“益氣升陽法”治療腹瀉的理論來源及文獻學基礎。
同時,脾腎乃先、后天之本,腎與脾生理上相互補充,病理上相互影響,無論脾虛還是腎虛,均可演變為脾腎陽虛證。人體的消化主要靠脾胃,也與腎有關,腎陽可以溫煦脾胃,促進水谷的消化,既要有胃主收納,又要有脾主運化,還要有腎陽的溫煦,腎陽的溫煦有助于恢復脾胃的升降功能,三者缺一不可。脾腎陽虛,命門火衰,火不暖土,脾土不得命門之火溫煦,致升降失常,清濁不分,混雜而下,故出現泄瀉等癥。
臨床治療當中,《脾胃論》針對脾胃氣虛、中氣不足、氣虛下陷、升降失調癥狀,選用補中益氣湯。補中益氣湯由黃芪、甘草、白術、人參、當歸、升麻、柴胡、陳皮組成,其功能主要為益氣升清、健脾止瀉,使中氣健旺,清濁升降有序,泄瀉自止[9]。方中重用黃芪補中益氣,升陽固表,為君藥。人參、白術、炙甘草補氣健脾為臣,與黃芪合用,增強補益中氣之功。當歸養血和營;陳皮理氣和胃,使補藥補而不滯,行而不傷,共為佐藥。柴胡、升麻升陽舉陷,“升清陽之氣于地道也,蓋天地之氣一升,則萬物皆生,天地之氣一降,則萬物皆死”闡明了升發陽氣的重要性,《本草綱目》謂:“升麻引陽明清氣上升,柴胡引少陽清氣上行,此乃稟賦虛弱,元氣虛餒,及勞役饑飽,生冷內傷,脾胃引經最要藥也。”兩藥兼具佐使之用。炙甘草調和諸藥,亦作使藥。全方補氣與升提并用,使氣虛得補,氣陷得升,為治脾虛氣陷之要方。本方“治在黨參黃芪,定在升麻柴胡”,益氣升提。
張教授認為,其臨床辨證以飲食減少,體倦肢軟,少氣懶言,面色晄白,大便稀溏,脈大而虛軟。或氣高而喘,身熱而煩,渴喜熱飲,其脈洪大,按之無力,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頭痛;或氣虛下陷,久瀉脫肛;或臟器下垂為主[10]。
張教授指出,中醫治療腹瀉自然以辨證論治作為基礎,但同時西醫的病理、檢驗等手段亦應作為治療的參考。把脾腎陽虛作為本證,把溫補命門、固澀止瀉作為重要的治療方法,同時結合西醫檢驗手段。同時,對于腹瀉的治療,臨床中除使用湯劑外,推拿、艾灸、貼敷、中藥灌腸等多種途徑綜合治療,針對性強,可以直達病所。正是基于“理證治病相結合、多種治法相結合”的原則。
3 典型病案
患者男性,27歲,2019年3月20日初診。主訴:大便次數多、粥樣大便8年余。患者8年前因受寒后大便次數多,每日5、6次,呈粥樣便,便時伴有小腹墜脹,便后小腹墜脹感緩解。同時,每于餐后排便,晨起五更瀉;易外感風寒,外感后腹瀉癥狀加重;腹部冷感,食冷、受寒后腹瀉癥狀、腹部冷感加重;納谷不馨,平素完谷不化;體質量下降,2018年體質量由75 kg減至60 kg;夜尿可,夜寐欠安,舌淡暗苔膩、黃白相兼、邊有齒痕,脈沉細。為進一步明確原因,2019年4月17日行腸鏡示:直腸炎。2019年6月5日胃鏡示:1)反流性食管炎(LA-B級)。2)慢性淺表性胃炎。近日患者上述癥狀加重,為系統治療前來就診,舌淡,苔薄白,脈沉遲無力。西醫診斷:1)反流性食管炎(LA-B級)。2)慢性淺表性胃炎。3)直腸炎。中醫診斷:腹瀉,屬于脾腎陽虛、命門火衰。治則:補腎健脾、溫補命門、固澀止瀉。以四神丸和補中益氣湯加減。處方:黃芪30 g,補骨脂10 g,吳茱萸5 g,煨肉豆蔻10 g,五味子15 g,五倍子20 g,肉桂 10 g,炮姜 10 g,太子參 10 g,石斛 10 g,砂仁10 g,訶子肉 20 g,煅牡蠣 20 g,升麻 5 g,炒白術 10 g,茯苓 10 g,炒雞內金 10 g,黃連 5 g,蓮子心 10 g,炙甘草 10 g,山藥 10 g,三七 10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每日早、晚兩次溫服,每次300 mL。
2019年4月19日2診:大便成形,每日兩次,偶有小腹墜脹感,腹部冷感明顯減輕,仍有不消化食物,腰酸減輕,夜寐差,舌淡苔膩、邊有齒痕,脈沉。處方以初診方黃芪加至40 g,加酸棗仁10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每日早、晚兩次溫服,每次300 mL。
按語:該患者以大便次數多、不成形為主癥就診,屬于中醫“腹瀉”范疇。病機為脾腎陽虛、命門火衰,治療以補腎健脾、溫補命門、固澀止瀉。方中以大劑量黃芪為君藥,大補元氣,補中益氣,升陽固表。張教授認為黃芪是一味五臟均補,尤以腎、脾、肺、心氣為主的“圣藥”;白術、太子參、山藥、炙甘草、砂仁補氣健脾為臣,與黃芪合用,增強補益中氣之功;補骨紙、吳茱萸溫腎暖脾;肉桂、炮姜補火助陽,引火歸元;肉豆蔻、煅牡蠣、五味子、五倍子、訶子肉收斂固澀、澀腸止瀉共為佐藥;升麻升陽舉陷止瀉,李時珍說:升麻治陽陷“久泄下痢”;雞內金消食和胃;石斛益氣養陰;針對失眠,張教授常用黃連、蓮子心配伍,以達到清心瀉火、養心安神目的;三七活血化瘀,《醫林改錯》言:“五更天泄三兩次……用二神丸、四神丸等藥,治之不效……不知總提上有瘀血。”張教授據此常用活血化瘀之品,共為使藥。2診時考慮患者夜寐差,加用酸棗仁增強養心安神之力。
4 總結
腹瀉的病因以本虛標實為主,本虛以脾腎陽虛、命門火衰最為主要,標實以肝郁、傷食、濕熱、寒濕為主。其病位在腸,但與肝脾腎關系密切。脾腎陽虛,命門火衰,運化減弱,水谷停滯,并入大腸而泄瀉。治療以補腎健脾、溫補命門、固澀止瀉之法,以四神丸和補中益氣湯加減,主要適用臨床表現為慢性腹瀉、五更瀉,或飯后泄瀉,大便稀溏,久瀉久利,不思飲食,食不消化,或腹痛肢冷,神疲乏力,舌淡,苔薄白,脈沉遲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