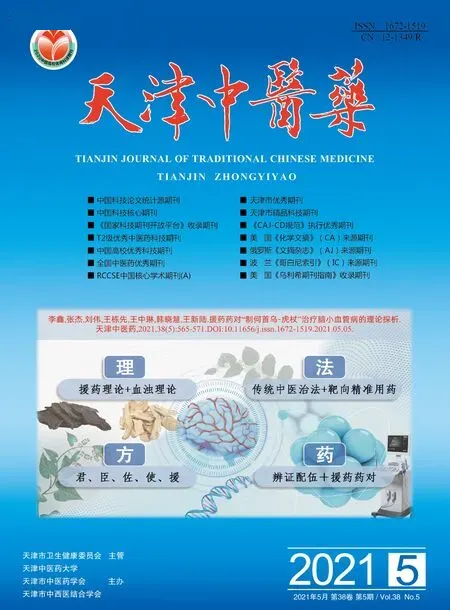侯玉芬教授從脾論治肢體淋巴水腫經驗*
劉壹,張玥,靖金鵬
(1.山東中醫藥大學,濟南 250014;2.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周圍血管病科,濟南 250014)
肢體淋巴水腫屬中醫“大腳風”“尰病”“腳氣”等范疇,常繼發于外傷、手術、感染、腫瘤、絲蟲病感染,系由淋巴管解剖變異或功能障礙致淋巴液在皮下聚集,繼而引起纖維增生,后期皮膚粗糙、增厚、彈性消失,硬如象皮,故有象皮腫之稱[1]。侯玉芬教授是全國第四、五批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博士研究生導師,主任醫師,從事臨床、教學、科研工作40余載,擅長中西醫結合診治周圍血管疑難病癥,尤其對淋巴水腫有著獨到的治療經驗,提出從脾論治,療效卓著。現將侯教授治療淋巴水腫的經驗整理如下。
1 病因病機
1.1 脾虛為本 淋巴水腫的發生與“脾虛”這個致病因素密切相關。《素問·至真要大論》曰:“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蓋脾主運化谷食和水液,其運化水液的功能,是指脾具有吸收、輸布水液,防止水液在體內停聚,以維持水液代謝平衡的生理作用。脾氣健運,能將胃和小腸消化吸收的津液經脾氣的轉輸作用上屬輸于肺,再由肺的宣降作用輸布于全身,使“水精四布、五經并行”(《素問·經脈別論》),亦能將小腸、大腸中的部分水液下輸膀胱,成為尿液生成之源;此外,脾居中焦,為水液升降輸布的樞紐,全身津液可隨脾胃之氣的升降而上騰下達。因此,若脾失健運,必然導致體內水液運化失常,而見水濕痰飲等病理產物,同時水濕泛溢肌膚所致的肢體粗腫亦是本病突出的臨床表現。
1.2 寒濕、濕熱、痰飲、瘀血為標 脾失健運所致的濕邪是貫穿疾病全過程的重要病理因素,在疾病過程中與寒、熱相互錯雜,日久致痰飲、瘀血共同為患。
1.2.1 寒濕困脾 從脾的生理特性來看,脾喜溫喜燥、惡寒惡濕,驟受風寒、涉水淋雨,久居寒濕之地或平素嗜食生冷均會導致寒濕內侵、困阻脾胃,以致脾虛失運,濕邪內生[2]。又因脾在陰陽學說中屬陰土,故其陽氣易衰,陰氣易勝,水濕又為脾所運化,因此脾虛所產生的濕邪等病理產物侵襲人體時最易傷及脾陽[3]。
1.2.2 濕熱內生 《活人書·卷十一》認為素患寒濕不解,久而化熱,濕熱蓄積于脾胃可致脾胃濕熱[4]。此外,若患者平素飲食過量而致宿食內停,或嗜食肥甘厚味,亦會導致脾胃呆滯,濕熱內蘊[5]。外感濕熱毒邪,如外傷、久居潮濕環境等,也是濕熱內傷的重要原因。薛雪有謂:“熱得濕而愈熾,濕得熱而愈橫。”此時濕處熱中,熱伏濕內,濕熱交織,羈久不愈[6]。
1.2.3 痰飲、瘀血錯雜 脾失健運可致體內水液代謝失衡、氣機郁滯、血行不暢,明朝李梃在《醫學入門》中述:“痰乃津血所成,隨氣升降,氣血調和則流行不聚,內外感傷,則壅逆為患。”指出濕邪隨氣血運行,若氣血不調,濕邪可聚而成痰[7],痰濁運化不及,凝滯脈絡,又可致血液運行不暢,《金匾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云:“血不利則為水。”故可見肢體腫脹加重;此外,血瘀日久可致肌膚失養,則發皮膚增厚、粗糙等癥;病積日久,正氣益傷,久病入絡,氣虛血瘀,痰瘀互結則見肌膚堅硬如象皮[8]。
可見,本病總屬本虛標實,在疾病的發展過程中本虛與標實相互影響、互為因果。一方面,脾氣虧虛是化生濕、熱、痰的病理基礎;另一方面,邪實又可損傷臟腑之氣,使脾氣更虛,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從而使疾病表現出病情反復、纏綿難愈的特點。
2 治療當以健脾為主
本病之本在于脾虛,因此,侯教授結合多年臨床經驗提出從脾論治,以健脾利濕貫穿疾病始終,臨床常用黃芪加四君子湯為基礎方,寓補氣健脾于其內。黃芪、人參、白術、甘草皆為甘溫緩和之品,奏益氣健脾之功,并佐以甘淡之茯苓以健脾滲濕,茯苓、白術相配,則健脾祛濕之功更甚。在此基礎上,侯教授喜用“桑”類藥物(如:桑葉、桑枝、桑白皮等),取其利水、消腫之功,同時桑葉、桑枝為芳香莖藤類藥物,通絡之力益著,正與本病肢體腫脹,后期皮膚增厚、粗糙的臨床表現相契合。最后權衡寒、熱、痰、瘀之主次輕重,兼以溫里、清熱、化痰、散瘀等治法,總結如下。
2.1 健脾溫腎,利水消腫 該法主要用于寒濕困脾所致的淋巴水腫。癥見肢體腫脹,皮色不變,按之凹陷,走路時感沉重,同時伴形肢冷,苔白膩,脈沉濡等。侯教授認為此時主要病機特點為“寒”和“濕”,兼有“瘀”,故臨床上常用真武湯加減(茯苓30 g,桑枝 30 g,益母草 30 g,黃芪 15 g,白術 15 g,白芍15 g,赤小豆 15 g,制附子 10 g,穿山甲 10 g,王不留行10 g,肉桂5 g,甘草5 g)。方中重用茯苓、桑枝、白術、制附子、肉桂等溫腎健脾以利水,佐以桑葉、益母草、穿山甲、王不留行等活血通絡。
2.2 清熱利濕,活血消腫 該法多用于濕熱之邪流注肢體所致的淋巴水腫,且侯教授認為此時病機以標實為主,為疾病治療的關鍵,病機特點為“濕”“熱”為患,兼有“瘀”。若“濕”重于“熱”,癥見患肢腫脹,皮色暗紅,邊界清楚,略灼熱,舌紅,苔黃膩,脈滑數者,多選用茵陳赤小豆湯加減(茵陳30 g,赤小豆 30 g,薏苡仁 30 g,桑葉 30 g,白豆蔻 9 g,牛膝10 g,黃柏 12 g,蒼術 12 g,澤瀉 12 g,佩蘭 10 g,甘草3 g)。方中重用赤小豆、薏苡仁、蒼術、桑葉等健脾利水,茵陳、黃柏清熱解毒。若“熱”重于“濕”,以患肢皮膚焮紅灼熱,邊界清楚,疼痛,伴有寒戰、發熱等全身癥狀為主者,常選用八妙通脈湯加減(金銀花 30 g,玄參 30 g,當歸 24 g,黃柏 12 g,牛膝 12 g,薏苡仁 30 g,蒼術 15 g,桑白皮 15g,甘草 9 g)。方中重用金銀花、玄參、黃柏等以清熱解毒,蒼術、薏苡仁、桑白皮等健脾利水,并配伍牛膝活血消腫。
2.3 健脾益氣,化痰軟堅 該法主要適用于水腫遷延不愈,正氣損傷而致痰凝血瘀并見,臨床多表現為患肢腫脹,皮膚粗糙、堅硬,按之不凹陷,或出現皮膚改變,如脂肪沉積、棘皮癥及疣狀增生,舌質淡、暗或有瘀斑,苔薄白,脈沉細等。侯教授認為此屬淋巴水腫后期,病機特點為“虛”“痰”“瘀”并見,虛實夾雜,選方多為補陽還五湯加減(黃芪30 g,當歸尾 12 g,赤芍 10 g,地龍 10 g,川芎 12 g,紅花 6 g,桃仁 9g,蒼術 12g,黨參 12g,白術 15g,雞血藤 15g,浙貝母 12 g,冬瓜皮 30 g,茯苓皮 15 g,桑枝 30 g,牛膝15 g,甘草5 g)。用藥多在健脾利濕的基礎上加入黃芪、黨參、桃仁、紅花等以益氣活血,浙貝母、地龍等以化痰軟堅。
3 熏洗纏縛,內外合治
《醫學源流論》曰:“外科之法,最重外治。”侯教授在運用內治法治療疾病的過程中同樣重視外治療法,并主張在疾病早期應用。對肢體淋巴水腫癥見患肢腫脹,皮色不變,按之凹陷,伴有形寒肢冷者,常給予活血消腫散(組成:丹參、赤芍各30 g,紅花、雞血藤、蒼術各15 g,延胡索、木瓜各9 g)熏洗患肢;癥見患肢紅腫、灼熱、疼痛者,常用冰硝散(組成:芒硝2 000 g,冰片10 g)外敷;同時輔以數字漸增壓力治療儀對患肢進行氣壓治療,并囑患者下地時外束彈力繃帶以增強療效。
在臨床治療肢體淋巴水腫時,侯教授亦重視日常調護,指導患者在生活中注意患肢防護,避免患側負重、干重活;平時注意保護好水腫部位,注意皮膚、指甲的衛生,避免燙傷、刺傷、凍傷、蚊蟲叮咬等外傷;平時不可穿過緊的內衣,以免淋巴回流受阻。
4 典型病案
患者女性,64歲,2018年9月4日初診。患者2年前因子宮內膜癌于當地醫院行手術治療,術后右下肢出現腫脹,皮膚潮紅,未予重視,癥狀逐漸加重。遂于當地中醫院就診,并口服中藥治療,癥狀略有好轉,但病情反復。1個月前患者右下肢再次出現紅腫。來診時右下肢腫脹,皮膚暗紅、略灼熱,納可,眠差,小便調,大便干,舌紫,苔黃膩,脈弦滑。查體:右下肢腫脹,皮色暗紅。左下肢皮溫正常,右下肢皮溫高,皮膚厚韌,無壓痛,右脛前凹陷性水腫,霍曼氏征(-),股三角區無壓痛。侯教授認為此病為大腳風,且濕熱毒邪較重,給予茵陳赤小豆湯加味,藥物組成:茵陳30 g,赤小豆30 g,薏苡仁30 g,蒼術 12 g,黃柏 12 g,懷牛膝 10 g,佩蘭 10 g,白豆蔻10 g,澤瀉 12 g,甘草 6 g,當歸 12 g,皂角刺 6 g,夏枯草12 g,蒲公英20 g,僵蠶10 g,桑枝 30 g。水煎服,每日1劑。9月29日2診,患肢紅腫減輕,二便調,舌紅,苔黃,脈弦,上方繼服。10月14日3診,患肢皮色正常,僅右足背輕度腫脹,舌淡紅,苔薄黃,脈弦,上方去澤瀉、蒲公英、佩蘭、白豆蔻,加黃芪30 g,黨參15 g,水煎服,每日1劑。10月29日4診,右足背腫脹較前明顯減輕,二便調,舌紅,苔黃,脈弦,上方去夏枯草和赤小豆,皂角刺改為12 g,加木瓜 15 g,絲瓜絡12 g。2019年4月14日隨訪,患者右下肢未再出現腫脹,偶有勞累后足背輕度腫脹,休息后即可緩解,納眠可,二便調。
按語:患者因濕熱之邪浸漬肌膚,流注下肢而見患肢紅腫、疼痛,治療宜清熱利濕,活血消腫。患肢皮色暗紅,熱度不甚,為“濕”重于“熱”,虛實夾雜,以“標實”為主,按照中醫“急則治其標”的原則,在治療上以清熱利濕為主,內服中藥以茵陳赤小豆湯化裁加減,方中以茵陳、赤小豆、薏苡仁為君,清熱解毒、健脾利濕。黃柏、蒼術、澤瀉、蒲公英更助君藥清熱解毒、利濕消腫之功,同為臣藥。佩蘭、白豆蔻芳香化濁、醒脾化濕,俱為佐藥。濕熱之邪凝滯脈絡,故加牛膝、皂角刺、僵蠶以活血通絡散結。3診時患肢紅腫明顯緩解,并考慮患者患病日久、正氣益傷、邪氣留戀,故酌減清熱藥,加黃芪、黨參以益氣扶正祛邪。4診時,患肢已無明顯紅腫,去清熱、消腫之夏枯草、赤小豆,久病入絡,故加木瓜、絲瓜絡以通經活絡,鞏固療效。
淋巴水腫作為慢性進展性疾病,后期治療難度大,且不易根治,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侯教授在治療淋巴水腫方面經驗豐富,提出從脾論治,以“健脾利濕”為主要治則,并主張在淋巴水腫早期配合外治療法,臨床療效顯著。不僅可以減輕患者病痛的折磨,同時也避免了疾病后期手術治療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