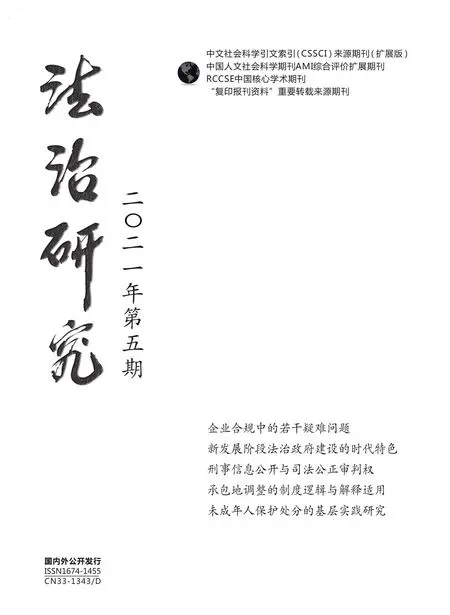民法典視野下土地經營權性質的再探討*
肖 鵬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在2014 年中央1 號文件中得到政策確認以來,如何實現其妥當的立法表達引發了諸多爭議,在堅持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逐漸形成了“用益物權+用益物權”①參見蔡立東、姜楠:《承包權與經營權分置的法構造》,載《法學研究》2015 年第3 期。“用益物權+債權”②參見高海:《論農用地“三權分置”中經營權的法律性質》,載《法學家》2016 年第4 期;溫世揚:《從〈物權法〉到“物權編”——我國用益物權制度的完善》,載《法律科學》2018 年第6 期。和“成員權+用益物權”③參見高飛:《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法理闡釋與制度意蘊》,載《法學研究》2016 年第3 期。等三種模式,闡釋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并進一步構建我國農村土地權利結構。其中,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是爭議的核心焦點之一。2018 年《農村土地承包法》修訂,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立法表達雖然初步完成,但是由于學界對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的爭議較大,并未形成統一的認識,立法表達采用了較為模糊的處理方式,典型的表現在于:土地承包權的規范過于簡單,④土地承包權的規定,僅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9 條出現。雖然可以確定土地承包權的主體應當是農戶,但是土地承包權的性質、內容等,均無明確的法律規定。土地經營權的性質爭議擱置⑤《農村土地承包法》對土地經營權性質爭議的擱置,最典型的表現是融資擔保制度。《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7 條確認土地經營權可以融資擔保,但是融資擔保并非法律術語。從我國意定擔保物權的現行規則來看,如果將土地經營權確認為物權,則應當適用抵押制度;如果將土地經營權確認為債權,則應當適用質押制度。同時,土地經營權性質爭議的擱置,也得到了立法者的確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認為,“鑒于對土地經營權性質見仁見智,這次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以解決實踐需要為出發點,只原則界定了土地經營權權利,淡化了土地經營權性質。”參見劉振偉:《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載《農村工作通訊》2019 年第1 期。。
《農村土地承包法》對土地經營權性質的模糊表達方式,不但使得對其相關法律規則進行科學完善成為必要,⑥參見陳小君、肖楚鋼:《論土地經營權的政策意蘊與立法轉化》,載《新疆社會科學》2021 年第1 期。也對學界關于土地經營權性質的探討產生了重大影響。在《農村土地承包法》修訂之前,無論是采用何種權利構造模式表述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立法表達中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應當一以貫之,是學界的基本共識。就土地經營權的性質而言,要么是債權、要么是物權,這植根于我國民事權利體系中債權物權的二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修訂之后,物權說和債權說均可以在現行法中找到足夠的支持證據⑦參見郭志京:《民法典視野下土地經營權的形成機制與體系結構》,載《法學家》2020 年第6 期。,使得對土地經營權性質的界定出現了物權說⑧參見蔡立東:《從“權能分離”到“權利行使”》,載《中國社會科學》2021 年第4 期。、債權說⑨參見高圣平:《〈民法典〉與農村土地權利體系:從歸屬到利用》,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6 期。之外的二元論,即根據不同標準將土地經營權區分為債權或者物權⑩參見宋志紅:《再論土地經營權的性質——基于對〈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目的解釋》,載《東方法學》2020 年第2 期。。2020 年《民法典》制定,土地經營權在民法典物權編用益物權分編土地承包經營權章中加以規范。但是,土地經營權入典并未終結土地經營權性質的爭議。在《民法典》制定實施之后,土地經營權債權說、物權說和二元論的爭議,依然是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立法表達研究的核心議題。土地經營權權利性質源于農村土地的權利分置邏輯,關乎土地經營權相關制度的完善,應當考慮《民法典》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度銜接,確有再探討?在2018 年《農村土地承包法》修訂之前,筆者認為土地經營權應當被界定為用益物權,這與農村土地權利分置的整體邏輯密切相關: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分置的基礎在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身份屬性。分置后土地承包權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中的身份關系,土地經營權應當取代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用益物權,成為純粹意義上的財產權。但是,現行法中土地經營權的產生主要基于農地流轉,應當對其權利性質重新作出解釋。參見肖鵬:《土地經營權的性質研究——基于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規范性文件的分析》,載《中國土地科學》2016 年第9 期;肖鵬:《農村土地“三權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權初探》,載《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1 期。的必要。
二、現行法中土地經營權的派生邏輯
土地經營權的派生邏輯,與其權利性質直接相關。《民法典》基本沿襲了2018 年《農村土地承包法》修訂中確立的土地經營權產生的三種情形。
(一)基于農地流轉產生的土地經營權
《民法典》第339 條規定的是基于農地流轉產生的土地經營權。?參見《民法典》第339 條的相關規定。考慮到《民法典》第342 條對其他方式承包的規定,《民法典》第339 條規定的土地經營權顯然只能適用于家庭承包方式,除了刪除與出租沒有實質差異的流轉方式轉包和沒有規定“向發包方備案”這一管理性規定外,其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6 條規定土地經營權派生邏輯是一致的。在家庭承包方式中,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基于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即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此為農村土地“兩權分置”。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采用法定方式向他人流轉土地經營權?
僅就《民法典》第339 條來看,土地承包經營權向他人流轉土地經營權的合法性基礎是其本身具備土地經營權,即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應當首先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之上為自己設立土地經營權,然后將該土地經營權通過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轉。此種解釋方式符合“用益物權+用益物權”的權利結構模式。但是此種解讀問題在于,一方面此種流轉背景下受讓方的權利性質難以統一,仍需要取決于流轉方式:采用出租等債權流轉方式流轉的,受訪方取得土地經營權租賃權;采用入股等物權流轉方式流轉的,受讓方取得土地經營權。另一方面如此理解也難以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相互銜接。《農村土地承包法》除了流轉土地經營權外,還存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這一術語,而且從整體的法律表達來看,兩者實質上并無差異。
(二)基于融資擔保產生的土地經營權
《民法典》第381 條明確規定了土地經營權抵押,而沒有采用融資擔保這一《農村土地承包法》?參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7 條的相關規定。中的術語,即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在抵押權實現時應當將地役權一并轉讓?參見《民法典》第381 條的相關規定。。考慮到土地經營權性質的探討在后文之中,此處仍采用了融資擔保。將流轉作為土地經營權設立了方式后,可以更好地理解《農村土地承包法》中作為受讓方的土地經營權人在其持有的土地經營權上設立融資擔保的規定。其主要的疑問是,承包方如何在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上設立融資擔保。
《民法典》第339 規定的土地經營權設立方式涵蓋了其他方式。從《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來看,代耕納入其他方式并無疑問。核心的爭議在于融資擔保是否應當歸入土地經營權設立的其他方式?有學者對此持肯定態度,認為其他方式至少應當涵蓋抵押。?同前注⑦。筆者認為,融資擔保不應當是土地經營權設立方式。土地經營權融資擔保與出租、入股、代耕等存在重大差異,不宜混為一談。無論是土地經營權抵押還是質押的設立,重視的均是土地經營權的交換價值,無須對農村土地的有形支配,?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620 頁。也不涉及經營土地權利的讓渡。而土地經營權出租、入股或者代耕,則需要將經營農村土地(即有形支配)的權利讓渡給受讓方。因此,承包方以土地經營權設立融資擔保時,土地經營權并未真正產生。
因此,《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的承包方以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不應理解為基于抵押或者質押產生土地經營權。這里需要闡明此種情形下土地經營權設立的時間和方式。合理的解釋是,承包方并未以土地經營權進行融資擔保,而應當是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抵押物或者質押物。在融資擔保實現時,不應處分土地承包經營權,而是應當處分土地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人通過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等法定方式設立土地經營權,受讓方取得土地經營權,?參見李國強:《〈民法典〉中兩種“土地經營權”的體系構造》,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0 年第5 期。金融機構就流轉價款優先受償。
(三)基于其他方式承包產生的土地經營權
《民法典》僅在第342 條規定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方可以流轉土地經營權。但是,并未明確規定承包方的權利稱謂。故而,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權利自然應當以《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為準,即土地經營權。21參見參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9 條的相關規定。此種土地經營權直接派生于土地所有權,發包方和承包方簽訂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經營權,從而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特定化為家庭承包方式中承包方的權利稱謂。22參見高圣平:《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與民法典物權編編纂——評〈民法典物權編(草案二次審議稿)〉》,載《法商研究》2019 年第6 期。
根據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取得方式,2002 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將其分為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區分的依據在于兩種承包方式功能定位的差異。家庭承包是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的“人人有份”的承包,具有社會保障的性質,而其他方式承包是通過市場化方式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23參見胡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7 頁。同時,對前者實行物權保護,而對后者實行債權保護。24參見柳隨年:《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說明》,載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2-10/18/content_5300882.htm,2021 年5 月20 日訪問。《物權法》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規定基本是對《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延續,最大差異在于第一次不區分取得方式明確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用益物權性質,“所有權+用益物權”的農村土地權利結構最終得以確立。25參見肖鵬:《“三權分置”下的農村土地權利結構研究》,載《中國土地科學》2018 年第4 期。值得關注的是,《物權法》雖然將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認可為用益物權,但是并未作出有別于《農村土地承包法》的進一步規定。不同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差異仍然存在。26比較典型的差異是,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得抵押,而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則被法律所允許。參見《物權法》第180 條和第184 條的相關規定。2018 年《農村土地承包法》修訂中,考慮兩種承包方式功能定位的差異,將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權利明確為土地經營權。27參見黃薇:《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210 頁。
值得關注的是,為了與家庭承包方式中土地經營權流轉方式保持一致,2018 年《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3 條將原來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修正為土地經營權出租。28同上注,第221 頁。《民法典》第342 條規定其他方式承包中土地經營權流轉方式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一致。其疑問在于,此處的流轉能否等同于家庭承包方式中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如果將兩者等同,受讓方取得土地經營權,則可能面臨承包方和受讓方同時陷入土地經營權困境。這里的關鍵是對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權利性質的界定,將在后文進一步闡釋。
三、土地經營權債權性質的重新厘清
在明晰現行法中土地經營權派生邏輯的基礎上,需要對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作出進一步的探討,這既是對其派生邏輯的驗證,也是完善其相關制度的基礎。
(一)土地經營權物權定性的困境
盡管土地經營權定位為用益物權,可以得到現行法和實踐樣態的支撐,但是土地經營權定性為用益物權也面臨諸多困境。其核心的問題在于,出租方式的合理解釋。從農地流轉的實踐來看,土地經營權物權說意味著否定已經大量存在的債權性租賃流轉。29參見劉銳:《〈民法典(草案)〉的土地經營權規定應實質性修改》,載《行政管理改革》2020 年第2 期。從權利體系的闡釋看,土地經營權物權說難以對通過出租方式設立土地經營權作出合理解釋,而只能將出租方式作出特殊化處理:出租不適用《民法典》租賃合同的規定、自設土地經營權再通過出租流轉、將出租設立的土地經營權作為債權。
遼寧銷售針對定向群體客戶,制定差異化促銷方案。如利用“春耕惠農”政策開展油卡非潤互動促銷,進一步挖掘了農業客戶對潤滑油的潛在需求。今年春耕期間,鐵嶺分公司50多名加油站經理對周邊971個村屯進行了劃片走訪,特別是加強與農村合作社等大客戶的聯系,登記潤滑油客戶306個。走進政府農機博覽會,宣傳春耕惠農政策,發放傳單5000份,現場擺置昆侖潤滑油,當場賣出機油30多桶。截至9月20日,鐵嶺分公司店銷潤滑油243.3噸,同比增長344.79%。
首先,出租不適用《民法典》合同編規定的租賃合同,30參見李國強:《〈民法典〉中兩種“土地經營權”的體系構造》,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0 年第5 期。其設立的是用益物權。此種觀點雖然可以作為土地經營權物權說的解釋路徑,但是將會與整個民法體系產生嚴重沖突。一方面,從《民法典》規定來看,合同編第十四章專章規定了租賃合同,出租產生租賃權并無爭議。而且土地經營權出租期限應當適用租賃合同的相關規定,這在司法實踐中也得到了認可。3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6 條第1 款規定:“當事人對出租地流轉期限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參照民法典第730 條規定處理。除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屬于林地承包經營外,承包地交回的時間應當在農作物收獲期結束后或者下一耕種期開始前。”另一方面,從集體建設用地的相關規范來看,2019 年《土地管理法》修訂明確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第63 條第3 款明確了只有出讓方式才能設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第4 款再次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租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作了區分表述,32參見《土地管理法》第63 條的相關規定。從而明確了出租方式的債權設定屬性。33參見宋志紅:《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設立的難點問題探討——兼析〈民法典〉和〈土地管理法〉有關規則的理解與適用》,載《中外法學》2020 年第4 期。此外,土地經營權還面臨再流轉的問題。從《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來看,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形式同樣應當包括出租、入股等方式。即便是土地經營權屬于用益物權,通過出租方式再流轉的,也只能適用權利租賃的規定,受讓方取得的是土地經營權租賃權,屬于債權;通過入股方式再流轉的,受讓方取得土地經營權,屬于用益物權。
其次,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自設土地經營權然后再通過出租流轉,即需要解釋次級用益物權設立的合理性,也面臨流轉中受讓方權利定位的難題。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自設土地經營權的理論依據在于“用益物權+用益物權”的權利構造模式,其合理性有待商榷。一方面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自設土地經營權不能與地上權人設立次級地上權簡單等同。德國法雖然存在地上權人可以設立次級地上權的規定,34參見[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冊)》,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652 頁。但是其目標是為了解決土地的空間利用問題,35參見孫憲忠:《德國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228 頁。并滿足無法籌到足以購買完整地上權資金的其他主體,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利用土地的需求。36參見于飛:《從農村土地承包法到民法典物權編:“三權分置”法律表達的完善》,載《法學雜志》2020 年第2 期。但是,土地承包經營權與土地經營權的設立,并沒有土地的不同空間利用的區分,而是在同一承包地塊之上同時存在兩個均具備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能的用益物權,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后者架空前者的局面,37參見袁野:《土地經營權債權屬性之再證成》,載《中國土地科學》2020 年第7 期。這不但在事實上不可能,38參見吳義龍:《“三權分置”論的法律邏輯、政策闡釋及制度替代》,載《法學家》2016 年第4 期。也不符合用益物權以物的利用為內容,同一標的物不得同時存在用益內容相同的兩個用益物權的原則。39參見王澤鑒:《民法物權(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270 頁。而且從農地流轉的實踐來看,土地經營權人往往也不是缺乏資金的弱勢群體。同時,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自設用益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同樣面臨流轉后受讓方的權利性質和名稱難以統一的問題,這與前文所述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困境類似,不再贅述。
最后,將出租方式設立土地經營權作出債權定性,并進一步將其排除在《民法典》土地經營權規范范疇之外,交由《民法典》合同編的租賃合同來調整,40參見房紹坤、林廣會:《土地經營權的權利屬性探析——兼評新修訂〈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載《中州學刊》2019 年第3 期。從而只將流轉期限為5 年以上經過登記的土地經營權作為用益物權。41參見房紹坤:《民法典物權編之檢視》,載《東方法學》2020 年第4 期;溫世揚:《〈民法典〉物權編的守成、進步與缺憾》,載《法學雜志》2021 年第2 期。如果《民法典》不將出租作為土地租賃權設立的形式之一,上述解釋并不存在邏輯障礙42參見郭志京:《民法典視野下土地經營權的形成機制與體系結構》,載《法學家》2020 年第6 期。。在《民法典》的既有框架中,無法回避出租設立土地經營權的規定,上述解釋路徑只能將部分土地經營權認定為用益物權,從而導致無法完成土地經營權權利性質的一體化構造,最終只能采用土地經營權性質二元論。43參見高海:《“三權”分置的法構造——以 2019 年〈農村土地承包法〉為分析對象》,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1 期;姜楠:《土地經營權的性質認定及其體系效應——以民法典編纂與 〈農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訂為背景》,載《當代法學》2019 年第6 期;王鐵雄:《土地經營權制度入典研究》,載《法治研究》2020 年第1 期。盡管《民法典》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現行規定,以及土地經營權流轉實踐的豐富多樣性,均可以為土地經營權性質的二元論提供支撐。44參見屈茂輝:《民法典視野下土地經營權全部債權說駁議》,載《當代法學》2020 年第6 期。但是,從民事權利的體系化構建出發,從沒有一種民事權利出現“時而是物權,時而是債權”的先例,45同前注⑨。這不符合民事權利規范中物債二分的基本規則46同前注?。。土地經營權也不應當例外,其權利性質應當作單一化的界定。換言之,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只能被界定為物權或者債權。
(二)土地經營權債權性質的證成
在物債二元區分邏輯前提下將土地經營權劃歸其中一元,47參見劉云生:《土地經營權的生成路徑與法權表達》,載《法學論壇》2019 年第5 期。債權說在解釋論上最為順暢48參見謝鴻飛:《〈民法典〉中土地經營權的賦權邏輯與法律性質》,載《廣東社會科學》2021 年第1 期。。從土地經營權的派生邏輯來看,土地承包經營權人通過出租或者其他方式49從《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整體來看,其他方式主要是代耕。代耕與出租的差異主要是代耕人一般不需要支付對價,其產生的土地經營權只能被定性為債權。需要說明的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設立土地經營權,一方面是法律為土地經營權設立方式的創新留有了空間,另一方面也是土地經營權應當被界定債權的體現,這是因為物權的設立方式應當是法定的,而不能由當事人任意選擇設立方式。設立土地經營權的性質為債權,并無闡釋上的疑難。土地經營權債權性質證成需要解決的是其它派生邏輯中土地經營權的性質問題。50融資擔保并非土地經營權的設立方式,作為債權的土地經營權能否抵押以及如何抵押的問題,將在土地經營權債權性質的體系效應中統一闡釋。
第一,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以入股方式設立土地經營權的性質。入股的一般理解是民事主體將自己的財產出資公司或者農民專業合作社,從而成為股東或者成員。51根據《公司法》和《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規定,股東或者成員的出資均應為貨幣或者可以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資產。土地經營權債權說的難題之一在于作為債權的土地經營權能否作為出資對象。一方面,無論是《公司法》還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均未明確禁止債權出資。52《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第13 條第2 款禁止的債權出資,是成員對該社或者其他成員的債權不得出資,土地經營權入股不屬于此種情形。另一方面,土地經營權入股應當區別于公司股東的出資或者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的出資。如前文所述,土地經營權入股應當理解為土地經營權的設立行為,土地承包經營權人通過流轉合同為公司或者農民專業合作社設立土地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為股東或者成員獲得收益,是設立土地經營權的對價,即《農村土地承包法》中的流轉價款。因此,土地經營權是物權還是債權,與債權能否出資無關。從法律效果上看,入股則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將土地經營權轉化為股權以享有股金分紅的處分方式,53參見單平基:《“三權分置”理論反思與土地承包經營權困境的解決路徑》,載《法學》2016 年第9 期。性質上屬于對權利的債權性處分,即僅將土地經營權處分給他人。54參見朱廣新:《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政策意蘊與法制完善》,載《法學》2015 年第11 期。無論是政策中對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保底收益的強調,還是立法中對公司解散時入股土地退回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規定,55參見《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16 條規定:公司解散時入股土地應當退回原承包方。均是對入股設立土地經營權債權說的有利支撐。
第二,其他方式承包中土地經營權的性質。有學者認為,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土地經營權與原土地承包經營權僅僅是權利名稱的差異,邏輯上無法認定為不同性質的權利,應當屬于用益物權。56同前注。筆者認為,此類土地經營權認定為債權并無太大阻礙。如前文所述,其他方式承包中派生土地所有權的土地經營權,從名稱上經歷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向土地經營權的轉變,從權利性質上則從2002 年《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債權變為2007 年《物權法》的用益物權。《民法典》并未明確規定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取得的權利,同時為了土地經營權流轉表達的一致,規定承包方可以流轉土地經營權。《民法典》此種對承包方權利的規定方式,為其權利性質的明晰,留下了充分的解釋空間。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土地經營權,與家庭承包方式中受讓方的土地經營權性質和內容相同,均為土地的商業性利用方式。57參見高圣平、王天雁、吳昭軍:《〈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 年版,第326 頁。從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土地經營權的實踐來看,“承包方有的與發包人是債權關系,如承包菜地,約定承包期3 年,其間是一種合同關系。”58同前注,第359 頁。即使是將其他方式承包中那些期限較長的承包關系定性為債權,也不影響為其提供保護。一方面,一項權利的效力強弱不能僅依據物債之分,更應考察實證規范對權利內容和效力的具體表達。59參見吳昭軍:《土地經營權體系的內部沖突與調適》,載《中國土地科學》2020 年第7 期。除了權利名稱外,無論是《民法典》還是《農村土地承包法》對其他方式承包的規定并未產生實質變化;另一方面從租賃權物權化的發展背景來看,一味強調作為租賃權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也不符合實際的立法情況。60同前注。因此,從權利保護而言,將此類土地經營權定性為債權同樣可以為權利人提供充分的保護。
第三,土地經營權入典、登記與否和期限長短均不應作為權利性質判斷的標準。首先,土地經營權物權說的重要依據在于土地經營權已經納入民法典物權編予以規范。61同前注。但是,從民法典用益物權分編結構看,土地經營權也并未采用其它用益物權專章規定的形式,而是置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章節中,62同前注。從解釋上看不能簡單因為土地經營權植入到了物權編就認定為用益物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章節完全可以在必要時隨帶規定債的問題。63參見龍衛球:《民法典物權編“三權分置”的體制抉擇與物權協同架構模式——基于新型協同財產權理論的分析視角》,載《東方法學》2020 年第4 期。其次,土地經營權登記的規定不能等同于土地經營權性質的規定,其作用“主要在于引導土地經營合同當事人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作出民事法律行為,以保護當事人的權益。而對土地經營權性質的確定,以其是否進行登記而進行不同類別之劃分,法律依據并不充分。”64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物權編理解與適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11 頁。從《民法典》的規定來看,有些權利雖未作登記卻為物權(例如:土地承包經營權),也有權利雖經登記卻并非物權(例如登記備案后租賃合同中的租賃權)65參見崔建遠:《物權編對四種他物權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載《中國法學》2020 年第4 期。;從國外立法例看,《荷蘭民法典》規定所有類型的法律行為(包括債權)均可登記66參見單平基:《分解、舍棄抑或改造:〈民法典〉編纂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定位》,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 期。。最后,期限長短更是無法勝任土地經營權性質的界分標準。以《意大利民法典》為例,用于植樹造林的土地租賃期限最長可約定為99 年,67參見《意大利民法典》,費安玲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392 頁。其租賃權的性質亦不會基于期限原因成為物權。相反,土地經營權登記和期限規定的多樣性,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土地經營權債權界定的必要性。因此,強化土地經營權的保護,完全可以通過租賃權的物權化來實現,而非將其規范為用益物權,從而加重對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負擔。68參見韓松:《論民法典物權編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規定——基于“三權分置”的政策背景》,載《清華法學》2018 年第5 期。
四、土地經營權債權性質的體系效應
土地經營權界定為債權,可以更好地完善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法律政策體系,實現“三權分置”背景下農村土地權利結構的重構和土地經營權抵押制度的健全。
(一)土地承包權實為土地承包經營權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通過《農村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完成了相應的立法表達。但是作為“三權分置”中間環節的土地承包權的規定非常簡陋,只出現在《農村土地承包法》第9 條中。土地承包權的主體、客體、內容和權利性質等均須進一步規范。在明晰了家庭承包方式中土地經營權的派生邏輯和權利性質后,土地承包權的相關問題豁然開朗。
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與受讓方達成合意,為受讓方設立土地經營權,該土地經營權為債權。此種情形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主體、客體、內容和權利性質等均不會因為派生了土地經營權發生變化。《農村土地承包法》中的土地承包權實質上就是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不但可以避免對土地承包權的重新解讀,還可以避免作為成員權內容的土地承包權和農地流轉中土地承包權概念上的混亂。69同上注。之所以規定承包方保留土地承包權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闡釋:一方面土地承包權可以理解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簡稱。故而除去《農村土地承包法》第9 條外,土地承包權既無規定的必要,也無規定的可能。《民法典》規定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后,同樣無須對同一權利再作出土地承包權的規定。70同前注。另一方面保留土地承包權的規定,表明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在設立土地經營權后其權利行使受到限制,不但將農村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在一定期限內交由土地經營權人行使,而且不得進行土地經營權的重復設定,尤其是在土地經營權經過登記取得對抗效力之后。同時,除非出現法定情形,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不得單方解除流轉合同。71參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2 條的相關規定。
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權利性質的明晰,奠定了構建“三權分置”背景下我國農村土地權利結構的基礎。土地承包權實為土地承包經營權,其權利性質為用益物權;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可以通過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為他人設立土地經營權,其權利性質為債權。因此,在家庭承包方式中,未設立土地經營權時,農村土地權利結構應為“所有權+用益物權”;設立土地經營權時,農村土地權利結構則為“所有權+用益物權+債權”。在其他方式承包中,由于沒有土地承包權的存在,其權利結構應為“所有權+債權”。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無論何種承包方式中土地經營權再流轉時的農村土地權利結構。按照《民法典》中租賃合同關于轉租的規定,經出租人同意轉租的,承租人與出租人的租賃合同繼續有效。72參見《民法典》第716 條的相關規定。因此,土地經營權再流轉時,土地經營權人的債權依然存在,受讓方也取得新的債權。如此以來,我國農村土地權利結構將會更加復雜,且沒有現實必要。因此,筆者建議,家庭承包方式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或者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的,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或者土地所有權人與再流轉的受讓方之間產生直接的債權關系,73在國外立法例中,農地租賃的轉租可以在出租人和新承租人之間產生直接租賃關系。《意大利民法典》第1649 條規定:“出租人同意轉租的,轉租被認為是發生在出租人與新承租人之間的直接租賃關系。”同前注,第395 頁。避免出現“所有權+用益物權+債權+債權”或者“所有權+債權+債權”的情形,從而維持我國農村土地權利結構的統一和簡潔。
(二)健全土地經營權抵押制度
由于土地經營權性質的不確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7 條采用了融資擔保的提法,沒有將其明確為土地經營權抵押或者質押。通常的理解是,土地經營權為物權的,則應當設立抵押,74同前注,第714 頁。土地經營權為債權的,則應當設立權利質押。《民法典》在第342 條和第381 條均明確規定了土地經營權抵押,這成為土地經營權應當被界定為用益物權的重要支撐之一。75同前注。土地經營權的債權定位既要證成土地經營權抵押的正當性,又要明晰土地經營權抵押的關鍵制度。
首先,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抵押既有學理支持,也可以從《民法典》現行規定中加以解釋。從抵押和質押的制度區分來看,兩者的主要差異在于對物的利用方式。抵押權的設立無須轉移財產的占有,質權的設立則需要轉移財產的占有。76參見[日]我妻榮:《新訂擔保物權法》,申政武、封濤、鄭芙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195 頁。土地經營權作為抵押物時,不能轉移農村土地的占有,只有將土地置于土地經營權人的占有、使用和收益范圍之內,土地經營權人才能從事農業經營、持續產生收益,才有按期履行債務的可能性。“土地經營權人以土地經營權設定擔保之后仍得行使其土地經營權,已與質權性質相抵觸,因為如若設定質權,土地經營權人必不得行使其土地經營權。”77高圣平:《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改后的承包地法權配置》,載《法學研究》2019 年第5 期。從我國《民法典》第399 條的規定來看,修正了《物權法》第194 條關于耕地上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的規定,保留了“法律規定可以抵押的除外”的但書規定。78參見《民法典》第399 條和《物權法》第194 條的相關規定。值得注意的是,《土地管理法》第10 條規定的土地使用權,是為了實現將國家或者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交由相關民事主體使用,79參見《土地管理法》第10 條的相關規定。其本身并無法明確為用益物權,而是應當根據其設立方式區分為用益物權或者債權。以建設用地為例,無論是獲得國有土地使用權,還是集體土地使用權,均可以通過出讓或者出租等不同方式設立。出租方式設立國有土地使用權雖然屬于債權,但是可以抵押也有明文規定。80參見國土資源部《規范國有土地租賃若干意見》第6 條第1 款:“國有土地租賃,承租人取得承租土地使用權。承租人在按規定支付土地租金并完成開發建設后,經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同意或根據租賃合同約定,可將承租土地使用權轉租、轉讓或抵押。承租土地使用權轉租、轉讓或抵押,必須依法登記。”因此,土地經營權抵押既可以納入《民法典》第395 條第2 款“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財產”,也可以認為是《民法典》第399 條中法律另有規定可以抵押的集體土地使用權。
其次,應當進一步健全土地經營權抵押制度。從實際操作來看,土地經營權抵押制度與土地經營權權利性質的關系不大,而是在于抵押權應當如何設立以及怎么實現。在抵押權設立方面,一方面應當正確處理土地經營權期限與貸款期限的關系。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設立抵押權的,應當明確在抵押權實現時可以處分的土地經營權的期限,該期限不得超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剩余期限;土地經營權人設立抵押的,貸款期限不得超過土地經營權期限,在抵押權實現時只能處分剩余期限的土地經營權。另一方面應當關注流轉價款支付方式與貸款期限、額度的關系。土地經營權人支付流轉價款一般是分期付款,即按年或者生產周期支付。此種支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貸款期限以及貸款額度,中長期貸款和大額貸款往往難以獲得,亟需土地經營權人的其他增信措施的配合支持。在抵押權實現方面,土地經營權變現困難,這既有農地嚴格用途管制的原因,也與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不完善相關,81參見肖鵬:《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制約與創新》,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4 期。傳統意義上的折價、拍賣或者變賣的抵押權實現方式往往難以奏效,這也成為阻礙土地經營權抵押順利開展的主要原因。貸款重組、按序清償82參見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農業部《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第15 條的相關規定。、強制管理、收益執行83同前注。等不同抵押權實現方式應當進一步積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