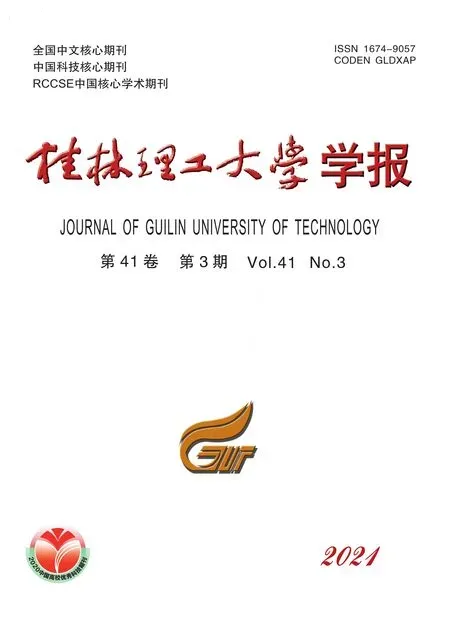不對稱轉體施工引起上、下球鉸偏位原因及分析
盛光祖, 秦建剛, 李 欣, 馬行川, 張廣潮, 涂建維, 徐朝政,詹曉歡, 姜云暉
(1.武漢地產集團市政建設管理有限公司, 武漢 430022; 2.中建三局城市投資運營有限公司, 武漢 430071;3.中鐵武漢勘察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漢 430074; 4.中南大學 土木工程學院, 長沙 410075;5.武漢理工大學 道路橋梁與結構工程湖北省重點實驗室, 武漢 430070)
0 引 言
武漢市常青路工程(青年路—三環線)跨鐵路主橋位于漢口站西側咽喉區, 采用95+105 m變截面連續鋼箱梁跨越京廣、漢丹、滬蓉等9股道鐵路線, 橋跨立面如圖1所示。橋面總寬51 m, 分幅布置[1-2], 橋梁橫斷面見圖2。受外部環境因素控制, 本橋采用墩頂不對稱結構轉體法施工[3], 兩側轉體長度分別為43.8和91.4 m, 轉體重量約86 000 kN, 轉體角度81°, 如圖3所示。為解決不對稱結構雙幅橋整體轉體的難題, 設計考慮在球鉸上方采用橫梁連接左右幅, 并設置臨時塔橫橋向張拉墩頂橫梁, 以改善轉體時橫梁的懸臂受力狀態。同時, 采用在短臂端進行部分配重, 在長臂側左、右幅梁底面, 距離中心球鉸半徑26.884 m處各設置一處輔助支撐, 與轉體球鉸一起, 形成三點支撐體系, 配合轉體短臂側梁頂配重共同作用, 以保證轉體的兩端平衡。每一處輔助支撐力設計按10 000 kN考慮, 并在輔助支撐處設置齒輪、齒條驅動系統, 由驅動系統實現左右幅梁體同步轉動。

圖1 橋跨立面圖

圖2 橋梁橫斷面

圖3 轉體結構平面布置
本橋轉體球鉸采用鋼球鉸[4], 球鉸半徑為8 m, 支承半徑為1.27 m, 中心銷軸孔徑0.11 m, 銷軸半徑0.1 m, 銷軸和上、下球鉸中心的銷孔周圍預留有1 cm的孔隙, 上球鉸和梁體直接采用螺栓連接, 下球鉸通過地腳螺栓錨固在橋墩橫梁上。
1 施工工序及出現的問題
本橋采用常規方式施工橋梁下部結構, 在框架墩頂安裝轉體球鉸, 采用支架法拼裝鋼箱梁。拼裝完成后, 進行短臂端配重, 并在長臂端安裝輔助支撐及相應的驅動系統; 然后逐步拆除支架, 形成轉體前的三點支撐穩定懸臂狀態; 最后啟動驅動系統完成橋梁轉體。
在配重吊裝、支架拆除以及轉體實施過程中, 上、下球鉸沿縱向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相對滑移和偏位現象, 最大偏位值接近2 cm, 如圖4所示。因本橋驅動系統采用的齒輪和齒條之間容差有限, 為了確保轉體安全順利進行, 防止偏位過大導致齒輪和齒條之間卡死或脫空, 本文從球鉸結構特點、受力特征等方面對該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影響進行分析。

圖4 上、下球鉸相對偏轉現場實景圖
2 工程實測結果
常青路跨線橋在施工過程中, 現場實測結果如下:
1)在配重和支架拆除工況下, 計算梁體變形在球鉸處產生的最大轉角為0.18°, 實測最大轉角為0.15°, 均小于球鉸極限狀態時的轉角0.20°, 轉體結構安全可靠。
2)配重和支架拆除完成并安裝輔助支撐后, 形成穩固的三點支撐體系, 施工過程中不平衡彎矩產生的上下球鉸偏位不會消失, 轉體將在上下球鉸偏位的情況下進行, 該狀況與現場實際情況吻合。轉體時由于水平力的產生, 球鉸偏位的情況有所加劇, 但在達到最大偏位后趨于穩定, 結構仍處于安全可控范圍內。
3 上、下球鉸相對偏位原因分析
結合橋梁的設計特點及施工工序, 通過深入分析可知, 本橋在施工過程中, 上、下球鉸產生相對偏位的原因主要為以下3點:
1)球鉸設計中銷軸和銷孔之間預留的1 cm空隙, 是上、下球鉸能夠產生相對偏位的前提條件。上球鉸受到水平力或彎矩時, 會產生相對滑移趨勢, 當外力克服上、下球鉸之間的摩阻力后, 上球鉸開始滑移。因銷軸和銷孔之間存在空隙, 此時銷軸尚不具備限位功能, 故上、下球鉸產生偏位。當上球鉸滑移至與銷軸接觸后, 帶動銷軸產生傾斜, 直至銷軸與銷孔卡死, 此后, 銷軸開始發揮限位功能, 滑動停止。
2)在施工過程中, 轉體配重和梁體支架體系拆除的先后順序, 將使梁體產生不對稱變形,進而使球鉸上方的橫梁產生一定的轉角, 最終帶動上球鉸產生一定的偏轉, 這是上、下球鉸能夠產生相對偏位的外部因素之一。
3)常規水平轉體是在轉臺兩側牽引一對關于球鉸中心對稱的水平力形成力偶,為轉體提供動力, 理論上球鉸整體僅承受力矩作用。而本橋采用的動力系統對球鉸不能夠形成力偶, 故在轉體過程中, 驅動力將對上球鉸作用一個水平反力, 這是偏位現象產生的外部因素之二。
綜上所述, 上、下球鉸產生相對偏位主要受梁體變形和水平反力兩個外部因素控制, 故主要結合兩個外部因素對球鉸偏位原因及影響進行詳細分析。
3.1 梁體變形影響
在轉體設計時, 雖然已采取了配重和增加輔助支撐系統的方法保證橋梁在轉體過程中的平衡, 但對實際施工工序進一步分析可知, 配重吊裝、梁體拼接和支架拆除過程中, 梁體沿橫向和縱向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受力不對稱狀態, 使得梁體產生不對稱變形, 此外, 轉體結構的不對稱(短臂43.8 m, 長臂91.4 m)也會導致梁體產生不對稱變形, 進而帶動球鉸沿梁體橫向和縱向產生相對滑移和偏轉。梁體變形對球鉸相對偏位的影響可等效為在上球鉸作用一個不平衡彎矩M, 因此, 在橋梁拆除支架實施轉體前, 球鉸承受上部橋梁自重(包括配重和球鉸自重)G和不平衡力矩M的作用。球鉸達到滑移臨界狀態時的M等于球鉸克服靜摩擦的抵抗力矩,即[5]
M=GRμ,
(1)
其中:G為球鉸承受的豎向荷載, 本工程為86 000 kN;R為球鉸半徑, 本工程為8 m;μ為上下球鉸摩擦系數, 取0.05, 因此M=34 400 kN·m。
圖5為配重及部分支架拆除后, 最不利工況下的梁體變形分析圖, 此時短臂端下撓70.6 mm, 長臂端靠近臨時塔位置梁體上撓0.93 mm, 對于球鉸位置, 相當于沿縱向球鉸上方梁體轉動角度為0.18°。

圖5 最不利施工工況下梁體變形分析
3.2 牽引系統水平反力影響
橋梁實施轉體時, 通過驅動設備對梁體施加兩個水平牽引力帶動橋梁轉動, 此時, 球鉸為橋梁提供一個沿橫橋向的水平支撐力, 實現梁體受力平衡。同時, 梁體會對球鉸施加水平反力, 如圖6所示。不考慮轉體時的風荷載, 球鉸承受的水平荷載為[5]

圖6 球鉸水平受力平面圖

(2)
式中:F1為克服主鉸摩擦所需驅動力;F2為克服滾輪小車摩擦所需驅動力;G為球鉸承受的豎向荷載,G=86 000 kN ;R1為球鉸支承半徑,R1=1.27 m;μ為上、下球鉸摩擦系數, 取0.05;R2為輔助支承半徑,R2=26.884 m;G1為輔助支撐承受的豎向荷載,G1=10 000 kN;μ1為輔助支撐滾動摩擦系數, 取0.05。對于常青路工程,F1=67.7 kN,F2=500 kN, 因此, 每個牽引力FT=567.7 kN, 則球鉸承受的水平荷載為
F=2cosθ·FT,
(3)
式中:θ為滾輪小車和中心球鉸的連線與橋梁中心線之間的夾角,cosθ=0.878,則F=996.9 kN。
由以上分析可知, 球鉸的相對偏位對結構的影響可等效為作用于球鉸的不平衡彎矩M和水平荷載F。結合工程實際, 可分為自重與不平衡彎矩作用和自重、不平衡彎矩與水平荷載共同作用兩種受力狀態, 后者分別按彎矩與水平荷載垂直和平行兩種情況考慮[6], 如圖7所示。因此, 采用ANSYS軟件建立有限元模型, 可分別對圖5所示3種受力狀態進行計算, 分析球鉸偏位對結構的影響。

圖7 球鉸受力分析
4 ANSYS有限元模型
4.1 模型的建立
為確保常青路跨線橋轉體施工的安全可靠, 采用有限元分析軟件ANSYS建立本橋轉體球鉸的精細化模型, 對球鉸在橋梁轉體過程中的受力特征進行深入分析。上、下球鉸以及銷軸采用三維實體單元進行模擬,上、下球鉸之間以及球鉸與銷軸之間的界面關系采用接觸單元進行模擬[7-8]。
有限元模型以及網格劃分如圖8所示。對下球鉸的下表面節點, 分別約束X、Y和Z3個方向的平動和轉動自由度, 對銷軸下表面節點, 約束其水平方向的平動自由度。球鉸自重以體荷載的形式施加, 豎向荷載在上球鉸的上表面均勻布置。為了施加不平衡彎矩和水平荷載, 在球鉸中心距離上表面0.2 m處建立結構質點, 并將該單元與球鉸上表面節點形成剛域。

圖8 球鉸有限元模型
4.2 模型參數
模型尺寸按球鉸實際尺寸取值, 球鉸制作材料為Q345B鋼材, 銷軸制作材料為40Cr鋼材。鋼材彈性模量為206 GPa, 密度8 750 kg/m3, 泊松比為0.3。上、下球鉸界面之間的耐磨板材料為改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彈性模量為850 MPa, 密度950 kg/m3, 泊松比為0.3, 界面之間的摩擦系數為0.05[9], 界面接觸剛度(FKN)取0.1。
5 計算結果分析
按照球鉸在施工過程中可能承受的3種受力狀態對模型施加荷載[10], 分別計算球鉸在3種不同工況下的受力特征。
5.1 自重與彎矩作用
圖9為自重和不平衡彎矩共同作用時, 上、下球鉸相對位移隨不平衡彎矩的變化曲線。當彎矩小于33 500 kN·m時, 上、下球鉸基本不發生相對位移;隨著彎矩的繼續增大, 上、下球鉸之間克服其靜摩擦力, 隨后逐漸產生相對滑動。相比于式(1)計算所得臨界彎矩值34 400 kN·m, 有限元計算值誤差為2.6%, 說明有限元計算結果合理可靠。

圖9 工況一荷載-相對位移曲線
當彎矩達到34 530 kN·m時, 上、下球鉸沿彎矩作用方向相對水平位移達到19.62 mm, 垂直彎矩作用方向基本無相對滑動, 相對豎向位移達到3.28 mm。銷軸孔徑與銷軸直徑相差20 mm, 此時上、下球鉸恰好與銷軸接觸, 達到臨界位移狀態, 上球鉸沿彎矩作用方向的轉角值為0.20°。此后, 彎矩繼續增大, 銷軸開始承擔荷載, 由于銷軸的限位作用, 位移基本不發生變化。實測球鉸最大偏位為20 mm, 有限元計算值誤差為1.9%。
上、下球鉸之間的接觸狀態和接觸應力如圖10所示。在86 000 kN的自重和34 400 kN·m的不平衡彎矩作用下, 球鉸整體出現沿彎矩作用方向的水平滑移, 并且彎矩作用方向的邊緣處出現局部脫離現象, 與現場實際觀測情況基本一致, 此時脫離位置界面接觸應力為0, 界面最大接觸應力達到50.5 MPa。當不平衡彎矩增大至39 700 kN·m時, 下球鉸與銷軸接觸位置應力達到268 MPa, 接近其容許應力值270 MPa, 此時銷軸最大應力為114 MPa, 遠小于其容許應力值, 上、下球鉸界面上最大接觸應力為87.3 MPa, 小于其容許壓應力值180 MPa。由以上分析可知, 沒有水平荷載作用時, 球鉸能承受的極限不平衡彎矩為39 700 kN·m, 極限狀態下, 上球鉸沿彎矩作用方向的轉角值為0.23°。若彎矩繼續增大, 球鉸與銷軸接觸位置將超過其容許應力值, 即球鉸能夠抵抗的極限不平衡彎矩由球鉸的材料強度控制。

圖10 工況一條件下球鉸界面接觸狀態和接觸應力
5.2 自重、彎矩與水平荷載共同作用
5.2.1 水平荷載垂直于彎矩作用方向 圖11給出了工況二對應的自重、不平衡彎矩和垂直于彎矩作用方向的水平荷載共同作用下, 上、下球鉸的相對位移隨彎矩的變化曲線。

圖11 工況二荷載-相對位移曲線
當不平衡彎矩小于32 500 kN·m時, 上、下球鉸基本無相對滑移,隨著不平衡彎矩繼續增大,上、下球鉸逐漸出現相對滑移。當不平衡彎矩達到33 500 kN·m時,上、下球鉸沿彎矩作用方向的水平相對位移達到20.63 mm,垂直彎矩作用方向(水平力作用方向)的相對水平位移達到6.61 mm,豎向相對位移達到3.55 mm, 此時達到球鉸與銷軸相接觸的臨界狀態, 界面最大接觸應力為50.1 MPa。此后, 銷軸開始承擔荷載, 結構仍處于穩定狀態。球鉸能夠承受極限彎矩值為39 200 kN, 此時, 上球鉸沿彎矩作用方向的轉角值為0.22°, 與工況一類似, 球鉸承載不平衡彎矩的極限能力由下球鉸自身材料強度決定。
5.2.2 水平荷載平行于彎矩作用方向 在自重、不平衡彎矩和平行于彎矩方向的水平荷載共同作用下, 球鉸相對位移隨不平衡彎矩的變化如圖12所示。

圖12 工況三荷載-相對位移曲線
當不平衡彎矩小于27 500 kN·m時,球鉸基本無相對位移,當不平衡彎矩等于30 000 kN·m時,球鉸達到臨界狀態,最大水平相對位移為20.18 mm,最大豎向相對位移為3.31 mm, 此后銷軸開始承擔荷載。當不平衡彎矩繼續增大至31 000 kN·m時, 下球鉸與銷軸接觸位置拉應力達到267 MPa, 接近其容許應力, 即在自重、不平衡彎矩和平行于彎矩方向的水平荷載共同作用下, 球鉸能夠承受的極限彎矩值為31 000 kN·m, 相比于水平荷載垂直于彎矩作用方向時, 減小了20.9%, 極限狀態下, 上球鉸沿彎矩作用方向的轉角值為0.27°。
6 結 論
本文針對常青路橋梁在極不對稱轉體施工過程中, 上、下球鉸出現相對偏位問題, 結合施工工序, 對偏位產生原因進行了分析, 并基于ANSYS軟件建立精細化有限元模型, 對球鉸產生偏位后的力學行為進行計算, 得出以下結論:
(1)橋梁實施轉體過程中, 在自重和不平衡彎矩作用下, 球鉸產生臨界滑移(球鉸與銷軸接觸)對應的臨界不平衡彎矩為34 530 kN·m; 在自重、不平衡彎矩和垂直于彎矩方向的水平荷載共同作用下, 球鉸臨界不平衡彎矩為33 500 kN·m; 在自重、不平衡彎矩和平行于彎矩方向的水平荷載共同作用下, 球鉸臨界不平衡彎矩為30 000 kN·m。
(2)不平衡彎矩超過臨界值后, 球鉸一側先與銷軸接觸, 并推動銷軸向另一側靠近。與另一側也接觸后, 因銷軸頂端與球鉸頂鋼板也預留有10 mm間隙, 若不平衡彎矩繼續增大, 銷軸將產生一定傾角, 直至銷軸與球鉸頂底鋼板及銷孔接觸, 此時達到最大位移20.18 mm, 此后, 銷軸開始承擔荷載。在自重和不平衡彎矩作用下, 球鉸最大可承受極限不平衡彎矩值為39 700 kN·m; 在自重、不平衡彎矩和垂直于彎矩方向的水平荷載共同作用下, 球鉸能夠承受的極限不平衡彎矩為39 200 kN·m; 在自重、不平衡彎矩和平行于彎矩方向的水平荷載共同作用下, 球鉸最大可承受極限不平衡彎矩值為31 000 kN·m。
(3)球鉸承受極限不平衡彎矩的能力由球鉸自身材料強度決定, 超過極限彎矩后, 下球鉸與銷軸接觸位置最先達到其容許應力值。常青路橋梁轉體施工全過程中, 球鉸實測最大轉角始終小于球鉸在極限狀態下的轉角, 轉體結構始終處于安全穩定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