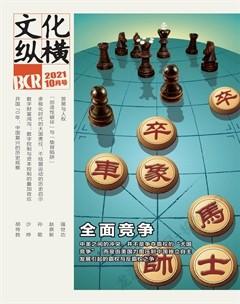中華文明何以五千年不斷流?
王凱歌
[關鍵詞]文明起源 大一統 中國文明連續性
在當今“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下,“何為中國”“何以中國”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從根本上說,中國問題可以歸結為:作為一個擁有長達5000年歷史、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復雜文明體,中國為何能夠保持文化的同一性、完整性以及文明的連續性?作為國家、文明和歷史的“中國”,是如何凝聚為一個豐厚的概念的?在后現代解構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盛行的當下,這些問題應被再次審視。
歷史學者往往將中國文明的獨特性與同一性,歸因于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以儒家為代表的正統思想的塑造。這種解釋被視為“文化決定論”或“政治文化學”,認為是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的路徑選擇和文明特色。正如論者所言,文化決定論的范式存在循環論證的問題,“不承認文化變遷的原因來自文化以外”,[1]忽視了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因素的作用。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來看,價值理念與思維方式并非憑空產生,其形成離不開特定的經濟社會環境,文化傳統的形成離不開社會結構與物質環境等客觀因素的塑造。[2]
本文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以許倬云的《漢代農業》與趙汀陽的《惠此中國》為案例,重新思考中國文明的連續性與同一性。許倬云從漢代精耕農業經濟的形成解釋中國文明的走向,探討中國走向大一統官僚制帝國的政治經濟成因;趙汀陽從四方族群逐鹿中原的歷史經驗中概括出歷史中國的成長方式,探討了“大一統”作為政治神學信念的實質。[3]兩者都重視小農經濟與農耕生活對于中國文明特性、精神世界與思維方式的塑造,從而跳出了以文化個性解釋文明特性的循環論證。
中國問題可以歸結為:作為一個擁有長達5000 年歷史、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復雜文明體,中國為何能夠保持文化的同一性、完整性以及文明的連續性?
小農經濟與大一統官僚制帝國的關系
農業文明可謂古代中國文明的底色。盡管曾經存在著發達的城市手工業,但無可否認,古代中國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耕文明。從文明起源上我們可以發問,為何中國沒有走向工商業文明,走向自治城市的松散聯盟,而是走向了精耕細作的農業文明,走向了大一統的官僚制帝國?
張光直先生指出,中國國家文明的起源主要依靠政治程序而非人與自然的關系。[4]在古代中國,財富的積累與生產力的提升主要不是靠技術進步或貿易,而主要靠政治組織程序,也就是政治整合社會的傳統。中國很早就實現了福山所謂的“現代國家”的構建,即中國在秦漢就建立起了中央集權的超大規模官僚制國家,[5]這可謂中國“政治程序”發展的巔峰。
從發生學或演化論的角度來看,中國走向官僚制國家與中國在周秦之際的經濟社會演變,尤其是小農經濟的確立有密切關聯。
從發生學或演化論的角度來看,中國走向官僚制國家與中國在周秦之際的經濟社會演變,尤其是小農經濟的確立有密切關聯。歷史學研究揭示出,中國官僚制國家的形成奠定在小農經濟上,而官僚制國家又有意地培養與鼓勵小農經濟。許倬云在《漢代農業》講述了一個中國何以走向農業文明形態的政治經濟學故事。自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在漢代確定下來,中國文明的發展方向就基本確定,再未脫離此軌道。然而,這并非歷史的定數。比如,在公元前5世紀到前3世紀動亂的戰國年代,中國始終有可能發展出一種以城市為中心的商品經濟(手工作坊業)。[6]那么,為何戰國以來發達的城市經濟沒有發展壯大,中國最終走上了對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的路徑依賴呢?
首先,人多地少的問題推動了農業精細化經營。戰國以來的技術進步推動了鐵器的廣泛使用,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鐵器開墾荒地,大量無主荒地被私人占有和經營。同時,自秦朝開始,人們不被允許自由遷徙,不得不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凸出,農民唯一的出路便是借助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開發利用那一小塊土地,由此推動了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

中國在漢代走向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基本方向
其次,戰國以來各國的變法運動強化了國家權力,推動了自耕農的形成。變法運動重塑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血緣宗法維系的封建制崩解了,地方行政改革廢分封行郡縣,加強了諸侯國君的集權。諸侯國設官分職,促進了非人格化的、富于功績制精神的官僚制產生。各國變法最成功的(也是最后開展的)是秦國的商鞅變法。商鞅變法廢除了“分土而治”的封建制,“為田開阡陌封疆”的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主的采邑權,“將農民從封建制度中解脫出來,建立起了一個在強大的地域性君主國家控制下的社會”。[7]實際上是承認了私人土地所有制,鏟平了介于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封建貴族勢力,造就了國家政權直接控制下的自由而獨立的自耕農。
最后,小農經濟成形得益于一個關鍵的政治因素:官僚制帝國以小農為統治基礎,國家主動培育小農。一方面,漢代國家限制獨立工商業的發展。這是由秦漢官僚制帝國的特性所決定的,維系帝國的穩定是首要任務,統治者努力抑制社會上各種集團對政權的潛在威脅。漢武帝時期采取的各種經濟管制措施,如壟斷緊要商品、發展官營工商業(鹽鐵官營),歧視性征稅(如告緡),以及其他一些財政和貨幣措施,將帝國的直接控制擴張到經濟領域。通過這些措施,國家達成了對社會的嚴密控制,獨立的工商階級勢力難以成長。
小農經濟成形得益于一個關鍵的政治因素:官僚制帝國以小農為統治基礎,國家主動培育小農。吊詭的是,政府調控土地分配的努力,并沒有阻擋自耕農破產的趨勢。
另一方面,國家又要限制土地兼并與大地主經濟。西漢一代,國家一直限制土地買賣與兼并,注重給農民授地,把大量無主土地與皇室領地分給無地農民,培養自耕農,并大力發展水利建設,造就了一個繁榮的農業經濟,為官僚制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爭奪兵源與稅收,漢朝政府不得不與大地主爭奪自耕農與人口,以阻止“私人地主控制下的田莊式種植園的出現”。[8]
吊詭的是,漢代政府在打擊私人獨立工商業的同時,卻間接造成了權貴對土地的投資。這種經濟社會現象曾被馬克斯·韋伯解讀為中國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商人發家致富后,不是進行資本再生產,而是購置田產宅院,培養子侄讀書參加科舉,這被他稱為一種對官職俸祿進行投資的“政治資本主義”。漢代政府調控土地分配的努力,并沒有阻擋自耕農破產的趨勢,大量自耕農因不堪賦役重負而破產,不得不出賣土地,淪為地主的佃農。這就導致從政府那里獲得的土地,經農民的買賣又流轉到了大地主手里,地主土地所有制得以形成。
盡管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并沒有走向羅馬帝國那種集體耕種的粗放式大莊園經濟,而是維持了精耕細作的小農經營(佃農經濟)。因為從實際生產率來看,受奴役的農業生產者的生產意愿,總是低于佃農身份的生產者。正如許倬云指出的,“一定要給予耕種者一些耕種意愿,最好的辦法就是佃戶耕好分佃的土地,地主再收租取得利益。”[9]就大地主的個人利益而言,佃農制也比集體耕作的做法更為可取。中國的佃農制,與羅馬驅使農奴集體耕作的大莊園經濟不同。羅馬在北非的大種植園,是由地主帶著監工(一般為兵團士兵)驅使奴隸進行集體耕作。在這種情況下,主奴差異以及階級關系的不平等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農作物的產量不會很高,于是更急需獲得大量的土地和勞力——這就是羅馬帝國不得不擴張的經濟動機。[10]相反,中國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既保證了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土地生產力的最大化,又在生產關系上避免了羅馬式集體耕作的奴隸經濟,從而避免了主奴差異與嚴重的階級不平等。
小農經濟模式的形成,從三個方面深刻影響了中國文明的發展方向。一、精耕細作的小農經營成為中國農業文明的最大特色。當然,這是皇權以強國家力量限制發達的城市經濟與私人工商業為前提的。造成的后果是,資本始終被分散束縛在小塊農地上,無法集中與轉化到工商業中來。[11]這也是中國在經濟條件上無法發展出資本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構成了對韋伯“中國命題”的有益補充。[12]
二、小農經濟培育出一個強大的文官集團,他們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政府官僚,與皇權既對抗又合作。從文化上講,文官集團以官方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為核心認同,其理想生活是讓佃農耕種自家土地,自己收租,以便有時間做學問,過一種上流階層的文士生活。這是韋伯所說的與現世采取調適主義的儒教倫理的擔綱者,儒家經典教育的目標是“君子不器”,而非培養技術或行政專家。
三、小農經濟也造就了整合廣土眾民為一體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國家。只有具備強大的國家能力,才能把分散的自然村落與人口聚合起來,以對抗游牧族群的侵襲,并建設大規模的灌溉工程。秦漢之后的農業經濟,的確是以大規模治水為特色。西方漢學家由此衍生出一種盛行的論調,認為中國大一統官僚制帝國的形成,應主要歸因于中國農業社會的大規模治水工程,最經典的命題莫過于魏特夫的“治水工程論”。然而,近年來一些新的研究質疑了魏特夫的理論,他們發現王權與大規模水利系統的發展之間并沒有魏特夫所說的相關性。[13]正如趙鼎新指出,戰國后期強大的官僚制國家的發展與當時的戰爭及變法運動密切相關,并非所謂“治水農業”的產物。[14]
其實,魏特夫的“治水工程”理論是由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引申而來的。馬克思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存在于俄國與印度的農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由于公社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個體依賴于公社,公社內部自給自足,從而造成了封閉性、孤立性與增長的停滯,成為支撐專制統治的基礎。又由于公社不存在私人企業的“自愿的聯合”,土地依賴于中央集權政府自上而下的大規模灌溉工程,而這種工程只有靠無限王權組織民眾徭役才能完成。魏特夫把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偷換為“治水社會”的概念,極為武斷地推論,正是東方中央集權政府的治水動員(徭役)造成了不自由與奴役,東方民族因而成為“奴性民族”,東方的“強國家”被貶低為“東方專制主義”。[15]須知,強大的國家能力并不等同于專制,古代中國政體也并非如亞里士多德所設想的君主奴役臣民的主奴關系——這是他對波斯帝國的想象。
事實上,馬克思、魏特夫據以判斷“東方專制”的兩大基礎—— 治水與農村公社,只是俄國與印度的情況,并不能完全說明中國的事實。
事實上,馬克思、魏特夫據以判斷“東方專制”的兩大基礎——治水與農村公社,只是俄國與印度的情況,并不能完全說明中國的事實。因為在中國,除了北方黃河流域的國家治水之外,也有著南方稻作區域豐富的自愿聯合的基層治水體系。[16]而且,中國精耕細作的小農經營也不能被涵蓋進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農村早就超越村社制,田產地契的正式確認意味著土地不僅被私有化,家庭的財產權也得到了保障,以家庭經營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得以形成。恰恰是土地歸家庭私有與經營,激發了中國社會的活力與動力;基層治水與家庭經營,也創造了燦爛的農耕文明。無怪乎馬克思驚嘆,面對英國的入侵,印度并沒有激烈抵抗,而中國人民卻迸發出空前的保家衛國的熱情——這是因為小農經濟造成了中國人強烈的鄉土意識。
總之,漢代精耕農業對中國文明產生了三個影響。第一,使中國建立以文治為取向的大一統官僚制帝國(區別于西方近代擴張式資本主義帝國);第二,使中國社會階層均平化,即便存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也不會造成主奴關系與嚴重的階級分化;第三,使中國成為“鄉土中國”,正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守土有責”,以親緣關系凝聚族群的方式也更為穩固,不像羅馬國家那樣蛻變為利益團體的結合,從而使中國社會內部保持強大的凝聚力。
馬克思驚嘆,面對英國的入侵,印度并沒有激烈抵抗, 而中國人民卻迸發出空前的保家衛國的熱情—— 這是因為小農經濟造成了中國人強烈的鄉土意識。
“旋渦模式”與中國歷史性的形成
中國在漢代確立起農業文明的形態與發展方向,奠定了古代中國文明的底色。若進一步追問,為何中國能從中原的華夏共同體不斷吸納融合周邊的多樣族群與文化,最終形成一個有著強大凝聚力的“文化中國”?為何中國能避免宗教、族群紛爭所導致的分裂,在歷史時空中連續地存在?歷史學家往往將其歸因于儒家的價值理念,如春秋公羊學以文化制度而非血統種族判夷夏的夷夏觀。而趙汀陽的《惠此中國》講述了一個不同于“文化決定論”的歷史理性選擇的故事,講述了使歷史中國得以不斷生長的“旋渦模式”。

北京天壇的建筑形制深受傳統中國“天下”觀念的影響
中國之所以能維系連續的存在,并非僅僅出于對儒家思想的認同,[17]而是人們形成了對“中國”這個神性概念的精神信仰。不過,“中國精神”的首要規則是方法,而不是教義。[18]人們對中國觀念的認同,更多的是由于接受它所能帶來的實質利益。趙汀陽借用托馬斯·謝林博弈論的“聚點模式”(focal?point)來解釋中國共同歷史的形成,即必定存在某種難以拒絕的吸引力,導致中國成為四方萬民的共同選擇,這構成了中國歷史性的內在動力結構。
中國之所以能維系連續的存在,并非僅僅出于對儒家思想的認同,而是人們形成了對“中國”這個神性概念的精神信仰。不過,人們對中國觀念的認同,更多的是由于接受它所能帶來的實質利益。
中國文明的長存能力在于,它自身具有一種難以解構而自足的“存在的秩序”(the?order?of?being),形成了自足的歷史性。從博弈論視角來看,“旋渦模式”是歷史中國的生長方式,即四方族群不斷聚集于中原而逐鹿中原,結果形成大規模的族群融合。“眾多相關者抵擋不住旋渦的利益誘惑而前仆后繼地主動加入游戲成為中國之主的競爭者,隨著博弈旋渦的規模逐步擴大,向心力的力度也隨之增強,終于達到穩定而形成了一個由中國旋渦所定義的廣域中國。”[19]
歷代統治者逐鹿中原的動力,在于掌握了中原豐富的精神文化資源,就可以最大化地節省統治成本,達到最大化的統治利益。在中原具有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中,最重要的是文字,掌握了文字也就掌握了歷史的書寫權,就有了文化上大一統的可能。中原最早發明和掌握了文字,正如許倬云所說,“這一文字成就,使商人擁有管理大型政治共同體的工具,也使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時代文化的重要資源”。[20]周人之所以能夠接續商人成為當時中國的領主,也是因為他們繼承了商人擁有的文化資源。更重要的在于,“漢字起源于象形,而不是語音的記號,這意味著中原語音并不能獨占漢字,也就是說,漢字可以獨立于中原語音而成為普遍共享的精神載體”。[21]這種開放性與可共享性,決定了爭奪中原的各方勢力都可以非排他性地使用這項資源,進而向周邊不斷輻射與擴展文明的影響力。
趙汀陽總結,中原的精神世界除了文字之外,還體現在周代開創的天命觀與大一統觀念,兩者都是政治神學概念,以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的天命無私原則,成為政治合法性獲取的最低成本策略,也是最高收益策略,可以帶來滾雪球效應。
這樣,中原的精神權力和合法性資源就成為天下群雄爭奪的目標,“逐鹿中原”成為集體的理性選擇。換句話說,中原之所以成為中國的旋渦核心,并不是因為中原是中國地理上的中心而便于統治天下四方,也不是因為中原的新石器文明最發達,或者資源最豐富、氣候最適宜、交通最便利……而在于中原擁有一個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一個人人都可以加以占用而有助于獲得、保有和擴展政治權力的精神世界。中原的擴展因此不是由中心向外擴的西方帝國模式,而是周邊不斷地、自覺地卷入旋渦的爭奪之中,同時也決定了,“中國是一個不斷生長甚至無邊生長的概念,即一個不斷趨近天下尺度的中國概念”[22]。
當四方不同的族群被卷入旋渦中,如何化解因文化、信仰與生活方式差異造成的激烈沖突,形成穩定的文明秩序呢?答案就在于天下秩序的“無外”原則。“無外”意味著沒有任何外部性,沒有自我與他者的區分意識,沒有敵我對立的斗爭意識。這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體系,沒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人”。

漢字的象形性使其可以獨立于中原語音而成為普遍共享的精神載體
天下秩序的“無外”原則意味著沒有任何外部性,沒有自我與他者的區分意識,沒有敵我對立的斗爭意識。這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體系,沒有一神教的排他性。
因此,中國之所以能維持長久存在、歷經變化而不被解構,不是因為文化個性,而在于它有一種“通過自身的變化而把外部性轉化為可以借力的力量”[23]。中國不斷地在變,從商人變成周人,從周人變成華夏族,從華夏經過秦漢的大一統整合變成“秦人”“漢人”,就像滾雪球一樣將周邊的族群與文化不斷卷入、融合進原來的華夏共同體,生長壯大為一個核心明確、邊緣模糊、可以無邊生長的“文化中國”。在趙汀陽看來,這種能力來源于中國“以變而在”的存在論。[24]西方人的存在論是,存在(being)就是存在(being),而中國人的存在論是,存在(being)就是生長、生成(becoming)。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來看,變在的存在論來自中國的農耕生產實踐。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主題是由早期中國的農耕生活所塑造的。中國思想演化的始發點是生生、生長(生長和扎根),即“生生”的問題,這必然與農耕生活有關。因為農耕之事,生長唯大,人們播下種子指望谷物生長,因而澆水施肥、改良土壤、精心栽培、深耕細作。中國人理解的存在之道,就是生長之道(“日新”),進一步延伸,最后落實為道德、政治、歷史、美學之道。可以說,中國文明的起源、特性與方法論,都能從農耕生活(尤其是農作物生長栽培的實踐)中得到解釋。
經歷如此巨大的變化,中國還是中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中國之以何種方式生長,正在于不變的“以變而在”的中國方法論。正如趙汀陽最后講述的希臘故事“忒休斯之船”,當這條船所有的破舊木板都被置換成新的木板后,這條木船看上去還是原來的那條木船。這是因為,中國文明的存在秩序或歷史性已經確定,正如質料因一直在變,而形式因卻沒有改變一樣。
結語
中國在漢代走向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深刻影響了中國文明的形態與發展方向。透過早期中國的農耕生活實踐,古人又為“中國”的不斷生長提煉了豐富的精神文化資源,中原因此成為一個“旋渦”,將周邊多族群、多文化卷入旋渦的博弈游戲中,歷史中國得以逐鹿中原的旋渦模式不斷生長擴大。
文化決定論以儒家公羊學的夷夏觀、天下觀等價值理念,來解釋中國的擴大,[25]而趙汀陽以逐鹿中原的利益機制,解釋背后的歷史理性選擇,也就闡明了中國大一統能夠成功的實質。后者不同于文化決定論的地方在于,博弈游戲的參與者對于“中國”的追求不是源于儒家道德教義的教導,而在于掌握“中國”這些精神資源所能獲得的最大統治利益,中國的不斷生長與擴大正是博弈游戲的結果。“中國”的原理不是一套道德教義,而是獨特的“以變而在”的存在論。
“ 中國” 的原理不是一套道德教義,而是獨特的“以變而在”的存在論。
當今的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依然在變革之中。中國人仍在頑強地堅持著因革損益、化古為今的變通之道,取法中西,繼往開來,與時俱進,不斷維新。
作者單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
(責任編輯:郭錦澤)
注釋:
[1]?潘維:《如何建設政治學的中國學派》,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
[2]?如李澤厚解釋中國人重視“中庸”“變通”的思想,就來自生產生活實踐中人對“度”的把握(如“無過”與“不及”)。這種方法從歷史經驗中建立理性最大化、功效最大化的方案,形成固定的方法論。
[3]?[18]?[19]?[21]?[22]?[23]?[24]?趙汀陽:《惠此中國》,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頁;第144頁;第43頁;第47頁;第50頁;第143頁;第138頁。
[4]?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139頁。
[5]?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頁。
[6]?[7]?[8]?[9]?許倬云:《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程農、張鳴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第8頁;第147頁;第28頁。
[10]?[11]?[13]?許倬云:《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鷺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頁;第33~34頁;第130頁。
[12]?在韋伯看來,中國缺乏新教倫理的入世禁欲主義、缺乏自治城市與獨立的行會組織,以及公共行政、法律、企業經營等沒有實現理性化。
[14]?趙鼎新:《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根源》,載《文化縱橫》2009年第6期。
[15]?涂成林:《治水社會與東方專制主義的互動邏輯》,載《哲學研究》2013年第3期。
[16]?徐勇:《從中國事實看“東方專制論”的限度》,載《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4期。
[17]?如趙鼎新認為,儒學為中華帝國提供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和認同感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古代帝國控制能力的不足。趙鼎新:《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根源》,載《文化縱橫》2009年第6期。
[20]?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頁。
[25]?“中國之地理擴展,并非如西方帝國主義憑武力來向外征服,而是一種自然的趨向于文化的凝聚與統一。”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