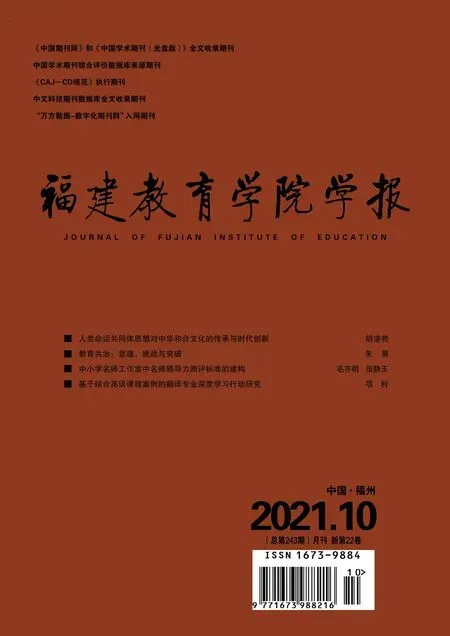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中華和合文化的傳承與時代創新
胡凌艷
(黎明職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跨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全球性理念,旨在追求全人類的共同發展,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堅持世界各國在主權平等、對話協商的基礎上合作共贏,實現人類社會的共建共治共享。近年來學術界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述掀起研究熱潮,學者們從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內在關聯、中華傳統文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路徑的影響等角度深入分析,并認為:“中國倡導并遵循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既顯示了當代中國的理念與‘和文化’理念的一脈相承性,又具有與當代世界和平發展的現實所需要的適應性。”[1]本文在此基礎上梳理和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重要論述對傳統和合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出場的時代訴求
當今世界的發展面對著一系列難題和挑戰,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狹隘社群利益交往實踐異化導致全球“正義”日漸式微。面對“人類社會向何處去?”“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中國共產黨的解決方案是以新發展理念構建全新的“多元一體”格局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世界的繁榮發展。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全球治理赤字的積極回應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科學地預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擴大世界交往和全球市場,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趨利性卻造成世界各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下的發展斷裂與失衡。當前,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諸如氣候變暖、能源短缺、環境污染、新冠疫情、恐怖主義、難民潮等難題,單憑他們自身的力量是難以有效解決的,而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奉行“資本至上”的原則,更不可能與發展中國家真正攜手合作解決問題。為了維護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西方發達國家甚至不惜犧牲發展中國家乃至全球利益,譬如當他們認為國際組織或協定(經貿、政治、軍事、生態等領域)的相關規則不利于自己時,就會強硬地要求改變規則甚至威脅退出,從而逼迫組織中的發展中國家做出利益的妥協和退讓。美國特朗普執政期間就以“美國優先”為由先后退出包括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伊朗核協議等多個國際組織和協定。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制度缺陷和局限性使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都不可能在全球性危機中獨善其身。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勢在必行,只有從全球治理的角度制定系統性規劃和方案,完善國家間合作機制,搭建國際一體化治理平臺,優化有效治理體系,共同遵守規則,才能協調矛盾和利益沖突,合力化解世界性危機,提升全球治理效能。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新發展理念的呈現與踐行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戰略性引領作用。
1.創新: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旨在超越西方傳統治理道路,以創新重塑全球治理的核心價值、道路理論、制度體系,推進新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立。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于將其作為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創新路徑,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協調: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主張“人—自然—社會—國家—世界”是一個系統整體,不能割裂這五者的內在聯系。很多全球性問題的爆發正是由于內部各種復雜因素縱橫交錯而導致的,因此全球性難題勢必需要人、自然、社會、國家、世界等多種主體的協調與合作來共同解決。3.綠色: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擔負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解決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要堅持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和諧并進,“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助推人類與自然的共存共榮。4.開放:在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反全球化浪潮不斷涌現的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以開放的心態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全球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聯動發展,促進世界共同繁榮。5.共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懷指向是實現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即世界各國人民能夠平等地共享發展的權利、機會和成果,實現全球范圍的共建共治共享。實踐證明,五大新發展理念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理論引領和路徑導向。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彰顯大國擔當的中國方案
中國共產黨堅守馬克思主義胸懷天下的情懷,關注人類前途命運,自覺承擔起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責任與使命,構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在推動中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和助推其他國家的發展,力求在和諧包容、多元共贏中最大限度地維護人類共同利益。這與西方發達國家弱肉強食、大國霸凌的傳統發展模式有著天壤之別。例如,“一帶一路”作為國家級頂層合作倡議,“使中國和亞非歐各國乃至整個世界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更好地實現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發展”。[2]目前,中國已與171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205 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據統計,“截至2020 年一季度,中國已規劃或在建‘一帶一路’項目共計3164 個,總金額達4 萬億美元。”[3]“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正是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行動的生動寫照,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情懷,以“中國方案”彰顯大國的責任擔當,推進中國夢與世界夢在共同命運中交相輝映。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和合文化致思方式的傳承
通常一種思想的產生是時代發展的產物,但從理論淵源來看其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從本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中汲取了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來源于以和合文化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是當代人對中華傳統和合文化中“天下大同”古老觀念的現代闡釋。“和合”的價值旨歸是實現萬物的和諧發展。倡導人與宇宙整體統一、自然萬物多樣差異、人與人和善友愛的致思方式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一)人與宇宙的整體統一
中國古代思想家在追溯世界本源時,主張“和實生物”的整體觀。老子認為世界是由陰陽二氣相互作用而成,當陰陽二氣能夠達到“和”的狀態,就能實現“道”。“道”是世間萬物的起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德經·第四十二章》),即世界是由“道”產生的一切包括天、地、人、物構成的完整的有機整體。宋代張載進一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論斷,認為“一物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正蒙·大易》)在張載看來,天、地、人都只是宇宙這個完整系統中的一部分,它們各負其責、彼此作用、相互影響,協調并共同推動宇宙這一有機整體的運行。明代王陽明則主張要將這種認知世界的整體思維方式拓展到統治者治國平天下的日常管理中,“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總之,和合文化要求從整體觀出發把宇宙萬物作為一個基于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普遍聯系的統一體。這種東方式整體思維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文明,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整體主義的方法論指導。世界是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很多全球性難題已不是單依靠某一個國家的力量或者只著力于某一領域的行動就能解決的,而是涉及經濟、政治、安全、文化、生態、社會等諸多領域和方面,這就要求我們要用整體主義的思維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強世界各國的多維立體性合作,共同應對挑戰。
(二)自然萬物的多樣差異
古代先賢們基于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觀察與探索來闡釋“和合”中自然萬物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易經》強調“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的一切變化有自身的規律,世間萬物人鳥獸蟲魚草木等均須受自然規律的支配,依照自身的習性來生長,這勢必會使世界因為差異而呈現紛繁多樣。和合文化并不認同事物的絕對一致和毫無差別,“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萬物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完全相同的事物終將走向偏執和單調,只有存在差異和沖突的事物在彼此的關聯與斗爭中才能實現對立統一,發展出新的事物,使世界生生不息。和合的實質是消除矛盾雙方的對立,達到和諧的狀態。對于任何和合體而言,首先要客觀地承認其內部不同事物間存在的差異,雖然這種差異必然導致矛盾雙方的對立和斗爭,但是“和合”旨在通過矛盾雙方對立的轉化達到最佳組合,最終有利于事物的發展。自然萬物的多樣差異是社會進步的前提和源動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應借鑒和合文化對自然萬物差異性和多樣性的承認,認識到世界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情況存在著巨大差異,不能一味地要求套用和追隨某一種發展模式或道路,只有允許不同國家根據自身國情探索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才能共同促進世界的發展繁榮,真正實現人類的命運與共,永續發展。
(三)人與人的和善友愛
如前所述,和合文化承認人或事物間是存在差異性的,那么,如何化解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沖突呢?和合文化主張“優先追求相互兼容最大化和相互傷害最小化的邏輯預期”[4],即采用“和”的思維以仁愛、寬容的原則與人為善并推己及人。譬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正蒙·中正》)古代思想家還將人與人之間的和善友愛原則拓展到國家統治和管理當中。孔子在回答顏淵何為“仁”時,強調要“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左傳·隱公六年》提出與鄰邦交往時要“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這說明,和合文化中“仁愛”不僅被納為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更是處理人與社會關系的價值追求和實踐指向。這種通過和善友愛來實現“和”的思維方式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當前,以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特征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不斷加劇,國際社會的分裂和矛盾沖突,實踐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試圖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矛盾是行不通的,反而造成無數平民的傷亡和苦難。只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推行和善友愛的交往方式,國家間不分大小、強弱,相互尊重與溝通,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平等協商,攜手合作,才能化解沖突和危機,構筑安全、穩定、發展、繁榮的新世界格局。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和合文化的守正創新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繼承了中華文明的血脈,傳承和弘揚了博大精深的和合文化精髓,使古老的和合基因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但是,和合文化畢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建筑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和合”的核心理念滲透著濃厚的封建專制主義色彩,具有歷史局限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繼承傳統和合文化豐厚精神底蘊的同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認識、分析世界,實現了對中華和合文化的創新性發展和超越。
(一)國際觀:從“協和萬邦”到“對話協商”
和合文化認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世界萬物的和諧共生是自然規律運行的結果,追求和諧是社會安定、國家繁榮的前提條件和必然要求,因此和合文化崇尚講信修睦、與鄰為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不是恃強凌弱、主動挑釁,更反對使用武力,其實質就是以“和合”的方式來化解沖突,協調各民族、各地區、各國間的矛盾。《尚書·堯典》中更是對如何實現國家間的“和”給出了明確的回答——“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即主張在“人”“家族”“社會”“國家”的層層關系遞進中通過仁德來實現和睦相處,從而建構以“中原帝國”為核心的網狀政治統治秩序。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摒棄將“和合”純粹地作為維護封建帝王專制統治途徑的基礎上對和合文化中的“協和萬邦”思想進行時代創新,提出要“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5]。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強調要在國家間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和平對話、多邊協商來解決國際沖突和爭端,消弭戰亂和矛盾,就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所強調:“協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應該成為現代國際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導以對話解爭端、以協商化分歧。”[6]盡管協商不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唯一途徑,但通過國家間的多邊協商化解隔閡、增強互信、擴大合作已是全球治理的必然趨勢。只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實現國家間的共商共量,才能帶來更好的共建和共享,最大限度守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二)治理觀:從“天下為公”到“共建共享”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是大同社會的鮮明標識,因此被歷代思想家所推崇。《禮記·禮運》曾有這樣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作為一種政治統治思想,“天下為公”強調“公利”優先于“私利”,社會整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因此,立君為公、行政尚公,即君王制度的設立和君主的日常統治出發點并非維護君主個人的私利,而是要以公心治天下,因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呂氏春秋·貴公》)“公”成為衡量君主賢明與否的重要標準。“天下為公”理念在和合文化乃至儒家思想中備受推崇,成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文化認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提供了理論借鑒。
但是,封建社會中孕育出的“天下為公”逃不出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宿命,君王的天下為公終歸是為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這恰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有著本質的區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追求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它所倡導的“天下為公”治理是立足于全世界的范圍,面向全人類,即超越了階級、民族和國家的局限,體現的是“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天下情懷和全球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在《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講話中強調:“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7]傳承于和合文化“天下為公”理念而建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摒棄了個體國家的“私”,從全人類“公”的角度出發,攜手各國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世界治理格局,努力“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
(三)發展觀:從“義以生利”到“合作共贏”
實現和合共生前提是處理好義利關系。“義”是社會統治所需的倫理規范和道德原則,“利”是人們生活中的物質利益,兩者都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當義利關系和諧時,政通人和社會發展;當義利關系不協調時,國家容易陷于混亂。和合文化主張要把“義”與道德相掛鉤,并作為人們認知和行動的重要評判標準。“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意思就是,只有在遵循“義”的前提下才去保障“利”的實現。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義和利是截然對立的零和博弈關系,恰恰相反,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左傳·成公·成公二年》中認為“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即道義的實行能給予百姓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使其安居樂業,最終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表明,利是通過義的價值導向和行動規范得以實現的,只有義以生利才能和合共生。
應該承認,諸如孔子的“以義制利觀”、墨子的“尚利貴義觀”等古代義利觀念對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定起著積極作用,但是,不管是“義”的價值內涵還是“利”的目標動機都是小國寡民下自然經濟的產物,從社會制度上無法超越封建主義,從地域輻射上無法拓展到全球范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蘊含的義利觀則不然,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倡導國際主義,強調通過國家間的平等合作來實現全人類的普遍繁榮,這是對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傳統義利觀的超越和時代創新。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反對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做法,主張西方發達國家不能僅考慮本國利益,采取單邊主義行動,而是應該從全球正義的角度出發,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給予更多的幫助和支持,搭建并不斷擴大同所有國家在經貿、安全、生態、反恐等諸多領域的合作平臺,共享發展成果,真正實現共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我們要注重利,更要注重義。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8]“一帶一路”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中關于“合作共贏”發展觀的成功實踐。
(四)交往觀:從“和而不同”到“交流互鑒”
回溯歷史,中華民族曾經歷三次民族大融合的礪煉,作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斷的華夏文明是各民族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晶,無論是“絲綢之路興起,中華文化西進,西方文化東漸,中華民族對于不同文明發展的成果始終都以‘和’之精神面對、接受、包容、借鑒,這是中華文明千年不衰的立身之道和倫理傳承。”[9]和合文化所推崇的“和而不同”一方面強調對人或事物要有足夠的包容:“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以大度兼容,則萬物兼濟”;另一方面強調求同存異、共存共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羹之美,在于合異”,即允許彼此間存在差異,不崇尚以武力尋求統一,而是通過相互協商實現合作。
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發展都有獨特性,由此形成的文明也各具形態,并沒有統一的模式和版本,基于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繼承古代“和而不同”理念的同時對其進行了現代話語的創新性發展,倡導尊重不同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世界上沒有哪一種文明可以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或優越于其他文明,任何對其他文明的偏見和歧視都可能成為世界沖突和矛盾的根源。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要鼓勵“促進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交流對話,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10]。唯此才能使國家間“不沖突、不對抗、不結盟”,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五)生態觀:從“天人合一”到“綠色低碳”
中國歷來重視探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二章》中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則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雖然諸子百家對世界的起源存在認知的差異,但是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卻有基本的共識,即人與自然萬物是同根同源的,天、地、人、物是息息相關、相互作用的一體,自然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基礎和支撐,因此人是不可能游離于自然而單獨存在的。漢代董仲舒認為“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春秋繁露·卷十三》)正是基于對自然與人為一體的判斷,傳統和合文化強調人要尊重自然規律,順勢而為,“天人交相勝”。譬如,孟子在《寡人之于國也》中提倡:“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顯然,古代的天人合一重視人與自然的內在聯系,主張根據四季時節的變化來從事生產,遵循自然規律來安排勞作,保障人們的基本生存,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提供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綠色情懷與理論依據。當然,古代的天人合一是自然經濟的產物,囿于生產技術和科學水平的落后,人在與自然的“和合”中只能被動地順應與屈服于自然,而非能動地把握規律、改造自然。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汲取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精髓,強調人要發揮作為實踐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尋求永續發展之路”[11]。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既反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的傳統工業化模式,也不認同單純地保護自然,維持人與自然表面的和諧,而是呼吁不同國家和民族要消除隔閡與矛盾,共同立足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12]。構筑起真正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美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