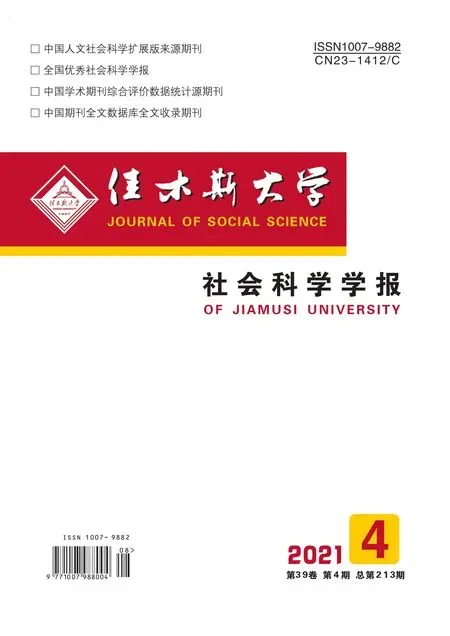蕭紅小說《小城三月》的空白書寫*
李韋函,徐曉杰
(佳木斯大學 人文學院,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空白”這一概念最早由德國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W·伊瑟爾提出。W·伊瑟爾認為,所謂“空白”就是指“文學文本中未被寫出的部分,它們存在于文本中已經寫出的部分向讀者暗示或提示的語言和情節結構中。”[1]207空白的存在,使讀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獲得了展示其價值意義的空間;同時,讀者也獲得了作品意義完成者的身份地位。由此,空白是一個積極的、引導閱讀得以順利進行的建構性力量,讀者在閱讀整合的圖式結構中完成其審美想象對文本的建構。W·伊瑟爾“空白理論”的問世沖擊了文學研究的傳統思維模式,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把讀者提到了文學研究的中心地位。作為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W·伊瑟爾始終按現象學的思路,把閱讀過程作為文本與讀者的關系來掌握和描述,認為文學作品是文本與讀者的結合。我們運用W·伊瑟爾的“空白理論”重新解讀蕭紅的《小城三月》時,這部作品作為審美對象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就動態地被建構了。
一、情節空白 盡顯風流
在W·伊瑟爾的“空白理論”中,空白出現在文本的各個層次,具有多種表現形式。蕭紅在《小城三月》中對情節的設置布滿了“未定點”和“空白”,這就有待于讀者在閱讀中對“未定點”加以確定和對“空白”加以補充。《小城三月》開篇即言明“我有一個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戀愛了”,這給讀者帶來的暗示是:作品在講述翠姨跟堂哥的戀愛史。然而文本沒有順應讀者原有的期待,反之將二人的戀愛過程作為空白和模糊點加以隱藏,巧妙制造陌生感,符合兩個人戀愛的朦朧性與內心遮蔽性,進而,在形式上和意蘊上對讀者進行了邀約。讀者帶著最初由文本引導形成的期待視野進入文本,卻在閱讀過程中受到阻礙。這時,一旦讀者在文本激發的作用下發揮出填補空白的主動性與再創造的能力,就得以根據文本提供的線索充分再現未言部分,將被中斷的故事情節還原。在此過程中產生的新的審美快感與審美經驗則是文本為不同時期的不同讀者提前準備好的禮物。
作者往往運用其最擅長的內聚焦敘事來設置情節的空白。《小城三月》就以孩童的非全知視角來描述翠姨與堂哥間或明或暗的簡短交集。這些寥寥的交集建構起審美對象的圖示化框架和召喚結構,情節之間的未定點則構成情節空白,引發讀者聯想與想象。比如作品寫到:“不過有一天晚飯之后,翠姨和哥哥都沒有了……我想一定是翠姨在屋里……我跑進去一看,不單是翠姨,還有哥哥陪著她。看見了我,翠姨就趕快地站起來說:‘我們去玩吧。’哥哥也說:‘我們下棋去,下棋去。’他們出來陪我來玩棋,這次哥哥總是輸,從前是他回回贏我。我覺得奇怪,但是心里高興極了……不久寒假終了,我就回到哈爾濱的學校念書去了。可是哥哥沒有同來……以后家里的事情,我就不大知道了……我走了以后,翠姨還住在我家里。”[2]35-36文本通過敘述者的介入完成情節上的跳躍,即“我”撞到翠姨與堂哥的會面,導致會面被中斷。又以敘述者的離開為故事情節留下空白,即“我”回哈爾濱的學校念書,留下翠姨與堂哥在家里,他們兩人到底說了什么、做了什么,讀者無法知曉。可見,情節上的中斷或“空白”恰恰是“一種尋求缺失的連接的無言邀請”[3]71。
文本舍棄對愛情橋段的全部精彩描述,利用敘述者的非全知視角的局限故意將二人的你來我往隱藏起來,僅提供讀者一些含糊的線索,將創作故事情節的權柄交由讀者。這樣做產生的效果是最大限度地激發欣賞者的審美快感,把文本轉化為讀者的經驗和新的期待視野。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參與文本審美對象和意義生成的再創造過程,于是作品中最為精妙絕倫的描述正是每一位讀者腦海中關于愛情模樣的美好向往的匯集,而所謂的“不著一字,盡顯風流”也正是蕭紅試圖通過“空白”來展現愛情的風情萬種。
二、形象空白 入木三分
魯迅曾站在以作品為中心的立場批評蕭紅的作品中“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4]2,暗示作品中人物形象略顯蒼白。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文學研究的思維范式開始從“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轉向“讀者中心”。時代不同,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也會不同,文學批評也應摒除先見,重新審視蕭紅對人物形象的刻畫。
蕭紅在《小城三月》中對人物形象的刻畫同樣布滿了“未定點”和“空白”。這在翠姨形象的描寫中得到體現。翠姨住在外祖父的后院,與外祖父家隔著一道帶著縫隙的板墻。每每外祖母招呼翠姨過來,有時翠姨會先從板墻縫中和“我”打了招呼,再回屋裝飾一番,“才從街上繞了個圈來到她母親的家里”[2]5。這里借空間設置的敘事手法給人物形象留有空白,人物的刻畫也達到了出神入化。翠姨是“我”外祖母的親生女兒,平日里卻沒有和“我”一樣住在前院,后院與前院之間的板墻雖然薄薄的不似水泥墻般厚重,甚至帶著裂縫,但它卻是翠姨內心的壁壘。這道板墻時刻提醒著她,使她舉止不能出格,于是她“走起路來沉靜而且漂亮,講起話來清楚的帶著一種平靜的感情”。同時,板墻還是翠姨同新的文化、新的思想之間的隔膜。翠姨對所有讀過書的人都會油然產生敬佩的情感,對讀書的態度是渴望又好奇。一道板墻,透著裂縫,讓翠姨看得到彼岸世界卻不能直接伸手觸到。對她而言,與堂哥和“我”這樣的人相比,從蒙昧世界到知識世界的路途總是遙遠的,可能需要繞過一條大街,有時比一條街還遠。
文本沒有直接描寫翠姨對所愛的執著,而是生動地勾畫了她為買絨繩鞋所付出的努力。這份執著不僅僅是一雙鞋,還是覺醒的自我、萌發的愛情和新的文化。翠姨雖早早地就愛上了絨繩鞋,卻沒有在它剛流行起來時就果斷買下來,這意味著翠姨行動的滯后性,同時還象征著翠姨意識覺醒的滯后、愛情追求的滯后、知識獲取的滯后以及命運抗爭的滯后。數次跑遍商場卻仍然買不到絨繩鞋,翠姨意味深長的那句“我的命,不會好的”深刻地象征著翠姨身上帶有“林黛玉”一樣的弱質性格和發自本能的悲劇命運感。
由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將這些圖式化的框架聯系起來,一個豐富立體的翠姨人物形象就被建構出來:溫雅、弱質性格、執著、有覺醒意識、有悲劇命運感、有求知欲,這些互相矛盾的因素決定了翠姨覺醒后的所有抗爭都未能轉化為向外的積極力量。最后,被逼得無路可走的生命只得以軟弱無奈的姿態寂滅。
“空白”不僅不是文學本身的缺點,而恰恰是它的特點與優點,它為讀者留下足夠的空間和余地,這不代表作家可以隨意地制造空白。具有審美價值的空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一定要經過作家獨具匠心的設計,有規律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樣才能營造高級的美感,激發讀者對美的感知,給閱讀過程帶來新的審美體驗。蕭紅塑造人物形象的空白設置恰恰是一種以讀者為中心的超越時代局限的創新意識。形象空白是最具美學價值并且經得住漫長歷史考驗的刻畫手法之一。
三、意蘊空白 大言無聲
《小城三月》篇幅雖小卻含有豐富的意蘊。這意蘊同樣需要填補“空白”來揭示。《小城》開頭和結尾都在描繪時值三月的小城的景象,都使用了草、花、樹的意象,只是情感色彩發生了變化。開頭更多地渲染春天的熱鬧,“三月的原野已經綠了……河冰發了……天氣突然的熱起來……小城里被楊花給裝滿了,在榆樹還沒變黃之前,大街小巷到處飛著……春來了,人人像久久等待著一個大暴動,今天夜里就要舉行,人人帶著犯罪的心情,想參加到解放的嘗試……春吹到每個人的心坎,帶著呼喚,帶著蠱惑……”[2]1;結尾則突出春天的短暫:“翠姨墳頭的草籽已經發芽了……這時城里的街巷,又裝滿了春天……但是這為期甚短……接著楊花飛起來了,榆錢灑滿了一地。在我的家鄉那里,春天是快的……春天的命運就是這么短……她們白天黑夜地忙著,不久春裝換起來了,只是不見載著翠姨的馬車來。”[2]45-46
看似還是一樣的季節,卻不再是同一個春天了。具體有何不同,文本沒有給出自己的闡釋,只提供讀者以情感變化的暗示和未言的空白,這體現蕭紅巧妙的筆法和文本更深層的意蘊。空白是吸引與激發讀者想象來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種動力因素,如果文本為讀者提供了全部的故事,沒給他留下想象空間,那么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厭煩。 我們帶著閱讀動力去層層剖析《小城三月》的多重意蘊,在審美欣賞過程中就會體悟到人類同自然一樣循環往復的宿命。小說結尾的意象比開頭多了一座翠姨的墳墓,也就是說翠姨終沒抵過寒冷的嚴冬,一場抗爭的結果是生命的終結與消寂。
《小城三月》是蕭紅在病榻上的絕筆之作,她在生命的最后時光中,發出了靈魂之問:翠姨是從蒙昧中覺醒的向往新文化的人,新思想到底能不能賦予她生命的意義,使她獲得自由的人生。也許答案被藏匿在文本蘊含的深刻意蘊之中,也許其實文本也并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一旦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提出了疑問,文學作品的無聲吶喊就被具體化了,讀者自身的哲學思考和審美體悟也隨之產生。意蘊層空白的精妙之處就在于此,它體現著大言無聲的哲學思考與審美體悟。
蕭紅在《小城三月》中正是通過對情節、形象以及意蘊的空白書寫,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將文本編織的圖景片段銜接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多層次的圖景結構,文本的意義也就在閱讀主體中被建構了。
W·伊瑟爾的“空白理論”與海明威的冰山原則不謀而合,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提出:“一座移動著的冰山顯得高貴,是由它那浮出水面的八分之一決定的。”[5]263就像深海處的冰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溫度的變化而改變體積,文本的“空白”也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它會因歷史、政治、文化的因素不同,各時期讀者也會根據自己的經驗世界和邏輯思維不斷地參與文本的建構,多元、多維、多重的文本闡釋會為讀者的審美體驗帶來無窮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