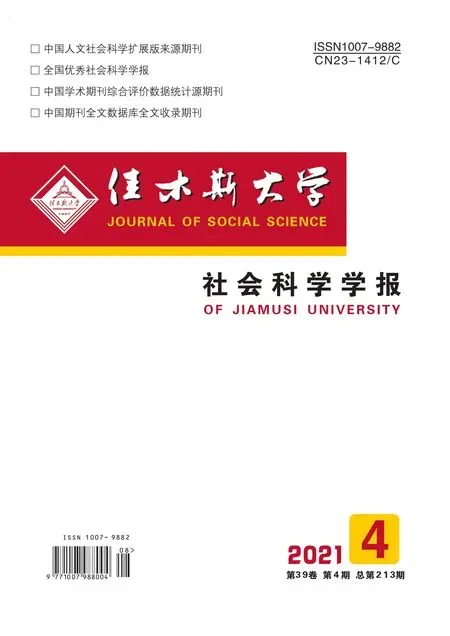中華書局版《史記》修訂本本紀部分標點獻疑五則*
王書才
(鄭州大學 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中華書局版《史記》點校修訂本,汲取歷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特別是經過當代專家們的辛勤整理,斷句標點方面可謂已更臻于完善。但白璧難免有微瑕,筆者細讀之后,發(fā)現修訂本仍偶存疏漏之處,故不揣淺陋,例舉于下,以獻疑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例一,三家注所引“字書”是不是書名?
《五帝本紀》“縉云氏有不才子”,《正義》云:“字書云縉,赤繒也。”[1]44
《史記集解序》“至于采經摭傳”,《索隱》云:“案字書,摭,拾也,音之赤反。”[1]4036
對上述二句中“字書”二字,修訂本均未加書名。這顯然是認為“字書”只是對《說文解字》之類書籍的泛稱,不需加書名號。但是,其后既然有明確的引文,那么就需要考察一下“字書”是否指的是《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系部》云:“縉,帛赤色也。”[2]274又《說文解字·手部》:“拓,拾也,陳宋語,從手石聲。之石切。摭,拓或從‘庶’。”[2]255
顯然,此處三家注所引“字書”內容均與《說文解字》不同,則足見這里的所謂“字書”不是《說文解字》。
那么,唐前有沒有名目為“字書”的書籍呢?核《隋書·經籍志》,可以發(fā)現其中有兩種名為《字書》者,一為三卷本,一為十卷本,還有一種名為《古今字書》者,亦十卷[3]943。
可見,唐前果有書名為“字書”者,則《史記》三家注引“字書”云云,則應在“字書”二字上加書名號,才是妥當的。
例二,《五帝本紀》“春秋國語”是一書還是二書?
中華書局1982年版《史記·五帝本紀》云:“予觀《春秋》《國語》,其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索隱》云:“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fā)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4]46-47
可見舊版認為,無論是司馬遷還是司馬貞,均以《春秋》與《國語》為兩種書籍。對此,修訂者認為舊版理解有誤,認為“春秋國語”應當是一種書籍,遂將《索隱》語句改標為:“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但正文由于疏漏,仍舊是“予觀《春秋》、《國語》”[1]54,致使對正文與《索隱》的標點前后未能一致。但在修訂本主持人的相關論文中,已經明確認為正文里的“春秋國語”也只是一種書:“標點改作:‘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fā)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按:《索隱》所言‘春秋國語’,當指《國語》。《太史公自序》‘整齊百家雜語’《正義》:‘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國語》號‘春秋外傳’,故稱‘春秋國語’,又稱‘春秋外傳國語’。”[5]275
這里面出現了一個問題,也即此處“春秋國語”是否真的如修訂者所認為的那樣,一定是僅僅指《國語》一書?也即此處“春秋”二字,是否是指與《國語》并稱的另外一本書?比如孔子所著的《春秋》,或者左丘明所著的“春秋左氏傳”?
當然,聯系到下句所謂“其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則紀事極其簡潔的孔子《春秋》顯然應該排除在外。那么,這就要從兩個方面論證這里的“春秋”是否指《春秋左氏傳》。一是在《史記》行文中,司馬遷是否曾用“春秋”來稱呼《春秋左氏傳》;二是《春秋左氏傳》里面有無明顯的“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的內容?
如果司馬遷書中曾稱《春秋左氏傳》為“春秋”,同時,《春秋左氏傳》里面又有明顯的“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的內容,那么,就可以證明《史記》舊版的標點就是無誤的,而修訂本的改動不但多余而且錯誤。
先來核查第一方面,看看司馬遷行文中,“春秋”一詞有無指《春秋左氏傳》的用例。
《十二諸侯年表序》云:“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索隱》云:“言表見《春秋國語》,本為成學之人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焉。”[1]650
此處修訂本一仍舊版,將正文中的“春秋國語”視作兩種書,而對《索隱》則標點為一種書。
這種正文與注文標點的不一致,固然已是不妥。更關鍵的是,這里司馬遷所說的“春秋國語”肯定是《春秋左氏傳》和《國語》兩種書。因為西漢中期司馬遷所讀到的《國語》與傳到今天的《國語》內容基本無異,其書分國別記述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等8國君臣言論與行事,而偏重于記言,略于紀事。而《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則按每年前后順序,詳列周、魯、齊、晉、秦、楚、宋、衛(wèi)、陳、蔡、曹、鄭、燕、吳十四國自共和元年(前841)至周敬王崩之年(前477)各國發(fā)生的大事,對這些事件因果、參與人物、年月等等的記述,大多取自《春秋左氏傳》而非《國語》,且其表又終結于孔子去世后的第三年,亦即孔子在世時的最后一任周天子周敬王崩殂之年,亦取《春秋左氏傳》終結于孔子在世時的最后一位魯國國君魯哀公去世之年之意。
那么,既然《十二諸侯年表》所記事件、時間均取自《春秋左氏傳》,而不是《國語》所有記載的,此已足以證明《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表見《春秋》《國語》”中的“春秋”正是指的《春秋左氏傳》一書。
其實,《史記》中“春秋”除指孔子《春秋》、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外,還指《公羊傳》,如《宋世家》“《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索隱》云:“《春秋公羊》有此說,《左氏》則無譏焉。”[1]1971此為司馬遷將“春秋三傳”之《公羊傳》稱為“春秋”之例。而且西漢官方行文,亦往往以“春秋”來稱《春秋公羊傳》等“《春秋》三傳”。如《淮南衡山列傳》膠西王的一位臣下議論道:“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1]3759此引《春秋》二句出于《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6]341。又如《匈奴列傳》:“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1]3523此處指《公羊傳》莊公四年所謂“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6]218可見西漢時,《春秋經》與“三傳”,皆可被稱作“春秋”。
由上述文獻證據,足見《十二諸侯年表》正文將“春秋國語”標點作兩種書,是十分正確的,而修訂本標點《索隱》時將其混為一種書,則是有誤的。由此,亦可初步斷定修訂本將《五帝本紀》正文與《索隱》中的“春秋國語”標點為一種書是存在錯誤的可能的。
而現在只要證明《春秋左氏傳》含有顯著的“發(fā)明”《大戴禮記》書中《五帝德》《帝系姓》的內容,就可以判定舊版點校本《史記·五帝本紀》的標點并無失誤。所謂發(fā)明,就是補充、闡述、印證之義。
那么《左傳》中有無“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的內容呢?顯然是存在的。
《大戴禮記·五帝德》陳述堯之功業(yè),云“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行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7]713-714《左傳》文公十八年“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兇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螭魅”一節(jié)[8]580-583,則對《五帝德》敘事有明顯的補充作用。
而《五帝德》陳述大舜一生時,云“舜之少也,惡悴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7]718,但其薦舉“八元”“八愷”的事跡,《五帝德》與《國語》均無所載,而《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一節(jié)[8]577-580,則對此作了詳細的鋪敘。
從上述些內容,足可以證明司馬遷此處所謂“春秋國語”乃是指《春秋》與《國語》兩種書,而非一書之名。
所以,無論是《五帝本紀》正文“予觀《春秋》《國語》”與相關的《索隱》注文,還是《十二諸侯年表》正文“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與相關的《索隱》注文,都應統(tǒng)一地標點為二種書,而不是一種。當然像目前修訂本這樣,正文里標點為兩種,《索隱》里標點為一種,前后矛盾不一,更是不恰當的。
例三,《周本紀》“作分殷之器物”之“分殷之器物”是否應加書名號?
《周本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集解》鄭玄注:“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1]163-164
張文虎:“此句(按指‘作分殷之器物’)文不成義,疑本云‘分殷之器物,作《分器》。’《分器》《書》篇,《集解》引鄭注可證。”[9]41
依鄭玄注,張文虎說甚是。“著王之命及受物”,正解說“作《分器》”三字者。證明原文中有“作分器”一句,而今本《史記》既有脫文又有誤倒,而修訂本對此全未校勘。
再者,今所知《尚書》百篇的篇名,一般為二字,少數為三字、四字者,無五字之篇名。鄭玄注言其篇名為“分器”,司馬遷所錄《尚書》篇名,應當與同是漢代人的鄭玄等所言一致,可證《分殷之器物》并非《尚書》之篇名。張文虎認為此處正文存在倒文與脫文,是可信的。當依據張文虎說加以補正。
例四,《項羽本紀》“蕭何亦發(fā)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集解》引如淳注云:“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1]412。
此處標點有誤,應標點作:“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
顏師古對此注釋云:“傅,著也,言著名籍”[10]38,也即將其姓名、年齡、身體狀況等信息記錄在冊。
對于“疇官”,《漢語大詞典》解釋為“世代相傳的專業(yè)官員,特指太史之類的歷算官”[11]4663。
此說不夠完備。此處的疇官,當是指主管工、商、農各類戶籍記錄與保藏的地方官員。所謂“各從其父疇內學之”,也即《國語·齊語》所謂“四民者,勿使雜處”,“士之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12]219-222。疇,原義為田,此處為“類別”之義。
《史記·歷書》“故疇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淳注云:“家業(yè)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學。”[1]1504所加標點甚是,亦足證實《項羽本紀》對如淳注的標點是有失誤,應該糾正,使之切當,而且前后標點一致。
《漢書·高帝紀》顏師古引如淳此注文,標點作:“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10]37亦甚是。
例五,“律”字后如有明確引文,此“律”字,是否應當加書名號?
《史記》三家注所引漢代律書文句,其出處,或稱作“漢律”,或簡稱為“律”。修訂本對上述兩類名目中凡稱“漢律”的字樣,一共6處,均加了書名號,這當然是很正確的。
但對于其后有明確引文的“律”字,不加標點,則不見得恰當。
《呂太后本紀》“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集解》引蔡邕語云:“律曰‘敢盜乘輿服御鉤’”[1]521。“律曰”后有明確引文,此“律”字顯系書名,當加書名號而未加。
這種情況,尚有十余例,列舉如下。
《文帝紀》“余皆以給傳置”,《索隱》引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1]536
《蕭相國世家》“何乃給泗水卒史”《索隱》引如淳云:“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1]2446
《商君列傳》“匿奸者與降敵同罰。”《索隱》云:“案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1]2711
《張丞相列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集解》引如淳云:“律有蹶張士”[1]3251。
《魏其武安侯列傳》“劾系都司空”《正義》引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1]3451
《匈奴傳》“是時雁門尉史行徼。”《索隱》引如淳云:“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1]3511
《淮南王傳》“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集解》引如淳云:“有罪失官爵稱‘士五’者也。”[1]3742
《淮南王傳》“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集解》引如淳云:“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1]3756。
《汲黯傳》“擇丞史而任之”《集解》引如淳云:“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各一人。”[1]3774
《汲黯傳》“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集解》引應劭云:“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1]3778
《汲黯傳》“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集解》引如淳云:“律,真二千萬石俸月二萬。”[1]3779
《酷吏傳》“曰為死罪解脫”,《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1]3819
凡上述語句中的“律”字,其后均有具體的引文,皆指具體的漢律之書,均當添加書名號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