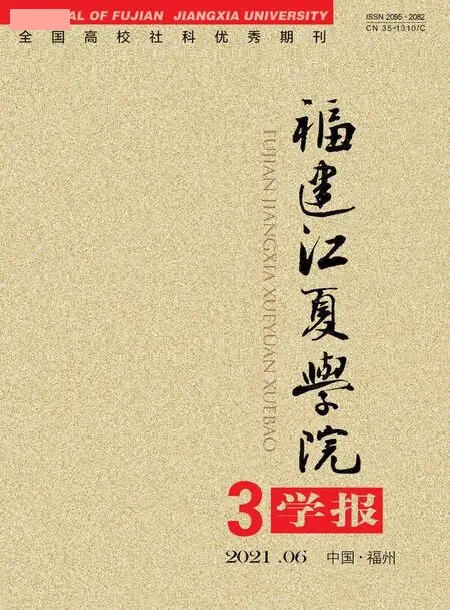王陽明論朱子、朱子學與“四學”
邱維平,徐 涓
(福建江夏學院設計與創意學院,福建福州,350108)
朱王異同是500年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主題,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的確,比較王陽明與朱子思想的關系,無論對認識兩位儒學巨擘的思想內涵,還是對理解宋明理學的諸多命題,都意義深遠。就現有的成果來看,大多數研究是從哲學觀念對比的角度來展開,而關于朱王二者思想繼承與變革問題的研究則并不多見。本文嘗試從王陽明對朱子本人、朱子學和訓詁、記誦、詞章和功利等“四學”①在王陽明文錄中,大量提及這四種學說,為了方便敘述,也為了與朱子學、王陽明學等相區別,筆者將它們統一命名為“四學”。的態度層面,來剖析朱王之間的思想淵源問題。筆者認為,王陽明對三者的態度并非是單純地尊崇或批判,而是較為復雜。具體地說,首先他對作為理學集大成者的朱子保持了足夠的敬意,但同時又對被神圣化的朱子之歷史地位作出了自己的判定;其次,他的思想雖然多有得益于朱子,但對于后者那“有不容于論辯者”[1]667的學說卻提出了諸多批評;最后,他對朱子及其后學展開的是學術層面的討論,但對“四學”卻給予了最嚴厲的批判,并由此展開對“學術之不明”根源的探究。顯然,厘清王陽明對朱子、朱子學和“四學”態度的不同層次,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王陽明在其心學思想創設過程中的多元心態,亦可使我們探尋在思想史的轉型過程中,革新者是如何完成從馮友蘭所謂的“照著講”到“接著講”乃至最終“自己講”的過程的。
一、尊朱又拒其于道統
王陽明出生時,朱子已歿近300年。在這段時期,朱子之學說從被禁到逐漸解禁乃至成為科舉考試和人心教化的權威教本,而他本人的地位也經歷了從生前的被打壓和歪曲到身后享祀孔廟、優入圣域的變化。因此,王陽明面對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朱子形象:作為理學巨擘的朱子和被尊為“孔孟后一人”[2]1114的朱圣人。前者集有宋以來周張二程思想之精華,博學多產,構建了龐大的理學體系,但同時其學又被陸象山屢屢視為“支離”,1200年后便已凝固在那些汗牛充棟的著述中,成為不可更改的歷史;后者則隨著前者的去世,被一步步地捧上圣壇,不可妄議②如成祖時代的饒州學者朱季友,就因批駁朱子學而被廷杖一百,書籍亦盡毀。,這其實是被意識形態化的朱子,其形象常為當權者所定義。總的來看,王陽明對前者表達了足夠的敬意,同時,又從其心學視角出發,對后者進行了去圣化的評價與定位。
(一)尊朱
明朝開國伊始就獨尊朱子之學,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自小就立志成圣的王陽明自然選擇的是朱子“格物致知”的成圣路徑:通過不斷格物窮理,以期豁然貫通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之境。錢德洪的年譜記載了王陽明18歲時初聞格物之學,“遂深契之”;而后在21歲時依朱子格物之訓而格竹,“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1]1002;27歲時又按晦庵之教,欲“循序致精”,但“沉郁既久,舊疾發作”[1]1003。這些經歷說明王陽明早年的確如島田虔次說的乃“何等狂熱的朱子之徒”[3]。正是在對朱子學說“照著講”的過程中,王陽明產生了困惑與懷疑,經千死百難,一步步地從“格物致知”說走向了“格心”說,從“知先行后”說走向了“知行合一”說,從而建立起迥異于朱子學的心學體系。這就不難理解他在1511年《答徐成之·二》中為什么會說朱子對自己有“罔極之恩”[1]668,通常來說,這是子女用來表達對父母養育之恩的感激之語,王陽明對此語的借用說明他視朱子為自己思想的重要來源。
除了感恩之情,王陽明對朱子的學識與貢獻亦不吝贊美之詞。例如,他雖然批評朱子只在“考索著述上用功”,但也稱贊其“精神氣魄大”“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實際上是對朱子“繼往圣,開來學”之貢獻的肯認。[4]42-43這在《答徐成之·二》中體現得尤為分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1]667-668因此,王陽明認為朱子與象山可稱得上“圣人之徒”。“圣人之徒”一語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5],意指能拒異端、傳圣人(主要指孔子)之道者。將朱子稱為“圣人之徒”,無疑是對朱子于儒學賡續所作貢獻的高度評價。
(二)去圣化
當然,王陽明雖感激和敬重朱子,卻不愿隨眾人圣化甚至神化后者。早在1241年,朱子就已經享祀孔廟,“取得與周張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統圣人的地位”。到1336年,他更是被封為齊國公,從此像孔子那樣“受到統治者的頂禮膜拜”。但王陽明似乎并未將朱子視為是不可批駁的“萬世圣人”[2]1114。比如,他認為朱陸爭論不休、相互譏諷,這說明二人皆“所養之未至”,用王陽明弟子周道通的話就是,朱子和象山涵養功夫仍未純熟,有“動氣之病”[4]124;而章太炎則認為二者意氣相爭,“更甚于《儒行》之‘可微辨而不可面數’矣”[6],故他們的氣象便不及“顏子、明道”。事實上,“朱子不及顏子、明道”論不僅體現在氣象方面,在道統論上更是如此。
道統論肇始于唐朝的韓愈,“至朱子而完成之”[7]287。在《大學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等文章中,朱子“以道心人心之十六字訣釋道統”,并詳述了道統的傳承過程:從“上古神圣”即伏羲堯舜禹等人“繼天立極”,經“成湯文武”等,再由夫子繼往開來,隨后顏子、曾子、子思續傳,“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直至千年后的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8]2-3。顯然朱子有暗示自己乃程氏兄弟后道統之繼任者之意,只是沒有明言,但他的弟子和后學“皆堅信不移”[7]287。如黃榦就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9]明初大儒薛瑄則把朱子直接比作孔子:“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后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后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后,有大功于道學者,朱子也。”[10]
然而,王陽明似乎并不認可朱子在道統中的地位。雖然遍檢王陽明之文錄也沒有找到“道統”二字,但在《別湛甘泉序》《象山文集序》和《朱子晚年定論序》等文章中,他都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道統論:圣人之學根由堯舜禹相授之十六字心法,孔顏曾孟相續而傳,孟子沒后則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后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1]202。顯然,在起源、孟子后的斷裂以及周程的接續等方面,王陽明采用了朱子的說法,區別在于王陽明突顯了顏子、明道的意義,而取消了小程子和朱子的位置。王陽明為何一再堅持“朱子不及顏子、明道”的看法?究其原因,在于他“夫圣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之論斷。這種盡心之學強調在“心地上用功”[4]80,“一于道心”[1]216而又能發之于父子兄弟朋友乃至天下萬物。這樣,能“不遷怒,不貳過”的顏子和主張“動靜一如”“無將迎無內外”的明道皆被認為是心學也就是圣人之學的傳承者,而“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4]80的子貢、側重于“道問學”的朱子則被視為偏離了圣人之學的正宗③現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亦判定朱子學說乃儒家正統之歧出,故稱之為“別子為宗”。。王陽明經常批評的周程之后“自后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之現象,矛頭所指的大概就是朱子及其后學。
綜上所述,王陽明肯定了朱子在學問層面繼往開來之貢獻,但在氣象和道統等方面,又視其在顏子、明道之下,從而將朱子“去圣化”,這顯然是受他重立大本而不重考索著述的心學立場影響所致。
二、承繼朱子學又超越朱子學
王陽明對朱子自身學說的態度,簡言之,就是承繼中超越,即從“照著講”漸漸走向“接著講”。承繼,是指王陽明大體是沿著朱子的命題構建起自己的學說的;超越,是指他通過否棄朱子的格物致知說等,形成了自己的良知學思想體系。作為“淵微”“精密”而又權威化的朱子學說的追隨者和背馳者,王陽明對朱子學的心理是復雜而又堅定的。
(一)視朱子學為“神明蓍龜”
在1520年回復羅欽順的一封信中,王陽明曾這樣說道:“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4]151正如許舜平所言:“后人動輒謂先生毀謗晦庵。”[4]70因此,往往不太相信王陽明這句話的真實性,認為這僅是他為了不與朱子之說產生大的沖突而使用的策略性說辭。應該說,這樣的理解對王陽明是不太公允的。
本文上一節曾提到,王陽明年輕時就精研朱子之學,尤其推崇其中的“格物致知說”。雖然后來他開辟出自己的思想天地,但正如唐君毅指出的:“王陽明之學,歸宗近陸象山,然實由朱子之學發展而出。”[11]他的問題意識和諸多重要命題,確實大都源自朱子而非一般人認為的陸象山:前者如龍場悟道前的關鍵難題“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1]1003,便是他對于朱子成圣功夫屢試屢挫而產生的結果;后者如“格物即格心說”則是從朱子的“格物致知說”曲折轉出的。此外“知行合一說”“《大學》古本論”等皆由批駁朱子的相應學說而推出。至于“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絲毫人欲之私”的至善論、良知乃獨知說等,則直接“借助于朱子”[4]275。難怪他會說:“若其余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4]70顯然,王陽明雖然自龍場后持“是陸非朱”[12]728之立場而終身未變,但一則他的思想乃孕育于朱子之學,如陳來認為“整個王陽明哲學的概念和結構都與《大學》有更為密切關聯,這也是王陽明受到宋學及朱子影響的表現之一”[13];二則他雖然在許多方面批判朱子所論,但正如上節提到的,他亦高度認可朱子“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之貢獻,因此,他才聲稱自己對朱子懷著“罔極之恩”。因此,“神明蓍龜”之譽即使有些策略性意味,亦不能否認其中包含的對朱子之學的真實情感。
(二)與朱子學的“毫厘千里之分”
《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第98條有這樣一句話:“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里之分。”[4]70王陽明之心學乃自朱子學轉出,或是后者的延續,但須強調的是,這種延續是批判與超越式的延續,“他思想發展的過程,無疑是對朱學的批判和擺脫朱子權威的過程”[14]880。也就是說,王陽明自從龍場悟道后,就慢慢接著朱子乃至孔孟周程,“講”自己之所“想”。觀其文錄,僅《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就直接“查引朱子共二十次……然凡所引,或全與朱子針針相對”[4]272。雖然論爭甚多,但王陽明認為自己與朱子的分歧主要是在“入門下手處”。朱王“入門下手處”有何差異?《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第6條:“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4]21第30條:“后儒不明格物之說,見圣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時講求得盡。”[4]30結合朱子的格物說④朱子的格物說:“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可知這里是批評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入門事。王陽明反對從知識入手,認為應從“修身”“立心”開始,應“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關于二人在這方面的不同,但衡今的解釋較為精到:“王陽明所云入門處,于周、程之主敬存誠近,與宗門之修禪定同。晦庵則以格物窮理為入門,道問學而尊德性,毫厘千里者以此。”[4]70意思是朱子認為須以“道問學”為“尊德性”的基礎與前提,強調知識對德性的不可或缺;王陽明則主張先立大本,“主敬存誠”為第一義,德性之養成不必經由知識的不斷累積而達至,而知識在德性的養成過程中自然會出顯。顯然,這是為學次第的不同,是成圣成賢之功夫階次的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形成為學次第差異的根源是二者對于“心”之認識的不一致。在朱子,心雖具眾理,但同時其又受氣稟所拘而“所發不盡合理”[15],就存有論而言,心與理斷無法為一,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16],這樣便不能不依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因此,自然主張“格物窮理,乃吾人入圣之階”。但王陽明則認為,“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主張直入本心,“不須外面添一分”[4]17,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4]221。
因對心與理之關系看法的根本差異,遂至“格物”與“格心”這一“入門下手處”的毫厘千里之別,二人其他種種不同,大都由此而來。在王陽明看來,像朱子那樣“先去窮格事物之理”,既“無著落處”也“始終是沒根源”,由物理(知識)而明性理(道德)的格物路徑,容易導致支離繁瑣而與身心無涉;在冊子、名物上用功,易使后學沉溺于訓詁記誦等學中而遠離圣學;知先行后使知行分離而導致知之不行;等等。此外,如對“道心”與“人心”及“未發之中”與“已發之和”等二分、著述繁多和《大學》新本分章補傳等現象的批評,亦是由“入門下手處”之異而延伸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入門下手處”的分別是從龍場開始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王陽明這一深刻體悟,標志著對朱子心與理二元論和格物說等的否棄,從此他與朱子漸離漸遠,與陸象山漸趨漸近,并且在批判前者和完善后者的過程中最終形成了致良知心學體系。
(三)“自幸”與“又喜”的真意
在《朱子晚年定論序》一文中,有一句歷來爭訟頗多的話:“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4]252這是王陽明1515年對自己作《朱子晚年定論》動機的概括,意思是朱子晚年已經自悔其先前之說,轉向了陸象山之心學,因此自己的學說其實無異于朱子之學,世人亦應“無疑于吾說,而圣學之明可冀矣”。五百年來,不少學者對王陽明這一說法進行了解讀。陳榮捷先生認為,王陽明在這里表明了欲與朱子之學“歸一”的想法[4]269。另外,一些當代學者則將其視為是“會通朱陸”“和會朱陸”思想之表達。束景南先生則否定了這些判斷,在新近出版的《王陽明大傳》一書中,他認為王陽明“一生都持批判否定朱學的立場,從來沒有想要‘合會朱陸’‘會通朱陸’”[12]736。他的證據是王陽明在寫《朱子晚年定論》的同時,還自定了《大學》古本,作了《格物說》,它們“都是嚴辨朱陸之學、批判朱學的,這才是王陽明的真實想法”[12]728。
王陽明與朱子學的分道揚鑣始于龍場悟道,自此后他的人生“都在與朱子的系統奮斗”[14]880,因此就學說而言,他的確未曾表現出與朱學會通的意圖。除了束先生所舉的《大學》古本和《格物說》外,《朱子晚年定論》及序言刊刻(1518年)后王陽明的思想發展軌跡亦是有力的證據:1519年的“良知之悟”,1526年和1527年的“王門四句教”和“王門八句教”的提出,1527年征思田前作的《大學問》等。這些標志著他已經完全“否棄了《朱子晚年定論》”,建立起了屬于自己的思想體系,因此非但未與朱學實現會通,反而進一步深化了與后者的差異。這樣看來,在《朱子晚年定論·序》中說的“自幸”與“又喜”應不是他內心的寫照,而是以調和之姿態緩解己說與官方朱學之間的緊張,“聊藉以解紛”[1]1030。
綜上可知,王陽明對朱子學說的態度也是充滿張力的。一方面,自18歲初聞格致之學到37歲龍場悟道的近20年的時間里,他循朱子之訓苦覓成圣之方,雖不得入,然亦知朱學于己之意義,故“蓋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另一方面,從21歲格竹致疾開始,他便對朱學有所懷疑,直至放逐黔地,勘破生死后“悟朱學之非,覺陸學之是”[12]433,從此在不斷與朱學的辯駁中逐漸完善、超越陸學,最終建立起自己的心學體系。他與朱學的漸離漸遠皆因其于艱難困苦中體悟到的良知之道,“不得已與之抵牾者,道固如是”[4]151。他堅信“致良知”方是儒學正道,心學方是孔門嫡傳,因此就王陽明本人來說,實際上是不存在和朱學會通、歸一之努力的,他的真正目標是要厘清朱子學中“不明”的地方,如對知識與德性的含混不清等,從而突顯心的意義與力量,回歸與彰顯自孔孟以來的主體性學說。“會通”與“歸一”,主要是后世一些學者如東林學派士人等試圖完成的工作。
三、批判“四學”又溯源于朱子學
(一)“先儒”“后儒”“世儒”的區別
在王陽明文錄中,經常可以看到“先儒”“后儒(后世之儒)”“世儒/世之儒者/世之學者”這樣的稱謂⑤僅《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中,“先儒”就出現了大約13次,“后世之儒/后儒”出現了大約17次,“世之儒者/世儒/世之學者”出現了大約10次。,若不加以甄別很容易混淆三者,模糊王陽明對三者態度的差異性,甚至給人以王陽明誹謗朱子的印象。因此,厘清三者的區別對于正確認識王陽明對朱子及其學說的態度是不無意義的。
三個稱謂中,“先儒”是有特定內涵的,往往指那些已經逝世的可以從祀孔廟的著名儒者。在孔廟中,主祀孔子,其他享祀的包括四個等級,即一等“四配”、二等“十二哲”、三等“先賢”和四等“先儒”。在1712年被作為唯一一個非孔子親傳弟子而提升為“十二哲”之前,朱子一直屬于“先儒”行列,所以王陽明說的“先儒”主要指的是朱子(有時也指二程)。“后儒”一般是在講述圣人之學后提到,比如《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第11條“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4]27,第52條則是在解釋完孟子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一語后提到“后世儒者”[4]53。因此,這個稱謂是包含朱子及其后學甚至“世儒”等在內的。“世儒”的意涵則稍微復雜。東漢的王充認為,“世儒”是些只會講解經書的儒生,“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圣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17],因此,不如那些著書立說的“文儒”。三國時的曹植則在《贈丁廙》一詩中寫道:“君子通大道,無愿為世儒。”“世儒”與“君子”相對,大概相當于“俗儒”。不過從王陽明有時用“世儒”,有時又用“世之儒者”來看,他指的“世儒”應是泛指當世的儒者,當然也有“俗儒”的意味。
王陽明在提到“先儒”時,基本上是與之論辯某個具體問題。如《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第111條是與弟子討論朱子“以學為效先覺之所為”之說法,第317條則是批評程頤和朱子“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的不合理之處。對“后儒”,王陽明批評他們或“不明圣學”[4]77,或沉溺于立言著述[4]27,或初學便要“講求得盡頭”[4]40,或“只得圣人下一截”[4]51,等等,總之是偏離了圣人精一、求放心之旨,支離繁瑣。顯然,矛頭有時亦是指向朱子的。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雖然王陽明和陸象山一樣都批評朱子“支離”,但在《紫陽書院集序》和《答徐成之第二書》中,他又認為是后世學者自身的原因導致支離瑣屑,朱子本非支離。在1522年的《與陸元靜》中,他更是指出:“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后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1]160這種矛盾現象,概因王陽明認為朱子雖“汲汲于訓解”,但其并非“玩物”,而是為了防止學者躐等而“失之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明,然后有以實之于誠正而無所繆”,意即朱子本人是“格致”與“誠正”、“涵養”與“進學”兼顧的,但后學則往往偏于一隅,皓首窮經,“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1]667。至于對“世儒”的態度,因其與“后儒”有重疊處,所以還是以批評其“舍心逐物”[4]73為主,但又經常把“世儒”和訓詁、記誦、詞章和功利之學等聯系在一起⑥可參看《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第143條,《王王陽明全集》中的《尊經閣記》和《別湛甘泉序》等文。,對于這“終身勞苦于身心,無分毫益”[4]51的“四學”,王陽明視之為徹底背離圣學的“異端”,認為它們甚至在楊墨老釋之下[1]195。
(二)對“四學”的嚴厲批判
應該說,朱子本身之學說肯定不在“四學”范疇內,事實上,正如溝口雄三所說的,作為“道德實踐之學”[18]的朱子學與訓詁注疏詞章之學是相對的。比如,在《大學章句序》中,朱子就認為:“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8]3概訓詁注疏之學乃漢學主流,以朱子學為代表的宋學則重在經文的義理闡發,故成了“對漢學的反動”(鄧廣銘);而記誦詞章又與科舉考試密切相關⑦王陽明在作于1525年的《萬松書院記》中指出:“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鶩于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參見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3頁。。島田虔次認為,宋代士大夫的內心深處大多“把科舉作為功利主義的象征”[3]77。可見,“四學”本身也是深為朱子所批判和拒斥的。然而,一方面,由于朱子學向外窮理的成圣路徑本身“還可旁通于詞章、考據”[19];另一方面,自元代開始其學說逐漸官學化,成為科舉考試依據的權威教材,因此如張元忭所言,朱子學雖大興,“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20]31。元朝的吳澄則認為,嘉定后朱門就已經慢慢墜入記誦詞章等俗學:“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后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20]343明初的胡居仁也發現,當時的朱子學人“已墮入訓詁注釋、詞章功利的歧途”[21]。可見,后來不少學者走到了朱子當年批判與否定的道路上,明顯背離了朱子學的本意。
對于“四學”,王陽明的批判甚烈。在1525年所作的4篇書院記中的3篇(《稽山書院尊經閣記》《重修山陰縣學記》和《萬松書院記》》)與《答顧東橋書》等中,都可看到相關文字。尤其是《答顧東橋書》,在被稱為“拔本塞源論”的結尾部分,王陽明悲憤地說道:“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子既沒,圣學晦而邪說橫……于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世之學者不再關注“復心體之同然”的圣學事業,紛紛借知識技能“濟其私而滿其欲”,天下幾成名利場,“功利之毒,淪浹于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但王陽明并未絕望,“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4]118可見,王陽明“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4]94而力倡良知圣學,直接的原因就是試圖克服“四學”等橫行造成的天下“學絕道喪”之危機。
(三)“明”學術與對朱子學的超越
從王陽明的表述來看,他并未將“四學”導致的危機之責任直接歸于朱子本人,但應注意的是,他不止一次地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于“學術之不明”。如寫于1526年的《寄鄒謙之·三》中就指出:“后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1]172即以為社會亂象只是表象,源頭在于“學術不明”。王陽明文錄中,表達“學術不明”之意的語句甚多⑧如《王陽明全集》第154頁“此學不明”,第153頁“道之不明”,第156頁“學之不明幾百年矣”,第172頁“皆由此學不明之故”,第186頁“此學不明于世久矣”,第194頁“學術不明”等。。大體上,它們包含兩方面意思:一是指圣學自周程后隱沒不彰。如寫于1527年的《答以乘憲副》開頭:“此學不明于世,久矣”[1]186,“此學”即指良知心學,依王陽明之道統論,心學即是圣人之學。二是指朱子學說存在的不足。如《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第134條所言:“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4]100這里指的正是上節論及的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入門下手處導致的“物外遺內,博而寡要”之弊病。其實,這兩層內涵是一體兩面的關系:正是朱子學本身有外求和繁瑣等弊病,加之后來的官學化,遂使圣學偏離“求盡吾心”的宗旨,長久湮晦而不顯,這才是世人紛紛踏入功利之途無法自拔的深層原因。“則今之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1]194因此,正如王陽明弟子黃綰所指出的,要改變“今日海內虛耗,大小俱弊”的局面,唯有“明學術而已”[22]。在王陽明,就是通過對朱子學中偏離圣學之部分展開持續批判,重新接續堯舜禹以來的求放心、致良知之道統,方為拯救天下的根本所在。
在《紫陽書院集序》的結尾,王陽明寫道:“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1]202“發明朱子未盡之意”可視為他“明學術”的主要內涵:朱子雖為理學集大成者,但其學并非如明初大儒薛瑄所說的“自考亭以后,斯道大明,無煩新著”[23],而是仍有罅漏,特別是他設定了一條經“道問學”而通往“尊德性”的成圣之路,將具有不同法則的二者視為同是一理,使學者常常溺于前者,導致后者落空。王陽明龍場之后,就開始劃清二者的界限,否定了“道問學”作為實現“尊德性”的前提,“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4]107,從而使圣學從支離繁瑣的桎梏中掙脫,回歸到孟子和象山那種直接簡易的路子。具體地說,他拒“事事物物上尋找定理”而主“心即理”,否“知先行后”而倡“知行合一”,駁所謂的“格致誠正”次第而熔于“致良知”之一爐,構建起自己直入本心、內外一如的心學體系。因此,雖然有論者認為“象山心學在‘大本大原處’為其確立了基礎,而象山心學的‘粗’‘沿襲之累’‘非純粹和平’等瑕疵則成為其構建‘精一心學’的學術動力”[24],但顯然王陽明心學產生的更重要的“學術動力”實來自朱子學。
四、結語
一代學術之興起常常是思想家因著個人與時代的雙重困惑,嘔心瀝血地去澄明學術不明之處的結果。在這過程中,面對權威化的現有思想與學術體系,新思想的表達者總是在繼承中尋求突破與超越,借用馮友蘭先生的說法,這種繼承與超越的關系常體現為從“照著講”到“接著講”乃至“自己講”的過程。
從王陽明對朱子、朱子學和“四學”的態度來看,他開始也是遵循朱子的方法去做“格物”功夫,這階段可謂是“照著講”時期。但通過自身求圣的體驗,他感受到心與理無法湊泊的苦悶,在顛沛造次中,他突破了朱子格物成圣之路徑,體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同時,面對功利化等學喪道絕的危機,他認識到根源在學術之不明,故須澄明朱子未盡之意,澄明學術的不明之處。這樣,他自然走向“接著講”的階段⑨張立文認為,馮友蘭所謂的“接著講”,“就是把原來不明確的概念明確起來,解釋清楚”。參見韓宵宵:《從“照著講”“接著講”到“自己講”“講自己”——訪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張立文》,《中國文藝評論》,2019年第3期,第123-134頁。。如他雖然和朱子一樣,始終圍繞《大學》展開思考與論述,但對包括“格物”在內的“八目”意涵皆提出了迥異于朱子的心學化理解;又如他承續朱子,重視對知行關系的探討,但他并不認同后者“知先行后”的觀點,而反復強調“知行合一”說;等等。由此他逐漸創制了自身的一套話語和思想體系,最終形成獨具特色的“良知說”,則完全是他“自己講”的學說了。回顧思想史的漫長發展過程,不難發現,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直至“自己講”,這大概是許多重要轉折時期(比如清末民初、20世紀80年代初期等)的新興思想家都曾有過的歷程,而思想史也正是經由一個個類似的過程完成了一次次突破與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