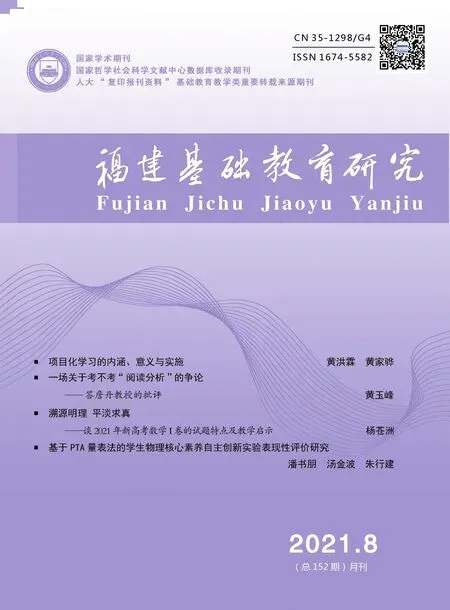一場關于考不考“閱讀分析”的爭論
——答詹丹教授的批評
黃玉峰
(復旦大學附屬中學,上海 200433)
2021 年7 月11 日,我在上海圖書館作了一個題為《致廣大而盡精微——我的真語文教學》的講座。講座從中華民國小學生的作文和對郁達夫的《故都的秋》談起。中華民國小學生的作文既有文采又有思想,我說,如今的博士生也未必寫得出。郁達夫的《故都的秋》,歷來經典的分析文章都說它是結構嚴謹,主題鮮明,而我說它只是為了“交稿”而玩弄技巧的“急就章”[1]并提出考試不應該“考閱讀分析”的建議。
我在微信朋友圈曬了這些觀點,引來了很多朋友的點贊,但也有朋友不贊同。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詹丹就批評我反對“閱讀分析”,說我連“不求甚解”與“不求解”都分不清。他在朋友圈說的原話是這樣的:
雖然我很尊敬一些名師獻身中學語文教育的熱情,但他們時有一些主張偏激、邏輯混亂的觀點,實在不敢茍同。比如,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的議論為支撐而要求廢除“閱讀分析”的老師,先就要考考他的閱讀能力:“不求甚解”和“不求解”有無區別?
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趙志偉看到了,憤憤不平,在朋友圈反駁詹丹:
去問問中學生,閱讀分析已導致了多少人文理不通,捫心自問,你們語文是這么學的嗎?
這種閱讀分析,恕我偏激,是一種從小學到中學的課堂公害。
誰不知道“不求甚解”與“不求解”不是一回事?
過了一個星期,詹丹又在朋友圈專門發文章《閱讀分析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評黃玉峰師和趙志偉兄的一種觀點》。文章前面還有一段說明:
本著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則,與黃老師和趙老師展開了一次簡短討論。因為沒多少空余時間,也因為趙老師的引言部分和黃老師和我,都關聯起來,所以主要就討論了這一段話,沒顧及趙老師文章的全部,或許有斷章取義之病。有一點需要說明下,我寫的文本解讀書,主要是給教師或者準備當教師的師范生看的,不是直接給中學生閱讀的,這點大家應該都清楚,如果以中學生特別是初中生的理解水平來衡量,判斷這些解讀要求為不切實際,可能是誤會了。雖然美術學院有位老師的孩子,在讀初中,說喜歡讀我的文本解讀,但這純粹是他的個人愛好,當然,也可能是他為要我的簽名故意這么說的。
于是有了我下面寫給詹丹的文字。
一
詹丹兄是個謙和的人,這是您給我總的印象——雖然我并不同意您某些觀點——不單是語文教學上的。
其實我們在語文教學上,并沒有什么分歧,是你誤會了我與志偉的意思。只是在“考”字上有不同意見。
相反,我覺得在課堂上必須講解,講得越生動越好。詹丹兄在文中說到有一個小朋友特別喜歡看你的閱讀分析書,我完全相信!因為你講得生動,講出了他沒有想到的東西。其他小朋友也有這個需求的。——問題是不能以您的分析去“考”他們!
我說我們在“閱讀分析”上并沒有分歧,是有根據的(說完全沒有分歧也不對,我與志偉都認為有些淺顯的文章,認為有意思的文章,就不必去“分析”)。
不妨把引起詹丹兄不滿的那段話再引一遍:
【黃玉峰】
如今的語文教學,都被考‘閱讀分析’‘標準化試題’搞壞了!語文教學亟需歸真返璞,從不考‘閱讀分析’開始!陶淵明說得好,‘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誠哉斯言,這才是真語文!
請注意,我說的是:“被考‘閱讀分析’‘標準化試題’搞壞了!”其中有個“考”字!確切地說是“被考‘閱讀分析’的‘標準化試題’搞壞了”!
我認為,又要考“閱讀分析”,又要標準化!必然搞壞語文教學!
我從來不反對在教學生一定要“閱讀分析”,否則要你教師上課干什么?教師上課就是要激發、點燃、喚醒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然而讓他自己去“學”,自己去“思”。
趙志偉老師上課喜歡一講到底,這個“講”,就是“閱讀分析”。我自己也常常一講到底,有時邊讀邊講,讀幾句,講幾句。把學生帶到我神往的境界!古人上課,也絕不會一味教孩子讀背,而不“分析”的。胡適母親多給教書先生錢,就是希望“先生”給她的孩子多講一點。講就是點撥,讓他開竅。
記得,我在幾天前答詹丹兄的微信中,說得很明白了,不知為什么詹丹兄還要說我反對“閱讀分析”!
不妨再貼我其中寫的一段:
我不是說不要分析,只是說不“考”分析!你的紅樓夢分析得很有味,我受益不淺,但我的紅樓夢和你不完全相同。你考我,我不及格;把我的作標準答案,也許你也不及格。上課可以也應該分析,好的老師的分析講解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啟發他們的思考,但如果一定要作為“標準”,那就索然寡味了!
而趙志偉也不是一概反對“閱讀分析”,他說:“這種閱讀分析,恕我偏激,是一種從小學到中學的課堂公害。”請特別注意“這種”這個限制詞!“這種”指的是那種蹩腳宣傳文章、說假話的文章、一看就明白的文章以及那種碎尸萬段、故作高深、故弄玄虛的分析。這樣的“閱讀分析”是不是該反對?
二
至于對陶淵明的話,我到現在還不明白我的理解錯在哪里?
詹丹兄說: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的議論為支撐而要求廢除“閱讀分析”的老師,先就要考考他的閱讀能力:“不求甚解”和“不求解”有無區別?(回應:我在哪里說過要“廢除”閱讀分析了?)
接著,詹丹兄又用了《辭海》對“不求甚解”的兩個注解(原意和引申義)來論證他的觀點:
一個是原義,指“讀書只領會要旨,不過于在字句上花功夫。”
玉峰請問:“不過于在字句上花功夫”,是不是“不要過度分析”的意思?
我們來讀一讀五柳先生的原話: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請注意這段話的關鍵詞是“好讀書”,首先是“好讀書”,好讀書,就是多讀書,讀很多書,因為好讀書,要讀得多,所以不在乎“求甚解”。
那么,什么叫“求甚解”。
查《說文解字》:甚,尤安樂也。——灝注:“甚,古今字。女部。‘樂也’。通作耽、湛。《衛風·氓》:‘無與士耽。’《小雅·常隸》:‘和樂且湛。’皆甚字之本義。從甘匹,會意,昵其匹耦也;甘亦聲”。
《漢典》:甚,會意。小篆字形,從甘,從匹。甘是快樂,匹,匹耦。沉溺于男女歡情。本義是異常安樂。
《漢典》:玄甚。——《老子》。注:“謂貪淫聲色。”
《列子·愚公移山》:甚矣,汝之不惠。
蘇軾《教戰守》: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周敦頤《愛蓮說》: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
林覺民《與妻書》:吾家后日當甚貧。
從以上詮釋看,“甚”有下列意思:極端,極其;非常,異常;過分等等。
再看《現代漢語詞典》:
基本釋義:(1)副詞。很;極。(2)超過;過分。常用組詞:甚至,甚囂塵上,不甚了了,不求甚解。
根據以上注釋,不求甚解的意思就是不求“過度解讀”,不求“唯一解釋”,不求“標準答案”。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在五柳先生的意思是:“我酷愛讀書,只希望讀很多書,讀書時只求了解個大概意思,不硬性求解,不鉆牛角尖,然而,當我有了心得,心領神會的時候,就高興得忘了吃飯。”這是陶淵明的讀書境界!
詹丹兄還說到《辭海》的另一個引申義“今多謂態度不認真,不求深入理解。”這既然是引申義,就不去談它了。
詹丹兄又引了龔斌的《陶淵明集校箋》,對“不求甚解”解釋為:
“謂讀書不過分執著于字句,以致穿鑿附會失其本旨。”[2]……但黃老師給出的解釋,卻與我們通常理解的不同。
不同在哪里?
我的意思不正是不要“穿鑿附會”“故弄玄虛”,乃至“過度分析”,“過于在字句上花功夫”嗎?詹丹兄怎么不理解呢?
君不見,如今語文教育的現狀,不正是“過于在字句上花功夫”嗎?
玉峰引陶公的話,說明不要“過度分析”,又錯在哪里?
怎么詹丹兄興起“先就要考考他的閱讀能力:‘不求甚解’和‘不求解’有無區別?”的念頭呢?
我說,陶公所說“不求甚解”,意思可能是“不要求得到徹底的肯定的唯一的理解”,陶公所說的“每有會意”,意思大概是“每當有了心得”有了啟發,便欣然忘食!
錯在哪里?
為避免極端,我還特地用了一個“可能”一個“大概”,我不敢那么自負,說自己已經完全領會了五柳先生的原意!
我說:不求甚解,是一種謙虛的謹慎的讀書態度,又錯在哪里?誰敢說,你什么都懂了,都“甚解”了!有什么錯?詹丹兄的很多文本解讀是極有價值的,但您敢說,您的解釋是絕對準確,唯一準確的嗎?
詹丹兄,我的意思陶公寫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諷刺那些什么都要求“確切解釋”,找“標準答案”的讀書風氣!一千六百年前的陶公的話似乎是針對今天的語文教學而說的。
何況考試與讀書又不一樣。在大學里,或者對中小學教師來說當然應該盡可能理解,理解得越深越好,但是千萬不要以為自己的理解一定是對的!這本質上是我在《“人”是怎么不見的》一文中批評的“教育專制主義”![3]
君子和而不同。詹丹兄是厚道之人,怎么就不能容許不同意見,而斥之為“不懂”呢?
三
多少年來,我們的語文教學,考“閱讀分析”,害得多少學生老師天天揣摩“上意”,為了迎合而失去了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失去了創造性,一個個成了“學奴”。玉峰不顧他人的嘲笑譏諷,乃至打壓,為之呼喊,希望我們的學生不要學得這么苦而又沒有收獲。請教詹丹兄我哪里說錯了?做錯了?
您不但是有話語權的人,而且在有話語權的人里面是有學問的人,我希望您對上面吶喊,救救語文,把“閱讀分析”從考卷里清除出去!
四
這里請允許我再貼幾篇支持我觀點的文字:一位是學生家長吳培慧,一位是復旦物理系的教授王培南,一位是原復旦大學出版社編輯夏德元,一位是福建省的資深老教師王立根,還有一位是百家講臺嘉賓、上海開放大學教授鮑鵬山。
【學生家長吳培慧】
寫得真好!從我家娃的情況來說,我一度懷疑這是不是和學校對語文老師的考核指標有關,而學校會給這樣的考核指標,可能來著與區里統考的題型,以及未來中考和高考要求。小學生階段每天教閱讀理解題,刷題,給解題思路,孩子對語文失去興趣,十歲的娃經過權衡利弊和我說:“反正我最后閱讀理解題無論怎么做,都和標準答案不一樣,不如我第一遍就隨便寫寫,到訂正的時候,聽了老師講解再寫,而且到訂正的時候,老師通過的標準也會松一點。這樣總用時最少。”做家長的也好難,既不合適在孩子然面前公然反對老師,也不適合要求孩子過度重視閱讀理解題目解題思路。只能家庭里用有限的親子時光鼓勵孩子對語文不要厭惡,孩子留給閱讀的時間真的是排除萬難擠出來的。另外,從寫作角度來說,我也發現了中外的教學差異,美國小學教學要求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著寫作,一上手就是非小說類寫作,從說服型的議論文開始,注重孩子思想的表達,他們認為,文學類的創作不要教,多閱讀,自然而然詞匯量會多和句子會更美,需要學習一點套路的只有功能性文章,更鼓勵孩子用語言去表達思想。而我們語文方面,小學階段基本上都是描寫文記敘文,帶一點點說明文,很少涉及議論文(四升五的小學生沒涉及議論文),只有教材里的“語文園地”(非主要課文)里口頭表達的練習要求。甚至有的老師在教寫作的過程中,要求一篇作文,一定要出現幾個比喻、幾個擬人、幾個排比,因為這樣可以拿高分。我也覺得當代的中國小學生頭腦絲毫不遜色,只是給他們自我表達的機會太少了,還要給程式性的閱讀理解和寫作預先留出時間,對大多家庭來說,課本以外的古詩文只能留給對“學有余力”的孩子。
【復旦物理系教授王培南】
我外孫正在讀小學,偶爾過問,發現現在的小學教學實在是難以理喻,語文和英語的許多題目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或答案,但是非得與老師的標準答案一致的才算對。數學也往往可以有不同的解法,但是也必須按老師的解法解題。這樣教出來的學生會好嗎?教育怎么到了現在這個地步,難以置信。可悲啊!
【原復旦大學出版社編輯夏德元】
語文教育要回歸常識,要敢于說真話,要承認文章天才,不要用一把尺要求每個學生……算了,放棄治療吧,不可能的
【原福建語文學會會長王立根】
舉雙手贊成,當年我高考只考一篇作文和一篇文言文翻譯。不是也出人才么?
【百家講壇專家鮑鵬山教授】
詹丹教授我素所敬仰,但中高考的閱讀分析我實在難以認同,理由有二:一是當年我在青海師大,每年主持高考閱卷,其中閱讀分析多數標準答案都在我們這些大學老師意料之外;二是本人文章曾經入選人教版高中語文教材以及諸多高考中考習題集和模擬試卷,其中閱讀理解題目,我自己不會做。
詹丹兄在朋友圈里,引用了很多語文“大咖”的話,以壯行色。這里不一一舉例分析了。我只是想引復旦陳引馳先生回復的一段話,他的這段話,把我的意思說得簡潔而明白,大概不至于在引起誤解吧!
(可見,我們對這么明白的話都會產生歧義,閱讀試題又怎么能用“標準答案”去考學生呢?考“閱讀分析”的危害難道還不明白嗎?)
【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
(你們)都是我尊重的老師。趙志偉老師多年不見,印象中人很溫和,下筆真是橫掃三軍。黃玉峰老師和詹丹兄那天的朋友圈發聲當時就看到了,在情感上我很傾向黃老師,其實好多年前就曾開玩笑地對時任上海市考試院院長的鄭方賢教授提過,不妨廢了現代文閱讀一類考題。當然也知道這辦不到,所以接著對鄭院長說:“知道這不可能,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嘛。”詹丹兄進行“文本解讀”持久不懈,集腋成裘,大著連連,我在出版社的學生問我要什么贈書,便要過兩種拜讀,此文亦可謂有理有節。
最后,要說我自己的看法,便是:教學中“閱讀分析”不能廢,考試之“閱讀理解”可以休!——標準答案之胡扯已到荒唐的地步,別的不敢說,如果拿來考中文系教授,至少過半得抽自己耳光。
五
蘇東坡有一首詩,道出讀書積累與學識、氣質的關系: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
而我們的教學,把大好時光,浪費在無聊的無益的無理的“分析”“創新”之中。
《光明日報》上有一位韓志成先生見了我的帖子,頗好奇地問我:“那你說考什么?”我回答:只考作文、文言翻譯、默寫……簡言之:
三個“多少”——讀了多少?記得多少?理解多少?
兩個“怎么樣?”——文章寫得怎么樣?字寫得怎么樣?
這是我2017 年給《文匯報》寫的文章,題為《我們的語文究竟該怎么考?》[4],供同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