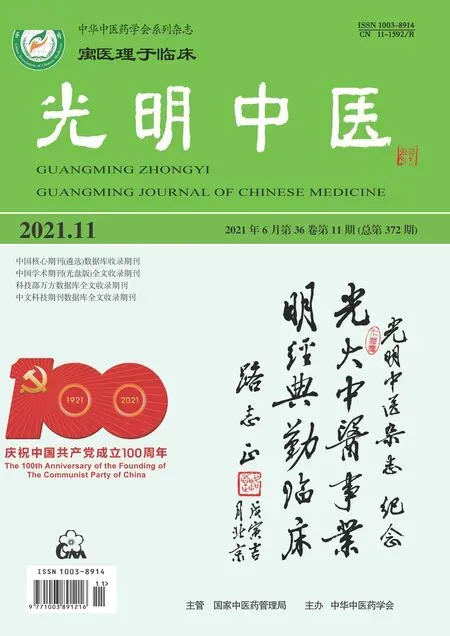癡呆病因病機古代文獻探源*
李偉峰 董新剛 王小璐 趙 云△
癡呆是以獲得性智能缺損為主要特征的一類慢性進行性疾病,其發病機制尚未明確。近年來,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和腦血管病發病率的急劇攀升,該病已成為中老年人的常見病、多發病。本病的治療和相關衍生費用高昂,對患者及其家屬生活質量影響極大。千百年來,中醫學在對癡呆的認識、治療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作為醫藥衛生領域的重要疾病和中西醫協同攻關的優勢病種[1],中醫藥防治本病的優勢和作用也將愈發凸顯。鑒于此,本文對癡呆的古代中醫文獻進行了初步的整理、校正、歸納和分析,以期為中醫藥防治本病提供文獻支撐和理論依據。
1 病名演變
中醫學對“癡呆”的稱謂百變多樣,多散在于紛雜的古籍之中。《左傳·成公十八年》曾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的記載,晉·杜預注曰:“不慧,蓋世所謂白癡”[2]。“不慧”“白癡”可視為本病名之初現,唐·孫思邈《華佗神醫秘傳·華佗治癡呆神方》則正式出現“癡呆”之名。雖然“癡呆”稱謂不盡相同,但相似稱謂在不同時期的文獻中均有記載,如《形色外診簡摩·百病虛實順逆》“血并于下,氣并于上,亂而善忘”稱“善忘”,張仲景謂“喜忘”,晉代《針灸甲乙經》、明代《針灸大成》“心性呆癡,悲泣不已”,有“呆癡”之說,王叔和《脈經·卷二》言“健忘”,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多忘候》云“多忘”,唐代《備急千金要方·卷十二》曰“好忘”,宋代王執中《針灸資生經》有“癡證”之稱等。與其他籠統記載不同,宋代《太平圣惠方》《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健忘證治》第一次對“健忘”進行了概念闡述[3,4],與此同時,在《景岳全書》首次將“癡呆”作為獨立病名提出之后[5],清代陳敬之《辨證錄》、葉桂《臨證指南醫案》也分別立了“呆病”和“神呆”篇章,可見,癡呆病名的演變過程,其實也是古代醫家對癡呆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
2 病因病機
2.1 年老髓空人至老年,腎氣日衰,精氣欲竭,腦髓失充,元神失養則易致癡呆發生,有關年齡與癡呆的發病關系,古代醫家早有記載,如:《靈樞·天年》“六十歲, 心氣始衰, 苦憂悲, 血氣懈惰, 故好臥, 八十歲, 肺氣衰, 魄離, 故言善誤矣”中的“善誤”,清代汪昂《本草備要·辛夷》“人之記性皆在腦中, 小兒善忘者, 腦未滿也, 老人健忘者, 腦漸空也”的“善忘”,《辨證錄·呆病門》有“人有老年而健忘者,近事多不記憶,雖人述其前事,猶若茫然,此真健忘之極也,人以為心血之涸,誰知腎水之竭乎”之論等,至清代,王清任《醫林改錯·腦髓說》則明確提出了“高年無記性者,腦髓漸空”的觀點,這與近代西方醫學漸進,醫家對腦的作用認識逐漸明晰有莫大關系。
2.2 肝失疏泄肝者,將軍之官,藏血舍魂,體陰而用陽,主疏泄而為氣機之樞;足厥陰肝經“循喉嚨之后,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故精神刺激、情志抑郁、臟腑功能失調或疾病日久均可致肝失疏泄、郁滯或上逆而現情志不暢、憂郁寡歡等癥,甚則上擾腦竅致精神失常。《靈樞·本神》有“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之論,《華佗神醫秘傳·華佗治癡呆神方》言:“此病患者,常抑郁不舒,有由憤怒而成者,有由羞恚而成者”[6]。明代《景岳全書·雜證謨》“癲狂癡呆”專論中提及“癡呆癥,凡平素無痰,而或以郁結,或以不遂,或以思慮,或以疑惑,或以驚恐而漸致癡呆”,認為癡呆與郁結、不遂、思慮、疑惑和驚恐等情志因素密切相關。另外,清代陳士鐸《辨證錄·卷之四》有“大約其始也,起于肝氣之郁……肝郁則木克土……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夫炭乃木之燼也,呆病成于郁,郁病必傷肝木……”[7]之載,葉天士亦有“神呆,得之于郁怒”之說,可見,肝失疏泄,氣機不暢之氣郁、氣滯、氣結乃引發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2.3 痰邪內擾痰邪可致多病,癡呆亦不例外,它既是本病的病理產物又是致病因素。明代胡慎柔《慎柔五書·卷一·師訓第一》曾載一因痰阻滯而致元神失用的醫案:“一痰癥, 曾有人病癡, 寸脈不起, 腳冷, 關脈沉洪,此陽氣為痰所閉……其病欲言而訥,但手指冷。此乃痰閉陽氣之病”[8]。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有“健忘,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雖然他們對真正癡呆的界定還十分模糊,但卻明確了痰與人的精神狀態密切相關。到了清代,醫家們對痰與癡呆關系已趨向明晰,不但有病因病機等理論闡述,還有治法治則、遣方用藥等具體措施,如陳士鐸的《辨證錄·呆病門》有“胃衰則土制水而痰不能消,于是痰積于胸中,盤踞于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治法宜開郁逐痰,健胃通氣,則心地光明,呆景盡散”也,《辨證奇聞·呆》有“痰不化,胃衰則土不制水,痰不消,于是痰積胸中,盤踞心外,使神明不清,呆成”,《石室秘錄·呆癥》亦有“呆病……此等癥雖有崇憑之,實亦胸腹之中無非痰氣,故治呆無奇法,治痰即治呆也”“痰勢最盛,呆氣最深”等,這不但從臨床癥狀、病因病機等方面對癡呆進行了深入剖析,還著重闡述了痰與癡呆的關系,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治療原則,創立了轉呆丹、洗心方、還神至圣湯等方劑。另外,清代另一醫家唐容川在《血證論》中也提到“有痰沉留于心包,沃塞心竅,以致精神恍惚凡事多不記憶者”,也同樣認為痰是“精神恍惚”“不記憶”的重要因素。
2.4 瘀血阻滯七情內傷、氣血虧虛、五臟虛損等致血瘀內停,經絡不暢,不能上充于腦、下養于心可發為癡呆。《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有“陽明證,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認為“善忘”與腸胃實、心肺虛和蓄血相關[9]。后世諸醫家如清代唐宗海在《血證論》中有“又凡心有瘀血,亦令健忘……凡失血家猝得健忘者,每有瘀血”“若血瘀于內,而善忘如狂”,林佩琴在《類證治裁·健忘論治》言:“惟因病善忘者,若血瘀于內而善忘如狂”。王清任在《醫林改錯》提到“凡有瘀血也,令人善忘”“癲狂癥,哭笑不休……乃氣血凝滯,腦氣與臟腑氣不接……”等,均提示了瘀血在善忘、健忘及癲狂癥的發病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2.5 心脾兩虛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多忘候》有“多忘者,心虛也。心主血脈而藏于神。若風邪乘于血氣,使陰陽不和,時相并隔,乍虛乍實,血氣相亂,致心神虛損而多忘”。《圣濟總錄·心臟門》“健忘之病, 本于心虛, 血氣衰少,精神昏憒, 故志動亂而多忘也”。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卷之一·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四》 “喜忘, 好忘前言往事也, 志傷則好忘。然心之所之謂志,志傷則心昏……”。可見,心志傷、心虛不足,心神虛損亦為“多忘”發病的重要因素。脾為后天之本, 氣血生化之源,氣血是人體生命、情志活動的物質基礎,氣血的正常運行有賴于心氣推動和脾氣運化統攝,心脾不足,氣血生化乏源、心血虧虛不能上榮腦竅,日久腦髓失養可致癡呆漸生,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健忘證治》提出“今脾受病,則意舍不清,心神不寧,使人健忘,盡心力思量不來者是也”。嚴用和《濟生方》云:“蓋脾主意與思,心亦主思,思慮過度,意舍不清,神宮不職,使人健忘”。元《丹溪心法》亦有“健忘者,乃思慮過度,病在心脾”之論,清代醫家沈金鰲《雜病源流犀燭》“健忘……或思慮過度而病在心脾,言語如癡而多忘”,李用粹《證治匯補》曾言:“憂思過度,損傷心胞,以致神舍不寧,遇事多忘。又思傷脾,神不歸脾,亦令轉盼遺忘”。治療方面,《重訂嚴氏濟生方》提出了“治之之法,當理心脾,使神意清寧,思則得之矣”,龔信、龔廷賢父子在《古今醫鑒·卷八》《壽世保元》有“然治之法,必先養其心血,理其脾土,凝神定智之劑以調理”的論述[10],由此,健脾當養心血、調脾土,佐以寧神定志乃是本病證的治療大法。
2.6 心腎不交心居上焦,屬火;腎居下焦,屬水,唐·孫思邈在《千金翼方·卷十二·養性》中指出,本病病位在心,因“腎精竭乏, 陽氣日衰”而致“心力漸退”發病,明代方隅《醫林繩墨》云:“大抵健忘之癥,固非一端而得,病之由皆本于心腎不交也”。清代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有“初起神呆遺尿,老人厥中顯然,數月來也不得寐,是陽氣不交于陰”。汪昂《醫方集解·補養之劑》亦有“人之精與志,皆藏于腎,腎精不足則志氣衰,不能上通于心,故迷惑善忘也”之說,由此,本病亦可由腎陰虧損,陰精不能上承,或心火偏亢,失于下降所致。治療上,以補益交通心腎為根本,達到心中之陽下降至腎以溫養腎陽,腎中之陰上升至心以涵養心陰的目的,羅國綱《羅氏會約醫鏡》提出了“治者,宜補腎而使之上交,養心而使之下降,則水火交濟,何健忘之有?”陳士鐸《辨證奇聞·呆》《辨證錄》有“治須大補心腎,使相離者相親,自相忘者相憶”“治法必須補心,而兼補腎,使腎水不干,自然上通于心而生液。”之論,林佩琴《類證治裁》謂:“故治健忘者,必交其心腎……自鮮遺忘之失”。程國彭《醫學心悟》也載有:“健忘之癥,大概由于心腎不交,法當補之”。鄭壽全在《醫法圓通·卷二·各癥辨認陰陽用藥法眼健忘》論述頗為詳細,他認為:“健忘一證……,此病法宜交通陰陽為主,再加以調養胎息之功,攝心于宥密之地,方用白通湯久服,或桂枝龍骨牡蠣散,三才,潛陽等湯,緩緩服至五六十劑,自然如常……”,對本病描述頗為詳細[11]。
2.7 中風致病歷代典籍對腦的作用、中風后“不識人”等癥狀記載頗多,如《靈樞·海論》“腦為髓之海……”,《素問·脈要精微論》“頭者,精明之府”以及《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邪入于腑, 即不識人; 邪入于臟, 舌即難言, 口吐涎”,《臨證指南醫案·中風》 “中風初起,神呆遺尿, 老年厥中顯然”“或風陽上僭, 痰火阻竅, 神識不清……”,吳鞠通《吳鞠通醫案·中風》“中風神呆不語,前能語時,自云頭暈,左肢麻,口大歪”等,但受社會發展及認知水平影響,眾醫家對腦在神明、記憶、思維的主導作用以及中風與癡呆間的內在關聯認識不清,始終處于模糊混沌狀態。明清后,西方醫學漸進,受現代解剖醫學影響,醫家們對腦在思維、認知和記憶中的作用才有了進一步深刻的認識和了解,逐漸明確了中風后腦絡阻滯,腦髓不能上充以濡養腦竅,致腦氣不通,神明不明亦可發為癡呆,誠如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12]所載:“人之腦髓空者……甚或突然昏厥, 知覺運動俱廢”“老年人精氣虛衰, 氣血不足, 以至陽化風動, 氣血上逆, 挾痰挾瘀, 直沖犯腦, 蒙蔽清竅, 元神失聰, 而靈機記憶皆失”等。
3 結語
古代有關“癡呆”的文獻紛繁龐雜,多散在諸典籍當中,其論述不盡相同,而今人以轉載居多,核對原文者寡,致以訛傳訛者眾。結合現代醫學對本病的認識,在對“癡呆”古代文獻探源、考校的基礎上,筆者對相關文獻脈絡進行梳理、歸納,總結并形成以下意見:古代“癡呆”之名雜而繁多,記載較為混亂;癡呆的發病與年齡、情志失暢、痰濁上擾和瘀血阻滯密切相關,與心、肝、脾、腎等臟腑功能失調緊密相連;癡呆的發病部位,明清以前認為在心居多,明清后多傾向于腦;古代文獻對癡呆的“癥”“證”描述較多,但對“記憶認知障礙”等現代醫學所明確的癡呆核心癥狀鮮有提及,提示古代醫家對本病的認識可能不夠全面和深入,但也印證了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內容應包含但不完全是癡呆疾病本身,可能涉及癲癇、愚鈍、健忘及神志異常等多種疾病,這就要求今人在對古代文獻進行研究時要多方參詳,去偽存真;與現代醫學相比,癡呆古文獻記載雖略顯單薄,但很多典籍卻清晰地記載了古代醫家對本病的辨證論治思路、治法治則和遣方用藥,這對我們深入探究癡呆發病的內在本質規律,尋找中醫藥防治本病的有效方法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參考和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