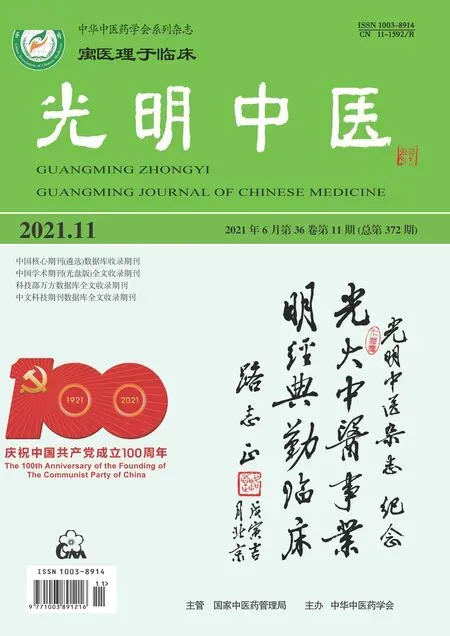《傷寒論》寒熱并用法舉隅
王藝霖 劉志龍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寒熱是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之一,是辨別疾病性質的2個綱領,寒證與熱證可以反映機體陰陽的偏盛與偏衰,“陽勝則熱,陰盛則寒”“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 因此,寒熱可作為一種分析疾病共性的辨證方法。然臨床證候往往復雜多變,所見之證并非單純為熱證或寒證,尤其是一些病程較長、病因復雜的疾病,常表現為寒熱錯雜。張仲景開創了中醫寒熱并用之先河,其運用寒熱并投之法,或增減藥量,或變化藥味,總以切合病情,分清主次為根本宗旨。《傷寒論》之寒熱并用方劑,是張仲景對方劑學的一大創舉。為探尋仲景治療寒熱錯雜證之辨證方法及藥物配伍原則,筆者將《傷寒論》中的寒熱并用法舉隅如下。
1 和解表里寒熱
1.1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傷寒論》262條:“傷寒瘀熱在里,身必黃。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主之”。 本方七分清利濕熱,三分表散外寒 。《傷寒溯源集》有言:“傷寒之郁熱與胃中之濕氣互結,濕蒸如淖淖中之淤泥,水土黏濘而不分……蓋以濕熱膠著,壅積于胃,故云瘀熱在里,必發黃也”。傷寒,是指外感風寒而表邪未盡,當見發熱、惡寒、無汗等癥。瘀熱,是指濕熱之邪郁于內,而見身黃、目黃、小便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既能發汗解表、利小便,又能清解在里之郁熱,故以此主之。尤在涇云:“此亦熱瘀而未實之證,瘀熱在里者,汗不得出,而熱瘀在里也”。方中麻黃辛溫,主入肺經,可散體表皮膚之寒氣,配伍辛溫之生姜、杏仁,辛溫宣發,解表散邪;赤小豆、連翹、梓白皮味苦性寒,清熱解毒利濕,可清解在里之濕熱;大棗、甘草甘溫悅脾,以為散濕驅邪之用;用潦水者,取其氣清薄偏浮,入體內善行肺經,不助水氣也[1]。
1.2 麻杏石甘湯《傷寒論》第63條曰:“發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第162條曰:“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此兩條文均論述了誤用汗法、下法后,邪熱內傳,邪熱壅肺而致喘的證治。表邪化熱入里壅肺,肺失肅降,導致肺氣宣降失常,故見氣喘之證;肺外合皮毛,邪熱壅滯于肺,熱迫津液外出,故有汗出之證。麻杏石甘湯為麻黃湯去桂枝加石膏而成,方中麻黃辛溫宣肺定喘,專疏肺郁,宣暢氣機;石膏辛甘寒,直清肺胃之里熱而生津,麻黃、石膏相伍,去麻黃之熱性而取其宣肺平喘之功效[2],又能透邪外出;杏仁宣肺降氣,助麻黃宣肺平喘之效;炙甘草調和諸藥。綜觀全方,寒熱并用,共奏解表清里,宣肺定喘之功效。
1.3 柴胡桂枝湯《傷寒論》146條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七日,發熱微惡寒,柴胡桂枝湯主之”。本條文論述了邪犯少陽,表證未解。本證系太陽表邪未解,而邪犯少陽,進而發展為太陽少陽并病。本方的證型特征為發熱微惡寒,發熱與惡寒并見,乃太陽表邪未解,“有一分惡寒,即有一分表邪”,此處的“微”字,說明惡寒程度較輕;且僅見肢體煩疼,而無周身疼痛,從以上癥狀來看,說明經過六七日,太陽表邪已轉為輕微之象。微嘔,比小柴胡湯證“喜嘔”程度輕,頻次少;心下支結,較胸脅苦滿而亦輕,說明外邪初犯少陽,樞機不利,但病邪不重。太陽、少陽證候俱輕,故取桂枝湯與小柴胡湯藥量各半,合劑而成,以桂枝湯調和營衛,解肌祛風,散太陽之表邪;以小柴胡湯清里透表,宣利樞機,以和解少陽半表半里之邪。
2 和解上下寒熱
2.1 黃連湯《傷寒論》173條曰:“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此條文中的“胸中”與“胃中”是指在體內相對的上下部位而言,“胸中有熱”,是指邪熱居于胃脘部,上至于胸膈,表現為嘔吐;“胃中有邪氣”,是指寒邪居于腹部,部位在脾,下至腸腑,表現為腹痛、下利。黃連湯證的病機為上熱下寒,胃中之熱邪上逆,而腹部寒凝氣滯,故用清上溫下之黃連湯以治之。方中以苦寒之黃連清胸中之熱;以辛溫之干姜散胃中之寒,二藥相合,清上溫下、平調寒熱,共為君藥;半夏和胃降逆止嘔,人參、大棗、甘草益胃和中,使脾胃升降之司得復,桂枝溫陽升清,既助干姜以散寒,又使體內上下之陽氣得以宣通,故而嘔吐止,腹痛除。本方的服法為“晝三夜二”,即白日服3次,夜間服2次,其意在少量而頻服,防止藥被嘔出,使藥性更為持久。
2.2 烏梅丸《傷寒論》338條曰:“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臟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藏寒,蛔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本條原文論述了蛔厥的主要癥狀與病機特點。其上熱緣于厥陰肝木相火之妄動所致,下寒乃由于太陰中土寒濕之不化。蛔厥的發生,一方面是因為體內素有蛔蟲,另一方面是因為肝熱而胃寒,故用烏梅丸以清上溫下,安蛔止痛。方中烏梅經醋泡制,增加其酸溫安蛔,澀腸止痢之功效,為君藥;蜀椒、細辛味辛溫性,辛可伏蛔,溫能祛寒;附片、干姜、桂枝溫臟祛寒;用苦寒之黃連、黃柏清熱瀉火;人參、當歸調養氣血,并配以米粉、白蜜,資其谷氣,驅邪不傷正,又可培土御木。綜觀全方,攻補兼施,寒溫同治,緩肝調中[3]。
3 和解寒熱錯雜
3.1 半夏瀉心湯《傷寒論》154條曰:“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半夏瀉心湯證的病機特點為脾胃虛弱,寒熱錯雜,升降不暢。痞證的成因為中焦寒熱阻滯,脾胃升降失司。 半夏瀉心湯證表現為虛、實、寒、熱以及氣機升降失常:其虛證乃系脾胃陽虛,可見便溏、泄瀉;實證表現為中焦氣機不暢,濕熱阻滯而有痞滿;其寒乃因脾胃陽虛而表現為脘腹冷痛;其熱乃因濕熱阻滯而出現舌苔黃膩,脈滑數等;清陽不升故見下利;濁陰不降故見嘔吐。治當和中降逆,平調寒熱,用半夏瀉心湯。方中半夏降逆止嘔,黃芩、黃連苦寒以泄中焦之熱,干姜、半夏辛溫以散脾胃之寒,用人參、大棗、甘草補脾助運,以復脾胃升降之司。諸藥相配,辛開苦降,平調寒熱,為治療痞證之良方。
3.2 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傷寒論》359條曰:“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本條論述的是上熱下寒相格拒的證治,其發病機理為平素本有脾胃虛寒,而又復用吐、下之法,使得脾胃更傷,而引起表邪內陷,入里化熱,因而出現寒熱格拒。從病位上看,脾與胃互為表里關系,最容易同時感受邪氣,在五行中,胃屬陽,脾屬陰,“陽道實,陰道虛”,故而胃多實熱證,脾多虛寒證,脾胃同病的時候常常表現為寒熱錯雜證候[4]。《絳雪園古方選注》云:“厥陰寒格吐逆者,陰格于內,拒陽于外而為吐,用芩、連大苦,泄去陽熱,而以干姜為向導,開通陰寒。但誤吐亡陽,誤下亡陰,中州之氣索然矣,故必以人參補中,俾胃陽得轉,并可助干姜之辛,沖開陰而吐止”。仲景立足于本病的病機,即胃中有熱,脾中有寒,寒熱錯雜,中土格拒,用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以治之。方中黃芩、黃連苦寒,可清泄胃熱;干姜性辛熱,可溫脾散寒;為防止芩、連之苦寒攻伐脾胃,故用人參扶脾補益中氣。全方寒溫并用,辛開苦降,調和脾胃。劉渡舟在《傷寒論十四講》中曾指出:半夏瀉心湯與干姜黃芩黃連湯皆能夠調和陰陽,使寒熱錯雜之邪得以和解,但半夏瀉心湯功在治痞;干姜黃芩黃連湯功在治嘔[5]。
3.3 柴胡桂枝干姜湯《傷寒論》147條曰:“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湯主之。” 熱郁在少陽,陽虛在內里,所以臨床既可見口苦、口干等熱象,又可見腸鳴、便溏或腹脹等太陰脾虛的寒象。“胸脅滿微結”提示患者經過汗、下之后,肺內陽氣下陷,郁積于肝內,陽氣與水飲相結,故有了“微結”的感覺。由于此證具有往來寒熱的特點,證屬少陽,故以小柴胡湯作為底方,方中柴胡、黃芩能夠和解少陽之邪,暢達樞機;瓜蔞根生津止渴;牡蠣軟堅散結;桂枝、干姜合用,能振奮中陽,溫化寒飲;炙甘草調和諸藥。因無嘔吐之胃氣上逆,故去小柴胡湯中半夏、生姜;由于體內有水飲結聚,故去人參、大棗,以防甘溫壅補。此方寒熱并用,既能清泄肝熱,又能溫散脾寒,可以和解少陽樞機,宣化水飲。 陳慎吾先生指出:“柴胡桂枝干姜湯治療少陽病而又兼見陰證機轉者,用之最恰。”劉渡舟認為本方在臨床上可以治療膽熱脾寒證。
綜上所述,《傷寒論》中寒熱同見之病機主要體現在外寒內熱、上熱下寒、寒熱錯雜3個方面,總以溫清并用為治療大法,調和陰陽,和解寒熱。各方證雖都有寒熱同見之特點,但在病因、病機、治法等方面各不相同,在藥物的配伍上也有所差異。通過《傷寒論》中寒熱并用法之研習,從中領悟張仲景遣方用藥的原則,學習中醫辨證論治之精髓。在臨床中,我們必須要抓住主癥,詳察病機,辨證論治,方能“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總言之,寒熱并用法是《傷寒論》中及其重要的內容,是張仲景對中醫辨證論治的一大創舉,具有很高的理論指導意義以及實踐應用價值,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